初二语文人教课标版上册第二单元8《台阶》备课资料父亲Word格式.docx
《初二语文人教课标版上册第二单元8《台阶》备课资料父亲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初二语文人教课标版上册第二单元8《台阶》备课资料父亲Word格式.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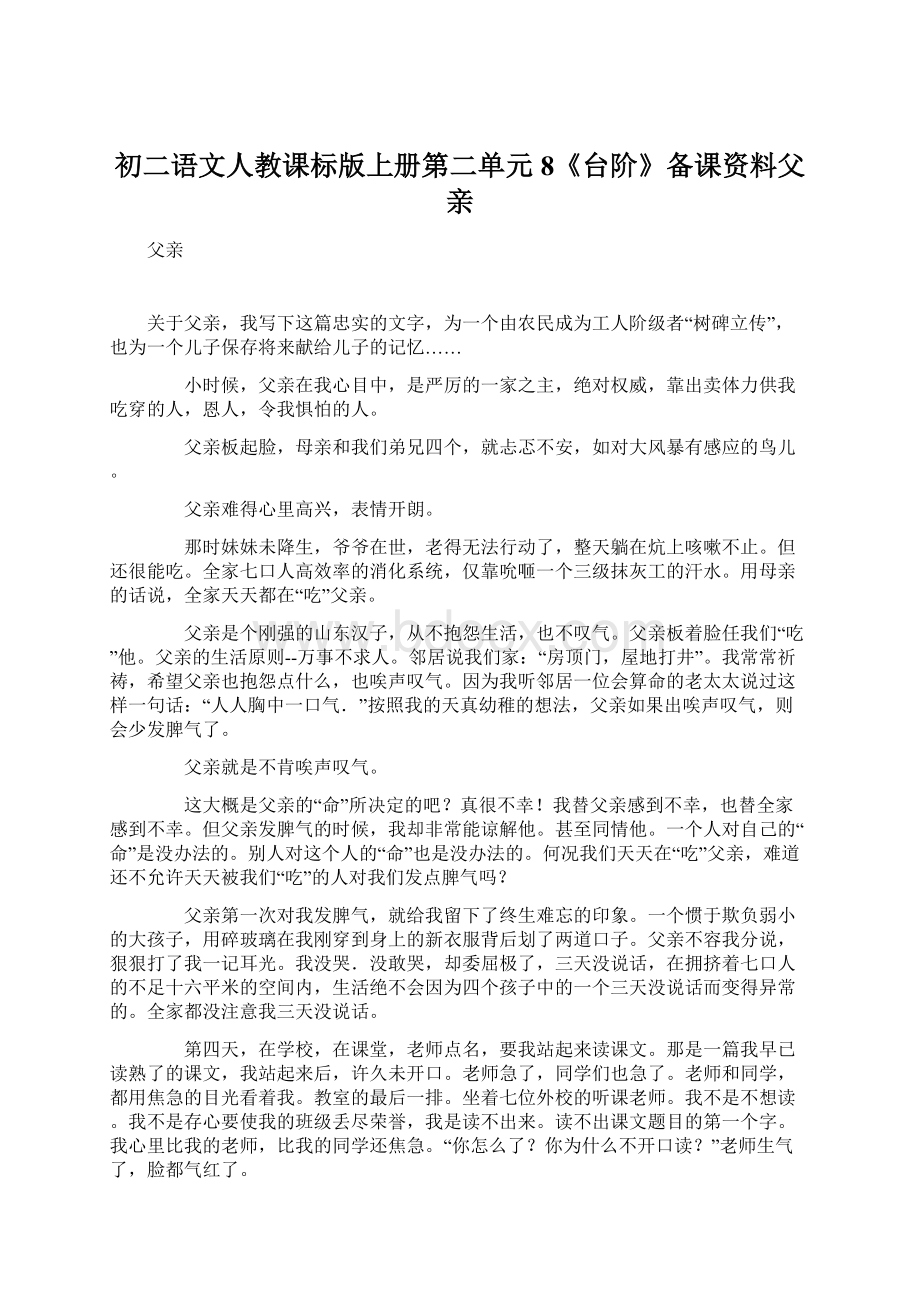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
多了一个“结巴嗑子”。
我,出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
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
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成府”。
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嗑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
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
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
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
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
母亲属羊。
像羊那么驯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
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
因为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
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20年。
中国的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
她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
虽然这憧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
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
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我以为是高于许多母亲们的。
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
父亲却鼓励我:
“盛呀!
再吃一碗!
”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用,又说:
“盛满!
”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他说:
“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
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怎样,一种由衷的喜悦。
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
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了。
还强吃掉半个窝窝头。
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
尽管撑得够受,但心里幸福。
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
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
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
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一天起,饭量大了。
党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
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浪崽子似的!
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的多欢,吃的多馋人哟!
”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
父亲引以自豪。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
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
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
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
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下去。
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
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
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的什么样,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
姐姐死的很冤,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
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晚了。
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
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
父亲认为,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
“西药,是治外国人的病的!
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
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
!
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
父亲这样对母亲吼。
母亲辩驳:
“中医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医。
“说这话的,就不是好中医!
”父亲更恼火了。
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而已。
邻居那个会算命的老太太,说按照麻衣神相,男属阳,女属阴。
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不可能有女孩。
说父亲的秉性大刚,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说我夭折的姐姐,是被我们家的阳刚之气“--”逃了,又托生到别人家中去了。
、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父亲将一包中草药偷偷塞进炉膛里,满屋弥漫一种苦涩的中草药味。
父亲在炉前呆呆站立了许久,从炉盖子缝隙闪闪出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父亲脸上。
父亲的神情那般肃穆,肃穆中呈现出一种哀伤我幼小的心灵,当时很信服麻衣神相之说。
要不妹妹为什么是在父亲离家,爷爷死后才出生呢?
我尽心尽意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希望父亲三年内别探家。
唯恐妹妹也像姐姐似的,“托生”到别人家中去。
妹妹的“光临”,毕竟使我想有一个姐姐的愿望,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弥补性的满足。
父亲果然三年设探家,不是怕“--”逃了妹妹,是打算积攒一笔钱。
父亲虽然身在异地,但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
“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忘不了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
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起用开销。
母亲彻底背叛了父亲的原则。
我们在“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很令人悲哀地结束了。
我们连心理上的所司“穷志气”都失掉了……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
父亲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么过的日子?
啊?
我每封信都叮嘱你,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过吗?
”父亲对母亲吼。
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响。
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爸爸,您要责骂,就大骂我们吧!
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
”哥哥不平地挂母亲辩护。
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儿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
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申明:
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
“你们这是干什么?
越大越不懂事了!
”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
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什么。
许久,父亲长叹了一声。
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
我心中悠然对父亲产生一种怜悯。
第二天,父亲带领我们到商店去,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斯期间。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
……”一一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浮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父亲一迭声说他错了。
“你说你什么干错了?
……”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
“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会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
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亲要回老家看看。
果真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当农民。
父亲这一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给我们带来希望。
我们并不迷恋城市。
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无毒的东西能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
父亲的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向往。
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
那是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的。
母亲从来也没有能够动摇过父亲的哪怕一次荒唐的念头。
母亲根本不具备这种妇人之术。
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使预先为父亲做种种动身前的准备。
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
在我们--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
最后,由父亲作出了裁决。
父亲庄严地对我说:
“老二,爸带你一块儿回山东!
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
对我,是一次大希望的大破灭。
对父亲,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
老家,本没亲人了。
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
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
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
羡幕我穿在脚上的那双崭新的胶鞋。
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
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掺面馒头,在故乡人眼中,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一种饥饿的氛围所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
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三百多元钱,除了路费,东家给五元,西家给十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全救济了故乡人。
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子离开了故乡……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
“孩子他妈,我把钱抖搂光了!
你别生气,我再攒!
……”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
母亲淡淡一笑:
“我生啥气呀!
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
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三百多元钱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角溢出,滴落在她衣襟上。
那一夜,父亲回身不止,长叹接短叹。
两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父亲始终信守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
父亲是很能攒钱的。
母亲是很能借债的。
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
所谓“对立统一”。
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
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思人。
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疑于溶淡骨血深情的衡释剂。
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而穷困之所以该诅咒,不只因为它造成物质方面的债务,更因为它造成精神上和增感上的债务。
父亲第三次探家那一年,正是哥哥考大学那一年。
父亲对哥哥想考大学这一欲望,以说一不二的成严加以反对。
“我供不起你上大学!
”父亲的话,令母亲和哥哥感到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好心的邻居给哥哥找了一个挣小钱的临时活--在菜市场卖菜。
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
父亲逼着哥哥去挣小钱,哥哥每天偷偷揣上一册课本,早出晚归。
回家后交给父亲五角钱。
那五角钱,是母亲每天偷偷塞给哥哥的。
哥哥实则是到公园里或松花江边去温习功课的。
骗局终于败露,父亲对这种“阴谋诡计”大发雷霆,用水杯砸碎了镜子。
父亲气得当天就决定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将父亲送到火车站。
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口探出身,对哥哥说:
“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
咱们全家七口,只我一人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啊!
……”父亲的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衷和哀哀的恳求。
列车开动时,父亲流泪了。
一滴泪水挂在父亲胡茬又黑又硬的脸腮上。
我心里非常难过,却说不清究竟是为父亲难过,还是为哥哥难过。
我知道,哥哥已背着父亲参加了高考。
母亲又一次欺骗了父亲。
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
我这个“知情不举”者,也欺骗了父亲。
我因无罪的欺骗感到内疚极了。
我,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难过……几天后,哥哥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母亲欣慰地笑了。
哥哥却哭了我又送走了哥哥。
哥哥没让我送进站。
他说:
“省下买站台票的五分钱吧。
”在检票口,哥哥又对我说:
“二弟,家中今后全靠你了!
先别告诉爸爸,我上了大学……”
我站在检票口外,呆呆地望着哥哥随人流走人火车站,左手拎着行李卷,右手拎着网兜,一步三回头。
我缓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手中紧紧擦着没买站台票省下的那五分硬币,心中暗想,为了哥哥,为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我无法长久隐瞒父亲哥哥已上了大学这件事。
我不得不在一封信中告诉父亲实情。
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
他再也没能返校。
他进了精神病院--个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个心理弱者的终生归宿。
一个明确的句号。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找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信。
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以上的信。
一封并不彻底的扫盲文化程度的信:
老大!
你太自私了!
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
根本没有弟弟妹妹!
你只想到你自己!
你一心奔你个人的前程吧!
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出你这个儿子!
有朝一日你当了工程师!
我也再不会认你这个儿子!
每句话后面都是“!
”号,所有这些“!
”号,似乎也无法表达父亲对哥哥的增怒。
父亲这封信,使我联想到了父亲对我们的那番教导:
“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不由得将父亲的教导做为基础理论进行思考:
每个人都是有把子力气的,倘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
哥哥上大学,其实绝不会造成我们家有一个人饿死的严峻后果。
那么父亲的愤怒,是否也因哥哥违背了他的教导呢?
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我所见识过的体力劳动者,大至分为两类。
一类自卑自贱,怨天咒命的话常挂在嘴边上:
“我们,臭苦力!
”一类盲目自尊,崇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蔽之曰:
“吃轻巧饭的!
”隐含着一种藐视。
父亲属于后一类。
如今思考起来,这也算一件极可悲的事吧?
对哥哥亦或对父亲自己,难道不都可悲么?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
以后的七年内,我再没见过父亲。
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父亲同时探家。
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
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
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哥哥上大学所落到的结果,远比父亲对我的人生教导在我心理上造成更为深刻的不良影响。
然而第二次被推荐,我却极想上大学了。
第二次即最后一次。
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
那一年我25岁了。
我明白,录取通知书设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人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
连干部同意不同意,至关重要。
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
我因此而优虑重重。
几经彻夜失眠,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之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在难料之中,请求父亲汇给我二百元钱。
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
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父亲是会明白我需要钱干什么的。
信一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
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来狠狠骂我一通。
肯定比其哥哥那封情更无情。
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即使他的儿子有当皇上的可能,他也是绝不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的。
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
二百元整。
电汇。
汇单的附言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槽别字:
“不勾,久来电”。
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
晚上,下着小雨。
我将二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
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摄着两迭钱,我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
我吱吱唔唔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迭钱被攥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
那时刻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在我耳边说:
“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
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
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幼小,长大后忘了许多事,但这些话却忘不掉。
我觉得衣兜里的两迭钱沉甸甸的,沉得像两大块铅。
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我的人格那么卑下,我的动机那么可耻。
我恨不得将我这颗肮脏的心从胸腔内呕吐出来,践踏个稀巴烂,践踏到泥土中。
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头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我哭自己。
也哭父亲。
父亲他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
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抹光彩,在一个儿子心中损坏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
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
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了二杠——负荷足沉重的位置。
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高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还是上了大学。
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而且还。
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
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
“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永远保留在我记忆中……三年大学,我一次也没有探过家,为了省下从上海到哈尔滨的半票票价。
也为了父亲每个月少吃一块臭豆腐,多吃一盘炒菜。
毕业后,参加工作一年,我才探家,算起来,我已十年没见过父亲了。
父亲提前退休了,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一次,受了内伤,也年老了,干不动重体力活了。
三弟返城了。
我回到家里时,见三弟躺在炕上,一条腿绑着夹板,呆在半空。
小妹告诉我,三弟预备结婚了。
新房是傍着我们家老鹰山墙盖起的一间“偏厦子”。
我们家的老屋很低矮,那“偏屋子”不比别人家的煤棚高多少。
我进人“新房”看了看,出来后问三弟:
“怎么盖得这么凑凑乎乎?
”三弟的头在枕上门向一旁,半天才说:
“没钱,能盖起这么一间就不槽了。
‘’我又问:
“你的腿怎么搞的?
”三弟不说话了。
小妹从分管他说:
“铺油毡时,房顶木板大朽了,踩塌掉进屋里……”
我望着三弟,心里挺难过,我能读完三年大学,全靠三弟每月从北大荒寄给我十元钱。
吃过晚饭后,我对父亲说:
“爸爸,我想和你谈件事。
”父亲看了我一眼,默默地等待我说。
父亲看我时的目光,令我感到有些陌生。
是因为我们父子分别了整整十年吗?
是因为我成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吗?
我不得而知。
他看我那一眼,像一匹老马看自己带大的一头鹿。
我向父亲伸出了一只手:
“爸爸,把你这些年攒的钱都拿出来,给三弟盖房子用吧!
”父亲又用那种有些陌生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仍下头,沉默半晌,才低声说:
“我……不是已经给了吗?
……”我说:
“爸爸,你只给了三弟二百五十元钱呀!
那点钱能够盖房子用嘛!
”“我……再没钱……”父亲的声音更低。
我大声说:
“不对!
爸爸,你有!
我知道你有!
你有三千多元钱……”父亲腾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脸色涨得通红,怒吼过:
“你!
……你简直胡说!
我什么时候攒下过三千元?
……”躺在炕上的三弟插嘴说:
“二哥,你何必为我逼爸爸呢!
爸爸一辈子都想攒钱,如今总算攒下了,能舍得拿出来为我盖房子?
”口吻中流露出一个儿子内心对父亲的极大不满。
我生气了,提高嗓门说:
“爸爸,你这样出不对!
三弟能在那样一间煤棚似的破屋里结婚吗?
那里出生的,将是你的孙子,或是你的孙女!
你将在子孙后代面前感到羞愧的!
……”我心中倏然对父亲鄙视起来。
“住嘴!
……”父亲举起了一只拳头。
拳没落到我身上,在空中出了片刻,沉重地垂下了。
母亲,回弟和小妹赶紧从里间屋出来,把我往里间屋拉。
……十年没见我,见我就教训我么?
好一个儿子啊!
你就是这样给你弟弟妹妹们作榜样的么?
你可算念成了大学了!
你给我滚!
……”父亲脸腮抽搐着,眼中喷射出怒火。
他那凶暴的语词中,有一种寒透了心的悲凉成分。
他用手用我一指,又吼出一个“滚”宇,再说不出别的话来。
我一下子挣脱了母亲和四弟拉住我的手,大声说:
“爸爸,我永远不再回这个家!
……”说完,冲出了家门。
我一口气走到火车站,买了一张三个小时后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一支接一支吸烟。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有人轻轻叫我,抬起头,见母亲和四弟站在面前。
四弟说:
“二哥,回家吧!
”母亲也说:
“回家吧,妈求你!
”“不……”我坚决地摇摇头。
母亲又说:
“你怎么能那样子跟你父亲争吵呢?
他的确是没攒下那么多钱呀!
他攒下的一点钱,差不多全给你三弟了……下个月初就要给你哥哥交住院费……”几个好奇的男人女人围住了我们,用各种猜疑的目光注视我。
我听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离开时叹了口气,说: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分明是被看成了个不孝之子了。
我打断母亲的活,说:
“妈妈,您别替我父亲辩护了!
我在大学时,您亲自写信告诉过我,我父亲已积攒下了三千元钱,他怎么能对他的儿子那么吝啬?
”母亲怔了一下,说:
“傻孩子,是妈不好,妈那是骗你的呀!
为了让你在大学里安心读书,不挂虑家中的生活……”听了母亲的活,我呆呆地望着母亲那张憔悴的脸,发愣许久,说不出话来。
“听妈的话,回家吧!
回家给你爸认个错……”母亲上前扯我。
我低下头哭了……我跟着母亲和四弟回到了家里。
我向父亲认了错。
父亲当时没有任何原谅我的表示。
小妹那时已中学毕业,在家待业两年了,一直没有分田工作。
母亲低眉下眼地去找过街道主任几次,街道主任终于给了一个活口说:
“下一次来指标,我给使把劲试试看吧!
”母亲将这活学给父亲,对父亲说:
“为了孩子,这人情,管多管少,无论如何也得送啊!
”父亲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钱包,递给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刚交了老大的住院费,剩下的,都在里边了……”牛皮纸钱包里,大票只有两张拾元的了。
母亲犹豫了一阵,将其中一张交给妹妹,妹妹就用那拾元钱买了点不成体统的东西,当天拎着去街道主任家“表示表示”。
怎么拎去的,又怎么拎回来了。
母亲诧异地问:
“怎么拎回来了?
”小妹沮丧地回答:
“人家不肯收。
”母亲又问:
“嫌少?
”“人家说,多年住在一条街上,收了,就显得不好了。
人家说,要是咱们非愿意表示表示,她家买了一吨好煤,咱们帮忙给拉回来……”小妹说罢,怯怯地瞟了父亲一眼。
父亲始终没抬头,听罢小妹的话,头更低下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开口说:
“我和你四哥……一块儿去给拉回来……”四弟刚巧从外面回来,问明白后,为难地对父亲说:
“爸,我们厂的团员明天要组织一次活动,我是团支部书记,我不能不去呀!
”小妹急了:
“什么破团支部书记,你当得那么上瘾?
明天不给拉回来,人家的煤票就过期了……”这一切话,我都在里屋听到了,我跨出里屋,对小妹说:
“明天我和爸去拉。
父亲突然莫名其妙地火了:
“谁都用不着你们!
我明天一个人去拉!
我还没老的不中用,我还有力气!
”头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雨,第二天白天,雨下得更大了。
我和父亲借了辆手推车,冒雨去拉煤。
路很远。
煤票是在一个铁道线附近的大煤厂开的,距我们住的街区,有三十来里。
一吨煤,分三趟拉。
天黑才拉回第三的。
拉第三趟时,一只车轮卡在铁轨岔角里。
无论我和父亲使出多大的力气,车轮都纹丝不动,像被焊住了。
我和父亲一块儿推。
一块儿拉,一个推,一个拉,弄得浑身是泥,双手处处是伤,终于一筹莫展。
在暴雨中,我听得见父亲像牛一样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我扶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对父亲大声喊:
“爸爸,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值班房找个人来帮帮忙!
”“你的力气都哪去了?
”父亲一下子推开我,弯下腰,用他那肌肉萎缩了的肩膀去扛车。
远处传来厂火车的吼声,一列火车开过来了。
在闪电亮起的刹那,我看见一块松弛的皮肤,被暴雨无情地鞭打着。
是一个老年人的丧失了力气的脊梁。
车头的灯光从远处射了过来。
父亲仍在徒劳无益地运用着微不足道的力气。
我拔腿飞快地朝道班房跑去。
道班工人发出了紧急停车讯号。
列车停住了。
道班工人和我一块跑到煤车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