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医李可治疗肝炎颈椎增生病经验方.docx
《著名中医李可治疗肝炎颈椎增生病经验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著名中医李可治疗肝炎颈椎增生病经验方.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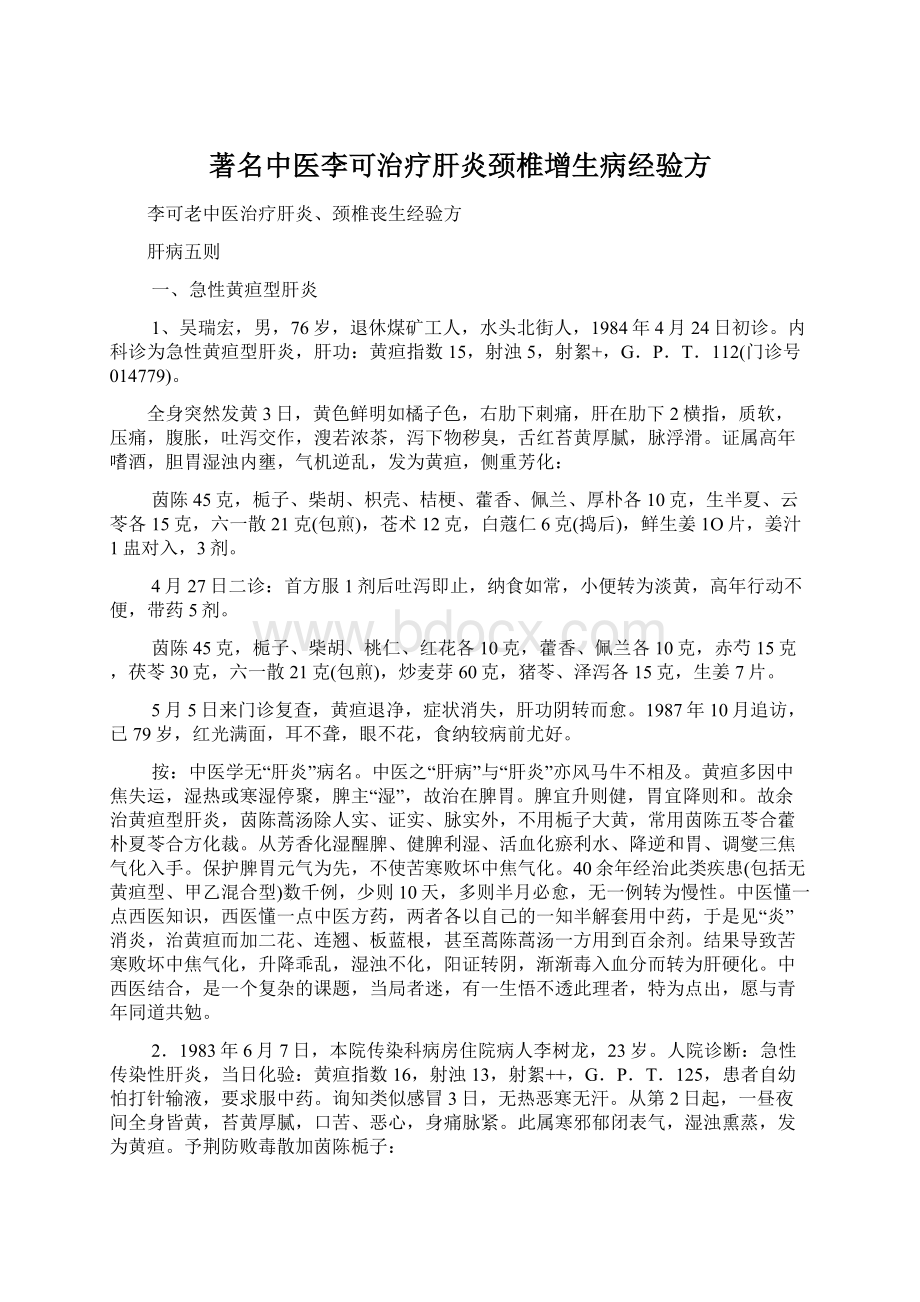
著名中医李可治疗肝炎颈椎增生病经验方
李可老中医治疗肝炎、颈椎丧生经验方
肝病五则
一、急性黄疸型肝炎
1、吴瑞宏,男,76岁,退休煤矿工人,水头北街人,1984年4月24日初诊。
内科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肝功:
黄疸指数15,射浊5,射絮+,G.P.T.112(门诊号014779)。
全身突然发黄3日,黄色鲜明如橘子色,右肋下刺痛,肝在肋下2横指,质软,压痛,腹胀,吐泻交作,溲若浓茶,泻下物秽臭,舌红苔黄厚腻,脉浮滑。
证属高年嗜酒,胆胃湿浊内壅,气机逆乱,发为黄疸,侧重芳化:
茵陈45克,栀子、柴胡、枳壳、桔梗、藿香、佩兰、厚朴各10克,生半夏、云苓各15克,六一散21克(包煎),苍术12克,白蔻仁6克(捣后),鲜生姜1O片,姜汁1盅对入,3剂。
4月27日二诊:
首方服1剂后吐泻即止,纳食如常,小便转为淡黄,高年行动不便,带药5剂。
茵陈45克,栀子、柴胡、桃仁、红花各10克,藿香、佩兰各10克,赤芍15克,茯苓30克,六一散21克(包煎),炒麦芽60克,猪苓、泽泻各15克,生姜7片。
5月5日来门诊复查,黄疸退净,症状消失,肝功阴转而愈。
1987年10月追访,已79岁,红光满面,耳不聋,眼不花,食纳较病前尤好。
按:
中医学无“肝炎”病名。
中医之“肝病”与“肝炎”亦风马牛不相及。
黄疸多因中焦失运,湿热或寒湿停聚,脾主“湿”,故治在脾胃。
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
故余治黄疸型肝炎,茵陈蒿汤除人实、证实、脉实外,不用栀子大黄,常用茵陈五苓合藿朴夏苓合方化裁。
从芳香化湿醒脾、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利水、降逆和胃、调燮三焦气化入手。
保护脾胃元气为先,不使苦寒败坏中焦气化。
40余年经治此类疾患(包括无黄疸型、甲乙混合型)数千例,少则10天,多则半月必愈,无一例转为慢性。
中医懂一点西医知识,西医懂一点中医方药,两者各以自己的一知半解套用中药,于是见“炎”消炎,治黄疸而加二花、连翘、板蓝根,甚至蒿陈蒿汤一方用到百余剂。
结果导致苦寒败坏中焦气化,升降乖乱,湿浊不化,阳证转阴,渐渐毒入血分而转为肝硬化。
中西医结合,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当局者迷,有一生悟不透此理者,特为点出,愿与青年同道共勉。
2.1983年6月7日,本院传染科病房住院病人李树龙,23岁。
人院诊断:
急性传染性肝炎,当日化验:
黄疸指数16,射浊13,射絮++,G.P.T.125,患者自幼怕打针输液,要求服中药。
询知类似感冒3日,无热恶寒无汗。
从第2日起,一昼夜间全身皆黄,苔黄厚腻,口苦、恶心,身痛脉紧。
此属寒邪郁闭表气,湿浊熏蒸,发为黄疸。
予荆防败毒散加茵陈栀子:
荆芥、防风、羌活、独活、前胡、柴胡、枳壳、桔梗、薄荷、栀子各10克,茵陈45克,川芎10克,茯苓30克,鲜生姜3片,冷水泡1小时,急火煮沸7分钟,2次分服,2剂。
2月9日二诊:
药后得汗,恶寒已罢,小便特多。
面目舌下、胸部之黄已退八九,呕止,食纳好,舌上黄厚腻苔化去大半,小便清长。
当日化验:
黄疸指数8,射浊10,射絮+,G.P.T.110,自汗不渴。
予和营卫,化湿退黄:
茵陈45克,桂枝、赤芍、炙草各10克,白术、茯苓各24克,猪苓、泽泻、桃仁各12克,鲜生姜5片,枣6枚,2剂。
6月11日三诊:
全身黄已退净,气短口渴,舌红少苔,尿淡黄,脉虚而数。
二诊过用渗利,气阴两伤。
口中觉腻,湿浊未化。
予益气养阴芳化:
生芪、茵陈各30克,生山药、石斛各30克,知母18克,白参(另炖)10克,藿香、佩兰各5克,3剂。
6月14日四诊:
纯中药治疗7日,肝功阴转,诸症均退。
唯舌红,口渴,脉数,气阴未复,原方去茵陈,加玉竹15克,带药3剂出院。
二、急性无黄疸型肝炎
七二五厂工人武文荣,33岁,1983年5月7日初诊。
病程75天,住院73天。
服茵陈蒿汤加板蓝根、大腹皮30余剂,板蓝根注射液160支,计用茵陈、板蓝根、大腹皮各1000克多,食纳日见减少,体质日见瘦削,面色黧黑,泛酸作呕,腹胀气急,腰困如折,左肋下隐痛不休,整日怠惰思卧。
舌胖淡有齿痕,苔白滑。
脉滑细,尺部极弱。
日仅进食不足半斤,食入则胀急不堪,恶闻油肉味,吃水果则吐酸水,口中粘腻不爽。
追询得病始末,始知患者素体阳虚,平日即觉胃寒膝冷,食少肢软。
病后倍感困乏无力,食入则吐,不以为意。
后被车间同事看出脸色发青,敦促就医,一查GPT已高达500单位,愈服药愈觉不能支撑。
据上证情,属劳倦内伤,寒湿浊邪阻塞中焦气化所致。
既无黄疸见症,何所据而用茵陈蒿汤?
以阳虚之体,寒湿之邪,复加寒凉攻泻妄施,无怪中阳日困。
且脾胃为后天之本,必赖先天肾阳之温煦,始能蒸化水谷。
今误投苦寒,先伤脾阳,后及肾阳,阴寒肆虐,永无愈期矣!
其面色黧黑,腰困如折,即是明证。
当以温药治其本,芳化治其标:
党参30克,灵脂15克,公丁香、郁金、吴茱萸、肉桂、藿香、佩兰、炙草各10克,炒麦芽60克,生半夏20克,泽泻18克,鲜生姜10片,枣10枚,姜汁10毫升(对入),3剂。
5月11日二诊:
药后呕止,胀消,食纳大增,日可进食1斤多,开始想吃肉类。
唯腰困仍著,予原方加肾四味120克,胡桃4枚,7剂。
11月16日,患者从孝义来信,知药后肝功阴转,体质较病前更好。
并寄赠名家医著3册,以表寸心云。
三、急性肝炎误治变症
高香香,女,30岁,灵石煤矿工人家属。
1983年6月27日初诊。
1979年初患急黄肝炎,经治3个月,服茵陈蒿汤加味方70余剂,计茵陈3000多克,板蓝根2000多克,栀子、大黄250克。
黄疸虽退,肝功持续不降,GPT120单位。
日见食少神疲,畏寒肋痛。
又服柴胡疏肝散加味方20余剂后,变生经闭、厌食、腹胀而呕涎沫,亦已3个多月。
面色萎黄无华,肋间刺痛不休。
痛作时按腹弯腰,头汗淋漓。
近日更增腰困如折,足膝冰冷,小便不禁。
脉细,左关特弱,舌淡,苔灰腻。
已成迁延性肝炎,病程长达5年。
证由过用苦寒攻下,损伤肝、脾、肾三脏之阳。
又过用辛散,致气血耗伤。
脾胃为后天之本,恶湿又主化湿,此经一伤,气血生化无源,故面色萎黄,食少经闭。
肝为人身元气之萌芽,过用辛散攻伐、苦寒解毒等品,致伤肝气。
肝寒则络脉滞,故胁痛不休。
肝虚则自顾不暇,木不疏土,土气更壅,故见厌食腹胀纳呆。
肾为先天之本,人之有生全赖命火之温煦,肾阴之濡养。
今苦寒伤损肾阳,肾气怯弱,故见腰困如折,虽在盛夏,瑟缩畏寒,小便失约。
故治疗此症之关键,要忘却一切先人为主之偏见,置“肝炎”于脑外,但先温养肝、脾、肾三脏之阳而救药误,治法便在其中矣:
生芪、当归、肾四味各30克,红参(另炖)、灵脂、吴茱萸、桂枝尖、生麦芽、细辛、炙草各1O克,赤芍15克,干姜30克,油桂2克,鲜生姜10片,枣10枚。
上方守服27剂,计用干姜、肾四味各810克,吴茱萸、细辛各270克,服至10剂时,呕涎、肋痛得罢,食纳大增,日可进食1斤多。
服至20剂时,面色已见红润,自感乳胀,又服7剂,月经来潮。
8月初化验,肝功阴转,诸症均愈。
按:
余治此败症,受张锡钝氏之启迪颇深。
张氏论治肝脾有独特见解。
张氏论日:
“俗谓肝虚无补法,以肝为刚脏,性喜条达,宜疏不宜补,补则滞塞不通。
故理肝之法,动日平肝,而遇肝郁之证,恒用开破肝气之药。
”张氏提出:
“……不知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而萌芽于肝。
凡物之萌芽,皆嫩脆易于损伤。
肝既为元气萌芽之脏,而开破之若是,独不虑损伤元气之萌芽乎?
”此论确有见地。
五脏病理,有虚即有实,肝脏何独不然?
肝郁,其气固不能条达。
肝虚,则其气亦无力条达。
凡遇此等证候(左关脉特弱)张氏重用生芪之性温而升,以之补肝,有同气相求之妙用。
重用生芪,少佐理气之品,覆杯即见效验。
张氏升散肝郁,喜用生麦芽,而不用柴胡。
他说:
“升肝之药,柴胡最效。
然治肝不升、胃不降之证,则不用柴胡而用麦芽。
盖因柴胡不但能升肝,且能提胃气上逆。
而生麦芽虽能升肝,实无妨碍胃气之下降。
盖其萌芽生发之性,与肝木同气相求,能宣通肝气之郁结,使之开解而自然上升……”肝与脾,有微妙的关系。
一人饮食不能消化,服健脾养胃药百剂不效。
脉见左关特弱,知是肝气不振,张氏投以生芪30克、桂枝尖9克,数剂而愈。
独创“补肝气以实脾胃”之论。
因“五行之理,木能侮土,木亦能疏土也。
”木气郁则过强而侮土,木气虚则太弱而不能疏土。
张氏的论述,对肝脾郁证的治疗,独辟蹊径,解破临床一大难题。
唯论中“柴胡提胃气上逆”之说未当。
似观《伤寒论·大、小柴胡汤证》以胃气上逆、喜呕、呕不止为主证,两方主药柴胡均用至半斤——按古今折算率,合今之125克。
如此大量,服1剂的1/3,即可止极重之呕吐。
余用两方,治验成千上万。
可证柴胡并无“提胃气上逆”之弊。
盖气机升降之理,以脾胃为枢纽,如轮之轴,是为中气。
脾升胃降,则中气左旋,肝从左升,肺从右降,当升者升,当降者降,是为无病。
况药物归经,各有妙用,药物功能,不止一端,而伤寒用药之灵妙,又不拘一法。
升肝者,兼能降胃,木克土之原始含义,即木气升发、疏泄,以助脾胃中之湿土,不致壅塞。
则柴胡升肝,不碍降胃。
此为五行生克制化之常。
此理,清代黄元御论之最详,民初彭承祖更有发挥,可参阅《中医系统学》。
四、产后阴黄重症
王秋梅,女,23岁,灵石火车站家属,1964年9月17日初诊。
病人处于半昏睡状态,其夫代诉病史:
产后未满3个月,患急性黄疸型肝炎61天。
初病时发冷发热,因产后体虚服补中益气汤两剂,7天后发现眼睛发黄,腹胀呕吐,渐渐全身发黄,到32天,全身落黄末,衣被尽染。
每日黎明必泻,泻后出汗、心悸,腿软不能走路。
畏寒,脐周冷痛,腰脊困痛难忍,整日弯腰如虾。
近1周来,过午即神糊思睡,小便浓绿色,大便灰白不臭。
请医院内科诊查,认为已进入肝昏迷状态,建议去省抢救。
因家贫,邀余诊治。
见患者神糊耳聋,头面四肢胸背皆黄,黄色灰暗如烟熏。
四肢枯细,眼眶深陷,神色憔悴,脐中筑筑跃动。
脉微细急,132次/分,舌胖淡润,微喘。
语声低微,神识似清似蒙。
脉证合参,由产后将养失宜,始病风寒外束,失于疏解,误服补剂,致寒湿内郁发黄,迁延失治,致正气日衰,寒湿秽浊之邪,充斥三焦,蒙蔽神明,昏睡蜷卧,自利喘汗,脾肾将败,肢厥脉微,脉至七急八败,已是少阴亡阳内闭外脱危候,唯下三部之趺阳脉尚清晰可辨,胃气尚存,正在青年,虽见肝昏迷之前兆,一线生机未绝。
拟回阳救脱,破浊醒神,以茵陈人参白通四逆汤、吴茱萸汤、三畏汤合方,加菖蒲、麝香之辟秽开闭为治:
1.茵陈、附子各30克,干姜、吴茱萸、红参(另炖)、灵脂、油桂、赤石脂、公丁香、郁金、菖蒲、炙草各10克,麝香O.3克(分冲),鲜生姜5片,枣10枚,葱白3寸,煎浓汁,小量多次分服,先单服麝香0.3克。
2.外用蜡纸筒灸黄法,以加强温肾回阳泄浊之力:
以6寸见方麻纸数张,蜂蜡1块,制钱1枚,湿面团1块。
将蜂蜡置铁鏊上加热溶化,将麻纸浸润均匀,卷成直径与制钱相等之蜡纸筒,接头处用蜡汁封固。
灸时,令病人仰卧,拭净肚脐,将制钱置于脐上,钱孔对准脐心。
再将蜡纸筒扣于制钱上,蜡纸筒下端与脐相接处,用湿面围一圈,固定密封,勿令泄气,脐周用毛巾围好,保护皮肤。
然后将上端点燃,待燃至离脐半寸,迅速将火吹灭,以免灼伤皮肤。
取下蜡纸残端,另换1支,如法再灸。
每灸毕1次,将脐中、制钱上、蜡纸残端内之黄色粉末(黄疸毒素)投入灶内烧化,以免传染。
于当日午时施灸6次,共拔出黄色粉末3小酒盅。
施灸过程,患者觉脐中有热流滚动,向四周放散。
灸至第6支时,患者全身微微见汗,松快异常。
约1小时许,施灸完毕,神识稍清。
其缠绵数十日之绕脐绞痛,灸毕即愈。
且腹中鸣响不停,矢气频转,呕逆大减,自患病以来第1次感到饥饿。
全家欢喜雀跃,其母做细面条1小碗(约1两半)顺利吃完。
.
9月18日二诊:
服药1剂,今口呕逆未作,四肢厥冷退至手足踝关节处,腹中时时呜响,矢气不断。
黎明泻延至8时后,泻后稍有气喘心悸。
脉仍微细而急,较昨有力,120次/分。
小便如前,不热不渴。
午前又施灸12支,拔出黄疸毒素4小酒盅。
神识清朗,耳已不聋,可以准确回答询问。
每日过午即神迷昏睡之象未见,嘱原方再服1剂。
9月19日三诊:
昨夜子时服完第2剂药,尿量约1500毫升,便不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