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从属性问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共同犯罪从属性问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共同犯罪从属性问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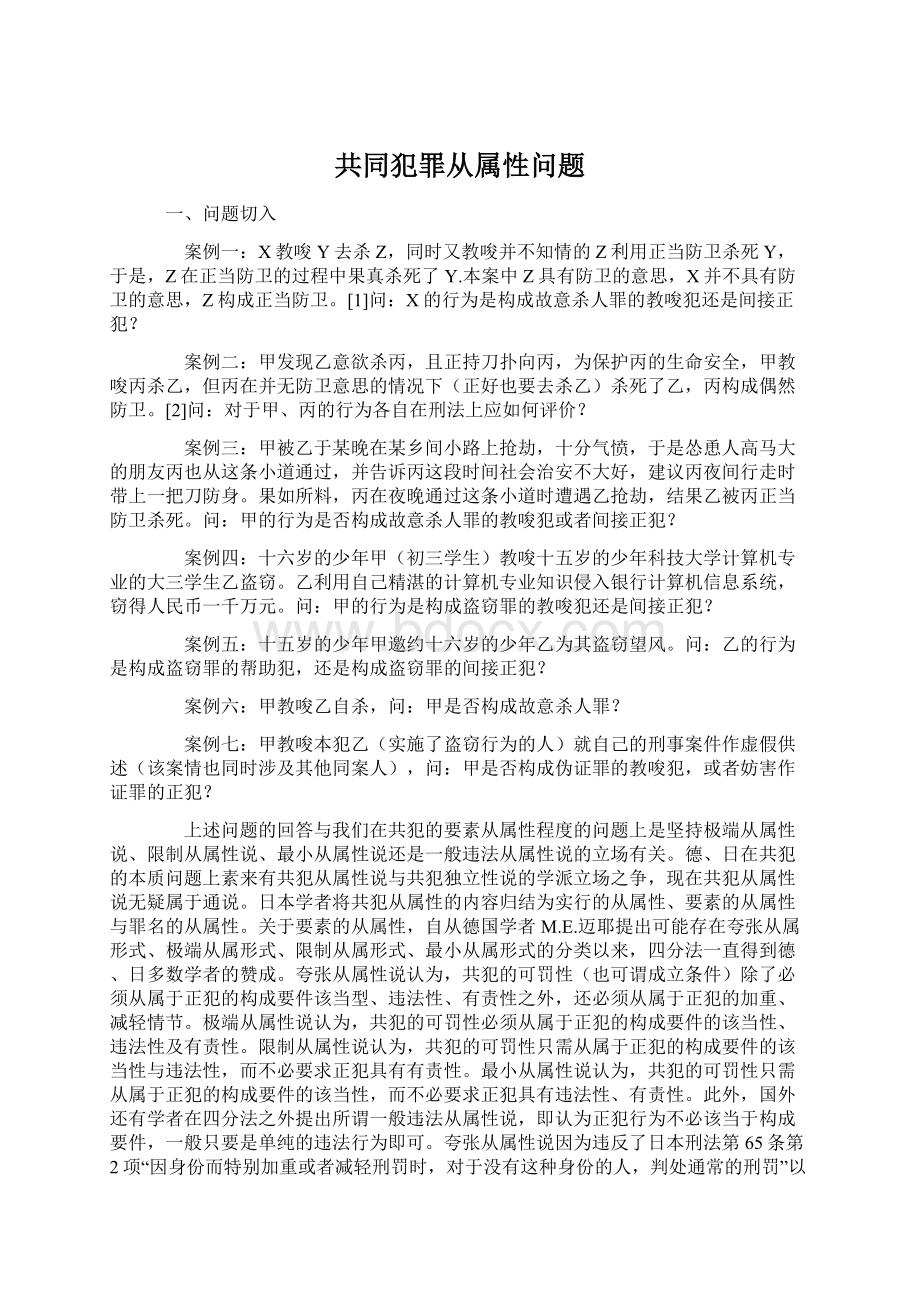
案例五:
十五岁的少年甲邀约十六岁的少年乙为其盗窃望风。
乙的行为是构成盗窃罪的帮助犯,还是构成盗窃罪的间接正犯?
案例六:
甲教唆乙自杀,问:
甲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案例七:
甲教唆本犯乙(实施了盗窃行为的人)就自己的刑事案件作虚假供述(该案情也同时涉及其他同案人),问:
甲是否构成伪证罪的教唆犯,或者妨害作证罪的正犯?
上述问题的回答与我们在共犯的要素从属性程度的问题上是坚持极端从属性说、限制从属性说、最小从属性说还是一般违法从属性说的立场有关。
德、日在共犯的本质问题上素来有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的学派立场之争,现在共犯从属性说无疑属于通说。
日本学者将共犯从属性的内容归结为实行的从属性、要素的从属性与罪名的从属性。
关于要素的从属性,自从德国学者M.E.迈耶提出可能存在夸张从属形式、极端从属形式、限制从属形式、最小从属形式的分类以来,四分法一直得到德、日多数学者的赞成。
夸张从属性说认为,共犯的可罚性(也可谓成立条件)除了必须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型、违法性、有责性之外,还必须从属于正犯的加重、减轻情节。
极端从属性说认为,共犯的可罚性必须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及有责性。
限制从属性说认为,共犯的可罚性只需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与违法性,而不必要求正犯具有有责性。
最小从属性说认为,共犯的可罚性只需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而不必要求正犯具有违法性、有责性。
此外,国外还有学者在四分法之外提出所谓一般违法从属性说,即认为正犯行为不必该当于构成要件,一般只要是单纯的违法行为即可。
夸张从属性说因为违反了日本刑法第65条第2项“因身份而特别加重或者减轻刑罚时,对于没有这种身份的人,判处通常的刑罚”以及德国刑法第29条“数人共同犯罪的,各依自己的罪责受处罚,不考虑他人的罪责”的规定,故几乎没有支持者。
本文拟在批判最小从属性说、极端从属性说以及一般违法从属性说的基础上,提出我们应提倡限制从属性说的主张。
二、最小从属性说批判
王昭武先生在2007年第11期《法学》上撰文“论共犯的最小从属性说——日本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发展与借鉴”(以下简称“王文”)指出,“我国刑法学通说认为,共同犯罪必须是所有共犯均构成犯罪,且教唆的对象限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因而我们采取的是极端从属性说。
事实上,与我国一样采取二元论共犯体系的日本刑法已完全摒弃了极端从属说,而以限制从属性说为通说,且因违法的相对性理论的提出,最小从属性说的影响力日渐扩大。
借鉴日本共犯的从属性理论,探讨要素从属性的内涵,倡导最小从属性说,对于发展我国的共犯理论,解决相关实际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3]笔者赞成王文关于我国应摒弃极端从属性立场的主张,但对我们应倡导最小从属性说的主张不能赞成。
最小从属性说认为,共犯的成立条件或者可罚性条件是正犯的行为只要具有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即可,无需正犯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与有责性。
按照德、日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犯罪论体系,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被害人的承诺、医疗行为、体育竞技活动、警察执行逮捕、法警执行死刑等都属于虽具有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即符合性)但阻却违法性的行为。
如果将最小从属性说贯彻到底,则在他人实施正当防卫时大声喝彩的,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
递给正当防卫人一把刀的,构成故意杀人罪帮助犯;
在大火即将烧到某人的房屋时,指使该人将邻居的屋顶掀掉的,虽然被指使人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但指使人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教唆犯;
父亲委托医生动手术将患阑尾炎的儿子的阑尾切掉的,虽然医生属于正当业务行为而阻却违法性,但父亲还是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教唆犯;
为警察勇捕逃犯而大声叫好的,虽然警察的行为属于依法令实施的行为而阻却违法性,但大声叫好的人还是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罪的教唆犯;
为法警依法执行死刑而拍手称快的,虽然法警的“杀人”行为被阻却违法性,但这些拍手称快的人还是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
等等。
这些结论存在重大疑问。
笔者下面一一驳斥王文的主张。
首先,王文提到的所谓最小从属性说的倡导者并非彻底的最小从属性说的支持者,至少并不否定限制从属性说的原则上的合理性。
王文提到,日本学者平野龙一率先对限制从属性说提出质疑,相继得到前田雅英、佐伯仁志等学者的支持,上述学者是立足于结果无价值论主张最小从属性说,而大谷实则以违法二元论作为其理论根据事实上也采取此说。
[4]下面我们不妨听听这四位学者的“真音”。
日本学者平野龙一在其经典教科书中指出,“虽然原则上违法是客观的、连带的,但例外的专属于一身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即正犯行为合法而共犯行为违法,或者正犯行为违法而共犯行为合法。
在认为构成正当防卫以防卫的意思为必要时,A教唆B揍C,然后又教唆不知情的C对B进行正当防卫,这时,因为A不具有正当防卫的意思所以违法,而C因为具有正当防卫的意思所以合法。
还有,在认为同意伤害违法时,甲委托医生乙切掉自己的手指,乙虽然对于伤害是违法的,但甲不能作为教唆犯进行处罚。
如后所述,部分必要的共犯,也正是这种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严格地讲,共犯只需从属于该当构成要件的正犯行为,是否违法,共犯与正犯应分别进行检讨。
如此说来,最小从属性说乃至(与违法共犯论相区别的意义上)因果共犯论,或许更为妥当吧!
但是,这只是属于极为例外的情形,也就是对于限制从属性来说只需作为例外考虑就可以了!
”[5]看来,最小从属说的首位提倡者原则上也没有否定限制从属性说,只是承认例外情况下的违法的相对性。
对于这种违法相对性存在的场合,限制从属性说只需将其作为例外加以考虑就行了。
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指出,“正如一直以来所指责的那样,在极端从属性说与限制从属性说之间,不管采取哪种从属形式,都不能仅从形式上妥当地解决问题。
例如,教唆12岁的少年杀人,不可否认构成教唆犯,因此,极端从属性说不能采用。
但是,命令12岁的少女盗窃,判例却未必作为盗窃教唆处理(最决昭和58.9.21刑集37.7.1070),由此说明,限制从属性说也未必妥当。
而且,若坚持限制从属性,共犯连带于正犯的违法性,这也常常未必正确。
即使共犯者(共同正犯者)违法,正犯者(共同正犯者)也可能存在正当防卫的情况(又如,委托他人杀死自己的,委托人即被害者也未必具有同意杀人罪的违法性)。
本来,就共犯处罚是需要正犯具有有责性还是只需具有违法性的形式论而言,也未必就因此划定了间接正犯与共犯的处罚范围。
从要素从属性的意义上看,‘至少正犯者没有实施该当构成的行为就不能处罚共犯’的这个意义上的最小从属性不能无视。
不过,这不意味着在正犯者欠缺违法性与有责性的所有场合均处罚教唆犯、帮助犯。
所以,关于要素从属性的议论,不得不说现在在解释论上已经失去了问题解决的机能。
”[6]其实,前田教授质疑限制从属性说,无非是两点:
一是,本来按限制从属性说在教唆无责任能力人时应成立教唆犯,但判例却未必总是作为教唆犯处罚,而是可能认定为间接正犯;
二是,认为按照限制从属性说似乎就意味着完全坚持违法的连带性而否认违法的相对性。
应该说这两点质疑都未必有理。
因为,主张限制从属性说也并不排斥间接正犯的概念。
尽管间接正犯概念的产生是为了解决极端从属性说所可能带来的处罚漏洞,但在德、日通说采限制从属性说的今天,也不否认保留间接正犯概念的必要性。
原因在于,在利用幼儿或者高度的精神障碍者等情况下,对于教唆者(利用者)还是需要作为间接正犯进行处罚,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所以不能因为采取限制从属性说却仍然承认间接正犯成立的可能,就因此得出结论认为限制从属说应予摒弃,而改采最小从属性说。
再则,关于违法的相对性,现在主张限制从属性说的学者,除个别学者在共犯处罚根据上采坚持彻底的违法的连带性的修正惹起说以外,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否认违法的相对性。
也就是说,不能将限制从属性说与坚持彻底的违法的连带性划等号,以此为由否定限制从属性说。
前田教授的主张还有另外一点疑问:
一方面认为最小从属性说合理,另一方面却认为也并非在所有正犯欠缺违法性和有责性的情况下,对参与者都要作为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进行处罚。
这难免让人怀疑最小从属性说在共犯处罚范围上的明确性。
最小从属性说的另一支持者日本学者佐伯仁志指出,“判例理论也赞成,在一定范围内,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难者中违法性阻却的判断在不同的共同犯罪人之间应当分别进行。
这样,全部地作为原则来说,最小从属性是妥当的。
当然,违法相对化只属于例外的情况,即使采用最小从属说,对于合法行为的教唆与帮助原则上还是不应处罚。
”[7]佐伯教授与前田教授一样,赞同最小从属性说的所谓理由,无非就是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难等个别、例外的情况下的违法性,有可能在共同犯罪人之间分别进行判断,也就是存在违法的相对性的情形。
如后所述,肯定违法的相对性并非是抛弃限制从属性说而采最小从属性说的理由。
佐伯教授与前田教授还同样认为,并不是对于合法的教唆、帮助行为都要作为教唆犯、帮助犯进行处罚,这同样暴露了最小从属性说在共犯处罚范围上的不明确性。
王文认为大谷实教授事实上也采取最小从属性说。
其实,大谷实教授是这样说明的:
“……(3)限制从属性说的修正限制从属性说,以正犯与共犯之间在违法性上连带(违法的连带性)为根据,认为正犯违法时共犯也必定违法。
但是,本来违法性应当对各个行为的客观面和主观面进行判断,认为正犯违法共犯也违法的所谓违法的连带性本身就有问题。
还有,按照限制从属性说,共犯是以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引起法益侵害的结果作为处罚根据的,所以,对于共犯的成立来说,重要的是两点:
一是以他人的犯罪意思或者规范的障碍为媒介;
二是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引起法益侵害或者危险的结果。
因此,即使正犯行为该当构成要件而不违法,如果间接正犯成立的话,作为共犯不违法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共犯成立的前提,并不以正犯行为违法为必要。
这意味着,过去的限制从属性说失去了根据。
但是,根据共犯的处罚根据,即共犯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引起法益侵害或者危险来看,共犯成立要件必须是正犯实施了实行行为从而导致了法益侵害或者危险。
这意味着共犯仅从属于正犯的实行行为和法益侵害、危险。
”[8]在笔者看来,大谷实教授无非是将正犯的违法性偷换成了“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导致法益侵害或者危险”,从而提出共犯无需从属于正犯的违法性,只需从属于正犯对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威胁的实行行为即可。
如果要概括的话,可将大谷实教授的主张归纳为“侵害、威胁法益的实行行为从属性说”。
该说明显存在两点疑问:
一是,这种侵害、威胁法益的正犯的实行行为与正犯的违法性未必存在本质的不同;
二是,若认为“实行行为”是裸的概念,即最小从属说所宣称的仅属于该当构成要件的未必违法的行为,则明显有悖通说所指称的“实行行为是指对法益具有现实的紧迫的危险性的行为”,也违背大谷实教授本人关于实行行为的主张,即“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必须具有实现构成要件的现实的危险性,在形式犯或者抽象危险犯的场合,由于没有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现实的危险性,所以不能谓之实行行为。
”[9]显然,大谷实教授本人也认为实行行为必须是能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现实的危险性的行为,这其实就是正犯行为的违法性。
既然如此,为了承认部分情况下违法的相对性的存在,而否定限制从属说进而提出所谓实行行为从属,实在是没有必要。
如下所述,承认部分情况下的违法的相对性,这是德、日当今绝对多数说的观点,但这并不影响仍维持着限制从属性说的通说立场。
王文认为大谷实教授事实上也赞同最小从属性说,但从上述引述来看,并看不出所谓“大谷实则以违法二元论作为其理论根据事实上也采取此说”。
从上述所谓最小从属性说支持者的主张来看,所谓最小从属性说的合理性,无非是部分情况下违法的相对性的存在。
但是,这些学者基本上均认为所谓违法的相对性只属于例外的情况,因而未必是原则上否定限制从属性说。
而且,即便或明确或模糊地支持最小从属性说,这些学者却又众口一词地认为,并非教唆、帮助合法行为的都要作为教唆犯、帮助犯进行处罚,这无疑暴露了最小从属性说在共犯处罚范围上的不明确性。
其次,部分承认违法的相对性并非一定要抛弃限制从属性说而改采最小从属性说。
王文中高频率出现的一个词是所谓违法的相对性。
其实,即使是采用限制从属性说的通说也未必完全否认违法的相对性。
仅就正犯与共犯关系而言(共犯从属性程度讨论的也是共犯与正犯的关系),所谓违法的相对性无非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正犯违法而共犯合法;
二是正犯合法而共犯违法。
关于第一种情形,主张限制从属性说的山口厚教授认为,“所谓的违法的连带性,是指对于正犯行为该当构成要件而且违法的肯定,只是共犯充足了构成要件要素的前提,承认了共犯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共犯(教唆、帮助)行为就违法,这乃不言自明的道理。
另外,与‘责任是个别的’一样,违法并不总是连带的(过去所谓绝对的违法的连带性的观念,现在不可能得到承认)。
”关于第二种情形,山口教授认为,“教唆、帮助是‘二次的责任’类型,在正犯行为阻却违法性的场合,就不存在介入刑法进行阻止的事态,追究背后者的刑事责任就不正当,应当否定教唆、帮助犯的成立。
例如,对于警察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教唆、帮助的,不成立共犯。
这意味着,限制从属性说是妥当的(在这种场合主张成立教唆、帮助的最小从属性说不妥当)。
”[10]可见,山口教授认为,在正犯行为违法的场合,虽然共犯原则上连带地违法,但在共犯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时,仍然可以否定违法的连带性。
在正犯行为存在违法阻却事由的场合,由于不存在刑法介入的必要,应否定作为“二次的责任”类型的共犯的成立。
从共犯的处罚根据看,彻底坚持违法的连带性而根本否认违法的相对性的,只有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和因果共犯论中的修正惹起说。
因为,责任共犯论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诱使正犯堕落从而陷入罪责与刑罚,所以,既然正犯违法,共犯当然也违法。
[11]违法共犯论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使正犯实施了违法行为。
承认绝对的违法的连带性是违法共犯论的当然结论。
[12]修正惹起说认为,共犯违法是从正犯违法行为引申出来的,故完全从属于正犯的违法。
[13]承认绝对的违法的连带性正是修正惹起说的特色,也是其软肋。
承认绝对的违法的连带性的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以及修正惹起说现在都几乎没有学者支持。
可以说,在共犯的处罚根据问题上,现在基本上是因果共犯论中的纯粹惹起说与混合惹起说之间的争论。
纯粹惹起说认为,对共犯的违法应进行独立的判断,承认彻底的违法的相对性,根本否认违法的连带性。
[14]而混合惹起说认为,正犯违法只是共犯违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共犯的违法应从正犯违法和共犯本身的违法两方面进行把握。
混合惹起说是纯粹惹起说与修正惹起说的折中,既部分承认违法的连带性,又部分承认违法的相对性。
混合惹起说因为既克服了纯粹惹起说彻底的违法的相对性的主张的缺陷,又克服了修正惹起说绝对的违法的连带性主张的不足,从而使共犯的处罚范围适中,现在已成为德国、日本的多数说。
[15]
可见,从共犯处罚根据上看,现在的多数说都承认违法的相对性,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
所以,以违法的相对性为由主张应采最小从属性说,现在看来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换言之,是否承认违法的相对性与是采限制从属性说还是最小从属性说,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硬性地将其捆绑在一起,不仅对得出正确的结论无益,而且使得要素从属性问题的讨论人为地复杂化。
王文还提到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争论。
[16]其实,采取何种从属性说与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之争基本上没有关系。
因为,众所周知,大谷实教授自称是二元论主张者,王文认为他事实上采最小从属性说,而平野龙一与前田雅英是公认的结果无价值一元论的坚定的支持者。
此外,彻底的结果无价值一元论者山口厚教授却坚决主张限制从属性说,而且,通常认为是行为无价值论者或者至少是二元论者的团藤重光、大塚仁、福田平等教授却与山口厚教授同属限制从属性说的阵营。
最后,最小从属性说因在共犯的处罚范围上缺乏明确性,其结果是更利于被告,更不利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王文认为采极端从属性说“也不无扩大正犯成立范围、置被告人于不利益之虞,如此,也有违‘存疑从无’这一刑事审判的‘金科铁律’”[17].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最小从属性说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文在结语中指出:
“如果借鉴日本的共犯从属性理论,倡导最小从属性说,可以更加明确共犯的成立条件。
”[18]笔者对此深表怀疑。
如前所述,几乎每位最小从属性说的所谓支持者,均一方面认为,只要正犯行为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即可,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并不是参与正犯的阻却违法性的行为全都要作为教唆犯、帮助犯进行处罚。
王文也认为,“教唆他人实施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时,尽管正犯阻却违法性,但其实行行为仍产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教唆人应从属于此实行行为,原则上仍应构成教唆犯,至于是否值得处罚,则另当别论。
”[19]这让人很纳闷:
他人正当防卫时你在旁边吆喝,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你在旁边喝采,原则上都可以将你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绳之以法,至于抓不抓你,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正如前述山口厚教授所指出的,在正犯行为阻却违法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刑法介入进行阻止的事态,本属于“二次的责任”类型的教唆犯、帮助犯根本就不成立。
再说,上述教唆实施合法行为的事例,就是凭普通百姓的一般法感觉,也不会认为成立教唆犯、帮助犯。
对于本文开头的案例一,王文认为,“因Z具有防卫的意思可构成正当防卫阻却违法性,而X并无防卫的意思不能构成正当防卫,其行为并不因Z不具有违法性而随之丧失违法性,因而正犯合法并不必然带动共犯合法。
”[20]其实,正如学者所言,“甲诱导X对乙进行不法伤害,乙正当防卫杀害了X.乙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但甲不成立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
因为在本例中,只能认定X支配了犯罪事实,而不是甲支配了犯罪事实。
但由于甲教唆X实施不法侵害行为,故甲仅针对X成立教唆犯。
”笔者表示赞成。
在案例一中,X的过错并在于唆使了Z正当防卫,而是在于教唆Y去杀Z,这里要讨论的是应将X的教唆行为评价为对Y的故意杀人行为的教唆犯还是单独评价为间接正犯的问题。
而要成立间接正犯,德国的通说认为,行为人应对整个犯罪过程存在优越的意思支配。
所谓意思支配,是指间接正犯者依其幕后地位的优越的意思(verlegenderWille)支配事件的过程(Geschehen),而含有犯罪支配的内涵。
[21]在本案中,Y是否接受教唆,接受教唆后怎么干,完全由Y的意思自由决定,所以,很难肯定X支配了犯罪过程,只能将其评价为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
对于案例二,王文认为,“在此案中,丙的行为尽管客观上起到了正当防卫的效果,但并无防卫的意思,其行为当然具有违法性,而丙的违法性显然并不能连带作用于甲,并不能由此认定甲构成杀人罪的教唆犯。
因为,甲虽客观参与了丙的犯罪行为,但就其实质而言,甲的行为仍属于‘面对急迫不正的侵害,为了防卫自己或他人的权利,而不得已实施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因而并不具有违法性。
由此可见,违法性及其阻却事由均具有相对性,成立共犯也就并非一定以正犯的违法性为要件,因而并非不可采取最小从属性说。
”[22]按照王文的说法,若丙有防卫的意思则构成正当防卫,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对于甲也同样,如果有防卫的意思则构成正当防卫,若甲唆使丙杀死乙,丙正好发现了乙向其扑来,于是出于所谓防卫的意思杀死了乙,丙因具有防卫的意思而没有“违法性”,而甲因为没有防卫的意思所以具有“违法性”而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
这应该是王文的当然结论。
但笔者看不出前后两种情形有什么不同,要说不同的话,仅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防卫的意思。
因此,王文所称的违法性无非就是所谓主观的违法性,这是彻底的行为无价值的观点,甚至就是心情刑法的体现。
[23]笔者认为,由于丙的行为客观上没有法益侵害的结果,所以丙的行为原本就没有违法性,对于原本就没有违法性的行为的参与也就无所谓违法性连带的问题。
按照王文的逻辑,对于案例三,王文大概会得出甲构成故意杀人罪的结论。
原因就在于王文所反复主张的,在制造了“利益纠葛状态”时,[24]即使丙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毕竟客观上造成了抢劫犯乙的鲜活的生命的丧失,这也属于一种“法益侵害”。
因为王文认为,“根据最小从属性说,医生的外科手术行为、家长的惩戒行为在‘形式上’已经伤害到患者、子女,已属于实行行为,只是因属于正当职务行为、具有社会相当性才‘实质上’阻却违法性;
同样,也应单独评价教唆人的教唆行为,通过认定其具有社会相当性而阻却违法性,并非一定构成教唆‘犯’,最终结论与限制从属性说并无不同。
”[25]按照这种逻辑,教师教育学生恐怕也是对学生进行了‘精神’伤害;
医生将患者脑袋中的恶性肿瘤取出来,也是一种“伤害”;
理发也是一种伤害,因为破坏了他人身体的完整性。
这种认为正当行为形式上也是有害的观点,正好是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一直以来所津津乐道的观点:
“正当行为,是指客观上造成一定损害结果,形式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但实质上既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法执行职务、正当冒险行为。
”[26]这种观点是东施效颦,完全照搬了与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存在根本性差异的德、日的相关理论。
正当防卫等正当行为之所以不构成犯罪的根本原因:
一是没有主观罪过,二是没有对法益具有现实的紧迫危险性的实行行为。
否则,我们若说,依法执行死刑的法警在故意杀人,警察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是在实施非法拘禁,税务人员强制征税是在实施抢劫,等等,想必不会有人认为这不荒谬。
从王文倡导最小从属性的主张来看,间接正犯这个概念似乎很不受欢迎。
王文认为,“……第三,运用教唆犯这一‘法律概念’即可解决此类问题,本无需适用间接正犯这一‘学理概念’;
第四,利用人是出于教唆的意思实施利用行为,并无亲自实施犯罪这一正犯意思,若将此类行为一律认定为间接正犯,无疑是将本可认定为教唆犯的行为也认定为正犯,既难言符合间接正犯的成立条件,也不无扩大正犯成立范围、置被告人于不利益之虞,如此,也有违‘存疑从无’这一刑事审判的‘金科铁律’。
进一步而言,若按照极端从属性说的观点,以利用人的行为作为间接正犯实行的着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未遂的处罚时点过早这一问题。
”[27]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存在重大疑问:
一是,间接正犯系学理概念本身并不能成为排斥其适用的理由。
不作为在我国也是学理概念,但我们能说尽量少适用吗?
间接正犯在德国刑法中虽是法定概念,但也只是在第25条中简单规定“通过他人实施犯罪的”。
在日本,间接正犯也只是个学理概念,但这丝毫不妨害理论和实务部门反复适用。
尽管日本在改正刑法草案中第26条规定“利用非正犯之他人实行犯罪的,也是正犯”,但对此草案规定,日本学者却认为,“把被利用者限定为‘非正犯之他人’,则在立法上完全否定了诸如‘正犯背后的正犯’这种法律形态存在的可能性。
此外,这种规定还可能阻碍有关间接正犯学说的发展。
因为,间接正犯是直接正犯的例外法律形态,一旦将其立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