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地板下的小人》Word下载.docx
《整理《地板下的小人》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整理《地板下的小人》Word下载.docx(6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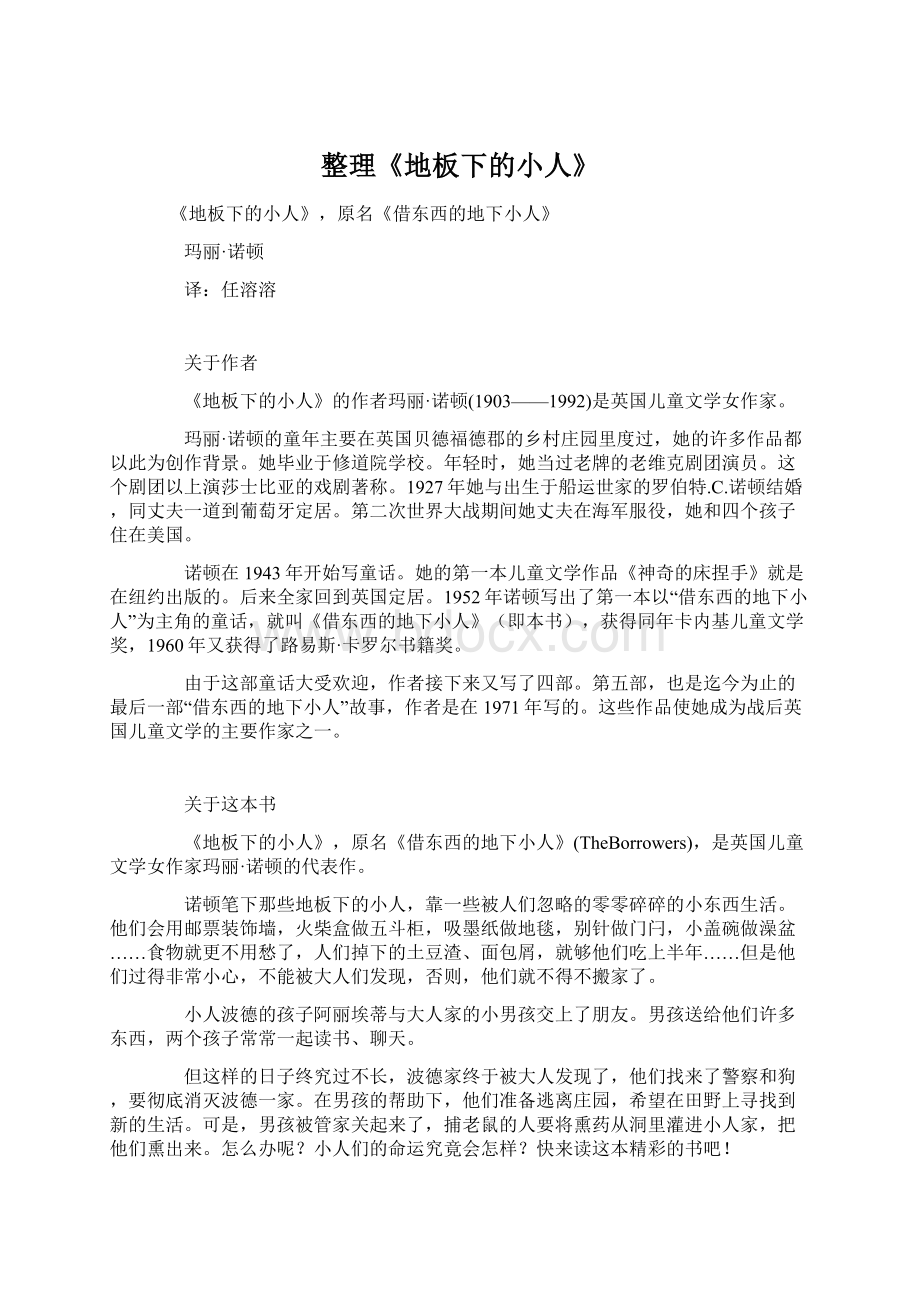
第一章 听梅太太讲小人
关于他们,是梅太太第一个告诉我的。
不对,她告诉的不是我。
那怎么会是我呢——那是个又野、又邋遢、又任性的小女孩,用生气的眼睛看人,据说还嘎吱嘎吱地咬牙。
凯特,应该叫她这个名字。
对,就是这个女孩——凯特。
反正叫她什么名字也没有多大关系:
她就这样跑到故事里来了。
在伦敦,梅太太在凯特的爸爸和妈妈的房子里住着两个房间,我想她是他们的一位亲戚吧。
她的卧室在二楼,她的起居室在叫做“早餐室”的房间。
早晨当阳光射在烤面包和果酱上时,早餐室是很不错的,但到下午光线暗了,房间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暗淡银光,就有一种忧郁的气氛,不过凯特是个孩子,她喜欢这种气氛。
在吃下午茶点前,她经常到梅太太的起居室里来,梅太太教她钩花边。
梅太太岁数大了,关节不灵活,她这个人——也不好说是古板,但的确是说一不二。
凯特和梅太太在一起时从不“撒野”,也不邋遢和任性。
除了钩织以外,梅太太还教她许多东西:
怎样把毛线绕成蛋形的球啦;
怎样织补啦;
怎样清理抽屉,并在东西上面盖一张薄纸挡住灰尘啦。
“你为什么这样一声不响啊,孩子?
”有一天凯特弯着腰,呆呆地坐在垫子上时,梅太太问她说,“你怎么啦?
你丢掉舌头了吗?
”
“不是的,”凯特拉着她的鞋扣说,“我丢掉钩针了……”她们正在做一条床罩……把一个个毛线钩的方块缝在一起,还差三十来个方块。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把它放在哪里,”她急急忙忙说下去,“就放在我床边书柜的底下一层,可是不见了。
“底下一层?
”梅太太重复说了一遍,她自己的钩针在火光中不停地闪烁,“靠近地板吗?
“是的,”凯特说,“但是我把地板看过了。
地毯下面也看过了。
到处都看过了。
毛线倒还在那里。
就在我放下的地方。
“噢,天啊,”梅太太轻轻叫了一声,“不要是他们也在这房子里!
“他们是谁?
”凯特问道。
“借东西的小人啊!
”梅太太说,在暗淡的光线中,她似乎在微笑。
凯特有点惊慌地看着她。
“有这样的人吗?
”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什么样的人?
凯特眨着她的眼皮:
“住在别人房子里的小人……专门借走别人东西的!
梅太太放下她手里的活儿:
“你说呢?
“我不知道,”凯特说着把眼光移开,使劲拉她的鞋扣,“这是不可能有的。
不过,”她抬起她的头,“有时候我又觉得一定有。
“为什么你觉得一定有?
”梅太太问道。
“因为有许多东西不见了。
比方说别针吧。
工厂没完没了地生产别针,每天人们买别针,然而就在你要用别针的时候,别针却没有了。
它们都在哪里呢?
就在要用的时候,它们都上哪里去了?
再拿缝衣针来说吧,”她说下去,“我妈妈买了那么多缝衣针——至少有几百枚——它们不可能满屋子都是。
“对,不可能满屋子都是。
”梅太太同意说。
“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们一直在买。
买了又买。
例如铅笔、火柴、火漆、发卡、图画钉、顶针……”
“还有帽针,”梅太太插进来说,“吸墨水纸。
“对,吸墨水纸,”凯特同意说,“但不是帽针。
“这你就错了,”梅太太说着,又把活儿拿起来,“我说帽针是有道理的。
凯特望着她。
“有道理?
”她重复说了一遍,“我是说——有什么道理?
“这个嘛,确实地说是有两个道理。
帽针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武器,而且,”梅太太忽然笑起来,“不过这听起来太荒谬了,再说,”她犹豫了一下,“这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可是跟我讲讲吧,”凯特说,“跟我讲讲你知道的关于帽针的事。
你见过吗?
梅太太用惊异的眼光看看她,“什么,当然见过……”她开始说。
“我说的不足帽针,”凯特很急地叫道,“我说的是你所说的那种人——那种借东西的小人!
梅太太深深吸了口气。
“这倒没有,”她马上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有人见过,”凯特叫道,“你知道的。
我看得出来你知道!
“嘘,”梅太太说,“用不着大喊大叫!
”她低下头来看凯特仰起来的脸,随后微笑着把目光移向远处。
“我有一个弟弟……”她犹豫地说起来。
凯特跪在坐垫上,“他看见他们了?
“我小知道,”梅太太摇着头说,“我根本不知道!
”她抹平她膝盖上的活儿。
“他是个吹牛大王,给我们,就是我姐姐和我,讲了那么多不可能有的事情。
后来,”她平静地说,“这已经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他在西北边境阵亡了。
他成为他那个团的上校。
他们说他足英勇牺牲的……”
“你只有这位弟弟吗?
“是的,他是我们的小弟弟。
我想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想了一下,仍旧暗自微笑,“对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这种不可能有的事情,这种奇怪的幻想。
我想他是出于妒忌,因为我们比他大——我们比他会看书。
他想使我们看得起他,也许是想使我们大吃一惊。
不过,”她看着壁炉的火,“他这个人也有点特别——也许因为我们是在印度那些神秘事物、魔法和传奇之巾长大的吧——我们总觉得他能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在戏弄我们,但有时候……对了,我们可说不准……”她俯身向前,照她的老样子十分干净地刷掉炉栅下一蓬火灰,接着拿着刷子,重新看着炉火。
“他不很强壮,第一次从印度回国就害了风湿病,缺了整整一学期课,送到乡下去休养,住在一位老姑妈家里。
后来我自己也去了。
这是座很奇怪的古宅……”她把刷子挂回铜钩上,用手帕擦干净双手,接着把她的活儿捡起来。
“最好把灯点亮。
”她说。
“等一等吧,”凯特靠过来求她,“请你讲下去。
请你告诉我……”
“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了。
“不,你还没有。
这座古宅……他是在那里看见了……他真看见了吗……”
梅太太大笑。
“他在那里看见了借东西的小人?
是的,他正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要我们相信。
而且,他好像不仅是看见了他们,还跟他们很熟,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分子,事实上,差不多可以说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借东西的人……”
“噢,请一定告诉我。
谢谢你。
试试看把事情回想起来吧。
从头讲起!
“我都记得,”梅太太说,“真奇怪,比许多发生过的真实事情记得还要清楚。
也许它也是件真实的事情,只是我不知道。
你瞧,重返印度的时候,我的弟弟和我在船上共住一个房间,我的姐姐通常和我们的保姆睡在一起。
在那几个极其炎热的夜里,我们老是睡不着,我的弟弟会接连几个钟头讲那个讲了又讲的老话题,把细节讲了一遍又一遍——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做些什么事,以及……”
“他们?
他们到底是谁?
“是妈妈霍米莉、爸爸波德和小阿丽埃蒂。
“波德?
“对,连他们的名字也不大对头。
他们自以为有了自己的名字——但和我们人类的名字大为两样——一听就知道,它们也是借来的,连亨德列里叔叔和埃格尔蒂娜的名字也是如此。
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借来的,根本没有一样东西是他们自己的。
一样也没有。
除此以外,我弟弟说他们非常敏感和自负,白以为拥有整个世界。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认为人类只是创造出来干脏活的——做他们的巨人奴隶。
至少在他们之间是这么说的。
不过我弟弟说,他认为他们在地底下都担惊受怕。
我弟弟想,正因为他们担惊受怕,所以才长得那么小。
而且他们一代比一代小,也越来越隐蔽。
古时候在英国的一些地区,我们的祖先似乎还公开提起过这些‘小人’。
“是的,”凯特说,“我知道。
“而现在,依我想,”梅太太慢慢地说下去,“如果他们还存在,你就只能在乡间一些幽静、偏僻的旧屋里找到他们——在这些旧屋里人们过着刻板的生活。
而这种刻板生活正是他们的保护伞:
因为他们最要紧的是知道哪些房间有人用,什么时候用。
任何地方只要有随随便便的人和没人管的孩子,或者养着什么动物,他们就住不长。
“索菲姑妈的旧屋自然是很理想的——虽然他们中还有人不满意,觉得有点冷,又太空。
我们这位索菲老姑妈由于二十年前一场狩猎事故而终年卧床。
房子里除她以外,别的人就只有烧饭的德赖弗太太和园丁克兰普福尔了,难得还会有个女仆什么的。
我弟弟生风湿病以后到那里去,也长期卧床。
在他到那里的起先几个礼拜,那些借东西的小人并不知道他来了。
“他睡在教室里面一问旧的儿童卧室里。
当时这间教室堆满乱七八糟的破旧东西——皮箱、坏了的缝衣机、写字台、裁缝用的假人、桌了、椅子,还有一架没用的自动钢琴——因为玩这自动钢琴的孩子们,也就是索菲老姑妈的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结了婚、死了或者离开了。
卧室的门对着这间教室,我弟弟躺在他的床上,能够看到教室壁炉上面挂着的滑铁卢大战①油画,角落里的一个玻璃门柜子,柜子里的钩子上和架子上陈列着一套玩具茶具——古色古香,十分精致。
夜里教室的门如果开着,他可以一直看到点着灯的过道通到楼梯口。
每天天黑下来时,他看见德赖弗太太在楼梯口出现就感到宽慰。
德赖弗太太总是端着一盘东西在过道上走过,给索菲姑妈端去饼干和一瓶白葡萄酒。
德赖弗太太下楼前,又总是在过道上停一下,把煤气灯旋小,让它只发出一点暗淡的蓝光。
然后他看着她噔噔噔下楼,在楼梯栏杆间慢慢地一点点消失不见。
“过道底下是门厅,门厅里有一座时钟,夜间他能听到它当当地报时。
这是一座老爷时钟,很旧了。
利顿·
巴扎德的弗里思先生每个月来给这时钟上发条,就像他的父亲在他以前、他的叔公在他的父亲以前那样。
据弗里思先生所知,这个时钟已有整整八十年没有停过,而在此以前,又不知有多少年从未停过。
了不起的是,它肯定从来没有移动过。
它贴近护壁板,周围地上的石板洗得那么勤,凶此里面高出来了,我弟弟是这么说的。
“在这时钟底下,在护壁板脚下有一个洞……”
①滑铁卢是比利时的一个镇,1815年拿破仑在这里打了大败仗。
第二章 波德一家
这是波德的洞——他的城堡的门户,他家的大门。
他的家并不在那时钟附近:
可以说是离它远着呢。
从洞口到他家,可得要走好多好多步积满灰尘的黑暗过道,过道上有一道道木门和铁门防御老鼠。
波德用各种东西做他的门——折叠干酪切削器的铁片啦、小钱盒带铰链的盖啦、纱罩和苍蝇拍的铁丝网啦等等。
“我不是怕老鼠,”他的太太霍米莉会说,“但我受不了那气味。
”他们的女儿小阿丽埃蒂想要一只还没睁开眼睛的小老鼠来亲手养大,“就像埃格尔蒂娜那样”,但是没有成功。
霍米莉会弄得锅盖乒乓响,对她叫道:
“你只要瞧瞧埃格尔蒂娜后来出了什么事?
”“埃格尔蒂娜,”阿丽埃蒂会问,“埃格尔蒂娜后来出什么事了?
”但没有人肯说。
只有波德一个人认识路,能穿过那些有趣的通道来到时钟底下的洞口。
也只有波德一个人能打开一扇扇门。
门上有用发卡和别针做的复杂机关,知道其中秘密的就只有他。
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厨房底下的住所里过着更安全隐蔽的生活,远远避开上面那座可怕房子里的种种危险。
不过就在上面那间厨房的地板下面一点,砖墙上有一个通气格栅,阿丽埃蒂透过它可以看到花园——一小段石子路和一个草墩,在这草墩上,春天盛开藏红花:
从一棵看不见的树上飘下小花;
接着一丛杜鹃花开花;
小鸟飞来——啄食,追逐,有时候打架。
“你把时间都浪费在看那些鸟上面了,”霍米莉会说,“这样有事情你就来不及做。
在我小时候长大的房子里,”霍米莉说下去,“那儿没有格栅,反而过得更快活些。
好,去把土豆给我拿来。
正是这一天,阿丽埃蒂踢着土豆,让它在前面滚,从贮藏窒沿楼上地板下满是灰尘的窄通道走。
她生气地用力踢土豆,因此土豆滚得很快,滚进他们的厨房,霍米莉正在炉子上弯着腰。
“你又来了,”霍米莉生气地转过身来对阿丽埃蒂叫道,“差点儿把我撞到汤里去。
我说‘把土豆给我拿来’,可不是说整个土豆。
你不能把剪刀拿去切下一块拿来吗?
“我不知道你要多少。
”阿丽埃蒂咕噜了一声,这时霍米莉哼哼哈哈地从墙上拿下钉子上挂的半把剪刀,插进土豆皮里。
“你把这土豆糟蹋了,”霍米莉嘟哝说,“切开以后,就不能再在灰尘中滚同去了。
“噢,这有什么?
”阿丽埃蒂说,“那里土豆多着呢。
“说得倒好:
多着呢。
你明白吗,”霍米莉放下半把剪刀,严肃地说下去,“你可怜的爸爸每次借一个土豆都要冒生命危险?
“我是说,”阿丽埃蒂说,“我们的贮藏室里多着呢。
“好了,现在别挡着我的路,”霍米莉说着又在周围忙碌起来,“不管怎么说,让我把晚饭做好。
阿丽埃蒂已经穿过开着的门走进起居室——壁炉已经生起火,房间里看起来又亮又舒服。
霍米莉对她这间起居室十分自豪:
墙上糊着从字纸篓里借来的旧信,按一行行字撕成一长条一长条,垂直地从地板贴到天花板。
墙上挂着几种颜色的同一幅姑娘时代的维多利亚女王肖像,它们都是邮票,是波德几年前从楼上起居室写字台上的邮票盒里借来的。
这房间里有一个小漆盒,里面塞满布,盖子打开,他们用它做高背长椅:
那常用的家具——一个五斗柜,是用火柴盒做的。
一张铺着红天鹅绒台布的圆桌,是波德用一个药丸盒的木头底,下面支着国际象棋棋子马的底座做成的——这件事曾在楼上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因为索菲姑妈的大儿子回家暂住,请教区牧师来吃晚饭,饭后准备下棋,结果缺了棋子下不成。
女仆罗萨·
皮克哈切特为此被辞退。
她走后不久,发现还不见了别的东西,从那时候起,德赖弗太太总管一切。
马那只棋子——应该说是它的半身像——如今站在角落里一根柱子上,看来非常神气,使房间有一种只有雕像能给予的气氛。
壁炉旁边,在一个倾斜的木头书柜里放着阿丽埃蒂的藏书。
这是一套维多利亚时代喜欢印的微型书,但对阿丽埃蒂来说,它们就像教堂的巨型《圣经》那么大。
这些书中有布赖斯版《大拇指汤姆世界地名词典》,包括最后的统计表;
有布赖斯版《大拇指汤姆词典》,包括科学、哲学、文学和技术的词条;
有布赖斯版《大拇指汤姆本莎士比亚喜剧集》,包括一篇评介作者的序;
还有一本全是空白页,叫做《备忘录》;
最后但不是最薄的,是阿丽埃蒂最心爱的布赖斯版《大拇指汤姆格言日记》,每天有一句格言。
这本日记有一篇代前言,是一个叫大拇指汤姆将军的小人的传记,他娶了一个姑娘叫默西·
拉维妮亚·
邦普。
本子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他们伉俪和他们的马车,马车的几匹小马和老鼠一样小。
阿丽埃蒂不是一个愚蠢的姑娘。
她知道马不可能和老鼠一样小,但她不理解,大拇指汤姆只有两英尺高,但对一个借东西的小人来说,他就像一个巨人了。
阿丽埃蒂从这些书里学会了阅读,靠抄墙上那些字学会了书写。
尽管如此,她并不一直记日记,她只是经常把那本日记拿出来,因为那些格言有时候能使她得到安慰。
今天这句格言就是:
“知足常乐。
”下面有一行:
“嘉德勋位始于1348年。
”她把这本日记带到壁炉旁边,坐下来,双脚放在壁炉铁架上面。
“你在那里干什么,阿丽埃蒂?
”霍米莉从厨房叫她。
“写日记。
“噢。
”霍米莉叫了一声。
“你叫我干什么?
”阿丽埃蒂问道。
她觉得很保险,霍米莉喜欢她写,霍米莉鼓励任何能提高文化的事。
霍米莉本人是个可怜的文肓,连字母也不认识。
“没事,没事,”霍米莉生气地说,乓的一声挪开锅盖,“待会儿再说吧。
阿丽埃蒂拿出她的铅笔。
这是支白色的小铅笔,拴着一根丝线,是从一张舞蹈节目单上扯下来的,虽然如此,到了阿丽埃蒂的手里,这小铅笔就像是一根擀面杖了。
“阿丽埃蒂!
”霍米莉从厨房里又叫起来。
“什么事?
“在炉火上扔点什么好吗?
阿丽埃蒂用足力气拿起膝盖上的大书,让它竖立在地板上,他们把燃料——煤屑和弄碎的蜡烛油——放在一个白镴芥末瓶里,用羹匙舀出来。
阿丽埃蒂只舀了几粒,翘起芥末羹匙撒在火上,不去盖没火焰。
接着她站在那里取暖。
这是一个可爱的壁炉,是阿丽埃蒂的祖父用马厩一个旧苹果汁榨取器的嵌齿轮做的。
嵌齿轮的辐呈星状地向外张开,火位于中心。
上面是个烟囱,用一个颠倒的小铜漏斗做成。
这小漏斗本来是一盏旧火油灯上的,这火油灯往日放在上面门厅的桌子上。
一些管子把烟从漏斗口送到上面厨房烟道里。
火用火柴棒点着,加上煤屑,火点起来铁就变热,霍米莉在铁辐上用银针箍炖汤,阿丽埃蒂则在上面烤食品。
冬天晚上过得多么惬意呀。
阿丽埃蒂把她的大书放在膝盖上,有时候读出声来;
波德在那里楦他的鞋(他是一位鞋匠,用小羊皮手套改做带扣靴子——不过真可惜,他只给他的家里人做);
霍米莉终于忙完家务,坐下来织毛线。
霍米莉用大头针,有时候用织补针给大家织毛线衣和袜子。
在她的椅子旁边,丝线团或者棉纱线团有桌子高,有时候她拉得太用力,线团会滚出开着的门,滚到外面都是灰尘的过道上去,阿丽埃蒂便被派去追它,把它滚回来时一路重新绕好。
起居室的地板上铺着厚厚的红色吸墨水纸,又温暖又舒服,还能吸水。
霍米莉只要得到新的吸墨水纸就换,不过自从索菲姑妈卧床以来,德赖弗太太难得想到吸墨水纸,除非忽然来了客人。
霍米莉喜欢不用洗的东西,因为在地底下晾干东西是件麻烦事。
水他们可多的是,热水冷水都有,这得谢谢波德爸爸,他用管子接上了上面厨房的锅炉。
他们在小碗里洗澡,这小盖碗原先是装鹅肝酱的。
洗完澡出来得把碗盖重新盖上,免得人们把东两放进去。
肥皂也有一大块,挂在洗涤处一枚钉子上,一条条切下来用。
霍米莉喜欢用煤焦油味的,但波德和阿丽埃蒂愿意用檀香的。
“你现在又在干什么啦,阿丽埃蒂?
”霍米莉从厨房里叫起来。
“还在写日记。
阿丽埃蒂又一次拿起大书,放回她的膝盖上。
她舔她那支大铅笔的笔尖,沉思着凝视了一阵。
她允许自己(当她的确想起什么东西要写时)写上一小行,因为她毫不怀疑,她再也不会有第二本日记了,如果一页写二十行,这本日记她就能用上二十年。
她已经写了近两年,而今天、3月22日,她读去年记的事:
“妈妈发脾气。
”她再想了一阵,最后在“妈妈”下面写上表示“同上”的符号“踁”,在“发脾气”下面写上“担心”。
“你说你在干什么,阿丽埃蒂?
阿丽埃蒂合上日记本。
“什么也不干。
“那就来帮我切洋葱,做个乖孩子。
你的爸爸今天晚上回来晚了……”
第三章 等爸爸回家
阿丽埃蒂叹着气把日记本放好,走进厨房。
她从霍米莉手里接过一圈洋葱,轻轻套在脖子上,去找一块剃刀刀片。
“说真的,阿丽埃蒂,”霍米莉叫起来,“你不该把它套在你干净的毛线衫上!
你想闻起来像一个泔水桶吗?
来,把剪刀拿去……”
阿丽埃蒂让那圈洋葱落到脚下,跨过它走出来,就像它是个孩子玩的铁环,然后动手把它切成片。
“你的爸爸回家晚了,”霍米莉又嘀咕了一遍,“可以说都怪我。
噢,天啊,噢,天啊,我真不该……”
“不该什么?
”阿丽埃蒂眼泪汪汪地问道。
她大声吸鼻子,想用袖子去擦。
霍米莉用手把落下来的一小圈头发拨回去。
她心不在焉地看着阿丽埃蒂。
“都为你打破了那个茶杯。
“但那是好多日子以前的事了……”阿丽埃蒂眨着眼睛开始要说,又吸了一下鼻子。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不是你的事。
这是我的事。
这不关那只打破的茶杯。
这和我对你爸爸说的话有关。
“你对他说什么了?
“这个嘛,我只是说……我说那套茶杯还有……在上面老地方,在教室角落的柜子里。
“我看不出你的话有什么不对。
”阿丽埃蒂一面说,一而让一片片洋葱落到汤里去。
“但那柜子很高,”霍米莉叫道,“得沿着窗帘爬上去。
你的爸爸上岁数了……”她一屁股坐在香槟酒铁皮帽软木塞上,“噢,阿丽埃蒂,我没有提到它就好了!
“不要担心,”阿丽埃蒂说,“爸爸会量力而行的。
”她从热水管口拔出一个香水瓶橡皮塞,让几滴开水落到一个阿司匹林瓶子的铁皮盖里,加上点凉水,开始洗手。
“也许是这样,”霍米莉说,“不过我要再跟你说两句。
茶杯算什么东两!
你那亨德列里叔叔一辈子喝东西只用橡果的壳儿,他可是活得很老很老,还有精力移居到别处。
我的娘家人只用一只骨制小针箍轮流着喝东西。
你只是碰巧有了一只茶杯……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
”阿丽埃蒂说着,在用绷带卷做的毛巾卷上把手擦干。
“我担心那窗帘,”霍米莉叫道,“他上了岁数,爬不上去了——怎么也爬不上!
“他那枚针能帮他爬上去的。
”阿丽埃蒂说。
“他那枚针!
那也是我教他这么办的!
我对他说,拿枚帽针去,在针头上贴上那种印有名字的布带,然后把帽针扔上去钩住窗帘,顺着布带往上爬。
那回是要他到她的卧室借一个绿宝石挂表,好让我看时间烧饭。
”霍米莉的声音开始发抖,“你的妈妈是个坏女人,阿丽埃蒂。
又坏又自私,她就是这么个人!
“你知道怎么办吗?
”阿丽埃蒂忽然叫道。
霍米莉擦掉一滴眼泪。
“不知道,”她声音微弱地说,“怎么办?
“我能够爬上窗帘。
霍米莉站起来,“阿丽埃蒂,你敢说这种风凉话!
“不过我能够!
我能够!
我也能够借东西!
我知道我能够!
“噢!
”霍米莉喘了一口气,“噢,你这坏丫头!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可怕的话来!
”她又在软木塞凳子上缩成一团。
“居然这样!
“好了,妈妈,谢谢你,”阿丽埃蒂求她说,“好了,不要生气了!
“但是你没看见吗,阿丽埃蒂……”霍米莉喘了口气。
她想小出话来说,低头看着桌子,最后才抬起憔悴的脸。
“我可怜的孩子,”她说,“可别这样随便说借东西的事。
你不知道……谢谢天,你永远不会知道,”她把嗓子压低,成了可怕的耳语,“上面是个什么样子……”
阿丽埃蒂不开口,半天才问道:
“是个什么样子呢?
霍米莉用她的围裙擦擦脸,向后抹平她的头发。
“你的亨德列里叔叔,”她开始说,“埃格尔蒂娜的爸爸……”她一下子停了口。
“听!
”她说,“那是什么声音?
一阵轻微的震动在木柴间引起回响——是远处的“喀啦”一声。
“你的爸爸!
”霍米莉叫道,“噢,瞧我这副样子!
梳子在哪里?
他们有一把梳子,是一把18世纪的梳眉毛小银梳,从上面客厅的柜子里借来的。
霍米莉把它插在头发上,擦擦她可怜的发红的眼睛,而当波德走进来时,她微笑着向下抹平她的围裙。
第四章 爸爸被看见了
波德慢步走进来,背着他那个大口袋。
他把他的帽针连同它上面晃来晃去的布带斜靠在墙上。
接着他在厨房桌子当中放下一只玩具茶杯。
“怎么,波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