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文体困境Word文档格式.docx
《沈从文的文体困境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沈从文的文体困境Word文档格式.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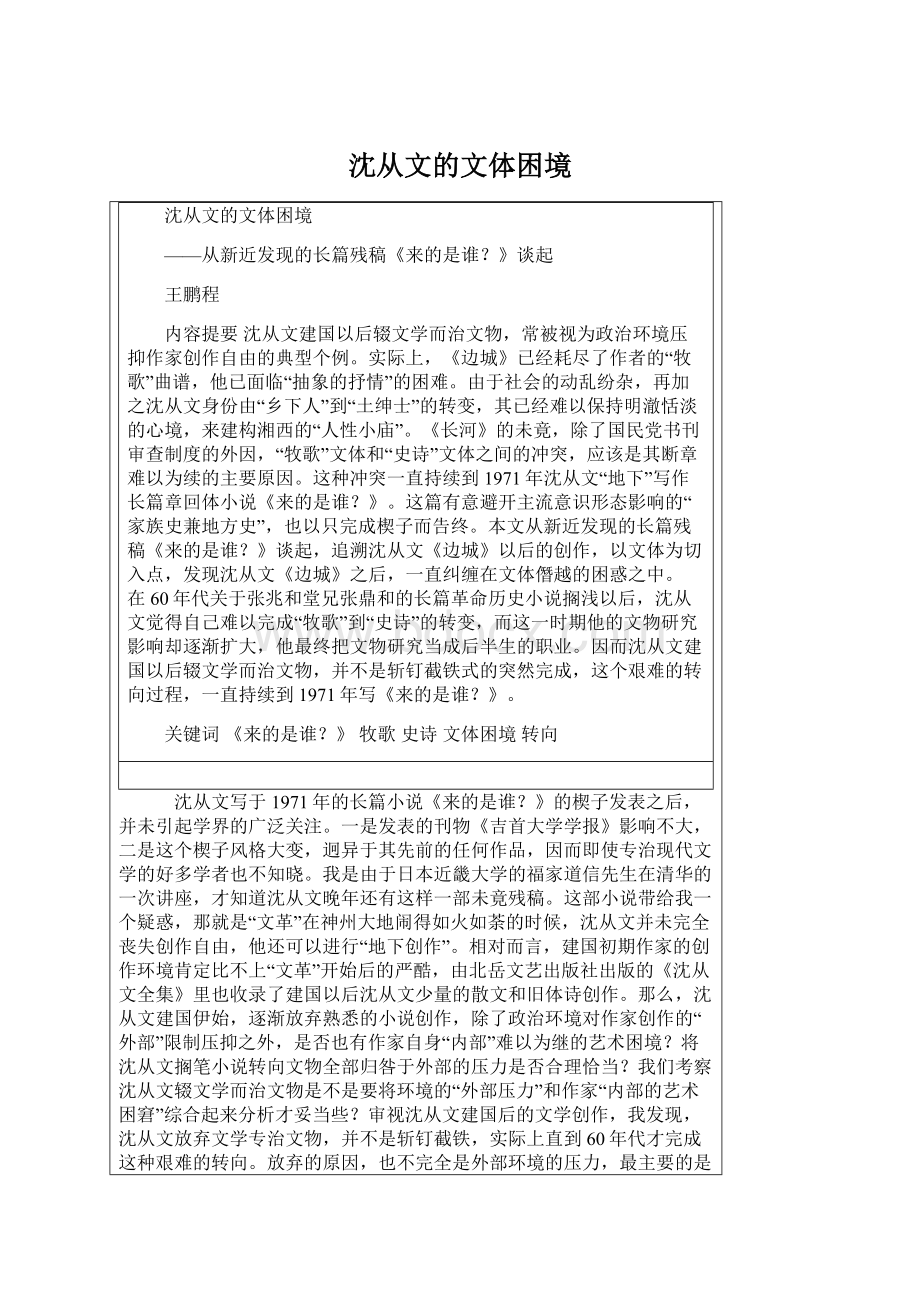
那么,沈从文建国伊始,逐渐放弃熟悉的小说创作,除了政治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外部”限制压抑之外,是否也有作家自身“内部”难以为继的艺术困境?
将沈从文搁笔小说转向文物全部归咎于外部的压力是否合理恰当?
我们考察沈从文辍文学而治文物是不是要将环境的“外部压力”和作家“内部的艺术困窘”综合起来分析才妥当些?
审视沈从文建国后的文学创作,我发现,沈从文放弃文学专治文物,并不是斩钉截铁,实际上直到60年代才完成这种艰难的转向。
放弃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外部环境的压力,最主要的是他擅长的带有牧歌情调的文体,难以适应“时代的抒情”的“革命史诗”文体。
一
》写于1971年,同《长河》一样,这是一部未竟的长篇小说,作者只完成了8000多字的楔子。
1971年6月8日,时在河北磁县1584部队二中队一连二排五班服役的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收到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沈从文的来信,牛皮纸做的信封里塞着《来的是谁?
》的楔子。
黄苗子收藏小说原稿30余年,2006年8月找出归还给黄永玉,2007年1月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第28卷第1期。
根据最近发表的沈
作者简介:
王鹏程(1979—),男,陕西永寿人,陕西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清华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从文1971寄给黄永玉的几封书函得知,《来的是谁?
》是沈从文接受黄永玉的建议之后,撰写的一部带有“家史兼地方志”色彩的小说,为了让“你们(黄永玉)一代和妮妮红红(黄永玉的女儿)等第三代,也知道点‘过去’和怎么样就形成‘当前’,以及明日还可能带来的忧患。
”但这不是小说的重点,小说的宗旨是“将近百年地方的悲剧和近似喜剧的悲剧,因为十分现实,即有近万的家乡人,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死光了。
你我家里都摊了一份。
我们其所以能存在,一半属于自己,一面则近于偶然。
特别是我的存在,好像奇迹!
因为一切学习过程,就近于传奇。
所以你的建议还是对的。
”[1]45小说前五章的大致内容沈从文在此封信件里也作了披露:
“第一章是‘盘古开天地’说起(史书上没提到,而从近年实物出土写下去)。
第二章将是二百年前为什么原因如何建立这个小小石头城,每年除公家‘改土归流’兼并了所有土地,再出租给苗民,到处都设有大仓库收粮。
省里还用十三四万民两经营。
这么小小地方还有个三品官,名叫辰沅永靖兵备道!
兼管辰州、沅州,两府所属十多县!
第三章、四章即叙述这么一个小地方,为什么会出了三四个总督(等于省长),四五个道伊(比专员大)、或者镇守使(等于师长)?
随后还出了个翰林、转而为辛亥后第一任总理。
另外又还出了大约两个进士(比大学毕业难)、四五个拔贡(比专科毕业难)、无数秀才,四五个日本士官生,上十个保定生,许多庙宇、许多祠堂。
第五章叙述辛亥以前社会种种。
假定可写十六章到廿章,前五章这么分配是恰当的。
”[2]45—46
早在抗战结束回北京不久,沈从文初次介绍黄永玉的木刻而写的《一个传奇的本事》一文中,已经谈到了黄永玉本人也不明白的家乡历史和家中情况。
在1979年为这篇随笔补充的“附记”中,沈从文对《一个传奇的本事》进行了说明,“从表面看来,只象‘借题发挥’一种杂乱无章的零星回忆,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纪录。
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
”这篇文章,用沈从文的话说,“以本地历史变化为经,永玉父母个人及一家灾难情形为纬交织而成一个篇章。
用的彩线不过三五种,由于反复错综连续,却形成土家族方格锦纹的效果。
整幅看来,不免有点令人眼目迷乱,不易明确把握它的主题寓意何在。
但是一个不为‘概念’‘公式’所限制的读者,把视界放宽些些,或许将依然可以看出一点个人对于家乡的‘黍离之思’!
”可能正是因为感到这篇短文“令人眼目迷乱,不易明确把握它的主题寓意何在”,“土家族方格锦纹”的效果难以表现出来,凤凰近二百年来复杂纷纭的历史变迁及人事更迭难以装进去,沈从文才听取了黄永玉的建议,撰写带有“家史兼地方志”[3]162—163色彩的《来的是谁?
从前五章的内容以及沈从文写给黄永玉的信来看,《来的是谁?
》是一部关于湘西的“史诗”,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写二百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构架比《长河》更为宏大开阔,无疑是一个很庞大的艺术设想。
小说的楔子写的是:
一九七×
年十一月间,天寒地冻,一个穿着破旧的皮领子大衣,戴着旧式油灰灰的皮耳帽的,身材看起来像南方人,装备看起来又像老北京的老头下了火车,拐进一个小胡同,寻找一个叫张永玉的人。
开门的是一个小姑娘,说没有张永玉这个人。
老头说,那就找张黑蛮。
小姑娘说,也没有张黑蛮。
老头说,那就找张黑妮。
小姑娘也叫黑妮,但不姓张,便说老头找错了,不给开门。
老头说,你们这里不是住的张梅溪吗?
你们不是一家人吗?
深受《沙家浜》中阿庆嫂影响的小姑娘对老头说:
“您找门牌错了,这里住的姓黄,门牌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
”小姑娘并没有开门,老头只得走了。
小姑娘的爸爸和家里其他两人看完电影后归来,小姑娘说了有个奇怪的老头来找。
小姑娘的爸爸琢磨了一会,便和家中人去火车站找那个神秘老头,结果看到一列火车已经驶开,放佛“正有个戴皮帽子、穿皮领子大衣的老头子,在车窗里向她连连招手,一面似乎还大声说,‘张黑妮,张黑妮,再见!
再见!
’”。
小姑娘和爸爸回家之后,在自家信箱里看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
“张永玉同志收”。
信里用淡墨写了五六行小字:
张永玉,你这个聪明人,真是越读《矛盾论》越糊涂,转向反面。
到今为止,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姓什么,妻室儿女也不明白自己姓什么,世界上哪有这种聪明人?
为什么不好好的作点调查研究,或问问有关关系的熟人?
你回家扫墓时,为什么不看看墓碑上写的是什么?
楔子的结尾写道:
姓氏本来近于一个符号,或许可以姓黄,也可以姓张,言之不免话长,要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常言道,无巧不成书,真正巧事还在后头,诗曰:
想知眼前事,得问知情人。
不然真糊涂,懂过一生。
世事皆学问,举措有文章,
一部廿四史,慢慢说端详。
就楔子中出现的人物而言,除过将姓“黄”改为姓“张”,似乎都能和黄永玉家对上号。
黄永玉(1924—)的两个孩子,一个叫黄黑蛮(1952—),一个叫黄黑妮(1956—)。
沈从文曾经谈到黄永玉的故乡“镇筸城”时,谈到“黄”“张”两姓。
他说“镇筸城”原来由“镇打营”和“筸子坪”合成,后改为“凤凰县”。
住在这个小小石头城里的人,“大半是当时的戍卒屯丁,小部分是封建社会放逐贬谪的罪犯(黄家人生时姓‘黄’,死后必改姓‘张’,听老辈说,就是这个原因)。
”[3]153由此看来,沈从文故意混淆生死界限,使小说具有魔幻色彩,实际上源于其家乡的传说。
从楔子也可以看出,《来的是谁?
》的确涉及到黄永玉的家史,但这似乎无关紧要。
正如楔子结尾所说的“姓氏本来近于一个符号,或许可以姓黄,也可以姓张,言之不免话长”。
令人惊诧的是《来的是谁?
》风格。
这篇小说显然是在借鉴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开头也类似与《红楼梦》第一回的“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小说的文体风格俨然不同于《边城》等作品的“抽象的抒情”,而是带有“黑色幽默”的调子,特别注重细节的铺写,又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特点。
小说的开头部分,以巴尔扎克式的笔法,描写了七十年代初期北京的肃杀景象,交代了一个“文革”的故事背景。
时值下班时分,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写到“公鸡”。
一是接客人的人类似与“公鸡”的神态。
更有甚者,从香港、海南岛等南方来北京探亲的来客,“手提竹篮中,间或还回露出个大公鸡头,冠子红红的,眼珠子黄亮亮的,也四处张望,意思像有意见待表示。
‘这有什么好?
路面那么光光的,一无所有。
人来人往,那么乱,不是充军赶会忙些什么?
……一只蚱蜢、一条蚯蚓也见不到!
’”这一段关于“公鸡”的描写,幽默滑稽,迥然异于沈从文的“抒情体”小说,沈从文试验以一种别样的文体来实现自己的小说复兴。
当然,小说并不陷于油滑,更多的是“油滑其肤,沉痛其骨。
”小说接下来写到老头子不小心挡住了一个“青壮”的路,不住的说:
“对不起,对不起!
”可是本应当表示歉意的“青壮”,却带着“一点官气”,反而狠狠瞪了“小老头子”一眼,用更偏北的口音说:
“哼,什么对得起对不起,废话。
”老头子说了句“少年有为撞劲足”,笑了笑,便向前走了。
如果说这件小事情表现了颇有礼貌的北京某种文明友好的东西已经流失之外,后面的敲门认亲则具有“荒诞”的味道。
当老头子敲开小姑娘家的门的时候,小姑娘也缺乏了对人的理解和同情。
特别是小老头这样一个老年人,也不能得到小姑娘的理解和信任。
小姑娘“因为前不久在学校里面演过沙家浜戏中的阿庆嫂,或多或少受了点影响。
因此和阿庆嫂式一般的想,‘这事情可巧,究竟是谁?
打的是什么坏主意?
’”“文革”样板戏的思维已经同化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女孩的头脑,她大脑里关于如何同人相处,全是“文革”的思维逻辑。
因而导致老头子千里迢迢而来,闷闷抑郁而去。
小姑娘的家人在看完电影回来之后,举手投足,也是模仿《沙家浜》中人物的样子。
而且对话中还提到了《沙家浜》的参编者汪曾祺:
爸爸脱了大衣看看菜汤,也用小勺子尝了尝,为了逗女儿开心,故意学者刁德一的口气,“高明,高明。
”因为女儿前个星期在学校刚演过阿庆嫂,做导演的还是戏本执笔的汪伯伯,一家人坐在前排,都为这件事满开心……
楔子中的人物,日常生活、思维逻辑都已经被样板戏同化,作者在8000字的篇幅里不断强化这一点。
沈从文通过小说中的小姑娘一家,将其表现的淋漓尽致。
他们还为参与《沙家浜》导演和创作的汪伯伯(即汪曾祺)而骄傲兴奋。
而正是因为样板戏的思想清洗,才使小姑娘置也许是小老头的远方来客于千里之外。
小说人物流露出对汪伯伯的钦慕,我们却不敢妄言整个小说也流露出钦慕之感。
沈从文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自己的得意高足因为参与样板戏的写作而天下闻名,以至于风光的登上天安门城楼,作为老师的沈从文却晚景凄凉,难免心中百感交杂,是羡慕,是讽刺?
我们不敢妄下断语。
另外,从语言来看,《来的是谁?
》语言干巴,并不好读,陌生的我们甚至不敢相信出自沈从文的手笔。
小老头子的形象也癫而不疯,似幻似真,颇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倾向,比80年代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足足早了十余个年头。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的“魔幻”资源,不是外来的输入,而是取自于中国古典文学。
这样一个带有挑战性质的创作尝试,究竟能否完成,沈从文也表示了自己人事上的顾虑和担忧:
“一是我人七十岁了,在偶然事故中二十四小时内即将步大姑爹大表伯后尘,可能性完全存在….其次即今冬明春可望回去,如安排了未完工作,都会影响这一工作的继续……”[1]46沈从文一是担心自己年纪大,怕突然离世;
二是担心上面安排工作,影响写作的继续。
除此之外,放弃自己的抒情问题,写作这种带有“魔幻色彩”而又不乏“黑色幽默”的带有“史诗”性质的小说,这种艺术上转身是否能够完成?
问题的关键在于,沈从文是个天生的诗人,善于雕琢精致玲珑的小玉器玩,他的专长在于构建比较小巧的“希腊人性小庙”,进行“抽象的抒情”。
已经创造熟稔了《边城》这种“抽象抒情”文体的沈从文,是否能够顺利地过渡到“家史兼地方志”式的史诗小说写作?
我认为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二
写作长篇,沈从文已经不是初次尝试。
1938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长河》的第一卷,因内容涉及湘西少数民族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在香港报刊发表时被删节,小说前后互不连贯。
1941年作者重新改写,经过两次送审和再次删节,才有部分篇章得以在内地刊物上重新发表。
后来作者再也没有提起笔来,将这部小说续完。
研究者大多将国民党的文艺审查制度当作《长河》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但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作者自身的艺术困境,如果环境允许,沈从文能够完成这部小说吗?
抗战开始之后,国民党在文艺上已无暇顾及,沈从文为什么不将这部小说写完呢?
沈从文在“文体”上遇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困惑。
这种矛盾和困惑实际上在《边城》完成之后就已出现。
1933年完成《边城》之后,沈从文“沉默”两年时间,小说创作数量也明显下降。
《边城》已经使他感觉到疲惫不堪或者力不从心。
尽管他自己说,“沉默并不等于自弃”。
沉寂较长之间之后他相继推出的《八骏图》、《来客》、《顾问官》、《主妇》、《贵生》等作品,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手法都发生了鲜明的转向,《边城》那种由“独特的风格”和“诚挚的感情”构成的“牧歌文体”已经渐行渐远。
实际上,在《边城》里,已经透露出“抽象抒情”的艰难和疲倦,譬如“在描绘地方上风土人情的时候,作者多次直接插话,表示热烈的赞叹。
一个作家不断用自己的称赞来加强他对某样事物的描绘,这是否说明他在捕捉对那事物的诗意感受上,多少有点力不从心了?
他后来屡次回忆写《边城》时的创作情绪,那种欣幸的口气就清楚地表明,他自己也知道
这样的心境多么难得。
再看看他一九三四和三五年间的创作情况,不但越写越少,而且越写越杂,简直又回到十多年前的杂乱里去了。
他本来应该趁热打铁,怎么反倒熄了炉火?
”[4]52现实的残酷纷乱使处在乱世中的沈从文难以漠然置之,这种对现实的“厌恶”和“绝望”,已经在他描绘湘西风土人情时的情不自禁的赞叹显现出来。
尽管没有冲淡对湘西“诗意”的抒情,已经多少显得作者不能恬静的进行“抽象的抒情”,或者说这座希腊人性小庙的建造已经耗尽了作者了“牧歌”曲谱。
作者这种情不由衷或是力不从心的慨叹,或多或少破坏了“牧歌”的和谐。
他自己后来多次回忆写作《边城》时的创作状态,似乎也表现了作者再难以回到那种优裕自如、恬静致远的写作心境。
沈从文疏远了自己熟悉的“牧歌”文体。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他难以保持继续不介入时代的天籁般的“吟唱”。
更为致命的是,他“那样顽强地想要把握住那种‘乡下人’的浑沌感受,自己却又一步步地努力要当一个城里的绅士,这就势必会受到那绅士阶层的世俗理想的牵制,最终还是对自己的审美情感发生了误解。
因此,就在快要攀登上文体创造的山巅的时候,他又身不由己地从旁边的岔道滑了下来。
惟其接近过那辉煌的顶峰,他最后的失败才真正令人悲哀,它以那样残酷的方式显示了人的世俗意识对艺术的巨大破坏力,它竟能从一个已经建立起个人文体的小说家手中,硬把那文体生生地抢夺走!
”[4]56
《边城》实际上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最高标杆,在此之后作者再也回不到写作《边城》时的单纯明澈,写作《长河》时甚至更糟。
再也没有对“诗意栖居”的向往,充斥其大脑的是解剖和描绘现实,以及概念化的对愚昧、落后、腐败的不齿和厌恶。
作者虽然也描绘风物,但总爱孜孜不疲的议论;
想“史诗”般的表现湘西的“常与变”,但老揪住“新生活运动”不放,并不惜笔墨,刻意的用调侃嘲弄的笔调增加幽默风趣,仍遮掩不住文体僭越之后的困窘。
看看《<
长河>
题记》,我们就明白了沈从文已经完全抛弃了他熟稔的“抒情文体”,而是侧重于“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
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
所以我又写了两本小书,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长河》。
当时敌人正企图向武汉进犯,战事有转入洞庭湖泽地带可能。
地方种种与战事既不可分,我可写的虽很多,能写出的当然并不多。
就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小处,它的过去、当前和发展中的未来,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另外却又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作品起始写到的,即是习惯下的种种存在;
事事都受习惯控制,所以货币和物产,于这一片小小地方活动流转时所形成的各种生活式样与生活理想,都若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发展。
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5]2
这种尝试已经在《边城》之后的创作已经开始。
人事上的“对立相左”难以和“抒情”之间的紧张和分裂,逐渐破坏式微了他作为“牧歌”作家的气质。
他适宜于雕琢小巧精致的、朦胧和水灵的“边城”,擅长做“水”的文章。
而《长河》除“水”之外,多了一个“土”字,是要做“水土”的文章,要求比《边城》厚实大气的多。
另外,短中篇(实际上《边城》也不过是一个比较长的短篇而已)是他最合适的“牧歌”载体。
一旦离开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他就明显显得力不从心或者难以为继。
这个问题在《边城》之后短篇创作上已经显现得颇为突出,尚不说要描绘带有“史诗”性质的《长河》。
他在《题记》中说,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水码头作背景,就他所熟习的人事做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常”是作者熟悉的,而“变”仅靠作者走马观花式的回乡印象,先入为主的憎恶分明的外部情感,很容易将“抒情”做简单化的处理,因而也就很难完成长篇幅的“抒情”。
第一章《人与地》写平凡人物生活中的“常”。
在这一章的结尾,作者点明即将进入“变”:
这就是居住在这条河流两岸的人民近三十年来的大略情形。
这世界一切都在变,变动中人事乘除,自然就有些近于偶然与凑巧的事情发生,哀乐和悲欢,都有它独特的式样。
然而“变”刚刚开始,激烈的矛盾冲突刚刚开始,情节刚刚展开,作者就为他画上了休止符。
沈从文遇到了“抒情”与“史诗”这个难以化解的矛盾。
除此之外,“牧歌”的文体不需要过多的人物,《边城》中的主要人物也不过四五个,而“史诗”要求的人物要多一些,人物之间的牵涉关系也要更为复杂一些,这是作者遇到的另一个艺术难题。
正因为如此,再加上《长河》第一卷出版遇到的审查删改,《长河》才难以为续,成为一部断章。
沈从文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远离“抒情”(或者资源干涸)之后艺术路向调整的拗手和艰难。
从《小砦及其它》开始,这种有意识的“回归抒情”愈来愈明显,但还是没有回到并未久违的叙述原点。
《小砦》喋喋不休,如同政论或是哲理文章;
《虹桥》啰啰嗦嗦,空发议论;
《新摘星录》唠唠叨叨,语言也拖泥带水,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
写于40年代中后期的《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等也同样没有回到《边城》那样的自然凝练、恬淡致远。
他“‘欲进还退’地试图重新写些关于乡土中国的美丽‘神话’和‘传奇’,但成就平平,了无起色。
这也印证了一个老掉牙的文学原理一一创作之所以为创作,就在于它不可重复,连作家自己也难以重复自己。
”[6]34
三
沈从文不是建国之后就全然放下文学创作而治文物研究,实际上他完全放下小说创作一直拖延到60年代。
这个抉择并不是当机立断、突然跳跃,而是抽刀断水、有一个复杂艰难的转变过程。
建国以后,沈从文仍有着很高的创作热忱。
他曾把自己的这种心态形象地比喻为“跛者不忘履”:
““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7]462不过这种创作的热忱,已经不是渴望重构“远离尘嚣的牧歌”,而是紧贴现实,做“时代的抒情”,这在他的信札里多有反映:
这回下乡去是我一生极大事件,因为可以补正过去和人民群众脱离过误。
二十多年来只知道这样那样的写,写了许多文章,全不得用。
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
因为基本上已变更。
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1951年10月28日致沈龙朱、沈虎雏)
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
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
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
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
(1951年11月8日致张兆和)
你说写戏,共同来搞一个吧,容易安排。
或各自作一个看看,怕没有时间。
因为总得有半年到四个月左右空闲,写出来才可望像个样子。
背景突出,容易处理,人事特殊,谨慎处理易得良好效果。
可考虑的是事的表现方法,人的表现方法。
用歌剧还是用话剧形式。
我总觉得用中篇小说方式,方便得很。
用把人事的变动,历史的变动,安置到一个特别平静的自然背景中,景物与人事一错综,更是容易动人也。
但当成戏来写,社会性强,观众对于地方性生产关系,也可得到一种极好教育。
只恐怕不会有空闲时间来用。
(1951年12月2日致金野)[8]123
由于环境的局促压抑,沈从文急于得到“主流”的接纳和承认。
我们当然能理解他在那个环境下的艰难处境,但他自己忽略了“远离尘嚣的牧歌”和“时代的抒情”之间的紧张对峙,这个“紧张的对峙”成为建国后沈从文新的“文体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