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杜诗观述论Word格式.docx
《陈寅恪的杜诗观述论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陈寅恪的杜诗观述论Word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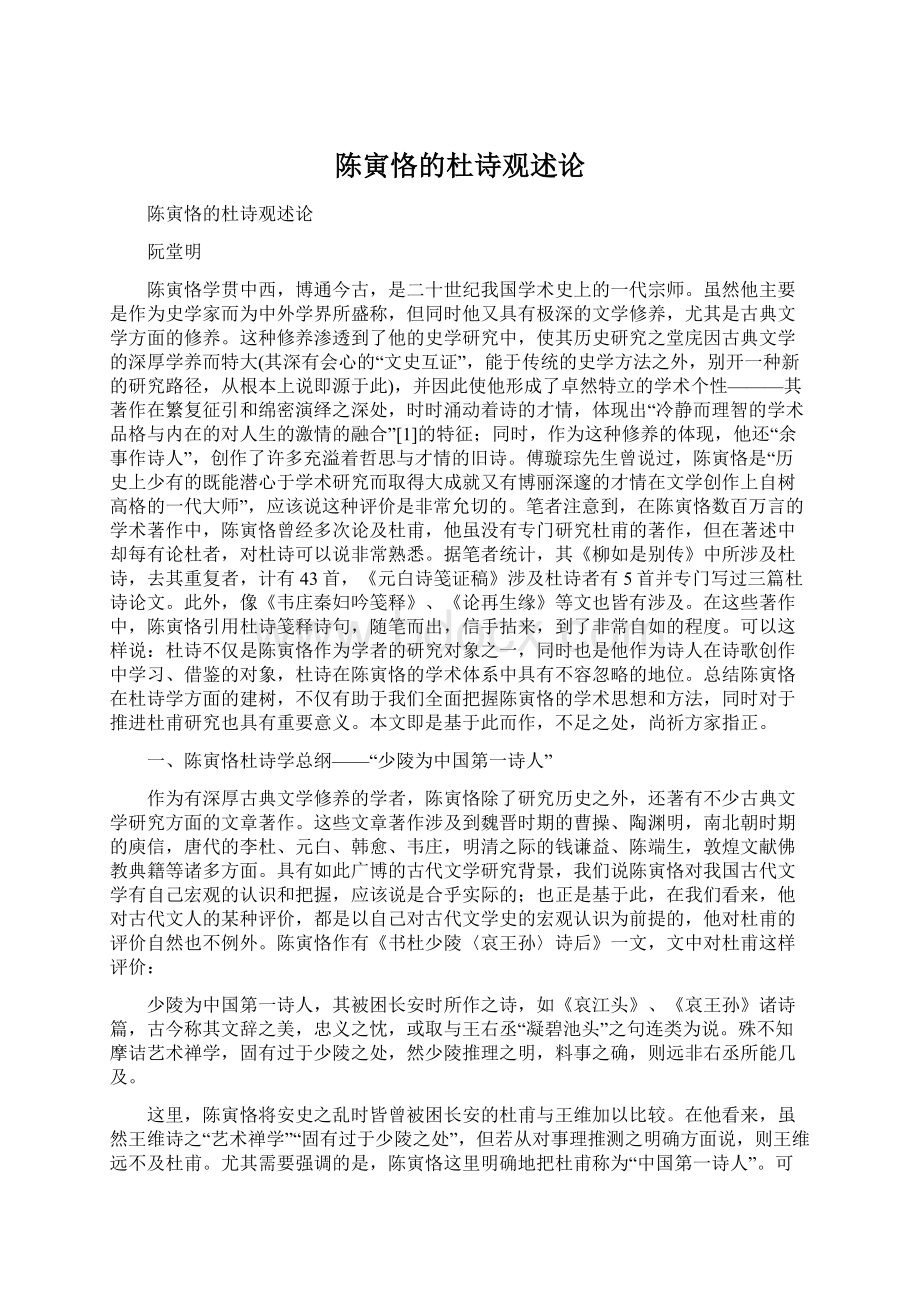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陈寅恪这里明确地把杜甫称为“中国第一诗人”。
可以说,这是他古代诗学观的根本观念,也是他杜诗学思想的最核心的内容。
众所周知,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历来与李白并称“李杜”,他们被看成诗史上双峰并峙、并驾齐驱的诗人,诚如韩愈《调张籍》诗中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也。
然而,也正是从唐代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杜优李劣”的观念。
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评价杜甫时即曾这样说过:
“(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
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
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
……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这里,元稹将杜甫说成是诗史上无与伦比的诗人,其实这也是把杜甫看成是“中国第一诗人”,元稹文中还将李白与杜甫比较,认为李白连杜甫之藩翰尚不能历,更遑论杜甫之堂奥了。
元稹所论,固然失于偏颇,但体现了自中唐以后杜甫一直被视为最大诗人、杜诗一直被视为古代诗学正统的事实。
陈寅恪这里虽未将李杜加以比较,但他以“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说明在他看来,杜甫是无与伦比的诗人。
他的这种杜诗观,与元稹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也是一脉相承的。
陈寅恪作有《元白诗笺证稿》,因此自然很熟悉元稹的诗文。
这样,他对杜甫的这种论述,便很显然应与元稹《杜君墓系铭》中的杜诗学思想具有渊源的关系;
而事实上,我们从陈寅恪《论再生缘》[2]一文中,看到他在论及“吾国诗中之排律”时,曾特地征引过元稹此文。
为说明的方便,兹将陈寅恪所引者转录于下:
《元氏长庆集》卷伍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略云:
“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
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
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
姚鼐《今体诗钞序目》略云:
“杜公今体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不可谓少。
数十韵、百韵中运掉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不觉其多。
读五言至此,始无余憾。
余往昔见(钱)蒙叟笺,于其长律,转折意绪都不能了,颇多谬说,故详为诠释之。
……
在征引元稹与姚鼐的文章之后,陈寅恪紧接着又加了按语:
“寅恪按,微之惜抱之论精矣,兹不必再加引申,以论杜诗。
”这里,陈寅恪虽是站在排律的角度征引元稹此文,但应该说还是体现了他对元稹此论的认同态度;
只不过相对于元稹立足于杜甫五言排律的声韵辞藻立言,陈寅恪则并不是站在“艺术禅学”的角度评价杜甫,因此虽同样以杜甫为第一诗人,但是在“第一”的内涵上,他与元稹又是有较大区别的。
总之,“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构成了陈寅恪杜诗观的核心内容,不仅体现了他的杜诗学思想,也同样是他的诗学观的体现。
由于陈寅恪深厚广博的古代诗学修养,他对杜甫的这种评价,是以他对古代诗学传统的理解为前提的,不能仅仅视作单一、孤立的评价。
这一点从下面的内容中,还可以得到更深入的证明。
二、陈寅恪旧诗的杜诗渊源———“取法少陵”
作为身兼文人的学者,陈寅恪还雅擅旧诗的创作,这是陈寅恪的家学———“义宁陈氏之学”的重要方面。
陈寅恪的先祖陈宝箴诗文兼擅,皆有法度,为世所称。
其父陈三立更是清末宋诗派———“同光体”的代表人物。
受这种家学的熏陶,陈寅恪也工于诗。
他为诗宗尚宋诗,又出宋入唐,注重独创,强调自得机杼。
他的诗虽散佚较多,但现存《陈寅恪诗集》中收集有330首。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杜诗之间的密切关系。
著名学者程千帆曾这样评价说:
“寅恪六丈当代通儒,余事为诗,亦复词采华茂,气骨清峻,而尤工于七言。
古体掩有香山、梅村之长,今体则取法少陵及玉溪、冬郎之所效则少陵者。
晚经浩劫,所存仅寥寥百十篇,而近百年时运推移,人情变幻,莫不寓焉。
”[3]这种评价揭示了陈寅恪所受杜诗的重要影响。
在众体中,陈寅格尤长于七律。
笔者曾对陈寅恪的诗进行过统计,在其现存330余首诗中,七言律诗计有173首,在其全部诗歌总数当中,占据了60%以上的比例。
应该说,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杜诗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杜律在唐代及后世为律诗之极则,七律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杜甫的七律兼备众妙,地负海涵,雄阔高浑,最能代表和体现杜诗之艺术成就。
后世师杜者往往衍其一绪,而恃以名家。
诚如《岘亻庸诗话》所言:
“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
义山学之,得其浓厚;
东坡学之,得其流转;
山谷学之,得其奥峭;
遗山学之,得其苍郁;
明七子学之,佳者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阔。
”作为极具才情的学者,陈寅恪的旧诗尤其是七律创作也深深得益于杜诗之沾溉。
当然,陈寅恪诗法杜甫,远不止在诗歌的形式上。
检《陈寅恪诗集》,中有《甲申春日谒杜工部墓》一诗,诗云:
少陵祠宇未全倾,流落能来奠此觥。
一树枯柟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
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
归倚小车浑似醉,暮鸦哀角满江城。
由题中“甲申”可知,此诗作于1944年。
据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43年夏,日军战火逼近湖南,时任广西大学教授的陈寅恪,为躲避战乱,于是年秋携家眷取道贵州辗转赴川,途中身染重病,饱受艰难,腊月底始到成都(时公历已进入1944年)。
此诗即作于他初到成都时[4]。
据陈寅恪之女流求《流求笔记》所述,当时“成都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生活极为艰苦,且陈寅恪的右眼当时已失明,行动极不方便;
但即便在这样的艰难中,他仍去拜谒杜甫墓,这就不仅传达了他悯时伤乱、渴求太平的愿望,也见出杜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杜甫当年为避安史的八年之乱而至成都,陈寅恪也因为日本侵华的八年战争而同样避难到成都。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际遇,同样的情怀,在时隔一千多年后上演了极其相似的一幕。
所以陈寅恪此诗,既有对杜甫深刻的理解,又包含有悯时伤乱的情怀。
《陈寅恪诗集》里还有两首由杜诗兴感而作的诗,一是作于1956年的《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律》,诗云:
林花天上落红芳,飘坠人间共断肠阿母筵开争骂座,太真仙去愿专房。
按歌未信宫商换,学舞端怜左右忙。
休问大罗云外事,春阴终护旧栽棠。
此诗题中的“唯见林花落”,出自杜甫《别房太尉墓》一诗。
“房太尉”,指的是玄宗朝旧臣房。
杜甫此诗主要表达了对这位前朝旧臣身后寂寞的伤悼之情陈诗由“唯见林花落”一句而致慨,借杜诗兴感,表达对现实的感受。
诗中“飘坠人间共断肠”之“共”字,将自己与杜甫绾结起来,也见出对杜甫“见林花落”时内心悲慨之深刻理解。
另外一首《戏续杜少陵秋兴诗“刘向传经心事违”句成七绝一首》,诗云:
刘向传经心事违,翁今儿古各相非何如东晋郗家好,父子天师道共归。
此诗作于1964年。
诗中“刘向传经心事违”一句,出自杜甫《秋兴八首》之三(千家山郭静朝晖)。
杜甫此句原是表达自己一生心事乖违之憾,而陈寅恪则借以讽咏1963年以来中苏两党交恶之事陈寅恪借续杜诗而表达对当时政治的看法,真可谓善用“古典”[5]者。
由此我们也可看出,陈寅恪熟识杜诗,可以随意引用。
在旧诗创作中陈寅恪每从杜诗中汲取营养,多有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者。
对杜诗的隐托和化用,可以体现杜诗对陈寅恪的影响。
笔者对《陈寅恪诗集》中隐括杜诗或化用杜句之情形作过统计,现将统计结果表列于下:
此表所涉及的陈寅恪的诗共40首,在《陈寅恪诗集》330首诗中,约占八分之一的比例。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独具才情与追求的诗人,陈寅恪诗法杜甫,并非对杜诗亦步亦趋,“生吞活剥”[6],陈寅恪作诗不是仅仅隐托杜诗融化杜句,而是迁杜入己,将杜诗融入自己的诗境中。
试看其《乙酉八月十一日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雠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此诗是1945年秋作者在成都获悉日军投降之喜讯后而作的。
从创作背景上说,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是极其相似的。
诗中作者抓住与杜甫在遭遇与情感上一致的契合点,以“闻讯杜陵欢至泣”一句融化杜诗“初闻涕泪满衣裳”,又以“还家贺监病弥衰”隐括杜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二句的回乡之意,从中不难看出二诗之间的关系。
然而,此诗虽有点化或隐括杜诗处,但又并非刻意地模仿杜诗,并非重复杜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而是要塑造自己的形象,故此诗虽有借鉴杜诗者,但不是照搬,而是有变化,表现在陈诗并非单纯地表达获悉日军投降的欣喜之情,在“家祭难忘北定诗”一句下,诗人注云:
“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因此,诗同时融入了家事之悲的内涵,故而结句云“喜心题句又成悲”,翻喜为悲,在感情上比之杜诗又更见深沉了。
由于杜诗的影响,陈寅恪的诗,也颇有杜诗沉郁顿挫之致。
比如其《甲辰五月十七日七十五岁初度感赋》一诗:
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
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
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
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
这首诗作是作者初度75岁生日之作。
前四句作者感慨世事人生,“百年”句点化杜甫《秋兴八首》其四“百年世事不胜悲”。
后四句自比“越鸟”,以“炎方”、“瘴海”喻自己处境之艰难,结句以孔安国唾壶为儒者所执之典,表达对学术事业被破坏之悲,篇终而接浑茫。
整首诗作者感怀人生,深沉郁勃,苍茫老健,颇有老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陈寅恪注重对杜诗之学习与借鉴,固然是其诗歌创作旨趣与追求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说,则是他与杜甫内在的精神、情感的共通性所决定的。
我们认为,这种共通性就是对家国丧乱与人世沧桑的深刻感伤。
杜甫处于唐王朝极盛而衰的历史转变时期,巨大的历史变故以及饱经离乱的身世遭遇,使他的诗重在表达忧国忧民与悲天悯人之怀抱,以及对世变沧桑与历史兴亡之感慨,而陈寅恪所处时代环境虽与杜甫不同,但其身世遭遇却极有与杜甫相似者。
蒋天枢先生论陈寅恪生平时说:
综观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
远客异国,有断炊之虞;
漂泊西南,备颠连之苦。
外侮内忧,销魂铄骨。
寄家香港,仆仆于滇越蜀道之中;
奇疾异遇,困顿于天竺、英伦、纽约之际。
虽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后,继以摈足,终则被迫害致死。
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耶?
先生虽有“天其废我是耶非”之慨叹,然而履险如夷,胸怀坦荡,不斤斤于境遇,不戚戚于困穷,而精探力索,超越凡响,“论学论治,迥异时流”。
而忧国忧民之思,悲天悯人之怀,郁勃于胸中,壹发之于述作与歌诗。
先生之浩气遒矣。
[7]
这段话不仅高度概括了陈寅恪一生命运之遭际,对其苦心孤诣与思想境界之把握也非常切当。
这种人生遭遇,使陈寅恪在对家国离乱及历史盛衰之感受方面,与杜甫是高度一致的。
正因为如此,陈寅恪才能从杜诗里寻求到深切的情感共鸣。
这样,当他以诗歌表达身世感受时,就会很自然地隐括或化用杜诗,此盖有不得不然之情形在焉。
陈寅恪论诗主情,尤重感慨。
由“吾侪所学关天意”、“文章声价关天意”、“文章存佚关兴废”等诗句中即可看出,陈寅恪每致意于抒发身世浮沉的人生体验与兴亡沦替的沉恸之感,像“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庚戌柏林重九作》)、“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兴亡哀感动人思”(《王观堂先生挽词》)、“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王观堂先生挽词》)、“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饯岁觥”(《丁亥除夕作》)等,都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陈寅恪这种重在抒慨、表达兴亡之感的诗与杜甫后期诗之抚今追昔、特重感慨是一致的。
他隐括杜诗与融化杜句,从根本上说就是由此决定的。
其实,对前表所列杜诗稍加分析即可发现,陈寅恪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所涉及的杜诗,主要是杜甫后期的诗,且多作于夔州期间,只有《兵车行》、《咏怀五百字》等少数篇什作于关秦地区。
众所周知,杜甫后期诗,尤其是夔州期间的诗,是他晚年历遍人生种种苦痛,阅尽人间盛衰之变以后之所作。
夔州期间,他不再像早年因为“穷年忧黎元”而奔走呼号,使得诗旨过于激切或直露,以至于后世有“几近于骂”之讥[8],而是超越具体的现实情事,升华至一种对历史人生作整体思考的高度。
诗中杜甫往往慨往悼今,感时伤世,既悲苦至极又从容潇洒,笔底波澜壮阔而又细入无间,最能见出日暮途穷时他激越悲怆而又留恋人生的丰富、深沉的情感。
此时杜诗中感时伤世与兴亡之感比以前更见深沉了。
陈寅恪对杜甫后期诗特加重视,主要即在于此。
在我看来,这不仅体现了陈寅恪的诗学精神与创作旨趣,说明杜诗尤其是杜甫后期诗,构成了陈寅恪诗歌渊源的重要方面;
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杜诗之隐括及杜句之融化,是他体认和挖掘杜诗精神、情感的一种方式,是他因为铭感于杜诗慨往悼今之精神而对其兴亡之感的阐发。
如果仅从诗歌渊源的层次上认识,那就严重地局限了它的意义。
陈寅恪在以诗证史时,主张对于古人要具“了解之同情”,而“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9],而后始可进行研究。
这里,他所论的虽是学术研究,其实也通于诗歌创作。
他的《柳如是别传》,便是通过笺释柳如是之诗以进入其精神、生活世界的。
对于陈寅恪而言,诗与学术是高度统一的,因此他在诗中借鉴杜诗,隐括或融化杜诗,也包含了对杜甫的理解在内,或者说也是以理解杜甫、进入其精神世界为前提的。
他在《读〈哀江南赋〉》中精辟地指出:
“古事今事,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一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这里,说的是文学创作中古今相通、“古典”与“今典”妙用之情形。
陈寅恪非专门的文学评论家,其学术旨趣也非是一般的谈艺论文,非总结文学的规律,因此陈寅恪此言尤其体现了他的诗歌创作经验与体会。
这也就告诉我们,他的许多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之诗,皆可视作他“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一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从而追求与杜甫之冥化如一。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杜甫与陈寅恪是异代之知己,时异而情同。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陈寅恪之注重杜甫后期诗,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杜甫精神内涵的体认、挖掘与发挥。
明乎此,对陈寅恪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对杜诗“诗史”意义的阐发———“以诗证史”
“以诗证史”,是陈寅恪对历史研究的创造性贡献,也是其治学的最精华的部分之一。
运用这种方法,他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
可以说,陈寅恪学术堂庑之构建,与这种方法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在探索这种方法形成的过程时,我们注意到,它与杜诗具有密切的关系,应该说是人们在笺释杜诗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杜诗自晚唐孟棨《本事诗》始,既已有了“诗史”之称,所以在宋代“千家注杜”的盛况中,即多有从当时历史之角度阐发杜诗者。
比如黄鹤在注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时即云:
“天宝十载,募兵无应者,杨国忠遣御史系捕送军前。
旧制,百姓有勋,免征役。
于是杨国忠选取高勋,行者愁怨。
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此诗所以有咸阳桥拦道哭之句也。
”(《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集》)这种依据历史对杜诗诗意的解释,应该说在实践上为“诗史互证”方法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而到了黄宗羲那里,趋于成熟,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曾说:
“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
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
”这里,黄宗羲明确提出了“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概念。
在他看来,不仅史可以证诗,诗也可以证史。
黄氏此论可以说是“诗史互证”形成的标志。
而在陈寅恪之前,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是以“诗史互证”方法注杜的代表性著作。
钱氏基于“六经皆史”的观念,认为“驯至于少陵,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胡致果诗序》),故而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通过诗歌与历史的考证,解读杜诗,从而使“诗史互证”作为一种学术方法而正式形成了。
与传统诗歌笺释中注重章句训释、注疏不同,“诗史互证”着力考察、挖掘诗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或从诗中发现历史,这就使诗具有了裨补史阙之功效。
对钱氏这种方法的意义,陈寅恪有着充分的认识与深入的理解。
他在《柳如是别传·
缘起》中这样说:
“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这里,他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钱谦益有直接的继承性。
另外,在《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中,陈寅恪还对钱谦益与朱鹤龄之注杜作了细致的考察,总结钱注杜诗之特点。
他引《钱注杜诗》篇首所录诸家诗话中《古今诗话》“杜甫诗自可为一代之史也”一则,云:
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
陈寅恪还考察过钱氏的《列朝诗集》,认为钱氏撰此之旨趣,非在论诗,而是“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借诗以存史”,体现出对钱氏学术旨趣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凡此,皆说明陈寅恪对钱谦益学术之重视。
应该说,陈寅恪所运用的“诗史互证”方法,就其渊源而论,正是源于钱谦益的《钱注杜诗》。
陈寅恪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研治杜诗,共写了三篇文章,它们是《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均见于《金明馆丛稿二编》)。
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中,他依据《旧唐书》安禄山传、史思明传中所言的“杂种胡”,以及《新唐书·
回鹘传》所称之“九姓胡”,认为“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
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
又引杜诗中对安禄山、史思明的“杂种”之称,指出:
“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
《旧唐书》多保存原始资料,不多改易词句。
故在《旧唐书》为杂种胡,在《新唐书》则易为九姓胡。
考宋子京改字之由,其意恐杂种胡一词,颇涉通常混种之义,易启误会,遂别用九姓胡之名。
”这里,陈寅恪将杜诗与历史互相对照、证发,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杂种胡”与“九姓胡”以及在名称上形成差异的原因。
《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一文,则通过等征引史料,认为诗中“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二句中的“朔方健儿”,过去解以郭子仪、李光弼所统之朔方军是错误的,应该是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同罗部落。
该部落勇健善斗,在其首领阿布思为回纥所掠后,为安禄山厚募招降。
在安史叛军攻下长安后,该部落被派守长安,助纣为虐,未久而叛归旧巢。
他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与通常的以庾解杜不同,而是反过来以杜解庾。
他针对庾信《哀江南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
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
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八句旧注解以指萧詧,将“无赖子弟”视作指陈霸先所存在的与史实乖误之情形(参考倪《庾子山集注》),由杜甫《咏怀古迹》(其一)中“羯胡事主终无赖”一句索解,认为杜甫这里以“羯胡”指安禄山,实际也是喻指侯景,而杜甫此诗可以看作是一篇《哀江南赋》之缩本[10]。
诗中杜甫自比庾信,而以玄宗比梁武,以安禄山比侯景。
通过一一比勘,陈寅恪进而得出了庾信“此赋八句乃总论萧梁一代之兴亡”的结论。
今按,杜甫此诗由庾信故居兴感,借描写庾信身世表达作者暮年萧瑟之感。
因此,诗中对庾信身世的描写,固有助于我们理解庾信《哀江南赋》之内涵。
陈寅恪由杜诗而索庾赋之解,与他所强调的“神游冥想”、“神理相接”是一致的,是一种极富于想象力的研究。
这种直臻诗人心灵之奥府而脱去表象之行迹的研究,看似主观性很大,一般人用之固不免流为臆说,而在陈寅恪这里,却超越了历史形相“个性之真实”,而臻于其素来追求的“通性之真实”,达到了极高明的境界。
此外,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为申论李白本为胡人,陈寅恪引用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二)“贾胡离别下扬州”一句,说明蜀汉在唐代曾为胡商行贾之区域,其地当时多有胡人往来侨寓,也是“以诗证史”之佳例。
陈寅恪以“诗史互证”的方法,阐发杜诗的“诗史”意义,站在杜诗研究的角度看,虽然稍显具体、零散,似乎无关杜诗宏旨,未及钱谦益《钱注杜诗》之浩繁丰富,但若就对“诗史”意义挖掘的深度来说,则《钱注杜诗》反远不及陈寅恪。
盖《钱注杜诗》重点在于“以史证诗”,通解诗意,着眼于诗意之把握,故其所牵涉之史,皆为个别、孤立之史实,彼此关联不大,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观;
而陈寅恪阐发杜诗之“诗史”意义,则偏重于“以诗证史”。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极高明而难以企及之处,在于他弘通的眼光与深邃的识见。
他对中国史的研究,是将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内,从世界史的整体高度与角度研究中国史;
而他对杜甫的研究,对杜诗所牵涉之历史的考察,也是超越了杜甫研究的范围,站在中国史的高度进行的(他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以杜诗解庾赋,最能见出其不受时代局限之弘通史识)。
因此,我们不能只从杜甫研究的角度来看待陈寅恪阐发杜诗“诗史”意义之价值。
实际上,陈寅恪对杜诗“诗史”意义的阐发,是他的历史研究整体的一部分。
陈寅恪的史学及历史观的重要特点是尤为重视种族与文化、民族迁徙以及社会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他的杜甫研究,即围绕此研究主题而展开,可以说是他整体的历史观在具体事例上的落实和体现。
比如,其《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所考察的“杂种胡”之义,以及《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中“朔方健儿”,即相互关涉,前者牵涉到安禄山种族之渊源,后者则牵涉到当时河朔之地各胡族部落之内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