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学与记忆.docx
《韩少功文学与记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韩少功文学与记忆.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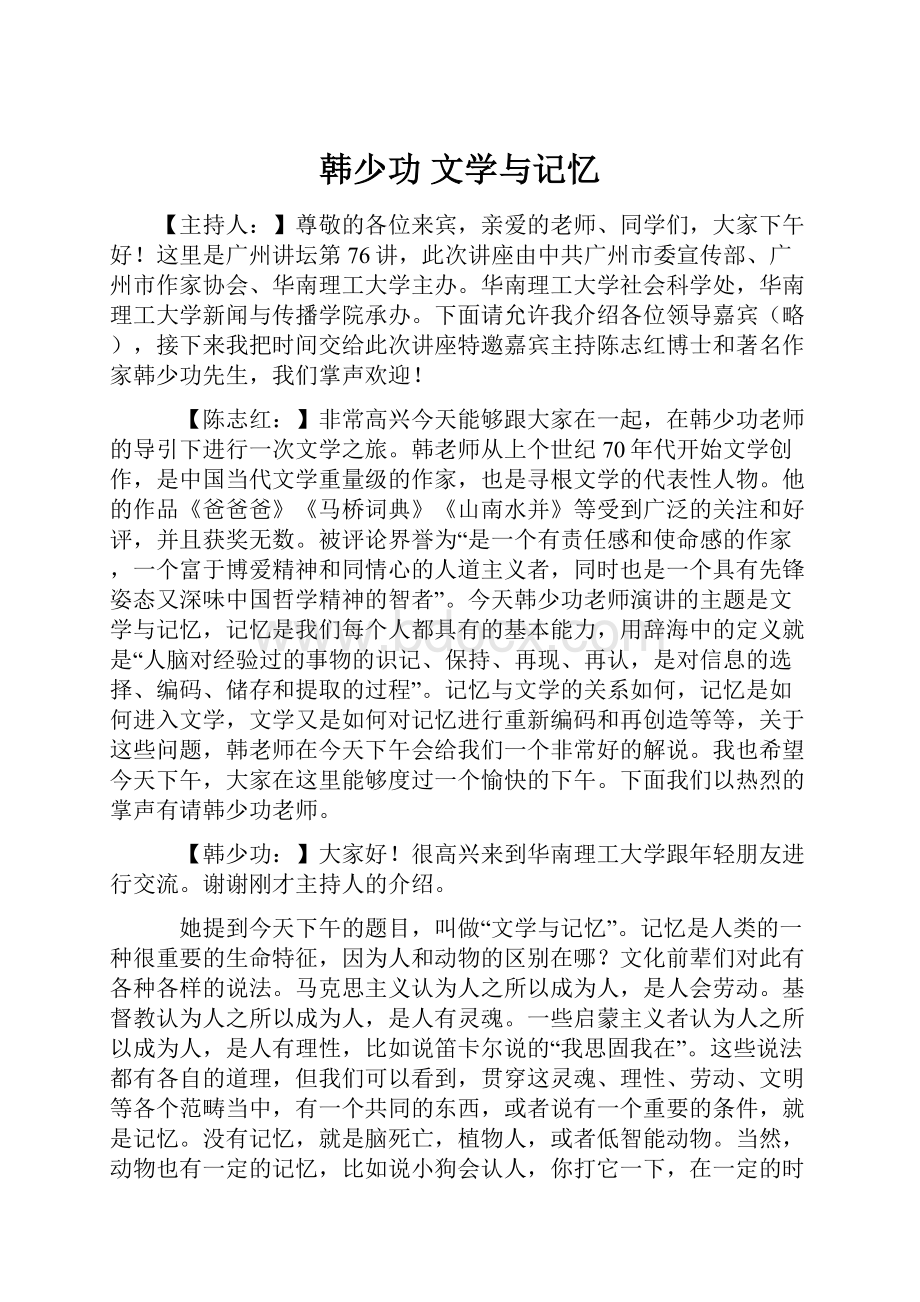
韩少功文学与记忆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这里是广州讲坛第76讲,此次讲座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作家协会、华南理工大学主办。
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各位领导嘉宾(略),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此次讲座特邀嘉宾主持陈志红博士和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我们掌声欢迎!
【陈志红: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在韩少功老师的导引下进行一次文学之旅。
韩老师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重量级的作家,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人物。
他的作品《爸爸爸》《马桥词典》《山南水并》等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并且获奖无数。
被评论界誉为“是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一个富于博爱精神和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先锋姿态又深味中国哲学精神的智者”。
今天韩少功老师演讲的主题是文学与记忆,记忆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基本能力,用辞海中的定义就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再认,是对信息的选择、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过程”。
记忆与文学的关系如何,记忆是如何进入文学,文学又是如何对记忆进行重新编码和再创造等等,关于这些问题,韩老师在今天下午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解说。
我也希望今天下午,大家在这里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韩少功老师。
【韩少功: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跟年轻朋友进行交流。
谢谢刚才主持人的介绍。
她提到今天下午的题目,叫做“文学与记忆”。
记忆是人类的一种很重要的生命特征,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
文化前辈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会劳动。
基督教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有灵魂。
一些启蒙主义者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有理性,比如说笛卡尔说的“我思固我在”。
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可以看到,贯穿这灵魂、理性、劳动、文明等各个范畴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记忆。
没有记忆,就是脑死亡,植物人,或者低智能动物。
当然,动物也有一定的记忆,比如说小狗会认人,你打它一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它看到你会畏惧。
这是狗的记忆。
但是人的记忆功能强大很多,与一般动物不可同日而语。
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包括文学,能对我们以前各种各样生存的经验,实现一种强大信息储存、编码、提取,用编年史、博物馆、纪念碑、摄影、小说、电视剧这样一些东西,强化了人类的记忆功能。
如果没有记忆,教育也是不可想象的,比如我们的华工大,不管数理化还是文史哲,都是记忆的积累和承传。
没有记忆,文学根本就无从谈起。
虽然我们作家需要想象力,但是哪怕是想象力,也是依托记忆来展开的。
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新加坡人,他说他父亲梦到的法国人、英国人都讲广东话,这是因为他父亲只知道广东话,想象无法超越他的知识边界,不过是把记忆的材料重新编织。
我们到国外看一看,发现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唐人街里面,唐人街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多中国餐馆。
很多华裔服装变了,口语变了,观念也变了,但是肠胃的记忆何其强大,到了吃饭的时候,还是念念不舍姜葱河蟹或者广东河粉。
让他吃法国人的奶酪,半生不熟的牛排,他还是不习惯。
包括不少“香蕉人”,所谓黄皮白心的,吃起中国菜还是津津有味。
特别是年纪大的时候,来自少年和家乡的肠胃记忆贯穿一生,甚至越老的时候越强烈,这也是很多人有过的经验。
前不久,还有一个很具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唱“红歌”,即50、60、70年代的一些歌曲。
一些知识分子认为“红歌”涉嫌极左:
要为“文革”招魂吗?
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想,这事可能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在“文革”时期度过青少年。
你不让我唱红歌,我还真的没歌可唱。
你让现在那些60岁左右的大爷大娘唱周杰伦的歌?
可能吗?
他们的唱红,其实只是一种青春记忆,与意识形态的阴谋没有什么关系。
包括很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人,一开口,情不自禁,可能还是会唱老歌,唱旧歌。
这种对声音的记忆,可能和与他们的青春经验,包括他们当时谈情说爱的经验,紧密地搅合在一块。
所以在一定的情境下,他会有一种特别的情绪冲动,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血压、心跳、呼吸。
这是一个自然的心理乃至生理的过程。
人们的道德感,也是依托记忆而建构起来的。
一个西方人,基督徒或穆斯林,想到上帝或真主的时候,可能形成一种自我行为的约束。
他们可能会记忆起一些文字、图片、场景、氛围,比如西方教堂常有的一些有关恐怖地狱的图面。
我就见过很多这种图画。
人干了坏事,死了之后去那个地方,比集中营恐怖百倍的地方,锯子锯,钻子钻,刀斧砍,血流成河。
这种形象化的教育,就是一些教义的熏陶洗礼,打造一些记忆,打造一些意识形态。
在中国汉区,我们的宗教感比较薄弱,但是我们也不乏中国式的宗教感情。
比方一个乡下老大爷,常说的一句话:
抬头三尺有神明。
这个神不一定是西方的上帝或真主,但它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神圣之物。
更多人会说,我们做事要对得起祖宗。
祖宗也是中国化的神,常常供奉在民居的大堂和正厅里,“天地君亲师”,或者现在稍加改良了的“天地国亲师”。
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建一些祠堂,做一些仪式,来祭祀先人前辈,也是制造一种记忆,类似宗教的功能,增强人们的自我行为约束,形成了一种所谓文明的传导。
今天会场横幅上面有一个“薪火”,也是这个意思,文明像薪火一样代代相传。
下面我要讲四点。
第一点,记忆受到事实的制约,所以有共同性。
第二点,记忆受到主体的筛选,所以有差异性。
在讲到这两点之前,我先说一个故事:
西方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给学生上历史课。
他的第一堂课非常别致,刚开始不久,突然从外面闯来一伙陌生人,进来就吵,进来就打,学生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十分钟过去后,学校保安把这伙人带走了,学生重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这位历史教授告诉大家:
同学们,刚才不是一个治安事件,是我们开始上课了。
请同学拿出纸和笔出来,把刚才这一幕的前前后后客观地描述下来。
同学们想一想,这一次的作业情况会怎么样?
不出所料,全班同学的描述,没有一份是相同的。
有人说是A先动手,有人说是B先动手、有人说C是这样说,有人说C是那样说,记录五花八门甚至互相矛盾。
历史老师说:
你们看,你们都是现场目击者,都是事件亲历者,你们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尚且如此不同,你们怎能保证我们对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描述,作为一个非亲历者、非目击者的描述,是正确而真实的呢?
这样看来,历史是什么?
历史不过是一大堆众说纷纭,甚至是五花八门、矛盾丛生的说法。
这也是一个关于记忆的实验。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知道我们面临的任务有多难。
所谓相信自己的记忆,进而相信自我,这个大话有时候真的不能随便说的。
这就牵涉到记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两个方面。
记忆受到事实的制约,当然会有共同性。
比方说今天下午,华工搞了一次讲座,请来了一个韩先生。
当这个事实进入大家记忆以后,有人会说韩先生长的很高,有人说韩先生长的很矮,有人说韩先生讲得好,有人说韩先生讲得糟,相关的记忆肯定是各各不一,但是今天来讲座的是一个人,不是一只狗,大家对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
讲座是下午发生的,不是早上发生的,不是半夜发生的,这一条大家也不会有异议。
这就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制约。
中国自清朝以来,大概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颇为不堪,落后,腐败、混乱,其原因是什么?
这一派有这个看法,那一派有那个看法,大家观点不一样。
但是两百年的落后是基本的事实,制约了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胡说八道指驴为马,说这两百年里我们是全世界NO.1,比其他国家干得更好。
因为有事实的制约,我们的文化记忆、文化风格和文化特性,也会表现出一定范围内的共通性。
有些外国作家说,到你们中国的书店去看,发现你们有一种小说特别多,就是官场小说。
《二号首长》《国画》什么的,你们也看过吧?
在我看来,这可能与中国人的历史传统有关,与记忆有关。
中国是一个农耕大国,有家族、家庭长期抱团定居的历史;用一个国外史学家的话来说,大河流域的农业水利建设,也会形成一种集中人力和强化行政的功能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产生强大的政府,形成官僚集权,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往下数,中央政府总是掌控一切,藩镇、采邑、诸侯、财阀形不成大气候。
拿这个特点比较一下游牧民族,会比较有意思。
我到过蒙古,在那里牧民们集中居住是不可能的,一集中,牛羊就没有吃的了,所以只能分头行动,带着自己的牛羊找没人的地方去。
牧民们逐水草而居,浪迹天下,居无定所,偶然聚到了一起,可能互为陌生人,谁听谁的?
古代欧洲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有漫长而普遍的游牧史,大家聚到一起,血缘、年龄不管用,财富大家都没多少,也不管用。
最后就是打架定输赢。
古希腊的民主最初就是一种武士民主制,军事民主制。
回过头来说,中国的官僚体制以及官本位的意识,后来通过科举制度的推广,变得更加精致,更加成熟,也更加顽固,以至到现在,“读书做官”还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社会潜意识。
很多企业招收高级技工,5000元/月,20000元/月,但招不到人。
很多父母情愿孩子去还是希望孩子考公务员,当一个科长工资不高,但有面子。
很多祠堂里的祖先牌位上,只记录两样东西,一个是你的学历,比如读过华工大,这是要记上的。
第二是你的官职,哪怕你只当过车间工会副主席,或者工会小组长,也是要记上的。
但你有多少存款,离了几次婚,去过多少国家,这些都不会上牌位。
这就是说,一个“读书”,一个“做官”,全齐了。
在这样黑压压的众多牌位的逼压之下,有些后人如何睡得着觉?
当和尚也想要个处级吧?
当校长更想要个厅级吧?
人们对官场的窥视欲、好奇心、想象力,岂能不产生一个巨大的读者群?
这也许就是当下官场小说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香港的情况很不一样。
内地的不少宫廷戏、官场戏,像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康熙大帝》,在那里的票房就很差。
描写孙中山的《走向共和》,表现国共相争的不少大片,香港人也不感兴趣。
为什么?
这就需要了解一下香港人的文化记忆了。
香港本就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地区的各种战争、造反、改革关系不大,因此不可能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政治局编外委员似的,也不可能像中原的老农民,个个都是皇帝国戚的知情人的关系户似的。
香港对朝廷政治一直很疏远,很隔膜,今天被割给英国了,明天又被领养回来了,就像一个流浪儿,今天去张家当儿子,明天回李家当儿子。
这个儿子会怎么想?
外婆不疼,舅舅不爱,都不待见,我与这个国家有多大关系?
“国破山河在”,“家书抵万金”,这个“国”与“家”之间的逻辑联系,怎么建立起来?
因此,香港文学写“儿女情”的多,写“天下事”的少,写“家”的多,写“国”的少,国家意识形态比较淡薄。
这种特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受到一些基本历史事实制约的。
记忆受主体的筛选,所以还有差异性。
我们常常见到,一对夫妻闹离婚,闹上法庭,男的说一通,女的说一通,对同样一桩婚姻,双方都可以说的痛哭流涕委屈万分,都是一肚子苦水。
他们也许都没有说假话,都有一点道理,但如此没法沟通,很可能是双方都剪裁了记忆,删除了自己不敏感、不留心、不愿意记住的一部分记忆。
前一段,流传一个段子,是对古代文学名著《西游记》的读后感。
大意是说,《西游记》说明了一个道理,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打不倒,凡是没有后台的妖怪都会被打死。
还有一条:
《西游记》里的天兵天将为什么打不过孙悟空?
因为他们是玉皇大帝的雇佣工。
为什么取经路上那么多妖魔鬼怪都难住了孙悟空?
逼得他去搬救兵?
因为那些妖魔鬼怪属于自我创业,生命力强。
还有人把《水浒传》换了一个书名,叫《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
同学们看一看,很多读者对经典作品的记忆就是这样的,与教科书的规定大相径庭。
我回忆,自己当小孩的时候,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不管是爱情片,还是伦理片,还是战争片,男孩们最喜欢注意电影里面的坏人,学来的大多是坏样。
由此可见,我们记忆一本书或一个电影,其实都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因欲望、利益、文化、具体情境而异,教科书并不能统一我们的记忆。
在座的大部分是理科生。
我孩子曾经问我学什么,我说你读理工科吧。
她问为什么,我说理工科好歹有一个道理可讲。
1+1=2,在常规情况下不会错到哪里,至于在高等数学里另有一说,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文科常常没有1+1=2。
一部《红楼梦》,有人说它是阶级斗争小说,有人说它是爱情小说,有人说它是佛家小说,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既然是都有道理,老师怎么教啊?
学生怎么学啊?
在人文领域里,多义性简直是家常便饭,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块钢锭与另一块钢锭差别不大,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差别很大,而人文学科是面对人,不是面对钢锭。
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86年,发现他们并不把“殖民”当作一个贬义词。
在他们的字典里,在他们的记忆里,殖民就是建设,开拓,开放,到落后地区传播文明,在那里修路架桥,办学校和办医院,就像我们建设大西部一样,激情燃烧的岁月呵。
我们经历了苦斗,我们贡献了多少青春,很多殖民者是这样的记忆的。
但面对同一段历史,被殖民者是另外一种记忆:
洋毛子多坏呵,屠杀我们的亲人,抢走我们的财富,霸占我们的土地和水源,调戏我们的妇女……因为完全不同的记忆,产生了不同的历史书写,以至“殖民”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与西方国家的情况迥然有异。
“文革”也是一段至今未能形成全民共识的记忆。
有些地方一旦出现群体事件,老工人们一上街,就把毛主席的像竖起来,把红旗举起来,高唱“文革”时期的歌曲,去找党委政府叫板。
很多知识分子则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式的红色恐怖卷土重来。
在“文革”中,我家也是一个受迫害者,包括我父亲就是“文革”中自杀的一个教师。
我能体会不少知识分子和官员对“文革”的恐惧,理解他们当年所受到的侮辱、残害、贫困、以及学业上的耽误。
但他们可能也得理解,老工人们可能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他们的“文革”记忆。
就一般的工人来说,他们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较少,享受着“领导阶级”的荣耀,就业稳定,福利稳定,与官员们的收入差距不大,一不高兴就可以贴领导干部的大字报。
那时候,我父亲作为教师,一个月粮票24斤,而工人一般是30斤,重体力岗位的工人是35到40斤。
工人的相对感觉很好,至少是好一些,难道很让人费解吗?
就算他们当年是既得利益者,时过境迁之后,他们现在成为最底层的“既失利益者”了,你能封住他们的嘴,不让他们说话?
几年前,我看到澳大利亚出版的一些资料,发现就在1965年,中国“文革”发生的前一年,离我们不远的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同样的大浩劫,甚至比“文革”更惨烈的悲剧。
印尼的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下,前后共屠杀了200多万人,以至两、三年之内,平均每天杀掉1500人。
仅美国大使馆提供的密杀名单就有好几千。
一点文明也没有,一点人道也没有。
奇怪的是,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文革”惨剧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但印尼大屠杀几乎销声匿迹,我们的传媒不说,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讨论,这是不是有点奇怪?
同样是杀人,难道1965年的杀人比1966年的杀人,就更高贵一点,更仁慈一点、更正义一点?
米兰•昆德拉,写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说过一句话:
文学就是要抗争遗忘。
我想补充一点:
文学抗争遗忘,更具体地说,是要抗争那些偏失的、虚假的记忆,抗争各种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商业寡头权力所强加给我们的遗忘。
第三点,谈谈记忆的造假。
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休谟,曾分析人的感觉能力。
他说人有两种感觉,其一来自真实的体验,比如说下雪了,你感觉到冷,就是真实的感觉。
其二来自符号、信号的灌输,是一种符号反应或条件反射,比如你老是听说蛇咬人,虽然从未被蛇咬过,但时间长了,也会对蛇感到害怕,成了一种疑似的、拟真的、几乎同样有效和可靠的感觉记忆。
但这两种感觉记忆是有区别的,后一种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
曾经有一首歌,《小和尚下山》。
老和尚说你下山很危险,女人都是老虎,会吃人的。
老和尚不停地这样说,于是小和尚下山以后,见到女人可能会真的很害怕。
这就是一种感觉记忆的造假。
历史上经常有这种情况。
50、60年代的革命文学,千篇一律地“忆苦思甜”,说以前地主如何坏,长工如何苦。
可我们下乡当知青,听有些当过长工的说,他们当年农忙时可以吃肉喝酒,东家待人还不错,比“大跃进”时代强多了……这些记忆让我们吓一跳,才知道自己以前的印象不一定靠谱,才知道革命文学的简单化和标签化到了何等程度。
又比如说,谈到欧洲的中世纪,我们都会想到以宗教法庭为代表的一片黑暗。
但我最近看了一个西方史学家的著作,他说这不过是一帮启蒙主义者,在16世纪以后,为了彰显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把前朝故意说得一塌糊涂。
他列举了很多数据,证明中世纪的欧洲人吃肉更多,人均寿命很长,文化有很大的积累和发展。
在这里,我不会就中世纪是否黑暗的问题下一个结论,只是给同学们提一个线索,只是说很多我们以前想当然的东西,觉得天经地义的东西,也许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30多年以来,中国的很多文艺作品正在走向世界,在国际社会获得关注。
其中有一本书,已经成为西方学子们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
此书作者是一个中国人,丈夫是英国人。
她在书里面写到,她80年代第一次到了西方世界,发现了那里有鲜花,让她深感震惊,因为她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花。
这让西方读者特别惊讶:
中国没有花。
有趣的是,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是这位作者的邻居,曾经笑着对我说,这位作者小的时候,经常跑到他家院子里偷花。
她怎么能说在没见过花呢?
同是在这一本书里,她说初到英国的时候,第一次上公共厕所,就跑到男厕所里去了,因为门前的小图标,一个是穿裤子的,一个是穿裙子的,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她说她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裙子。
这当然又让西方读者大为惊讶:
中国连裙子都没有。
到了这一步,这本书的卖点足够多了吧?
刺激性足够强了吧?
问题在于,“文革”时期虽然裙子少一些,但那时候的江青,所谓“文革”的罪魁祸首之一,也穿过裙子,还号召女人们穿布拉吉,就是苏式的那种连衣裙。
还有一本小说,在英语世界名气很大。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军人,与一位护士产生爱情,互相放电。
但是他在老家有一个媳妇,是个小脚女人,于是他百般纠结,在一个痛苦的离婚过程中苦苦挣扎,命运不能不令人同情。
我不知道60年代的中国还有没有年轻的小脚女人,但我知道早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就禁止妇女缠足裹脚。
美国读者不明白这一点,据说小说初稿也不是这样写的,小脚女人这一情节安排是美国编辑要求作者改成这样的,以增强小说在美国市场的吸引力。
我得承认,虚构是作家的权力。
文学不是新闻、不是科研报告,虚构一个小脚女人也未尝不可。
但因为这样的虚构太多,因为这一类虚构被某种政治力量刻意地放大,西方很多观众和读者对中国的记忆就被严重造假。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小脚女人,没有穿过裙子,也没有见过鲜花,可能男人还留着长辫子,还在三叩九拜和茹毛饮血。
当他们2008年来中国参观奥运会,当他们来到广州、上海、北京,难怪很多人的感觉是:
哇,这根本不是中国。
问题出在哪里?
是中国错了?
还是西方的观众和读者错了?
或者说西方的读者和观众从什么地方开始错起,为什么会错?
在座的作家张欣,写过很多生动好看的都市故事和白领故事,但她的笔下没有小脚女人和长辫子,没有张艺谋电影里的那些怪异和腐朽,倒是很可能让不少西方的出版商、记者、批评家、翻译家感到陌生,在他们看来,缺少一种“中国性”和“东方性”。
这也许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内还难于化解和排除的一种文化障碍,甚至有时候会成为国际交往中的短路和翻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定时炸弹。
最后一点,谈一谈记忆书写者的责任。
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重现记忆和再造记忆。
既然我们知道记忆这个东西如此重要,知道记忆这一片汪洋大海里面有那么多暗礁和漩涡,下笔的时候也许不妨对自己有几点提醒:
一是尊重他者。
每个人的肩上都没有扛一个他人的脑袋,更没有扛一大堆集体化的脑袋,因此记忆总是个人性的,是有偏向、有侧重的,是局部和微观的。
这当然很正常,也很正当。
我们都有自由释放自己记忆的权力。
这正是共建民族记忆、人类记忆的坚实基础。
但尊重他人的自由,是自由的应有之义。
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南岛,有一些暧昧的行业,以至有钱有势的某些男人感到特别幸福。
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性放纵的另一方面是性压抑,包括很多农民工,长期处于夫妻两地分居的状态,承受着性剥夺的严酷事实。
海南《天涯》杂志主编,我的继任者,曾说过杂志的来稿情况。
他说,现在男作者来稿的80%是写偷情,女作者来稿的80%都是写离婚。
我不是说,偷情和离婚不是重要的生活内容,也不是说偷情和离婚这种题材在作者的笔下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问题只在于:
那么多玩不起偷情和离婚的人,包括那么多底层劳动者,生存问题尚未解决,吃饭成问题,看病成问题,孩子上学成问题,与这80%有什么关系?
读多了这个80%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文学杂志都按这个比例来打造我们的记忆,进而影响大家对社会的认识,会不会出现一个可疑的偏失?
二是尊重差异,其实这也是尊重他者的另一种说法。
文学有高下之分。
低档的文学可以偏执,高档的文学务必包容。
三流的文学可以标签化,一流的文学应有多义性。
有些文化官员常犯错误,不准抹黑政府,就得把每一个党政官员都写成正面人物;不准美化敌人,就得把每一个地主、资本家都写得青面獠牙。
西方人也常犯这种错误。
前不久我看了一个影片,是表现德国纳粹罪恶的,据说在西方好评如潮。
但我看了非常不满意,因为影片中间出现的纳粹,完全不是人,是野兽。
这种妖魔化在政治上非常正确,但它不尊重敌人,没有对方的视角,就变得极为弱智和矫情,反而削弱了批判的力度。
这就像以前我们中国很多影片,总是把国民党表现得鬼鬼祟祟,獐头鼠目,蛇行鼠蹿的那样。
这十几年好些了,国民党都成了俊男美女,但日本人呢,清王朝呢,以及自由民主派心目中的中国革命呢?
是不是还要妖魔化下去?
这不是说历史和政治没有是非之分,只是说粗糙的、垄断的、偏执的、标签式的批判,因为不尊重对方的视角,不尊重对方的记忆,以及对方记忆的可能性,反而会变得十分脆弱,在效果上往往适得其反。
这样的原则,不仅是要体现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政党与政党之间,也要体现在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之间。
我们眼下有很多少年作家,写年轻人的叛逆,满腔忧愤,批判父母,批判老师,批判社会,这都没有问题。
我尊重你的这种记忆,但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你大概不可局限于这种个人记忆。
你除了理直气壮表现少男少女的记忆以外,你可能还需要尊重你所攻击的老师、家长、社会,尊重他们的记忆视角。
所谓“有容乃大”,大作家有大容量,不会只有一腔要死要活的小资脾气。
其实,每个人都有记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时候显得褊狭一些,不过是自己的一部分记忆进入了沉睡,进入了冷藏。
我们也不用着急。
符号的洗脑与反洗脑不论如何激烈,人的生命存在,人类社会的延绵不息,终究会推动人类心理的自我修复,春夏秋冬,天道有常,包括在一定时候唤醒人们遗失的记忆。
不少父母都有过这种体会:
孩子在成家和就业之前,你说什么他都不听,都听不进去。
但当孩子走向社会了,当上爸爸妈妈了,两代人之间就比较好沟通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变化?
显然,是孩子与父母的生存经验开始接轨,激发出孩子的记忆需求,于是妈妈当年说过什么,爸爸当年说过什么,朋友、邻居、老师当年说过什么,都慢慢的苏醒过来。
对于作家们来说,写作常常就是这样,受到生存际遇的推动,回应心灵的呼唤,实现一次次记忆的复活与再生。
这种复活与再生,常常会使我们在某一天,某一刻,发现自己焕然一新。
【陈少红:
】韩老师讲了一个多小时,辛苦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韩老师的精彩演讲!
我在下面认真听了一个小时,真是感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本书。
韩老师刚刚从很多层面阐述了文学与记忆的关系,我简单梳理一下几个观点。
韩老师讲到记忆,它的共同性问题。
第二个讲到记忆受到主体的制约和筛选,由此产生的差异性问题。
同时还讲到记忆由于文化传播、交流的过程,还有每个人感觉不同而产生的真与伪的问题。
第四点是今天演讲非常重要的一点,谈到记忆在文学书写中的责任。
韩老师特别讲到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集体的记忆。
这个中间本身就包含了筛选、重新建构的过程。
今天下午,这个演讲也使我对记忆如何进入文学,同时文学应该如何重新编码、记忆,有了一些理性方面的认识,非常感谢!
下面我们进入互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