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驴肉火烧文档格式.docx
《河间驴肉火烧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河间驴肉火烧文档格式.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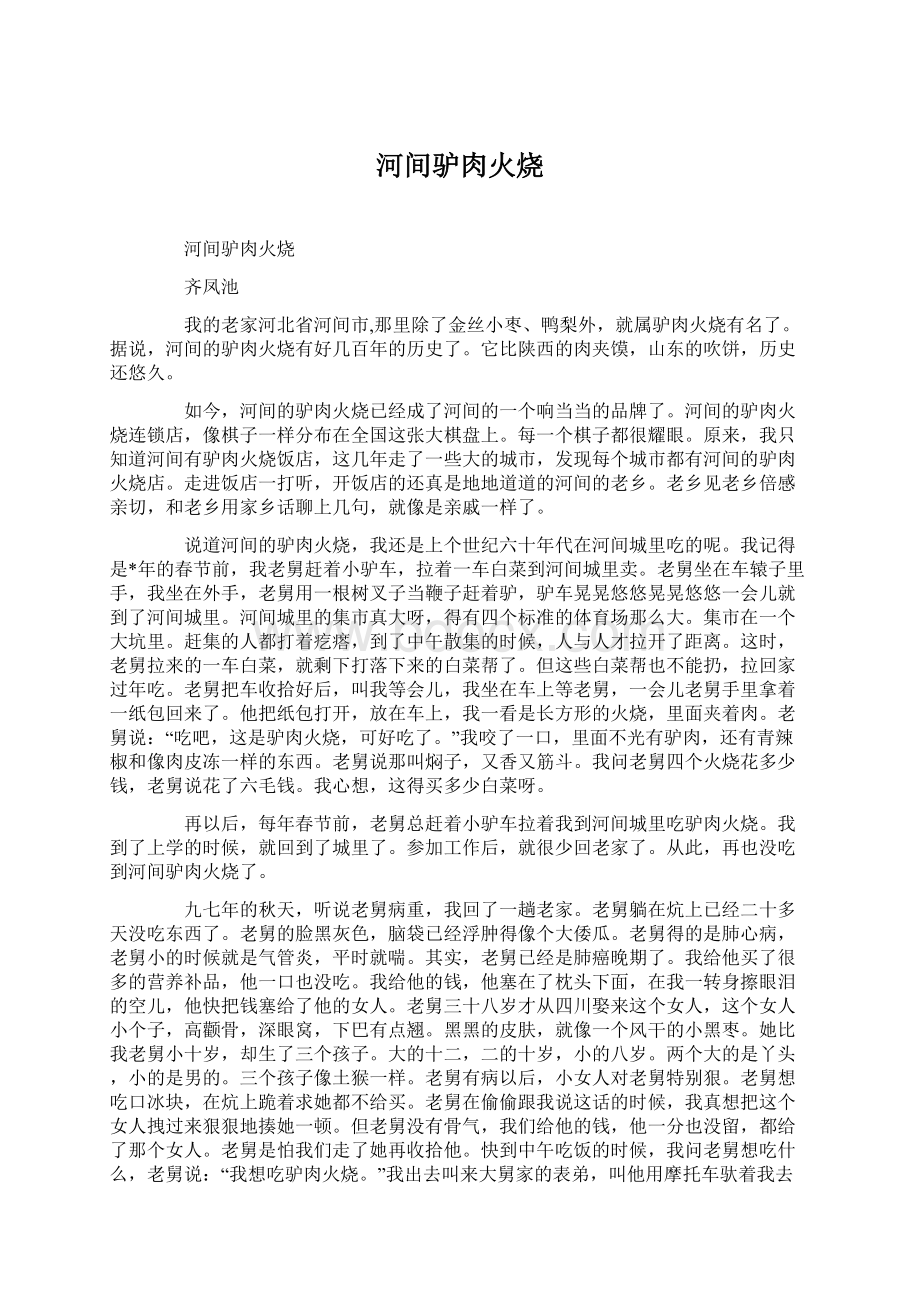
我给他的钱,他塞在了枕头下面,在我一转身擦眼泪的空儿,他快把钱塞给了他的女人。
老舅三十八岁才从四川娶来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小个子,高颧骨,深眼窝,下巴有点翘。
黑黑的皮肤,就像一个风干的小黑枣。
她比我老舅小十岁,却生了三个孩子。
大的十二,二的十岁,小的八岁。
两个大的是丫头,小的是男的。
三个孩子像土猴一样。
老舅有病以后,小女人对老舅特别狠。
老舅想吃口冰块,在炕上跪着求她都不给买。
老舅在偷偷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真想把这个女人拽过来狠狠地揍她一顿。
但老舅没有骨气,我们给他的钱,他一分也没留,都给了那个女人。
老舅是怕我们走了她再收拾他。
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问老舅想吃什么,老舅说:
“我想吃驴肉火烧。
”我出去叫来大舅家的表弟,叫他用摩托车驮着我去河间城里。
半个小时我就买回来了驴肉火烧。
我把驴肉火烧放在老舅的枕头旁边,叫老舅吃。
老舅的眼泪刷刷地流了出来,泪水一直流到枕巾上。
最后,老舅用被子蒙住了脑袋,唔唔地哭起来。
我在老家住了十几天,一直到老舅去世。
我给老舅买的那十块驴肉火烧,老舅连块渣也吃到,全被那女人和三个孩子吃了。
老舅只闻到了点驴肉的香味儿。
其实,老舅要吃驴肉火烧的目的我非常清楚,他是想叫我吃,但那女人又不给他钱,所以说自己想吃。
结果,老舅到死也没吃到驴肉火烧。
发丧老舅的那天,我在河间城里买四十八块驴肉火烧,因为老舅正好四十八岁。
我在老舅的贡桌上摆上了驴肉火烧。
我把剩下的全扔在了送老舅去墓地的路上。
我扔一块,那女人闭一下眼,好象那驴肉火烧砸在了她的良心上,砸在了她的疼痛之上。
如今,我们家门口也开了两家河间驴肉火烧店,我爱吃,也想吃,但就是没买过。
因为看到驴肉火烧,我就想起当年老舅给我买驴肉火烧时的情景,闻到驴肉的香味,我的鼻子就发酸,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下来。
河间醉枣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河间市,民国以前叫河间府。
你可别小瞧河间,过去那地方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清朝的纪晓岚诞生在河间。
另外,河间还是向大清皇宫里输送太监人才的基地。
据说现在国内就剩下一个太监了,就住在天津,谁要想见他一面得花几千块钱的见面费。
听说那太监也是河间人。
其实这些都不算出名,最出名的还得是为《诗经》作续的毛苌。
现在河间的西诗经村和君子馆村,自古至今从未更改过。
汉代中央政权尊崇儒学,学术空气浓厚,于是长年耳濡目染,得到伯父毛亨亲传的毛苌,遵照伯父的遗愿在河间开始传诗讲学,地点就是诗经村及北面三里处的君子馆村。
西汉孝景前二年,(公元前155年)景帝刘启封他的儿子刘德为河间王,也就是献王。
刘德对毛苌十分尊重,封他为博士,传授弟子,自此《诗经》由河间传向中国更广阔的区域。
因此,河间太了不起。
河间不仅出名人,而且河间的鸭梨、金丝小枣也是享誉全国。
走进河间的土地,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
平原上是行距均匀的树行,有梨树,有枣树。
河间国内有名的鸭梨之乡,河间的金丝小枣在世界上有名。
每年春天枣树一开花,整棵树就被签定了合同。
我的老家在河间东九吉齐家村,姥家在高家坞。
两个村相距一里。
我小的时候是在姥姥家长大的。
我的祖父祖母去世的早,所以就把我寄养在了姥姥家。
姥姥家在村子的最南面,出门就是野地。
村子南面有一片柏树林,里面有好几座大坟,坟的旁边有石人、石马、石桌、石凳。
听姥姥说,这是太监坟,这里埋着好几个太监。
长大后我才知道河间这个地方不仅出名人,而且出太监。
我姥姥那个村就出了好几个太监。
太监的家人都搬到了京城里去住了。
就把身上零件不全的太监留在了坟里在村头坐着。
文革期间,坟地里的石人、石马、石桌、石凳都被砸了,树也被砍了,坟也被平了,栽上了枣树和犁树。
我姥姥家的院子里有棵枣树,就长在东墙根边,上了墙头,就可以摘到枣了。
枣树有碗口粗,树有一房多高,树的脑瓜特别大,每年都结很多枣。
每年秋天枣快熟的时候,我发现枣被阳光晒的那面特别红,不被晒的那面碧绿。
姥姥说:
“枣会转,跟着太阳走。
”我早晨起来看枣红的那面就朝着太阳,到了晚上,枣红的那面还冲着太阳。
姥姥说的枣跟着太阳转是真的。
枣熟的时候,不用摘,用竹竿打。
姥姥在树下的地上铺一块席子,我用竹竿一打,枣就掉下来了。
打下来的枣,不用洗,用手搓挫,或在衣服上擦擦吃最好。
姥姥说,水一洗就不好吃了。
我把枣在衣服上擦擦,放在嘴里一咬,真是又甜又脆。
那股甜味跟任何水果都不一样。
有一种钻进肺腑的感觉。
姥姥把又大又红的枣挑了一笸了,她在碗里倒了酒,找来一个坛子,她用筷子夹着枣在酒碗里一沾,然后放进坛子。
她沾一个放一个。
我问姥姥:
“把枣放进坛子里,再把酒倒在里面不行吗?
”姥姥说:
“那不行,必须把枣都沾上酒,酒多了不行,枣会烂的;
酒少了,枣醉不了”。
姥姥把枣沾上酒,放进了坛子里,酒没剩下,坛子里的枣正好满了。
姥姥用塞子把坛子口堵上,在上面又用泥封上,就把坛子放在阴凉的西厢房里去了。
“啥时候可以吃”。
姥姥说,等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从姥姥做醉枣那天起,我就盼着快快过年好吃醉枣。
一天一天过得真慢哪!
但总算盼到了过年。
三十那天还不给吃,非得到了初一早晨有人来拜年了才给吃。
初一吃了起五更的饺子,姥姥从西厢房搬出坛子,打掉坛口的泥,用锥子启开木头塞,一股醉枣的味迅速在屋里弥漫开来。
姥姥用筷子夹出一大碗,给我也夹出一小碗,然后把坛子又盖上塞,又放到了西厢房了。
我用手捏着枣,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
一股浓浓的酒香带着淡淡的枣味和甜味,迅速沁入心脾,醉枣的肉已经不脆了,但肉质比脆的时候更好吃,更有口感。
姥姥给我的那一小碗醉枣也就是二十几个,不一会我就吃没了。
可我还想吃,就把目光盯在了那一大碗上了。
拜年的人陆陆续续,很少有人吃碗里的醉枣,吃的也就是象征性的吃一个尝尝。
剩下的那些醉枣,姥姥叫我全吃了。
那年过了春节,出了正月,我就回城里上学了。
从姥姥家回来有四十年了,我一直没吃到老家的醉枣了。
因为再想吃姥姥的醉枣,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姥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去世了,在姥姥去世的二十多年里,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姥姥做醉枣的情景,每次想起姥姥,我就情不自禁地回味出醉枣的甜味和眼泪流到嘴里的苦涩味道。
叔叔的梨树园
河间的金丝小枣很有名,但是,河间的鸭梨更有名。
河间的鸭梨皮薄肉厚含糖量高,如不小心掉在地上,就能摔成八瓣儿,这一点也不是夸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去老家,正赶上鸭梨大丰收,我和叔叔家的弟弟到梨园摘梨。
弟弟在树上摘,我在树下接,他摘一个往下扔一个。
有一个大鸭梨我没接住,结果掉在了地上,摔了个稀酥。
我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弟弟说:
“没什么,摘梨时经常摔碎梨,小心点就是了。
”梨摘下来,放在筐里,也要加小心,不要相互磕碰,碰破了皮就不好收拾了。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烂。
这也是弟弟告诉我的。
我们把摘下来的梨,放在地窖里,喝了酒的人是不许下窖拿梨的。
梨要是沾了酒味,也会烂的。
放在地窖里的鸭梨,要等到春节期间才拿出来卖,那样可以卖个好价钱。
我叔叔家承包了一片梨树园,有三百多棵梨树。
按一棵树结二百斤梨,三百棵树能结六七万斤鸭梨。
当时市场上的鸭梨价格是一块钱三斤,我叔叔承包的这片梨树一年能收入两千多块。
那时我上一个月的班,刚开六十多块钱。
一年最多能开七百多块,叔叔的梨园一年就能挣两千块。
我叔叔家的日子,在村里也是比较富裕的。
叔叔一天天就守在梨树园,他吃在园里,睡在园里。
叔叔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梨树园里,这片梨园被叔叔收拾得象片世外仙境。
梨园的四周是用槐树条编织的篱笆,槐树条长得非常茂盛,每根枝条上长着一寸长的刺,人要想钻进去非得挨扎,槐树条的篱笆成了一道安全的屏障。
叔叔在梨园干了一个承包期就不干了,打算转给了别人。
因为叔叔的背上长了一个象核桃大的疮,整天流脓打水的。
每天叔叔就用棉花沾,等棉花洇透了,再换上干净的。
后来,疮越来越大,越烂越深。
叔叔实在受不了了,就去了河间医院。
到了医院一检查,是淋巴癌,已经扩散了。
叔叔也没住院,就回家了。
叔叔每天就躺在梨树园的小房子里,每天早晨还出来转转。
看看他收拾的梨树。
每次看到挂满树的鸭梨,他的脸上总浮现出一层蜡黄、紫青的微笑。
叔叔的表情其实是很痛苦的。
他的病和他心是疼痛的。
那年,树上的梨结得那叫个多,梨长得也特别的大。
雪白的大鸭梨上都长着一层白霜。
春天的时候,梨树开满雪白的花时,叔叔说,今年一定多结梨。
等花落了,坐果了,枝头上的小梨一嘟噜一嘟噜的,真叫人喜欢。
客商一来,就把整片树按三百钱一棵订下了。
那年梨真卖了个好价钱。
三百多棵树的梨卖了将近十万块钱。
但是,叔叔没等到客商来拉梨,就去世了。
叔叔死的时候,流了有一洗脸盆的黑血。
等血不流了,叔叔就咽气了。
人们把叔叔从小屋里抬出来,穿过梨树的时候,树枝上的鸭梨直碰人们的脑袋。
因为鸭梨结的太多了,把树枝都压弯了。
雪白的大鸭梨上挂着一层白霜,有的还挂着水珠。
就象鸭梨也含着眼泪,被人们一碰就哭了。
叔叔死后的第二年,梨园没有承包给别人,由弟弟继续承包干。
但,梨的产量明显少了。
梨园也开始荒芜了。
而且鸭梨的价格也下来了。
弟弟承包的梨园,不但没挣钱,而且还年年赔了几千块。
后来,这片梨树园就转给了别人。
别人承包后,也赔钱。
再后来,这片梨树园就没人愿意承包了。
村里请风水先生给看了看,风水先生说,这片梨树累死了。
说我叔叔死的那年,梨结的太多了,梨树的元气和梨树的魂也和叔叔一起死了。
从此之后,这片梨树就荒芜了。
到了两千年以后,村子扩建,那片梨树全砍了,盖上房子。
我叔叔家的新房就建在了梨树园里。
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看到这片新房,就想起从前的那片梨树园,想起梨园就想起我的叔叔,想起我的叔叔,我就止不住泪水和悲声。
河间饺子粥
我老家沧州河间有一种家常饭叫饺子粥。
我小的时候,在老家经常吃。
平时不过年不过节的,赶上集市了,姥姥拿两个鸡蛋换一缕韭菜,然后打几个鸡蛋,包一盖帘饺子。
饺子是两种面的,有一半是白面的,有一半是白薯面,白面的是给姥爷和我吃的,白薯面的是姥姥的。
姥姥把饺子包好后,大锅里的水就烧响边了。
等姥爷下地回来,饺子就下锅。
我坐在门前的石台上,晒着中午的阳光,浑身暖洋洋的。
门前过去了一辆牛车,车上坐着几个下地干活的人,我姥爷肩扛着锄,走在牛车后面,我看了姥爷后,飞快地跑到屋子告诉姥姥,姥爷下地回来了。
这时姥姥坐在大灶旁边正烧火,水开了,姥姥掀开锅盖,姥先用勺子把水搅动转起来,然后把两样面的饺子下入锅内。
她用勺子轻轻地擦着锅底,把下到锅里的饺子也转动起来,等饺子都飘起来了,姥姥把锅盖盖上,锅开之后姥姥又浇了一瓢水,随后,她用小瓢舀了一碗玉米面,手抖动着,把玉米面洒到饺子锅里。
等水再开的时候,饺子粥就熟了。
姥姥用大碗给姥爷盛了一碗全是白面的饺子粥,给我也盛了一小碗。
她给自己也盛了一碗。
但她碗里一个白面饺子也没有。
我问姥姥怎么不吃白面的,姥姥说,她不爱吃白面的,就爱白薯面的。
后来我才知道,姥姥哪是不爱吃白面的,她是省下来叫姥爷和我吃。
姥姥做饺子粥,也是为了省些粮食,怕饺子汤白搭了,在汤里洒点玉米面,当粥吃。
我回到城里后,家里也做过几次饺子粥,但饺子全是白面的,饺子被我们捞出来吃了,粥却剩下了。
孩子们没有吃过饺子粥,不知道饺子粥的味道,更不知道我做饺子粥的寓意利用意。
他们总是挑饺子吃,同时,感到吃饺子粥是一件新鲜的事,觉得好玩。
其实,这哪是什么好玩呀,我每次吃饺子粥的时候,都会想起我的童年,想起我的姥姥。
我上班之后,经常回老家去,每次去都给姥姥带很多好吃的东西,临走还要给姥姥留下零花钱。
当我每次要走的时候,姥姥总是拉着我的手,不愿松开。
当我出了村子的时候,姥姥还站在村头的土坡上向我望着。
其实,姥姥是看不见的。
她的双眼在我回城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每次,见我的时候,她一是听我的声音,二是用手摸我。
后来她的耳朵也听的不准了。
她就摸我的头,她一摸就知道是我回来了。
姥姥的眼睛还能看见点东西的时候,每年冬天我们都把她接到城里,住上一冬。
可后来,她一天天岁数大了,就说什么也离开老家了,她怕这把老骨头扔在外面。
所以,她一直到老死,也没离开她那间老屋。
姥姥去世快二十年了,姥姥做的饺子粥,也断顿了快二十年。
我多想再吃一次姥姥做的饺子粥啊,尝尝粥里的白薯面饺子的味道。
祖父留下的遗产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祖父在去世前,请村里的长辈和村里的先生把家里的房子和值钱的家具列了一份清单。
我父亲哥仨,每人分了三间房子和部分家俱.我作为齐家的长孙也分得了一份.我祖父住的那三间老房和屋里的两个枣木立柜分给了我.我伯父和我父亲都在外地,也不打算再回老家,就把分的房子给了我叔叔.分给我房子,祖父、祖母先住着,但分单已经由父亲从老家带了回来。
64年我祖父去世了。
六八年我祖母也离开了人世。
分给我的房子就先由叔叔家住着。
分给我伯父和父亲的房子叔叔没几年就给卖了,叔叔一家六口人就住在祖父分给我的房子里。
我长大后,父亲给我看过分单,分单是在毛草纸上写的。
我看了只是嘿嘿一笑。
其实,分给我的房子我也不能要。
我又不能将房子安上轱辘推回来,再说,我叔叔家还有两个弟弟。
就是非得给我,我也不能要。
到了九十年代,农村规划,根据宅基地和人口重新分地盖房。
我叔叔在梨树园重新盖了三间新房,两个弟弟每人也盖了三间,分给我的那三间老房要拆了村里才给新宅基地。
由于房契和分单都在我这里,叔叔要想在村里再要一块宅基地必须得有我本人签字村里才给。
于是,我叔叔从老家来了,叔叔从没有来过我家,我知道叔叔和我伯父有矛盾,俩从来不通信,我父亲多次劝我叔叔,我叔叔认为我父亲和我伯父一心,不向着他。
另外,叔叔怨两个哥哥都到了城里,把他留在了乡下,照顾老人,他心里有一肚子的委曲,所以跟两个哥哥从来不走动。
叔叔来我家好几天了,每天好吃好喝,但他一直闷闷不乐,象有什么事不好开口,到了第五天我父亲问叔叔,有事你就说,需要钱你就说话。
我叔叔吞吞吐吐地说了,我祖父留给我的那三间老房的事。
我父亲说:
“连我的房子都不要了,你侄儿的房子他也不要。
”我叔叔说:
“我想把那三间老房拆了,重新再盖,然后跟村里再要三间宅基地。
”我父亲说:
“你愿意拆就拆吧,钱不够了我给你添。
“那三间老房的房契村里要,光光口头说不算,必须得有房主的签字。
”我父亲把我叫来,给叔叔写了一张字条,签上了我的名字,交给了叔叔。
叔叔说:
“光签名不行,还得盖上章,印上手印。
”按照叔叔的要求,我全办了。
这时,我叔叔的脸上才见到了一点笑模样。
他把字条叠好,装在了内衣兜里,第二天早晨就回老家了。
九五年我回家的时候,叔叔在梨园盖了六间正房,非常漂亮,院子也非常宽敞。
院墙外栽着一排枣树,大门冲东开,门楼是用彩砖镶嵌的,老远一看明光闪闪。
我那三间老房也没拆,由我弟弟住着。
院墙是新垒的,屋里做了简单的装修,门窗全换上了塑钢的,而且安上了茶色玻璃,过去老房子模样,一点也看不到了。
我弟弟比我小六岁,在村里的小学当老师,他细高的个儿,白镜子,小眼睛,单眼皮,脑袋长的有点象枣核,说话办事是典型的小土财主作风。
我到家的第二天,他叫我和他到集市上去买菜,看我想吃什么买什么。
到了集市上,他看到卖鲤鱼的了,他说:
“哥,咱买几条鱼,给你熬着吃吧。
”我说:
“什么。
”他挑了四、五条大的鲤鱼,放在称上。
约完之后,要算账交钱了,他不掏钱。
我只好把钱付了。
到了卖肉的地方,他说:
“哥,咱再割上几斤肉吧。
“好,给我们割几斤。
”卖肉的好象也相着我弟弟,一刀下去割了十几。
我付了钱,弟弟拎着肉,拎着鱼,见了村里人就说:
“我哥从城里来了,不买肉不买鱼怎么行呀。
”中午吃饭的时候,弟媳妇熬了一条大鱼,炒了一个菜,剩下的肉和鱼冻了起来。
吃饭的桌上没有酒,我弟弟问我:
“哥,你喝酒吧?
”我掏出十块钱,叫来上小学的侄女,“去给伯父到小卖部买瓶酒,剩下的钱自己买点吃的。
”小侄女接过钱雀跃着飞出房子,一会儿,弟媳拿着一瓶沦州白酒进来了。
我弟弟不会喝酒,喝一杯脸就象红布一样了。
我叫弟媳妇给我抓一把花生米来,我就着花生喝酒。
熬的那条鲤鱼我一筷子也没夹,两个侄女和我弟弟把一条五斤多的大鲤鱼吃的就剩下一个鱼头。
吃了中午饭,弟弟到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去了。
我一个人站在祖父分给我的老院子里,看着装修一新的老房子,回想着我小时候,老房子的模样。
想到了房子我又想起了爷爷的模样,我心里不由一阵酸楚。
老房子变了,院子也变了。
就连我的弟弟也象重新装修过了一样,好象与我失去了血缘和亲情,而且变得非常陌生了
姥姥炖干菜
我小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人口多,父亲工资收入少,母亲怕我挨饿,就把我送到了沧州河间的姥姥家。
姥姥家生活比较好,家里有劳力,打的粮食,吃饭一点不成问题。
就是平常吃不到新鲜的蔬菜。
特别是到了开春以后,连干菜叶子也很难吃到了。
赶上姥姥家来了客人或是远道来的亲戚,姥姥就从盐缸里拿出一块腌的猪肉,切上十几片,将房梁上挂着筐摘下来,从里面拿些干豆角、干萝卜、干芥菜、干茄子用开水一沏,泡上个把钟头,等干菜泡软了,洗净切成丝,放入大锅里一炒。
等炒出香味来,放酱油,咸盐,花椒,大料,加足水,再把腌的猪肉片放在锅内。
开锅以后,姥姥在锅边贴一圈白玉米面饼,盖上大锅盖,开始烧火。
我坐在姥姥身边,像个小馋猫似的盼着饭菜快点熟。
见柴草快烧没了,姥姥叫我到院里的柴垛上抱点柴禾来,我飞快地跑到院里,抱来柴禾,就又守在姥姥身边等着。
大约抱了有七八次柴禾,屋里就弥漫了肉炖干菜的香味了。
我守在锅台旁边问姥姥:
“可以吃了吗?
姥姥。
“再等会儿,要不菜烂不了,嚼不动。
”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姥姥终于把锅盖掀开了。
巴掌大的玉米饼子一面雪白一面焦黄,锅里炖的干菜还开着锅直冒泡。
满屋弥漫着炖干菜的香味。
姥姥先用勺子给我盛了一碗,我端着到院里的碾台上吃去了。
姥姥给来的亲戚盛了一大碗,放在桌上,自己又到院子里去给猪添食了。
姥姥看我碗里的菜快吃完了,她拿过去在锅里又给我盛一点。
这是我在姥姥家吃得最香,最顺口的一顿饭了。
回到城里后,我就再也没能吃到肉炖干菜了。
但每当想起在老家的日子,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姥姥炖的干菜。
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了,吃腻了大鱼大肉,开始思念家常便饭和地里的野菜。
于是许多大饭店里也增加了许多老内容,新花样。
当年我在姥姥家吃的炖干菜,现在许多大饭店就有,但叫法不一样,有的叫乱炖,有的叫干炖岁月。
虽然名字叫法不一样,但菜的内容是一样的。
我每次去饭店都点这道菜,尽管色香味浓,但吃的感觉还是差点味道。
我始终找不到当年姥姥炖干菜的那种滋味和幸福了。
因为姥姥已过世多年,那段难忘的日子也早就搁浅在了我记忆中最醒目的地方了。
姥姥包的菜饽饽
我小的时候,正好赶上挨饿,家里怕我饿坏了,就把我送到了沧州的姥姥家。
姥姥家的日子也不是很富裕,但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每天三顿饭有稀饭也有干粮,就是很少吃新鲜的蔬菜。
姥姥家有几亩菜地,春天和秋天什么菜都种,但摘的菜都卖了。
剩下的不好的和卖剩下的留着家吃。
但这两个季节还是能吃到菜的。
俗话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一进如二伏,地里就全种大白菜了。
因为大白菜产量高,可以多卖钱,姥姥家的那几亩地全种上了大白菜。
到了下霜之前,地里的大白菜就长满了芯,棵棵成。
上称一约,每棵都有七八斤,大的有十来斤。
砍下来的大白菜,打落下来的菜帮,好的留着吃,老的菜帮喂猪。
成车的大白菜往家里拉,我小舅把白菜放进菜窖里,留着过年的时候卖个好价钱。
我小舅码白菜的时候,码一层白菜上面铺一层高粱秸,小舅说,这样可以通风,白菜不烂。
小舅整整码了一菜窖白菜,起码也得有上万斤。
剩下的瘪白菜,姥姥把它挂在用草拧成的绳子上,晾起来。
整个院子晾了好多的瘪白菜。
上冻后,小舅推着独轮车开始串村卖白菜了。
还没到春节,那一窖大白菜就快卖没了。
这时我们连菜帮也吃不上了。
一天三顿吃咸菜。
开春的时候,地里一片枯黄,连一点绿色也看不见。
可以吃的野菜还躲在土地的被子下面睡大觉呢。
下了两场春雨后,地里才见点点绿色在闪烁。
为了能吃到菜,姥姥从草绳上摘下几棵干白菜,放在大盆里,用开水一泡,等菜软了,用凉水洗净了,切成馅,再卖几根香油果子,切碎了掺在干白菜馅里,包菜饽饽。
姥姥用开水烫一盆玉米面,用凉水沾着手,把玉米面拍成薄饼,把干白菜馅包起来,然后贴在大锅的边上。
姥姥把锅边都贴满了,锅里的水也就开了。
姥姥把锅盖上,开始烧火,我在旁边看着。
姥姥手里的小木棍在灶堂里不停地挑火,使火庙更旺。
当柴草快烧没了,姥姥叫我到院子里的柴堆再抱点柴火来。
我小跑着抱来柴火。
两抱柴火烧完之后,姥姥就不烧火了。
过了十几分钟,姥姥才把锅盖掀开。
姥姥用铲子把锅边的菜饽饽铲下来,放在浅子里,面朝下,嘎咯朝上。
焦黄的嘎咯又香又脆,我手捧着菜饽饽吃起来。
里面的馅又香又烂糊,特别好吃。
这是我第一次吃干白菜馅的菜饽饽,也是最后一次吃姥姥包的菜饽饽。
第二年的春天,我就回了城里上学了。
从那以后,我很少回老家。
十年八年回一次,也想不起来吃,就是我真的想吃,姥姥也不会给我包了。
因为姥姥在我回到城里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再想吃,只能回忆姥姥包饽饽的情景,梦里咀嚼姥姥包的菜饽饽的味道了。
老屋
推开栅栏,屋檐上的瓦松又长高了许多,儿时在上嬉戏的那块青石依然卧门旁。
门虚掩着,父亲没在家,大概又去北山了。
我推开那扇用旧铁皮堵着漏洞的屋门,迈进那已像张弓的门槛,一缕光柱透过屋顶伸道地面,墙上又多了几道雨水淌过的痕迹。
说老屋已千疮百孔,饱经沧桑并不是夸张。
因急于赶路,我有些累了。
于是躺在散发芳香的土炕上,头倚着那个裹过我童年的发卷,好温馨!
那粗布被面贴在脸上好柔软好舒适,这是妈妈亲手织的!
蓦地,我的心猛地一颤。
手印,墙上那个手印又把我拽进了童年。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总是弓着瘦弱的身子不停地咳着。
晚上,妈妈在昏暗的油灯下吃力地摇着纺车,我在一旁搓着棉卷,那雪白的棉卷像春蚕一样快速地吐着丝线。
纺累了,她就坐在炕上,眯着眼睛,一边缝补衣裳,一边给我讲着“凿壁偷光”的故事。
三个哥哥趴在炕沿上捏着铅笔头,在用过几遍、被橡皮擦出小洞的本上写着作业。
爸爸的头刚沾上枕头,就已鼾声如雷了。
妈妈急促的咳声把我从美梦中惊醒。
妈妈已咳成一团,脖上的青筋似乎就要崩裂,她用枕头用力地堵住嘴,恐怕吵醒劳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