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淡而内奇陶诗的审美追求文档格式.docx
《外淡而内奇陶诗的审美追求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外淡而内奇陶诗的审美追求文档格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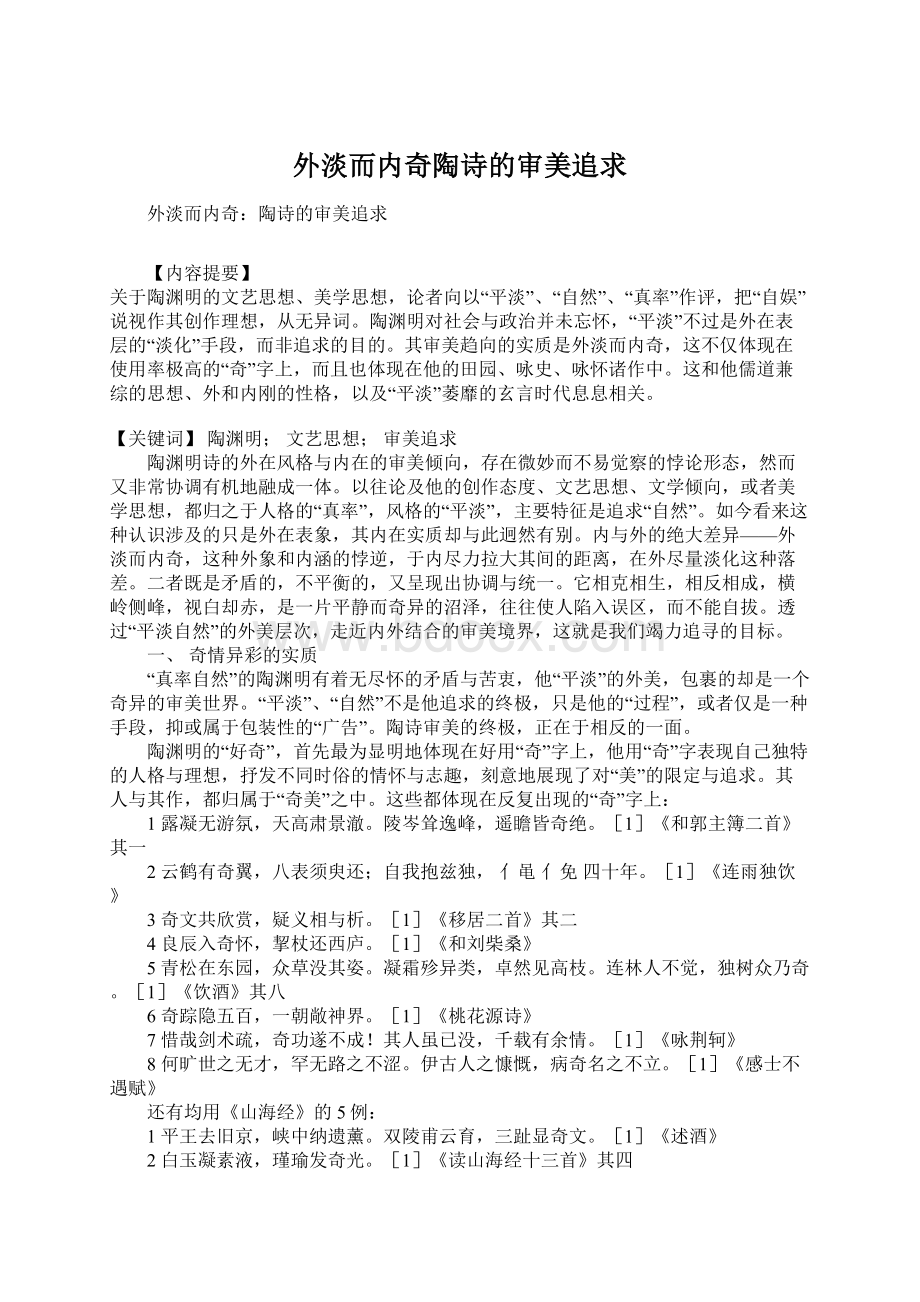
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1]《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2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
自我抱兹独,亻黾亻免四十年。
[1]《连雨独饮》
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1]《移居二首》其二
4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
[1]《和刘柴桑》
5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1]《饮酒》其八
6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1]《桃花源诗》
7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1]《咏荆轲》
8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
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
[1]《感士不遇赋》
还有均用《山海经》的5例:
1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
[1]《述酒》
2白玉凝素液,瑾瑜发奇光。
[1]《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四
3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
[1]《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五
4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
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1]《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二
5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
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1]《蜡日》
加上《读史述九章·
管鲍》的“奇情双亮”,《祭从弟敬远文》的“爰感奇心”,为外祖父所作传记的“奇君为(衤者)褒之所得”,凡16例。
超出了每被人们称道的“化迁”、“大化”的数量,在不丰的陶作中,数量不能说不多。
而且从38岁开始,一直用到暮年,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不能不算作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这些为数众多的“奇”字,长期为我们所忽视。
这些“奇”字,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
奇怀、奇心、奇情;
奇踪、奇功、奇名;
还有奇文、奇树、奇鸟、奇色、奇光、奇翼、奇歌以及奇绝。
用《山海经》的5例,或许没有多少深意,但至少见出诗材选择的特异与开阔,都和《山海经》奇异事物相关,此前无人如此集中地描写,这显示了他“好奇”的一面。
其余几例就颇有些意味:
例1与例5,本为平常的山和树,却从中看出或想出“奇”来。
特别是后者,与例2一样,均为自况之词,或为独飞八表的云鹤,或如卓然挺立的高松,均寄托与众不同的志趣与审美趋向。
可以看出作者独立不群的奇逸人格。
例4的“奇怀”仅在平常的“良辰”中发想,平静中见出“奇”来,很能显出陶之为人为诗的本色。
例7的荆轲欲求之“奇功”,例6通向桃花源“理想国”的“奇踪”,其奇绝或胸中之“奇怀”就自不待言。
他好读书,且好读奇书,从例3可看出来。
让他自己说,便是“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1]《读山海经》其一。
还有“好奇”的《史记》使他引发了那么多的感慨。
就是“周王传”,即出土不久的《穆天子传》也进入视野。
读奇书而生“奇怀”,有奇怀而自具“奇心”,因而对“奇功不成”、“奇名不立”自然就有许多感慨,就有不少的悲愤、沉痛与激烈。
总之说起襟怀、心意、志趣、理想、功业、名声,乃至所读之书,所想之歌,甚至山石、峰岑、树木、飞鸟,都烙上“奇”字的鲜亮印记。
平平淡淡的陶渊明,怎么发出这许许多多的奇情异想,奇绝得让人惊诧!
这些奇绝异语,在他淡化的一生与诗文里,一经发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对于他的人格与诗风,都须重新审视一番。
至于审美追求,如果仍停留在“真率”、“自然”、“平淡”上,似乎就再不能那么惬人心意。
以上诸多“奇”字,和他审美追求最为密切的,应是《饮酒》其八的“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陶诗之美是人格化的,他的审美追求极境,亦属人格化的。
他不愿做普通的像“连林”之树的人,企求“卓然见高枝”,岁寒而后凋式的人格美。
这种人格美在“众草没其姿”的春夏是显不出来的,只有“凝霜殄异类”时俗树凋落,松树仍青,方显高枝之卓然,突现出独特与奇异。
东篱之秋菊与东园之青松,无不寄托岸然自异、远弃流俗的胸襟抱负。
清人温汝能《陶诗汇评》卷3说:
“此篇语有奇气,先生以青松自比,语语自负,语语自怜,盖抱奇姿而终于隐遁,时为之也,非饮酒谁能遗此哉!
”“奇树”所体现的“奇气”与“奇姿”,正是他紧接下一首的“禀气寡所谐”独立不群的性情流露。
所追求的人格与企望的审美境界,就是独特与奇异。
这里只表示了在外界自然变化中的显示,那么对这种奇绝独异美的追求方式与手段又将是怎样的呢?
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会看得更为清晰:
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位从弟颇得陶渊明风范之仿佛,敬远的性格志趣爱好亦与他相近。
他向这位知己敞开心扉,倾诉自己绝大的孤独与寂寞,自叹自逊而又自尊自宽,俯仰之间盘旋跌宕出一股凛然劲直之气,傲物自高之意隐约可见。
按《宋书》卒年63岁说,则此诗作于距归隐尚有两年的39岁。
此为示志亮意之作,看他那铁心“栖迟”隐居的样子,很可能与桓玄即在本月初公开篡晋称楚有关,开口“寝迹”、“貌与世相绝”,闭口“荆扉昼常闭”,颇有“声明”性质。
此前四年即安帝隆安三年冬,他已入桓玄幕府,隆安五年冬丁忧家居,作此诗已居忧整两年。
时安帝被桓玄迁居浔阳,无论是从晋从玄,在当时于渊明都很便捷。
看他“平津苟不由”不屑一顾的语气,似有不愿火中取栗的理智。
清人陶必铨说:
“是年十一月桓玄称帝,着眼年月,方知文字之外所具甚多。
”[2]卷3引陶渊明诗文一涉及到政治,便非常谨慎。
诗题若不标示年月,他那绝不会无动于衷的心情,即“文字之外所具甚多”的想法,便无法从文字中揣知。
我们特感兴趣的,是这诗中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两句,或许为写雪而写雪,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13还透过一层说:
“‘倾耳’二句写风雪得神,而高旷之怀,超脱如睹。
”清人张玉谷亦云:
“就雪申写二句,声销质洁,隐以自况,不徒咏物之工。
”[3]307不管其或然或未必然,无论是否有此用心,如上文所言陶诗美属于人格化的审美,我们完全可以用此二句作为打开陶诗审美趋向的一把钥匙:
他追求诗美的方式与境界,真如他笔下的这场大雪,他追求美的过程与形式就像雪之飘落——“倾耳无希声”一样;
所达到的境界与效果,亦如雪之“在目皓已洁”一般。
陶诗乍看平淡无奇,甚或散缓乏力,熟视却淡中有味,平中含奇。
平淡的外表,或者说特意淡化的外在,却包裹着让人惊讶的内在。
以“无希声”的运作,达到“浩已洁”未能轻易料到的效果。
如果说前者属于道家“大音希声”的黠慧,后者则带有儒家“大济苍生”的执着与憧憬。
陶之思想儒道兼综,其审美追求亦出于二者相济互补,而“在目浩已洁”的另一具象,即确属自况的“独树众乃奇”,它们共同展示陶渊明审美追求的同一旋律:
外在的淡化与内在奇特的交融,平淡与奇情异彩构铸为一体。
二、田园奇情异彩的体现
最能体现陶渊明的审美追求与诗美境界的,莫过于他的最负盛名的“田园诗”了。
他的田园诗,既是诗化的田园,美化的田园,也是人格化的、哲理化的田园。
当然还要包括疲倦与贫穷,饥馁与冷冻,灾害与不幸。
所以他的田园诗是由省净的诗语,独立的人格,以准“农民意识”的哲思浇灌出来的,由付出“君子固穷”代价换来的,由对“八表同昏”的官场决裂后愤发出来的。
对此,须以足够的“综合治理”,避免以往解读误差;
否则重复无谓的讨论,只能陷入积淀已久的误区。
我们曾经指出他的田园诗是由“田园世界”与“官场世界”的对峙构铸的,田园的“风光”是由厌恶且横眉冷对的“车马喧”与“樊笼”作参照系,强烈比照出来的,所以这类诗并不“平淡”[4]85-86。
这里仅就他纯粹的“田园风光”,其审美追求,不是“静穆”,亦非“平淡”、“自然”、“真率”,而是具有更深厚更广阔的社会意义。
陶诗凡123首,其中纯属于田园风光的并不多。
若按文学史家的划分,弃官前有《和郭主簿》二首、《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荣木》等,弃官后有《归园田居》5首、《饮酒》、《杂诗》、《咏贫士》等组诗中一部分,以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等,约20多首,占不到1/6。
而这些亦并非纯写田园风光或田家乐。
若以较纯粹眼光看,就剩下《和郭主簿》其一,《归园田居》5首,《怀古田舍》其二,《饮酒》其五、其八,《咏贫士》其一、其二,还有《读山海经》其一等16首,占其作1/8。
这些诗中,拥有最容易使人不忘的描写田园风光的景致:
田畴,稻苗,远村炊烟;
披草来往,但道桑麻;
晨兴荷锄,带月而归;
东篱采菊,南山在目;
草木扶疏,众鸟欣鸣;
乃至于鸡鸣狗吠,深巷桑树,都一一上了诗,展现了一道道“田园美”、“农夫乐”的风景线。
且不说就在这些诗中,还包含着和这些美乐风光相毗邻的“田家忧”与“农夫苦”,以及对官场的横眉冷对。
单就这些风光本身看,当时却被视为“田家语”。
为他辩护的钟嵘,有感于“世叹其质直”,在《诗品》中却标举他的“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谓为“风华清靡”,这正是既非“田家语”的描述句,亦非田园风光的景句。
由此看来,他用“田家语”所写的田园诗,在南朝170年间并未当作“平淡”、“自然”的独特风格看待。
就是对他最为崇敬的萧统,只选两首田园诗入《文选》,且在热情严肃极加推扬的《陶渊明集序》里也视为“傍流”。
的确,在徜徉山水名园时流行东晋百年的玄言诗潮中,陶之“种豆南山下”、“但道桑麻长”确实属于“质直”的“傍流”,大为不合时宜。
鲍照《学陶彭泽体》模拟的只是喝酒与弹琴,看来田园风光之类,还算不上“彭泽体”,至于劳动与贫困就更不用说了。
江淹遍拟汉魏以来30家古诗,杂奏陶句以略变的《陶徵君田居》,还有些田园风味,但这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
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征引那么多的篇目,评论了那么多的作家,却未有及陶;
《世说新语》被视为魏晋风流名言集,片言只语泛化性的收录,亦未及陶。
《宋书》、《晋书》、《南史》、《莲社高贤传》以及萧统,都为陶立传,还有颜延之的诔文,显得异常热闹,但却仅具纯然隐士的“轰动效应”,谁也没有把他看做地道的正宗诗人,似乎他的存在,只占有隐士长长画廊的一席。
专论诗人的《诗品》,看重的却是非“田家语”的“风华清靡”的一面,只好委屈他排入“中品”。
总之陶被看重的只是因为做了坚决的隐士,而陶诗难入时流,充其量只是“隐逸诗人之宗”罢了。
其实,何至于此!
只要留意《陶渊明集序》所说的“不以躬耕为耻”,我们再把他还原到门阀制度的东晋,就会更为清楚。
由奢侈无度的西晋流亡出来的东晋,只要看看玄风在两晋愈煽愈炽的思潮,就可知两晋有许多相似之处。
西晋束皙早年写了语言通俗事涉“贱职”的《劝农》与语及饥饿的《饼赋》,便被视为“文颇鄙俗”,遭到“时人薄之”的批评,公然郑重见载于《晋书》本传。
至于他专写饥寒冻饿的《贫家赋》,不知被会讥讽成什么样子,故史家更不屑一顾。
陶诗的饥饿与乞食,或许与束赋有关,所遭到“质直”如“田家语”鄙弃,就势所难免。
当时门阀士族身当国政重任,不以事务为怀,否则便落入鄙俗。
陶之曾祖陶侃,“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早年寒宦,就曾被人骂为“小人”、“溪狗”。
《南史》本传谓渊明“夫耕于前,妻锄于后”,除了种豆刈稻,颜《诔》还说他“灌畦鬻蔬”,浇园种菜,看来还要挑担叫卖;
又要“织纟句纬萧”,既打草鞋又编席子。
搞这些副业,在于“以充粮粒之费”,同样还得自己推销。
干了这么多的“贱业”,自然有许多甘苦之言。
他又是好作诗文的人,忍不住就选择点写进诗里。
被誉为圣典的《诗经》,其中称为“劳者歌其事”的《国风》,除了《七月》、《》便没有几篇,陶诗当亦复如是,何况他是个名士,名士是很要面子的,这就给我们留下不少遗憾。
所以读他的《归园田居》,总觉得像是写日记,原本是留给自己看的,写得很矜持也很谨慎。
总而言之,陶诗就好像蒸馏水,想写而不能写的和不愿意写的,不知还有多少,一经过滤,被蒸发掉的肯定不少。
所以嗜好陶诗的东坡,每次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
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陶诗,在望空为高的东晋时潮中,确实是支“旁流”,然而更是个奇迹
。
在高级贵族与皇室分权而治的门阀社会,“躬耕为耻”无疑是流行性的社会观念,要不以之为耻,就要付出极大的勇气。
愤然归隐固然能博得隐士虚名,但抗起锄头种豆就不那么“雅”了。
《晋书·
隐逸传》里排在渊明前边的陶淡,为陶侃之孙,“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结庐山中,养鹿为伴。
这种“隐”法当然很“逸”,而陶渊明之隐,则有时累得“四体诚乃疲”,何况还要累出个“耻”来,不然萧统为何说他“不以躬耕为耻”。
他挥锄于豆苗稻秧中,面对“草盛苗稀”,也明知须“戮力”、“肆微勤”。
有时灾年“收敛不盈廛”,但总抱着一般常年会有“力耕不吾欺”的安慰,或者“岁功聊可观”的企望。
农夫或准农夫的饥寒温饱的哀乐喜怒,起码在他的“田园诗”得到一定的表现。
他的田园诗既有风光恬静的“田家乐”,也有晨兴晚归的含辛茹苦;
有“四体诚乃疲”的“田家苦”,有“寒馁常糟糠”的“农夫忧”,也有“拙生失其方”做庄稼汉的烦恼,还有“秉耒欢时务”与“即事多所欣”的娱悦;
有“过门更相呼”与“披草共来往”的农民式交往,也有“父老杂乱言”与“但道桑麻长”的乡村之音。
这些农家的自存自在的田园旋律,是诗化的、美化的,也是农民化的、辛苦化的;
是隐士的视野,也是田夫的眼光。
他毕竟不同于岩栖的隐士,而是回乡投入到农民行列。
虽不完全等同田夫,尚有嗜酒的“大宗消费”,但并非怪诞的醉汉或狂妄的酒徒,亦有“倾壶绝余粒”的尴尬与无奈。
究其实质,萧统说是“寄酒为迹”,其实未尝没有借酒骂世的份儿。
他又是从官场五进五出的过来人,看透了“大伪斯兴”的上层社会,对门阀士族的乱与篡至为洞悉,其厌恶的劲儿较之农民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时时渗透在他那看似恬静安宁的田园诗中,这正是他常用“尘网樊笼”、“轮鞅深辙”、“密网宏罗”比喻官场的原因。
亦缘此而把上流社会耻辱观念决然颠覆倒置,把当官看做“志意多所耻”的肮脏行当,做农夫则“即事多所欣”。
他“载欣载奔”到家园,干干净净地做起“转欲志长勤”的农夫,理直气壮地作起委实“带刺”的田园诗。
所以,他的这种田园诗,具有批判与净化的效应,正如萧统《陶渊明集序》所言:
“弛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仅“平淡自然”所能概括,“隐逸诗人”所能范围。
他的田园题材,他的力耕思想,他的带有泥土味的哲思,还有他对农村的爱,对官场的憎,都是用锄头耕凿出来的,用爱憎浇灌的审美境界。
这在“辞意夷泰”、千人同腔的玄言诗流行的东晋,真是横空出世,迥然异样超拔时俗的奇迹,别具不同凡响的奇情异彩。
陶渊明刻意带有装饰和保护双层作用式的外在淡化,长期障住我们的眼目,“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经久不息地拥有“平淡”一类陈陈相因的赞美,而淡漠了横眉冷对的“而无车马喧”,淡化了孤傲愤然的“心远地自偏”。
前者的“无我之境”,分明倾注有后者的“有我之境”,“平淡”的外装分明包裹跌宕的愤激,“悠然”的前提建立在批判的锋芒之中。
可以说陶渊明所有的田园诗,无不锥处囊中,刺向虚伪门阀官场。
他是站在敌视喧嚣官场的角度,来描摹田园的宁静;
从厌恶上层社会的虚伪,来赞美农夫的真淳。
桃花源里“秋收靡王税”的向往,不正侧面说明农村“冻饿固缠己”的真实原委,这也正是把看似可惭可愧可耻的“乞食”,却毫无顾忌地写进诗里的原由。
因而陶诗并不是一味的陶醉他的精神家园,他也并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守望者。
所以,他的为官所作诗及归隐后的田园诗几乎每篇都处于官场与田园的对立的情绪中,诸如“息交游闲业”与“聊用忘华簪”[1]《和郭主簿》其一,“园林”与“世情”、“好爵”与“养真”[1]《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平津”与“栖迟”[1]《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八表同昏”与“静寄东轩”[1]《停云》,“平陆成江”与“闲饮东窗”[1]《停云》,“适俗”与“守拙”[1]《归园田居》其一,“即理愧通识”与“所保讵乃浅”[1]《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一形似有制”与“安得久离析”[1]《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性本爱近山”与“久在樊笼里”[1]《归园田居》其一,“野外”与“人事”,“穷巷”与“轮鞅”,“掩荆扉”与“绝尘想”,“草庐寄穷巷”与“甘以辞华轩”[1]《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田家苦”与“异患干”[1]《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代耕本非望”与“卓然见高枝”[1]《饮酒》其八,“一世皆尚同”与“禀气寡所谐”[1]《饮酒》其九,“一士长独醉”与“一夫终年醒”[1]《饮酒》其十三,“幽兰生前庭”与“见别萧艾中”[1]《饮酒》其十六,“投耒去学仕”与“志意多所耻”[1]《饮酒》其十八,“吾亦爱吾庐”与“颇回放人车”[1]《读山海经》其一,这些极为对立性的对比,虽曾间或有些徘徊,但多是剑拔弩张地对峙于陶诗中,既“跌宕昭彰”,更“抑扬爽朗”,它确实警示人,使贪者廉与懦者立。
驰竞与鄙吝,虚伪与欺诈,在这里被扫荡得一干二净。
纯洁高尚的人格尽兴得到展示,官场的伪诈被按入受审位置,道德的鞭挞暴起一道道红栗。
被颠倒的社会观念,重新再颠倒过来,贪婪与伪诈永远牢订在耻辱柱上。
在这些诗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外在的“平淡自然”与“真率”,透过淡化的表层,感受到爱与憎的碰撞,感知到内心的激荡与不平。
他对纯洁的田园是那样的欢欣,对官场是多么横眉厌弃,这种不平衡的“合奏”却构建成极为协调的旋律,微妙而奇绝地响奏在他的田园诗里,既有别于古老的农事民歌的沉重与被动,又不同于后来王、孟、储、韦、柳的田园诗,它实在呈现了一道颇具奇情异彩的风景线。
它是在儒道互动的熔炉里打造出的双刃剑,又淬上田园的汗水,显示出同锄头一样的光芒,可以锄去那些荒秽“杂草”!
虽然那么不起眼,甚至于看到“悠然见南山”,让读者冷淡了“而无车马喧”,这未尝不是陶诗奇绝的另一侧面;
在“异患”丛生的门阀社会,亦未尝不是经过淡化处理的护身盾牌,有冲刺也有防卫一样。
三、咏史咏怀诗的奇趣
除了田园诗外,咏史、咏怀、拟古、杂诗等,也显示追求同样奇情异彩的审美情趣,而且奇绝的笔触伸展得异常广泛。
他受过饥饿的威胁,所以一口气写了七首一组的《咏贫士》,对他来说,本属题中应有之意,而在诗史上却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西晋皇甫谧《高士传》或许即蓝本所在,然而体现的只是史家冷静叙写与客观礼赞,陶诗不同的是每一贫士都渗透自己的影子,带有系列性人我比勘与自我写照的性质,使这一特殊的“贫士画廊”从而具有异样的光彩。
前二首为总冒与自画像,以下所采用“对话”形式,即人即我。
其二、三、四、七都用了“我”、“吾”第一人称,使“对话”人我不分,每诗末尾结以议论,如清邱嘉穗语“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几乎泯去人我之迹。
其五的“岂不实辛苦?
所惧非饥寒”,为最见肺腑之言;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是陶公一生的大本领。
在实话实说中射发出“与道污隆”的异彩,在质朴平淡中闪动与世迥别的奇情亮节。
在东晋门阀贵族极为特权的时代,却“大为贫士吐气”,旷世罕有,已经够奇绝了。
明人黄文焕《陶诗析义》卷4说:
“七首布置大有主张
,‘岂不寒与饥’,‘穷有愠见言’,‘岂忘袭轻裘’,‘岂不知其极’,‘岂不实辛苦’,‘所乐非穷通’,‘固为儿女忧’,七首层层说难堪,然后以坚骨静力胜之,道出安贫中勉强下手工夫,不浪说高话,以故笔能深入,法能喷起。
”诗法确实奇绝,7篇或起调陡然醒快,或结语正反跌宕,中间或顿挫往复,每用“岂不”或“岂忘”句式起伏转折,故“法能喷起”,显得更加跌宕奇绝。
另外,所咏“贫士”皆为先秦两汉人物,“无论魏晋”,或许与《史记·
循吏列传》不取当代亦同一用意,故此组诗亦为咏史之作。
咏史诗既名为发思古之幽情,故最具安全系数,可以不涉异患。
而且又能寄托心意,发愤然不平之块垒,所以陶诗咏史多至20多首,亦占其诗1/6,数量与其田园诗比肩。
所咏可分三类:
一是荆轲、程杵、颜回、秦之三良、屈贾、韩非,大多为有所为而不成的悲剧人物;
二是夷齐、箕子、二疏,以及《咏贫士》中的张长公、荣叟、黔娄、袁安、仲长蔚、黄子廉,属于有所不为,亦带悲剧色彩;
三是精卫、刑天、夸父等神话人物,以及玄圃、神树仙鸟,与游仙诗相近。
咏史诗中最为着名的是《咏荆轲》,钟嵘语尤其能见出陶渊明“又挟左思风力”一面。
咏荆轲诗,始见于建安文学,王粲残诗有“荆轲为燕使,送者盈水滨。
缟素易水上,涕泣不可挥”;
阮《咏史诗二首》其二“燕丹善勇士,荆轲为上宾。
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
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
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
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
”似亦残篇。
王粲、阮、曹植都有咏三良诗,由所咏的对象相同来看,这些咏史之作,可能都为同时共作,豪宕如曹植当亦有咏荆轲之作,惜其无存。
完整者惟左思《咏史》其六,只写酣饮燕市,而易水送别与刺秦一概无言,意在张扬“与世殊伦”、“贱者千钧”的布衣精神,带有蔑视权贵的批判锋芒,激昂慷慨的风格与王粲、阮的悲愤近似,却与士为知己死的悲壮异趣。
陶作前半近于王、阮,整体主旨反而疏离于左思的主题,遗憾“奇功遂不成”,但“且有身后名”,而且“千载有余情”,明清论者多以为渊明目击晋宋禅代,此诗深有寄托,“别有心事”,不便明言。
今人多视为泛咏,与时事无涉。
无论怎么说,此诗绝与平淡自然无涉。
就连说过“渊明诗平淡”的朱熹,亦言: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这两条在《朱子语类》卷140中前后比邻相连,反映了陶诗接受史上先后异论带有普遍性规律。
合观似言:
“平淡”只是陶诗外相,本相则为“豪放”,这种内外悖论的风格,只是不容易觉察罢了。
故前辈学者有云:
“人皆赏其冲淡,而陶之精神实不在冲淡,自冲淡学陶者多貌似而神非。
”[5]105又云:
“陶诗不是滞水而是暗潮,表面象是平静,实质内容是动荡的,充满了英气。
‘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虽躬耕而天下大局在其胸矣。
《咏荆轲》的写作,流露出的热情可看出他不忘情社会。
……对黑暗现实的不满通过对英雄的颂赞表现出来。
”[5]158陶诗审美主要趋向,确实存在表面与实质的矛盾,即淡与奇的矛盾,而且融化得让人“不觉”,就委实显得更加奇异,这在其他咏史诗就更显示出这种特色。
那首被公认为“金刚怒目”的《读山海经》其十,宋人就说过:
“末句云:
‘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何预干戚之猛耶?
”[6]656今人据此甚至说:
“陶渊明所表现的不是什么‘金刚怒目’式愤怒,也无意歌颂精卫、刑天的不屈精神,这是一首吟咏超然处世的达观之诗。
”[7]17对此且不论是否让人心悦诚服,陶诗的表层常常披上一领“平淡的外衣”,甚或悠闲的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