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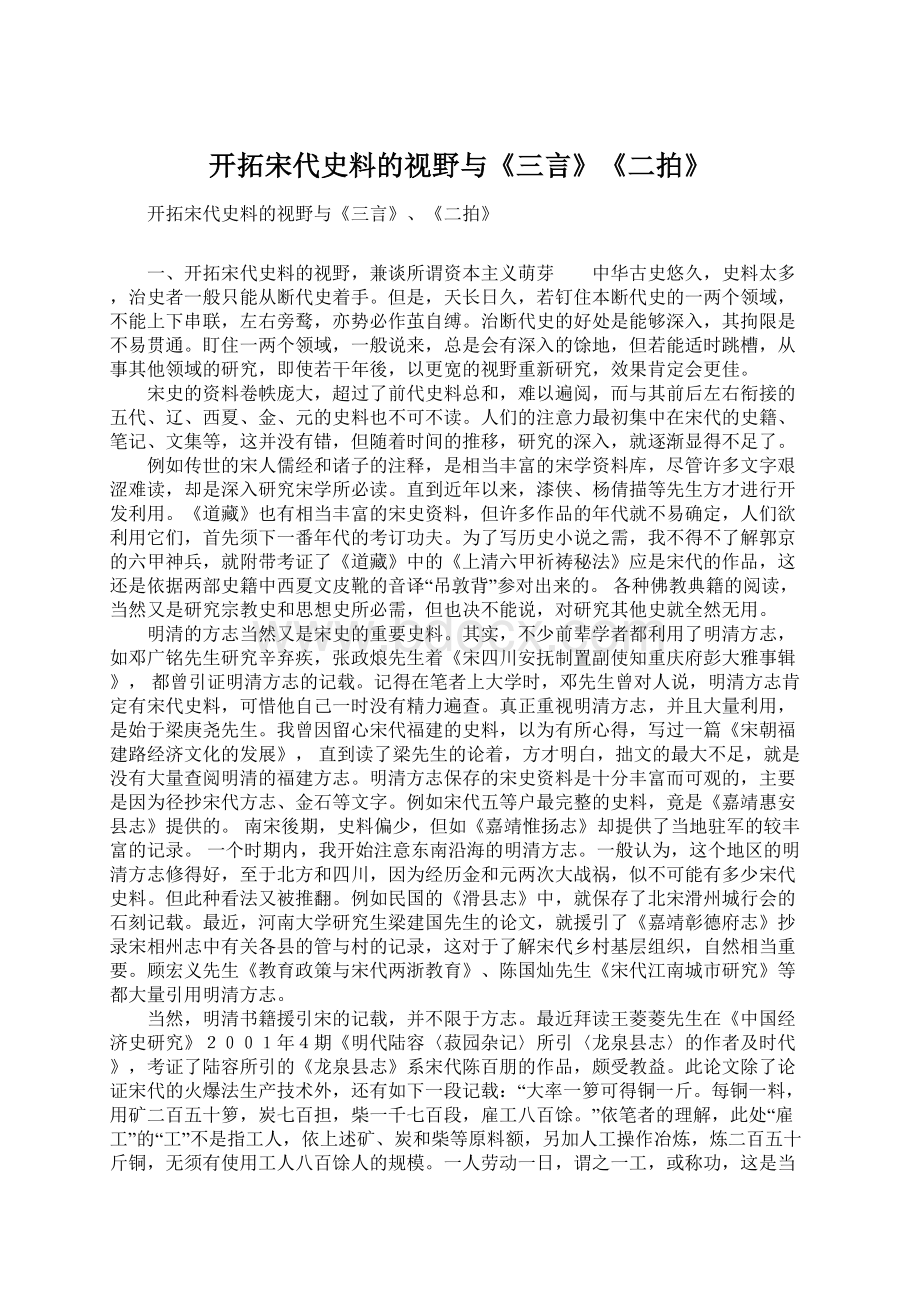
当然,明清书籍援引宋的记载,并不限于方志。
最近拜读王菱菱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4期《明代陆容〈菽园杂记〉所引〈龙泉县志〉的作者及时代》,考证了陆容所引的《龙泉县志》系宋代陈百朋的作品,颇受教益。
此论文除了论证宋代的火爆法生产技术外,还有如下一段记载:
“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
每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馀。
”依笔者的理解,此处“雇工”的“工”不是指工人,依上述矿、炭和柴等原料额,另加人工操作冶炼,炼二百五十斤铜,无须有使用工人八百馀人的规模。
一人劳动一日,谓之一工,或称功,这是当时普遍的计量单位,“雇工”即是指依每一工支付的工值。
大致产铜一斤,约费三个多工。
《朱文公文集》卷20《与曾左司事目札子》说,南康军“打造步人弓箭手铁甲,一年以三百日为期”,“计用皮、铁匠一万八千工,钱五千二百馀贯”。
此处也用“工”作为支付雇值单位,皮匠和铁匠平均每工二百八十八文。
此条史料可与《龙泉县志》互相印证。
此处顺便谈一下对所谓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作为主要产业,是适合个体经营的,有很长时期的稳定的租佃制。
古代也有作为次要产业的手工业和商业,而大工商业是不适合个体经营的。
从史料上看,大工商业大致可有三种经营方式,一是使用奴隶,这在秦汉的史料中相当明显,二是使用雇工,这在明清的史料中相当明显,三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联合经营。
姜锡东先生注意到宋代商人“连财合本”,手工业者也有类似情况。
古代大工商业经营发展的总趋势,是以雇佣制取代奴隶制,唐宋之际正是此种转变的重要时期。
前引王菱菱先生援引的“雇工”史料,又提供一条重要的史料新证。
一些学者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是侧重于手工业的雇佣制,并且认为,只有到明中期,方才算得上有资本主义萌芽。
的确,自唐宋到明前期,如今找不到大量手工业的雇佣制记录,古代大量的史料堙没,是无法再生的。
但是,在这八、九百年间自然不可能没有大工商业,此类大工商业又是如何经营的呢?
从相当稀缺的史料看来,唐宋大致已不像秦汉时期那样使用奴隶,而确是雇工或联合经营。
例如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明确记录了当地大量使用雇工的情况。
有人认为,井研县是落后地区,没有代表性。
其实,井研县就宋代而论,也算不上落后地区,而即使算落后地区尚且如此,先进地区岂非是理应雇工更为普遍。
明代前期的大工商业经营似也应如此。
已故的前辈学者、明史大家王毓铨先生在晚年,很不赞成使用“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我个人也有同感。
因为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其实应有政治、经济、思想、科学等诸多因素的综合配套,不可能是手工业雇佣制的单一因素。
某些促使西欧封建制和农奴制瓦解的因素,例如土地买卖的兴盛,货币地租的发展,工商业中雇佣制的发展等,是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即使晚到清朝,也看不出此类因素会使中国这个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行将解体。
总之,唐宋时的大工商业雇佣制是存在的,但今人不必将此视为资本主义萌芽。
尽管此类雇佣制与近代资本主义雇佣制有相似或相近的方面,事实上却没有因此而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考古文物资料当然也是重要史料,文字的表述有局限性,有时远不如图片和实物真切。
我个人不常查阅考古、文物之类杂志和书籍,朱瑞熙先生在这方面比我强得多。
我们撰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最後的配图工作全由他一人承担,堪称驾轻就熟,没有长期的积累,是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就完成的。
古人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信息时代,许多门类的学科无此必要,但对史学而言,学者到各处参观名胜古迹,是很有必要的。
例如研究宋朝军制,山西沁县城内关帝庙宋碑和河北定州开元塔的施主题名,就提供了重要史料。
我国有繁多的家谱传世,其中往往追溯到宋代,当然有史料价值。
例如许怀林先生的《“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就是使用了清道光时的《义门陈氏大成宗谱》。
但是,传世家谱中显然有许多乱攀祖宗的情况,确实需要认真考证和甄别。
朱瑞熙先生有一次与我谈及此事,都有同感。
一位研究唐史的吴丽娱先生给我看一部周恩来的传记,我读后,建议她写一篇澄清史实的文章,论证周恩来的祖先其实是冒认宋代理学家周惇颐为祖宗。
文章在《历史研究》刊出后,周氏人群哗然,一时之间,纷纷来信,对吴丽娱先生责难,其实又讲不出什么道理,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史学素养。
类似的情况当然不止是周氏一个宗谱。
上世纪八十年代,报上接连介绍了几个岳飞后代的宗谱,我对邓广铭先生说,这几个岳氏宗谱看来都是伪托者,邓先生表示完全同意,因为宗谱上所载显然与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等宋代史料不合。
不料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岳飞新传》,竟在不征求本人意见的情况下,使用一部《岳氏宗谱》作封面,真令人啼笑皆非。
为了对一些宗谱祛伪,朱瑞熙先生撰写了《〈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中的伪作》。
我也写了《岳飞后裔考略》,在张政烺先生论证的基础上,论述《唐门岳氏宗谱》作伪,而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的自序中,也对传世《贡氏宗谱》中《武德大夫贡文宪公传》之作伪,作了论析。
二、《三言》与《二拍》中的若干宋代史料论析 笔者在学生时代读过《三言》,在个人的粗浅印象中,一直将《三言》、《二拍》之类视为明代小说和史料。
直到拜读漆侠先生《知困集》中的《〈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方知其中的一部份脱胎于宋人话本,是可作宋代史料使用的。
漆侠先生的文章主要是从经济史的角度,认析了《三言》、《二拍》的若干史料价值。
最近因为撰写《水浒传》的文章,必须以宋元话本、元杂剧和《三言》、《二拍》作为参照系,在翻查《三言》、《二拍》时还是有所心得。
宋人话本并无原始的宋本传世,即使是较早的《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之类,或系元人写本,或系明嘉靖时刊印,而《三言》、《二拍》成书更晚,故後人的窜改就势不可免。
这是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的。
即以《冯玉梅团圆》为例,其中有“我宋建炎年间”,明显是宋人的口吻。
但书中称金人为“鞑虏”,又可证明不是南宋前期或中期的作品,因为南宋称金人和女真人为“虏人”或“番人”,直到後期方称蒙古人为“鞑虏”之类。
此处分明是将女真人误用蒙古人的称呼。
此小说的故事来源於《说郛》卷37《摭青杂说》。
《摭青杂说》中的“吕忠翊”和“广州使臣贺承信”,完全是宋人的习惯官称,意即是吕姓忠翊郎和贺姓承信郎,承信郎也确是包括在低品武官“使臣”的通称之内。
然而在话本中,却改为“关西一位官长,姓冯,名忠翊”,这就流露出元人的窜改痕迹。
再说《拗相公》。
话本末尾有“後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是宋人口吻。
但其中又有“北宋神宗皇帝年间”,宋人并无将本朝区分为北宋和南宋之语,属後世窜改无疑。
话本中记述王安石雇驴骡,命仆人“江居把银子称付主人”,这也不大符合宋人的用银习惯,宋人即使用银,一般是以银折钱。
显然,唯有将传世的宋人话本和《三言》、《二拍》中的後人窜改之语辨别和剥离,宋人话本与《三言》、《二拍》中的记录方可作为宋代史料使用。
此外,《三言》、《二拍》中的故事,如果能找到更原始的宋人话本,当然就不必再用两书中的记录。
例如《警世通言》卷4《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卷12《范鳅儿双镜重圆》即是脱胎于上述《拗相公》和《冯玉梅团圆》,就不须再将此两回书用作宋代史料。
今人搜采宋代史料,应注重载于《三言》、《二拍》中,而如今已找不到更原始记录的宋人话本。
然而《三言》、《二拍》中也有虽是讲宋代故事,其实却是明人创作的“拟话本”。
欲精确分辨明人的拟话本与宋人的旧话本,自然是困难的事。
依个人的阅读经验,明人模拟者,在追拟宋代名物制度的细微处,是不大可能惟妙惟肖的;
而经明人加工的宋人话本,即使搀杂了明代的名物制度,也必然在名物制度的细微处,能够惟妙惟肖地反映宋代社会生活的现实。
如果在名物制度的细微处能确定为宋代者,大致可依宋人话本处理。
由于漆侠先生已经罗列了《三言》、《二拍》中的若干宋代经济史料,以下主要就他的论文之外,摭拾若干零星史料,进行考订,以补史之阙文。
今列举1、制度:
《二刻拍案惊奇》卷5《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看来是大致照抄宋话本。
如说“秦申王荐于高宗皇帝”,是南宋人的口吻。
话本说:
“有一个宗王家在东首。
有个女儿名唤真珠,因赵姓天潢之族,人都称他真珠族姬。
”又称宋神宗皇后为“钦圣皇后”,王韶的儿子王寀入宫,“妃嫔每要奉承娘娘,亦且喜欢孩子”。
按宋神宗后向氏的谥号确是钦圣。
据《铁围山丛谈》卷1:
“国朝禁中称乘舆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谓至尊为官家,谓后为圣人,嫔妃为娘子,至谓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
”如宋哲宗称祖母高后为“娘娘”。
宋徽宗时,一度改称宗女为“族姬”,为时不长。
南宋话本的记载虽然不准确,但非後人所能杜撰。
“妃嫔每要奉承娘娘”,“娘娘”照理应称“圣人”,可能是宋人尊向氏为太后,故称“娘娘”,也可能是经明人窜改,或南宋後期已将“圣人”改称“娘娘”,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醒世恒言》卷13《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说:
“保和殿西南有一坐玉真轩,乃是官家第一个宠幸安妃娘娘妆阁。
”也以“娘娘”相称。
《宋史》卷243《刘贵妃传》,“时又有安妃刘氏者,本酒保家女”,“擅爱颛席”,“林灵素以技进,目为九华玉真安妃,肖其像于神霄帝君之左”。
安妃本非宋朝贵妃之类正式的“内命妇”等级名号,而是因宋徽宗迷信道教而赐名。
另可参见《宋史》卷462《林灵素传》。
小说的对玉真轩的描述,并且引用了蔡京诗:
“保和新殿丽秋辉,诏许尘凡到绮闱。
雅宴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看安妃。
”可在《宋人轶事彚编》卷2引《碧湖杂记》中得到印证,其中蔡京诗只有几个字的差异。
宋朝宫女也有依外命妇名号,“或封国夫人、郡夫人”。
小说着重描写“内中有一位夫人,姓韩,名玉翘”,称“韩夫人”,即是封号为国夫人、郡夫人者。
《二刻拍案惊奇》卷14《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话说宣教郎吴约,字叔惠,道州人,两任广右官。
自韶州录曹赴吏部磨勘。
宣教家本饶裕,又兼久在南方,珠翠香象,蓄积奇货颇多,尽带在身边随行。
作寓清河坊客店。
因吏部引见留滞,时时出游伎馆”。
在受骗後,“看看盘费不勾用了,等不得吏部改秩,急急走回故乡”。
此段记事完全符合宋代的史实。
宣教郎是从八品文阶官,录曹是录事参军的简称。
因宋代对外贸易发达,广南韶州的官员容易拥有“珠翠香象”的奇货。
宋时“磨勘”为铨选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南先生《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有详细论述,而“磨勘”的结果正是“改秩”,即升官,而非除授实职“差遣”。
《古今小说》卷11《赵伯昇茶肆遇仁宗》有西川“王制置”,宋仁宗又命赵旭出任“新制置”,“制置”是制置使的简称,属宋时的方面大员,後世不设此官。
“仁宗问司天台苗太监”,宋时设司天监,其长官可称大监,大监与太监通用。
此处无疑是宋人话本使用本朝的官称,可与史籍互相印证。
太监一词,宋与明清的词义迥异,明清时成了宦官的称谓。
若将宋代的宦官称为太监,便成无知妄说。
《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记载宦官,则称“穿宫的高品近侍中大人”。
据《宋史》卷169《职官志》,宋朝宦官有阶官称“高品”和“祗候高品”,宋徽宗时改称“左班殿直”和“祗候殿直”。
宦官分属内侍省或入内内侍省。
所谓“穿宫的”可能即是指入内内侍省。
宦官称“中大人”,似可补史料之缺佚。
但“中大人”一词如果用于第二人称时,为“某中大人”,在汉语中似嫌拗口。
另据《云麓漫钞》卷3,“今人呼中官之次者曰阁长”,“今呼内官阁长以上为大官,亦始于唐”。
大约在第二人称时可称“某大官”或“某阁长”。
“令公”一词,原意专指中书令。
《世说新语•;
德行第一》称晋朝中书令裴楷为“裴令公”。
《魏书》卷48《高允传》,高允任中书令,“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为令公。
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
唐季五代,武将藩镇往往加中书令的虚衔,称号遂滥。
《古今小说》卷6《葛令公生遣弄珠儿》称五代後梁大将葛周为令公,说他有“中书令兼节度使之职”。
据《旧五代史》卷16和《新五代史》卷21,葛从周或称葛周,但他生前授侍中,并无中书令的头衔。
可见所谓“葛令公”,亦不过出自宋代说书人的随意杜撰。
小说称申徒泰由葛周“补他做个虞候”,又“令公分付甲仗库内,取熟铜盔甲一副”。
按虞候是唐宋时的官称,又当时称兵器库为甲仗库,故此卷可大致判定为宋话本。
今人最熟悉的“令公”,当然是“金刀杨令公”,至今戏曲中传唱不衰。
按《宋史》卷272《杨业传》,他在生前只是一个战区副司令,其官衔是云州观察使,按宋时习俗,可称杨观察;
身後追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
北宋前期,太尉是三公之一,官位甚高。
但在宋人话本《杨温拦路虎传》说:
“话说杨令公之孙,重立之子,名温,排行第三,唤做杨三官人。
”杨业即使在身後并无中书令之官衔,而讹称杨业为杨令公,亦是由来已久。
《古今小说》卷9《裴晋公义还原配》称唐朝宰相裴度为“裴令公”,卷15《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称五代史弘肇为“四镇令公”,符彦卿为“符令公”。
裴度、史弘肇和符彦卿确是“拜中书令”,“兼中书令”。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最後交待说:
“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
”应是南宋说话人的口吻,南宋人往往仍称开封为京师,而称临安为行在。
其中有“郭部署向前与尚衙内道”。
按宋英宗赵曙即位後,部署就避其御讳,改称总管,话本中居然保留了他的御讳,可证明是创作在他登基前。
小说中又有“怎见得司理院的利害”,按五代时,诸州设马步院,宋太祖开宝六年,“改马步院为司寇院”,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又“以司寇院为司理院”。
由此可见,此话本最初的创作时限,应在宋太宗到宋仁宗时。
但此後显然又辗转修改,如小说中提及“村东王保正家”,保正又是晚至王安石变法时方才创设。
小说的风格颇与宋人话本《碾玉观音》相似,在开头引用了不少宋诗,而对作者都是避免名讳,只使用号或官称,如“洪内翰”是洪迈,“张紫微”是张嵲。
两人都是南宋人,这又是南宋时再行加工的明证。
《裴晋公义还原配》有一些属唐宋时代的官名,如“唐璧授湖州录事参军”,又“复除湖州司户参军”。
“外面一人,约莫半老年纪,头戴软翅纱帽,身穿紫絝衫,挺带皂靴,好似押牙官模样”,“紫衫押牙”,押牙即是押衙。
此类官名非金元以降所有。
同书卷8《吴保安弃家赎友》有“蔚州录事参军”、“代州户曹参军”之类官名,也可反映话本产生的时代。
《警世通言》卷30《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以开封着名的游览胜景金明池为背景,“忽一日,有两个朋友来望,却是金枝玉叶,凤子龙孙,是宗室赵八节使之子,兄弟二人,大的讳应之,小的讳茂之”。
“节使”是节度使的简称,宋朝确有宗室授节度使虚衔的制度,而元明无节度使官衔。
宋人称呼也有官衔前加排行的习俗,但宗室不呼姓。
如《朱子语类》卷130说:
“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向。
”参照《宋史》卷234《宗室世系表》,宋太祖弟魏王赵廷美的五世孙都是“之”字为辈,如赵动之、赵葵之等,故小说大致是反映了宋朝的宗室制度。
《古今小说》卷17《单符郎全州佳偶》中有“扬州府推官”,称府当然是明代的事。
但故事中确有不少宋代的名词,如“单司户”是单姓司户参军,“郑司理”是郑姓司理参军,“邢四承务”是邢姓老四,任承务郎。
邢春娘说:
“我司户正少一针线人。
”据《说郛》卷73《旸谷漫录》谈到宋代士大夫雇用女使,“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折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级截乎不紊”。
小说中称“正值金鞑子分道入寇”,既用“鞑子”的称呼,又可证明为南宋晚期,或是明代人改写。
《警世通言》卷28《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目今所见最早的白蛇传故事,大致是照抄宋人话本,但也掺杂了明代的若干名物。
例如货币使用银两,这是明代的情况。
许宣姐夫寻思说:
“今日坏得些钱钞。
”“钱钞”两字联用,已非宋人词汇,而是金元明的词汇。
白娘子自称“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
按宋朝有左、右班殿直,本是北宋正九品武阶官,属三班院管辖。
宋徽宗时又改为宦官的阶官,而武官的左、右班殿直改名成忠郎和保义郎,三班院则在无丰时已改为吏部侍郎右选。
“白三班”大约是指白姓勾当或管勾三班院公事,既有“三班”,“殿直”就只能是元丰改制前的武阶官,似可证明白娘子传奇最早应起源于北宋时,後经各代说书人辗转修改。
小说是以南宋为背景,开头说:
“话说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杭州临安府过军桥黑珠巷内,有一个宦家,姓李名仁。
见做南廊阁子库募事官,又与邵太尉管钱粮。
”小说中称“李募事”。
“南廊阁子库募事官”找不到史料印证,但校注者严敦易先生估计“当是指的宋代的左藏南库”,而“募事官是小吏性质的杂职”,看来有一定道理,这反而是明人难以杜撰者。
太尉则是武人尊称。
许宣是李仁妻弟,“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
“将仕”当然是将仕郎。
小说叙述许宣找白娘子,“迳来箭桥双茶坊巷口”,白娘子住宅“对门乃是秀王府墙”。
後来“做公的”要抓白娘子,也“迳到双茶坊巷口秀王府墙对黑楼子”。
按秀王是宋孝宗的生父,“追封秀王,谥安僖”。
《梦粱录》卷10《诸王宫》载:
“秀安僖王府,在後洋街。
”《淳佑临安志》卷7《桥梁》:
“黑桥:
秀王府解库前。
”虽与小说中的地名不合,但《咸淳临安志》卷21《桥道》所载的桥名就与前一地方志有异,故小说记载的秀王府方位未必就是杜撰。
小说叙事说:
“那大尹随即便叫缉捕使臣何立,押领许宣,去双茶坊巷口捉拿本妇前来。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有“缉捕使臣王观察”,“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贵”。
使臣是宋朝八、九品的十等武阶官的通称。
缉捕使臣当然是宋代特有的官称,《永乐大典》卷14626《吏部条法》第25页就有“临安府缉捕使臣”,可知这确是宋制。
小说叙述许宣被判刑,“决杖免刺,配牢城营做工,满日疏放。
牢城营乃苏州府管下”。
後来又“押发镇江府牢城营做工”。
牢城是宋朝厢军的一种,往往以发配罪犯充。
但苏州府却掺入了明代的地名,南宋时应称平江府。
“李将仕与书二封,一封与押司范院长,一封与吉利桥下开客店的王主人”。
押司是宋时的吏名。
另据《夷坚志补》卷8《临安武将》,“向巨源为大理正,其子士肃”,“呼寺隶两人相随,俗所谓院长者也”,院长是与刑法有关的吏胥的尊称。
类似的记录是《警世通言》卷36《皂角林大王假形》,这个神怪故事说真知县赵再理被假知县、妖怪皂角大王所害,“开封府断配真的出境,直到兖州奉府县”,“到牢城营里”。
另有《醒世恒言》卷14《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当案薛孔目初拟朱真劫坟当斩,范二郎免死,刺配牢城营”。
孔目也是宋代的吏名。
《古今小说》卷36《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大致应是照抄宋人话本,其中有若干耐人推敲的细节。
“店二哥道:
‘告官人,公公要去,教男女买熬肉共蒸饼。
”据《青箱杂记》卷2:
“仁宗庙讳祯,语讹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
”既然不避宋仁宗的御讳,似可判断此话本的创作时间最初是在宋仁宗之前。
小说中宋四公说:
“东京有五千个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
按宋朝有东、西、南、北四京,但并非是同时设置。
南京应天府是设置于宋真宗大中祥符时,而北京大名府是设置于宋仁宗庆历时,如将最初的创作时间定在宋真宗时,恰好是“三都”。
《宋会要》兵11之7载,宋真宗时,设有“捉贼使臣”。
将“捉贼”改成“捉事”,可能是明初的事。
朱元璋造反起家,忌讳“贼”等字,我曾见过明代翻刻的宋版《忠文王纪事实录》,将其上的“贼”字统统剜去。
小说中有两个地名,一是“平江府提刑”,提刑即提点刑狱,二是“定州中山府”。
按苏州升平江府,定州升中山府,已是北宋晚期的事。
小说中称“将带一行做公的去郑州干办宋四”,“又象个干办公事的模样”。
按南宋避宋高宗赵构御讳,将官名“勾当公事”改称“干办公事”。
故此两处“干办”即显示了南宋人窜改的痕迹。
但另一处滕大尹说:
“不想王遵、马翰真个做下这般勾当。
”不避宋高宗的御讳,又疑为宋代以後之改动。
小说称“缉捕使臣马翰”为“马观察”。
前引《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有“三都捉事使臣“。
《水浒传》第十七回何涛自称“小人是三都缉捕使臣何涛”,人称何涛为“何观察”或“缉捕观察”,特别是也有“三都”一词,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相同。
似可推测,北宋时的捉贼使臣到南宋时改称缉捕使臣。
小说还另有“王七殿直王遵”,此人当是排行第七,而殿直的官名已如前述。
通过以上考证,可判断此小说自北宋、南宋到明代,经不断修改。
小说称“宋四公只见一个丞局打扮的人”,按“丞局”应为“承局”的笔误,也是一种小官。
小说称赵正偷盗“钱大王府”,当然是指原吴越国钱氏後裔,但自钱俶纳土归宋之後,其後代并不封王。
“钱大王”也不可能在白玉带丢失後,“差下百十名军校”,前去搜索张员外的解库。
《警世通言》卷9《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描写唐朝大诗人李白,其中说“阁门舍人接得番使国书一道”。
按唐朝有通事舍人,而宋朝到南宋孝宗时方置“合门舍人”。
由此亦可推断此篇原是南宋话本。
《皂角林大王假形》说的是宋徽宗时,赵再理“授得广州新会知县”,到任後“客将覆判县郎中”。
宋朝以高品官出任低品差遣,可称“判”。
“郎中”按宋时的称呼习俗,当是赵再理任知县前的差遣。
“客将”就是衙前,客将和衙前都是沿袭五代武人的旧衔,其实已非武人,而是吏胥。
小说叙述赵再理“即往大王庙烧香,到得庙前,离鞍下马”,骑马而不坐轿。
《朱子语类》卷127说,“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
“今却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
赵再理骑马,还是反映北宋的情况。
《警世通言》卷13《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大致上也是抄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