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鲁迅藏书险遭出售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1944年鲁迅藏书险遭出售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1944年鲁迅藏书险遭出售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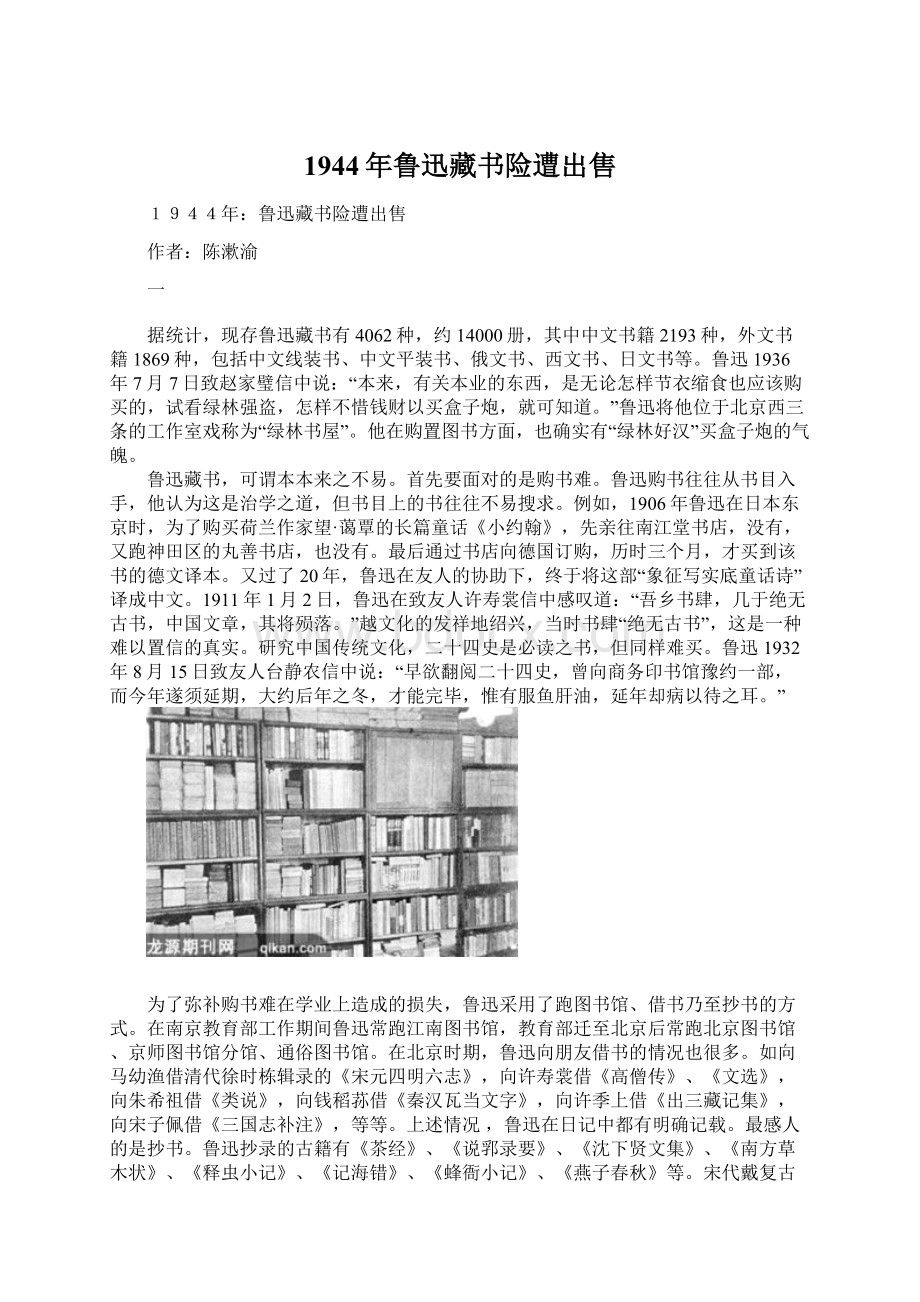
如向马幼渔借清代徐时栋辑录的《宋元四明六志》,向许寿裳借《高僧传》、《文选》,向朱希祖借《类说》,向钱稻荪借《秦汉瓦当文字》,向许季上借《出三藏记集》,向宋子佩借《三国志补注》,等等。
上述情况,鲁迅在日记中都有明确记载。
最感人的是抄书。
鲁迅抄录的古籍有《茶经》、《说郛录要》、《沈下贤文集》、《南方草木状》、《释虫小记》、《记海错》、《蜂衙小记》、《燕子春秋》等。
宋代戴复古的《石屏集》(又作《石屏诗集》),鲁迅从1913年8月下旬开始抄录,至同年11月26日,历时80天,共抄了10卷,272页,均用蝇头小楷。
1913年10月1日夜,鲁迅抄录《石屏集》时发病。
他在日记中写道:
“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
当然,藏书之不易更在于耗资甚巨。
据有人统计,从1912年5月至1936年10月,不到25年,鲁迅的总收入为124511.995元(甘智钢:
《鲁迅日常生活研究》,第43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
而据鲁迅日记的“书账”,鲁迅购书款总数为12165.524元,约占鲁迅总收入的1/10,是他家用、购房之外的第三大开销。
以上统计虽然不一定精确无误(1922年鲁迅日记缺失,有时欠薪,也不能反映物价浮动的情况),但却足以说明购书在鲁迅日常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1912年岁末,鲁迅整理完5月至12月的书账,感慨万千地写道:
“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
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
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鲁迅晚年,仍在为书价的飞涨而困扰。
他在文章中说,有一种乾隆时代的刻本,售价已跟当时宋版书价接近。
清代禁书,售价也高达数十元至百余元。
在散文诗《死后》中,鲁迅还描写了一个他“死后”仍向他兜售明版《公羊传》的勃古斋小伙计,表达了他对这类无孔不入地盘剥清贫文人的书贾的烦厌和憎恶。
二
在介绍鲁迅藏书时,必然要涉及1944年秋因出售这批藏书而引发的一场风波。
1963年6月7日,许广平在《北京晚报》发表的《火炬·
黎明·
旭日东升》一文中提到这件往事:
“鲁迅逝世以后,汉奸周作人在华北充当敌伪督办,他借口鲁迅母亲等人生活困难,指示别人整理出鲁迅所藏的中文、日文及其他外文书籍,编成书目三期,到南方去出卖。
我因开明书店一位朋友的帮助,得知此事,托其借来书目一看,大惊失色,知为有意毁灭藏书,企图以此来消除鲁迅影响,因即设法辗转托人留下全部藏书。
文中所说的“开明书店一位朋友”,指的是顾均正先生,他当时在开明书店编辑理化教材,是许广平住在上海霞飞坊时的邻居。
据周海婴先生回忆,变卖鲁迅藏书的消息是顾夫人周国华转告的,许广平“一听几乎昏了过去”。
文中所指的“辗转托人留下全部藏书”,所托之人系指郑振铎、唐等鲁迅生前友好。
许广平的这篇文章刊出之后,立即引起了周作人的反弹。
次日,周作人给《北京晚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视为周作人的一篇佚文——
记者同志:
七日贵报登有许广平女士的一篇文章,中间说及出售鲁迅藏书的往事,辞连鄙人,仿佛说是我的主意,事实有她当年的一封信为凭,完全不是这样的。
今照抄一份送上,请赐一阅。
据信中所说,自民国卅一年春即不能汇款,以后先母先嫂的用度即由我供给,此为分所当然,说不上什么‘鼎力维持’,但是‘俾将来继续清偿’,结果却是一番胡来的诬蔑,实真是最可感荷的了。
不敢希望沾污一点贵纸的篇幅,只是请你花费些许贵重的工夫,请把那书信通看一过罢了。
此致
敬礼
六月八日
周作人
周作人在致《北京晚报》记者的信中极力表白的是:
一、出售鲁迅藏书跟他完全无关。
二、以许广平1944年8月31日致他的信为凭,证明1942年春至1944年秋,鲁迅母亲和原配朱安的生活费系由他支付(或垫付)。
周作人抄录的许广平来信主要内容是——
……
日前上海报载,有北平家属拟出售藏书之说,不知是否属实。
果有其事,想为生计所迫使然。
鲁迅先生逝世以来,广平仍依照鲁迅先生生前办法,按月筹款,维持平方家属生活,即或接济不继,仍托平方友人先行垫付。
六七年间未尝中辍。
直至前年(卅一年)春间,身害大病,始无力如愿,病愈之后邮政银行商店俱无法汇款,而平方亦无熟人可托,束手无策,心甚不安。
不久前报载南北通汇,又多方设法仍苦无成。
其间重劳先生鼎力维持,得无冻馁。
前者出售藏书之消息倘属事实,殊负先生多时予以维持之意,广平特恳请先生向朱女士婉力劝阻,将鲁迅先生遗书停止出售,即一切遗物亦应妥为保存,亦先生爱护越先贤著作之意也。
至朱女士生活,广平当尽最大努力筹汇,如先生有何妥善方法示知更感。
倘一时实在无法汇寄时,仍乞先生暂为垫付,至以前接济款项亦盼示知,俾将来陆续清偿,实最感荷,先生笔墨多劳,今天以琐屑相烦,殊深感愧,尚祈便中赐教一二,俾得遵循。
同年6月20日,《北京晚报》记者侯琪将周作人6月8日来信及抄件转寄许广平,许广平阅后,于6月21日致函《北京晚报》记者,澄清史实,以防读者不知底细,受到蒙骗。
信中说:
转来周作人信,知此汉奸年老仍火气十足,希免其罪恶之责,而来信未能一语反驳其出售藏书之事。
这事乃一九四六年我到北京时,见了宋紫佩先生,亲自告诉我周作人如何下令馆员整理书目情况(后来,周作人迫他认其私宅偷盖房屋而要他〔宋〕认是公账。
即有通同作弊之嫌。
宋愤而生病,致双目失明,现已死)。
宋当时在北京图书馆任职,情况不会不确。
后见朱女士(鲁迅前夫人)亲手交出整理书目三本(现存鲁迅博物馆)。
我当即劝她保存遗物,并允负责其生养死葬,立有合同,以防周作人家属挑拨发生问题。
这些都有文件在博物馆内。
当然,从我写给周作人的信(来信附来的)看出,我那时听说出售藏书,明知是他所为。
朱女士目不识字,如何能策划图书馆人来给她服务呢?
事实了然,后面主使即是谁。
我苦心孤诣,写这封信去,说明请他暂为垫付,以后陆续清偿。
他却并无清单寄来,我自无法清偿,现在仿佛是我“胡来诬蔑”。
而不知他身为汉奸,喧赫一时,当其尚未下水时,亲友为之挂怀,钱玄同先生天天去他家守望。
我亦曾写信给他,并寄去五百元,托辞说母亲年老,怕受惊吓,请他亲自陪送老母南下。
后接母亲来信,说:
年老不能来,寄来的钱,自作零用了。
周作人写文章在上海《戏周刊》上说,他不能南下(当时很多人劝他南下),因老母寡嫂需他维持。
好像他的作汉奸是为了老母及寡嫂(朱女士),已经轻轻地把“汉奸帽子”推给别人了,明眼人当然晓得的。
至老母寡嫂生活,事实是一九三六年鲁迅死后,每月由北新书局支付一百元,到“八一三”抗战起,即行停付。
战争期间,我即托在辅仁大学任教的李霁野先生按月垫给朱女士五十元(这之前,我因儿子身体多病,经朋友介绍,想到南洋工作,要离开上海。
曾有信给周作人,托其照顾北京家属。
经其回信,说母亲他可以负担,朱女士则不管了。
我才无法,转托李霁野先生,每月筹寄五十元的)。
后来,北京沦陷,上海亦成孤岛,李霁野逃离南方,我又被人拘禁,就听说有北平(旧称)出售藏书之事。
由来薰阁人亲自带至南京,陈群看了书目,全部包下,但来薰阁负责人忠于周作人,望在上海得更高价,才到上海向书肆兜售,我才得知。
观我给周作人信中所说(你们转来的),实千方百计想对北京家属负责,而不是如他所说“胡来的诬蔑”的那样子人物。
许广平在这封信中,说明周作人幕后主使出售鲁迅藏书一事是宋紫佩揭露的。
宋先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又在北京图书馆任职,他提供的情况“不会不确”。
此外,也澄清了她当年尽力维持鲁迅母亲和朱安生活的事实。
此信当年并未公开发表,现收入1998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许广平文集》第3卷。
三
作为这场售书风波的当事人之一,唐介绍了朱安女士当时的真实态度,以及周作人接济母亲和朱安的真实情况。
1944年11月,唐以“晦庵”为笔名在上海出版的《万象》第四期、第五期上发表了《帝城十日》一文,涉及了他跟刘哲民到北京调解此事的情况,惜此文系日记体,内容甚繁,仅10月14日、15日两天的日记中简单提到此事,而且隐去了有些当事人的姓名,使读者不知其详。
1980年4月,唐先生又撰写了《〈帝城十日〉解》,对许广平1961年在《图书馆》杂志第四期刊登的《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经过》一文进行了补充。
据唐回忆,1944年秋天,有一份出售鲁迅藏书的书目通过北京琉璃厂来薰阁书店向南方兜售,首先得到这份书目的是开明书店。
消息传开,最感震惊的是嗜书如命的藏书家、鲁迅生前友好郑振铎。
他激动地说:
“糟糕!
要把鲁迅的书卖掉了,这哪能行,这哪能行呵!
”他当时在上海一家私人小银行当秘书,听到此事也很着急,便趁跟友人刘哲民到北平的机会,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极力阻止鲁迅藏书流散。
一方面,他携带了郑振铎的多封亲笔信,分致来薰阁、修绠堂等书店和赵万里等版本专家,请他们共同保护鲁迅藏书;
另一方面他又带着许广平的亲笔信跟宋紫佩先生取得联系。
1944年10月14日傍晚,宋先生带唐先生到北平阜成门西三条二十一号拜会了鲁迅遗孀朱安女士,说明了保护鲁迅藏书的来意。
朱安开始颇为激动。
她指着自己的鼻子冲着宋先生说: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
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唐先生耐心介绍了上海全部沦陷之后的情况:
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毒刑拷打,甚至遭电刑炙烧,以及南北交通阻梗,汇款不易等情况,朱安的情绪才有所缓和。
据唐先生了解,朱安跟家里那位老女工每月生活费约需9000元(指沦陷区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准”票),而以抚养“老母寡嫂”为由拒绝南下的周作人每月仅补贴朱安150元——据唐先生回忆,当时乘三轮车去一趟北平西山的车费就要100元,对于维持朱安生活而言,这的确是杯水车薪。
而且,这150元原是周作人每月孝敬老母的零花钱,鲁母临终前让朱安代收,作为对终身服侍她的儿媳的一点补偿。
朱安每当收下周作人这一百五十元,眼泪直往肚里咽。
唐先生转达了上海方面的态度:
朱安所需生活费仍由许广平负担;
倘若许广平有困难,上海的朋友也愿意凑钱代付,总之千万不能出售鲁迅藏书。
听到唐先生这番恳切的话语,朱安“当即同意,卖书之议,已完全打消”。
这就是唐先生采取的釜底抽薪法。
今天,我们面对保存完好的鲁迅藏书,对许广平先生和唐等鲁迅生前友好的保存和抢救之功自然会产生缅怀感念之情。
寻访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陈光中
一
1933年,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女作家冰心发表了一篇小说,名为《我们太太的客厅》。
她是这样开头的: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
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
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里聚会,从略。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
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
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从这段暗含调侃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冰心对“太太的客厅”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
曾经有人评论说,她是以这篇文章嘲讽了“所谓洋式家庭中人们生活和精神的空虚和浮靡”。
当时的人们都知道,冰心所说的这位“太太”,是实有其人的。
她就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
然而,林徽因真的是一个整日沉湎于说东道西的庸俗家庭主妇、一个多愁善感无病呻吟林黛玉式的旧时闺秀、一个以咖啡浓茶和不着边际的空谈打发无聊时光的洋派“太太”吗?
其他人显然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著名作家萧乾曾经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
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
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
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
……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
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
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可见冰心的小说毕竟是小说,当不得真。
现实生活中的林徽因,是一位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女性。
林徽因生于1904年6月10日,祖父是光绪年间进士,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两个叔叔是广州黄花岗烈士;
父亲林长民则是一位职业革命家。
梁思成生于1901年4月20日,他的父亲梁启超与林长民是多年至交,因此他们“包办”了两个孩子的婚姻。
1921年,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到北京读书,梁思成与她初次见面。
他曾说:
“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
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
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梁思成最不可能从事的事业就是搞建筑。
他生下来腿部便有疾患,虽经矫正治疗后基本恢复正常,双脚始终还有些内斜;
二十多岁的时候,又遭遇了一次意外的车祸,落下残疾,以致终生跛足。
搞建筑需要经常进行野外考察、实地测量,这样的身体如何能够适应呢!
另外,梁思成的爱好十分广泛,他不仅喜欢各种体育项目,还酷爱音乐,在美术上也颇有天赋。
实际上,梁思成原本是打算学美术的。
但是,这时在他的生活中突然闯进了林徽因,使得他怦然心动,从而做出了决定一生的选择。
1924年7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双双奔赴美国学习;
4年后完成学业,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了婚礼。
去欧洲考察半年后回国,经梁启超安排,到少帅张学良亲自担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工作。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故,与前些年逝世的李夫人合葬于西山脚下。
那造型简洁古朴庄重的榫状墓碑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的。
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设计的第一件建筑作品,居然是父亲的墓碑!
当年8月,林徽因生下一个女儿。
为纪念晚年自号“饮冰室主人”的父亲,他们为女儿起名为“再冰”。
梁思成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父亲给他寄过一本新刊行的古籍《营造法式》,引起他很大的兴趣,那本书是朱启钤1917年在江南图书馆发现的。
朱启钤是一位狂热的建筑学爱好者,就是因为有了这本“宝书”,他自筹资金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并积极邀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
由此,他们回到北京,租下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一个四合院,在那里住了将近7年时间。
几年前,为了寻找这“北总布胡同3号”,我前后去了6次。
但由于门牌改动等原因,始终一无所获。
关于那段经过,我把它记述在我的《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一书的第五册里。
没想到的是,在书出版后不久,我突然接到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先生打来的一个电话。
他告诉我:
老宅如今的门牌是24号,他愿意亲自带我前去。
那院子当初之所以未能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位于胡同中段、隐藏在一个饭馆旁边小夹道的后面。
南边的一排房子显然是年头已久的老屋,从靠西的大门进去,则是一座几乎占了整个院子的新居民楼。
那楼房建于20世纪80年代,原先院中的大部分建筑都被拆除。
它完全彻底地破坏了整个院子的格局,难怪梁从诫先生不断地摇头叹息。
大门一侧有棵老树。
梁从诫称那树为“马樱花树”,也有人叫它“芙蓉树”。
梁从诫的姐姐梁再冰在她写的文章中曾经介绍,梁家住的是一个“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樱花树和丁香树”。
如今那马樱花树虽然还在,而正房、廊子和垂花门却已经不见踪影了。
后来,梁从诫给我看过一份复印件,是林徽因1936年写给她的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上面有一幅手绘的旧居平面图。
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献,建筑师的缜密、家庭主妇的细腻、作家的幽默与风趣……都通过这张小小的信纸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由于梁思成夫妇的生活环境已经基本稳定,投奔他们的亲戚很多,因此尽管宅子不小,却十分拥挤。
林徽因在信中诙谐地说:
没想到一个“老爷”和一个“太太”,居然会发展出17张床和那么多的铺盖。
这17张床的使用者还不包括一名拉黄包车的车夫,现在他仍借住在别人家里,否则,“他只能站在院子里过夜了”!
当然,17张床中不能没有梁思成夫妇的。
他们的卧室就在林徽因的“私人空间”右边,处于重重床铺围困之中的“一位老爷”和“一位太太”。
而正房里卧室旁边那间最大的屋子,就是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林徽因才华出众、热情好客,她家里自然形成了一个文化沙龙,许多学者、名人都是常客,这里还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故事。
在那些客人中,有一位金岳霖先生比较特殊。
这位金先生身材高大仪表出众,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曾经有许多“洋姑娘”追求他,有一位甚至一直追随来到中国,但是他却一见钟情地爱上了林徽因。
梁思成他们住在北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他家后院。
有一次梁思成考察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他说,自己苦恼极了,因为同时爱上了他和老金两个人,不知该如何是好,居然让梁思成帮她拿主意。
梁思成十分痛苦,想了一夜,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自己的确在各方面都不如老金。
第二天,他对林徽因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他祝愿他们幸福。
当时他俩都哭了。
不料过了几天,林徽因告诉梁思成,老金在得知情况后对她说:
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老金真是坦荡君子,说到做到,他们三个也成了最好的朋友。
后来老金几乎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个成员,无论在北京还是去内地,始终相依相伴。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终生不泯,至死未婚。
晚年他与梁思成及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从诫和夫人称其为“金爸”。
这可真是一段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
对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说,在北总布胡同居住的这7年很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1932年8月4日,儿子出生。
为了表达对《营造法式》修撰者李诫的仰慕之情,他们为儿子取名“从诫”。
而他们许多重要调查和研究成果,也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据统计,在那几年里,梁思成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事们调查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对其中的206座进行了详细测绘,完成图稿1898张,可谓业绩斐然!
这些调查工作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
他们不仅要忍受恶劣的天气、泥泞的道路、早出晚归的辛苦,还要承担遭遇土匪抢劫、感染霍乱等传染病的危险。
在回到北平家中后,则忙于整理资料、绘制图样、研究调查结果、撰写总结文章。
难怪林徽因在她画的平面图中着意标出了梁思成那张很大的绘图桌,梁思成诸多著作中那些精美异常的建筑图样,有很多都是出自位于西耳房中的绘图桌上。
1937年,当梁思成夫妇在外地考察的时候,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他们赶紧回到北平。
7月28日,北平被日军占领,几天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带着全家悄悄离开了北平。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辗转于云南、四川,林徽因肺病复发,竟致卧床4年。
在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家里仅有的一些东西陆续送进当铺,以换取必要的食物。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保持着乐观的情绪。
林徽因躺在床上,写出了许多格调清新的诗句;
梁思成在昏暗的油灯下,编纂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当时,一些美国朋友曾来信劝他们到国外去工作或治病,梁思成回信说:
“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
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林徽因支持他的选择。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
1946年7月,他们返回阔别8年的北平,住进清华大学的宿舍。
1947年12月,林徽因又做了肾切除手术。
那几年梁思成很忙。
他刚刚开始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便接到两所美国大学的邀请,前去讲学。
经中国外交部推荐,他还担任了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
由于林徽因病重,他不得不提前匆匆回国。
那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
梁思成除了在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还要在家里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
1948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
一天深夜,有一位朋友带着两位解放军军官来到他们家中。
军官告诉他们,如果与傅作义的谈判不能成功,解放军将被迫攻城。
为了保护京城里的古建筑不致被战火毁坏,请他们在地图上详细标出有关建筑的位置。
这件事使梁思成受到很大触动,他发动教师和学生根据以往搜集的大量资料,以最快的速度编出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林徽因对全书进行了仔细审核。
这本《简目》的问世,不仅为各路解放大军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使大量文物古迹得以保全,同时,也成为1961年4月国务院所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主要依据。
四
新中国成立后的那几年,梁思成与林徽因是忙碌而且愉快的。
他们主持进行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徽因在病榻上完成了纪念碑装饰图案的设计与绘制。
从1946年被医生判处“死刑”时起,林徽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又继续工作了将近十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但是,她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55年4月1日,她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年仅51岁。
林徽因似乎是梁思成的护佑神,随着她的离去,厄运也开始降临了。
195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
到了文化大革命,梁思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自然受到更猛烈的冲击。
从痛失爱妻林徽因开始,梁思成接连遭到许多不幸。
但在“不幸”中也会存在“有幸”,有一位女性陪伴他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10年,使他在饱受磨难的晚年能够感受到难得的慰藉。
这位女性就是林洙。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北京医院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