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鲁迅文学思想之比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陈独秀与鲁迅文学思想之比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陈独秀与鲁迅文学思想之比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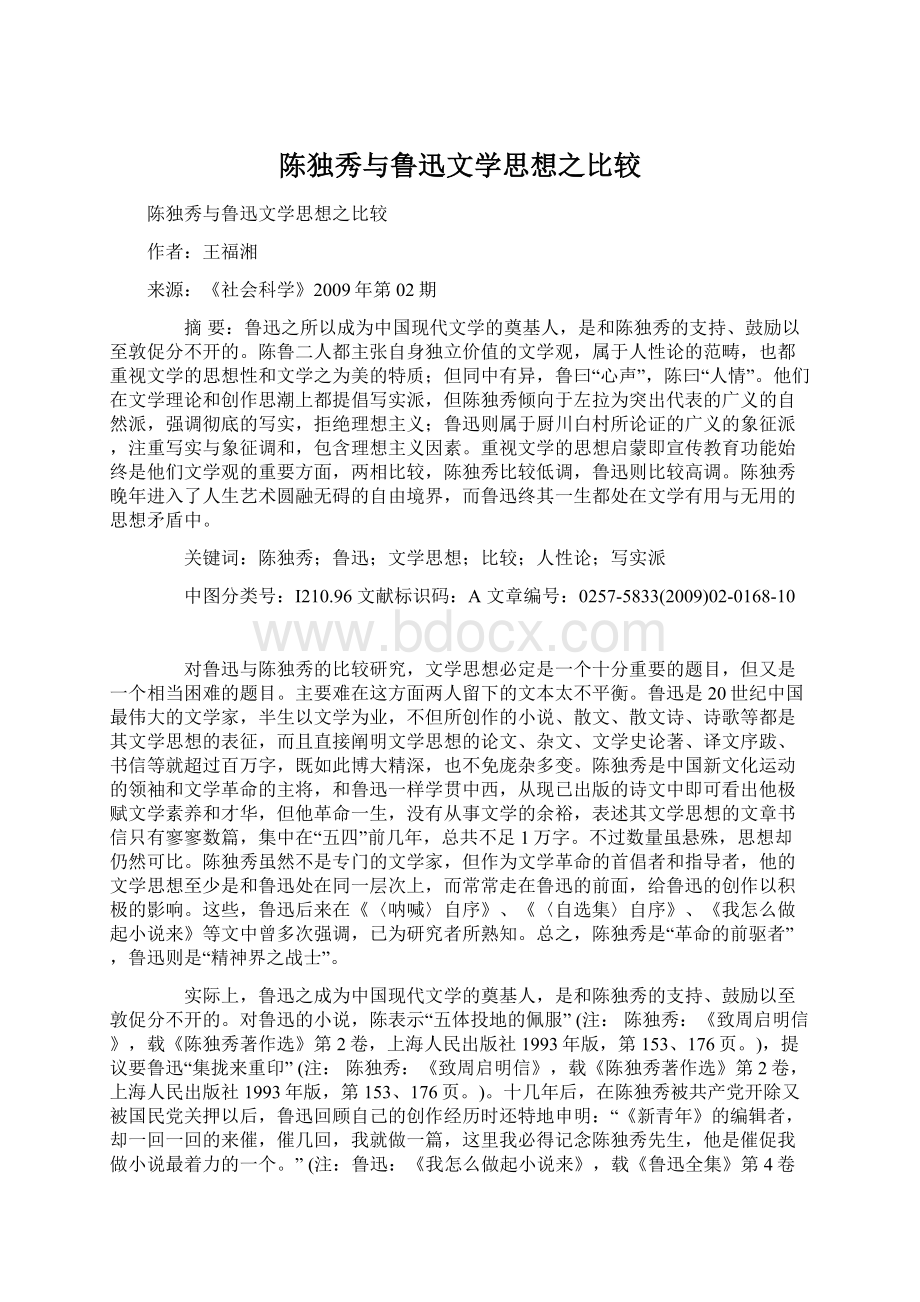
0257-5833(2009)02-0168-10
对鲁迅与陈独秀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想必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题目,但又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题目。
主要难在这方面两人留下的文本太不平衡。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半生以文学为业,不但所创作的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等都是其文学思想的表征,而且直接阐明文学思想的论文、杂文、文学史论著、译文序跋、书信等就超过百万字,既如此博大精深,也不免庞杂多变。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文学革命的主将,和鲁迅一样学贯中西,从现已出版的诗文中即可看出他极赋文学素养和才华,但他革命一生,没有从事文学的余裕,表述其文学思想的文章书信只有寥寥数篇,集中在“五四”前几年,总共不足1万字。
不过数量虽悬殊,思想却仍然可比。
陈独秀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家,但作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和指导者,他的文学思想至少是和鲁迅处在同一层次上,而常常走在鲁迅的前面,给鲁迅的创作以积极的影响。
这些,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自选集〉自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等文中曾多次强调,已为研究者所熟知。
总之,陈独秀是“革命的前驱者”,鲁迅则是“精神界之战士”。
实际上,鲁迅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是和陈独秀的支持、鼓励以至敦促分不开的。
对鲁迅的小说,陈表示“五体投地的佩服”(注:
陈独秀:
《致周启明信》,载《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176页。
),提议要鲁迅“集拢来重印”(注:
)。
十几年后,在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又被国民党关押以后,鲁迅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还特地申明:
“《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注:
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1-512页。
)鲁迅坦然承认: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注:
《〈自选集〉自序》,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5-456页。
)杂文的写作也是如此。
作为一种文体的现代杂文是和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然而其源头却是陈独秀在《新青年》开辟的专栏《随感录》,鲁迅应邀参加《新青年》后,也成为《随感录》的主要作者之一。
在《新青年》需稿的时候,陈独秀就要求周氏兄弟写《随感录》。
他在一次给周作人的信中说:
“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
陈独秀:
《致周启明信》,载《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鲁迅对陈写的《随感录》也特别赞赏,他曾批评《新青年》的某一期“无甚可观,惟独秀随感究竟爽快耳”(注:
《210825致周作人》,载《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页。
鲁迅逝世一年后,陈独秀还以当年的主将身份撰文,高度评价鲁迅“独立思想的精神”,肯定“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注: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所说的“短篇幽默文章”,无疑包括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小说和杂文。
陈鲁二人惺惺相惜,虽无私交,却是建立在相同思想基础上的真正的战友和同志,他们和胡适等其他先行者一道,共同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辉历程。
一
鲁迅自弃医从文始,就以提倡新文学(包括创作、翻译、出版、评介、研究)为自己全部的事业,而陈独秀即使在写《文学革命论》的时候,也只是把它作为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一环。
这当然和他们的童年经历、成年后的志向以及自我的定位有关。
有意思的是,他们从各自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的文学素养出发,却达到了大致相同的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其理论基点是人性论。
在早期的文言论文中,鲁迅就认为文学是“知者”的“心声”与“内曜”,本质上是自由的、真诚的。
“内曜者,破黑甚暗者也;
心声者,离伪诈者也。
《破恶声论》,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他指出文学与科学的区别,是表现“美上之感情”和“明敏之思想”,“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注:
《科学史教篇》,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
强调文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超功利的本质:
“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
”但文章有“不用之用”,“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优秀的文学作品还有“启人生之门必机”的特殊效用,能使读者心领神会,精神上获得教益,因而“自觉勇猛发扬精进”。
他肯定“诗言志”,反对“诗无邪”,认为“强以无邪,即非人志”,以所谓道德规范限制诗人的创作,是“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文学即“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不能发伟美之心声(注:
《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72页。
这种基于普遍人性的自由的文学观在鲁迅头脑里根深蒂固,“五四”以后他用白话文更明确地论说了文学与国民精神“互为因果”的关系: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注:
《论睁了眼看》,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他仍然强调文学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反思“五四”时期“须听将令”的“呐喊”并非自己“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心声,于是“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注:
《〈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420页。
鲁迅把反对文以载道、主张独立自由的文学观贯彻在他的小说史研究中,认为“唐人小说少教训;
而宋则多教训。
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
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
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
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注: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即使在大革命时代,真诚拥护革命的鲁迅却并不赞同文学要和革命发生多大关系,认为那些宣传、鼓吹、煽动革命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
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注:
《革命时代的文学》,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423页。
对“革命文学”的经典比喻,“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注:
《革命文学》,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页。
所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他在关于魏晋文学的著名演讲中,肯定曹丕所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甚至提出了与经常公开主张的“为人生”貌似对立的文学史观,“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注: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
一言以蔽之,即是“抒写自己的心”。
而人道主义者鲁迅“自己的心”乃是对人民、对人类的博大的爱心,所以他说,“创作总根于爱”(注:
《小杂感》,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页。
)。
1927年以后,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文学思想上则接受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理论影响,但他没有变成单纯的阶级论者,而是同时包含阶级论和人性论,二者消长起伏,其矛盾最终都未能解决。
当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掀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向鲁迅发起“围剿”的时候,鲁迅没有从根本上即从理论上反对这个运动,他还承认提出这个口号的功劳,只是表示了对倡导者们自命为无产阶级代表身分的真实程度的怀疑,批评了他们所谓“革命文学”内容的空洞和艺术的拙劣。
他“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
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注:
《文艺与革命》,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而文艺在形式上不同于一般宣传品的特征,纵观鲁迅对自己创作的评论,除了表现的“技巧”或曰“技术”,还有“趣味”(注:
《“醉眼”中的朦胧》,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用现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艺术的审美乃属于文学的本质特征。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的陈独秀,其实和鲁迅一样很有文学天份,他虽无意于做一个文学家,却毫无疑问是一位善写旧体诗的现代诗人。
他常常有感而发,赋诗言志,情景交融而力透纸背,尤其可贵的是他历尽磨难,诗情终身不减,诗句老而愈工,字里行间抒写了他的崇高人格和博大情怀。
近些年来陈独秀的诗作已被陆续搜集并整理出版,已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他精湛的诗歌艺术,发表了这方面的论著。
有这些出色的诗歌为证据,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陈独秀的文学思想文字虽然不多,却决不是虚泛的理论和肤浅的感想,而是和鲁迅一样有深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以及自身的创作体验作底蕴,所以真切深刻,言简而意赅,言近而旨远。
根据目前能够看到的资料,最早传达陈独秀文学思想的是1904年《安徽俗话报的章程》里关于小说的介绍:
“无非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还要有趣哩。
《安徽俗话报的章程》,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此时陈独秀对文学的思考还很简单,标准是传统的通俗的人情和趣味,但已经表现出超越古人的文学眼光。
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前夕,他为苏曼殊的悲情小说《绛纱记》作序,认为“死与爱皆有生必然之事”,又是“人生最难解之问题”,作者意欲探讨二者“孰为究竟”,男女主人公“一殁一存,而肉薄夫死与爱也各造其极”。
序言又介绍英国唯美派作家王尔德由《圣经》故事改写的著名悲剧《莎乐美》,称赞“王尔德以自然派文学驰声今世,其书写死与爱,可谓淋漓尽致矣”(注:
《〈绛纱记〉序》,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8页。
虽与普通的流派说法相异,但见仁见智亦无不可。
陈独秀从《莎乐美》中看到的不是唯美的艺术形式,而是“淋漓尽致”地“书写死与爱”的“人生之真”,这正是唯美派与自然派的内在相通之处。
对王尔德及《莎乐美》的赏识,实乃陈独秀对欧洲近代文学史的真知灼见。
序言借用法国人柯姆特的话,提出爱情为“生活之本源”的人性论文学观,归纳出苏曼殊与王尔德及他本人文学思想的同义性。
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为苏曼殊新作《碎簪记》写的序,重申了这一文学观:
“食色性也,况夫终身配偶,笃爱之情耶?
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
而此则其最痛切者。
古今中外之说部,多为此而说也。
《为苏曼殊〈碎簪记〉作后叙》,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这就进一步指明文学创作是“个人意志之自由”受社会压迫的产物,爱情之痛则为其最,比鲁迅的“心声说”更具体。
对于文学自身的独立的特殊的价值,陈独秀也有更明确的表述。
当胡适在通信中提出“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时,陈独秀极力支持,希望他“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这样催生出来的。
但陈独秀对胡适“须言之有物”一语却表示不解和质疑:
“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
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
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
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
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
《答胡适之(文学革命)》,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220页。
)在《新青年》刊登的另一封通信中,陈独秀继续批评“言之有物”论的弊病,进而阐发了自己以“达意状物”且“美妙动人”为其本义的文学观:
何谓文学之本义耶?
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
达意状物,为其本义。
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
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
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
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
(注:
《答曾毅(文学革命)》,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3页。
)
不言而喻,陈独秀所达之“意”和鲁迅所发的“心声”一样,都包含了思想的成分。
鲁迅发表过一篇《亻疑播布美术意见书》,提出“美术者,有三要素:
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
“作者出于思,倘其无思,即无美术。
”这里“美术”即指艺术,包括“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注:
《亻疑播布美术意见书》,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文章”就是今之文学,“思理”之中就有今之思想。
陈独秀更重视思想在文学中的位置,他强调说:
“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
”他以西方著名作家为例,证明“西洋大文豪,类为大哲人”:
“三大文豪之左喇,自然主义之魁杰也。
易卜生之剧,刻画个人自由意志者也。
托尔斯泰者,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世文明,其宗教道德之高尚,风动全球,益非可以一时代之文章家目之也。
”“若英之沙士皮亚,若德之桂特,皆以盖代文豪而为大思想家著称于世者也。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续)》,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可见陈鲁二人都认为,思想性为文学应有之义,即文学本是有思想的,无思想不是真正的文学,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
陈独秀也许是最早提出了文学的“美”的本质,且对“文学美文之为美”作了具体的解释:
“结构之佳,择词之丽(即俗语亦丽,非必骈与典也),文气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动人:
此四者,其为文学美文之要素乎?
应用之文,以理为主;
文学之文,以情为主。
《答常乃(古文与孔教)》,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强调“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区别于“以理为主”的“应用之文”,正是陈独秀人性论文学观的主要论点。
陈鲁二人主张自身独立价值的文学观,都属于人性论的范畴,他们也都重视文学的思想性和文学之为美的特质;
所以,在文学理论思潮上,陈独秀推崇以情为主的广义自然派,鲁迅则认同根于生命力的广义象征派。
二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诚然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所倡“三大主义”是破旧立新的纲领性主张。
但全文以驳论为主,详述中国文学的缺点即文学革命的理由,而正面申说他的文学思想的文章,以1920年2月12日《晨报》刊登的《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
——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最为全面系统。
这是研究陈独秀文学思想和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他在综合大量的中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可惜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大纲”只是一个框架。
其中“文学底界说”一节在列举培根等人的说法之后,明确提出“我的主张”:
“
(一)艺术的组织;
(二)能充分表现真的意思及情;
(三)在人类心理上有普遍性的美感。
”三者之中,又以第三点为本。
他论证在“文学的饰美”方面“白话胜过文言”,认为白话文“‘白描’是真美,是人人心中普遍的美”(注:
《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
——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载《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3页。
文学艺术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注: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载《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陈独秀在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仍然把文学艺术与政治经济区分开来,指出无政府主义“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
因为艺术离开了物质社会的关系,没有个体自由底冲突,所以他的自由是能够绝对的,而且艺术必须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了一切束缚,天才方可以发展”(注:
《社会主义批评》,载《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
这种基于普遍人性的真美的自由的文学观,加上他所接受的历史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观,就使他在文学思潮上倾向于广义的自然派,即以左拉提倡的自然主义为理论代表,把在此前后欧洲各国的现实主义作家都包括在内,甚至唯美派的王尔德因符合“以情为主”的标准也被拉了进来。
还在文学革命前,陈独秀就撰写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近代欧洲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历史:
“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
自然主义,唱于十九世纪法兰西之文坛,而左喇为之魁。
氏之毕生事业,惟执笔耸立文坛,笃崇所信,以与理想派文学家勇战苦斗,称为自然主义之拿破仑。
此派文艺家所信之真理,凡属自然现象,莫不有艺术之价值,梦想理想之人生,不若取夫世事人情,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美也。
故左氏之所造作,欲发挥宇宙人生之真精神真现象,于世间猥亵之心意,不德之行为,诚实胪列,举凡古来之传说,当世之讥评,一切无所顾忌,诚世界文豪中大胆有为之士也。
他赞扬自然派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当时青年文士及美术家,承风扇焰,遍于欧土,自然派文学艺术之旗帜,且被于世界。
”“现代欧洲文艺,无论何派,悉受自然主义之感化。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57页。
)他认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
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自然主义尤趋现实,始于左喇时代,最近数十年来事耳。
虽极淫鄙,亦所不讳,意在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视写实主义更进一步”(注:
《答张永言(文学-人口)》,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因此,他不但反对古典主义,也从根本上拒斥理想主义:
欧洲自然派文学家,其目光惟在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彼所描写之自然现象,即道即物,去自然现象外,无道无物,此其所以异于超自然现象之理想派也。
理想派重在理想,载道有物,非其所轻。
惟意在自出机杼,不落古人窠臼,此其所以异於钞袭陈言之古典派也。
与陈独秀不同,鲁迅在开始从事文艺运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时候,却选择了“摩罗诗派”,“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
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
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注:
他所呼唤和立志要做的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也就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可是失败的经验使他反省,看见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
),从而淡化了理想的色彩,消沉了战士的斗志。
十年之后应邀参加《新青年》的鲁迅,虽然恢复了战斗的意气,但在文学上则不再张扬理想主义,转而提倡写实与象征。
《狂人日记》就是融写实与象征为一体的典范,《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艺术倾向。
鲁迅最早翻译的小说家是俄国的安特来夫、迦尔洵和阿尔志跋绥夫,他称安氏“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
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注:
《〈域外小说集〉杂识》,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
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注:
《〈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又称阿氏,“是俄国新兴文学的代表作家的一人;
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注:
《〈幸福〉译者附记》,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这些评价实际上正是鲁迅追求和已达到的艺术目标。
鲁迅的文学思想从摩罗派向写实派即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除受个人经历和俄国文学的影响外,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所主导的时代潮流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鲁迅自云是“遵命文学”,“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注:
),陈独秀的文学主张对这一转型的作用乃是不言而喻的。
但鲁迅决非亦步亦趋的追随者,他有独立的思想和文学的天才,所以他的现实主义就不是单纯的客观的普通意义的写实,而具有现代性的艺术特质,除前面提到的与象征相融合外,更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显示灵魂的深”,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注:
《〈穷人〉小引》,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04页。
在显示人的灵魂这一基点上,现代的写实派和摩罗派本有着潜在的联系,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则给鲁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的体系,鲁迅文学思想看起来发生了转型,其实是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