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docx
《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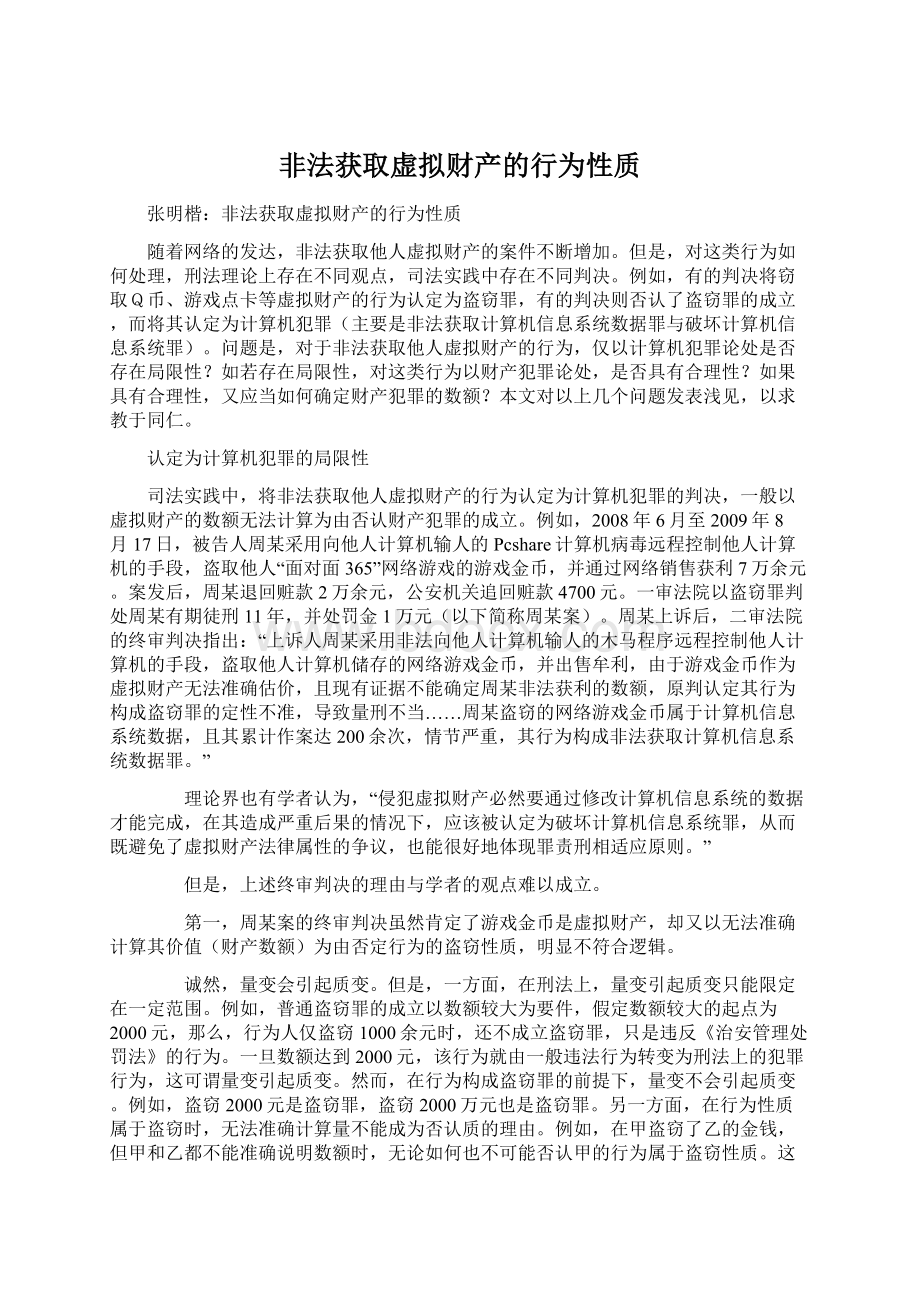
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
张明楷:
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
随着网络的发达,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案件不断增加。
但是,对这类行为如何处理,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判决。
例如,有的判决将窃取Q币、游戏点卡等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有的判决则否认了盗窃罪的成立,而将其认定为计算机犯罪(主要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问题是,对于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仅以计算机犯罪论处是否存在局限性?
如若存在局限性,对这类行为以财产犯罪论处,是否具有合理性?
如果具有合理性,又应当如何确定财产犯罪的数额?
本文对以上几个问题发表浅见,以求教于同仁。
认定为计算机犯罪的局限性
司法实践中,将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计算机犯罪的判决,一般以虚拟财产的数额无法计算为由否认财产犯罪的成立。
例如,2008年6月至2009年8月17日,被告人周某采用向他人计算机输人的Pcshare计算机病毒远程控制他人计算机的手段,盗取他人“面对面365”网络游戏的游戏金币,并通过网络销售获利7万余元。
案发后,周某退回赃款2万余元,公安机关追回赃款4700元。
一审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万元(以下简称周某案)。
周某上诉后,二审法院的终审判决指出:
“上诉人周某采用非法向他人计算机输人的木马程序远程控制他人计算机的手段,盗取他人计算机储存的网络游戏金币,并出售牟利,由于游戏金币作为虚拟财产无法准确估价,且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周某非法获利的数额,原判认定其行为构成盗窃罪的定性不准,导致量刑不当……周某盗窃的网络游戏金币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且其累计作案达200余次,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
理论界也有学者认为,“侵犯虚拟财产必然要通过修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才能完成,在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应该被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从而既避免了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争议,也能很好地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
但是,上述终审判决的理由与学者的观点难以成立。
第一,周某案的终审判决虽然肯定了游戏金币是虚拟财产,却又以无法准确计算其价值(财产数额)为由否定行为的盗窃性质,明显不符合逻辑。
诚然,量变会引起质变。
但是,一方面,在刑法上,量变引起质变只能限定在一定范围。
例如,普通盗窃罪的成立以数额较大为要件,假定数额较大的起点为2000元,那么,行为人仅盗窃1000余元时,还不成立盗窃罪,只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
一旦数额达到2000元,该行为就由一般违法行为转变为刑法上的犯罪行为,这可谓量变引起质变。
然而,在行为构成盗窃罪的前提下,量变不会引起质变。
例如,盗窃2000元是盗窃罪,盗窃2000万元也是盗窃罪。
另一方面,在行为性质属于盗窃时,无法准确计算量不能成为否认质的理由。
例如,在甲盗窃了乙的金钱,但甲和乙都不能准确说明数额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否认甲的行为属于盗窃性质。
这是因为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具有类型性,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属于特定类型的行为,其性质不可能由于数额难以计算就发生改变。
刑法虽然针对盗窃罪规定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与“数额特别巨大”三种量刑规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在任何一起案件中都必须查明行为人所窃取财物的具体数额。
换言之,在对盗窃数额不能准确评定的情况下,只要有证据证明达到了数额较大、巨大或者特别巨大的标准,即使未能确定具体数额,也能相应地定罪量刑。
例如,倘若能够肯定行为人的盗窃数额不少于5000元,即使不能确定具体数额,也应当按“数额较大”定罪量刑。
同样,倘若能够确定行为人的盗窃数额不可能少于60万元,即使不能查明具体数额,也应当按“数额特别巨大”处理。
事实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难以准确计算价值的盗窃行为,也没有否认其盗窃性质。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4月2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4款规定:
“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显然,毒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虽然无法准确估价,但盗窃毒品、淫秽物品的行为性质没有变化,仍然成立盗窃罪。
既然如此,对于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就不能以数额难以计算为由而否认盗窃罪的成立。
第二,周某案的终审判决虽然肯定行为人非法获利,但以现有证据不能确定行为人非法获利的数额为由否定行为的盗窃性质,同样不符合逻辑。
“非法获利数额”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
一方面,如果说非法获利数额就是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数额,那么,在周某案中,所谓“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周某非法获利的数额”也就意味着“虚拟财产无法准确估价”。
但如上所述,难以计算被害人的财产数额或者行为人所窃取的财产数额,并不直接影响行为的盗窃性质。
另一方面,如果说非法获利数额是通过销售、转移所盗财物而获取的数额,那么,这种数额难以计算以及是否有证据证明,更不影响行为的性质。
倘若终审判决所称的不能确定非法获利数额,是指不能确定行为人最终实际获得的利益数额,则意味着行为人盗窃财物后的销赃数额不明的,不成立盗窃罪。
据此,行为人盗窃一台手提电脑后,不能查清销赃数额的,就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一套住房后将其出售,但不能査明出售价格的,也不能认定为受贿罪。
可是,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立。
如所周知,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7项规定:
“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
”其中的销赃数额可谓行为人的获利数额。
但是,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不管行为人销赃数额多高,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数额并不因此增加。
既然如此,就只能按被害人所丧失的财物数额来计算行为人的盗窃数额。
如果盗窃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将所盗财物高价卖给他人,达到诈骗罪数额起点的,除成立盗窃罪之外,还另成立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
正因为原有司法解释存在明显缺陷,所以,2013年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删除了上述规定。
由此看来,以被告人的非法获利数额不能得到证明而否认行为的盗窃性质,明显不当。
第三,“周某盗窃的网络游戏金币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这一结论,并不能直接否认周某的行为成立盗窃罪。
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对象都可能具有多重属性,网络游戏币虽然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但仅此还不足以否认它是财物或者财产。
倘若虚拟财产既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也是财物,就不能以计算机犯罪属于特别规定为由对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以计算机犯罪论处。
因为《刑法》第287条明文规定:
“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所以,只要行为构成盗窃罪,即使利用(侵人)了计算机信息系统,也不能认定为计算机犯罪。
诚然,刑法与民法理论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还存在争议,可是,单纯避免争议并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良策。
如果为了避免争议,对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一概以计算机犯罪论处,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妥当性,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若对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一概以计算机犯罪论处,导致处罚的不均衡、不协调,或者形成不应有的处罚漏洞,则必须解决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问题。
事实上,如后所述,将针对虚拟财产实施的犯罪行为一概以计算机犯罪论处并不合适。
第四,将针对虚拟财产实施的盗窃等行为一概以计算机犯罪论处,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其一,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是对公法益的犯罪,但上述周某的行为主要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个人法益。
通过将某种行为认定为侵害公法益的犯罪来保护个人法益,明显不当。
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侵害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利,也不利于附带民事诉讼。
例如,张三花5万元购买了Q币等虚拟财产后,随即被李四窃取。
如果对李四的行为仅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那么,张三就难以行使相关的诉讼权利。
这种做法不仅忽视了对张三财产的保护,而且进一步侵害了张三的相关诉讼权利。
其二,当行为人采用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他人的网络游戏币、Q币等虚拟财产时,不可能认定为计算机犯罪。
例一:
A等人在游戏厅以暴力相威胁,让被害人说出网络账户与密码,然后通过设置新密码的方法,将其价值数万元的Q币据为己有。
这种行为并没有非法侵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也不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构成要件,更没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例二:
B以欺骗手段让他人将价值数万元的Q币转人自己账户的,也不可能认定为计算机方面的犯罪。
例三:
网络运营商的工作人员C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合法进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盗卖虚拟财产的,不能以计算机犯罪论处。
显然,认为“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建立在没有全面了解各种可能发生的案件的基础上,因而不可取。
换言之,如果按照周某案终审判决的观点,对于上述A、B、C的行为就没有办法处理,会形成明显的处罚漏洞。
其三,将针对虚拟财产实施的盗窃等行为一概以计算机犯罪论处,并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
例如,A准备了50万元现金,打算用于购买Q币,但在购买之前被甲悉数盗走。
B准备了50万元现金后立即购买了价值50万元的Q币,但购买后还没有使用,乙立即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一次盗走了B的全部Q币。
按照周某案终审判决的观点,对甲应认定为盗窃罪,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对乙应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法定刑。
或许有人认为,对乙可以适用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是,对乙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本身并不能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倘若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一定是考虑了行为人所侵害的财产数额,这反过来说明应当重视对被害人财产的保护。
况且,即使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也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
综上所述,将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计算机犯罪的观点与做法,既可能形成处罚漏洞,也可能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因而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还有学者指出:
"对于盗窃、诈骗虚拟财产(包括虚拟货币和虚拟装备)的行为应当交由游戏公司自己加以解决……当丢失虚拟财产的玩家向游戏商报告了丢失的虚拟财产的品名和丢失的时间并报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游戏账号和身份证号码后,游戏商应从盗窃、诈骗者的账下将虚拟财产予以没收,然?
?
后发还给丢失者,游戏商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或者永久关闭盗窃诈骗他人虚拟财产的玩家的游戏账号,以示惩戒。
”不能不认为这种想法过于天真。
一方面,如果没有法律制裁,只是关闭游戏账号,就不可?
?
能对盗窃、诈骗虚拟财产的行为起到任何抑制作用。
例如,即使关闭原有账号,行为人也可以立即注册新的账号,于是盗窃、诈骗虚拟财产的行为层出不穷,因而不可能保护被害人的法益。
另一方面,如果只是由游戏公司发还给丢失者,根本不可能救济不知情的其他被害人。
例如,甲将乙的高级游戏装备盗卖给不知情的丙,丙向甲支付了1万元人民币。
乙发现自己的游戏装备被盗后,联系游戏公司,游戏公司将游戏装备发还给了乙。
可是,游戏公司不可能救济丙的财产损失。
不难看出,上述“对于盗窃、诈骗虚拟财产(包括虚拟货币和虚拟装备)的行为应当交由游戏公司自己加以解决”的观点根本行不通。
认定为财产犯罪的合理性
在行为人以盗窃、抢劫等方式非法获得他人虚拟财产时,可以肯定该行为属于盗窃、抢劫行为,以及行为人具有故意与非法占有他人虚拟财产的目的。
关键的或者有争议的问题只有一个,即虚拟财产是否属于刑法上作为财产犯罪对象的财物?
如果能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么,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就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法益,应认定为财产犯罪。
一方面,人们不可能在承认虚拟财产属于刑法上财物的同时,又认为虚拟财产不值得刑法保护。
这是因为作为财产犯罪对象的财物,并没有特别的限定。
另一方面,只要承认虚拟财产是财物,不管采取何种犯罪论体系,都能肯定这类行为成立财产犯罪。
概言之,只要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