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对形而上学本原观的解构及其伦理意义Word文档格式.docx
《德里达对形而上学本原观的解构及其伦理意义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德里达对形而上学本原观的解构及其伦理意义Word文档格式.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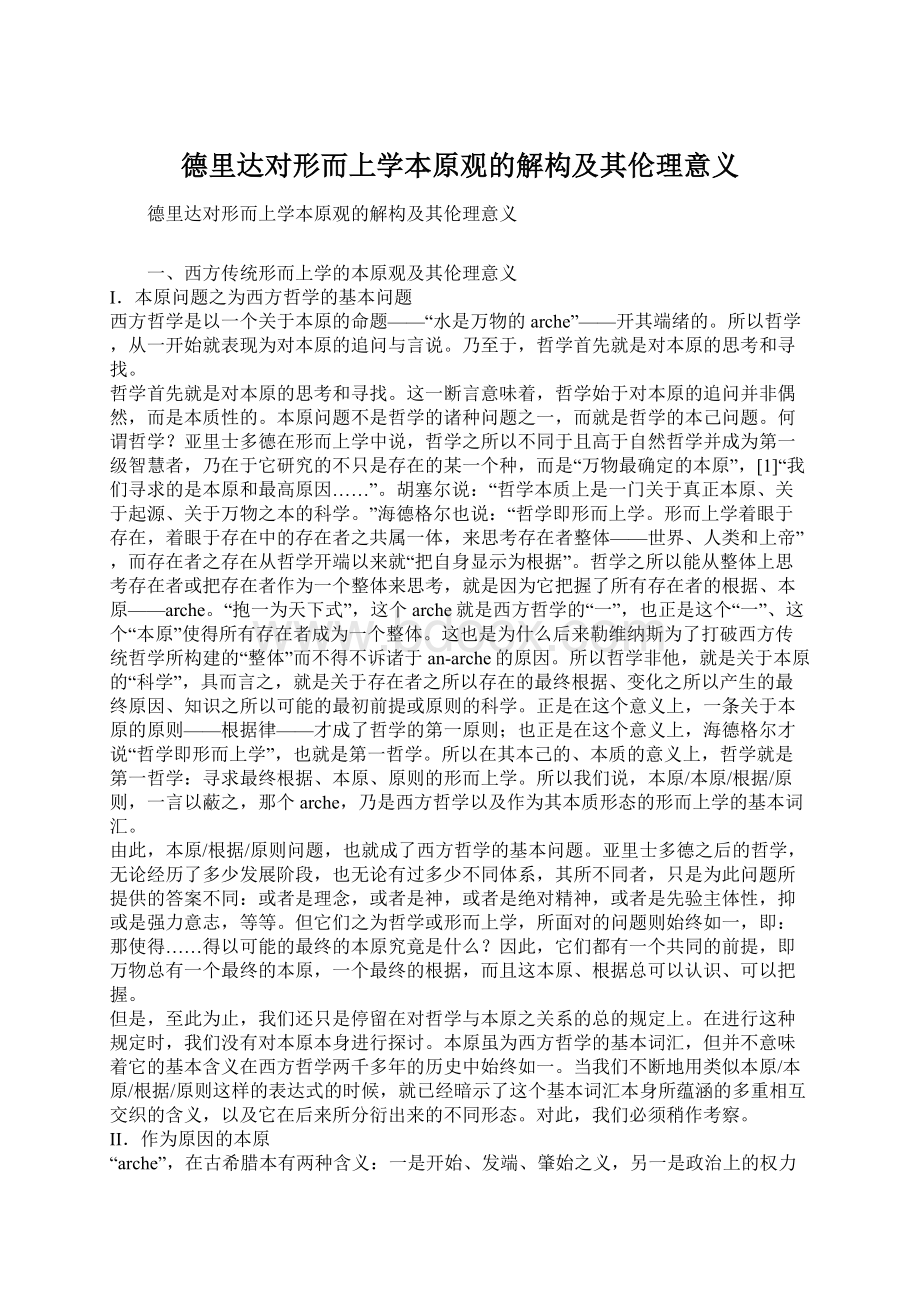
由此,本原/根据/原则问题,也就成了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无论经历了多少发展阶段,也无论有过多少不同体系,其所不同者,只是为此问题所提供的答案不同:
或者是理念,或者是神,或者是绝对精神,或者是先验主体性,抑或是强力意志,等等。
但它们之为哲学或形而上学,所面对的问题则始终如一,即:
那使得……得以可能的最终的本原究竟是什么?
因此,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万物总有一个最终的本原,一个最终的根据,而且这本原、根据总可以认识、可以把握。
但是,至此为止,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对哲学与本原之关系的总的规定上。
在进行这种规定时,我们没有对本原本身进行探讨。
本原虽为西方哲学的基本词汇,但并不意味着它的基本含义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如一。
当我们不断地用类似本原/本原/根据/原则这样的表达式的时候,就已经暗示了这个基本词汇本身所蕴涵的多重相互交织的含义,以及它在后来所分衍出来的不同形态。
对此,我们必须稍作考察。
II.作为原因的本原
“arche”,在古希腊本有两种含义:
一是开始、发端、肇始之义,另一是政治上的权力、政府官员和统治之义。
正是这后一种含义后来演化出了“根据”、“原则”等义。
但是,据语文学家考证,在这两种含义中,前一种含义要更古老,它在荷马那里就已出现。
在荷马史诗中,动词archein就意味着引导、打开、开始,而并没有命令、权力、主宰等义。
只是到了希罗多德与品达那里,这后一层意义才出现。
但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这后一种含义竟逐渐压倒乃至取代了前者而成了arche在哲学上的主导意义——这一点在希腊语的arche最终演变成拉丁语的principium时达到了顶点。
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当泰勒斯等其他的早期自然哲学家说万物的本原是水或其他东西时,这个arche究竟只是时间意义的本原,还是同时也已具有了支配、统治乃至根据、原则等意,这一点尚有争论。
但到亚里士多德那里,arche作为一个哲学词汇已同时具备了“开端”与“统治”这两种含义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ReinerSchurmann甚至认为把arche的这两种含义在哲学上结合起来乃是亚里士多德的创新。
但是,这种结合是否也是arche的一种含义压倒乃至最终取代另一种含义的开始?
无论如何,这种结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自觉。
他在《形而上学》中在总结arche的含义时写到:
“arche的含义有:
事物开始的部分,比如一条线或一条路,无论在相反的那一端。
事物最好的出发点,例如学习时,我们有时并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最容易学好的地方开始的。
事物从它的某个内在的部分首先产生的,比如船从龙骨开始,房屋从基础开始……事物从某个不是它内在的部分开始产生,运动变化都从它开始产生,比如小孩是从他的父亲和母亲开始,而打架是从骂人开始产生的。
运动变化的事物是由于某个东西的意志而产生运动和变化的,例如城邦的统治,寡头政治、君主政治和僭主政治,也都被称作archai,技术也是这样,特别是建筑术。
由于它而开始认识事物的,也叫作本原,比如,假设是证明的开始。
原因也有这么多含义,所有的原因也都是本原[即本原——引者]。
所有的arche有个共同点,它们是事物的存在、产生以及被认知和说明的起点;
但它们有的是在事物以内,有的却是在事物以外的。
所以,作为arche的本性,它是事物的元素,事物的倾向和选择,事物的本质,事物的目的因——因为‘善’和‘美’是许多事物的知识和运动的起点。
”[10]
从这段对arche之含义的总结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几个重要信息:
一、亚里士多德已明确认识到arche的含义中包含了“统治”这一意义,比如在第个含义中。
二、他指出,在存在、变易和认知三个领域中,都存在arche:
“所有的arche有个共同点,它们是事物的存在、产生以及被认知和说明的起点”。
具体地说,在存在中它是开始并主宰万物的实体;
在变易中它是原因;
在知识中它是认知所依赖的前提。
[11]由此,这样一种arche,就成了“事物的元素”、“事物的本质”,最终成了“事物的目的因”。
它是在事物的分析中不可还原或不可归约的最后的因素。
但在这段话中,更为重要的是它所传达出的第三个信息:
即arche被等同于原因,或原因被等同于arche:
“原因也有这么多含义,所有的原因也都是本原”。
Arche转变成了原因。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思想史后果的转变。
正是由于这一转变,亚里士多德对arche的解释与他的四因说重合了:
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对于本原或本原的追寻成了对原因的追寻,成了对终极因、第一因的寻找,而他的四因说也正是对那些在他之前的各种关于本原、本原的学说的一种因果性的重新解释:
米利都的哲人们追寻到的是质料因,毕达哥拉斯追寻到的是形式因,恩培多克勒追寻到的是动力因,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追寻到的是目的因。
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四因的经验从何而来?
显然,它主要来自于对变易的经验,更准确地说,来自于对人类的制造活动的经验:
只有在制造活动——如建筑:
它之为architecture本身已传达出了这种信息——中,人才能鲜明地经验到所谓四因。
这样,在把arche经验为原因之际,哲学发生了何种变化?
在这种经验中我们获得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
在阿那克西曼德那里,在赫拉克力特那里,在巴门尼德那里,arche是被经验为原因的吗?
何谓原因?
“真正的原因只能是那种开始并永不停息地开始一个行动的东西。
”[12]有因必有果。
原因总是与结果联系一起。
当arche与原因被等同时,我们从中听到的是否是一种因果的必然性?
而在因果的必然性中,“果”是否又始终已被“因”统治着、决定着?
因此是否在这里,在原因这个表象中,arche的两种基本含义才可能真正结合起来?
[13]并且前一种含义逐渐为后一种含义所压倒并最终取代?
不特如此。
因不仅统治着、决定着果,而且这种统治与决定是“事-先”的:
在作为“果”的“事情”发生之前、之先,一切都已经决定好了、安排好了。
所以,在因果性统治的领域中,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新鲜的事情发生,根本就没有发生、开端、肇始这回事。
一切都是现成存在的。
也唯有现成存在者,才适合因果性的范畴。
III.本原与存在,或形而上学与存在论
亚里士多德把arche解释为引起变易的第一因或终极因,然则这个终极因,这个arche,在他这里究竟是什么?
他说,那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本身”:
“假若那些寻求各种存在者之元素的人所寻求的就是这些本原,那么,这些元素必然并不为就偶性而言的存在所有,而是为作为存在的存在所有。
所以我们应当把握的是作为存在而存在的最初原因。
”[14]因而,这“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就是使得具体存在者得以存在的那个存在本身,就成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开篇就写到:
“有一门学科,它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和由于本性而属于它的那些属性”,[15]仅隔几行,他就写下了我们刚才引用过的那句话:
“[既然]我们寻求的是本原和最高的原因……”。
[16]可见,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作为存在的存在”当作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它才是最终的arche:
真正的本原、原因或根据。
一如海德格尔所说“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于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arche,aition,Prinzip】”,正是由于此根据,“存在者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才成为在其生成、消亡和持存中的某种可知的东西,某种被处理和被制作的东西。
”[17]
此“作为存在的存在”又是“什么”呢?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它就是“ousia”——由系动词的分词形式on(being)演化而来的正式名词形式——一般被理解为“本质”或“实体”,但海德格尔认为应该是“在场”或“在场状态”的“东西”。
[18]所以海德格尔说:
“根据显示自身为在场状态。
”[19]此在场状态在存在论时间状态上的含义就是“当前”:
古希腊人总已经从当前、现在出发来理解和经验存在、在场了。
所以存在、在场即当前、现在:
过去已不存在,未来尚未存在,唯现在存在。
[20]就此而言,存在是非时间的,而时间是不存在的。
[21]于是,被理解为ousia的arche也就超出于时间的流变之外,作为超时间、非时间的本原,隐秘地主宰着、统治着一切时间性的变易和生成。
由此出发,我们才可以理解,何以形而上学必然是在场形而上学。
因为形而上学所追求的作为存在的存在,总已经被预先理解为现在存在,即在场。
唯现在存在,过去与将来不仅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消磨。
正如德里达所看到的,过去与将来被看作是颠覆在场的消磨作用,而在场又被视为那存在者的意义或本质。
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一直都未改变。
[22]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之所以“纯形式”才是第一实体、第一因、最后的根据或本原,就是因为唯纯形式才永恒在场,才脱离了时间的变化,才是纯粹现实,才真正存在。
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说只有纯形式或神才是真正的第一推动力、第一因、至善、最终的根据或本原时,他说的实际上是:
在场——那超出时间变化之外的永恒的在场本身、纯粹现实,才是第一推动力、第一因、至善、最终的根据或本原。
所谓“纯形式”或“神”只不过是它的名字。
但它之所以能成为第一推动力、第一因、最终的根据或本原,又是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万物都以它为追求的最高目的。
因此正如德里达所说:
“作为‘纯粹现实’的第一推动力是纯粹在场。
作为纯粹在场,它通过它所激发起的欲望而引起了全部的运动。
它是至善,是最高的可欲对象”。
欲望总是对在场的欲望。
[23]正是这种对在场的欲望、对纯粹现实的欲望,引发了全部的运动。
所以本原形而上学最终成了在场形而上学,成了欲望形而上学。
这样一种以在场为最高目的的形而上学,也是一种“在场目的论”。
[24]
但当我们说,亚里士多德把最终的arche规定为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本身的时候,或存在之所以成为形而上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乃是因为它才是最终的arche的时候,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即:
arche与on的关系问题。
Arche与on,究竟是谁来回答谁?
arche还是on才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词汇?
究竟对arche的追问还是对存在的研究才是西方哲学的核心?
如果说,存在之所以在后世哲学中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恰恰是因为它被视作了真正的arche,那么显然,对arche的追问要比对存在的追问更根本、更一般,形而上学要比存在论更基本、更一般。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想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在中西哲学之间——来思考现代哲学的困境。
如果存在论——由于其与西方语言本身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而真的只为西方哲学所独有,那么形而上学是否也仅为西方哲学所独有?
或者相反,作为对本原、本原、根据的追问,形而上学乃是一切人类思想不可逃避的共通命运?
如果真的如此,我们能否超越存在论,而在形而上学这个更一般的层面上展开中西思想的对话与交流?
但是,如果,如果对arche的追问,对本原、本原、根据的追问,最终又不得不回到存在问题,就是说,如果最终的arche只能是存在,如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
或如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根据问题的区域最终不得不回到Dasein之生存的“超越”,[25]就是说,如果形而上学最终不得不回到存在论,那又怎么办?
但事情又真的如此吗?
根据问题真的必须回置到存在问题?
形而上学真的必须回置到存在论?
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至少勒维纳斯就开始试图对存在论与形而上学进行区分、剥离。
但我们这里只能提出而无法展开这个问题。
IV.作为原则的本原[26]
如果说,在古希腊arche的含义无论怎样嬗变都还始终保持着本原、肇始这样一种基本的含义,那么随着被拉丁化为principium,这样一种开端、肇始的意义就逐渐让位于它的另一种基本含义:
统治、宰制。
Arche变成了principium,本原变成了原则。
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转变。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当我们说arche同时也是telos的时候,意味着由它肇始的是一个变易的过程:
向着telos生成的过程,或不如说是这个telos逐渐实现的过程。
虽然arche作为被先行视见的telos,因此作为eidos,自身似乎是超时间的,永恒在场的,但它所开其端的却是一个时间性的生成变易的过程:
arche是一个生成变易之过程的arche。
但现在,当arche变成principium时,它所起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肇始一个变易过程,如在人类制造领域中所经验到的那样,而是提供一种原则和基础。
与它相对的也不再是一个时间性的变易过程,而是一个等级秩序:
principium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说明一个变易是如何发生并向何发生,而是说明一个秩序如何可能。
这种变化如何可能?
arche如何可能从一个肇始的动力、目的变成了一个静止的原则?
这也许是因为,人们经验arche的领域已发生根本的转换了:
如果说在古希腊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们主要是在人类制造活动的领域中来经验arche;
那么在中世纪——这里首先是中世纪——人们则主要是在一个已经被创造出来的世界的等级秩序中来经验arche。
这是一个有着鲜明等级秩序的被造世界。
秩序如何可能?
秩序来自原则:
持久的原则制造了秩序,[27]而且统治着秩序。
在古希腊那里,arche是变易的原因;
而在中世纪这里,principium则是秩序的原因。
“Arche—变易”模式被“principium—秩序”模式取代了。
在这个“原则-秩序”模式中,时间被遗忘了,生动的变易过程凝动了,Arche中的肇始、发端的含义也为统治、主宰含义所取代了。
Arche纯粹成了一个国王、一个统治者。
“为了把思辨的目光凝固于作为纯粹的regnat、作为由一个‘国王’所拥有的支配与统治的本原上,它丧失了把本原视为开始、视为诞生事件的洞见”。
[28]
到近代,自笛卡儿与莱布尼兹之后,arche依然被理解为原则,但是,它已不再是一个秩序的原则,而是一个论证的的原则:
“原则就是一个论证的起点、本原。
”[29]因为对于一个近代的理性主义者来说,“具有优先性的领域”既不是人类的制造活动,也不是那个秩序井然的被造世界,而“是命题与它们的合法性的领域。
”[30]于是在莱布尼兹看来,本原就是一个陈述,一个表达在语词中的法则,一个断言,莱布尼兹称之为“公理”。
“公理”源自何处?
最终是由心灵设置:
“原则是由心灵设置的某种东西。
”[31]于是人,而不是中世纪的“神圣实体”——上帝,在近代成了最后的原则。
至此,从古希腊以来,人们在经历了到自然中、到上帝那里寻找最终的arche之后,最后终于回到人自身这里来寻找arche。
“人是最后一个起源的领域,是最后的可能的本源领域”,于是至此,从自然到上帝,再从上帝到人,形而上学的所有资源都被穷尽了。
[32]当然,这里的人,充当着最后原则的人,并不是一个经验的人,而是一个先验自我。
先验自我通过它的反思行为,通过它的意识,把它自身构造为客观存在的最终的原则和本原。
[33]这样一个先验自我,从笛卡儿、莱布尼兹开始,经过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一直到二十世纪的胡塞尔,最终由一个逻辑证明的原则,演变成了一个存在论的原则:
一切存在者最终都是作为意向行为的相关项而被作为构造活动的知觉和意向性行为构造起来。
这样一种立足于先验自我的主体性原则,最终成了整个近代的时代原则。
至此,古典形而上学对最终arche的寻找终于走完了它应走以及能走的历程。
V.没有他者与未来的本原
arche,从作为肇始与统治相结合的本原,到作为原因的本原,再到作为原则的本原——在这一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它的最源初的肇始、发端的意义越来越弱,而它的主宰、统治、支配的意义则越来越强。
于是,它之由肇始而逐渐成为原因以及最终成为原则的历史,也就是它逐渐变为原则进行统治、支配的历史。
而作为制造秩序并对世-界进行宰制、支配的原则,本原在这一历程中也就逐渐获得了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作为原则的本原,arche自身超出时间之外,永恒在场,无生无灭。
柏拉图的理念如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亦如是,后世一切本原几乎都如是。
比如在亚氏那里,arche作为第一因,被理解为纯粹的在场,它同时既是本原又是目的,一切变易、生成都由它肇始并向它而去,而它自身却作为纯形式不生不灭永恒在场。
及至中世纪乃至近代,作为原则的本原,无论是以神圣实体之名,还是以先验自我之名,其自身都超出时间之外并统治一切。
乃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不例外,虽然它的完满实现必须要通过进入时间、进入历史,但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重演”,因为在这之“前”它“早”以以概念的形式在理念中、在思维王国中实现自身。
这样一种超时间的原则/本原,由于它的永恒在场,它便把一切时间都预先锁闭于它自身,收拢于它自身,如同如来佛的手掌,而时间不过是在它之中跳跃的悟空。
于是,这种作为原则的本原,就成了一种没有未来的本原,没有那种作为绝对未来因而不能回溯到现在的未来的本原。
其次,作为原则的本原,它唯我独尊,排斥异己,排斥他者,永远维持自身同一。
无论是作为神圣实体的上帝,还是作为先验自我,还是作为绝对精神,原则、至高神都只能是一个。
“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34]——这不仅是犹太教的基本教义,也是整个西方思想的基本教义。
它的哲学表达就是:
除我这个原则/本原外,你不能有其他原则/本原。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唯一神的信条。
总是寻找唯一的神,唯一的原则/本原。
甚至重点还不在这寻找,而在这寻找之前的对唯一原则的信念本身。
正是由于对这唯一的原则/本原的信念,西方人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勒维纳斯后来极力要解构、要打破的整体。
这是一个封闭的整体,没有他者、也不能容忍他者的整体,任何他者、异者都要必须被同化、吸收进这个整体之中。
因为这个整体在其本原处、本原处、原则处、根据处,一句话,在其arche处,就是唯一的,就不能容忍他异、差异的存在,就不能容忍有通往他者和外部的开口。
最后,这个作为原则/本原的arche,总已经是一个现成化的arche。
它自身的发生、生成,它自身之如何可能,自亚里士多德甚至从柏拉图以来就一直没有得到追问,被追问的始终是它究竟是什么。
从柏拉图的理念到亚里士多德的作为纯形式、纯粹在场的神,到中世纪的神圣实体,一直到近代的作为先验自我的主体,所有这些曾经的原则/本原都只是一些现成化的“什么”,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都只是一些存在者。
但是正是这样一些现成化的“存在者”,却成了最终的、最后的、最高的原则,乃至“原则的原则”。
这个最高原则亘古不变,统治一切。
它是衡量一切善恶、是非、美丑、进步反动、对错的最后的准绳。
即使到今天,人们仍在寻找这最后的诸原则的原则,在各个领域里:
政治、伦理、经济、宗教等等。
人们到处在寻找着所谓的“金科玉律”,所谓的“普世原理”。
人们争相宣称自己发现了这最后的原则,并因此以自己为正义的化身、真理的化身。
但是,并没有人怀疑这个原则本身究竟是否真的现成存在。
于是,人的不断出离自身、绽出自身的生存、不断当下涌现着、缘起着的活生生的生存,那不可主题化、不可现成化的生存,乃至涌现着、缘起着、源起着的的世界,在最后竟都被一个现成的存在者——某一个作为原则/本原的arche——主宰着、统治着,衡量着、判断着。
于是生活、生存、世界、时间,从根本上就被封闭了、窒息了,未来因此在本原处就已被封死了,他者从起点上就被抹去了。
这是一种没有绝对未来意义上之未来的生活-世界。
这种在本原处对未来和不可同化的他者的抹消,是一种本源的暴力,原暴力。
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火刑,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都是要从根本上、从起点上、从本原上抹消作为绝对他异性的他者,以维护一个唯一的、纯粹的本原-源头-根据-原则。
现在让我们回到德里达,看德里达如何解构这种传统的本原形而上学或传统形而上学的本原观。
二、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本原观的解构及其伦理意义
I.德里达对传统本原形而上学的解构
完满无缺、自身同一、唯我独尊,既是本原又是目的,不生不灭,永恒在场,是衡量、裁判、统治一切是非、美丑、善恶、进步反动的终极根据、原则和统治者——这就是传统本原形而上学对本原的理解。
德里达的解构所要针对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对本原的传统理解,以及以此种本原观为基础的传统形而上学。
然而,德里达究竟如何解构?
如果要想深入具体地了解这种解构究竟是如何进行的,那就必须去诸个重构德里达的解构个案:
对柏拉图的解构,对亚里士多德的解构,对黑格尔的解构,对胡塞尔的解构,对海德格尔,对索绪尔的解构,对塞尔的解构,对弗洛伊德的解构,等等。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此我们只能满足于从整体上对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作一些提示,尽管这些提示不可避免地因此是粗略的。
策略之一:
本原的替补化
虽然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替补就已经得到某种思考;
[35]早在卢梭,替补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替补”之真正成为一个哲学话题或一个问题,是自德里达始。
但一说起德里达对“替补”的思考,人们往往立刻把它与一种文学批评联系起来——这也难怪,德里达讨论替补的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是他在《论文字学》中对卢梭的《忏悔录》中所涉“替补”现象的解读,而《忏悔录》又往往被看成是一部文学作品。
我们这里姑且不说,对文学的解读同样可以是哲学的;
我们只需指出一点,德里达不仅在《论文字学》里谈到了替补,而且在《声音与现象》中同样谈到了替补——但这一点却往往被忽视了,即使是在讨论《声音与现象》的文本中。
然而,恰恰是在《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关于替补之思考的哲学意义才比较纯粹的显现出来。
我们强调这种思考的哲学意义,是因为在那里,德里达明确地是把替补与本原联系在一起来谈,而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说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是关于本原的思考。
《声音与现象》集中讨论“替补”问题的是第七章:
该书的最后一章,标题是“本原的替补”。
如我们前文所说,这样安排并非偶然,它恰恰透露出了德里达的用心所在:
《声音与现象》正是对传统哲学的本原问题的解构,更具体地到这最后一章,乃是对传统形而上学之本原/替补结构的解构。
何谓本原/替补结构?
它是传统形而上学对本原与替补之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解:
替补总是某种本原之替补,或对本原的替补。
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