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docx
《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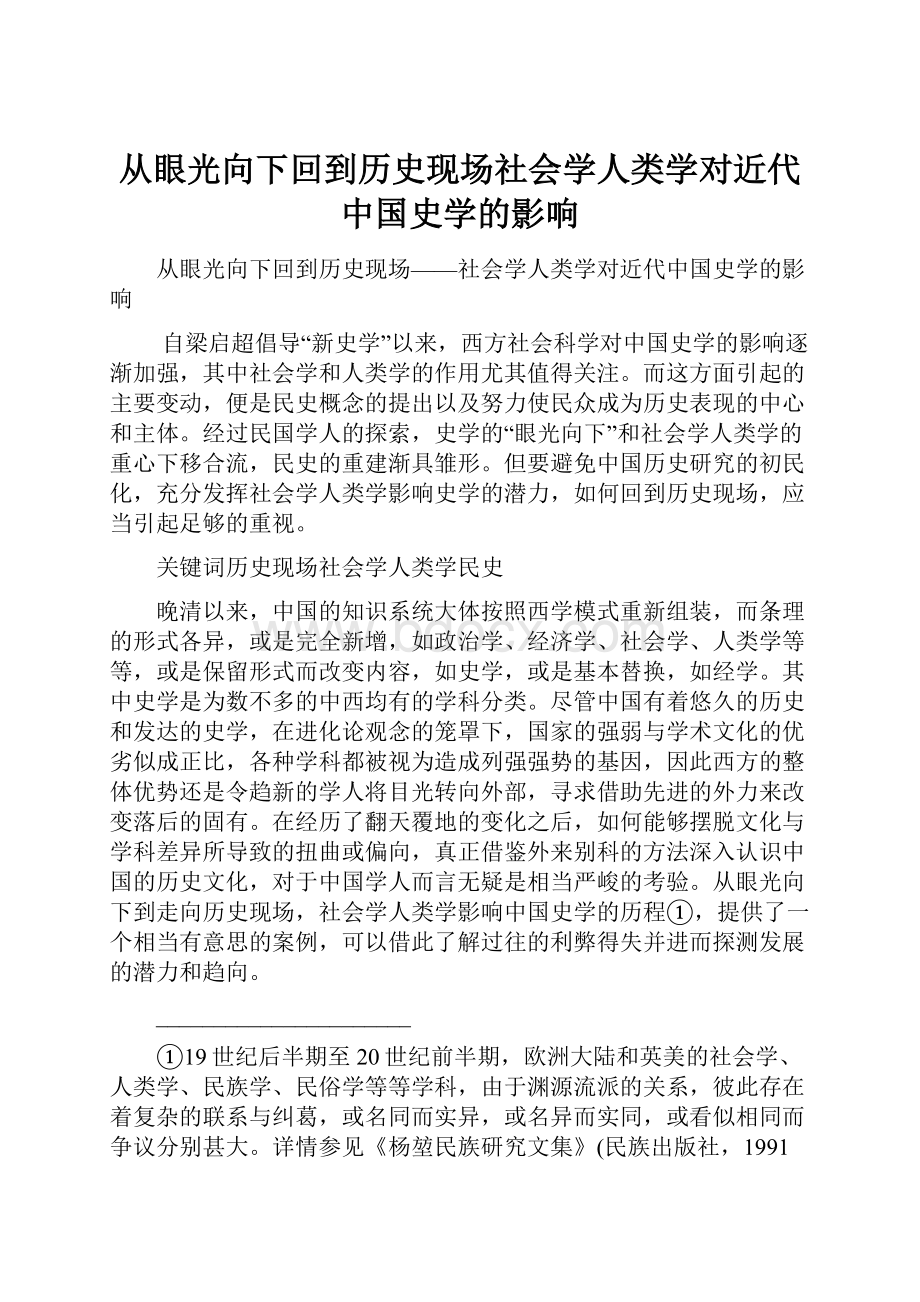
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逐渐加强,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
而这方面引起的主要变动,便是民史概念的提出以及努力使民众成为历史表现的中心和主体。
经过民国学人的探索,史学的“眼光向下”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民史的重建渐具雏形。
但要避免中国历史研究的初民化,充分发挥社会学人类学影响史学的潜力,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民史
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系统大体按照西学模式重新组装,而条理的形式各异,或是完全新增,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或是保留形式而改变内容,如史学,或是基本替换,如经学。
其中史学是为数不多的中西均有的学科分类。
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史学,在进化论观念的笼罩下,国家的强弱与学术文化的优劣似成正比,各种学科都被视为造成列强强势的基因,因此西方的整体优势还是令趋新的学人将目光转向外部,寻求借助先进的外力来改变落后的固有。
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如何能够摆脱文化与学科差异所导致的扭曲或偏向,真正借鉴外来别科的方法深入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无疑是相当严峻的考验。
从眼光向下到走向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影响中国史学的历程①,提供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案例,可以借此了解过往的利弊得失并进而探测发展的潜力和趋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欧洲大陆和英美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学科,由于渊源流派的关系,彼此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与纠葛,或名同而实异,或名异而实同,或看似相同而争议分别甚大。
详情参见《杨堃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和《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所收录的有关各文。
而考古学的归属,同样因地而异。
一、创新史学
讲到近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大都会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开端。
虽然不能说西方的各种学术分科至此才开始影响中国的史学,梁启超的确用进化论框架树立起一个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的概念模式。
除了学界前贤已经讨论过的各种问题外,“新史学”明显是用学术分科的眼光来看待中西史学的差别以及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梁启超开篇就指出: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在批评从前史家之弊时,又强调其中之一,是“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
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
因为历史是要通过“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各种相关学科均为主观所当凭借,“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①
《新史学》发表于1902年,而梁启超关注泰西的分科治学早在前一世纪末。
戊戌政变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集中阅读了大批日文书籍,尤其是日本翻译的各种西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
所得“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
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②所以大声疾呼有志新学者学习日本文。
梁启超的上述表述,很可能是为了强调学习日文的好处,却容易造成其到日本之后才知道西学分科的错觉。
实际上,他在国内时已经接触到西学的分类。
1897年康有为编辑《日本书目志》,付梓前梁启超曾经阅读,并撰文为之鼓吹。
他认为:
“泰西于各学以数百年考之,以数十国学士讲之,以功牌科第激励之,其室户堂门,条秩精详,而冥冥入微矣。
吾中国今乃始舍而自讲之,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也。
”为了追赶泰西,梁启超主张以日本为媒介,因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
”③与后来的《论学习日本文之益》相比,只有通过翻译与直接学习语言的差别,而借道日本,则如出一辙。
梁启超虽然提出要“创新史学”,关注的重心其实并不在学术本身,而是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其时梁启超改信国家主义,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然则但患其国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
”④梁启超重视泰西的各种学科,目的首先也在于改造社会。
所以他批评此前治西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忽略更具本原性的政学,并希望农夫学农学书,工人读美术书,商贾读商业学,士人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君后读明治维新书,以强国保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梁启超: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页。
②梁启超:
《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0—81页。
③《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2—54页。
④梁启超: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
关于《新史学》与晚清政治思想界的关系,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5—196页。
不过,梁启超重视史学,仍有其学术上的考虑。
在他看来,“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
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怅怅然不解其云何。
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务通彻数千年来列国重要之事实,文明之进步,知其原因及其结果,然后讨论诸学,乃有所凭借。
不然者,是犹无基址而欲起楼台,虽劳而无功矣。
”①而历史虽然与各种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关系密切,还是有轻重之别和缓急之分。
梁启超主张创新史学,原因是他对旧史学极为不满,批评旧史学有四大病源,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而最为关键的,还在历史究竟以少数人为中心,还是以多数人为关照。
“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
”历史固然是英雄的舞台,但“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
”而中国历代史书,不过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
“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
”②
梁启超重视群体,是从进化论的观念出发,“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
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然则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人历史之范围也。
”中国作史者,“不知史之界说限于群”,③人物传记于人群大势毫无关联。
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史之界说”。
他说: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
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
近世史家,必探家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以此为据,梁启超甚至断言“中国前者未尝有史”,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有史无史的争论。
按照梁启超的标准,中国不仅没有史学,甚至连史料也相当缺乏.“今者欲著中国史,非惟无成书之可沿袭,即搜求材料于古籍之中,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
”④
如何改变上述状况?
梁启超已经有所注意,在《东籍月旦》评介市村瓒次郎等人的《支那史》时,他特意指出该书“稍注意于民间文明之进步,亦中国旧著中所无也”⑤。
不过,梁启超更主要的还是寻求其他学科的援助。
从新史学后来的发展看,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考古学,二是社会学。
《中国史叙论》第七节“有史以前之时代”论及黄帝以前的远古历史,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必须依靠其他学科的发展所提供的人类共例。
梁启超了解到,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下遗物,于是史前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订定而公认史前分为三期,即石刀期、铜刀期和铁刀期。
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二期。
“此进化之一定阶级也,虽其各期之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见,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
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有史前之史,决不为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页。
②梁启超: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页。
③梁启超: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10页。
④《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2页。
⑤《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9页。
除了借助于考古学,梁启超还从社会学所总结出来的人群公例,推断中国远古社会的发展状况。
当时社会学的一般原理认为,“凡各人群,必须经过三种之一定时期,然后能成一庞大固结之团体。
第一为各人独立,有事则举酋长之时期;第二为豪族执政,上则选置君主,下则指挥人民之时期;第三为中央集权,渐渐巩固,君主一人专裁庶政之时期。
”①一群之中,自然划分三类,一为最多数之附属团体,将来变成人民之胚胎;二为少数之领袖团体,将来变成豪族之胚胎;三则最少数之执行事务委员,将来变成君主之胚胎。
三类人逐渐分离,权力也由民主而封建,最后进到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
梁启超着重介绍考古学和社会学,只是针对史前社会,而且主要是借助浮田和民翻译的《史学通论》、《西洋上古史》等书②,也许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些学科后来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冲击。
不过,这些学科在欧洲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许多方面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学科之间的分界受历史渊源的制约,相互纠葛,错综复杂,对于研究人类历史的影响力正在逐渐释放的过程之中。
梁启超显然和当时新进的中国知识人共同感觉到这些学科的不同凡响。
此外,梁启超还以进化论的观念将这些学科依据其他人群的研究所揭示的若干规则视为人类社会的通则,断言“此历代万国之公例”必然适合于中国,而研究缺乏甚至完全没有文献记录的上古社会,与研究同样缺乏文献记录的下层群体历史有着某种共性,这种共性预示着可以将研究远古社会的方法移植到对社会民众历史的研究方面。
梁启超创新史学的呼吁激起了不同的反响.尽管对于他“中国无史”的过激之论颇有争议,但是关于重视历史的中国历来缺少群体性民史的看法,却引起普遍的共鸣。
《新世界学报》、《政艺通报》以至后来的《国粹学报》、《东方杂志》,陆续刊发了不少文章,讨论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问题,无论是主张无史还是坚持有史,都“同意‘历史’应该是国史,是民史,是一大群人的历史,是社会的历史,同时历史叙述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解放出来,而以宗教史、艺术史、民俗史、学术史作为它的主体”③。
清季知识人的当务之急是社会政治变革,至于学术方面,因应时势的需要,这时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大都翻译模仿日本各书而来,其中自然也吸取了新的成分。
尽管新进学人普遍同意应当以民史为主,但如何才能修出民史,认识并不一致。
有人主张“修史必自方志始,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者耳”④。
刘师培则认为后来的方志不足以供国史之采择,因而要另行编辑乡土志。
⑤总体而言,清季知识人在创新史学方面各自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新编各史较旧史确有很大改观。
不过,仔细分别,他们的努力更多的体现在利用历史教育民众方面,即开民智鼓民气,也就是章太炎所说“贵乎通史”的两个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
⑥至于如何表现民的历史,既无成果,又缺史料,不知如何下手。
因此主要还是借鉴泰西和日本史学的体例,改变旧史以政治史为中心,以王朝世系为线索的格局,从典章制度等方面观察社会面相和进化因果,而未能真正深入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生活的层面,做到以民为历史的中心加以展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9—10页。
②石川祯浩:
《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06页。
③王汎森: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93页。
④《方志》,《新世界学报》第7期(1902年11月30日)。
⑤《编辑乡土志序例》,《国粹学报》第2年第9期(1906年10月6日)。
⑥《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67页。
后来进京师大学堂任史学教习的陈黻宸,对于民史的缺乏和撰写的困难感受深刻而具体。
他虽然感叹“今之谈史学者辄谓中国无史之言之过当”,所编《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读史总论》开宗明义,“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
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是故史学者,乃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
”他认为分门别类的历史,只是史家之分法,“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
”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陈黻宸有如下表述:
“非社会不足以成政治,非政治不足以奖社会。
政治之衰败者,断不容于社会文明之世。
社会之萎落者,即无望有政治振起之期。
社会兴于下,政治达于上。
有无限社会之权力,而生无限政治之举动。
有无限政治之举动,而益以表明无限社会之精神。
转辗相因,其果乃见。
”政治决定于社会,“故言史学者,必以能辨社会学为要。
”
据此来看中国的现实,学者“往往识足以动天地无尽之奧,而不足以知民俗之原,辨足以凿浑沌七窍之灵,而不足以证闾里之事。
”而欧美各强国,“于民间一切利病,有调查之册,有统计之史,知之必详,言之必悉,如星之罗,如棋之布,如数家人米盐,厘然不遗铢黍。
彼其所以行于政治者,无一不于社会中求之。
而我国之社会,究不知其何如矣.总之,社会学之不明,则我中国学者之深诟大耻也。
以是言史,夫何敢!
”虽然陈黻宸称许“力学有识之士,发愤著书,往往有得于父老之传述,裨乘之记闻,大率支离烦琐,为荐绅先生所不言。
采其遗文,加之编辑,反足激发性情,人人肝肺,东西南北,类聚群分,歌泣有灵,按图可索,言史学者不能无意于社会学矣”,却不得不承认“且我中国之史之有关于社会者甚少矣.今试发名山之旧藏,抽金匮之秘籍,与学者童而习之,屈指伸而论其大概,亦若条流毕具,秩然可观,然不过粗识故事,无与纲要。
即择之稍精,而有见于古今治乱盛衰之故矣,然于其国之治之盛,不过曰其君也明,其臣也贤,于其国之乱之衰,不过曰其君也昏,其臣也庸。
于此而求实事于民间,援輶轩之故典,亦徒苦其考据无资,虽华颠钜儒,不足以识其一二。
故无论人之不知有社会学也,即令知之,而亦心不能言,言之而亦必不能尽,尽之而亦必不能无憾于浩渺杳冥,泛然如乘不系之舟,莫穷其所自之,而社会学乃真不可言矣。
”①他本人所编撰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在民史方面也很难有所建树。
清季是中西学乾坤颠倒的时期,趋新学人宁可附会西学,很少敢于提出异议。
与梁启超一样,在文献记载不到之处,同时期的学人也将目光转向泰西新起的学科,考古学便是社会学之外他们公认可以补远古历史不足的重要领域。
刘师培认为,欲考古政,厥有三端,即书籍、文字、器物,尽管他心目中的考古学主要还是金石器物,毕竟对地下发掘寄予希望,惋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
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
”②章太炎也表示:
“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
亦有草昧初起,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
”③
清季学人的无奈,显示出他们向往的民史并非简单地可以借助西学条理系统而成形。
如果没有后来学人的努力,民史大都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正如今人所指出的,这时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至于“如何研究历史”,则是民国以后学人的任务。
至少从主流派的眼界看去,民史的建立是如此展开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675—681页。
②《古政原始论》,《刘申叔遗书》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64页。
刘师培曾撰文《论考古学莫备于金石》,掘地的目的也是获得遗物。
近代中国人对于考古学的理解,长期受固有学问的制约,与欧美不尽相同,主要关注在于考订古器、考订解读文字和以器物文字考订古史(尤其是文献可征的古史)方面。
详情另文论述。
③《訄书》重订本《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1页。
二、眼光向下
重在民史和寄望掘地,都可以说是“眼光向下”的表现。
民国学人创新史学的努力,仍然沿袭前贤指示的路径。
这与其说是清季学人的眼光敏锐,毋宁说是时代的潮流和趋势。
不过,民国时期史学的建树,开始是包含在门类甚多、取径不一的整理国故之中,而整理国故最初由胡适的用西方系统条理中国材料和提倡科学方法抢了风头。
胡适对于民史的开发似乎不够热心,加上不满于经济决定论有过于武断之嫌,使其对于唯物史观相当怀疑,也是明确表示过不能苟同唯物史观的少数学人之一。
稍后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引起一场关于中国旧籍与上古历史的讨论,主要取向还是继续胡适的理念,要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史料。
因此一度民史的建立似有被忽视甚至被遗忘之嫌。
1926年初,魏建功撰写了《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对顾颉刚、钱玄同、柳诒徵等人关于古史的争论发表意见,虽然他站在顾、钱的一边,对柳诒徵的观点和态度不以为然,但他的结论却超越了争论的主题,重提民史建树的方向。
他说:
我的结论:
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历史,现在还没有。
所谓‘正史’,的确只是些史料。
这些史料需要一番彻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紧将历来的乌烟瘴气的旧心理消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
新历史的系统是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历史的长度要依史料真实的年限决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长的君主的朝代为起讫;历史材料要把传说、神话、记载、实物……一切东西审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结果,客观的叙述出来。
如此,我们倒不必斤斤的在这个旧心理磅礴的人群里为新史料的整理伴他们吵嘴,把重大工作停顿了!
①
魏建功批评“国故”能叫人钻不出头,与顾颉刚的看法不尽相同。
他的意见,显然是希望后者跳出“国故”的纠葛,回到社会学和考古学所指示的眼光向下的轨道上去。
其实,在这方面,顾颉刚与胡适的看法也有所分别。
师生二人都重视国学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具体而言,则侧重不同。
胡适认为(或者至少同意):
“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
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
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
”因此他所设定的总系统是一部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等10项专史的中国文化史。
②这虽然可以说几乎等于一部通史,却并不着重于民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1926年1月27日).
②《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顾颉刚的看法在所撰《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辞》中有明确表述:
“国学是什么?
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乍看上去,这与胡适的意思并无太大区别,不过顾颉刚是在回答近来常有人说“我们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因为国学是腐败的,它是葬送青年生命的陷阱”的批评时做这番表述的,他强调“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
可是就在这一年,胡适面对陈源等人的批评,却部分改变了原来对整理国故的看法。
1919年,胡适在回答毛子水关于整理国故益处不大,世界上许多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议论时说:
“学问是平等的。
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①而这时胡适却“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呼吁青年离开国学这条死路,去走科学的生路。
②这也是1928年至1929年后师徒二人渐行渐远的潜因之一。
此事后来两人都主要从疑古和信古的分别来理解,其实深究起来,应该还有另外一面。
顾颉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辞》,首先是针对社会上对于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表示出来的偏见。
1925年12月,北京大学举行27周年校庆纪念会,国学门开放供人参观,参观者先到考古陈列室,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再到明清史料陈列室,也感到诏谕的尊严,最后到风俗和歌谣陈列室,很多人则表示轻蔑的态度。
顾颉刚认为:
“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艺儿而轻蔑它。
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
”③
顾颉刚虽然强调材料的平等,毕竟受个人训练的约束,对于考古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的研究古史计划,只是准备研究古器物学,而未及真正的考古发掘。
胡适、傅斯年等人在这方面比他要彻底。
胡适在赞同顾颉刚疑古之初,即主张先把古史缩短两三千年,“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④对此顾颉刚没有正面回应。
他无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但他立志首先要“破坏伪古史的系统”。
⑤所以当李宗桐提出研究古史载记不足征信,“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时⑥,顾颉刚同意这是极正当的方法,应当极端注重发掘,却还是认为其论断“颇有过尊遗作而轻视载记的趋向”。
他的理由是,“无史时代的历史,我们要知道它,固然载记没有一点用处;但在有史时代,它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弥补它们单调的缺憾。
我们只要郑重用它,它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
”⑦
顾颉刚的意见涉及考古学与中国史料的关系,相当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他已认为“经籍器物上的整理,只是形式上的整理;至于要研究古史的内部,要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便须应用民俗学了。
”他并且坦承:
“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
”⑧由于当时所讨论的古史,大都在商周以降的有史时代,顾颉刚实际上更加注重载记。
只是他力图摆脱经学正统对于古史的解释,决心致力于“
(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
(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论国故学》,《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②《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1926年7月)。
③顾颉刚:
《一九二六年始刊辞》,《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④《自述古史观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