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淑敏小说艺术特色.docx
《论毕淑敏小说艺术特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毕淑敏小说艺术特色.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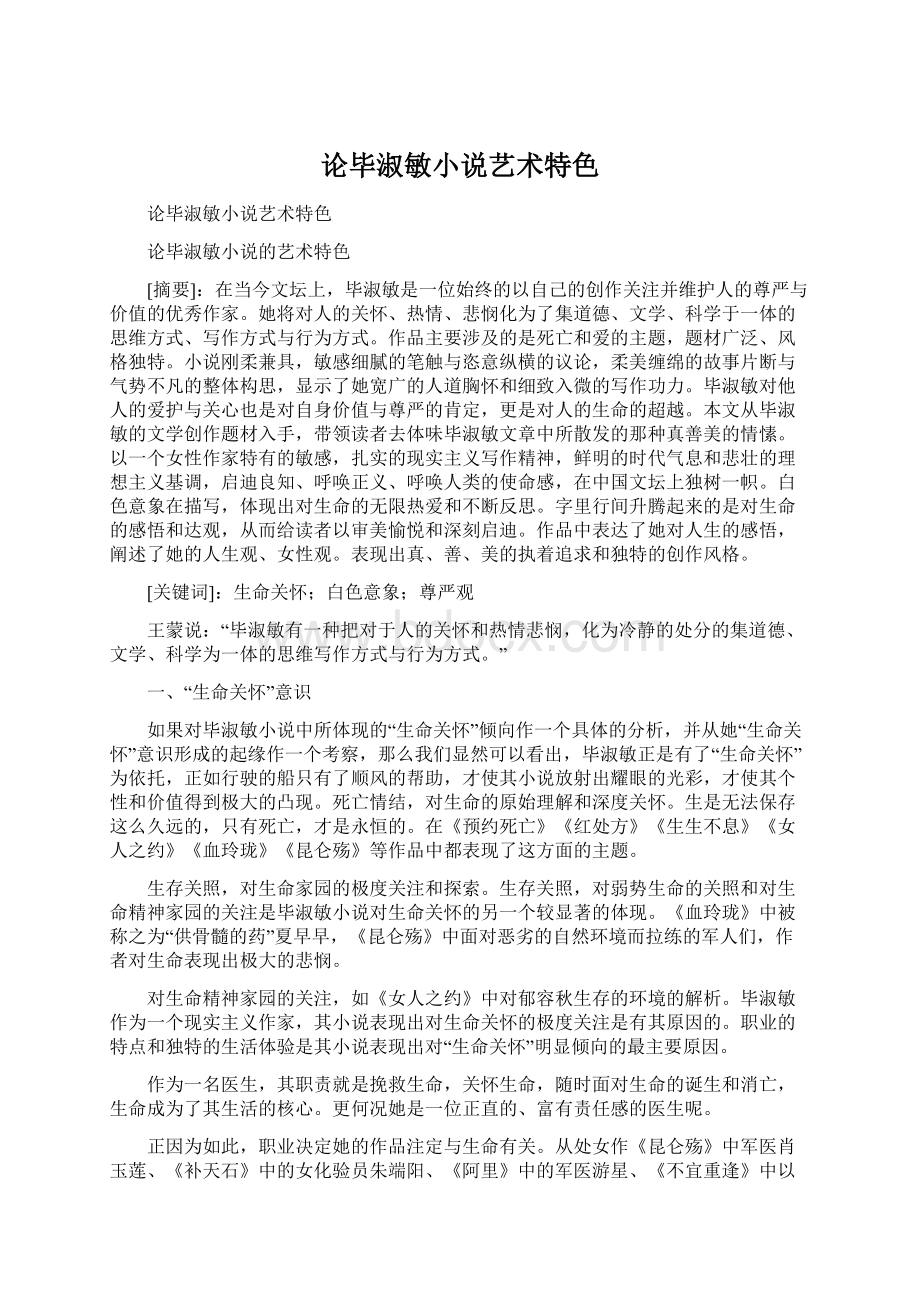
论毕淑敏小说艺术特色
论毕淑敏小说艺术特色
论毕淑敏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
在当今文坛上,毕淑敏是一位始终的以自己的创作关注并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优秀作家。
她将对人的关怀、热情、悲悯化为了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作品主要涉及的是死亡和爱的主题,题材广泛、风格独特。
小说刚柔兼具,敏感细腻的笔触与恣意纵横的议论,柔美缠绵的故事片断与气势不凡的整体构思,显示了她宽广的人道胸怀和细致入微的写作功力。
毕淑敏对他人的爱护与关心也是对自身价值与尊严的肯定,更是对人的生命的超越。
本文从毕淑敏的文学创作题材入手,带领读者去体味毕淑敏文章中所散发的那种真善美的情愫。
以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扎实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悲壮的理想主义基调,启迪良知、呼唤正义、呼唤人类的使命感,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
白色意象在描写,体现出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和不断反思。
字里行间升腾起来的是对生命的感悟和达观,从而给读者以审美愉悦和深刻启迪。
作品中表达了她对人生的感悟,阐述了她的人生观、女性观。
表现出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
生命关怀;白色意象;尊严观
王蒙说:
“毕淑敏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分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为一体的思维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
一、“生命关怀”意识
如果对毕淑敏小说中所体现的“生命关怀”倾向作一个具体的分析,并从她“生命关怀”意识形成的起缘作一个考察,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看出,毕淑敏正是有了“生命关怀”为依托,正如行驶的船只有了顺风的帮助,才使其小说放射出耀眼的光彩,才使其个性和价值得到极大的凸现。
死亡情结,对生命的原始理解和深度关怀。
生是无法保存这么久远的,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
在《预约死亡》《红处方》《生生不息》《女人之约》《血玲珑》《昆仑殇》等作品中都表现了这方面的主题。
生存关照,对生命家园的极度关注和探索。
生存关照,对弱势生命的关照和对生命精神家园的关注是毕淑敏小说对生命关怀的另一个较显著的体现。
《血玲珑》中被称之为“供骨髓的药”夏早早,《昆仑殇》中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拉练的军人们,作者对生命表现出极大的悲悯。
对生命精神家园的关注,如《女人之约》中对郁容秋生存的环境的解析。
毕淑敏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表现出对生命关怀的极度关注是有其原因的。
职业的特点和独特的生活体验是其小说表现出对“生命关怀”明显倾向的最主要原因。
作为一名医生,其职责就是挽救生命,关怀生命,随时面对生命的诞生和消亡,生命成为了其生活的核心。
更何况她是一位正直的、富有责任感的医生呢。
正因为如此,职业决定她的作品注定与生命有关。
从处女作《昆仑殇》中军医肖玉莲、《补天石》中的女化验员朱端阳、《阿里》中的军医游星、《不宜重逢》中以前是军医后来成了作家的秦苏模,到后来《预约死亡》中的齐大夫、《生生不已》中的袁大夫、《预约财富》中的毕刀,再到长篇处女作《红处方》中简方宁、以及《血玲珑》中的魏晓日,无不与军人或是医生的职业有关。
从上面分析可知,毕淑敏小说之所以这么关注生命,与她的职业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
生命关怀,毕淑敏个性和价值的凸现。
当我们把视角对准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这一点时,毕淑敏才显出她在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的独特个性和存在价值。
甚至可以说,当我们在考察她小说中的人文关怀时,可以说,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是其人文关怀的核心。
毕淑敏以其独特的方式构筑了一个“生命关怀”的艺术世界,我们只有把握这个贯穿其整个小说创作的“脉络”,才能真正深刻感受到其小说的巨大魅力。
使其小说既不纯粹是“新写实”,也不是“私人写作”亦或“身体写作”,既不全是“新体验小说”和“军旅小说”,也不是“文化关怀小说”,毕淑敏就是毕淑敏,如果硬要给她归为哪一派,那么,从其作品来看,我想“生命关怀小说”是比较妥帖的。
而这正是她独特个性的体现和她在文坛价值的最好体现。
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无论是悲壮的死还是苟且的活,作者都倾注了她那具有独特内涵的对人的终极关怀。
毕淑敏对于人的深层关怀,已经从政治的道德的层面深入到对生命现象的揭示,又从个性之爱深入到了人类的大同之爱。
二、毕淑敏作品中的白色意象
白色意象,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和不断反思。
做过20多年医生的毕淑敏总喜欢与白色结缘,笔下有白衣、白口罩、白帽,有白雪、白花、白发、白粉,这些白色意象倾注了作者对生命的理解和诠释,闪烁着作者对生命的关爱和思索。
作为一个16岁就开始了医务工作生涯、有20多年医务工作经验的女作家,在她眼里,她把医务人员用的白衣、白口罩、白帽等与朴实无华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白色美而不妖,露出隐隐的寒意,从象征的意味上安抚了人类焦躁的心灵。
”“做医生的,就该终生穿着白的工作服,永远一尘不染。
每逢钻进白衣,就进入了一个特定的角色,需忘我,需认真,需冷静如水,需严谨如丝丝入扣的卡尺。
”毕淑敏在《红处方》和《血玲珑》里,就多次提到过白衣、白口罩、白帽等,无论是简方宁身上的白衣,还是魏晓日的白口罩、白帽,都寄托了作者对生命灵魂亦或是生命本身拯救的情思。
从1987年至今,毕淑敏创作的小说中,大多数作品都涉及到与白衣、白口罩和白帽有关的卫生员或护士或医生,也涉及了白茫茫的藏北高原。
藏北高原的积雪以及在高寒、缺氧中献给失去年轻生命的白花,给了我们更多对生命的理解。
在漫长的冬季,藏北高原厚厚的积雪,诉说了一个又一个圣洁的灵魂在风雪中悲壮而去的故事,《昆仑殇》中在为了实现某些人个人的意志的拉练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失在苍茫的白雪高原上,这里,作者通过郑伟良对拉练的怀疑和一号最后反思,表现对生命的极度关怀:
郑伟良已经闸不住了,思路如江河直下:
“况且,象这样肩冰衔草式的原始行军方式,自身的供给尚无法保障,又能有多少战斗力呢?
它只能模糊人们对现代化战争的认识,以为有了精神就能打胜仗。
其实,战争的物质性是异常直接的。
吃苦不是目的,只是一种达到胜利的手段。
我敢说,如果红军有毛皮鞋,他们绝不会穿草鞋去翻越夹金山。
抛却了这个实质,反而津津乐道于复制苦难本身,不正违背了先辈们的意愿吗?
红军正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受苦,自身才去受非人的磨砺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追求苦难而忽略军人生命的价值,正是对传统的背叛。
”
郑伟良对一号的“攻击”,就当时情况而言,是对司令的背叛亦或是对“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的挑战,所以,纵是死了,司令也不能原谅“攻击”他的个人意志的郑伟良,让他和肖玉莲死后都不能相爱在一起,但正是通过他表达了作者对军人生命的格外珍重,是一种对生命的极度关怀。
作品结尾处有这么一段文字:
墓坑,就是--那些数字?
它们从指挥员的统计表上走下来,在这暗淡的黑夜变得如此狰狞可怖,张着巨大的口将吞噬进那些年轻的生命。
一号孤零零地站在墓地,感到难以自制的悲哀。
不要登报,不要升迁,不要和呢军帽比高低,只求这高耸的土丘填回去,让地面重新冻结得像钢铁一样坚硬……
在这里,通过一号的反思,表现出作者明显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关怀意识。
显然,作者是力图通过积雪上关于生命消亡和灵魂的拷问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终极关注,“白雪”作为一个意象,它涵盖了作者当时对生命的价值的全部理解。
白花,这里是花圈的代名词。
《冰雪花卉》里,白花,作为一个独特的意象。
这些白色意象,呈现了作者长年生活的“白色”环境里,昭示了作者对生命的酷爱,对生命的礼赞,对生命的顶礼膜拜。
三、毕淑敏作品中体现出的尊严观
人人都要有尊严,那么,个人尊严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
这是毕淑敏在创作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有的人以身价显赫、地位高贵来作为尊严的资本,有的人企图用金钱来买到自己的尊严,而从不在自身内在修养上下功夫。
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是最可贵的,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只有人才追求生命的意义,才如此看重精神世界的价值,毕淑敏作品中所体现的尊严观的价值,恰恰是在弘扬人的精神追求的同时,注意到了对尊严观赖以存在的基础,既生命的关照。
“自尊,便是自己尊重自己,只要自己不倒,别人可以把你按倒在地上,却不能阻止你满面尘灰遍体伤痕地站起来。
”《女人之约》中的郁容秋,极度渴望尊严,由于生活上的一度做法不检点,而被人戏称为“大篷车”,得不到人们的尊重。
为了重新获得尊严,在工厂被“三角债”套牢面临困境,大家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她主动请缨,使用种种手段,终于将工厂的债权讨回。
对此功劳,她唯一企求的报酬是希望厂长能够当着全长职工的面给自己鞠上一躬,还她以尊严。
在这里,郁容秋对尊严的理解注重的是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注重社会对自己的评价。
但这样的自尊,只能是企求而不是真正的自尊,她也不懂得真正的自尊,她竭力想要别人一句好话而不能如愿,那么她的悲剧结局和可怜之处就显得易见了。
毕淑敏塑造的这个渴望尊严而不得的人物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思索。
可以肯定毕淑敏在创作中执着地、深切地关注人的尊严这一问题。
尊严对人如此重要,那么尊严的实质在毕淑敏的作品中究竟是什么呢?
夸耀概括为两点:
第一:
尊严是有别于物质享受的精神满足,它不是对金钱物质之类初级层次的需求。
第二:
尊严注重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评判,注重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美的自尊,人格的尊严和力量才是真正的尊严。
在今天,当尊严与生命发生冲突的时候,现代人会做出理性的评价。
这或许正是毕淑敏的文学创作别具深意的地方。
四、毕淑敏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待死亡的态度
死亡是人生的归宿,无言的结局。
死亡又是人生的终极辉煌,最后的升华。
谁也逃不脱一死,“万岁”是不可能的。
死亡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命形态,它折射着生命的悲凉与无奈,作为与生存密切相关的人生问题,死亡又寄予着人类对生的种种态度。
意识到死,才能自觉的生存。
因此,一个对死亡过分敏感的作家也必然会对生存有超乎寻常的执着。
事实上,毕淑敏始终对生的探讨,她恰恰是以对死亡的彻底逼近,来表达着对生命的感悟。
尤其是她把人物设置到特殊的背景中,让他们面对死亡的种种纠缠和折磨,来展示生命的诞生、挣扎、毁灭的动态过程,并用勇敢达观的态度思索人的存在问题。
在生与死形态展示的背后,流淌着毕淑敏对生命存在的诗情向往、对生存意义的永恒追问。
个体生命的生老病死是悲哀的,特别是当死亡的残酷与生命的美好构成强烈冲突时,人生本身浓烈的悲剧意味就不言自明了。
毕淑敏是个敏感而细腻的人,她总是能从平凡琐碎的世事中洞察人生的不幸与尴尬,进而探求生存的终极意义。
《生生不已》就是一篇极富哲理意蕴的小说。
女工乔先竹在与关大夫的闲谈中得知女儿患上了脑肿瘤,于是,这一对平凡的夫妇全力以赴抢夺女儿,却始终因医治无效而失败,在经受丧女之痛的打击后,乔先竹消耗着自己快要枯竭的身躯,重新孕育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凄婉的故事,除了生动感人的描写之外,更深的意义在于触及到了一个颇具哲理的主题——生命的循环不已。
无死自然生,无生也必然无死。
生和死在本源上是一体两面的存在。
我们承认死亡使得生命更为匆忙、短暂。
然而,死亡并不是虚无,而是显示生命的标志。
人之生命象自然之循环一样,周而复始,在完成了死亡时又重新开始又一环新生。
就象是乔先竹一面体验着死亡的步步逼近,一面也同样感受着自己对新生命的孕育过程,新生儿的到来无疑代表着生命进程的不断延续。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毕淑敏道出了关于生与死的人生的哲学意味。
其实生命从它诞生时起,就受到来自生命内部和外部两种力量的牵拉,这种力量既可促进生命的成长,又会造成对生命的威胁,《昆仑殇》就隐喻了生命的这种存在方式。
作者将故事的背景放在极左的年代,一个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生命,不实事求是的病症恶性流行的年代,牺牲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被神圣了,明知前进是死,却不能不进,因为后退就意味着终生也抹不去的屈辱。
生命受到来自外部的戕害性力量的干扰,而人只有顺从。
于是我们看到这一幕:
在海拔五千公尺的高原永冻地带,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国军人正在徒步行走。
他们给养极差,没有必要的御寒设备,甚至还被人为地造成饥饿。
而进行这次原始行军仅仅是因为“一号”与“呢军帽”争高低!
仅仅是“一号”想在军区制造一个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