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当官与做学问Word格式.docx
《漫谈当官与做学问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漫谈当官与做学问Word格式.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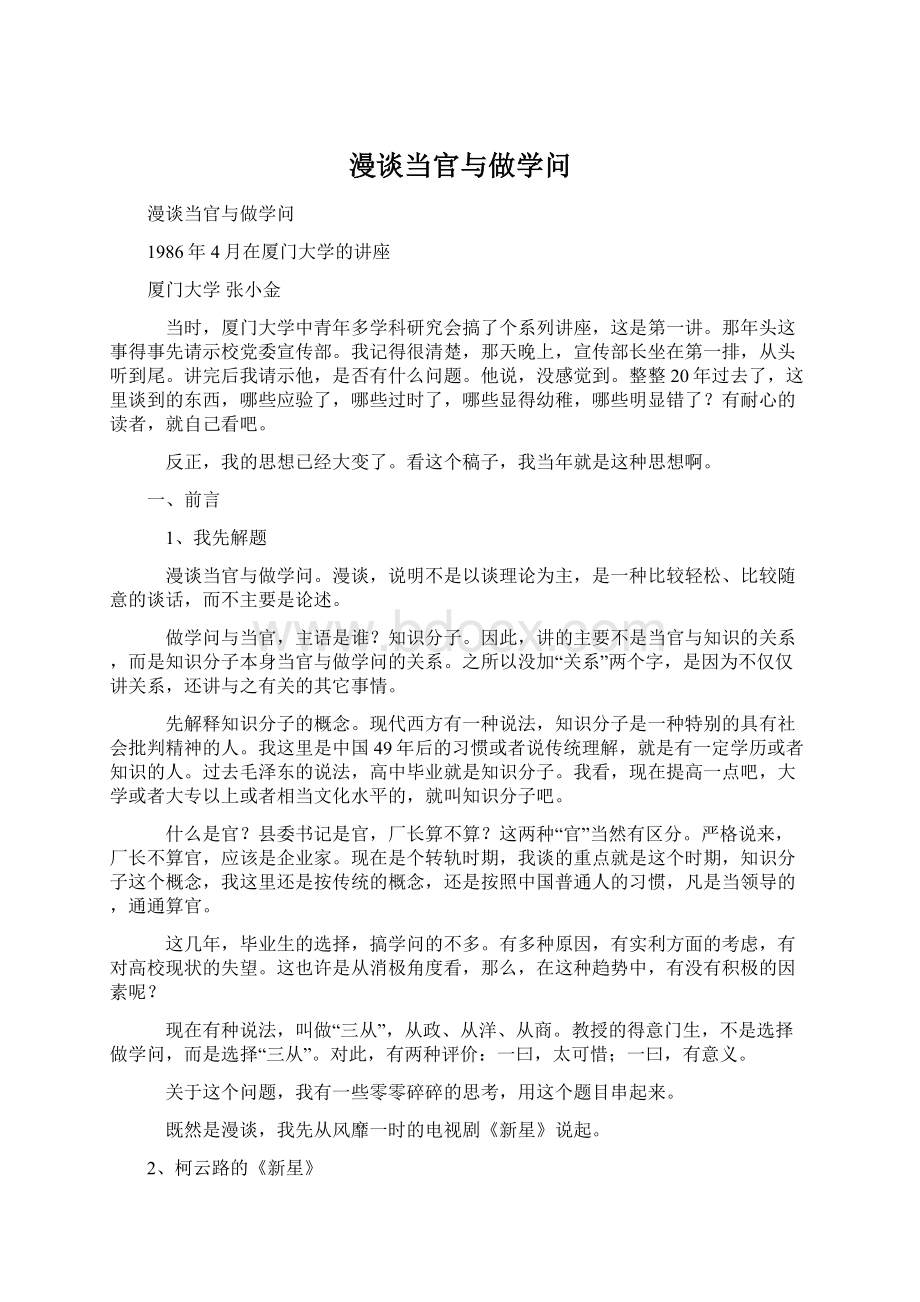
教授的得意门生,不是选择做学问,而是选择“三从”。
对此,有两种评价:
一曰,太可惜;
一曰,有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思考,用这个题目串起来。
既然是漫谈,我先从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新星》说起。
2、柯云路的《新星》
小说就引起了大的轰动,许多报刊发表了评论,在北京召开了大型座谈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短期内收到了大量听众来信。
但所有这些媒体的作用,都不能与电视相比。
《新星》电视剧播放引起的轰动是空前的。
电视剧的播放使得小说销售一空,出版社赶快加印。
全国有80多家电视台播放,上海电视台,还有其他几个台,重播了2遍。
许多电视台,比如中央台和太原台,收到大批来信,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将军也投书报刊。
有个地委书记把《新星》的录像带拿到会议上放,看录像成了开会的内容。
文学的社会功能、社会反应,如此广泛,激烈,是中外罕见的。
小说写的是一个县的改革斗争,但却写出了整个中国目前改革的全景。
改革为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不能迟缓?
小说写出了改革潮流目前所处的战略态势以及将要往哪个方向发展。
连夏衍看了,也觉得这部作品写得相当大胆。
它像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今天才开始构思的,但它却在今天已经问世了。
作者在政治上的勇气和预见性,是值得钦佩的。
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开拓深刻,有新意,有艺术魅力的作品;
是一部敢于直面现实,近距离地全景式地反映改革生活的、有强烈时代气息和历史感的成功之作。
柯云路自己说,企图通过众多的不同层次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来凝铸当代社会生活图画。
他说,改革只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我们并不是为改革开药方的。
柯云路是我所熟悉的一位青年作家。
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三千万”,一举夺得80年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
他的第二篇重要作品《耿耿难眠》,获得当代文学奖,这是他和他的妻子罗雪珂共同写作的。
雪珂的《女人的力量》,小说和电影都获奖。
在《当代》杂志的颁奖会上,他们说过一句话,“我们始终没有写出来我们思索达到的东西”。
可以说,这一点,在《新星》中部分达到了。
《新星》是82年开始构思的。
81年冬天,我在他们家住了3天,我们三个人讨论了许多的问题。
那三天我们整天聊天,其他什么也不干。
那次谈话的许多内容,甚至我讲的一些小故事,后来都在他的一些小说中有反映。
那时候,他们的中篇小说《历史将证明》刚出笼。
这部小说是以批判白桦的《苦恋》为背景的。
历史将证明什么呢?
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如果说在那部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官”的关系,还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那么在《新星》中,知识分子本身已经当官了。
《新星》的主题当然不是当官与做学问,但是李向南这样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当官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改革勇气和能力,给人启迪。
李向南算不算知识分子,算,他当官本来就是所谓干部知识化的产物。
但他身上有一些新东西,是传统知识分子没有的。
李向南有知识,有理想,有思想,雄辩,同时,他还有经历,有眼光,懂实际,懂权谋,干练,有开拓精神。
他是干部结构转型、知识分子社会功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
我原来想借这样一部影响大的文艺作品来谈这个问题,所以在最早定题目时,我就有这个打算,副标题就是“从《新星》谈起”。
但是有两个原因,使我遗憾的放弃了这个打算。
一个,最近一直很忙,没有时间来重读这部长篇小说;
另外,我给柯云路和罗雪珂写了一封信,想请他们写几个字支持一下我们的讲座,结果到今天也没等到回信。
虽然放弃了这个线索,但我今天还会不时地提到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当然,我只能凭一点记忆。
放弃这个线索之后,我找了另一个线索,这就是一篇有影响的文章。
当官与做学问成反比吗
——邓伟志的文章:
“淡化当官心理”
我所尊敬的一位社会学家邓伟志,最近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淡化当官心理”。
他对这个问题作了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有价值的意见,也引起了广泛反响。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学问与做官成反比。
就是一个公式:
学问=K/当官。
从这个结论,他提出了一个对策,一个口号。
就是:
淡化当官心理。
现在要问的是,这个公式,这个口号,准确吗?
全面吗?
适时吗?
这个公式至少有点小缺点。
定性定量都有点不到位。
首先概念没定性,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官,从质的方面没有明确规定性;
也没有准确的量化,作者这里用了“模糊数学”一词,显得有些滑稽。
在这种理解下,学问尚好理解,学问的大小,成果的多少和水平的高低等等;
而当官,是理解为官的大小,还是当官时间的长、短,也就是要问,官当得越大,学问就越受影响,还是当官时间越长,学问越作不来呢?
也许二者兼有?
自变量至少是二元的。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不用数学语言,不用公式。
就取它的意思好了。
总之,当官对做学问有负作用。
邓文从社会和个人两方面来论证当官与做学问的反比关系。
首先,从全社会来说,想当官的人多了,做学问的人就少了
第二、从个人说,二者成反比例,当官影响做学问。
我们先分析第一条。
实际上它建立在两个假定之上:
第一、知识分子仅仅由当官和做学问这两个部分人组成;
第二、知识分子的总数不变。
否则,当官的多了,做学问的不一定减少,同样可以随之增加。
同理,当官的少了,做学问的也不一定增加。
这两个假定,在当代中国并不成立。
因此,从全社会来说,当官与做学问成反比的结论,尚缺乏可信的推理。
再看第二条。
应当承认,这个公式并非没有道理。
邓伟志作了一些论证。
他作了一个调查,当然,调查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中国人向来主张“盖棺定论”。
人没死,不能把话说死,学问到底有多大?
从个人说,当官与做学问成反比关系的公式,邓文是借助一个简单统计,即通过对收入《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中姓马的人物的统计,得出结论的。
他查了《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人物中,姓“马”的最多,有26人。
其中:
没当官,或只当过三、五年小文官的---20人;
当过官,但著作不在当官时写的---3人;
一直当官,且有学术成就的——3人;
可见,不当官而出学术成就的是多数,既当官又出学术成就的是少数。
23:
3嘛,结论出来了。
总而言之,当官是影响做学问的,因此,知识分子不要想当官。
知识分子中想当官的人多了不好,提倡淡化这种心理。
这个推理有没有一点道理,能不能够说明问题?
这个统计和推理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仔细考察也还有些问题。
先说资料的准确性。
这大概不用怀疑。
我没有复查,我觉得不必,公开见报争鸣,应该不会有假;
一共才26,两位数加法,也不会有计算有误。
从方法本身来看。
首先要问的是,样本是独立事件吗?
样本的随机性如何?
“马氏谱系”样本的随机性如何,与我们一般要考察的当官与做学问的知识分子是否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呢?
这并非不证自明之事。
从社会科学辞典中,抽出姓马的,不能说是随机的;
而且样本太少了,如果再找一些样本,姓刘的、姓张的…,能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呢?
严格说来,这不是统计而只是举例,因此,只能是一种说明而不是证明。
我那天随手取一本《唐宋词选注》,上选的词家,唐朝19人,其中2人未做过官,占10%;
宋朝92人,未做官的26人(含情况不详者)占28%,二种情况,当过官的都是大多数。
那么,我能否据此就做出结论:
做文学家与当官并不成反比呢?
也不能。
从方法角度说,对“马氏”社会科学家的这种统计和对唐宋词家的统计,都不足以得出当官与做学问关系的结论。
其次,这里当过四、五年小官,以及当过官但著作不在当官时写的人,他们当官与日后的才能、学问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这也是个必须先证明的问题。
当然,所有这些挑剔都还不很严重。
如果把当官看作一种职业,把学者看作另一种职业,而学者的职能就是做学问,那么当官与做学问的排斥关系好象就很简单,很显然了。
其实,在这种理解上,岂只当官与做学问成反比,做其它许多工作,例如,当企业家、金融家、外交家,军事家等等,不都与做学问成反比吗?
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一连串反比例函数,或者干脆把公式改为:
从事非学者职业与学问成反比,就是:
学问=K/从事非学者职业
如果我们把当官看作一种实践活动,那么与这种实践活动有关的学问,是不是也一定成反比呢?
当总统当然会影响从事物理学研究,所以爱因斯坦不愿当以色列总统。
但是,当总统的“学问”是否也与当总统的时间成反比呢?
当一个阿波罗登月工程总指挥,也许会影响他对于基础科学的研究,甚至影响他对于工程技术、火箭技术的,电子技术的研究,但对于管理指挥一个大的科研工程、航天工程这样的“学问,这成反比还是成正比呢?
有些人不把那当学问。
在他们的视野里,学问只是书斋里搞出来的那些东西,甚至只是故纸堆里的东西。
这里牵涉到对“学问”的看法。
在某些人看来,有关“当官”的“学问”不算学问,属于左道旁门。
其实这里边学问很深。
谁说作总统没学问,做总统可要学问了。
毛泽东说过,梅兰芳能演戏,可不能当总统。
此话一点不假,梅兰芳能当总统吗?
没那学问。
我们现在知道,当总统,当一个科研工程总指挥,是要有学问的。
从事这种实践,对搞这类学问是不成反比的。
前者是做领导的学问,后者是管理的学问,都是做官的学问。
在中国古代,就把这叫做统治术。
统治术是不是一门学问?
古代没有专门研究。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历来有两件事,只能干,不能说的。
一直做着,可是不能说,更不能说研究。
说是犯忌的。
一个是房中术。
张贤亮最近有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起轩然大波。
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他写了那个犯忌的事情。
还一个呢,就是统治术。
中国历代帝王官僚,历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还有野心家、权术家,都有统治术。
里面有价值的东西不少,只不过没有给予总结,使之上升为理论。
但我说,如果研究领导科学,那里面还是有不少可借鉴的。
我们现在有了更好听的现代名称,当然内容也更科学。
现在有两门科学,一门叫领导学,或者领导科学,一门叫管理科学。
这是现代关于当“官”的学问。
与之有关的还有一大批科学,比如认识科学,决策科学,系统科学、人才学,社会学,组织心理学,等等。
对于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之类,笼统说当官与做学问成反比,恐怕根据不足。
常常有这种人,他们在去官时做出的学问,内容和水平都来源于他们当官时的实践。
就说《新星》中的李向南吧。
李向南有没有做领导的学问?
尽管只有30几岁,但领导才能、政治成熟度令人佩服。
李向南当了县委书记,对他认识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对他研究统治术,领导科学,没有帮助吗?
只成反比吗?
在新星的末尾,李向南对康乐说,要去当一个政治学术家,为改革的人提供战略思想、方案、理论、决策。
他有没有资格?
有。
这个资格首先就在于他当县委书记的实践,否则他能研究得出来吗,能写得出来吗?
他当县委书记的实践对他做这种学问难道只有反作用吗?
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他做这种学问的条件和优势所在。
这种所谓统治术,政治权术,在《新星》里有个名词,叫做政治智慧。
有个评轮家说,无论叫政治智慧还是政治权术,这种色彩在李向南身上实在是太浓厚了。
他怀疑,对于无产阶级的理想主义的斗争,李向南对于政治手腕的玩弄是否过分了。
我想,这可能是一种书生气。
我认为,这正是表现他的政治智慧的特别突出的内容。
确实,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革命的政治,似乎应当是一种更为光明磊落的政治。
但从作者所揭示的现实政治斗争场景来说,斗争的主要对手是老谋深算又有社会基础的政客,这种色彩或者素质就是李向南这样的改革者所必备的。
如果说,柯云路在《三千万》中写出了社会各阶层存在的复杂的关系网,那么,《新星》则写出了产生这种关系网的历史淤积层——一个在古老的历史淤积层上生发出来的新的历史淤积层。
我年少时也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完全应当是公开表现和公开宣传的那样的。
现在我明白了,当年我太幼稚。
我记得,81年在榆次时,我们三人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两位主人似乎有点分歧,或者说差异吧。
这一点差异,也反映在《新星》和《女人的力量》之中。
后者是罗雪珂独立的作品。
那里面有个说法,男人富于逻辑力量,女人富于直觉;
男人是科学型的头脑,女人是艺术型头脑。
这可能是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
当我们读着小说中犬牙交错绵里藏针的命运搏斗的场面,我们的感觉能与李向南相比吗?
不能,完全不能!
一个人,当他处在这个位子和不处在这个位子时,客观外界,对象系统对于他的各种作用,反映,激发……是很不相同的。
还是那句老话,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听别人说梨子的滋味是不行的。
81年那次柯云路对我说,他坐了一年牢,体会了许多在正常情况下没法体会到的事情,认识了许多在正常情况下认识不到的道理。
要谈最具有这方面才能的,我看还是毛泽东。
要论当“官”的学问,很少有能超过毛泽东的。
无论人们怎样评论他,也不能不承认他多方面的学问,包括当领导的学问。
他当了大半辈子的一把手,谁能说他当“官”的经历与他的学问只成反比呢?
也许有人以为他并没有什么学问,他晚年的作为,总括一些与他并不直接相关的人所做的事,还有一些别的历史原因,使年轻一代人中的某些人,对他怀着一种不屑一顾的心理。
把他当作神当然是不对的,但走向另一极端似乎也太浅薄。
我个人认为,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所能产生的最杰出人物之一。
我强调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土壤这个词,这是为配合“最杰出”这个形容词。
我说这话可能要得罪今天不少听众。
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一个诗人,一个书法家,特别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在他生活的时代,是无以伦比,是可以和国内任何一个名家媲美的。
在国外学者所列出的本世纪社会科学62项重大成果中,就有他的农民与游击战争理论。
在这个题目上,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他的领导学。
你去翻翻“毛选”四卷,看看他指挥解放战争的才能。
翻翻“毛选”五卷,看看他领导新中国初期时处理各种复杂局面的才能,你一定会心生钦佩之情。
人们说到他晚年的错误时,说他犯了一种老年痴呆症。
我想,尽管到他生命的晚期,有一种用脑过度的迹象,但他的领导艺术,还是表现出一种境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胡乔木说过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宗教和陷井。
这是说他文化-革命理论的错误。
但他在为达到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目的时,他在掌握最高领导处理各种复杂局面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比如粉碎林彪政变的种种的处置,比如对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等等,仍然让人感到一种不可企及的高超的政治才干。
有人把这叫做辩证法大师的水平,有人说这仅仅是玩弄权术。
玩权术是个贬义词,在我们党内,确有这类人,但把所有政治斗争仅仅看成玩弄权术,也有片面性。
扯远了。
上面我们对邓文提出的公式作了许多挑剔,并非要否定当官对作学问的干扰和影响。
只想指出他不够全面之处。
我的观点是,这个公式虽不完全准确,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这是这个社会落后的表现。
不仅要淡化知识分子,而且要淡化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思想。
而要改变这种官本位,向现代社会过渡,喊一个淡化的口号不解决大问题。
其次,在这个过渡时期,当前要鼓励一些适合当官的知识分子当官,这对全社会有好处。
邓伟志从当官与做学问互相排斥的公式,就提出要淡化当官心理的号召。
为什么当官影响做学问,知识分子就不要当官呢?
我认为这个推理还省略了一个大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前提,这个前提就反映了一种价值观。
知识分子是干什么来的,他的唯一理想,最高理想,他的唯一社会功能,或者主要社会功能,他对社会的唯一贡献、最大贡献,就是做学问吗?
只有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才能作出进一步推理。
只有首先肯定,知识分子的唯一的,最高的社会功能就是做学问,才能推理说,当官影响做学问,所以不要当官,或者说,什么影响做学问就别干什么。
否则,你影响好了,有什么关系?
这就转入第二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
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
知识分子做学问,当然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
但这是知识分子唯一的社会功能吗?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那种“秀才”形象。
而在许多知识分子自己的心理中,似乎做学问也是他的唯一正业,正道。
我们先来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
他们是干什么的,发挥什么作用。
邓伟志说,正因为当官与做学问有冲突,所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众多文人不当官。
他并且为此举了五种不同类型的例子。
因为当官与做学问有冲突,所以文人们就不要当官了,这意味什么呢?
这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做学问是古代知识分子最高的人生理想。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什么因素影响做学问,就放弃什么,就排除什么,宁愿不做官也不影响做学问。
是不是这样呢?
事实上,这种人固然有,但相反的例子更多。
我们已经说过,举例子是容易的,它能说明而不能证明。
列宁早就说过,为了要证明任何观点,都可以找到例子的。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影响最大。
孔孟经典被历代文人视若圣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文人士大夫的座右铭和口头禅。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当然也做学问,但主流的儒家知识分子是积极入世的。
他们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的”的。
纯学术的风气是到近代才起来的。
马克思的名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从西方来说,从希腊以来的哲学,其传统确实是以解释世界为主题。
因为逻辑学、知识论成为哲学的主流;
但中国,特别是儒家思想,从某种程度说,却不是重在“解释”而是重在“改变”世界(这并非中国知识分子高于西方之处,这里暂且不论)。
儒家型知识分子在社会危机的时期,总是用他们的“道”来“拨乱反正”,“纲纪世界”,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治国、平天下的”的理想抱负,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管理的功能。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管理功能,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一方面,为管理社会提供一种规范。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以“礼教”来维持的。
谁提供这种“礼教”,谁来执教,怎样传下来,怎样化开去,这都是古代土阶层即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功能。
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一些做学问性质的工作,但那是与以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为目的的那样一路做学问大相径庭的事。
古代社会是“礼治”社会,礼治社会少不了卫道士,卫道士就是士阶层。
士为社会提供礼数。
社教虽然吃人,但提供了一种秩序。
中国封建社会,金观涛说它是个趋稳定系统(结构)。
为什么它能长期保持稳定结构?
其中儒家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这种礼数,广义说一种文化,是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知识分子作为主体去参与社会管理。
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重要社会功能。
这种管理功能,也可以从二个方面考察。
最直接的当然就是做官,在朝做官的知识分子充当皇权的工具,执行着管理国家的功能。
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都是普遍现象。
另外,大批在野的士,即乡绅,在社会管理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越是下层,越是边远的地方,官吏越难控制到基层,而在野的乡绅正好补足了这个欠缺。
乡绅指那些科举出身,已经退任或休闲在乡里的绅士,大多身兼地主或与地主关系密切,即既具经济势力,又因与外界政治势力密切,文化优势更不待说了。
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大多数人根子仍扎在故里。
所谓衣锦还乡嘛,这是很多人的理想。
总之,中国古代社会能够产生令人惊异的井然秩序(固然是保守的)和稳定结构,能把高度一体化的行政管理和道德伦理贯彻深入到全国上下,原因不一而足,但依赖于一个广泛分布于朝野城乡的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去提供社会规范和从事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管理,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古代知识分子发挥社会管理的功能,是使中国封建社会成为超稳定系统的重要原因。
最早为知识分子完成上述社会功能提供理论基础的,是孟子的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其中虽然暴露出阶级的偏见和历史的局限,但还是反映了对脑力劳动特征的认识,也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社会管理功能的某种有价值的认识。
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看,知识分子是想当官的。
因为要实现这个理想,就要走当官的路(且不说个人的社会地位,待遇)。
因此,历代知识分子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竞相挤入仕途。
不要说把做学问作为唯一理想,就是当作最高理想,也不会是多数人的心愿。
为了做学问,就不要当官,这种人不多。
往往是,官作不成了,才去做学问。
这才是事实,这顺序不能颠倒。
就拿李白来说吧。
李白是公认的伟大诗人。
如果没有李白,整个中国诗坛都要为之减色。
尽管如此,但他的志向本来并非在此。
政治上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这才是他的抱负。
李白两次从政,一败如洗。
从历史的辩证法来说,这个失败无论对李白还是对中国文学史,都是一大幸事。
它阻止了李白向一个政治家的努力,成就了他成为一个大诗人的命运。
但是,我们还是很清楚,李白并不是因为做学问这个最高理想才不做官的,并不是因为当官与做学问成反比才不做官的。
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文学家做官受挫,或辞官或被罢官,在文学上做出成绩,在这一点上与李白大同小异。
应当指出的是,当官的一段实践,无论是对于他们认识统治阶级内部情况,还是认识整个社会,都不是没有裨益的。
对于他们的思想和才干,都有重要影响。
而且,一般都不是因为当官对做学问有影响,才不当官的。
因此,说古代文人为了做学问而不去当官,决非普遍现象。
崇尚做学问,“不屑为官”的心理,古代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也有过,但成为一种在知识界有巨大影响的社会心理,则是近代以来的事。
清代考据风气盛起,使做学问的路子转向;
另外,近代以来西方纯学术之风传来,为知识而知识的风气,加上知识分子自视清高,不求做官的风气浓起来;
清末政治腐败,以后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