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钱钟书读《拉奥孔》Word下载.docx
《52钱钟书读《拉奥孔》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52钱钟书读《拉奥孔》Word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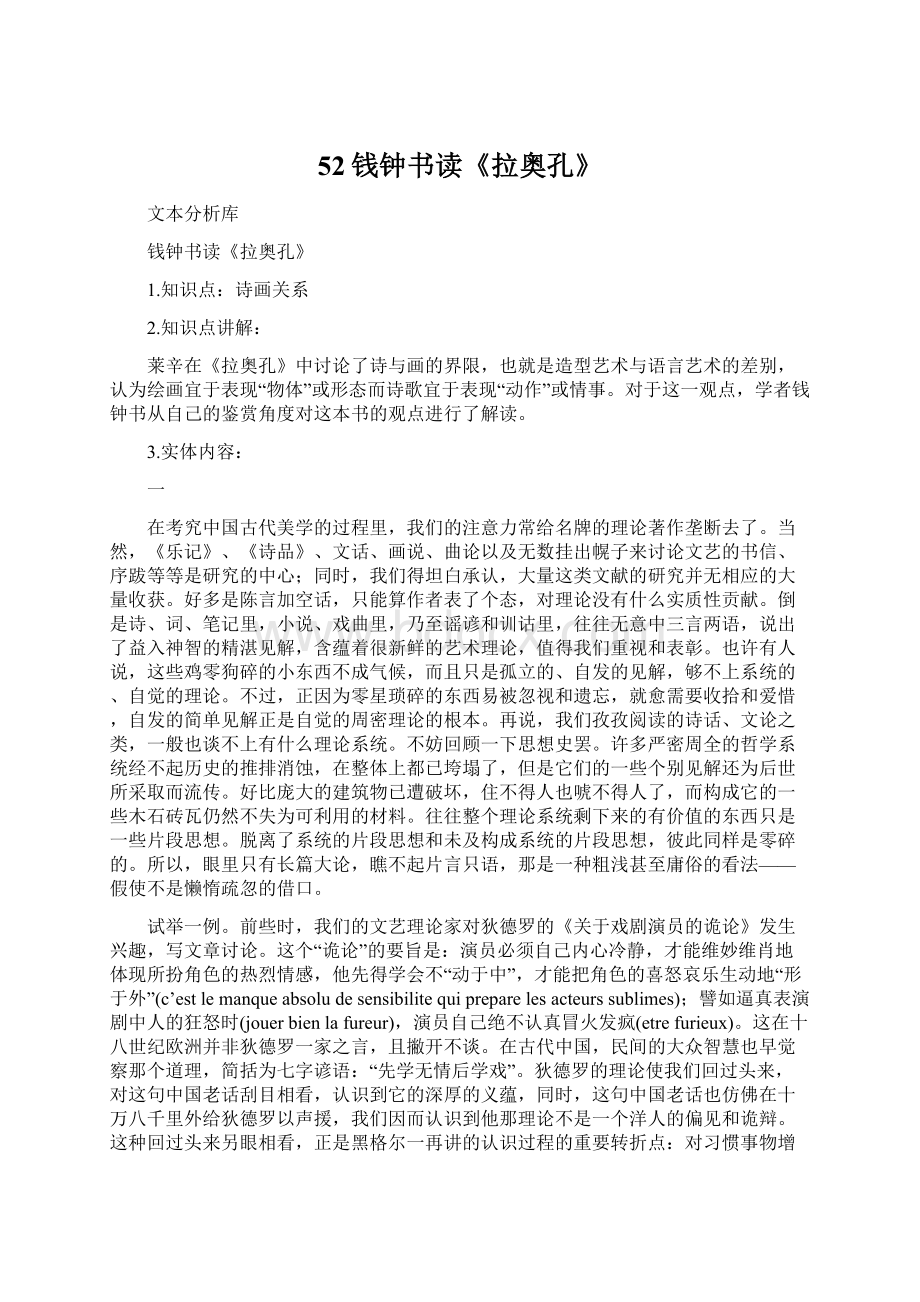
演员必须自己内心冷静,才能维妙维肖地体现所扮角色的热烈情感,他先得学会不“动于中”,才能把角色的喜怒哀乐生动地“形于外”(c’estlemanqueabsoludesensibilitequipreparelesacteurssublimes);
譬如逼真表演剧中人的狂怒时(jouerbienlafureur),演员自己绝不认真冒火发疯(etrefurieux)。
这在十八世纪欧洲并非狄德罗一家之言,且撇开不谈。
在古代中国,民间的大众智慧也早觉察那个道理,简括为七字谚语:
“先学无情后学戏”。
狄德罗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对这句中国老话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深厚的义蕴,同时,这句中国老话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给狄德罗以声援,我们因而认识到他那理论不是一个洋人的偏见和诡辩。
这种回过头来另眼相看,正是黑格尔一再讲的认识过程的重要转折点:
对习惯事物增进了理解,由“识”(bekannt)转而为“知”(erkannt),从老相识进而为新或真相知。
我们敢说,作为理论上的发现,那句俗语并不下于狄德罗的文章。
我读莱辛《拉奥孔》的时候,也起了一些类似上面所讲的感想。
二
《拉奥孔》里所讲绘画或造型艺术和诗歌或文字艺术在功能上的区别,已成套语常谈了。
它的主要论点——绘画宜于表现“物体”(Korper)或形态而诗歌宜于表现“动作”(Handlungen)或情事——中国古人也浮泛地讲到。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就引陆机有关“丹青”和“雅颂”分界的话:
“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
”邵雍《伊川击壤集》卷一八里两首诗说得详细些:
“史笔善记事,画笔善状物,状物与记事,二者各得一”(《史画吟》),“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诗画吟》)。
但是,莱辛不仅把“事”、“情”和“物”、“形”分别开来,他还进一步把两者和时间与空间各自结合;
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雕塑只能表现最小限度的时间,所画出、塑出的不可能超过一刹那内的物态和景象(niemehralseineneinzigenAugenblick),绘画更是这一刹那内景物的一面观(nurauseinemeinzigenGesichtspunkte)。
我们因此联想起唐代的传说。
《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引《国史补》:
“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
‘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
’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卷二一四引《卢氏杂说》记“别画者”看“壁画音声”一则大同小异)。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批驳了这个无稽之谈:
“此好奇者为之,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从那简单一句话里,可见他对一刹那景象的一面观的道理已稍微觉察。
“止能画一声”五个字也帮助我们了解一首唐诗。
徐凝《观钓台画图》:
“一水寂寥青霭合,两崖崔翠白云残,画人心到啼猿破,欲作三声出树难”,“三声”当然出于《宜都山水记》:
“行者歌之日:
‘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艺文类聚》卷九五引)。
诗意是:
画家挖空心思,终画不出“三声’连续的猿啼,因为他“止能画一声”。
徐凝很可以写:
“欲作悲鸣出树难”,那只等于说图画仅能绘形而不能“绘声”。
他写“三声”,此中颇有文章,就是莱辛所谓绘画只表达空间里的乎列(nebeneinander),不表达时间上的后继(nacheinander),所以画“一水”、“两崖”易,画“一”加“两”为“三”的连续“三声”难。
《拉奥孔》里的分析使我们回过头来,对徐凝那首绝句、沈括那条笔记刮目相看。
一向徐凝只以《庐山瀑布》诗两句传名,也许将来中国美学史会带上他的姓名的。
西方学者和理论家对《拉奥孔》的考订和辩难,此地无须涉及。
这本书论诗着眼在写景状物,论画着眼在描绘故事,我也把自己读它时的随感,分为两个部分。
三
诗中有画而又非画所能表达,中国古人常讲。
举几个有意思的例。
苏轼《东坡题跋》卷三《书参寥论杜诗》记参寥说:
“‘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
’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尔!
”陈著《本堂集》卷四四《代跋汪文卿梅画词》:
“梅之至难状者,莫如‘疏影’,而于‘暗香’来往尤难也。
岂直难而已?
竟不可!
逋仙得于心,手不能状,乃形之言。
”张岱《琅擐文集》卷三《与包严介》:
“如李青莲《静夜思》诗: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故乡’有何可画?
王摩诘《山路》诗:
‘蓝田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尚可入画,‘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则如何入画?
又《香积寺》诗: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泉声’、‘危石’、‘日色’、‘青松’皆可描摹,而‘咽’字、‘冷’字决难画出。
故诗以空灵,才为妙诗;
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屑也。
”值得注意的是,画家自己也感到这个困难。
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之一五: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世说新语.巧艺》第二一:
“顾长康道:
‘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董其昌《容台集。
别集》卷四:
“水作罗浮磬,山鸣于阗钟’,此太白诗,何必右丞诗中画也?
画中欲收钟磬不可得!
”(按非李白句,乃僧灵一《静林精舍》诗)。
程正揆《青溪遗稿》卷二四《题画》记载和董的谈话,“‘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华亭爱诵此语,曰:
‘说得出,画不就。
’予曰:
‘画也画得就,只不象诗。
’华亭大笑。
然耶否耶?
”
莱辛认为一篇“诗歌的画”(einpoetischesGemalde),不能转化为一幅“物质的画”(einmateriellesGemalde),因为语言文字能描叙出一串活动在时间里的发展,而颜色线条只能描绘出一片景象在空间里的铺展。
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对比着上面所引中国古人的话,就见得不够周密了。
不写演变活动而写静止景象的“诗歌的画”也未必就能转化为“物质的画”。
只有顾恺之承认的困难可以用莱辛的理论去解释。
“目送归鸿”不比“目睹飞鸿’不是一瞥即逝(instantaneous)的情景,而是持续进行(progressivecontinuing)的活动;
“送”和“归’包含鸟向它的目的地飞着、飞着,逐渐愈逼愈近,人追踪它的行程望着、望着,逐渐愈眺愈远。
这里确有莱辛所说时间上的承先启后问题。
其他象嗅觉(“香”)、触觉(“湿”、“冷’)、听觉(“声咽”、“鸣钟作磬”)里的事物,以及不同于悲、喜、怒、愁等有显明表情的内心状态(“思乡”),也都是“难画”、“画不出”的,却不仅是时间和空间问题了。
即就空间而论,绘画里有结构或布局的问题。
程正揆引的一联诗把空间里辽远不沾边的景物连系起来,彼此对照,即使画面具有尺幅千里之势,使“湖西月”和“江北鸿”一时呈现,也只会两者平铺陈列,而“画不象”诗里那样上句和下旬的清楚呼应。
在参寥引的两句诗里,大自然的动荡景象为宾,小屋子里的幽闲人事为主,不是“对弈棋”而是“看弈棋”,“看”字是句中之眼,那个旁观的第三者更是主中之主;
写入画里,很容易使动荡的大自然盖过了幽闲的小屋子,或使幽闲的小屋子超脱了动荡的大自然,即使二者配比适当,那个“看棋”人的特出地位也是“画不就”的。
再说,写景诗里不但有各个分立的、可捉摸的物体,还有笼罩的、气氛性的景色,例如“湿”却“人衣”的“空翠”、“冷”在“青松”上的“日色”,这又是“决难画出”的。
这些是物色的气氛,更要加上情调的气氛.比莱辛先走一步的柏克(E.Burke)就说:
描写具体事物时,插入一些抽象或概括的字眼,产生包罗一切的雄浑气象,例如弥尔顿写地狱里阴沉惨淡的山、谷、湖、沼等等,而总结为“一个死亡的宇宙”(auniverseofdeath),那是文字艺术独具的本领,断非造型艺术所能仿效的。
事实上,“画不就”的景物无须那样寥阔、流动、复杂或者伴随着香味、声音。
就是对一个静止的简单物体的描写,诗歌也常能具有绘画无法比拟的效果。
诗歌里渲染的颜色、烘托的光暗可能使画家感到自己的彩色碟破产,诗歌里钩勒的轮廓、刻划的形状可能使造形艺术家感到自己的凿刀和画笔技穷。
当然不是否认绘画、雕塑别有文字艺术所无法复制的独特效果。
汪中《述学》内篇一《释三九》上说诗文里数目字有“实数”和“虚数”之分。
这个重要的修辞方法可以推广到数目以外去,譬如颜色字。
诗人描叙事物,往往写得仿佛有两三种颜色在配合或打架,刺激读者的心眼;
我们仔细推究,才知.实际上并无那么多的颜色,有些颜色是假的。
诗文里的颜色字也有“虚”、“实”之分,用字就象用兵那样,“虚虚实实”。
苏轼咏牡丹名句:
“一朵妖红翠欲流”;
明说是“红”,那能又说’‘翠”呢?
不就象笑话诗所谓“一树黄梅个个青”(咄咄夫《增补一夕话》卷六)么?
原来“翠”不是真指绿颜色而言,“乃鲜明貌,非色也”(冯应榴《苏诗合注》卷——《和述古冬日牡丹》第一首引《纬略》、《老学庵笔记》,参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八、杨慎《升庵全集》卷六三)。
诗里只有一个真实颜色,就是“红”;
“翠”作为颜色来说,在此地是虚有其表的。
杜甫《暮归》:
“霜黄碧梧白鹤栖”;
“碧梧”叶已给严霜打“黄”了(参看《寄韩谏议》注:
“青枫叶赤天雨霜”),所以即目当景,‘碧”没有“黄”和“白’那样实在。
李商隐《石榴》:
“碧桃红颊一千年”,是“碧”又是“红”构成文字里自相抵牾的假象。
“碧+、桃”是个落套名词,等于说仙桃、仙果,所以“碧”是虚色,不但不跟实色“红”抵牾,反而把它衬托,使它愈射眼,并且不是拉外物来对照,而仿佛物体由它本身的影子来陪衬,原是一件东西的虚实两面。
畅当《题沈八斋》:
“绿绮琴弹《白雪》引,乌丝绢勒《黄庭经》”;
“绿”、“乌”实色,“白”、“黄”虚色。
韦庄《边上逢薛秀才话旧》:
“也有绛唇歌《白雪》,更怜红袖夺金觥”;
“白”虚色,“绛”、“红”、“金”实色。
再举白居易诗里几个例。
《新乐府.红线毯》:
“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红蓝花”就是“红花”,所以只有“红”色,“蓝”是拉来装场面的。
《九江北岸遇风雨》。
“黄梅县边黄梅雨,白头浪里白头翁”;
上句虚色,下句实色。
《紫薇花》:
“独立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花是真“紫”,人是假“紫”。
写一个颜色而虚实交映,制造两个颜色错综的幻象,这似乎是文字艺术的独家本领,造形艺术办不到。
设想有位画家把苏轼那句诗作为题材罢。
他只画得出一朵红牡丹花或鲜红欲滴的牡丹花,他画不出一朵红而“翠”的花,即使他画得出,他也不该那样画,因为“翠”在这里并非和“红”同一范畴的颜色。
虚色不是虚设的,它起着和实色配搭的作用;
试把“翠”字改为同义的“粲”字,或把“碧桃”改成“仙桃”、“蟠桃”,那两句诗就平淡乏味、黯淡减“色”了。
西洋诗里也有这种修辞技巧。
例如英语“紫”(purple)字有时按照它的拉丁字根(purpureus)的意义来用,不指颜色,而指光彩明亮(brighthued,brilliant),恰象“翠”字“乃鲜明貌,非色也”。
十八世纪写景大家汤姆逊(JamesThomson)在《四季》诗(TheSeasons)里描摹苹果花,有这样一句:
“紫雨缤纷落白花”(onewhiteempurpledshowerofmingledblossoms)。
“白”是实色,“紫”是虚色。
歌德的名言:
“理论是灰黑的,生命的黄金树是碧绿的”(UndgrundesLebensgoldnerBaum);
“黄金”那里又会“碧绿”呢?
这里的“黄金”,正如“黄金时代”的“黄金”,是宝贵美好的意思,只有“情感价值”(Gefiihlsweft),没有“观感价值”(Anschauungswert);
换句话说,“黄金”是虚色,“碧绿”是实色。
假如改说:
“白花雨下炫人眼”或“生命宝树油然绿”,也就乏味减色了。
文字艺术不但能制造颜色的假矛盾,还能调和黑暗和光明的真矛盾,创辟新奇的景象。
例如《金楼子》第二篇《箴戒》:
“两日并出,黑光遍天”,邓汉仪辑《诗观》三集卷一冯明:
期《滹沱秋兴》,“倒卷黑云遮古林,平沙落日光如漆”;
或李贺《南山田中行》:
“鬼灯如漆照松花”,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卷二五徐兰《磷火》:
“别有火光黑比漆,埋伏山坳语啾:
唧”。
西洋诗歌也有同样的描写,我接受莱辛限定的范围,只摘取一二写景的词句,不管宗教诗里常用的这类比喻。
莱辛称赞弥尔顿《天堂的丧失》里有“诗歌的画”,在《拉奥孔》草稿中列举该诗章节为例;
这些章节都叙述继续进展的动作,不是“物质的画”所画得出的。
不过,他似乎没注意到弥尔顿有些形容物象的话也一样无法画入“物质的画”。
就象他说地狱里的阴火“没有光明,只是一片可以照见的黑暗”(Nolightbutratherdarknessvisible),又说魔鬼向天开炮,射出一道“黑火”(blackfire)。
本身黑暗的光明或本身光明的黑暗不可能用造形艺术去表达。
中国画里的“黑日”在雨果诗里就见过。
“一个可怕的黑太阳耀射出昏夜”(Unaffreuxsoleild’ourayonnelanuit)。
一位大画家确曾有把黑太阳画出来的企图,那就是度勒(A.Durer)的名作《忧郁》(Melencolia)。
尽管那幅画里的黑太阳也博得雨果的叹赏,我们终觉得不如他自己的诗句惊心动魄。
竟可以大胆说,若不是事先知道,我们看不出度勒画的就是黑太阳。
度勒的失败不是偶然的.“火光黑比漆”、“黑太阳”等光暗一体的景物只能黑漆漆而又亮堂堂地在文字艺术里出现。
一个很平常的比喻已够造成绘画的困难了,而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
莱辛在草稿里也提起绘画不能利用比喻,因而诗歌大占胜着,但是没有把道理讲清。
譬如说,“他真象狮子”,“她简直是朵鲜花”,言外的前提是,“他不完全象狮子”,“她不就是鲜花”。
假使他百分之百地“象”狮子,她货真价实地“是”鲜花,那两句话就不成为比喻,而是“验明正身”的动植物分类法了。
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
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
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
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
佛经里说起“分喻”,相比的东西只有“多分”或“少分”相类(《翻译名义集》第五三篇《阿波陀那》条,参看《大般涅槃经·
如来品》第四之二又《狮子吼菩萨品》第一一之三)。
中国古人讲得更透彻。
刘向《说苑·
善说》记惠子论“譬”,说“弹之状如弹”则“未谕”,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四《答李生第二书》又《第三书》根据“岂可以弹喻弹”的意思,总括出比喻的辩证原则。
一方面“凡喻必以非类”,另一方面“凡比必于其伦”。
《全唐文》卷七二一杨敬之《华山赋》形容山势说:
“上上下下,千品万类,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也恰是皇甫湜那两句话的诠释。
比喻是文学词藻的特色,一到哲学思辩里,就变为缺点——不谨严、不足依据的比类推理(analogy)。
《墨子·
经》下:
“异类不吡(比),说在量”,《经说》下举例:
“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
逻辑认为“异类不比”,形象思维相反地认为“凡喻必以非类”。
中国成语不是说什么“斗筲之人”、“才高八斗”么?
木的长短属于空间范围,夜的长短属于时间范围,是“异类”的“量”,所以“不比”,但是晏几道《清商怨》的妙语:
“要问相思,天涯犹自短”,不就把时间上绵绵无尽期的长“相思”和空间上绵绵远道的“天涯”较量一下长短么?
外国成语不也说瘦高个子“象饿饭的一天那么长”(Ilestlongcommeunjoursanspainetmaigrecommecareme-prenant)么?
可见“智与粟”比“多”、“木与夜”比“长”,在修辞上是容许的。
所以,从逻辑思维的立场来看,比喻是“言之成理的错误"
(Figuraeunerrorefattoconragione),是“词语矛盾的谬论(einecontradictioinadjecto)因而也是逻辑不配裁判文艺(dassdieLogiknichtdieRichterinderKunstist)的最好证明”。
难道不也是绘画不能复制诗文的简单证明么?
造形艺术很难表示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情景。
元好问《中州集》卷九张檄小传摘句,“骇浪奔生马,荒山卧病驼”,近人许承尧《疑盒诗》卷丁《兰州赴京师途中杂诗》,“古道修如蛇,枯杨秃如拳,晚山如橐驼,坐卧夕阳边。
”把山峰比卧驼是以物拟物的贴切比喻,说的是静止状态,绝不是什么“继续进展”的“动作”。
问题是:
怎样把它写入“物质的画”呢?
把山峰画得象一头骆驼么?
画了山峰,又沿着它的外廓用虚线勾勒一头骆驼么?
画一座大山,旁边添一头小骆驼,让读者来比较么?
那都不成为山水画,而只是开玩笑的滑稽画,因为滑稽手法常“把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相似转化为全部相等”(DieKomikverwandleHalbe-undViertelsahnlichkeitinGleichheiten)。
袁凯《海叟诗集》卷二《王叔明画<
云山图>
》。
“初为乱石势已大,橐驼连峰马牛卧”,题画诗完全可以用比喻这样描写,所题的画里要真是那种景象,就算不得《云山图》,至多只是《畜牧图》了!
这个道理,前人早懂得。
狄德罗说,诗歌里可以写一个人给爱神射中了一箭,图画里只能画爱神向他张弓瞄准,因为诗歌所谓中了爱神的箭是个譬喻,若照样画出,画中人看来就象肉体受重伤了(cen’estplusunhommeperced'
unmetaphore,maisunhommeperced’untraitreelquonapercoit)。
我在不是讲艺术的书里,意外地碰上相同的议论。
倪元璐《倪文贞公文集》卷七《陈再唐<
海天楼时艺>
序》;
“画人貌人者,贵能发其河山龙凤之姿,而不失其颧面口目之器,苟使范山模水以为口目而施苞羽鳞鬢之形于其面,则非人矣!
”汪曰桢《湖雅》卷六:
“时适多蚊,因仿《山海经》说之云:
‘虫身而长喙,鸟翼而豹脚’。
……设依此为图,必身如大蛹,有长喙,背上有二鸟翼,腹下有四豹脚,成一非虫非禽非兽之形,谁复知为蚊者!
”十八世纪一部英国小说嘲笑画家死心眼把比喻照样画出(theridiculousconsequenceofrealizingthemetaphors),举了个例,《新约全书·
马太福音》里说到责人严而对已恕的恶习,用了一个有名的比喻。
“只瞧见兄弟眼睛里的灰尘(mote),不知道自己眼睛里有木杆(beam)”,有位画家就画一人眼里刺出长木梁,伸手去拔另一人眼里插的小稻草。
一句话,诗里一而二、二而一的比喻是不能画的,或者说,“画也画得就,只不象诗”。
四
《拉奥孔》所讲的画,主要指故事画(I'
istoris)。
那时候,故事画是公认为绘画中最高的一门,正如叙事的史诗是公认为文学中最高的一体。
文艺复兴以来的风尚一直如此,阿尔培谛(LB.Alberti)的权威著作《画论》(DellaPittue)就强调故事画是画家最伟大、最尖端(grandissima,summa)的成品。
一幅面只能画出故事的一场情景,所以莱辛认为画家应当挑选整个“动作”里最耐寻味和想象的那“片刻”(Augenblick),千万别画故事“顶点”的情景,因为一达顶点,情事的演展已到尽头,不能再“生发’(fruchtbar)了,那个“片刻’仿佛女人“怀着身孕”(pragnant),它包含从前种种,蕴蓄以后种种。
这可以说把莱伯尼兹对感觉的普遍定义应用在文艺题材上,莱伯尼兹的名句是,“现在怀着未来的身孕,压着过去的负担”(Lepresentestgrosdel’aveniretchargedupasse)。
抽象地说,时间的每一片刻无不背上有负担而腹中有胚胎。
在具体人生经验里,各个片刻却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所负的担子或轻或重,或则求卸不能,或则欲舍不忍,所怀的胎儿有的尚未成熟,有的即可产生,有的恰如期望,有的大出意料。
艺术家就根据这种种来挑选合适的情景。
黑格尔讨论造形艺术时,再三称引莱辛所批驳的文格尔曼(Winekelmann),只一笔带过莱辛,甚至讲拉奥孔那个雕像时,还不提莱辛的名字,但是把他的论点悄悄地采纳了.黑格尔也说,绘画不比诗歌,不能表达整个事件或情节的发展步骤,只能抓住一个“片刻”(Augenblick),因此该挑选那集中前因和后果在一点里的景象(inwelchemdasVorgehendeundNachfolgendeineinenPunktzusammengedrangtist),譬如画打仗,就得画胜负可分而战斗尚酣的片刻。
包孕最丰富的片刻是个很有用的概念,后世美学家一般都接受了而加以心理学的说明。
这个概念不仅应用在故事画上,一位英国诗人论人物画,也说,画中人的容貌应当“包孕着”许多表情而只“生产出”一个表情(pregnantwithmanyexpressionsbutdeliveredofone)。
画故事不要挑选顶点或最后景象的道理,中国古人也已了解。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七《题摹<
燕郭尚父图>
“往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
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弦也。
伯时笑曰;
‘使俗子为之,作箭中追骑矣。
’余因此深悟画格。
”看来唐人早“悟”这种“画格”。
楼钥《攻婉集》卷七四《跋<
秦王独猎图>
》:
“此《唐文皇独猎图》,唐小李将军之笔。
……三马一豕,皆极奔骤,弓既引满而箭锋正与豕相直。
岂山谷、龙眠俱未见此画耶?
”李公麟对于富有包孕的片刻很有体会,只要看宋人关于他另一幅画《贤巳图》的描写,岳珂《桯史》卷二。
“博者五六人,方据一局投进。
盆中五皆卢,而一犹旋转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观者皆变色起立’(参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五回里的白话改编)。
避免“顶点”,让观者揣摹结局,这一切都由那颗旋转未定的骰子和那个俯盆狂喊的赌客体现出来。
《独猎图》里的景象,结果可以断定,《贤巳图》里的景象,结果不能断定,但是两者都面临决定性的片刻,悠然而止,留有“生发”余地。
唐、宋两位姓李的大画家当然不会知道什么莱辛和黑格尔的,就象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木刻家比逸克(ThomasBewick),也未必看到、听到他们的理论,然而他也常用一个富于含意的情节来表达整个故事,暗示即将发生的悲剧(tellingastorybysuggestivedetail,foreshadowingatragedy)——一句话’他挑选那留有生发余地的“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