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惇书法史讲座稿 张恨无整理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黄惇书法史讲座稿 张恨无整理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黄惇书法史讲座稿 张恨无整理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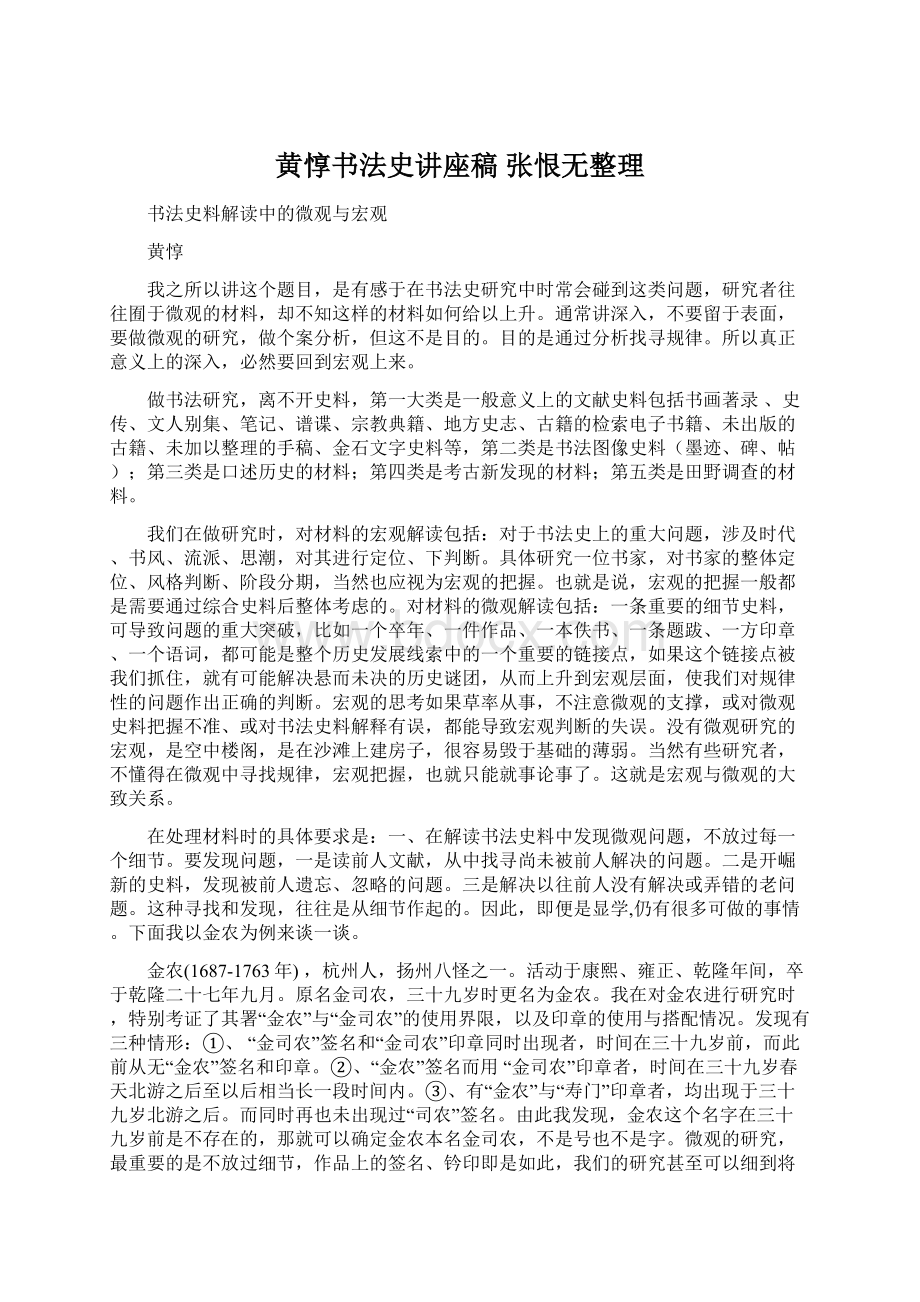
①、“金司农”签名和“金司农”印章同时出现者,时间在三十九岁前,而此前从无“金农”签名和印章。
②、“金农”签名而用“金司农”印章者,时间在三十九岁春天北游之后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③、有“金农”与“寿门”印章者,均出现于三十九岁北游之后。
而同时再也未出现过“司农”签名。
由此我发现,金农这个名字在三十九岁前是不存在的,那就可以确定金农本名金司农,不是号也不是字。
微观的研究,最重要的是不放过细节,作品上的签名、钤印即是如此,我们的研究甚至可以细到将有纪年的作品上的签名和钤印,逐年排列。
从所举例的作品可知:
雍正二年秋九月,38岁的金农已决定北游,因为此前他已接受山西泽州陈幼安的邀请。
金农视此次北游为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的壮举。
经过数月准备,到次年三月才离开扬州。
他先赴北京,九月再赴山西。
北游共历四载馀,到雍正八年是才南归扬州。
从39岁前金司农的署款及其款印可证实:
1、三十九岁前落款都为“金司农”。
2、款印有:
“金司农”、“寿田”、“江湖听雨翁”。
3、闲印有:
“金氏冬心斋印”、“与林处士同邑”。
那么,我们会有疑问,金司农何时更名为金农?
我们来看金农的一件作品,《王彪之井赋轴》,作于雍正三年乙巳(1725年)首春,时金农39岁。
创作时间为金农北游前夕,距前介绍的雍正二年九月的两个册子,仅隔三个月。
这是我们现今所能看到署款为“农”的第一张作品。
但是其上仍然用“金司农印”。
在金农研究中,我既然发现了改名的问题,我还要追下去,打破沙锅问到底。
“金司农”为何更名为“金农”?
改名前后的书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对我们了解金农书法的发展有什么价值?
如何对金农一生的各体书法作品作出分期,以及金农书法在前碑派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有那些?
因此,这样的追问就使微观的发现向宏观的方向提升。
对上述疑问,我们可有如下解释:
作为初名的“司农”,为其父母或老师所起,是一种功名利禄的寄托。
金农将“司农”改为“农”,由封建时代管理农业的最高官员,理想中的人上人,一下子变成为最底层的“农”夫。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饱学之士的金农当然不会不知。
考察其原因,与金农三十九岁前的境遇有关:
1、三十岁时金农父亲去世,因此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靠。
2、他曾跟随二载的老师何焯(义门)失势,使其深感前途未卜。
3、三十岁前后大病一场,生活艰辛。
4、三十五岁起金农赴扬州,以卖诗文、书法为生计。
“司农”之梦破灭,他却天天要写着这样一个名字。
从他这一时期所用闲章看,如“江湖听雨翁”(漂泊、流浪)、“与林处士同邑”、“布衣三老”,(隐士)再后还有“纸裘老生”(贫寒),无不反映出他的人生追求发生着与“司农”梦相反的轨迹,并迫使他通过更名,从无望的仕途憧憬中,回到现实中来。
我们可从南京艺兰斋所藏《金农书翰十七通》的其中四篇来说明金农的署名情况。
金农北游归来途经山东时的作品(约44岁),《临华山庙碑册》(黄易手装题签本),是其隶书成熟的代表作。
饿笔渴隶,不让古人。
充分表现了金石气息。
此时“金农印信”与“寿门”对章,也出现于这一时期作品上,说明金农已更字“寿门”。
金司农”考证的水落石出,也促使我在解读他的书作时获得这样的信息,金农行草成熟于改名之前,而他隶书的高潮,正在其改名后的北游期间,四年后北游南归经过曲阜时留下的数件隶书作品,已经十分成熟。
他的诗稿作品中既然有这样的信息,于是又促使我认真地从他的诗集中,解读出他关于书法追求、变革的信息来。
我将金农一生以《华山庙碑》为基础所变革的各体书法归为隶书、碑行、抄经体楷书、隶楷、漆书五大类。
而这五类书体的变革,居然在金农的诗中都有明确的交待。
这类作品是金农以汉隶为根基,参以北齐楷隶为体,并追求“木板气”的创造性实践。
其有诗云:
“书看北齐字,画爱江南山”。
比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临西岳华山庙碑册》(48岁作)即是此种风格。
金农的楷隶,晚清人魏锡曾(?
—1881)曾为《冬心先生续集》作跋记云:
“尝于吴兴书船见先生自书此序,楷隶小册,审为真迹。
”我们不难推测金农楷隶书的由来,一是北齐石刻文字,而是古代木板雕刻文字。
此类书体的风格特征是横竖笔画粗细划一,工整而有木板雕刻之气,同一作品中重复之字似出一辙,如灯取影,不避形态雷同。
决不使用倒薤用笔。
金农将楷隶与其隶书、漆书作品区分得非常明确。
金农的写经体楷书,我们可从金农47岁所刻的《冬心先生集》扉页上看出端倪。
其诗歌中对写经体楷书也有记载:
一
圣僧手写心弗违,
朱丝阑好界画微。
法王力大书体肥,
肯落人间寒与饥。
阅岁六百方我归,
如石韫玉今吐辉。
此中妙谛多福威,
昆明浩劫增歔欷。
二
手闲却嬾注虫鱼,
且就嵩高十笏居。
到处云山到处佛,
净名小品倩谁书
三
昙石襄村荒非故庐,
写经人邈思何如。
五千文字今无恙,
不要奴书与婢书。
我们把宋代刻经与金农写经作一比较,可知其由来是古代佛门的写经体楷书。
此类书体的风格特征是早年肥,中年以后与其他品类间有笔法上的渗用,晚年易瘦,瘦即寿,然不论肥瘦都有浓重的佛门审美特征。
创作时间:
47岁以后始见写经体楷书。
此类书体的历史价值是,关于其写经体楷书,以往多不被人关注,或简单地将其同于一般的楷书,或误称为漆书,更未注意到此举在书法史上的重要价值。
以写经为佛事的书法家历代皆有,若赵孟頫,若董其昌,然如金农这样化俗为雅,以古代佛门抄经或佛经木刻版本取法者,金农实为历史上第一人。
我们再来看金农的另一类书体,漆书(渴笔八分),所谓“用笔似帚却非帚,渴笔八分书绝奇”。
其诗中透露消息:
“偶游海州,州人供茗治具于僧庵,乞余作书,庵中沙弥复请余取名号,薄暮振衣,老兴不浅,记之以诗:
州人昨知我能书,
预设纸笔侯僧庐。
舒城长毫老不秃,
鄱阳精楮白雪如。
泉上呷茶松下饭,
饭毕挥扫日未旰。
风有声兮声满堂,
巨幅大家供传看。
……
历史上截毫之说,来源于传为秦祖永的《七家印跋》,这是个彻头彻尾的伪材料。
金农对漆书有记:
“予年七十始作渴笔八分。
汉魏人无此法,唐、宋、元、明亦无此法也。
康熙间金陵郑簠虽擅斯体,不可谓之渴笔八分。
若一时学郑簠者,亦不可谓之渴笔八分也。
乾隆丁丑正月杭郡金农书记。
时年七十有一。
”
研究时,我们还能于微观中再有微观的发现。
最细微的是我从他的诗中,发现他曾关心一种特殊的笔法——倒薤笔法。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厉鹗在金农三十岁前后写给金农的一首诗,诗中规劝金农“论书近捃拾,勿事徵倒薤。
”这是说两人论书时,探讨过“倒薤”撇法。
以后又读到金农北游期间的诗《上党张水部出观宋范宽画独山草堂图》,诗云:
“宋楮坚光未糜坏,款字低行类垂薤。
”看画看到款字,还看出垂薤用笔,如果没有特殊的眼光,没有对笔法的实践,是发现不了的。
所以倒薤的用笔特征,很早在金农书法中出现。
如果以上算作文献史料,那么还要到书法图像——另一种史料中去验证。
这一验证太妙了,居然把金农的几种体分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在界定其各种书体时,找到了金农自己区分书体的用笔特征。
例如,金农的行草、隶书,晚年的漆书都使用“倒薤”撇法,几乎成了他的专利,可是他的抄经体楷书,他的楷隶书,绝对不用“倒薤”。
倒薤的用笔特征。
金农隶书中的倒薤撇法可从《临华山庙碑册》中看出来。
再有就是以诗证史以诗作为史料来研究诗人,是文学史中常用的方法。
然而,古代的书家许多都是诗人,所以,以诗证史对于书史研究来说也具有同样的价值。
金农的诗,反映了他的书法艺术观念,也同样折射整个时代书法观的转变。
其中最重要的一首,就是五十岁举博学鸿词未中,从北京南归路过山东时写的一首诗:
会稽内史负俗姿,
字学荒踈笑骋驰。
耻向书家作奴婢,
华山片石是吾师。
——金农《鲁中杂诗》
如果说以上细节微观的研究,是为了把握金农书法的变化,而努力使我们可在宏观上对金农一生书法作出分期,那么这首诗,不仅使我们了解到金农的艺术观念,进而可以判断,在康雍乾时期,远早于阮元在嘉庆后期(1814)提出的《南帖北碑论》,就有金农这样的师碑观念的彰显。
解读这首诗还可以发现,关于对待二王一脉帖学的态度,关于不师名家而师无名书家的宗法观念,关于由师帖到师碑的取向转变,己囊括了清代所有阶段碑派的宗法认识。
这就从宏观上促使我们认识到,清代前期的碑派活动和观念的形成,是有根可据的,也映证了我与李昌集、庄熙祖两位先生早在1989年于《书法篆刻.中国书法史略》中提出的前碑派问题。
由微观的发现上升到宏观的发现,使两方打通,再回到细节上去,发现就会更多。
例如金农不但实践过金石气,很多人不注意他也实践过木板气。
又例如金农的碑行,为什么不敢写成大幅的作品?
(这些现象都可视为前碑派的艺术特征。
)金农身后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为什么到赵之谦时代这样的大作品比比皆是?
再从金农的周围看,金农和当时活动于扬州的许多书画家,都受到郑簠和程邃的影响,如郑板桥、高翔、高凤翰、汪士慎、朱青雷等等,于是前碑派的线索、活动方式、取法对象等宏观上的问题逐渐清晰。
九十年代中期我写了篇《前碑派与汉碑》的论文,指出汉碑热潮在清初的表现,指出当时学郑簠的书家很多,是有流派的。
清代的碑派书法起于对汉碑隶书的风靡。
这就从史的层面,突破了碑派是清中叶才出现的旧说。
完全不是先有了阮元的《北碑南帖论》才有了碑派的思潮。
这是宏观层面研究的新成果,而其基础正来源那些细节的微观史料的解读。
第二个方面是,在宏观把握中寻找微观的支撑点。
宏观和微观,看似在两个层面,其实往往交织在一起,即便是好像己成为共识的观点,前后没有微观史料的支撑,或许也不能使人信服,甚至产生疑问。
所以有些疑问不如自己提出,自己设法去解决。
我在写明代初年书法大势时,注意到台阁体的风靡与八股取士、程朱理学有关。
关于这样一个问题,在宏观上议论,可以讲出很多道理。
《朱子》在这一时期,作为官学,人皆知之。
所以翻开明永乐中胡广等奉敕编纂的《性理大全》,即可找到朱熹的论书,其中“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是其名言。
用这样的理由说明明初人不学宋人,似乎就够了。
可是为什么在明初“摒除胡元之制”的大方针下,元代赵孟頫的书法却丝毫未损呢?
我们来看明初的山水画。
我们知道书法的兄弟——绘画,在明初,回到了宋人的轨迹上,而元人的画风则受阻,这是摒除胡元之制的结果。
然而,明代的书法却继续沿着元人的路走。
所以要解释明初书法不学宋人似乎容易,而解释赵孟頫为什么仍受到欢迎,却似乎是不合历史逻辑的。
朱元璋孙子朱有燉(1379-1439)集成《东书堂法帖》十卷,他在凡例中说:
“予生平不乐宋人书”。
所以这部刻帖,自晋到元,名家书皆收,独缺宋代,(只收入苏易简摹兰亭序一件)朱有燉在《自序》中有如下一段话:
“至赵宋之时,蔡襄、米芾诸人,虽号为能书,其实魏晋之法荡然不存矣。
元有鲜于伯机、赵孟頫,始变其法,飘逸可爱,自此能书者亹亹而兴,较之于晋唐虽有后先,而优于宋人之书远矣。
”这条史料,有三个特征:
①、偏僻,不易为人注意,很少人会注意刻帖上的序和凡例。
②、是有代表性,代表了皇家的书法观。
③、是有时代性,把受朱子影响观点写得明明白白,还把为什么赵孟頫受到欢迎的疑问给予解决。
这样我们对整个明代书法发展线路的了解清晰起来,也突现出赵孟頫在明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价值。
《东书堂法帖》中为什么赵孟頫受到欢迎的这段资料,促使我们对明代许多复杂的问题的解读,有了一把进门的钥匙。
使宏观的判断有了具体的支撑点。
以后到了成化年间,为突破台阁体影响,吴门派先导书家吴宽、沈周,改变路线直学北宋苏、黄,是为第一个波澜,可是这个波澜对赵孟頫的喜好依旧,这表现于文徵明一生对赵氏的效仿和尊重。
再以后到晚明,吴门派衰退,云间派崛起,是为第二个波澜,赵孟頫成为超越的对象,因为只有对赵的超越,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突破元和明初的笼罩,使宋代以上的书法得以复兴。
明代的云间(上海之古称)派,也是较为复杂的问题,云间派的提出有两个版本,但都发生在晚明,一是王世贞版,一是董其昌版。
王世贞云间派的名单:
陈璧——沈度、沈粲——陆深。
1、王世贞笔下的“云间派”有贬意。
说他们“园熟精致”,“不能洗通微院气”,“盖所谓云间派也”是以看不起的口吻写的。
2、王世贞笔下的“云间派”与“院体”(即台阁体)同义。
3、王世贞立场在吴门。
“天下法书归吾吴”。
“吴中自希哲,征仲后……法书之迹,衣被遍天下,而无敢抗衡。
”故可以说,提出所谓‘云间派’,正为突出吴门书派。
董其昌云间派的名单线索是陆机、陆云——沈度——张弼——陆深——莫如忠、莫是龙——董其昌。
他是云间人,立场与王世贞相反,所以对家乡的书家充满着热情。
两人的不同侧重反映了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苏松之争”。
云间派问题的焦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焦点一是明代书坛确有苏松之争,二是苏州书家与松江书家对赵孟頫的不同价值观。
云间派书家对吴门书家之不满,缘于文徵明以后书坛的变化。
我们看莫是龙对祝枝山、文徵明的批评:
“国朝如祝京兆希哲,师法极古,博习诸家。
楷书骨不胜肉,行草应酬,纵横散乱,精而察之,时时失笔,当其合作,遒爽绝伦。
平生见公墨迹惟金山寺石刻碑,写张说诗,及余家藏写阮籍《咏怀诗》焉。
草法通神,无可拟议。
文太史具体《黄庭》而起笔尖微,病在指腕,虽严端不废,未见岿峨磊落之姿。
王贡士盘旋虞监,而结体甚疏,虽烂然天真,而精气不足。
晚年行法飘飘欲仙。
吾乡陆文裕子渊全仿北海,尺牍尤佳,人以吴兴限之,非笃论也。
数公而下,吴中皆文氏一笔书,初未尝经目古帖,意在佣作,而以笔札为市道,岂复能振其神理,托之豪翰,图不朽之业乎!
”
我们看到这段文字似乎批评得很有理,既说了好话,又指明了弊端之所在。
以上观点可在范允临的云间画派论述中得到映证:
“学书者不学晋辙,终成下品,惟画亦然。
宋元诸名家,如荆、关、董、范,下逮子久、叔明、巨然、子昂,矩法森然,画家之宗工巨匠也。
此皆胸中有书,故能自具丘壑。
今吴人目不识一字,不见一古人真迹,而辄师心自创。
惟涂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即悬之市中,以易斗米,画那得佳耶!
间有取法名公者,惟知有一衡山,少少仿佛,摹拟仅得其形似皮肤,而不得其神理。
曰:
“吾学衡山耳。
”殊不知衡山皆取法宋元诸公,务得其神髓,故能独擅一代,可垂不朽。
然则吴人何不追溯衡山之祖师而法之乎?
即不能上追古人,下亦不失衡山矣。
我们把这两段话,对比着解读,问题便发现了。
莫是龙说陆深全仿李北海,人以吴兴限之,非笃论也。
谁限的,就是你吴门人限的,你吴中都是学文徵明,而我云间是超过赵孟頫直追唐代,所以云间利害,才可图不朽之业。
这才是莫是龙真正的意图。
董其昌除了为陆深鸣不平,又提出了莫如忠,这是他的老师,说莫如忠“自二王之外一步不窥”,岂是你文徵明作梦可以想得到的。
在董其昌一生的书法题跋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开派愿望,他自言莫如忠教他书法后,三年便将文、祝置于眼角,他一直要与赵孟頫比高低,说我书因生得秀,赵孟頫因熟得俗。
如果仅仅将这些看作是董其昌的偏见,我以为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以宏观的高度来解读这些史料,前面我提到的朱有燉《东书堂刻帖》自序中的那段话,便有了重要的意义。
即既然明初赵孟頫的书法一直施展着重大的影响,那么吴宽、沈周而下的吴门派,虽然己突破赵孟頫向宋四家学习和取法,但赵孟頫在吴门诸家中仍然有着崇高的地位。
我们看莫、董二人在陆深问题上的言论,就可以知道,对待赵孟頫的态度,是松江书家与吴门书家的分水岭。
他们知道要与吴门争高低,就必须超越赵孟頫这座山峰,才能真正继承宋以上传统,从而在历史上立脚。
对待赵孟頫的态度,是松江书家与吴门书家的分水岭。
这也证明,明初没有云间派,云间派之产生与抗衡吴门派有互为因果之关系。
所以云间派出现于万历时代,是莫是龙和董其昌的共同理想。
只是莫是龙万历十五年就夭折了。
那时董其昌才三十五岁,后来董其昌羽毛渐丰,成名之后他正式提出了董版云间派: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
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
文、祝二家一时之标,然突过二沈未能也。
以空疏无实际,故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
他不是不争,而是强烈地希望在吴门派衰退之际,拉起云间派的大旗,这也是晚明人典型的心态。
当然,从这个意义上看清了云间派书法的追求目标,怎么还会去相信一个崇拜赵孟頫的明初,会有一个超越赵孟頫的云间派呢?
所以这可反证明初没有云间派,董其昌把二沈、张弼拉进来,只是标榜乡邦文化,他所言“文、祝二家一时之标,然突过二沈未能也。
”才是实话。
这样我们得出结论,云间派的核心艺术观是反对吴门末流只学文徵明,不学古人。
主张革除因因相袭之习,提倡越过赵孟頫,将直追本源与显示个性相结合。
这是晚明最具鲜明特点的理念。
也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反映。
以上是在复杂的书法史料中,如何站在宏观立场上,把握书法史发展的脉络,同时又从细微的辨析中,从微观角度给予支撑,使这种立场始终站在坚实的基础上。
第三方面我要讲的是,史料之解读,需要放到宏观层面去深入剖析。
同样一段史料,解读的深入决定着研究者掌握了多少信息,我以为这种解读的深入至关重要。
例如在对赵孟頫的研究中,我注意到他曾有一卷小楷《过秦论》,写于他第一次出仕大都后的第五年,是应杭州来的石岩所求,卷后赵氏跋云:
“至元辛卯秋,民瞻自江左来谒选,时时相过,慰余寂寥,风雨中持黄素四幅求小楷。
适案上有贾生《过秦》三篇,乃为书之。
八月晦日集贤滥直赵孟頫书。
石岩携此卷归杭州後,于当年十二月初七会鲜于枢、郭天锡等。
鲜于枢在卷後跋云:
“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
此卷笔力柔媚,备极楷则。
後之览者,岂知下笔神速如风雨耶!
斯文又古今又一奇也。
至元辛卯十二月七日,鲜于伯几父记”
我从大量的史料中注意到,赵孟頫虽很年青就有书名。
但被称为当代第一,这是第一次。
本来这样的题跋并不费解,但是因为我关注杭州文化圈与大都文化圈的不同,关注杭州文化圈书法观与大都文化圈的书法观有什么不同,于是将上面一段题跋放到宏观层面上解读。
这一解读,却发现了许多问题。
第一,为什么赵孟頫在北京写《过秦论》时,有“寂寥”之感,风雨中作长卷,大有“风雨故人来”之叹?
第二,为什么作品到了杭州却引得如此高的评价?
于是我解读出以下信息。
其一,赵孟頫在大都并不被认为是一个艺术家,而只是一个被统战了的前朝王孙,他的字与北方大都文化圈也格格不入,所以寂寥,或可以说无人问津他的书法。
其二,“当代第一”是杭州文化圈提出的,也就是说在野的文人提出的,此时的“当代第一”并非朝野共识。
其三,赵氏书风代表的南方杭州文化圈的审美认识,所以被杭州书坛认可。
我想这样的解读较之最初表面的认识深入了许多,这是解读史料背后信息的典型例子,这也为解读同时代其他书法史料,在宏观层面打开了广阔的思路。
赵孟頫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自度南後,士大夫悉能书,纵复不至神妙,去今人何啻万万。
盖少小握笔,便得曲肖神情。
今人童幼学书,为师者悉皆恶,书之人小,及省事,稍欲学古,俗气以渐入,恶体不可复洗,岂不可叹也哉。
若今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母》等帖,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
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拥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
尚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
吾每怀此意,未尝敢以语不知者,俗流不察,便谓毁短颜鲁公,殊可发大方一笑。
至元二十六年九月七日,信笔书去,子庆必不以为过也。
”
这是一篇纲领性的宣言,也是他从南方来大都後的第一次全面的观察书坛时局。
所透露的重要信息是:
(1)、说明当时由金入元的阁僚大臣,大多崇尚颜真卿书法,如果举例,一是金代有影响的书家任询,二是由辽入元的重臣耶律楚材、刘秉忠、元初北方重要儒臣许衡等,皆书学颜真卿。
这种在北方风靡的具有刚烈色彩的书法在元初有着广泛的市场。
(2)、说明由杭州、吴兴这个江南文化圈来到大都的赵孟頫,出于书家本能,感到时代之压,责任心驱使他决心以回归二王为复古指向,改变北方“近世又随俗皆好颜书”的风气。
并且提出从童子学书入手,也就是今人所谓早期教育入手,以扭转当时书法之衰势。
他尤其指出颜书的缺陷,称“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拥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
”从信中还可知赵氏这种观点,在大都已有流露,但每每遭受阻力,故其云:
“吾每怀此意未尝敢以语不知者,俗流不察,便谓毁疑颜鲁公,殊可发大方一笑。
忽必烈死后,赵回到家乡,来往于湖州、杭州之间。
到成宗大德二年,他的书法突然在全国红了起来,这是因为成宗召他去大都写金经。
可是这个过程在史书上一笔带过,要了解实情,只有开崛新的史料。
这样我又找到大德二年方回描述成宗召赵孟頫入京写金经的诗《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诗中写赵孟頫:
“天下善书今第一”。
这证明了我前面的解读是正确的,赵孟頫要到大德年间才被朝野认可“天下第一”。
此时的赵孟頫“精神如玉鬓如漆,天上知己密如栉”,“门前踏断铁门限,若向王孙觅真迹”。
对比他初上大都时“孑然一身,四千里外,仅有一小厮自随,形影相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方回在《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诗中云:
“青藜夜照玉堂直,外补已至二千石。
不合自以艺能累,天下善书今第一。
魏晋力命王略帖,摹临有过无不及。
真行草外工篆隶,兼有与可、伯时癖,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侯掷缣帛。
门前踏断铁门限,若向王孙觅真迹。
有时乘兴扫龙蛇,图画纸素动成匹。
有时厌俗三叹息,何乃以此为人役。
如池如沟弃残墨,如冢如陵堆败笔。
太湖西畔松雪斋,七弦风清碧山碧。
桃花水肥钓鳜鱼,春雨春风一蓑笠。
胡为舍此复尘埃,鸣鞭更上金台驿。
白马二十四章来,一大藏经五千帙。
订讹补譌重缮写,金字琅函较甲乙。
考工记属冬官卿,润文使专宰相职。
北门学士董此事,一儒迥胜缁辈百。
精神如玉鬓如漆,天上知己密如栉。
省台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