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1Word文件下载.docx
《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1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1Word文件下载.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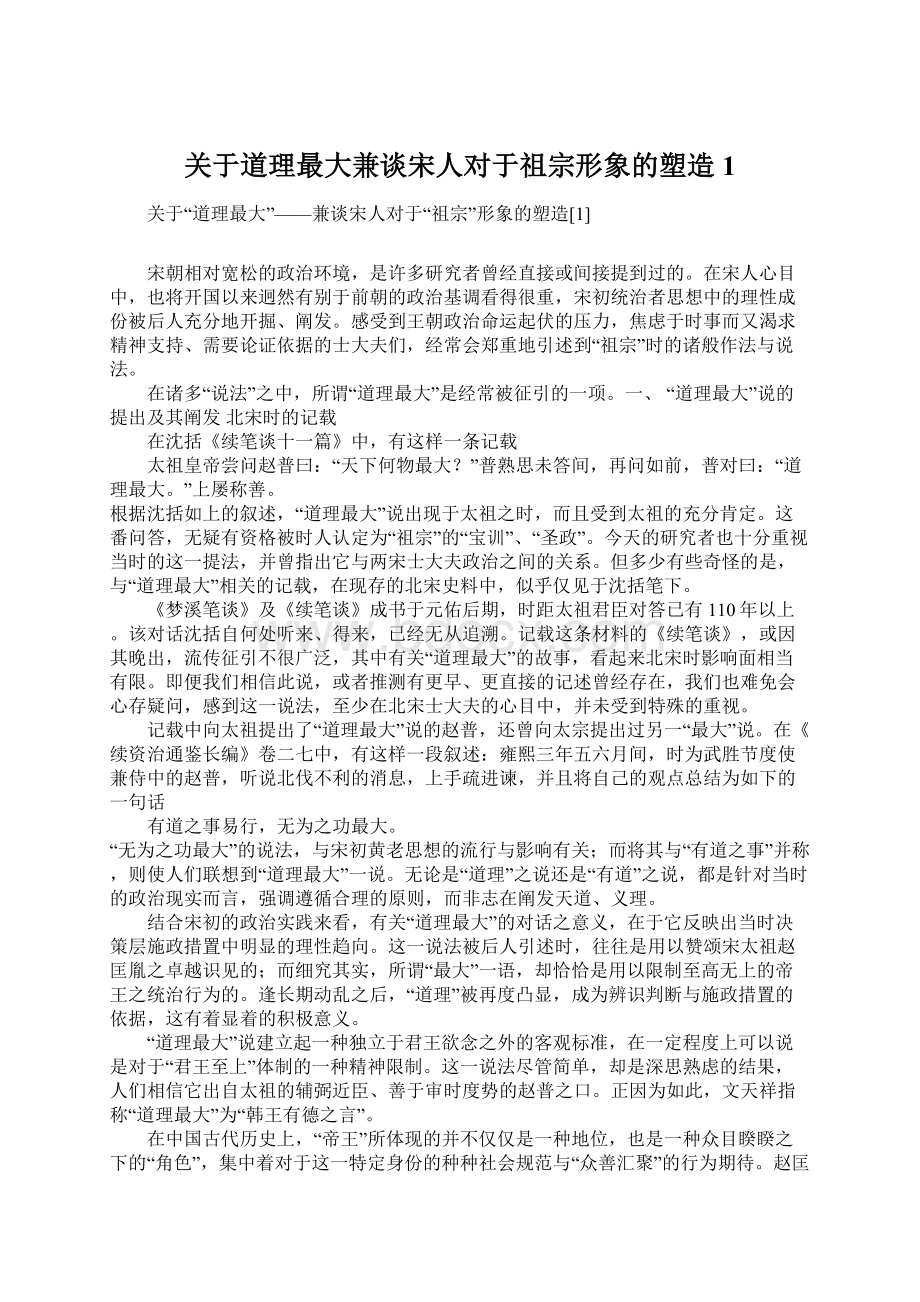
所谓“变家为国”,实际上体现为一个过程,而非一日所能成功。
赵匡胤作皇帝后不久,就曾发出“尔谓天子为容易耶”的慨叹。
李焘在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记事之末,引述石介《三朝圣政录》与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文字,记载了太祖的两件“德行”
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
左右请其故,上曰:
“尔谓天子为容易耶?
属乘快指挥一事而误,故不乐耳。
”
尝弹雀于后苑,或称有急事请见。
上亟见之,所奏乃常事耳。
上怒诘之,对曰:
“臣以为尚亟于弹雀。
”上愈怒,举斧柄撞其口,堕两齿。
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
上骂曰:
“汝怀齿,欲讼我乎?
”对曰:
“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
”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这正反映出自军阀向帝王身份转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不断调适的过程。
无论“乘快指挥”,还是对奏事臣僚的“怒骂”,都是军阀习性的自然流露;
而反思时的“不乐”,及对于臣下的“慰劳”,正体现出太祖对于自身角色的认识与行为矫正。
这样一种改造过程,事实上并非痛快顺畅。
“上悦”二字所反映的,与其简单地认定为史官的缘饰,不如说是赵匡胤省悟到自身的“皇帝”身份后特意做出的一种符合其角色期待的姿态。
与历史上的其它王朝一样,自赵宋建国之日起,设定帝王角色、塑造帝王形象的努力即一直在进行之中。
所谓“角色”,无疑由帝王的个人行为所体现;
但从特定时代的角度观察,符合规范的角色不是由宋初帝王个人扮演而成,而是由当时的士大夫参与塑就的。
不仅如此,其后嗣君臣们仍然共同继续着这一设定与塑造的过程。
有关“道理最大”的申说与阐发,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所谓“道理”
“道理最大”之说,其实算不上赵宋统治者的发明。
关于所谓“道理”,前代的统治者不能说未曾重视。
秦始皇刻石琅琊台,其歌咏秦德的颂词中就说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万物之纪。
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
东抚东土,以省卒士。
唐代贞观年间太宗君臣讨论治道时亦曾多次谈及“道理”。
王方庆缀辑于唐高宗时的《魏郑公谏录》卷二《对齐文宣何如人》中,记载着这样一段对话
唐太宗谓侍臣曰:
“齐文宣何如人?
公对曰:
“非常颠狂。
然与人共争道理,自知短屈,即能从之。
臣闻齐时魏恺先任青州长史,尝使梁还,除光州长史,不就。
杨遵彦奏之。
文宣帝大怒,召而责之。
恺曰:
‘臣先任青州大藩长史,今有使劳,更无罪过,反授小州,所以不就。
’乃顾谓遵彦曰:
‘此汉有理。
’因令舍之。
太宗曰:
“往者卢祖尚不肯受官,朕遂杀之。
宣帝虽颠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
祖尚不受处分,虽失人臣之礼,朕即杀之,大是伤急。
一死不可再生,悔所无及!
宜复其官荫。
《贞观政要》卷六《慎言语第二十二》也记载了如下一件事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
“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
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
“君举必书,言存左史。
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
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
愿陛下慎之。
太宗大悦,赐采百段。
贞观十年,太宗因袒护所宠异的越王而引起魏徵“正色进谏”,太宗于是对群臣说
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
朕之所言,当身私爱;
魏徵所论,国家大法。
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徵所论,始觉大非道理。
为人君言,何可容易!
而在太宗责备辅臣李靖等思虑不周时,也是批评其“大非道理”。
以上所说“道理”,事实上就是指理由、事理或者情理,指言行、治事应该遵守的轨范。
魏徵、杜正伦都以“道理”作为依据来评议君主、规谏君主,而君主也以“道理”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
杜正伦从其职事出发的谏言,所谓“非止当今损于百姓”之说,立论之基点显然是对帝王形象的维护;
尽管当时没有冠以“最大”二字,但“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的说法,实际上也揭举出“道理”作为至上标准的警示之义。
尽管北宋史料中很少直接引述“道理最大”者,但君臣之间有关“道理”的议论却颇为不少。
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例是,元佑元年十二月,学士院出题策试馆职。
围绕苏轼所出策题,在朝廷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左司谏朱光庭、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等人认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要求惩戒“为臣不忠”之罪。
当时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出于对朋党相争的戒惕,并不赞成如此小题大做。
在傅尧俞、王岩叟等人的追问之下,她断然否认有偏袒苏轼之意,王岩叟等进而紧逼说
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于道理上断。
这句话虽然使高氏感受到压力,却未能结束殿廷上的激烈争辩,关键显然在于双方所认定、所执持的具体“道理”并不相同。
除去通常是指情由、事理,指具体原则之外,在有些场合下,“道理”用来指称带有根本性的法则。
例如宋太宗雍熙元年,
上尝语宰相曰:
“统制区夏自有道理。
若得其要,不为难事。
必先正其身,则孰敢不正?
若恣情放志,何以使人凛惧!
朕每自勉励,未尝少懈。
到北宋中期,这一类用法逐渐增多。
熙宁年间,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宗旨的新法迅疾推开,人才问题成为突出的“瓶颈”,
安石因言今文章之士不难得,有才智实识道理者至少。
上以为识道理者殆未见其人。
作为根本性法则的“道理”,不止是指治国之道。
熙宁五年五月,宋神宗与宰辅王安石、冯京等人讨论“一道德”之说,有一番关于“道理”的对话
王安石说道:
“臣观佛书,乃与经合。
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
神宗接着说:
“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
王安石:
“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
神宗:
“诚如此。
在这里,神宗口中的“道理”,实际上即是王安石所说的“理”。
这使我们联想到北宋中期儒家学者对于“道德性命之理”的探讨与追求,联想到“理”之内涵“由认知性向本体性升华”的过程。
蔡卞在讲到王安石的学术贡献时,说:
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
由汉迄唐,源流浸深。
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
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
初着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
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二程也曾明确地说
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
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
“元无少欠”的“道理”,无疑是至高无上的。
在北宋中期整体学术氛围的影响下,士大夫们逐渐倾向于将“道理”上升到“天理”层面予以阐发;
而“道理最大”说正是随着这一情势的发展,得到了重新解释。
南宋时对于“道理最大”的阐发
到南宋时,原本平实朴素的“道理最大”一语,被赋予了无尽的意义。
伴随理学的形成,出现了一个对于以往“文本”重新予以解读的过程。
南宋时的一些士大夫纷纷将自己迭出的新见、理解与创获,纳入到对于“祖宗圣训”的诠释体系中。
绍兴年间,李季可作《松窗百说》,其中的“朱五经”条,提及“道理最大”事,说
昔我太祖皇帝尝问忠献赵普曰:
“天下何者最大?
”普曰:
”上深以为然。
所以定天下垂后世者,莫不由之。
从沈括笔下的“上屡称善”到此时的“所以定天下垂后世者,莫不由之”,显然已经从总结祖宗经验的角度上了一个台阶。
宋孝宗乾道五年三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在进对中提到赵普与太祖关于“道理最大”的对话,并且说,“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忠。
”孝宗肯定说:
“固不当任私意。
”针对这番对话,纂辑《中兴两朝圣政》的留正等人发挥道
天下惟道理最大。
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
……寿皇圣帝因臣下论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
固不当任私意。
呜呼,尽之矣。
两年之后,孝宗再度提到祖宗时的这一说法
上曰:
“朕于听言之际,是则从之,非则违之,初无容心其间。
”
梁克家奏:
“天下事惟其是而已,是者,当于理之谓也。
上曰:
“然。
太祖问赵普云:
‘天下何者最大?
’普曰:
‘惟道理最大。
’朕尝三复斯言,以为祖宗时每事必问道理,夫焉得不治?
我们又看到“臣留正等曰”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天之所以能成造化之功者,以其无容心也。
是以生育肃杀自然有至理寓乎其间。
夫圣人之心亦如是而已。
举天下之事,是非利害杂然至乎其前,而吾一概以无心处之,方寸湛然,处处洞彻,天下之事焉往而不得其当哉!
臣知艺祖之心、寿皇之心即天之心也。
留正等人将赵普当年所说“道理”引申到“天心”、“至理”的高度,并且将此意加诸于“艺祖之心”,不知太祖君臣对此会做何感想。
若能起赵普于地下,精吏干而“寡学术”的他,在后人阐发的这番有关“道理最大”的“大道理”面前,恐怕要喟叹弗如了。
到南宋后期,以“天道”、“天理”为统贯,“道理最大”与“祈天永命”等说,成为当时儒家士大夫揭举以救国运的鲜明旗号。
自宁宗后期始,从朱熹、张栻的学生吴猎、曹彦约,再到真德秀、魏了翁、陈贵谊乃至包恢、牟子才、杨文仲等,几乎形成了宣扬“祈天永命”的“话语圈”。
真正能够反映其胆魄与识见的,是嘉定三年六月,时为秘书郎兼学士院权直的真德秀面对宁宗侃侃而论的一番话
臣闻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于人心、万世犹一日者,公议是也。
自有天地以来,虽甚无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坏人纪、敢为而弗顾者,能使公议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议不存于人心。
善乎先正刘安世之论曰:
公议即天道也。
天道未尝一日亡,顾所在何如耳!
从北宋的刘安世到南宋的真德秀等人,视“公议”、“人心”为“天道”的体现,这是“天道”观进步的反映。
而在其后南宋晚期的六十年中,“天道”“天理”讲说更盛,与此同时,士大夫胸中的这股浩然之气却日渐销蚀。
嘉定六年十月,真德秀向宁宗进“祈天永命六事”,说是
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极治矣,而召公作诰,一则曰祈天永命,二则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
盖天命靡常,圣贤所畏,而况今乎!
十二年后,宝庆元年六月,真德秀借奏对垂拱殿之机,力劝初即天子之位的宋理宗“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贤臣,结人心,为自立根本”。
针对霅川之变,他直截了当地批评理宗“处天伦之变未尽其道”,极论“三纲五常所以扶持天地”的道理,并且劝告皇帝“此既往之咎而臣犹有言者,欲陛下知此一大欠阙,自此益进圣学、益修圣德。
”他苦心孤诣地强调说
惟我祖宗继天立极,其于事亲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义。
故先朝名臣或以为家法最善,或以为大纲甚正,或以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
猗欤休哉!
圣子神孙所当兢兢保持而勿坠也。
绍定二年,真德秀为陈均所作纲目体史书《皇朝编年举要备要》作序,五年为《续通鉴长编要略》作序,都将书中所载“圣祖神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与“祈天永命、植国于千万祀”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史弥远死后,理宗希望对于家国颓势有所振饬,“厉精为治,信向真、魏”,以致时人“号端平为元佑”。
被召入朝的真德秀、魏了翁等人,怀着“老臣事少主”的“惓惓之心”,再三再四申进“祈天永命”之说,重祭“祖宗家法”大旗。
“道理最大”作为“家法最善”之组成部分,继而频频出现于臣僚章奏、士大夫议论之中。
淳佑间,时为侍左郎官的徐元杰上奏,讲到其师真德秀教授的“君臣交际之礼”,并且说
陛下为四海亿兆万姓纲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纲常者也。
《孝经》曰:
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况有道之世,市议道谤,其可咈哉!
天地间惟道理最大,人言之所以必争者,顾惜此耳。
淳佑九年,吴渊在其为《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所作之序中称
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
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
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内兴起未艾也。
这一说法表述比较平易,而对“道理最大”说的政治估价却相当之高,实际上是视该说为赵宋开国致治的基调了。
与褒崇理学的思想氛围相呼应,南宋后期的儒者致力于阐发“道理最大”说中的义理含意。
淳佑七年,前兴国军军学教授刘实甫在为《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所作序文中强调说
尝拜观艺祖皇帝问赵普曰:
”普对曰:
”此尧舜之问,稷契之对也。
我朝所以理学昌明者,其论已兆于此。
而国家延洪之休所以超轶汉唐者,徒恃有此义理耳。
舍义理而言治,非知言者也。
他努力开掘这番问答中深奥的义理内涵,认定北宋初年的“道理最大”说为宋朝“理学昌明”之朕兆,并且将“国家延洪之休所以超轶汉唐”的原因归结至此。
宝佑元年,姚勉在其廷对中写道
天开我朝,道统复续。
艺祖皇帝问赵普曰:
”此言一立,气感类从;
五星聚奎,异人间出:
有濂溪周惇颐倡其始,有河南程颢程颐衍其流,有关西张载翼其派;
南渡以来,有朱熹以推广之,有张栻以讲明之。
于是天下之士亦略闻古圣人之所谓道矣。
姚勉从宋初“道理最大”的对答中紬绎出有宋之“道统”谱系,勾勒出覆盖天下之道学流派。
这种搜源探流、由此及彼的功夫确实令人钦佩,而他自己也凭藉这份殿试对策获取为当年状元。
景定五年理宗去世后,议谥于朝堂,群臣斟酌再三,最后选定谥曰“理”。
据周密说,
盖以圣性崇尚理学,而天下道理最大。
于是人无间言。
掩映于“道理最大”这面旌旗背后的,其实是士大夫们的痛苦与无奈。
宋季士风平弱芜浅,理学门徒往往囿于“正心”“诚意”而不能针对时事有确当发明。
痛感国势日去,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所谓“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追求,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其局限性暴露无遗。
“道理最大”之说三番四复挂于口头,却终究未能寻得治国治世抵御外侮之“道理”。
咸淳四年十月,度宗临轩策试进士,试题中先声说一番“自身而家,自家而国”、“天下虽大,治之在道;
四海虽广,治之任心”的道理,继而说
惟我艺祖以“何物最大”质之元臣,上接三圣传心之印;
洞开诸门,“正如我心”,用肇造区夏,丕式于后之人。
朕获承至尊休德,乃念为君之难。
次年初,时任嘉兴知府的文及翁作《传贻书院记》,其中一段,几乎是照搬了数月前的进士策题
有宋受命,肇基立极,艺祖皇帝一日洞开诸门,曰:
“此如我心,少有邪曲。
”人皆见之。
识者谓得三圣传心之妙。
又一日,问“世间何物最大?
”时元臣对以“道理最大”。
识者谓开万世理学之原。
猗欤盛哉!
从“洞开诸门”说到“三圣传心”,进而推演到帝王之“正心”——这一阐述思路,究其实际,是从南宋大儒朱熹处得来。
朱熹本人似乎从未直接提及“道理最大”一说,即便是在他纂辑于孝宗乾道年间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之前集卷一《韩忠献王赵普》目下,虽然肯定赵普“谋虑深长”、“国初大臣鲜能及者”,却也未及“道理最大”事。
不过,就太祖“洞开重门”且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事,他倒曾经向孝宗皇帝抒发感慨说
臣窃谓太祖皇帝不为文字言语之学,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与尧舜之心如合符节。
此其所以肇造区夏而垂裕无疆也。
伏惟陛下远稽前圣,而近以皇祖之训为法,则一心克正而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
曾经游于朱子之门的滕珙,将上引这番话概括为“论太祖正心之法”。
而晚宋诸儒进而将“何物最大”与“太祖正心之法”联系起来,甚至将“道理最大”拔高到“开万世理学之原”,则可以说是不大不小的一项发明。
把“道理最大”与“正君心”合为一体的认识,影响到后代许多儒生。
明人魏校《庄渠遗书》卷二《皇极讲义》中,有这样一段平白通俗的解释
天下惟君最尊,惟道理最大。
君不能尽这道理,天下何所宗名?
虽至尊,实与凡庶何异?
故周公曰:
“其惟王位在德元”。
必须君心略无偏邪,行出来的事事尽善,大中至正,更无以加,与天下做个样子。
这一段话,讲得堂堂正正,气势凛然。
不像南宋那般“南渡末流”,尽管忧国忧民,言谈举止却充溢着一派“冗沓腐滥之气”。
南宋覆亡前后,“道理最大”的调子还一直在弹。
黄应龙上奏,围绕着“道理最大”一说,从太祖到理宗、度宗,拉出一脉“上继尧舜”的道统
自艺祖皇帝开辟宇宙以来,一以“道理最大”为立治之本。
陛下熙明之学,亲得理宗皇帝之的传,道统大原,上继尧舜……
咸淳十年王义山在为稼村书院所拟秋试策题中,着意梳理出有宋一朝理学发展之脉络,说道:
本朝自“道理最大”之言发于开国之元臣,而吾道之脉有所寄。
迨至仁祖,宋兴已七十馀年矣,而斯道之在天下,既衍而昌,既沃而光,日以鸿厖。
自天圣五年赐进士《中庸》篇、宝元元年赐进士《大学》篇,而后周程张之学始出。
盛哉,仁祖之有功于斯道也!
迨至理皇,又从而表章硕大之,而理学又大明于天下……理学一源固得于我祖宗阐明之功……
就是这位王义山,在入元之后,作《宋史类纂》一书,其自序中说
尝谓洙泗而下,理学之粹惟宋朝为盛。
自国初“道理最大”之言一发,至仁宗天圣四年赐新进士《大学》篇,于后又与《中庸》间赐,着为式。
自是而天下士始知有庸、学。
厥后周程诸子出焉,至晦翁而集大成。
理学遂大明于天下后世。
对于天圣年间“御赐”《大学》、《中庸》篇的叙述,王义山本人前后并非一致,但这并不妨碍他将“道理最大”追溯为“吾道”之源,不妨碍他阐明“理学遂大明于天下后世”的脉络。
南宋灭国之后,像王义山、文及翁这样自视为“宋人”、或者至少有“先朝”情结的入元遗民,仍然念念不忘“道理最大”之说。
至元二十八年,文及翁为淳佑十年进士第一的方逢辰撰写墓志铭,其铭文曰
猗欤先朝,以儒立国;
道理最大,继天立极。
於穆理皇,道久化成;
观乎人文,理学大明。
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后官至翰林学士的吴澄,在其《无极太极说》中,将“道理”与“太极”联系起来
道者,天地万物之极也。
……曰太极者,盖曰此极乃甚大之极。
……此天地万物之极,极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极。
邵子曰:
道为太极。
太祖问曰:
“何物最大?
”答者曰:
”其斯之谓欤?
从各个方面对于“道理最大”予以发挥的例子还有不少。
而且,除去士大夫讲义、奏疏、策题、序跋、碑记之外,在南宋后期的制诏命词乃至往来笺启中,也不时出现“道理最大”的说法。
君臣之间的一段简单对话被如此高频率地重复,在宋代的历史上恐怕并不多见。
二、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据信出现于北宋初年太祖时期的“道理最大”一说,直至南宋时期才有了日益广泛的传布与流行。
伴随着理学骎骎乎日盛的过程,这一说法蕴涵的意义被充分地开掘出来。
太祖君臣对话究竟出自什么样的具体背景之下,本已不易考明;
而可以确知的是,这一说法与北宋立国以来为政施治理性化的趋势相吻合,并且因此而被宋人认定为赵宋“祖宗之法”的内容。
就这一方面而言,“道理最大”说与宋太祖誓碑说颇有类同之处。
我们今天的讨论,不是要对此说证实或是证伪,而是希望从这一具体说法出发,探讨赵宋“祖宗之法”、祖宗形象的塑造形成。
赵宋的“祖宗之法”,事实上是指宋朝的“列祖列宗”建立与维持的一些轨范。
随着宋代历史的推移,对于“祖宗之法”的重新发掘、对于“祖宗”形象的再描绘与再定位也表露得日益明显。
也就是说,“祖宗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祖宗”形象实际上处于不断被重新解释与再度塑造的过程之中。
在这种重新诠释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当时群体性的政治取向。
所谓“祖宗之法”由历代的举措决策积淀而成,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列祖列宗的所有举措都被不加甄别地包容在内,而是根据现实需要,择取“祖宗故事可行者”予以认定。
经过后世判别筛选的方针原则,被层层叠叠地融汇其中。
南宋吕中在其《宋大事记讲义》中曾经说
创业之君,后世所视以为轨范也。
惟其如此,有志于天下国家的宋代士大夫们尤其注意于刻划、维护“创业之君”的形象。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魏国忠献王韩琦》目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求质于公,公指数事:
其一,太祖惑一宫鬟,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
公曰:
“此岂可为万世法?
己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
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
”遂去此等数事。
守道服其清识。
这样的取舍润饰其实不是为了太祖本人。
“此岂可为万世法”一句,以反诘的方式清楚地揭示出《圣政录》、《宝训》等着述的编纂用意。
《圣政录》《宝训》所记录的,是宋朝自太祖以来历代君主的“圣政嘉言皇猷美事”,是供后世帝王直接汲取借鉴的本朝经验;
其编纂目的在于“履祖宗之圣迹,以兴太平”,就其性质而言,可以说是因应治国需求的“帝王学教材”。
赵宋一朝对于《圣政录》《宝训》的纂修不可谓不重视,而李焘在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注文中,却曾多次指出《圣政录》及《宝训》中记载年代、官名、事件不确切的问题,并且概括说:
“《宝训》于年月先后,或多不得其实”“《宝训》润文,遂失事实耳”。
这类问题的出现,从一侧面表明,《圣政录》和《宝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记录,而是重在政治导向的“祖宗嘉言懿行录”;
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流布祖宗朝的“盛美之事”,传授治国章法,以垂范后世。
“为万世法”,无疑是当时具备强烈历史责任感的士大夫们追求的目标。
在这样正义而神圣的目标之下,拣选祖宗言行、塑造可供仿效的祖宗形象显然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宋大事记讲义》卷四《真宗皇帝·
圣学、经筵》目下的“讲义”中有这样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