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王名篇《走窑汉》及点评Word下载.docx
《小说王名篇《走窑汉》及点评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小说王名篇《走窑汉》及点评Word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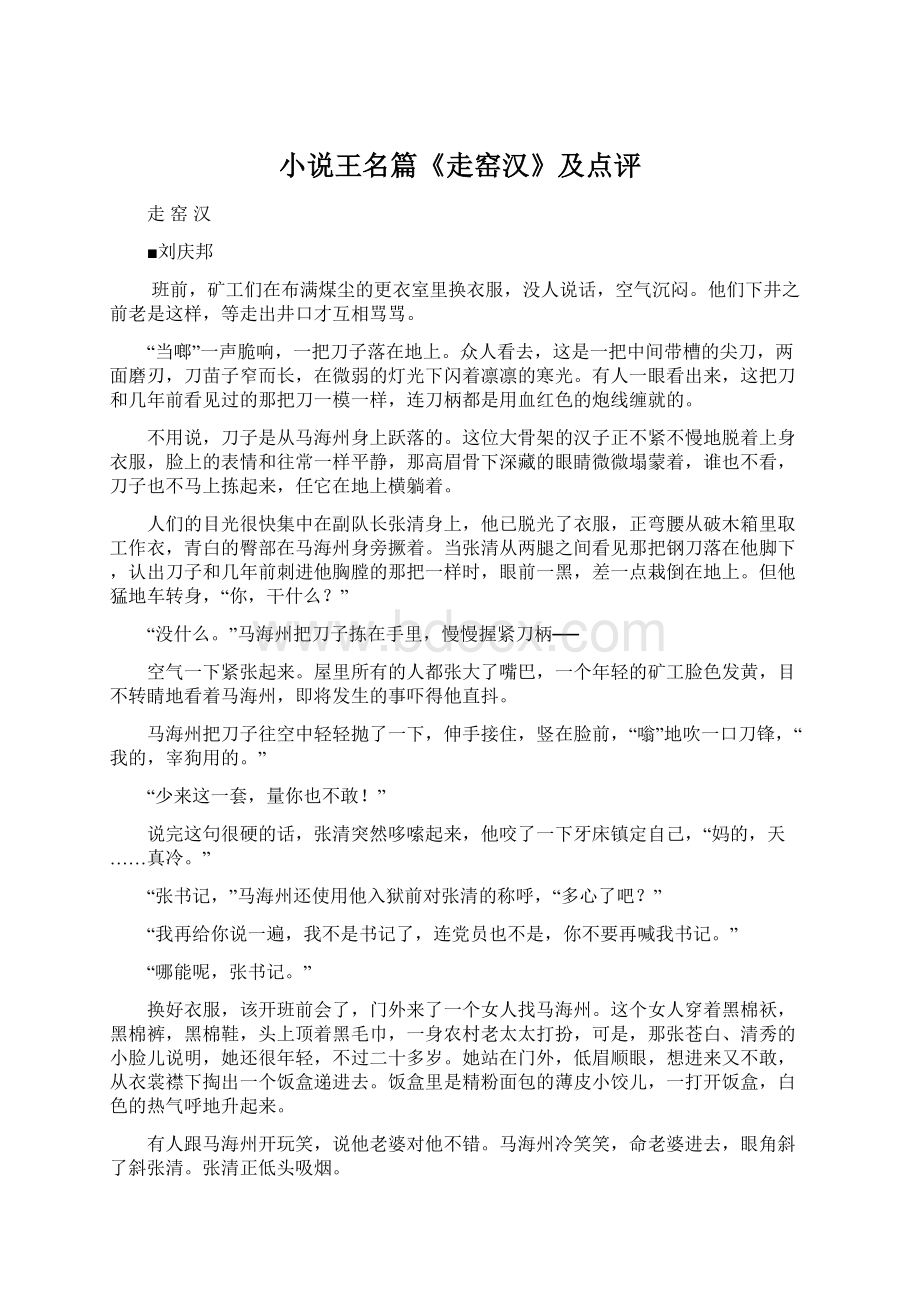
门外下起了大雪,雪片子上下翻飞。
马海州胡乱吃了几个饺子,就把饭盒盖上,放在一边,拿出一盒尚未开封的过滤嘴香烟,对老婆说:
“小蛾,给师傅们散。
小蛾把烟一一送到众人面前,唯独没给张清。
“为啥不给张书记?
”马海州问。
“不要不要,我有,吸着哩。
”张清说。
小蛾看看男人,站着没动。
“听见没有?
”马海州提高了嗓门,“为啥不给张书记,他不是要给你迁户口吗!
小蛾眼里马上涌出了泪水。
但她很快擦干,一把揪掉头上的黑毛巾,往张清面前走去,“张书记,吸烟。
张清刚要接,她一低手,把烟扔在地上,白白的烟卷立时滚上一层煤尘。
张清不开班前会了,站起来,左右裹了裹衣服,先自走向井口。
马海州紧紧跟在他身后。
马海州干活是没说的。
几年的监禁生活,他那高超的采煤手艺不但没有生疏,恰恰相反,他所在的劳改场所也是一座煤矿,只不过是用高墙、电网、枪和狗围起来画地为牢罢了。
如果眼下这座煤矿曾使他当过胸佩红花的青年突击手的话,那么,电网内的煤矿却把他造就成一架采煤的机器。
他一到工作面,就扒掉上衣,露出马熊一样宽阔的脊背,拼命和煤壁过不去。
这个班所有的工人都愿意和马海州一个场子干活。
而马海州只想在张清身边干,弄得张清每个班都转换几个地方。
在这熄灭矿灯就漆黑一团的井下,一双恶狠狠的目光老盯着他,他不能不防备。
打马海州突然提前释放(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救出过一个掉进冰窟窿的儿童)回来,并坚决要求回这个队,他就感到一种潜在的危险,时时威胁着他的生命。
他开始做噩梦,时常半夜里惊醒。
为此,他要求调换一个班,可第二天,马海州就到这个班来了。
马海州那一天到晚紧闭的嘴巴,那神情中严肃的宁静和目光里流露出的不可侵犯的威严,使队里每一个领导都不敢和他打别。
取代张清的那位党支部书记每次开会都表扬他,并准备让他当失足青年转变的典型,马海州用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手势拒绝了。
班中休息时,马海州拖着一把尖镐出来了。
别的矿工各自找地方坐下、躺下,只有两个人还在游动,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落脚处。
一个是身影高大的马海州,另一个是张清。
张清刚要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会儿,马海州就一晃一晃地过来了,几次都是这样,简直像甩不掉的影子。
张清极度烦躁不安,他借一个事情到调车场去了。
马海州瞅着那盏跳荡的灯光在巷道尽头消失,才离开人群,单独找一个地方坐下。
他熄灭矿灯,黑暗中摸到一块坚硬的煤,在手里一点一点捻碎。
那边的人见马海州不在跟前,开始讲女人。
他们每个人都装有一肚子女人的故事,而且津津乐道。
矿工们常年在沉闷、阴暗的坑道里劳作,对于他们来说,最值得珍爱的莫过于女人,而最可恨的是,当他们在地底下挥洒汗水时,人家在地面勾引他们的老婆,说实在的,谁都有这个担心。
因此,他们对这方面的事特别敏感,特别关注。
哪个灯房姑娘品行不端,谁家老婆偷汉,某干部是玩弄女性的老手,镇上那个“白母猪”最近涨价了,等等,每天都有新鲜的话题,而且谈起来兴高采烈,一阵阵发笑。
一记猛烈的金属撞击声,使他们的说笑戛然而止。
有人听出来,这是尖利的镐头劈在溜子槽上发出的声响,并很快作出判断,这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干的,用意不言自明。
于是,巷道里静下来了,静得能听见各自的心跳,谁也不再提及“女人”二字。
如果说这是工友们出于对马海州的惧怕心理,也不完全对。
不错,他虽然识字很少,但头脑清晰,遇事有独到见解,吐口唾沫一个坑,有一种使人服从的威力。
可是,他对每一个工人兄弟都很温和,劳改释放回来更是如此,连一句重话都不说,生怕伤了谁。
一次,一个叫小四的矿工,家里失火,烧得只剩下一口水缸。
老婆带着孩子来了,哭哭啼啼,要求矿上救济。
救济款还没批下来,马海州来了,一把甩给小四二百块钱。
小四不要。
马海州说:
“怎么,看不起我?
小四愣了一下,“马哥,我给你磕头!
”他正要下跪,马海州转身走了。
钱,是小蛾从家里带来的。
出了那件见不得人的事以后,小蛾本想一死了之,但是,马海州在被戴上手铐、抓进囚车时,大声对藏在一棵树后哭泣的她喊:
“田小蛾,不许你死!
……”
小蛾受的羞辱还用说吗!
回到家里,她仿佛成了一只妖魔鬼怪,连三岁的孩子都朝她扔瓦块。
大年初一,她日上三竿才起床开门,却发现门鼻上挂着一只烂帮漏底的布鞋。
她关起门来把布鞋烧了,第二天又被人挂上一只……凡此种种,小蛾都默默地忍受下来了,她耳边时时回响起丈夫在囚车腾起的烟尘中抛过来的那句话。
一年四季,风雪雨霜,她向自己的那一份责任田里洒着汗水,一季又一季收获着庄稼。
土地不嫌弃她,不辜负她,她打的粮食并不比别人少,然而,人们斜眼看见,这个女人身上的补丁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瘦弱了。
当她接到男人的电报匆匆赶来矿山时,给马海州带来一个砖头似的布包,打开来看,里面全是大大小小的票子。
可是,马海州并不稀罕,他冷冷地看了小蛾半天,说:
“我以为你早不在人世了呢。
小蛾的嘴角抽搐着,抽搐着,说:
“我现在就……去……死!
”说罢,咬着下唇,一摆头就往外跑。
马海州一把抱住了她,抱得紧紧的。
小两口都哭了,泪水滚滚而下。
接下去,人们在井口、电影院、自由市场等地方,时不时地看见这个浑身皂衣的女人。
而这个修女似的女人不论到哪里,必定有马海州陪伴。
他俩相依相傍,十分亲热,像是要补偿失去的生活,再也不愿分离。
细心的人还发现,凡是这两口踪迹所至之处,不远的地方必定还有一个张清。
换句话说,张清走到哪里,他俩就出现在哪里。
有人跟张清开玩笑:
“哎,你的两个保镖不错呀,够忠于你的。
张清的脸黑了:
“哼,白看看吧,敢动我一根毫毛试试!
下班了,工人们急着洗热水澡,三下两下扯光衣服,嘻哈着,踮着脚尖,猴子似的往热气腾腾的澡堂里钻。
张清出了井口,一闪身躲进调度室里去了。
每天,那个讨厌的家伙,老是和他在一个池子里洗澡,老是瞅他身上那块地方,他简直烦透了。
今天,他要等别人都洗完再进去。
张清走进澡堂时,几乎没人了,黑乎乎的水面上漂浮着缕缕白气,水也不大热了。
他左右看看,确认那个人走了,才慢慢下进池子里,把整个身子淹到脖子处。
靠池边闭上眼睛,长长出了一口气。
忽听有人重重地下水,张清不由得心里一惊,凭感觉,他知道又是那个姓马的,他妈的,太可恶了。
尽管他闭着眼睛,仍“看见”了马海州那张开的鼻孔,河马一样的下腭,和深藏在眉骨下面充满敌意的目光。
他决计不睁开眼,也坐着不动。
水池里静下来了,连水的波动也感觉不到,怎么回事?
张清睁开一点眼缝,看见马海州也像他一样在对面靠着。
他心里十分焦躁,恨不得扑过去扼死他。
可他明白,自己绝不是马海州的对手。
管澡堂的老工人催他们:
“哎,该放水了,还泡?
哩,再泡就软了!
张清说:
“你诈唬啥,老子今天不走了!
老工人笑了,“是张队长呀,我听说人家要做你的活儿,你小子没多少蹦?
了。
张清站起来,拍了一下胸脯,“姓张的拔根汗毛,竖根旗杆,想打我的黑枪,没那么容易!
”他瞥了一眼马海州。
马海州也站起来了,水中煤尘的沉淀使他的汗毛变得又粗又长,他漫不经心地擦着,两眼直视张清左胸,那里有一块伤疤。
伤疤又开始痉挛地抽动。
那可怕的一幕在张清脑子里重新晃过之后,他不由得打一个寒战,伤疤下面也隐隐作疼。
他转过身去。
可是,马海州很快又站在他面前了,两眼直直地盯着那块伤疤,像是在欣赏他所创作的一幅杰作。
张清不洗了,他咬着牙,把拳头握起来晃着,做出一种类似疯狂的举动。
马海州也不洗了,他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门外,正下着雪,一片灰蒙蒙的。
张清走出更衣室,见门口立着一团黑影,黑影说:
“张书记……”
“见鬼!
”张清逃也似的走了。
马海州喊:
“小蛾,过来!
张清身后马上响起宽厚的嘴巴嘬在脸蛋上的啵啵声。
回到家里,小蛾给男人端菜斟酒。
男人低头喝起来,她坐床沿往外看着。
天黑了,窗外一片清冷的雪光。
这是单身职工宿舍楼四层的一间屋,门上装的是暗锁,他们的蜜月就是在这间屋度过的。
当时,他们幸福得差不多每天都要落泪。
是呀,全队的工人谁不夸马海州的小女人长得漂亮,粗腿,胖手,细腰,白脸儿,特别是那一双眼睛,纯洁清澈,露出孩子般的稚气和娇憨,令马海州爱不释手。
那些天,不到临下井的前一刻,马海州绝不离开妻子,匆匆离去,往往半道上又匆匆返回,推推门看是否真的锁上了。
在他下井干活时,不许小蛾出屋,无论谁叫门也不许开,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出了那件让马海州一想起来就心如刀搅的事。
出事那天,他们的蜜月刚刚度过一半。
如今,他们又住进了这间屋子。
现任党支部书记出于好心,打算给他另调一间屋,以免引起不愉快的回忆。
马海州平静地说:
“这样吧,如果队里住房有困难,我们就睡在这间屋门口的楼道里……”
酒饭一毕,马海州仰躺在床上,两眼直愣愣地瞅了一阵屋顶,又让小蛾讲那件事情的经过。
那件事的始末小蛾已经复述过不知多少遍了。
可马海州还让她讲,而且越问越细,连那个坏蛋的两只手各放在什么部位都问到了。
小蛾不敢不讲。
无非是那个狗日的(小蛾语)怎样拿薄铁片捅开了暗锁,怎样谎称马海州把钥匙交给了他,还说每个工人的老婆来了都要做贡献,谁的贡献大就给谁迁户口,等等。
小蛾讲完,马海州大发脾气,质问小蛾:
“谁让你讲这些的!
”……于是两口子就哭,哭罢就疯狂地亲热,尔后,小屋陷入了沉寂的深井。
可是过不了多大一会儿,两口子就衣着整齐地出来了,像是去走亲戚。
他们双双来到二楼张清门口,粗的声音:
“张书记!
细的声音:
他俩一递一句喊着,节奏把握得很好,显得不急不躁,彬彬有礼。
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
楼后有人说话:
“张队长,哎,哎,慢点儿,怎么从这儿下来啦?
地震啦?
没人答话。
张清找到矿长,提出回家探亲一个月。
矿长不准。
他跟矿长发火,无用。
第二天下井,张清自己包一个场子,闷头闷脑地干起来。
马海州要的采煤场子和他紧挨着。
张清往上挖,马海州也往上挖。
按井下的说法,一个跑,一个撵。
两根矿灯的光柱不时地碰在一起。
张清的场子冒顶了,破碎的天顶突然间倾泻而下。
他刚要撤出来,觉得两腿很沉,像陷进了淤泥河,怎么也拔不动。
接着,身子也被一些强有力的东西团团挤住,这些东西在迅速上移,眼看要勒紧他的胸口和喉咙,“活埋!
”这个可怕的念头在脑子里闪过之后,他把两手举起来,拼命扭动身子,无效。
大声呼救,溜子的轰鸣盖过了他的声音。
顶板还在冒落,面对这灭顶之灾,他无能为力,只有等死。
“天哪!
这……这是怎么啦?
”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一束灯光指过来,在他那扭曲的脸上停住。
他知道,这是马海州的灯。
从刚一冒顶的那一瞬间起,说不定姓马的就发现了,但这个狠毒的家伙绝不会救他,他妈的,可遂了你的心了,你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想到这些,他睁开眼睛,多少天来第一次朝马海州直视过去,占有了死亡仿佛使他突然得到了优势,撇紧的嘴角露出高傲和蔑视。
他看见,马海州的眼皮向下塌蒙着,鳄鱼皮一样粗糙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装没看见,到时候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没那么便宜!
他正要大声喊马海州的名字,“噼里啪啦”又一阵碎矸碎煤落下来,压死他的手臂,拥住他的脖子,他喊不出来了。
尘雾中,他见马海州扑上来了,随着一张扒锨在他身旁左右猛扒,碎煤碎矸退下去了,他的胸部和手臂露了出来。
当他意识到马海州要干什么,两只手突然抓住扒锨,死死不放,“你……别管我……让我……”
“啪!
”马海州扫脸抽了他一巴掌。
他一愣神,手松开了。
马海州又扒了几下,两手掐住他的两个胳膊窝,一使劲,把他拽了出来。
他的裤子被拽烂了,两只深筒胶靴也留在了冒落物里,矸石划破了他的腿,鲜血流出来。
但他的命保住了。
就在马海州把他拽出来的一刹那间,一块巨大的盘石落下来,砸在他刚才站立的地方,一声闷响,烟尘腾起,几根钢梁铁柱顿时化为乌有。
张清浑身抖起来了,他双手抱住马海州的一只胳膊,扑通跪倒,声泪俱下地说:
“海州兄弟,你救了我的命,我……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
马海州往下看了他一会儿,笑笑,厌恶地把胳膊一甩,转身朝工作面下头走去。
马海州救了张清的事很快在矿上传开了,人们说张清走运,并得出结论,说马海州根本没有害张清的意思,他们都认为,张清应该重重地感谢马海州,趁这个机会和解和解,说不定还能成为好朋友呢。
这天晚间,张清提了几瓶好酒,请现任支部书记陪同,到马海州屋里致谢。
门开了,马海州堵在门口,问他们有什么事。
小蛾正脸朝里坐在床沿上哭,小肩膀一抽一抽的。
听见有人来,马上倒在床上,拉开被子蒙住头。
这个女人更瘦弱了。
支部书记说了一大堆表扬马海州的话。
“您弄错了,我谁也没救过。
支部书记示意张清把酒提进去。
“海州兄弟……”
“出去!
”马海州往门外一指。
张清硬着头皮把酒放在一个方凳上。
“小蛾!
”马海州喊。
小蛾没动。
“小蛾,起来,看谁来啦!
小蛾“呼隆”跳下床,乌发往后一甩,两眼谁也不看,径直走到方凳前,抱起捆在一起的酒瓶子,斜举过肩,使劲朝门外摔去,“嘭”,酒瓶全碎,瓶碴飞溅,酒流了一地。
做完这些,小蛾又蒙头躺在床上。
支部书记愣了一下,赶紧上前,双手笼住马海州的双肩,推他坐下,说:
“小马,你听我说,听我说……”
马海州纹丝不动,两眼盯着张清。
张清低下头,走到门外,他踩到一块瓶碴子,发出了声响,他一惊,打了个前跌。
在同一天晚上,马海州和田小蛾又去叫张清的门。
张清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放他们进去,马海州说:
“张书记,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听说这玩艺儿能当钥匙用,不知怎么个用法?
”他拿出一个薄铁片伸在张清脸前。
这正是张清使用了不知多少次的那种铁片。
他的脸黄了,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退,退,但他突然站住,拳头握起来说:
“姓马的,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说吧!
马海州把低头站着的小蛾轻轻揽在怀里,胳膊搭在她脖子上,大手在鼓起的乳房上抓着,说:
“我想跟书记学点见识。
张清抄起一把椅子,举过头顶――
小蛾赶紧转身,张开双臂护住男人,觉得不妥,要冲过去夺椅子。
马海州拉住她,闭着嘴巴笑了一下。
张清把椅子打在暖水瓶上了,打在电话机上了,打在柜子上了,他像发了疯一样,抡开椅子,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打得稀烂。
尔后一头扑在床上“哞哞”地哭起来。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这班的人在更衣室里换好了衣服,却迟迟不见副队长张清来开班前会。
有人猜测,他可能到医院看病去了,因为近日他举止有些不正常,老是犯愣。
有人见他刚买回一碗饭,一口未吃就扣在泔水缸里了。
还有人在他背后无意中咳嗽了一声,他竟吓得一下跪在地上……
突然,井口方向传来一阵救护车凄厉的尖叫声。
一个矿工跑来报告说:
“张清跳窑了!
大家一惊。
窑深百丈,摔下去必定粉身碎骨,救护车用不着了。
人们的目光集中在马海州脸上。
马海州的表情和往常一样平静,高眉骨下深藏的眼睛微微塌蒙着,谁也不看。
矿工们纷纷朝井口跑去,要看个究竟。
马海州坐着没动。
不一会儿,那个叫小四的矿工跑来,脸色煞白地对马海州说,小蛾跳楼了,她是从四楼那间宿舍的窗口跳下去的,已摔得脑浆迸裂。
马海州呼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了。
原刊《北京文学》1985年第9期
■点评
这活儿让他做绝了
这算什么故事?
分明是法律观照的对象。
矿工马海州为报妻子被奸污之仇,用刀刺了队长张清,为此坐了几年牢。
法律行使了自己的权威,履行了它的公道。
但是人的灵魂呢?
法律能因此消除它的不安宁吗?
一条刀疤和数年监狱生活不仅给这对冤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而且也使得各自的神经变得更敏感、更微妙、更复杂。
何况在他们中间还时时夹着马海州的妻子小娥的身影,这柔弱的女性,她那承受一切痛苦的神态,足以使读者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
于是,小说行使了其艺术光照的魅力。
《走窑汉》给人以激动,心弦一直是绷得紧紧的,读者时时被一种预感缠绕着,始终感到要发生什么,但始终又担心要发生什么。
短短的篇章,它表现了诸多人的情与性:
爱情、名誉、耻辱、无耻、悲痛、复仇、恐惧、心绪的郁结、忏悔、绝望、莫名而无尽的担忧、希望而又失望的折磨、甚至生与死,在这场灵魂的冲突和较量中什么都有了。
这位不怎么出名的作者,这篇不怎么出名的小说写得太棒了!
要解释这样一种灵与肉的空隙“黑洞”是不可能的,它只能乞求于艺术的描写,“而且还是一鳞半爪、不系统的描写。
马海州那一天到晚“紧闭的嘴巴、严肃宁静的神情、不可侵犯的威严”的背后混杂着血与泪的复仇心理。
他所背负的耻辱值得同情,他的刚毅、勇气和厉害的谋算值得佩服,但他走向复仇的每一步的背后也不乏残酷,特别在他救活张清的背后使人感到一种人性的毁灭。
马海州的一举一动,一眼一神,一招一式,甚至他没有表情的沉默,都使张清和小娥的精神处在极其敏感的高峰状态。
整个阅读过程,我们也处在这样一种高峰状态。
这两年短篇不怎么景气,而刘庆邦却把《走窑汉》这“活儿”做绝了!
请抽空读一读,它不会超过八千字。
人性之美与生命之痛
――关于刘庆邦《走窑汉》
陈福民■
《走窑汉》是为刘庆邦赢得声誉的早期代表作,或者换言之,文坛是通过《走窑汉》认识和把握刘庆邦的小说创作的。
尽管庆邦在这二十多年来已经大步向前走了,但一直以来,《走窑汉》都是专属庆邦的最重要的“标签”。
这是有道理的。
这篇写于1985年的短篇小说,在某些技术方面,显然得益于那个时代蔚然兴起的先锋小说实验潮流,这使得刘庆邦的传统煤矿、煤窑题材创作鲜明地区别和优越于同类作家的同类写作。
同时,《走窑汉》继承并光大了严肃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及其性格上,在人性深度的挖掘上,在生活真实的提炼与表现上,都达到了令人难忘的程度。
需要记住的是,1985年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一方面,各种先锋实验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借鉴,另一方面,各种新颖震撼的思想观念铺天盖地,这两个因素给文学写作插上了飞翔的双翼。
《走窑汉》的诞生,在这个意义上是恰逢其时的。
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关系设置得并不复杂。
矿工马海州因为自己的年轻媳妇小蛾被干部张清侮辱,持刀伤人后入狱,由于机缘巧合救人立功而提前出狱回到矿上。
这时的干部张清也下放到矿工班组,马海州再次启动了他的寻仇报复计划。
小说结尾,张清因不堪压力和恐惧而崩溃自杀。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仇人死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小蛾在闻知这个消息后,也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时隔二十五年,我至今仍然无法忘记当初阅读这个悲惨的故事所带给我的强烈痛感和压抑!
关于窑工生存的艰难,关于他们如荒漠般的生活资料的匮乏,关于隐藏在他们冷漠坚硬背后丰富火热的精神世界,所有这些,都是庆邦通过《走窑汉》告诉我们的。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庆邦通过什么方式来讲述这些。
在这篇不到七千字的短篇小说中,庆邦所传达和呈现出来的意蕴可谓富饶精深之至!
就人物性格而言,马海州坚定的复仇意志,张清面对寻仇的恐惧感和强作镇定,小蛾受辱后的艰难求生以及被作为复仇工具的双重侮辱,都在庆邦笔下栩栩如生。
就小说情节构思的推进而言,庆邦巧妙地运用了回叙、插叙等手法,使一个看似枯燥的故事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紧张感与压抑感贯穿了小说的始终。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庆邦对汉语的深深体味与出神入化的运用,他深知汉语“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真谛,从不使叙事语言一览无余,而是刻意收敛,只让情节与画面自己说话,在几乎是寂然无声中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故事。
在所有这些方面,庆邦都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树立了一个标杆,贡献良多。
“短篇王”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谁是《走窑汉》的中心人物?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有必要再次提起。
表面看来,马海州当然是这个悲剧故事出场最多的人物,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直隐在马海州身后的小蛾才是分量最重的中心人物。
在小蛾身上,庆邦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与感慨。
这个被侮辱的女人,含辛茹苦却善良坚韧,张清侮辱了她第一次,马海州从来没有考虑过她的真实感受,只是把她当做复仇的工具来使用,这是传统男权强加给她的双重侮辱。
如果说张清的崩溃自杀是一场人性自我较量的偶然结局,那么小蛾的自绝,则是人性觉醒后对这双重侮辱的自觉惨烈抗议。
她没有文化,不懂女权主义理论,但她却用生命的最后一跳,表达了对马海州复仇的不认同,并且显示了人性的光辉。
如果考虑到当时女权主义尚未形成风气,那么庆邦对小蛾这个人物的发现与刻画,就更加不同凡响。
庆邦多次表示,他是喜欢美好的事物的,但同时,他也不止一次地坦承“越写越痛”。
在人性之美与生命之痛的中间,庆邦饱受折磨,《走窑汉》则是这种写作的最好诠释。
但这种折磨是值得的,它是文学的义务。
因为这种折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庆邦未来的写作保持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