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论文集文档格式.docx
《鲁迅小说论文集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鲁迅小说论文集文档格式.docx(4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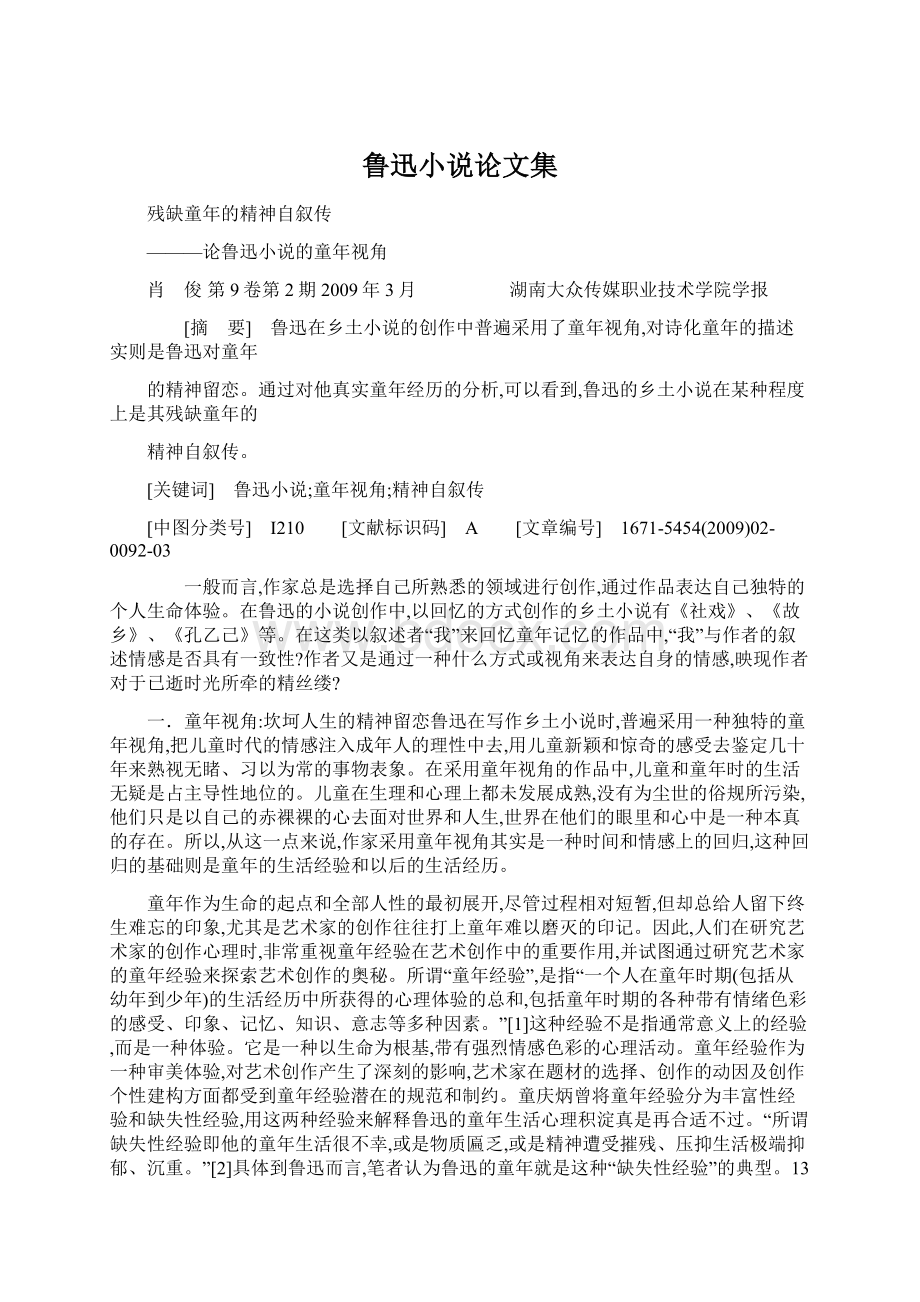
”[1]这种经验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经验,而是一种体验。
它是一种以生命为根基,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心理活动。
童年经验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艺术家在题材的选择、创作的动因及创作个性建构方面都受到童年经验潜在的规范和制约。
童庆炳曾将童年经验分为丰富性经验和缺失性经验,用这两种经验来解释鲁迅的童年生活心理积淀真是再合适不过。
“所谓缺失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不幸,或是物质匾乏,或是精神遭受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抑郁、沉重。
”[2]具体到鲁迅而言,笔者认为鲁迅的童年就是这种“缺失性经验”的典型。
13岁之前的鲁迅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的祖父是种地的农民鲁迅出生时,绍兴周家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曾经显赫一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儒文化意识贯穿着这个家的升沉起落。
鲁迅的先祖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
这时鲁迅的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日常生计绰绰有余。
周家讲究读书,周介孚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的雄心,所以在门上悬有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伯翰林的匾额。
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疼爱更不必说,在几个孩子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
所以,这时的鲁迅生活是非常幸福的。
但是,命运之神是残酷的。
在鲁迅13岁那年,一连串的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
首先,祖父周介孚为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后因科场案发而被捕入狱,鲁迅兄弟只好避难乡下。
接着父亲周伯宜久病不愈。
随之是长辈的怨恨、亲友的辱骂、同族的倾轧和世人的冷眼。
作为破落户的周家长房子孙,鲁迅过早地承受了世态炎凉的煎熬、摧残和人世变幻的惊奇、震惊。
从那时起,鲁迅已经不再有少年人任性的权利,生活不再允许他像其他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他的内心世界因家庭的变故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正如鲁迅所言:
“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
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不如了。
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3]“有谁从小康家庭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4]这样,命运之神先是给鲁迅一个宽裕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将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全部推到他的鼻子底下,鲁迅心中的伤痛可想而知,家庭变故所带来的缺失和坎坷,使他很早就在饱尝世态炎凉中认识了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卑劣。
这种缺失性经验也成为某种情结残留在鲁迅的潜意识深处,驱动或影响着他一生的创作活动,也促使他重新打量这个世界。
在这种情形下,在乡下度过的那些快乐日子就成为鲁迅苍凉世界的唯一亮色。
因为在这儿不仅可以免读深奥难懂的《四书》、《五经》,而且还可以同农村的孩子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一起,到密如蛛网的河上去划船、钓鱼、捕虾,欣赏带着点点渔火的水中夜景;
或到岸上放鹅、牧牛、摘罗汉豆,呼吸清新的空气……每逢村子里演社戏的时候,鲁迅就和小伙伴一起摇船来到半个在岸上、半个在湖里的戏台前面,看武生翻筋斗。
虽然那些日子是短暂的,但正因为它的短暂才显得弥足珍贵。
这些美好的回忆使鲁迅在精神上特别留恋故乡,以至于以后他在作品中反复描写故乡以及故乡的伙伴。
二、故乡重塑:
缺失童年的精神自叙
尽管童年经验会对作家以后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但必须清楚的是,作家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童年经验已经不是童年经验的本真状态,而是经过作家记忆的再组织和再创造。
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这种童年经验逐渐被社会化所压抑,成为一个神奇隐秘的世界,深深埋藏在个体心理最底层的黑色大陆中,只有特殊情境才能重新激活这种记忆。
小时侯,鲁迅家庭突遭变故,从此以后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再也找不到“平坦”两字。
带着童年些许美好但多数是苦涩的回忆,鲁迅上路了,他开始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奋斗。
但这奋斗却是一连串地受排挤、受迫害的过程。
鲁迅将这些经历形象地概括为“交华盖运”,所谓“华盖运”就是倒霉、事事碰钉子的意思。
事实的确如此。
1894年,鲁迅因祖父科场案逃出家门,寄居在乡下亲戚家,忍受着被看作“乞食者”的痛苦;
1898年,迫于族人的欺压和流言的中伤,他告别母亲,离开绍兴,只身一人去南京求学;
1902年,他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日本留学,前后在异邦共生活了7年;
1909年回国后,他为生计所迫而奔波于杭州、绍兴、南京等地;
1912年,他孤身一人随民国政府教育部迁到北京,寄居在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达7年之久;
1919年,鲁迅把全家接到北京生活,不久又因“兄弟失和”而被赶出八道湾寓所,此后在京城几度搬家迁居;
1926年,为了避开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和婚姻中的尴尬境地,鲁迅千里南下厦门,后因受厦门大学当局的排挤而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不久,他被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定居;
1927年,定居上海后,困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日军炮火的轰炸,他又一次次地避难于家门之外……其间的鲁迅亲眼目睹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迷茫与困惑、中国农村的日益凋敝、广大国民的麻木不仁与自己家庭的衰败和不和。
对于一个忧国忧民而又看不到出路的战斗者来说,他苦闷、仿徨、孤独、焦灼……面对令人绝望的现实,他不得不走向他的内心,转向并不十分温馨的童年,重拾些许温情的往事。
毕竟,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那段美好而又短暂的农村生活和那些活泼的小伙伴们,童真的友情瞬时间成了一片葱笼迷人的绿洲。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令人绝望的现实人生激起了鲁迅对童年故乡的追忆。
他之所以采取童年视角写作,是为了逃避或寻找精神的慰藉与内心的寓居。
弗罗伊德曾说:
“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
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
”[5]现实的不如意使鲁迅逃向了精神的乌托邦。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空间距离的拉大,他渐渐淡化了对故乡的负面印象,童年生活在他心中变得具有不可言喻的美丽。
当然,他这时描写的童年生活已经不是童年生活的本初,而是经记忆重塑后的童年生活。
于是,我们读到了《故乡》中的少年闰土。
看到了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地,也看到了闰土手捏钢叉向一匹碴尽力刺去;
读到了《社戏》中双喜和阿发的好客,看到他们在朦胧的月色中,乘着大白鱼似的航船,嗅着豆麦水草的清香去看社戏。
不过,在鲁迅的内心深处,温情的回忆却始终无法使他忘却故乡给予他的打击和耻辱,特别是他在故乡的失败经验、童年的缺失性经验使他在沉浸于儿时梦境的同时,多了一份清醒的理性意识。
于是,我们既看到了少年闰土的天真活泼,也看到了中年闰土的愚昧麻木,还看到了观赏“吃人”的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正在一步步地被周围的人同化。
此外,鲁迅还是一个“进化论”者。
他说: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的童年视角创作,一方面是为了寄托自己对祖国乃至人类社会的未来希望,只有没“吃人”的孩子们才有资格营构“真的人”的社会;
另一方面是为了用儿童的纯真与美好去对照成人社会中的种种丑恶与伪善,以此来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警醒,焕发出“救救孩子”的社会责任感与启蒙激情。
从这个意义上看,鲁迅采取童年视角创作不仅是一种逃避,而且是他用来启蒙的一种武器。
这就使鲁迅在进行童年视角创作时除了表现儿童的纯真无邪外,还多了一份清醒的理性审视,显得深刻而又有韵味。
三、复合视角:
现实人生的理想重构
鲁迅在运用童年视角创作的作品中,为什么都采用第一人称呢?
运用第一人称“我”来回顾往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
一是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二是被追忆的“我”的童年眼光。
这两种眼光可以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
他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
简言之,鲁迅运用童年视角的作品中普遍采用了复合视角:
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
儿童的心理和认知能力决定了他们对事物感知的新奇,在他们的眼中,可以看到一个独特而又清新的世界,流露出对世事本来面目的真情,也感受到身心受束缚折磨的痛苦,反馈出他们对生活和自然人性的正当要求。
《故乡》和《社戏》可以说是典型的从童年视角传达儿童心态的架构。
《故乡》采用20年后的“我”和20年前的“我”交替聚焦,往事的回忆使叙述成年的“我”转入童年经验的“我”,即儿童的“我”,这种视角的转换又使叙事状态真正进入儿童的本体世界。
在童年的“我”的眼中,少年闰土是紫色圆脸、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神奇少年,他懂得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瓜地刺碴,知道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而“我”自己只能生活在“只看见院里高墙上的四角天空”,心中充满无限向往。
这时的“我”充满了儿童式的忧郁和感伤,因环境的封闭,身心很容易纤弱,呈现病态,缺乏独立自由的意识,从而养成萎缩的人格。
而20年后呈现在成年的“我”的眼中却是苍凉萧瑟的故乡,先前美丽的景象一点也不复存在,记忆中神话般的英雄小闰土现在也变得麻木萎缩,被生计压得愁苦不堪,孩童时代那种美好的友谊也随着闰土的一声“老爷”而灰飞烟灭。
“我”现在对故乡现实的不满,实际上是在儿时感受的基础上发生的,因为在“我”的回忆中存储了儿时与少年闰土的关系。
如果没有儿时与闰土的交往和对故乡美好的印象,现在的“我”无论对闰土还是对故乡,也就无所谓满意与否了。
20多年后的“我”在自己的环境中已经不是一个儿童,但当他重返故乡时,在精神上也回到童年,他是以童年的回忆重新感受现在的故乡。
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对现在的故乡懵懂无知,像一个孩子一样不知该如何应付周围的人,像一个孩子一样对周围世界的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感到新奇和敏感。
正是因为这种新奇和敏感,“我”才能深刻地感受到闰土精神上的变化:
“我”眼中的少年闰土聪明勇敢,敢于月夜刺碴;
而中年闰土面对残酷的社会,却忍气吞声、含辛茹苦,成了一个木偶人;
少年闰土天真烂漫,与“我”相处,情真意切、亲密无间,而中年闰土见到“我”却“恭敬”地叫“老爷’;
少年闰土对生活充满美好向往,而中年闰土却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香炉和烛台。
作者正是通过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对比运用,向人们展示童年回忆与故乡现实的反差,使人们深刻地感受到故乡的现实,感受到封建枷锁对农民思想的毒害和束缚,感受到劳动农民世代反复着奴隶命运的主观原因。
总之,鲁迅在作品中总是采用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对比运用,成人视角流露出其一贯冷峻尖刻的批判锋芒,而儿童视角则传递出童年时代生命体验中的那份童趣,在单纯中寄寓无限,于雅朴中悄悄传递了那份深重永恒的儿童感情。
(责任编辑 张 敏)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现代心理学美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84.
[2]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
61.
[3] 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4]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15.
[5]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M].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鲁迅的童年经验与其小说创作中的深层叙事结构
徐顽强第17卷第6期天中学刊2002年12月
摘要:
鲁迅早期生活的压抑感及其记忆,构成了其童年经验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内容。
这种过于压抑的童年
经验不仅仅影响了鲁迅特定的创作心态与作品中的情绪基调,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其小说创作的取材与立意以及
深层叙事结构。
关键词:
鲁迅;
小说创作;
童年经验;
叙事结构
Abstract:
DepressionwasanimportantanddistinctcontentinthelifeofLUXun’schildhood.Theexperienceof
excessivedepressioninhisearlylifenotonlyinfluencedhisspecialmoodinthecreationandthekeynoteoffeelingin
hisworks,butalsothedrawofmaterialsandtheidealandthedeepstructureofnarrationinhiscreationofnovels.
Keywords:
Luxun;
creationofnovel;
childhoodexperience;
structureofnarration
中图分类号:
I210.9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261(2002)06-0051(03)
与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一样,鲁迅是说不尽的。
面对鲁迅的小说作品,就像面对着一块融铸着多种优良成分的合金,你不能不被其中那种质感极强的黑色基调所吸引。
那种基调在人们心理上所引起的感觉往往是沉郁的、压抑的,也是坚实、明澈、富于爆破力与穿透力的。
可以这么说,鲁迅的小说作品存在着一种情绪上的连贯性,仿佛它们全都随着同一股水流在移动。
作为读者,我们常常不能自己地受着这种忧郁的寂寞的水流的浸润和带动,渐渐沉入到鲁迅的小说世界里。
这是一个弥漫着浓烈的悲剧气息的世界,聚集着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压迫、病痛和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苦闷悲哀。
在这个世界里,季节往往是严冬寒秋,天气总是阴沉凄冷,时辰总在黄昏夜半,景色常常枯索苍凉;
而人物,不是形容枯槁,日见颓唐,便是每况愈下,穷苦潦倒,默默地走向死路。
鲁迅小说作品中这种浓烈的悲剧气息是与其对“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关切密不可分的。
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
自序》里曾经说他是“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1](P1427)。
实际上,鲁迅写的最多的也是最为成功的还是“下层社会的不幸”,还是各种各样的悲剧。
这些不幸不仅涉及到贫困、疾病和欺凌,而且最多的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它包括了多种多样不幸的死亡。
这里有不幸的夭折和自杀,悲惨的被杀和倒路而死,幼儿的病故和野兽的吞噬;
这里有死亡的仪式与生者的哀痛。
这一切,归根结底,是鲁迅童年经验对他创作心理的影响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因为叙事中起作用的更基本的力量是心理力量,是童年心理的发展决定着什么故事被讲述,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力量使然。
在探讨人的无意识方面卓有成效的精神分析学派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童年经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童年经验对于一个人的心理倾向和特点的形成是至为关键的。
一个人在童年时对环境中的人、事或物的体验,多半会影响他成长后的政治观点、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等。
对于作家,则会影响到他对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定向,直至本人创作风
格的形成。
二
童年经验或早期经验,首先无疑主要是对家庭和家庭成员以及家庭生活的印象与经验。
对于鲁迅而言,基本上是在一种被压抑的和沉重的氛围中度过他的最重要的一段童年时光的。
在鲁迅的童年经验中有着他的对于不愉快的和压抑的早期生活的极为敏感的记忆,或者说,早期生活的压抑感及其记忆,构成了鲁迅童年经验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内容。
就像人们已经熟知的,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福清一家的最大的灾难和厄运,就是1893年,周家的家长介孚公因犯“科场案”遭捕入狱,并被判“斩监候”。
这无疑使正家道败落的周家又遭釜底抽薪之灾,自此更加一蹶不振。
这时,鲁迅仅十二、三岁,正值天真无忧的少年时光。
在此之前,鲁迅也有过快乐的童年生活。
但是,祖父的入狱却结束了这一切,并以此彻底改变了鲁迅今后生活的色彩和走向。
他不仅被讥为“乞食者”,而且此后不久,父亲又突发急症,两三年即告谢世。
在这段时期中,鲁迅作为长子长孙不得不过早地分担起家庭的重负,在世人的冷眼中受尽了“侮蔑”和炎凉,遭到和忍受了种种难堪、屈辱、自卑和压抑。
如果说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病逝使他幼嫩的心灵曾为家庭的不幸而感到悲伤,那么,被称为“乞食者”的轻蔑和长辈亲朋的倾轧以及乡邻的流言,还有那药房与当铺间的连年奔走,则使他过早地尝遍了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人生酸苦。
这一切,他在其后的《呐喊?
自序》等作品中曾有过一些反映。
鲁迅对人生的印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2](P91)显而易见,鲁迅对这一段早期生活的经验,记忆是极为深刻的,他以后多次由此而提及自己的出身、家庭和早期生活。
但是,对鲁迅少年心灵的影响又何止是这种世态的炎凉。
弥漫在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周围的封建传统意识氛围,几乎在他童蒙未开之时,就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巨网,企图把他永远地禁锢并扼杀在其中。
鲁迅是怀着一种受到伤害的心情走向人生、社会的。
在对人世的感慨和洞观的背后,不知隐藏了他多少滞重的记忆。
如果说上述经历使得鲁迅对旧的社会与旧的人生方式感到彻底绝望与憎恶并最终决定他成为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的话,那么他的大姑母的惨死、小姑母的早逝以及他的继祖母与母亲等人的不幸命运,则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隐痛与沧桑之感,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进入了对人生的形而上的思索。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极其重视群体价值和血缘关系的文化环境中,任何一个亲人的不幸与离世都会给其他亲人带来极深的刺激与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感触直至探索。
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我们发现了鲁迅在中西、新旧两种文化观念冲突下内心的矛盾与无奈。
特别是在他童年经验的另一部分,当他看清了聚族而居的周氏家庭那种纠缠、复杂的关系、那种令人伤怀的“窝里斗”与不安宁之后,除了与之“决绝”、“逃到异地之外,实无更好的选择。
但逃避毕竟不等于解决,当鲁迅数年后在创作中重新面对它们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感到“无法排遣的悲哀”与无法解决的“懊恼”、“无聊”。
正是这种童年经验影响了他创作中那种一以贯之的情绪潜流。
他虽然对旧的社会、旧的人生在理智上充满了憎恶与绝望,但他在情感深处,在潜意识中却不能甚至不愿像别人那样慷慨激昂甚至兴高采烈地埋葬它,因为那社会、那人生里毕竟有着他的一份血和肉。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竭力张扬个性的鲁迅身上不仅仅看到他的敏感与决绝,同时也体会到了那种无可奈何的、难以彻底解脱的“寂寞”、“无聊”乃至“孤独”。
所以我们说,鲁迅的“孤独”决不仅仅是“前行者”的孤独,它更是一种徘徊于“明暗之间”,对人生无法做出圆满调和与拯救的“影”的忿闷与孤独。
正如蒂利希所说的那样:
“绝望的痛苦是这样一种痛苦:
由于非存在的力量,存在者知道无力肯定自己。
”[3](P50)这一点在其创作早期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鲁迅的童年经验不仅仅影响了他的特定的创作心态与作品中的情绪基调,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小说创作的取材与立意。
已经有许多论者明确指出,鲁迅叙事作品中的大部分人物及故事与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家庭生活都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三
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鲁迅的童年经验与其小说创作中的深层叙事结构的关系。
所谓深层叙事结构,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一种单一的、能够阐明不同的表层结构的意义模式,它实质上是一个作家深层的知觉结构,是作家人生观或世界观的基本结构。
它常常规定着我们对于经验的感知与反应、评论与表现。
换句话说,任何一位作家创作的深层叙事结构实质上都对应着他个人对经验、人生的独特知觉结构。
这种联系着“更为普遍的有关生活、社会和宇宙的概念”的知觉结构,它的雏型与基本支架实际上与一个人的早年生活经验(包括青少年时期)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关系。
这种宏大与复杂的结构直接影响着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深度与广度,也潜在地制约着一个作家作品思想内涵的丰富与深刻。
这一点在鲁迅的创作与生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正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过的那样,鲁迅的小说创作是弥漫着极其浓重的悲剧气息的,这种悲剧气息的发生是与鲁迅童年所经验的无数悲剧事件分不开的。
在鲁迅的人格与心理发生与发展的最关键的十多年里,家庭一直是变故迭起,厄运不断,似乎人世间所有的悲剧都集中在鲁迅的面前,让他不能不看,不能不记,纵使多年之后也“不能全忘却”。
不仅如此,更使他倍感悲凉的是,在他留学日本期间,从幻灯中看到的中国人的麻木冷漠以及创办《新生》的失败都给他深深的刺激与失望,加重了他的寂寞与悲哀,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正像鲁迅自剖的那样: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后来也亲历或尝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2](P92)由此可以看出,寂寞感、孤独感以至于对人生的无聊感,是鲁迅童年经验以及青少年经验所留给他的最深刻最主要的心态与情绪,这也是他把整个社会与人生看作一个“铁屋子”的必然原因,是鲁迅个人对于过去与现在的绝望的根本所在,是他把希望寄托于“孩子”与“将来”的深刻缘由。
正如他所说,“希望是在于将来”,而在他则是“我之必无”,尽管在别人那里“他之所谓可有”。
鲁迅之所以感到即使是创作与回忆也无“意味”但却还是要创作,用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看来,不能不归因于他早年的经验在他心理上所造成的“压抑”过重而不得不将之“升华”。
鲁迅在《呐喊?
自序》中深刻剖析道:
“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2](P91)“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
”[2](P92)总的来说,鲁迅即使在写作《呐喊》与《彷徨》之时,那种对人生的寂寞感、无聊感和痛苦感也是毫无改变的。
这种对人生的深刻悲剧感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物必然都是悲剧人物,且有着必然的不幸命运与悲剧结局。
因为在鲁迅看来,这整个人生与社会就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2](P92)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和社会观,鲁迅创作前期的小说作品中写了两类悲剧:
一类是父辈的悲剧,也就是“昏睡者”的悲剧,或者叫做“日常几乎无事的悲剧”;
另一类就是子辈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