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久隔帖》Word格式.docx
《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久隔帖》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久隔帖》Word格式.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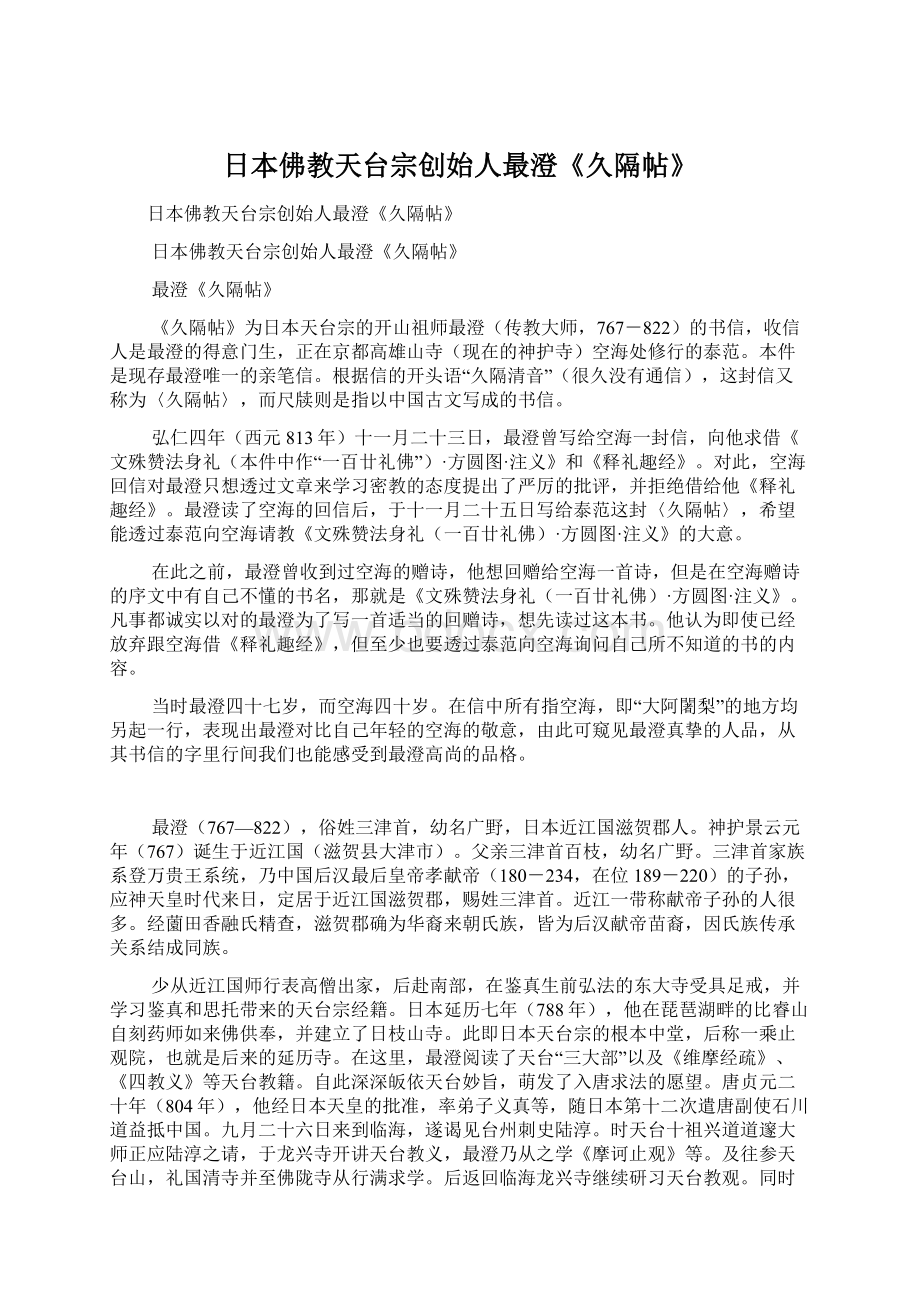
后返回临海龙兴寺继续研习天台教观。
同时,亲手抄写了大量的台宗典籍。
道邃还于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亲手为最澄授圆教菩萨戒。
关于最澄在临海龙兴寺的求法,日本的《睿山大师传》是这样记述的:
“时台州刺史陆淳延天台山修禅寺座主僧道邃,於台州龙兴寺阐扬天台法门《摩诃止观》等。
即便刺史见求法志随喜云:
弘道在人,人能持道,我道兴隆今当时矣。
则令邃座主勾当为天台法门,纔书写已,卷数如别。
邃和上亲开心要,咸决义理,如泻瓶水,似得宝珠矣。
又於邃和上所,为传三学之道,愿求三聚之戒。
即邃和上照察丹诚庄严道埸,奉请诸佛授与菩萨三聚大戒”。
最澄回国时,自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
回到日本后,在比睿山大兴天台教义,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
临海龙兴寺遂成为日本天台宗祖庭,为历代日本天台宗僧人和信徒所瞩目。
最澄手迹《山家学生式》。
延历寺藏。
延伸阅读
日本书法史的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中国书法是日本书法的根源,日本书法家们常常谦逊地称中国为“娘家”,而中国的书法家们也每每以这一点感到由衷的自豪。
悠久的历史渊源,丰富的文化遗产,确实值得文明古国的炎黄子孙们为之骄傲。
然而,在当时,中国书法是如何启示着彼岸的人们的?
这种启示的历史原因是什么?
有几个方面?
它有些什么可以总结的特征?
要了解日本书法史,首先要对日本的历史有个大概的概念,作为以后分析、判断、对照的基础。
而在我国一些不搞日本史研究、只是爱好书法艺术的同行;
特别是年轻朋友中,这个基础是略有欠缺的。
这里先提出一个最简单的历史分期表,以供参考:
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古坟期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大和相当于六朝和隋,奈良约相当于初、盛唐,平安则经晚唐、五代、北宋;
镰仓则当南宋和元;
室町相当于明;
江户、明治相当于清。
统一了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一艰难但也许是饶有兴趣的跋涉。
依附于中国书法的派生物
——实用的文字构成了书法艺术的基础,这是万劫不移的金科玉律。
我们应该先来研究一下,日本在最古时代是使用什么文字?
也就是说,构成日本书法艺术的基础的早期文字是怎样的?
这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
即使是最早的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也是到了汉、魏以后才出现的。
中国的《汉书 地理志》记载:
“东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日本历史的书写者们也许会为这种凤毛麟爪式的记录而苦恼。
因为它的历史记载与中国相比竟要少掉漫长的殷周、春秋、战国、秦等时期,少了一千多年。
作为日本历史上最赫赫有名的珍宝——由汉武帝颁赐的“汉委奴国王印”这枚金印的存在,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最早日本的记载还是出现在中国的史籍上,日本当时还没有自己的史籍。
追溯日本的历史,大约也只能追到汉代为止了。
西晋年间,百济(位于今朝鲜半岛)国有一位名叫王仁的人到了日本,他曾被任命为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
还带去了孔老夫子的《论语》和《千字文》,作为皇子学习的课本。
可以想象,不管王仁如何谆谆善诱,对于这位皇子而言,这些生疏的“之乎者也”也肯定是索然乏味的。
然而,令皇子头痛的汉字汉文,却首次光临了日本。
从此,它作为古代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标记工具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功劳。
汉字的进入日本,揭开了日本文化史的序幕。
我们的跋涉需要有一个较理想的起点,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一段历史时期加以特别详细的考察。
曾被认为是日本现存最早史籍之一的《日本书记》,是用纯淬的古汉语写成的。
我们可以先引出一段记载海神国的文字来加以证实:
彦火火出见尊(人名),忧苦甚深,行吟海畔时,逢盐土老翁。
老翁问曰:
“何故在此愁?
”对以事之本末,老翁曰:
“勿复忧,吾当为汝计之。
”乃作无目笼,内彦火火出见尊于笼中,沉之于海,即自然有可怜小汀,于是弃笼游行,忽至海神之宫。
其宫也,雉堞整顿,台宇玲珑。
这是一段神话故事。
和中国古代文化的起初总离不开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之类的神话一样,《日本书记》中也记载了大量的神话。
且来看看这段文字,除了个别语气词用得略嫌生硬之外,行句遣字完全符合古汉语的格式,甚至还出现了“雉堞整顿,台宇玲珑”等对仗工稳的骊句,足见撰者对中国古汉语的驾驭技能已经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境地。
南北朝时的《宋书·
蛮夷传》还收存了当时的倭王“武”致刘宋顺帝的表文,其中颇多优美的辞章。
如:
“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态。
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
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都是标准的古汉语,特别是表中居然还有“臣亡考济(允恭天皇)”和“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等句,“亡考”是中国古代习惯指故去的父亲的专有名词,“功亏一篑”也是成语,在日本向中国进献的表中出现这种文句和典故。
还不足以令人愕然吗?
如此强烈地追求纯粹的汉语风格,是由于日本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
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为了文化的记录和流传,它必须借用外来的文字作为补偿以满足需要。
在它与中国交往时,它是处于从属者的地位上的。
而且,在魏晋时代已经成熟了的散文、骈文与初具规模的诗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确实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之倾倒于中国文化自是势在必然。
据说在早期日本的统治中心里,还有一部分汉人;
倘此说属实的话,那么这些汉人对于日本朝野热心仰慕中国文化的浪潮,也一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汉字被引进日本后,这些天皇、大臣,乃至于一般官吏们都开始俨俨然地追求起中国风度来了,上引的两段记载正是说明了当时日本人的这种心理。
倾向于中国文化的风潮一直持续了很久,它必然在早期的日本书坛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平安朝是日本书法艺术的第一个高峰。
我们可以通过对它的考察来看看,中国文化是如何无孔不入地渗透并反映在日本人的作品中的。
传为平安朝书法三巨头的空海、嵯峨天皇、桔逸势的作品,全部都是标准的晋唐风貌。
著名的嵯峨天皇据说是个有为的君主,以天皇的身分参加书法创作,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作品,其中有一件是《李峤诗残卷》,是写唐代诗人李峤的诗的。
天皇为什么会选李峤的诗作为书写内容,这本身就是个很有趣的题目。
李峤诗共有一百二十首。
我们不厌其烦地把目录抄出来,供大家思考:
乾象十首:
日、月、星、风、云、烟、露、雾、雨、雪;
芳草十首:
兰、菊、竹、藤、萱、萍、菱、瓜、茅、荷;
灵禽十首:
凤、鹤、乌、鹊、鹰、凫、莺、雉、燕、雀;
居处十首:
城、门、市、井、宅、池、楼、桥、舟、车;
文物十首:
经、史、诗、书、赋、檄、纸、笔、砚、墨;
坤义十首:
山、石、原、野、田、道、海、江、河、洛;
嘉树十首:
松、桂、槐、柳、桐、桃、李、梨、梅、桔;
祥兽十首:
龙、麟、象、马、牛、豹、熊、鹿、羊、兔;
服玩十首:
床、席、帷、帘、屏、被、鉴、扇、烛、酒;
武器十首:
剑、刀、箭、弓、弩、旌、旗、戈、鼓、阵;
音乐十首:
琴、瑟、筝、琵琶、钟、箫、笛、笙、歌、舞;
玉帛十首:
珠、玉、金、银、钱、锦、罗、绫、素、布。
这种应制式的诗作,肯定是精芜参杂。
而且,以每首二十八字算,一百二十首是三千六百字,加上标题等更是近四千字。
以书法作品而言,可算是少见的鸿篇巨制。
嵯峨天皇对它竟不惜花费如此心血,实在令人惊讶。
他当然不会是出于实用目的才去书写的,李峤诗对于他的日常起居乃至军国大事毫无关碍。
大概是对汉字充满感情的天皇,看到这种精雕细琢的玲珑玩意儿,感到特另别的新奇有趣并由衷地佩服吧?
很可惜,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诗卷已经残缺了后半段。
对汉唐文化的心慕手追,一直持续于相当中国晚唐和北宋的平安全期。
被奉为“羲之再世”的日本平安“三迹”之一的小野道风,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草稿叫“屏风土代”。
相传他在三十二岁时,由朝廷大臣公推并被天皇亲点成为御书家,在当时可谓名扬天下。
这篇草稿的内容是一组汉诗,但并不是转抄唐人的,作者是日本诗人大江朝纲。
读了这些诗,可以想见当时日本的汉学影响是如何地强大。
诗共有十一首,题云:
《春日山居》;
2.《寻春花》;
3.《惜残春》;
4.《书斋独居》;
5.《山中感怀》;
6.《林塘避暑》;
7.《山中自述》;
8.《送僧归山》;
9.《问春》;
10.《楼上追凉》;
11.《七夕代牛女》。
为避累赘,引一首以飨读者:
古洞春来对碧湾,茶烟日暮与云闲。
山成向背斜阳里,水似回流迅濑间。
草色雪晴初布护,乌声露暖渐绵蛮知圮上独游客,疑是留侯授履还。
干仄、对仗、韵、用典、句式,全都齐了,把它混在唐人的别集中,谁能分辨得出来?
说它出自古代日本人的手笔,大概谁也不会不惊讶的吧?
平安“三笔”也好,“三迹”也好,从他们留下的作品来看,书写内容大部分是汉诗。
在这些汉诗中,真正日本人自己写的诗倒也不多见,最普遍的是抄录唐诗。
由于遣唐使的频繁派遣,促进了中日之间的交流,中国文化被作为——种楷模原封不动地带到日本,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丁还是在草创阶段的日本文化的倾心。
如果说由于“三笔”的首座空海和尚在访问唐朝后带回了大量的佛经佛具,因此三笔时代的文化艺术也不免染上了宗教影响的话;
那么到了继后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这“三迹”时期,这种宗教影响就相对淡薄了。
贵族官僚出身的书家们,致力于追慕唐风文化,研究诗文、学习书法,而对于宗教却很少瞩目。
他们并不是先宗教后艺术,而是把追慕文化艺术提高到突出的地位。
平安朝的“三笔”和“三迹”这两期书法的不同点,在这里是充分反映出来了。
平安“三迹”作品之中,出现最多的唐诗内容是白居易的诗。
据说有人专门进行过调查:
白居易的诗作,占了全部唐诗作品的绝大多数。
三位巨擘都有录白居易诗的作品。
小野道风有白诗《新乐府断简》;
藤原行成的《白诗卷》一气录写了白诗《八月十五夜同诸客玩月》等十首,可称洋洋大观。
至于藤原佐理,还有一篇写白居易新乐府《杏为梁》的作品。
这首《杏为梁》似乎已经反映出词的意味,它之受到日本书家的宠爱而出现在异国的书籍中,是否出于纯粹的偶然?
偶然性是存在的,但其中并非没有必然的趋势。
所谓偶然性。
当然是指在当时作为两国交流的媒介——遣唐使、学问僧的个人爱好。
他们自然先把自己喜爱的东西带回日本去。
我们看到了白居易的作品,看到了李峤的作品;
但我们并没有在日本古代书法中看到陈子昂、骆宾王、孟浩然等人的诗作。
唐代寺人的作品要进入日本,首先必须先通过遣唐使们这一关,如果通不过,那就别梦想“名扬海外”。
然而,什么是它的必然性呢?
尽管嵯峨天皇等“三笔”和小野道风等“三迹”,是那么虔诚地孜孜以求唐代文化,但唐代文化毕竟是借来的异国文化。
空海和尚和同时的最澄和尚都有《请来目录》,是记载从唐朝带来的各种佛经佛具的备忘录。
这“请来”两字用得很妙,它证明这些高僧们并不以此作为自己的“国粹”。
如果用在书法上,那么就是“请来书法”。
自然,书家们也不会数典忘祖,他们也知道“请来”的含义。
日本民族顽强的自尊心,不但在古代的政治、外交上反映出来,在文化艺术的交流上也同样反映出来,这是很可贵的。
既然是“请来”的文化和“请来”的书法,对于这些艺术家们而言,就有个接受的问题。
日本当时没有自己的文字,必项依靠汉字,这是无法更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但在接受异国文化为自己服务时,他们就有了选择的权利。
他们可以舍弃那些与自己民族性格(乃至个人性格)格格不入的东西,而吸收与之相吻合的东西。
白居易在唐代是仅次于李、杜的大家,有是够权威的地位;
他的诗作又具有明白清畅、老妪能解的特点,比较大众化。
异国人学习汉语是个困难的过程,而佶屈聱牙的风格和清新通脱的风格相比,自然是后者更容易被接受。
在进入日本的唐诗这个范围内,白居易的独占鳌头自然是可以估计到的了。
至于乐府长短句的出现也是同一道理。
比起排律整齐的诗来,长短句更口语化、散文化些,更易获得较多的读者。
文字的基础决定了书法的基础。
在书写内容上如此依赖于汉诗的日本书法,艺术上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唐风之外的。
关于平安时期书法是如何追求晋唐风韵的,我们留待下章详细考察。
这里先提出一个有意义的证据。
在碑学不发达的日本古代,流传有“上州三碑”之称。
其中尤以《多胡碑》最为有名。
书写的是汉字汉文。
由于它在艺术上与中国碑刻有很多相通之处,颇受中国学者的器重。
清代碑学太盛,杨守敬在《楷法赏鉴》中收录了《多胡碑》,赵之谦的《补环宇访碑录》中也榜上列名。
最有趣的是碑学巨擘翁方纲,以《多胡碑》与《瘗鹤铭》并称双美,俨然把它当作中国碑刻一般,即此也可见这方号称“上州三碑”之首的石碑,是如何地与中国的丰碑巨额息息相通的了。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假名书法的起源。
被日本人称为“自己的文字”的假名,是到了平安朝的中后期才兴盛起来的。
假名出现的依据,自然是中国的汉字。
只是不完全是楷、隶式的汉字,而更多地含有草书成分在内。
可以说,没有那些精于汉字汉文的“中国通”们,假名是很难形成的。
早期日本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但它却有自己的语言。
它所遇到的问题是怎样记录自己的语言。
学习汉语,虽然解决了记录的问题,但必须按照汉音来读;
自己的语言则没有了。
如何在借用汉字以解决文字记载的同时,仍然不失却自己的语言系统;
换言之,如何把自己的语言与中国的汉字相结合,这是当时日本人最关心的课题。
远在奈良时代,一些有心的日本学者就开始了创造民族文字的尝试。
第一个突破是万叶假名的出现。
它是一种假名形式,但用的却是汉字,这岂不令人奇怪?
中国的文字是一字一音的表意文字。
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它与以字母排列的表音文字是迥然相异的。
而日本民族的语言却是倾向于字母排列的表音系统。
比如:
“樱”这个字,在汉语中就表示樱花,只有一个读音。
而在日语中,一个音节变成了三个音节,用三个音联合组成“樱”这个字。
由于这一点,日本古代的人们对学习汉语就感到特别困难。
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造成了很多隔阂。
在进行日语与汉字相结合的过程中,日本学者们采用的解决办法是,以中国单个的表意文字作为日本语的注音。
在没有出现纯粹的假名文字之前的这段时期里,汉字一直扮演着为日语标音的角色。
从表意到表音是个重大的突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现代假名的滥觞。
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假名,在使用上也很不方便。
可以想象,汉字写一个“樱”字,标成日本音却要写三个子,效率降低了三倍,这是不符合文字使用频率日益提高的社会需要的。
但它确实显示出了日本民族的自强心理,当时的学者们不甘于日本文字领域钓寂寞;
他们不愿意借用异国文字来曲折困难地表达日本民族特定的生活事务乃至军国大事,他们宁惠用这种那怕是落后的文字系统来满足自己的民族感情。
日常需要的迫切性成了培育日本假名文字的温床。
从此,日本民族的文字开始了它们早就应该开始的长途跋涉。
第一次表现出这种跋涉的喜悦的,似乎是平安三笔之一的空海和尚。
他有一件《伊吕波歌》的作品。
1975年,由日本奈良市把它的原拓赠送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件在日本妇孺皆知的短歌作品,第一次成功地把汉字的结构(主要是草书的结构)演变为真正的假名字母。
歌的起首“伊吕波”这三个字是译音。
伊字的假名是取“伊”的偏旁,(是以字的草书写法),弓是“吕”字的草书变体,性是“波”字的草书变体。
倘这件作品属实的话,那么,在日本的平安中期已经完成了用假名注日语语音的过程,而其根据正是中国的草书。
值得注意的是,《歌》中的四十七个日文字母各不相同,它在当时起到字母表的作用,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使用。
随着在实际使用中越来越系统和严密,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日语字母表《五十音图》。
日本的学者们并不讳言假名来源于草书这一事实。
近代著名学者尾上柴舟在评论小野道风的《消息帖》时说:
消息帖作为小野道风的汉字草书作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中可窥假名书法从汉字草书中汲取艺术营养的形成“痕迹”。
(见《书运全集》卷十三,《平安朝初期概观》)虽然假名的母体是中国的草书。
但日本人却并不因此而沮丧,因为这确实是一种与中国汉字截然不同的表音文字系统。
日本民族完全可以因这丰功伟绩而自豪,并因此受到中国人的由衷敬佩。
假名与汉字草书的这种特殊关系,在书法艺术上也必然显示出明显的痕迹。
尾上柴舟上述的重点是放在假名书法这一点上,可见他至少是认为小野道风的作品也显示出假名书法的萌芽状态的。
此外,著名的书家纪贯之是一个兼善两美的多面手。
纪贯之的《寸松庵色纸》是标准的假名书法,格式与汉字绝然’相异,但他《桂宫旧藏万叶集》中所写的那些标音汉字却又极其精致。
从这种现象中,不正可以看到假名文字和假名书法的基础所在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
假名作为一种文字系统,虽然是从汉字中蜕化出来的,但由于突破了表意这一关而形成了日本民族所习惯的表音特点,就不能把它看作是汉字简单的翻版。
但是,从书法角度上看,由于它与汉字草书有着千丝万缕的承传关系,它就很难突破中国书法的那一套表现方法。
进行假名书法创作,必须熟练地掌握中国书法的结构、线条、章法等艺术上的法则,因而,当时的它仍然是中国书法的派生物。
我们说日本书法(包括汉字和假名)之所以能与中国书法进行交流,中国观众在看到这些作品时感到并不陌生,其原因即在于此。
——欣赏趣味、创作过程、艺术语言的相似,在两国观众的心里油然产生一种亲近感,在看西方抽象画派展览时也许会出现的目瞪口呆的突兀感,在看日本书法作品展览就不会产生。
此无它,两者的艺术渊源一致故也。
好了,我们已经了解了日本文字的产生和书法艺术的产生,这给以后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通过这一段也许略嫌枯燥的探寻,我们找到了几条主要的线索,应该把它总结一下:
(1)日本最早出现的是汉字书法,这是因为,日本最早的文字是汉字。
(2)日本民族文字——假名出现得较晚,它的依据是中国的草书与楷书。
(3)由于以上两点,中国书法的艺术标准和规律对于日本书法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4)同样由于以上原因,日本书法艺术的发展就与中国书法截然不同,它属于双线型的发展状态。
这两条线就是:
1.汉字书法,2.假名书法。
两者不可缺一,共同从文字基础上构成了日本书法的历史。
这里研究的是书法史,而不是文字学或文学。
因此,对于我们而言,第四个特点是尤其需要注意的,它又成为我们以后各个学术观点展开的基础。
书法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
纵观整个日本书法的历史,就会明显地感觉到:
书法与宗教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依赖关系。
书法史上的第一个巨擘空海就是入唐的僧人。
如果以平安时期为日本书法史的第一个高潮的话,那么这个高潮就是由僧人们掀起的。
反过来,宗教又借助于书法而巩固自己的地位。
没有哪一派宗教不依靠书法而能在日本站稳脚跟,禅宗的流传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种似乎不可理解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奥妙?
日本是个非常尊崇佛教的国度。
空海入唐带回了许多佛经佛具,促进了日本佛教划时代的发展。
这一向被传为佳话,但这是平安朝的事,事实上早在大和时期(相当于中国隋朝),日本就已经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以求佛法了。
《隋书·
东夷传》载:
使者曰:
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
所谓的“重兴佛法”,当然是指隋帝继北周废佛法之后竭力复兴佛教的情况。
在日本的《驭戎概言》中则是这样记载的:
“及至圣德太子听政时,所遣多为求佛法之使节……。
”
这两段记载很吻合,从记载中可以总结出两点:
①当时日本很注意中国统治者对宗教兴废的动向。
他们情报很快,隋朝在佛教上一有新政策,他们立刻就作出反应了。
②圣德太子派遣遣隋使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学佛法,想通过引进来振兴本国的佛教。
有意味的是当时的遣隋使团中,已经出现了僧人。
圣德太子并不完全认为这是一种官方外交,它应该包括宗教专家们互相探讨和传授等重要内容。
最高统治者的这个政策,马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了。
从木宫泰彦制的《遣唐使一览表》中可以看到,除了无法查考的以外,几乎每一次都有学问僧随遣唐使同行。
多时竟达二十六人。
这些学问僧大批涌入唐朝,又涌回日本;
他们在唐朝的目睹耳闻,自然会作为楷模而传授给本国的上层人士。
规模宏大的取经活动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
反映在书法上痕迹更是明显。
由于很多学问僧入唐的使命就是搞文化交流,他们首先学到了书法;
回到国内又是理所当然的权威,于是,偶然的历史条件给僧人们造成了钻研书法的有利条件和优越地位。
前面已经提及,日本早期文化的特征是“请来”。
既是“请来”,这去“请”的媒介就很重要,现在这媒介由僧人们来担任,僧人们就有了得天独厚的资格。
而他们的宗教职业习惯又无所不在地反映在任何事物上,于是他们的书法的宗教色彩又是无法消除也无法避免的。
木崎爱吉的《摄河泉金石史》中有这样一个结论:
“我邦金石文字,大抵皆蒙上佛教思想之影响。
”他的着眼点更高:
他不仅看着这些僧人的手迹,还注视着更早的碑刻金石,范围更大了。
确实,看看被誉为日本古代名碑的《宇治桥断碑》记载的是一个僧人如何施福于大众,造了一座桥等等的颂辞;
而其书风纯类《张猛龙碑》;
比它更早的《法隆寺佛背刻铭》,则又是典型的六朝写经书风,这些例证都可以说明,在当时,书法与宗教的关系,是以书法形式书写宗教内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而这种关系的完成,是通过身兼僧人和书家两美的那些人之手,根据我们的考察:
日本书法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宗教与艺术的化合物。
释迦牟尼在日本真是好运气。
他一直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一代代被顶礼膜拜着,从未受到过任何阻挠和压制。
似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