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板娇黄的屋子文档格式.docx
《地板娇黄的屋子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地板娇黄的屋子文档格式.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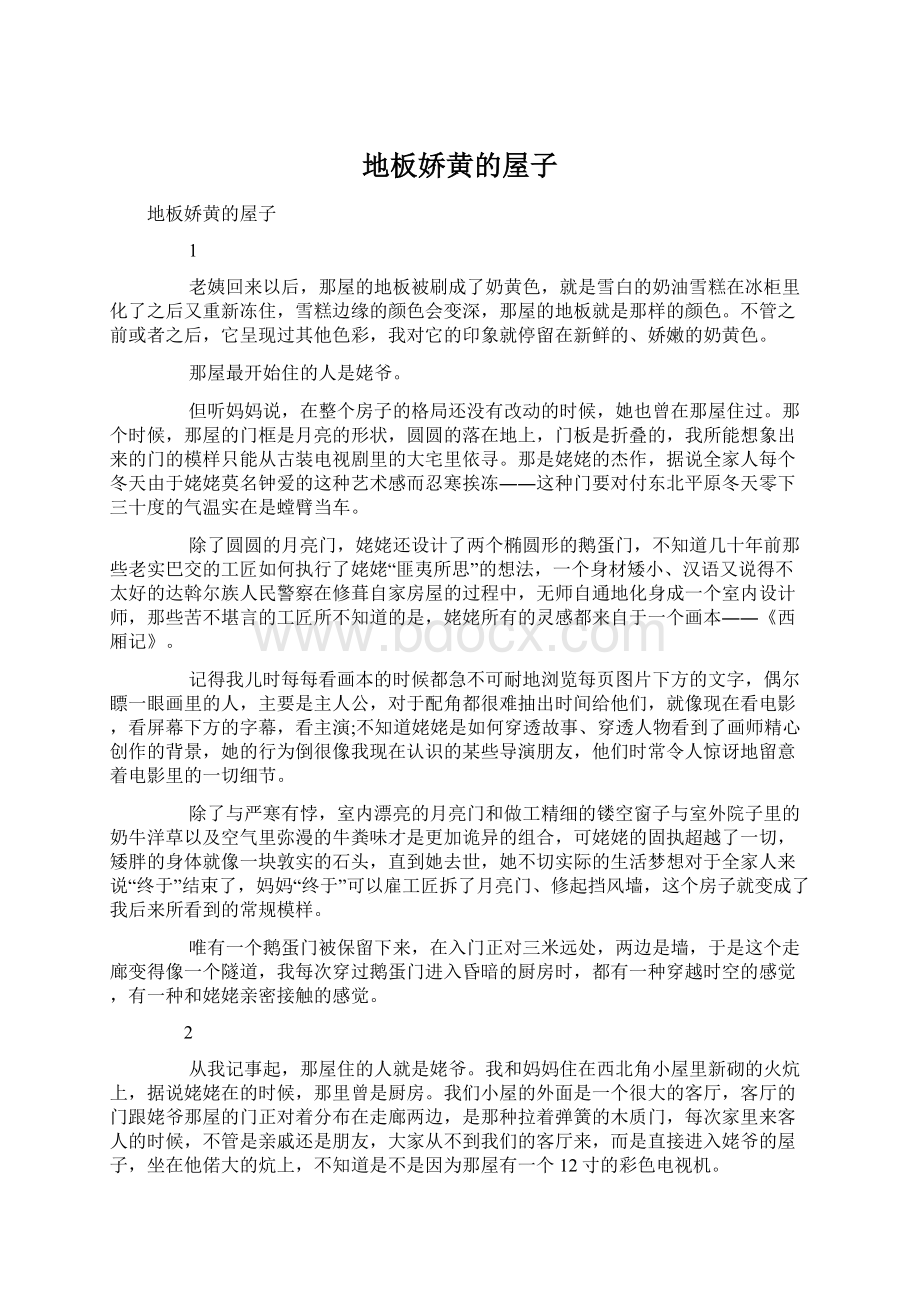
记得我儿时每每看画本的时候都急不可耐地浏览每页图片下方的文字,偶尔瞟一眼画里的人,主要是主人公,对于配角都很难抽出时间给他们,就像现在看电影,看屏幕下方的字幕,看主演;
不知道姥姥是如何穿透故事、穿透人物看到了画师精心创作的背景,她的行为倒很像我现在认识的某些导演朋友,他们时常令人惊讶地留意着电影里的一切细节。
除了与严寒有悖,室内漂亮的月亮门和做工精细的镂空窗子与室外院子里的奶牛洋草以及空气里弥漫的牛粪味才是更加诡异的组合,可姥姥的固执超越了一切,矮胖的身体就像一块敦实的石头,直到她去世,她不切实际的生活梦想对于全家人来说“终于”结束了,妈妈“终于”可以雇工匠拆了月亮门、修起挡风墙,这个房子就变成了我后来所看到的常规模样。
唯有一个鹅蛋门被保留下来,在入门正对三米远处,两边是墙,于是这个走廊变得像一个隧道,我每次穿过鹅蛋门进入昏暗的厨房时,都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有一种和姥姥亲密接触的感觉。
2
从我记事起,那屋住的人就是姥爷。
我和妈妈住在西北角小屋里新砌的火炕上,据说姥姥在的时候,那里曾是厨房。
我们小屋的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客厅,客厅的门跟姥爷那屋的门正对着分布在走廊两边,是那种拉着弹簧的木质门,每次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大家从不到我们的客厅来,而是直接进入姥爷的屋子,坐在他偌大的炕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屋有一个12寸的彩色电视机。
我所认识的姥爷已经不是老姨和妈妈笔下那个酒鬼“恶魔”,他总是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个米色的宽檐帆布帽,坐在正门前面水泥地上摆着的一个小板凳上。
那个板凳是摆在那里而不是钉在那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姥爷每天坐的位置都一样,坐在那里晒太阳、临风、吐痰,看几米远的大门外走过形形色色的人,就像看一个荧屏。
妈妈说,姥爷总是拖着偏瘫的身子,右手拄着拐杖,左手夹在肋下,领着我去不远的老田家小卖店买零食,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只知道姥爷如果不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就在那屋看12寸的电视。
电视上有8个按钮,是8个频道,那个扁扁的按钮按下去会发出“咔嗒”一声,按下这个钮,另一个就会弹起来,就像在打地鼠,所以我很热衷于做姥爷甚至全家人的人体遥控器。
就算没人指使我,我偶尔也会带着小伙伴站在那里偷偷地疯狂地“打地鼠”,听着按钮们被死死按下去之后不停发出的“咔嗒咔嗒”声,成就感十足。
电视开着的时候,如果按钮没有被死死按下去,那么会出现所有按钮都挺立着的情况,这个时候电视上的画面会消失,布满不断跳动的黑白雪花,近距离观看刺得我眼睛涨疼,所以按钮必须被“死死”按下,彻底!
不留余地!
然后彩色的画面又出现了,感觉自己像个魔术师。
电视被偷的事我不确定发生在姥爷去世之前还是之后。
姥爷去世的时候是深夜,我似乎听到一些熙攘的声音,隔着客厅看到那屋恍惚的灯光,第二天却是在大姨家的炕上醒来的。
大人们都不知去向,只有表哥表姐陪着我,再回家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姥爷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感觉姥爷去世这件事在我心里那么轻描淡写,没有看到他静静地躺在什么地方,没有看到一张表情和蔼的黑白照片,没有看到全家人穿着丧服的情景,没有听到撕心裂肺的哭泣,什么也没有,只是从那个夜晚之后,我的生命中再也没有姥爷这个人了。
3
老姨是在那屋住的时间最长的人。
她是一个把炕当床的人。
住过炕的人都知道炕是一个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一般比板凳高,四边至少有两边是跟墙成90度角砌在一起的,如果第三边也挨着墙,那一定是有窗户的那面墙。
人们会选择炕上两面都有墙的“安全区域”摞叠好的被褥,一层一层摞上去,之后用一张被单蒙上,不是简单地随便一蒙,而是把这个由被褥摞成的长方体没挨墙的两面都整齐地盖好,我妈妈会在长方体的上方折出一个三角形,它是多余被单重叠的地方。
于是这个长方体就有了名字――被垛,而这个行为则被称作“扇被单儿”。
姥爷没去世之前,我总看到妈妈站在那屋的炕上扇被单儿的情景;
老姨回来之后,那屋的被垛就消失了。
她把好几层褥子铺在炕的中央,蜡染的床单就那么散在褥子四周,被子安然地像一个锅盖盖在褥子和枕头之上,每到晚上她钻进去就睡了。
有的时候,她躺在被窝里看电视――一台新买的21寸大彩电,有遥控器,我不用再跑过去按出“咔嗒”的声音,妈妈盘腿坐在炕上按遥控器上的按钮,毫无声音,现在回想起来,总是给她按上颐指气使的神情。
我从心底里认同老姨从不叠被的行为,打小就对叠被有一种抵触――每天晚上一层一层地铺好,睡一觉,早上又一层一层地叠回去,觉得甚是多余。
老姨的行为让我有了勇气,开始向妈妈抱怨,妈妈是那种冷不丁就毒舌一下的女人,她答:
那你还吃饭干什么?
反正吃了也要拉掉。
多年后看到韩寒也有这种理论――为什么要叠被呢?
反正是要铺开来睡的。
颇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之感。
老姨有的时候不喜欢我去她的屋子玩,可能是因为她要写作,也可能是因为,用她们的话说,我屁股上有钩子,总在她的“床上”“委嗤”,把她铺得像睡美人似的被褥坐得皱皱巴巴、面目全非。
后来,她提议把大彩电搬到我和妈妈住的小屋,兴许是她受不了我一到假期就一下午一下午地看《新白娘子传奇》了吧。
没了电视,尽管很渴望,但很难再理直气壮地进她房间,她话少,坐在她的炕上,没什么聊的,没什么玩的,虽然我很小,也能有些许尴尬的感受。
后来,准姨夫的到来再次成了我大摇大摆进她房间的理由,有时候把大摇大摆换成火速奔跑――每天傍晚放学,冲进她的房间,把地板踏得“piapia”响,把准姨夫泡在杯子里的红茶一喝到底。
要说杯子,真是巨大,可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杯子,是以前装雀巢咖啡颗粒的玻璃罐,那个时候的人总喜欢用罐头瓶当杯子,粗粗胖胖的,姨夫的雀巢咖啡罐还算比较有造型的了。
我很爱姨夫这个人,他总把我逗得咯咯笑,总伸出他那曾经被树枝捅穿的舌头吓唬我,我爱那个时候家里的气氛,他的到来让我的家从温暖变成了热烈。
可我并不知道他有一天是要将老姨带走的,带到一个离我的家乡有上百公里远的城市。
火焰一般的热烈应是有代价的,你燃起了火堆,总要烧掉一些树枝,等火熄灭的时候,那凉意就更明显。
老姨走了以后,那屋的炕上没了被垛,也没了被窝。
只有一张格子花纹的地板革,上面不时落些灰尘。
4
房子空荡荡的,日子久了,漫长的寒冬就更难挨。
那时候,一个叫荣芳的表姨刚刚离婚,带着一个叫小雪的孩子,四五岁。
她前夫是旗乌兰牧骑歌舞团的一个舞蹈演员,只不过这个男人并不以舞出名,而是以“酒鬼”闻名大街小巷。
表姨带着小雪搬进了那个地板还没有褪色的房间,她是一个歌手,嗓门何止嘹亮,每每说话都似乎将屋内的气温升高。
小雪理着短发,像长在头上的绒毛,介于金色和亚麻色之间,有一些达斡尔族人天生像染过头发。
她骨骼精细,却淘气得像一只小山羊。
虽然我才三年级,但是我的个头已经很高了,总坐在班级的最后一排,小雪是一个小矮人,她的头只到我的腰,她总是用双臂环住我的臀,使劲抬头看我傻乐。
妈妈是在那个时候买了“黑耳朵”给我,一只耳朵黑黑,眼睛黑黑,身上有黑色斑点的草兔。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兔子,竟然不是传说中的浑身雪白白,双眼红彤彤,我傻了吧唧地料定它是一只非凡的兔子。
它喜欢串门,总在各屋窜来窜去,总大摇大摆地跳进那个屋子,有时把从别处踩来的土印在娇黄的地板上,像以前的我。
她们来了不久以后,小雪被表姨改名为娥眉,我猜想她是想跟过去彻底告别吧,可“酒鬼”并不这么想,总要来看女儿。
我见天听表姨嘴里提起他总是充满蔑视,以至于我每次听到他的名字也下意识地撇着嘴。
在表姨的描述中,他似乎没有一天不是烂醉如泥,可他来看女儿的那天却非常清醒。
他拎着一袋水果从我们家院子的大门小心翼翼地走近我们,客气地跟妈妈打了招呼,还有我。
我并没有见到他抱小雪的样子,也听不见他们在屋子里说些什么,他进去之后就将那屋的门半掩着,可我能感受到父女重聚之后的喜悦、幸福、兴奋,好像什么字眼也不足以表达,那是我从没感受过的。
我只记得我也曾从远处张开双臂向我高大的父亲奔去,当我到了他的面前,他只是冷冷地说,他马上就要离开了,身边还站着那个把他抢走的女人。
那天,我用一根小树枝打我的猫,它发出前所未有的惨叫。
妈妈从厨房出来后并没有责备我,她问我是不是因为正军来看小雪让我想起了爸爸,我扑到她的怀里号啕地哭,我说,我的爸爸连一个酒鬼都不如。
表姨和小雪好像是我不在家的时候搬走的,我脑中从没有那样一个印象,她们在装包装车的印象,就像我不知道她们当初是怎么来的,突然在一个放学的傍晚,她们就出现在那个屋子,突然在一个放学的傍晚,她们又消失了。
搬走的原因我也不甚清楚,至今也没有问。
只记得当初的我并没有害怕她们的离开,也许是因为我更害怕看到他们父女一次又一次在我眼前重聚吧。
有一天,我和妈妈锁门正要走,突然听见已经空荡荡的那屋传来击打地板的声音,那频率比人的脚步快得多,我们好奇起来,俯在窗户一看,是黑耳朵在试图跃到炕上――它从远处狠命奔跑助力,到炕边上一跳。
我们观看的时候,它一次也没有成功,不过应该有成功的时候,因为电视机搬回去没多久,遥控器的按钮就已经被它全部咬掉了。
我想,也好,那偌大的屋子放一个21寸的彩电,那偌大的炕上,蹲着一只黑耳朵黑眼睛的兔子。
5
表姨她们在的时候,那屋的地板就已经斑驳了,一块一块的磨损,像一朵一朵酱色的碎花。
表姨爱穿高跟鞋,坚硬的粗细不等的跟儿,所以她把地板踩出的声音跟我不一样,是“咔咔”声,非常铿锵,就像她的生命。
我再也不像老姨在的时候那样,每每踩在她亲手粉刷的地板上都小心翼翼、胆战心惊,我也不用担心把她的床单“委嗤”皱了之后她有些不悦的脸。
我把我所有的玩具摆了一炕,在炕上随即挑选位置“铸造宫殿”“建造村落”,以及坏蛋们的“巢穴”。
兔子丢了以后,电视又被妈妈折腾回了我们的小屋,妈妈似乎也放弃了家里会热闹起来的愿望,索性不拼命烧那屋的炕和火墙了,愈加寒冷的房间渐渐被摒弃,家里的猫咪也不爱进去。
我记得有一个夏天,我跟好友娃娃去她亲戚家玩,结果躺在人家的炕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也不记得回家的路,直到她妈妈决定回去我们才离开。
我到家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但时间已近8点,我走进院子,看到整个房子灰蒙蒙一片,不知道是停电了还是妈妈没有开灯,总之那种朦胧的灰暗压抑着我。
走近房门时,看到妈妈坐在那屋炕上的身影,我抿着嘴唇走过去,她没有说一句话就把我按在炕上照着我的屁股拍了几下,并不疼,她哭泣的声音才让我疼。
她说,她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找不到我。
我至今也没想通妈妈为什么会坐在那个房间等我,那屋的地板不是早就不再娇黄了么?
6
1996年,我10岁,妈妈的单位盖起了家属楼,我们终于要告别这间有院子的平房。
房子加院子连同我们所有人曾经的气息和一只黄白相间的虎斑猫一共卖了两万两千块钱。
妈妈在那间屋子空旷的炕上和地板上打包我们全部的家当,虎斑猫这个时候已经六岁了,它叫葛日威。
当妈妈告诉它,我们就要搬到楼里,让它留在老房子的时候,它像默认了一般没有做任何辩白就垂着头走开了,只是显得有些难过。
我看着妈妈在那个屋子打了无数个包裹,看着她用塑料绳捆了一个又一个,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与那个屋子最后的交集。
听说这个有院子的平房是姥姥在上世纪70年代末盖起来的,虎斑猫葛日威是这个平房里唯一降生过的生命,它的妈妈生它在那个房间上面的二层棚里,是老姨使用那个房间的时期。
姥姥在这个房子里死去,姥爷在这个房子里死去,葛日威的妈妈在这个房子里死去,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这个房子,留它做了最后的坚守。
我回去过,在门廊见过它一次,它不吃不喝不理人。
再去的时候,它也死了。
院子里的树都被砍掉了,平房被新主人刷成了其他的颜色――对我来说非常怪异且陌生的颜色。
(责任编辑杨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