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论文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文档格式.docx
《精品论文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精品论文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文档格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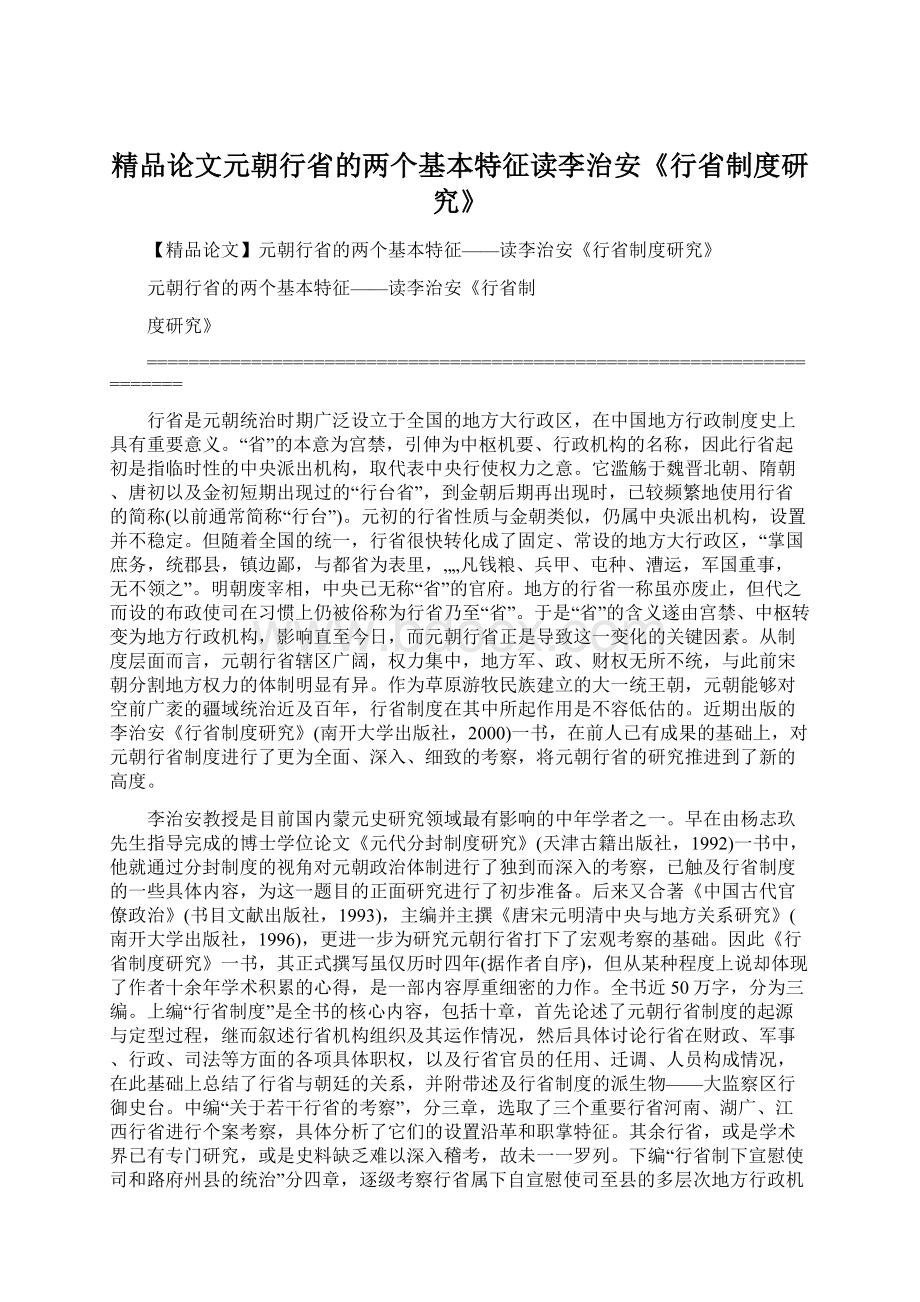
下编“行省制下宣慰使司和路府州县的统治”分四章,逐级考察行省属下自宣慰使司至县的多层次地方行政机构,对元朝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所论已不限于行省本身。
最后是全书结语,概括元朝行省制度的主要特点和历史作用,指出元朝行省具有两重性质,其职能主要是为中央收权,同时兼替地方分留权力,自身的权限则具有“大而不专”的特征,成为中国古代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一种较高级演化形态,对明清地方行政也
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史料翔实,持论谨慎,言必有据,很多地方填补了蒙元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如上编第三章“行省与地方财政”、第七章“行省与乡试”等)。
书中论点建立在充分、细密的具体研究基础之上,因此具有很强说服力,绝非无根空谈。
比较而言,我认为其中的两处观点尤其具有重要价值。
其一,是元朝行省同时具有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官府的两重性质。
其二,是元朝行省虽然具备汉族官制的表象,但本质上仍是蒙汉二元混合的制度。
这可能也是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
我们知道,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
但有一点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都省)分支机构的性质。
《行省制度研究》对这一问题有准确的概括。
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末尾,以及结语第一节“行省的两重在上编第一章“
性质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文中,作者一再指出:
“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
“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
在阐释这一“两重性质”时,作者主要是从元人有关行省“分天下之治”、“分镇方面”、充“方面之寄”之类说法立论。
我认为还可从另外的角度进行补充。
在元朝,行省实质上是中书省的下属,要接受后者的节制和领导,但从统领路府州县的角度以及官名、品秩等侧面来看,行省与中书省又具有某种“平等”关系。
就全国范围而言,行省的设置并未覆盖全部路府州县,离首都大都较近的山东、山西、河北地区称为“腹里”,仍由中书省直辖。
换句话说,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中书省,将全国路府州县的大部分交给自己的分支机构——行中书省统领,但仍保留了自己直辖的一部分。
在管理层次上,中书省统行省、行省统路府州县的三级关系并未完全普及于全国,而更全面地看毋宁说是中书省与行省共统路府州县的两级关系。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叙述全国行政区划称“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即以两者并列。
《大明一统志》卷首《图叙》则称元朝“内立中书省一,以领腹里诸路;
外立行中书省十,以领天下诸路”。
都省与行省“官名品秩略同”,文书往来亦用对等的“咨文”,均反映了两者“平等”的一面,这种特点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
中书省直辖区“腹里”地域广阔,共二十九路、八直隶州,以下又辖三属府、九十一属州、三百四十六县。
其人口、面积,均在大多数行省之上。
大德十一年(1307)岭北行省建立以前,广袤的漠北草原也包括在“腹里”范围以内。
中书省不仅要从大局上节制、领导诸行省,同时还要亲自处理腹里众多路、州上禀的政务。
这是元朝行政体制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中书省“勾当繁冗,不能守着纪纲,从朝至暮押文书有”的原因之一。
大致在世祖末年行省制度定型前后,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疏云:
窃见中书内省,密迩皇宫,统余省于上游,弼圣君于中域。
但当坐而论道,据槐府以秉钧;
宽以宅心,守台司而助化。
今也
汴梁以北,北京以南,西界长安,东穷远海,毫厘细务,靡不相
烦,升斗微官,亦来取决,岂非管辖兼辕衡之用,要领兼衽袂之
资乎,„„更望陛下于腹内取中,别立一省,谓之燕南等处行中
书省,以间汴梁、北京、辽阳、安西四省之间。
凡外路受敕牒以
下官,行省注之,然后咨呈都省,乞颁敕牒可也。
凡随朝诸有司
当受付身者,委都省出之;
凡外路诸有司当受付身者,行省出之。
如此,则上庑远地而堂陛愈高,都省增崇而天王益重矣。
或者以
为国家因四远及蛮荆之新附,故立行省以镇之,内不须立也。
不
知汴梁有省,岂汴梁亦新附之地哉,事在不疑,惟陛下察其可否
而行之。
这篇奏疏反映出时人对行省的两种不同理解。
赵天麟将行省真正理解为地方行政中的第一级层次,所以要求将其设置完全普遍化,增立“燕南等处行中书省”,使中书省彻底高踞于诸行省之上,脱离路府州县的具体事务。
但按照当时上层统治集团中比较常见的看法,行省只是从中书省分离出去、镇抚“四远”
新附”之地的派出机及“
构,距中央较近的地区没有必要再立行省。
直到元朝后期官修政书《经世大典》,仍然说“夫外之郡县,其朝廷远者则镇之以行中书省”。
事实上直到元末,腹里地区也并未转变为赵天麟所建议的“燕南行省”,中书省“管辖兼辕衡之用,要领兼衽袂之资”的窘境一如既往。
从研究元朝地方行政的角度而言,“腹里”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各行省。
《行省制度研究》一书受题目所限,未能将腹里地区放在整个元朝地方行政体系中与行省一同予以充分讨论,似乎稍显缺憾。
就元朝行省的两重性质而言,上述与中书省的某种“平等”色彩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方面。
曾有学者对这一方面过于强调,完全忽视了中书省对行省进行领导、节制的巨大作用,忽视了元朝在中央集权方面的种种设施,于是就认为元朝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大体上只局限于“腹里”地区,各行省应视为相对独立于中书省的平行政府机构,这种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赵天麟早就指出行省“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
《行省制度研究》则将行省权力特征概括为“大而不专”,并对元朝中央政府对各行省进行有效控制、约束的各种制度和机制进行了透彻分析。
不过,行省作为从中书省“分”出去“治外”的机构,因而获得了与中书省一样相应集中的权力,“体势侔中书”,“所制者远,所统者众,所寄者甚重”,也是不争的事实。
就一地区范围而言,行省权力集中的程度,比中央的中书省也略有过之(中书省至少在制度上不掌军权)。
同样是中央派出机构,行省与前朝的道、路一类机构存在明显区别。
它在始出现时就被赋予比较全面的权力,级别较高,机动性较大,职在抚治而不仅是监察,并且这种集中的权力在行省地方化以后仍然得到保持。
但这与承自前代的汉族模式中央集权体制是否存在矛盾呢,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行省制度本质上所反映出的蒙汉二元性。
《行省制度研究》上编第二章“行省机构组织与圆署分领制”末尾概括元朝行省机构组织和权力运作的特征,指出其“表面上的汉官制,实际上是蒙汉二元制”。
尽管其名称、官职设置与前代行台省、行省十分相近,似乎是汉地官制,但就实质内容而言,元朝的行省主要是按照大蒙古国燕京、别失八里、阿母河三处“行大断事官”模式建立的。
“在由朝廷直接委派,代表朝廷分镇,与朝廷行政中枢互为表里、分辖内外及一府多员、圆议连署等方面,行省制与
燕京等处三断事官制,如出一辙。
”[11]这一看法十分精辟,但似乎言未尽意。
再看一下上编第七章“行省制的派生物——行御史台”末尾,作者对元朝行御史台所进行的分析:
元行御史台的大区监察,虽然也可以看作汉唐以来地方大区
监察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从汉地传统王朝监察制所继承的部
分毕竟有限。
„„从行御史台的镇遏职能看,行台大区监察,也
是蒙古统治者控制新征服区域的重要举措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元行御史台大区监察体制乃是蒙元帝国统治的条件下,融
有蒙古法和汉地监察传统二元因素的地方监察的新尝试。
它大抵
适合元王朝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及需要。
入明以后,由于行省被
相互牵制的三司所取代,元帝国旧有的对征服区域控制的政治军
事课题也不复存在,行御史台大区监察体制自然也就失去其继续
保留的必要性了。
[12]
我认为,这段论述也完全适合于、甚至是更加适合于概括元朝行省的实质。
既然“行省制的派生物”行御史台是如此,那么行省制本身难道不更是如此吗,作者在上编第二章提到了行省的“蒙汉二元制”特征,却并未像对行御史台那样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在结语中,仅仅只言片语地谈到元朝行省“酷似十个大军区”,“既是大军区,又是财赋征集区”[13],也没有就这种“军区”特征所隐含的“蒙汉二元制”问题继续作出总结。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要“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去探索其(按指行省)历史根源和复杂背景”,注重强调元朝行省制背后“隐藏着(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发展历程的必然抉择”,所以对其“军区”特征只能当作历史长河中“蒙元统治者对帝国疆域军事控制的偶然行为”[14],不便多费笔墨。
实际上这两者未必矛盾。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合理调节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进行过反复摸索,行省制的确只是其中的一段过程,从宏观上来看具有某种必然性。
但它之所以在元朝统治的特定环境下出现,归根结底仍然是由“军事控制的偶然行为”所决定的。
不妨从行省“地方化”的过程来看这一问题。
尽管行省在金朝末年已经大批设立,大蒙古国也有被汉族文人比附为“行省”的三处行大断事官设置,但当世祖忽必烈建立汉族模式的元王朝后,并未在地方上普遍设立行省,而是设置了类似于前代“监司”性质的十路宣抚司,稍后又废宣抚司,改立宣慰司。
世祖前期,很多地区的宣慰司与行省迭相废置,反映出蒙古统治者在究竟采取哪一种形式来统辖地方这个问题上,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时没有明确的想法。
与宣慰司相比较,行省的设置灵活性更大,往往因需临时处理地方重要事务设立,事毕裁撤,或因军事目的而设,工作重点在为战事服务,其地方化的程度明显不足。
推动行省制度发展的关键事件是平宋之役。
至元十一年(1274),因伐宋设置荆湖行省,由伯颜以中书左丞相领行省事,“所属并听节制”[15]。
荆湖行省是一个军事性质的行省,在当时成为伐宋战争的前敌最高统帅部。
史料谈到伐宋战争时,往往径以“行中书省”名之,或称之为“大行省”。
渡江之后,面对转瞬到手的江南大片土地,元廷自然地采取了设置行省的办法,实施简便有效的管理。
随着各路军队对所向地区征服的完成,南方的江淮、江西、湖广几大行省也就诞生了。
由于各行省控制的区域都很大,对一些局部地区又设立宣慰司进行管理,两者在一段时间内都具有明显的军事管制性质,仅范围大小有异。
尽管元廷似乎曾有一种以宣慰司“道”作为统一地
方监临区划的倾向[16],但行省设置仍然长期保持,这主要是由平宋以后江南的动荡局势所造成的。
南宋残余力量长期坚持抵抗,后来江南人民又因不堪赋役重负而纷纷起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位尊权重的行省不但不能罢撤,反而需要进一步强化事权、明确责任,以便及时而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维护元朝在江南的统治。
于是就出现了至元后期到成宗初年有关行省的一系列规定,包括核定行省官制及辖区、授权行省总领管内政务、定行省官迁调之法、并行枢密院于行省等等。
如《行省制度研究》所言,这些措施使得行省的基本性质由中央派出机构演化成为地方最高官府。
总体而言,元朝的行省是从北方推广到南方的,但它在南方以及西南边陲的四川、云南却体现出更强的生命力,首先得到了充分发展。
这与南方和西南距离元朝中央相对较远、中央难于直接控制有很大关系。
当元朝新定江南、连续设立行省之际,行省在北方却一度萎缩。
荆湖行省随着元朝大军的南下不复存在,原设于东北的北京(或东京)行省也被废罢。
至元十五到二十三年,北方只有陕西、甘州(或宁夏)两行省,且置废不常。
然而在南方趋于成熟的行省管理体制反过来又对北方产生了影响。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廷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居其间,宣慰司望轻”,罢宣慰司,设东京行省(后改称辽阳行省)。
四月,中书省臣又请立“汴梁行中书省”,圣旨以河南“户寡盗息”未予批准。
[17]河南虽未设省,但陕西、甘州(寻改甘肃)两行省的建置却在这段时间内基本稳定下来。
到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终于设立河南行省。
河南行省之设又使得南方的江淮、湖广行省辖区发生变化,两省的“江北州郡”除个别地区外都被“割隶”河南,江淮行省也因而更名为“江浙行
省”。
至此元朝行省的辖区划分初步奠定,“地方化”已大体完成。
行台省”、从元朝行省地方化的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它与前代王朝的““行省”有某种联系,但仅凭前代的影响,尚远不足以使它在元朝发展成为一套完备的制度。
其制度定型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与行御史台一样,仍然是“元王朝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及需要”、“对征服区域控制的政治军事课题”。
特殊的民族统治背景,使得行省制度蒙上了一层与汉地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不甚协调的外衣,所谓“蒙汉二元制”,其含义主要应在于此。
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汉族士大夫对行省制度的批评当中体会这一点。
如南宋降臣程钜夫在题为《论行省》的奏疏中说:
窃谓省者,古来宫禁之别名,宰相常议事其中,故后来宰相
治事之地谓之省。
今天下疏远去处亦列置行省,此何义也,当初
只为伯颜丞相等带省中相衔出平江南,因借此名以镇压远地,止
是权宜之制。
今江南平定已十五年,尚自因循不改,名称太过,
威权太重,凡去行省者皆以宰相自负,骄倨纵横,无敢谁何。
所
以容易生诸奸弊,钱粮羡溢则百般欺隐,如同己物,盗贼生发则
各保界分,不相接应,甚而把握兵权,伸缩由己,然则有省何益,
无省何害,„„今欲正名分,省冗官,宜罢诸处行省,立宣抚
司,„„凡旧日行省、宣慰司职事,皆于宣抚司责办。
[18]
如《行省制度研究》所指出,程氏的上述批评事实上不无偏颇之处。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批评似乎并非个别事例。
南宋遗民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在卷五二《职官六》记述魏晋隋唐“行台省”之制后,引用南宋胡寅之论云:
“是政出于朝廷,又出于行台,夫岂国无异政之体哉~”接着他自己又评价说:
“然则行台省之名,苟非创造之初,土宇未一,以此任帷幄腹心之臣;
则必衰微之后,法制已隳,以此处分裂割据之辈,至若承平之时,则不宜有此名也。
”考虑到马氏在《通考》中较少发表自己的议论,上面这段话就颇有可能是借题发挥,目标针对的是元朝行省。
宋朝原无行省之制,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行省受到的批评(程钜夫建议设立的宣抚司实际上即以南宋制度为范本)。
但生长于北方原金统治区的王恽也有同样的看法。
成宗即位之初,王恽上《元贞守成事鉴》,其中一款以“慎名爵”为题,略云:
今四海一家,廓然无事,收揽威权,正在今日,朝廷宜重而
惜之不轻与。
人谓如李唐季年使职或带相衔,初无分省实权。
何
则,既远阙廷,岂容别置省府。
所以然者,盖亡金南渡后一时权
宜,不可为法。
[19]
王恽与程钜夫虽来自不同地区,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上追溯了行省出现的背景,但却殊途同归地强调行省只是一种“权宜”产物,不应成为经久之制。
这只能说明行省制度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抵触,并非汉地制度自然发展的结果。
然而,类似的反对言论并未起到作用,这是因为行省的确适应元朝统治的特殊需要。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中央集权固然要加强,而稳定地方局势的任务则更为迫切。
平宋以后江南局势长期动荡,致使元廷必须予各军事占领区以相对集中的事权,以便遇到紧急事变能够迅速决策并付诸行动。
任何扯皮、掣肘、推逶现象,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行省才在南方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即使在江南形势基本稳定、大一统局面完全告成之后,元朝政权的民族色彩也仍然长期保持,民族隔阂长期存在,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终元一代基本没有改变。
这样行省在稳定地方统治方面的特殊价值,显然也并未消失。
另外,元朝沿用大蒙古国以来的游牧分封制,大量宗室外戚被分封于漠北和东北地区,在中原又各自领有大小不等的投下分地。
对于这些天潢贵胄及其狐假虎威的家臣,一般的地方官府难以治理,非设立位高权重的行省不足以压制。
辽阳、岭北两行省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最后,元朝疆域辽阔,为汉唐所不及,路府数量繁多,中央很难一一统属。
设立数目有限的行省,代替中书省对其力所不及的地区进行管理,中央再从大局上对诸行省实施节制,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确实也是一种具有明显优点的统治模式。
凡此种种,都导致过去主要出现于“创造之初”或“衰微之后”的行省(行台省),到元朝演变为“承平之时”的正规典制,从而在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仅如此。
尽管行省在元朝的制度化具有某种“不得已”的背景,但它与传统汉式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的不协调因素并未在其制度化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
相反,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元朝行省极少扮演体现地方独立性、代表地方利益的角色,而主要起到了巩固中央集权体制、维护大一统局面的作用。
就中央与各行省的关系而言,我们很少看到双方发生权力冲突的材料,相
反更常见的却是中央责令各行省充分发挥自主权,批评它们“不详事体轻重,无问巨细,往往作疑咨禀,以致文繁事弊”,要求“除重事并创支钱粮必合咨禀者议拟咨来,其余公事应合与决者,随即从公依例与决,毋得似前泛咨”[20]。
并且元朝之灭亡,主要是亡于社会矛盾尖锐化所造成的下层人民反抗,而并非亡于地方的分裂割据。
其所以如此,除去元朝中央政府能够通过各种制度和机制对行省进行约束、控制外,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元朝的民族统治背景所决定的。
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
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
行省宰执当中,丞相不常设,平章政事在多数情况下为一省之长。
元朝统治者对这一职务非常重视,“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21],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
而实际上,行省总制一方的权力主要就表现在平章政事(设丞相时当然还有丞相)身上。
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
汉人不章以上得掌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说到底只是为了体现“得与军政”[22]的原则。
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在防范汉人掌握行省大权方面是煞费苦心的。
比较而言,将行省的主要权力交给蒙古、色目贵族显然就保险得多,因为这些人几乎全都出身于怯薛,属于皇帝(大汗)的世仆家臣,皇帝可以比较放心地对他们“委任责成”。
而他们对皇帝、对朝廷的忠心,在一般情况下无可怀疑。
作为一个异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得到某一汉族地区的拥戴来策动分裂。
元朝个别时期曾出现行省官员对抗中央的军事行动,如仁宗时的“关陕之变”和文宗即位以后四川省臣的叛乱,但那都是由皇位争夺引发的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中央先乱而地方后乱,并非地方势力自然成长导致与中央的冲突。
总之,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
萧启庆先生说:
“对蒙古统治者而言,地方分权之弊可由种族控制之利来弥补。
”[23]所言也是这层含义。
元朝中央分权与地方,与皇帝放权于宰相一样,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
尽管行省在元朝并未造成“内轻外重”现象,并且为巩固大一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根源自然也在于此。
还是回到《行省制度研究》一书。
白璧难免微瑕,书中个别地方也偶有疏漏,谨就管见所及略陈二处。
上编第二章“行省机构组织与圆署分领制”在叙述行省掾属(吏员)时,为其加上了官品,称行省掾史(令史)、通事、译史、知印为正从八品,宣使
为正从九品(第28,33页)。
这一表述似乎欠妥。
我们知道,元朝不像前后各代王朝那样注重官、吏之分,官大多由吏出身,低级职官又常常重新充任一些高级、重要机构的吏员。
行省地位崇高,其吏员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低级职官。
武宗至大元年(1308)统一规定“内外诸衙门令史、译史、通事、知印、宣使
有出身人等,于内一半,职官内选取”。
其中具体规定,行省令史、通事、译史、知印于正从八品职官内选取,宣使于正从九品职官内选取。
[24]但恐怕不能就此认为行省令史、通事等品秩正从八品,宣使正从九品。
因为这些吏职由职官充任者仅是一半(武宗以前大概还不及一半),剩下一半应当仍由六部、宣慰司等机构吏员转补,或是由行省自行选辟。
这些非职官出身的吏员,似乎就不宜称其为八品、九品了。
元朝不重官、吏之分,但并非完全将其混淆为一,品阶只是官员(包括低级的首领官、杂职官)级别的标志,似未施用于吏员。
《研究》一书将充吏职官的原有品级当作吏员的品级,可能是一疏误。
又下编第三章“散府与诸州”征引王恽《王复墓志铭》所载王复“自中书舍人出知归德府”时,称“元中书省未见舍人的正规设置”,因此以为此处的中书舍人是
(第441页)。
按世祖至“王恽沿用唐宋制度对王复中书省属员职务的雅称”
元七年(1270),曾一度考虑仿唐宋制度并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
计划虽未实施,但却“用前代三省属官制”在中书省设立了给事中二员、中书舍人二员。
中书舍人掌“外制”,与翰林学士掌“内制”相对,其职掌亦与唐宋相同。
据王恽所载,王复出知不过这一制度仅维持一年,到至元八年即告废罢。
[25]
归德府的时间恰是至元八年春,可知他的中书舍人职务货真价实,并非拟古的“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