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纳里.docx
《弗兰纳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弗兰纳里.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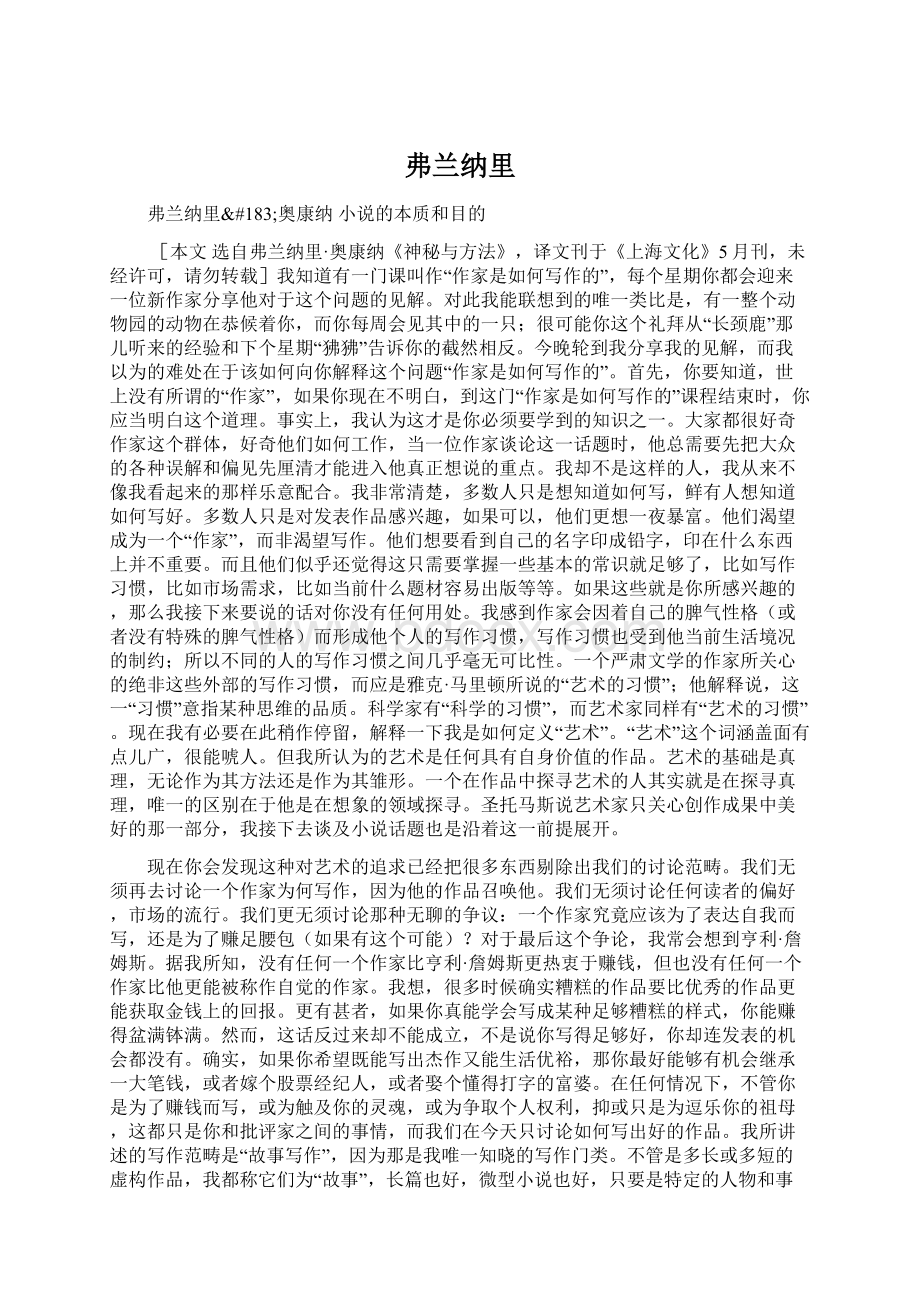
弗兰纳里
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的本质和目的
[本文选自弗兰纳里·奥康纳《神秘与方法》,译文刊于《上海文化》5月刊,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我知道有一门课叫作“作家是如何写作的”,每个星期你都会迎来一位新作家分享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
对此我能联想到的唯一类比是,有一整个动物园的动物在恭候着你,而你每周会见其中的一只;很可能你这个礼拜从“长颈鹿”那儿听来的经验和下个星期“狒狒”告诉你的截然相反。
今晚轮到我分享我的见解,而我以为的难处在于该如何向你解释这个问题“作家是如何写作的”。
首先,你要知道,世上没有所谓的“作家”,如果你现在不明白,到这门“作家是如何写作的”课程结束时,你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事实上,我认为这才是你必须要学到的知识之一。
大家都很好奇作家这个群体,好奇他们如何工作,当一位作家谈论这一话题时,他总需要先把大众的各种误解和偏见先厘清才能进入他真正想说的重点。
我却不是这样的人,我从来不像我看起来的那样乐意配合。
我非常清楚,多数人只是想知道如何写,鲜有人想知道如何写好。
多数人只是对发表作品感兴趣,如果可以,他们更想一夜暴富。
他们渴望成为一个“作家”,而非渴望写作。
他们想要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印在什么东西上并不重要。
而且他们似乎还觉得这只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就足够了,比如写作习惯,比如市场需求,比如当前什么题材容易出版等等。
如果这些就是你所感兴趣的,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对你没有任何用处。
我感到作家会因着自己的脾气性格(或者没有特殊的脾气性格)而形成他个人的写作习惯,写作习惯也受到他当前生活境况的制约;所以不同的人的写作习惯之间几乎毫无可比性。
一个严肃文学的作家所关心的绝非这些外部的写作习惯,而应是雅克·马里顿所说的“艺术的习惯”;他解释说,这一“习惯”意指某种思维的品质。
科学家有“科学的习惯”,而艺术家同样有“艺术的习惯”。
现在我有必要在此稍作停留,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定义“艺术”。
“艺术”这个词涵盖面有点儿广,很能唬人。
但我所认为的艺术是任何具有自身价值的作品。
艺术的基础是真理,无论作为其方法还是作为其雏形。
一个在作品中探寻艺术的人其实就是在探寻真理,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是在想象的领域探寻。
圣托马斯说艺术家只关心创作成果中美好的那一部分,我接下去谈及小说话题也是沿着这一前提展开。
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对艺术的追求已经把很多东西剔除出我们的讨论范畴。
我们无须再去讨论一个作家为何写作,因为他的作品召唤他。
我们无须讨论任何读者的偏好,市场的流行。
我们更无须讨论那种无聊的争议:
一个作家究竟应该为了表达自我而写,还是为了赚足腰包(如果有这个可能)?
对于最后这个争论,我常会想到亨利·詹姆斯。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比亨利·詹姆斯更热衷于赚钱,但也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比他更能被称作自觉的作家。
我想,很多时候确实糟糕的作品要比优秀的作品更能获取金钱上的回报。
更有甚者,如果你真能学会写成某种足够糟糕的样式,你能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这话反过来却不能成立,不是说你写得足够好,你却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
确实,如果你希望既能写出杰作又能生活优裕,那你最好能够有机会继承一大笔钱,或者嫁个股票经纪人,或者娶个懂得打字的富婆。
在任何情况下,不管你是为了赚钱而写,或为触及你的灵魂,或为争取个人权利,抑或只是为逗乐你的祖母,这都只是你和批评家之间的事情,而我们在今天只讨论如何写出好的作品。
我所讲述的写作范畴是“故事写作”,因为那是我唯一知晓的写作门类。
不管是多长或多短的虚构作品,我都称它们为“故事”,长篇也好,微型小说也好,只要是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有机组成最终构成有深意的叙事,我都称这样的小说为“故事”。
我发现大多数人就算坐下来动笔写个故事也不一定知道什么是“故事”。
他们会发现他们画了张配有简要说明的速写,或者写了篇配有速写画的随笔,或者写了碰巧里边有个人物的社论,又或写了意在说明某个大道理的案例,再或其他什么大杂烩。
等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在写“故事”的时候,他们觉得最好的补救方式就是去学学他们认定的“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或者“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
在很多人眼里,技巧是个固定的东西,是个你能将素材转化为作品的数学公式;然而在最好的故事里,技巧浑然天成,是从素材里自然生长出的部分,又或者这样说,是从未被写过的,全新的“自然生长”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聊聊“故事”,所以我想谈谈我眼中小说的“最小公分母”——事实上,这是个具体的东西——以及从它衍生出来的其他侧面。
这个“最小公分母”和人的感官密不可分,因为小说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我们的感知器官所决定的。
人类的知识始于感知,故事也始于人所感知到的部分。
写故事的人调动读者的感官,你无法用抽象的理念调动别人的感官。
对大多数人来说,比起陈述一个抽象的理念,描述并且重新创造他们切实所见的东西要困难得多。
然而小说的世界全是切实的东西,这也是刚开始写作的人不屑于重新创造的部分。
他们最初总是被强烈的情感和虚幻的理念所吸引。
他们叫嚣着成为先锋派,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想写故事,而是想为某个空洞的构想搭架子。
他们关心问题,却不关心人,关心宏大的议题,却不关心每个人存在的肌理,关心历史上的案例和所有能引起社会反响的事件,却不关心真正构成人类困境的那些确确实实的生活细节。
摩尼教徒区分精神和物质,对他们而言,所有物质都是罪恶的产物。
他们追求纯粹的精神,而且希望摒弃任何物质的干扰,直达精神的彼岸。
现代精神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并影响了与之相关的现代思维方式,但要这样写小说就着实困难了(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小说很大程度上必须是“有血有肉”的艺术。
一个最常见也最令人伤感的现象是,有些作者有着极丰富的智识,又有着异常敏锐的心理洞察能力,但是他却试图仅仅凭借这些来写小说。
这样的作家会一次次地拒绝书写饱含激情或者充满观察细节的语段,其结果是他们的作品极其乏味。
事实上,收集素材是小说作家的一项最基础也最卑微的工作。
小说就是关于任何人生于尘土归于尘土的事情,如果你不想搞得自己满身尘埃,那你不应该奢望着写小说。
写小说不是一份你所以为的“体面”的工作。
当小说作家最终认清这才是小说的真相,并且打定主意要继续下去,那他就必须认清写小说将会是一项多么艰苦的工作。
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女作家曾写信告诉我,她从福楼拜那里学到,要把一样东西“写活”,至少要让读者经历三次震撼的感官冲击;她还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五种感官,所以才必需有至少“三次”之说。
如果你忽视了其中任何的感官体验,你的小说就可能写砸,而如果你同时忽视了两种以上的感官体验,那么你笔下的人物几乎是不在场的。
翻开《包法利夫人》,你会感到惊艳,因为其中所有的语段都可以上述这个标准检验,但全书中有一个特别的段落尤其使我折服,使我不得不停下来感叹作者的笔力。
福楼拜为我们描绘正在弹奏钢琴的爱玛,查尔斯在一旁凝视她。
福楼拜如此写道:
“至于钢琴,她的手指在琴键上移动得愈快,他就愈是赞叹不已。
她挺直身子敲击琴键,从高音区一口气弹到低音区。
这架旧钢琴很久没有校音了,经她这么一弹,发出重叠的颤音,窗子开着的时候,一直能传到村子的那头,执达吏的书记员光着头、穿着便鞋从大路上走过,常会掖着文件驻足聆听。
”你越多次阅读这样的语段,你可以从中受益的东西也就越多。
最终,我们和爱玛一起,听这架古旧的钢琴“发出重叠的颤音”,而在村子的那一头,我们正在和这位栩栩如生的穿着便鞋的书记员一同从大路上走过。
就小说之后爱玛的命运而言,我们很可能觉得,这架钢琴有没有发出重叠的颤音,又或者这个书记员是不是穿着便鞋,手里有没有掖着文件都无关紧要,但是福楼拜必需创造出一个可信的村镇,好把爱玛置于其中。
请永远记得,小说作家应该首先给他笔下的书记员穿上便鞋,再去关心那些宏大的理念和涌动的情感。
当然,这恰恰是有些人所鄙夷的。
这也是狭义的自然主义走向穷途末路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作品中,细节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这对生活来说是其自然属性,对作品来说也是其自然属性。
在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完全写实,而不做任何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者。
艺术是一种选择,艺术的真实正在于那些使艺术作品“活”起来的真实。
和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是一段更漫长的累积细节的过程。
短篇小说比长篇需要更戏剧化的过程,因为短篇小说中更多的目的将要在更有限的篇幅中达成,细节必需承载更多的短时力量。
在好的小说中,特定的细节会从这个故事里汲取深意,当这样的细节出现,它们就成为了象征。
而今“象征”这个词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正如“艺术”这个词一样。
他们似乎觉得象征是作家有意放置在文本里的,其目的是唬住普通读者——有点类似文学共济会里的暗号。
他们似乎认为这是作家在表达一种他事实上没有在表达的东西,而如果他们有幸读到一部饱受赞誉的象征作品,他们对待这部作品的方式就好像在解答一道代数难题,找到X。
当他们真的找到了,或者认为他们找到了这个X,他们就会充满成就感,仿佛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个故事。
很多学生带着“理解”故事的目的来阅读作品,反而把“理解”这一过程变得复杂,把自己弄糊涂了。
我认为,对于小说作家本人而言,他运用象征只是因为他的作品需要它。
你可以说象征是重要的文学技巧,但在此之外它还作为点睛的细节同时作用于故事表层和深层,拓宽小说的所有维度。
我认为正确的读书路径始终是去注意书里发生了什么,不过对于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更多的故事发生在小说肌理,是我们第一眼没有注意到的,甚至是我们的双眼看不到的。
我们的思维更多不是被书里的象征符号牵引,而是被小说肌理发生的事件吸引。
有些批评家说小说在多个层面运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象征越真实,它就可以引你抵达越深的地方,它也可以展示更多的涵义。
以我本人的作品《慧血(WiseBlood)》为例,主人公的鼠灰色轿车既是他的布道台又是他的棺木,同时在他自己眼里,这也是他助逃亡的工具,当然,他没有真正意义上逃离他的困境,直到这辆车被巡逻警推下悬崖。
这辆车是某种死亡象征,象征生命中时刻蕴藏着死亡,而他的“失明”则是生的象征,是死亡中的一线生机。
正因为书中有了这些涵义,才使得这部作品如此重要。
即便读者不一定读出这些深意,但并不妨碍这些象征对读者产生影响。
这是现代小说作者隐藏或说遮掩他们的主旨的方式。
小说作者需要拥有或者习得的那种让小说别具深意的眼光,我称之为“洞悉隐秘意义的眼光”,这是一种能够从一个生活的景象或处境中看到各种不同现实维度的眼光。
中世纪的《圣经》诠释者找到三条开掘神圣经文的路径:
一条他们称作寓言诠释(allegorical),一个具体的故事指向一个具体的道理;第二条,他们称作道德诠释(tropological/moral),意在找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第三条则是隐秘意义的诠释(anagogical),是看到上帝恩赐的生命(theDivinelife)和我们个体使命之间的联系。
尽管这原是给《圣经》做注解的方法,它也可以成为我们面对一切艺术创作的态度,成为囊括最多可能性的阅读方式,而且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小说作者下定决心要写出永久进入文学史的作品,那他就必须培养自己这种从生活细节中见微知著的眼光。
这听起来像悖论,但却是事实:
看待生活的视野越是宽广,越是复杂,这样的视野就越容易被压缩到小说里。
人们总习惯这么问:
“你的这个小说的主旨是什么?
”他们期盼你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
“我的这个小说的主旨是机器发明以后,中产阶级需要面对的经济压力”或诸如此类的胡扯。
当他们得到这样一个答案后,他们就会心满意足地离开,而且觉得再没有必要读这个小说了。
有些人认为你读了一个故事,就为获得一个涵义,然而对于小说作者来说,整个故事本身就是小说的涵义所在,因为这是人生经历,而非抽象的概念。
很多人眼中小说的另一大特征在于,小说有意写得让读者觉得故事就发生在他们身边。
这不是说读者必须把自己代入小说中的角色,或者对里面的角色产生同情,或诸如此类的情感投射。
这仅仅意味着小说应当呈现鲜活的生活,而非做新闻报道。
另一种类似的说法是,小说虽是叙事的艺术,但非常仰仗戏剧元素。
故事的戏剧性和舞台表演的戏剧性不完全相同,但如若你对小说的发展史有所了解,你会知道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样式,在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