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Word下载.docx
《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Word下载.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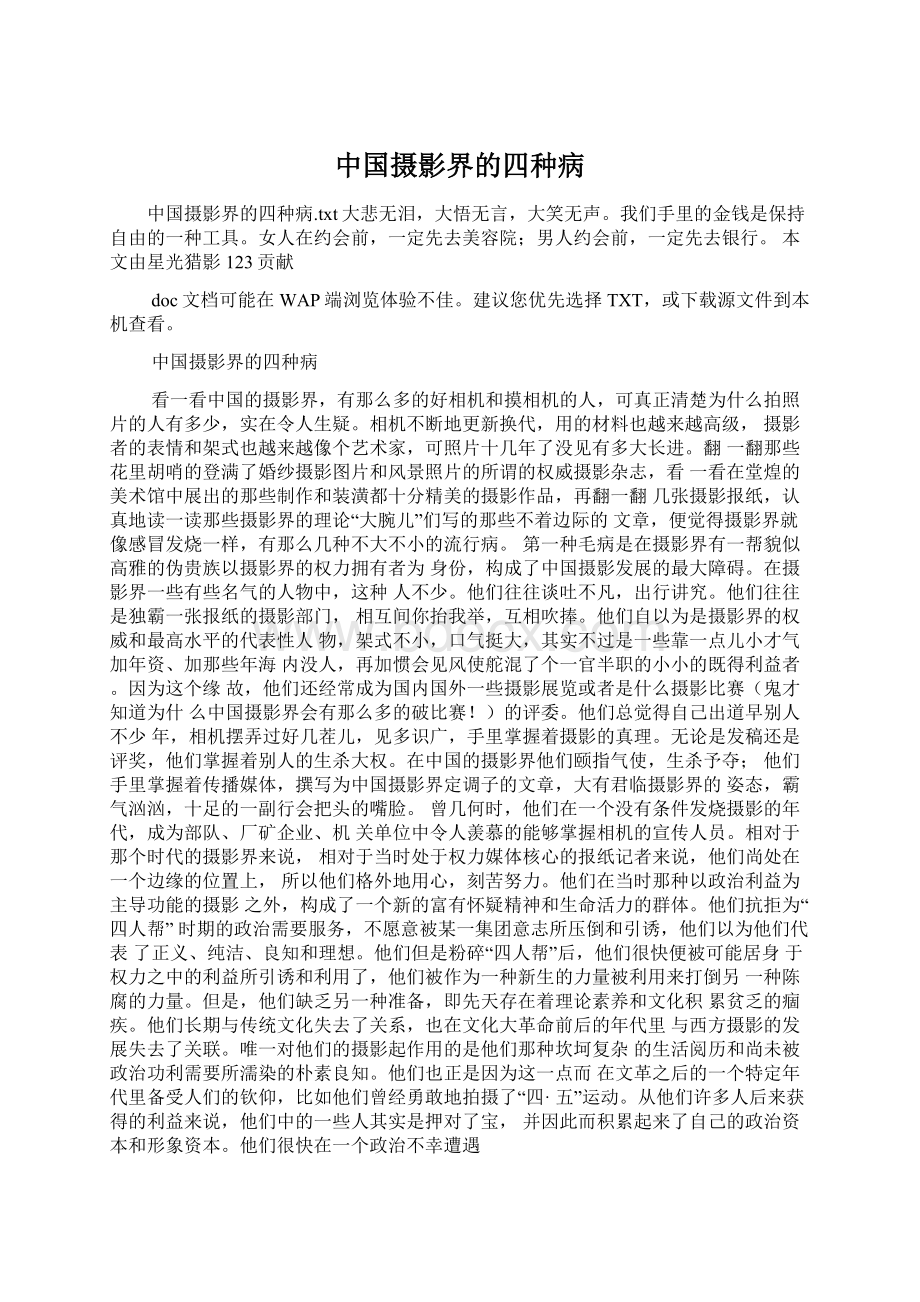
他们手里掌握着传播媒体,撰写为中国摄影界定调子的文章,大有君临摄影界的姿态,霸气汹汹,十足的一副行会把头的嘴脸。
曾几何时,他们在一个没有条件发烧摄影的年代,成为部队、厂矿企业、机关单位中令人羡慕的能够掌握相机的宣传人员。
相对于那个时代的摄影界来说,相对于当时处于权力媒体核心的报纸记者来说,他们尚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所以他们格外地用心,刻苦努力。
他们在当时那种以政治利益为主导功能的摄影之外,构成了一个新的富有怀疑精神和生命活力的群体。
他们抗拒为“四人帮”时期的政治需要服务,不愿意被某一集团意志所压倒和引诱,他们以为他们代表了正义、纯洁、良知和理想。
他们但是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很快便被可能居身于权力之中的利益所引诱和利用了,他们被作为一种新生的力量被利用来打倒另一种陈腐的力量。
但是,他们缺乏另一种准备,即先天存在着理论素养和文化积累贫乏的痼疾。
他们长期与传统文化失去了关系,也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年代里与西方摄影的发展失去了关联。
唯一对他们的摄影起作用的是他们那种坎坷复杂的生活阅历和尚未被政治功利需要所濡染的朴素良知。
他们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在文革之后的一个特定年代里备受人们的钦仰,比如他们曾经勇敢地拍摄了“四·
五”运动。
从他们许多人后来获得的利益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是押对了宝,并因此而积累起来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形象资本。
他们很快在一个政治不幸遭遇
可以交换得到相当利益的特殊时期,被人们看中并加以信任和重用了。
出于一个时期的一种新的需要,出于此时摄影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具有的神圣地位,也出于他们在摄影之外并无什么特别的才能和优势,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快成了各大报刊的摄影方面的权威人物,并且很快分到了房子,获得了职称、职位和在80年代初时无人指责和怀疑的声誉地位。
就这一结果来说,这些人到80年代初时,已经达到了他们的颠峰状态。
他们的摄影观念、手法、可能达到的成就,此时已经到达了尽头。
他们想超越四·
五运动时的那种摄影观念,但就他们自身的积累而言,他们缺乏起码的理论准备,无法从更广大更完整的角度去判断和从事摄影工作,因为他们的一切摄影活动都几乎是以直觉为其动力的。
所以,像其它人一样不能免俗,这些名声显赫但严重文化底子准备不足的摄影家“摄而优则仕”,很快便当官儿去了。
当官儿没有什么不对,这种活儿总得有人去干。
问题是当官儿不仅没有使他们在历史、文化、摄影美学发展的脉络等等方面及时地补上这早就欠缺的一课,而且使这些文化底蕴不足的摄影家一下子处在了一个高高在上、掌握了中国摄影生杀大权的位置上。
他们的这种先天的不足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摄影发展中,很快便显现了出来,特别是当我们横向地与当代中国的美术界或者是文学界进行比较时,这种营养不良和先天不足更为明显。
说实话,这批人直到今天拍的照片,和他们20年前拍的照片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和长进。
他们依然在依靠早先对摄影的那种简单的理解和生活经验以及个体直觉力、甚至靠一时的情绪冲动这几样东西来支撑起他们的摄影活动。
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些很快进入大学进行深造,并且在80年代初、中期毕业的人中,有很多开始拿起了相机。
他们没有什么名气,一切从头做起。
但他们一上手便重新与世界摄影的最新潮流发生了关系。
他们也不受什么固定的框框约束,他们追随库德卡、威金、索德克、阿勃丝、雪曼、布拉塞、法兰克、克莱因、马克,搞新闻摄影的一上来就是荷赛的美学指标。
尽管这种追随有它的问题,但是,相比于这批充满活力的摄影新人来说,那些功成名就的摄影家理论及文化功底明显不足的一面开始显露出来。
他们的积累中似乎只有一个布勒松或者是亚当斯;
他们多数是一些搞报道摄影的行家,但对摄影的复杂功能不闻不知,总是对报道摄影不自信,总是十分混乱地在觉得他们是在搞什么艺术,好像不说自己搞的是“摄影艺术”或者是“艺术摄影”就是降低了自己的身分一样;
他们十分内行而且严肃地在那里干一些怎样给照片起一个非常“艺术”的傻名字之类的特别土的事儿;
然后还对新起来的这些摄影家指手划脚,说这照片找不到焦距,那照片曝光不行,俨然一副教师爷派头;
而且他们把持着国内几份少得可怜的摄影报纸和杂志,死活不发表他们的东西,不让这些新生的摄影家冒出来。
这些人的权威地位在一个摄影功能不断分化的时代,在一个艺术摄影的观念和语言迅速转换的时代,在一个根本就不尿你那个权威地位的时代,受到了蔑视和挑战;
相机的广泛普及也使他们过去那种谁掌握相机就等于是掌握了摄影的专制地位迅速丧失了;
而他们较早就熟知和习惯的那种摄影语言在今天也已经不足以使他们独霸天下了。
仅就艺术摄影在今天的形态和发展而言,讲求思想和观念的显现,讲求摄
影与其它艺术语言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的新的摄影形态,使那些本来就缺少理论准备和没有观念头脑的摄影家们一下子就晕头了,一下子就亮出了令人难堪的家底儿。
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说的那样,那些毫无理论准备和功底的摄影界的权威人物过去看上去像个猴子一样,本来坐在那里时指手划脚人模人样还挺唬人,可一旦把他们拉到今天这个他们靠直觉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经验已经无法判断摄影的时代,就等于是把他们哄到树上去了,结果我们看到因为着急和闹不明白而在树上呲牙乱叫的这些猴子们露出了平时我们看不到的两块红屁股。
但他们自己的感觉仍然很好,他们开始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博学和有修养,比如在互联网上讨论讨论纪实摄影,说一些十二分小儿科的话还拿出个挺严肃的架式来;
再比如发烧音乐什么的。
他们总要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他们那种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的权威表情来。
你还得敬仰着他们,视他们为先辈,为无法企及的高峰,仿佛将来随着他们的逝去,摄影也将会从这个国家消失掉那样。
他们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他们经常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组织个什么发奖会,或者经常有人掏钱请他们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到处搞什么摄影联谊会,到处去找摄影界大腕儿的感觉,而且每到一处都会得到那帮摄影业余爱好者众星捧月般的待遇。
他们在地方上一旦出行都会有摩托车开道,警笛长鸣,招摇过市,向你显示他们是中国摄影这块地皮的绝对霸主,谁都怀疑不得!
老子天下第一,谁都得有求于我!
中国不就是这么两张摄影报纸吗?
不就是这么几本少得可怜的摄影杂志吗?
你想发表照片出出名吗?
你不求我求谁去?
真是牛得一塌糊涂。
其实,除了一帮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摄影到底是什么的头脑简单、被这些摄影“大腕们”唬住的发烧友之外,除了把那份报纸的订数提上来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人把他们当回子事儿了。
这些人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摄影界的新权贵。
这些人根本就不再想关心摄影本身的事。
他们的摄影观念早已经过时了,他们不想、也想不出在观念上如何超越自己。
他们只是一些曾经靠着摄影得到了一些利益而现在不想丧失这些利益的人。
因为他们之间靠一种江湖上的“哥们儿”关系互相勾结、串连起来,形成了中国摄影界一帮低俗不堪却又霸气十足的新权贵。
估计他们也就这么着了,但你别想让他们轻易地放弃这种虚假的权威的架式,因为那样他会丧失掉许多已经到手的利益,比如说名气,比如说职位,比如说评委资格,等等。
另有一些人,可以被看作是摄影界的技术伪贵族。
他们是一些摄影器材和摄影技术方面的专家。
他们格外讲究照片的专业素质,满嘴的影调、颗粒、锐度等等这些听上去特别唬人的专业技术术语,并且特别讲求以此来判断一幅照片的好坏高下。
这些人把相机、镜头、暗房技术看成摄影的本质,并且以专家自居,以此而显得高傲不凡。
这些人经常在一起集会,每次到一块儿便是扛着价格昂贵的各式相机,浑身披挂,然后在一起比来比去,仿佛不是来说摄影的,而是倒卖器材来了!
他们是一帮地到的器材发烧友。
他们在报刊上写文章,谈的全是相机厂
的工程师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摄影家的问题。
他们认为,无论你拍的照片内涵如何,无论你拍的照片有什么样的精神价值或者社会价值,如果你的照片的技术质量达不到他们认可的那些指标,便不被看作是“上档次”的摄影艺术。
他们将拥有不同相机的人分为三六九等。
相机在他们眼里是一个摄影从业人员的身分,他因为拥有名贵的相机而比别人高出一头去(借以显示他的财富足以买得起如此昂贵的相机,以在别人面前显示他的有钱?
)。
他们的傲视同辈,仅仅是因为他是相机方面的技术专家。
他们一天到晚一见面就是谈这相机那相机,谈什么大制作,谈这相纸、那胶卷。
这种姿态不像摄影家,而像个照相器材店的伙计。
但他们又处处以搞艺术自居,而且自以为是摄影这一方地界的另一种权威人物,这就使他们成为目前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另一支障碍的力量。
摄影界的第二种病,是流行一种虚伪的纯朴风。
表现乡村风情,表现农民的纯朴与生活的自然天真,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美术界曾成一时风气,但到80年代中期,这种潮流便结束了,因为那些下过乡的画家们不再沉湎于对往事的回想之中,而转过来面对80年代中期以后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了。
摄影界则不然,好像国的摄影家有那么一种浓重的农民情结一样,一上手便把镜头对准了农民,到现在也对农民不依不饶。
摄影界的这种毛病的表现较为复杂,大体可分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的纯朴表现在那些从小身居城市,吃商品粮长大的摄影家身上。
他们在城市中呆腻歪了,然后想到山野村落中走走。
他们自命是对农民和乡村生活充满了热爱,并且自命为到农村去拍照片是什么“回归大自然”。
于是他们借出公差或者是假期的机会,或者干脆就是请“创作假”(所谓的摄影“作品”竟然是在创作假里造出来的,真是见鬼了!
),而且内心还很神圣地奔赴那些穷乡僻壤,而且还是越穷的地方越好,不穷的地方不过瘾,最好是穷得一家人只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的那种地方,才是他们认为摄影家创作的好地方。
他们奔赴那里,拍农民的生活,拍农民的表情,拍农民的黑黝黝的没有虚肉的后背(据说是这个部位象征着民族的脊梁!
),而且努力地要去拍出一点儿苍桑感来。
一边拍,一边脑子里想着早些年四川画家罗中立的那幅油画《父亲》。
其实此时他的父亲正坐在北京一座豪华的酒楼里揽红拥翠,胡吃海撮。
这种摄影不过是一种旅游观光客式的猎奇的过程。
他们在这种“旅游”(他们称为是“搞创作”)的过程中,放松自己在喧哗嚣闹的都市生活中疲惫已久的身心。
他只不过是在乡村生活中缓解了自己的问题,(他们称作是“净化了心灵”!
)不过是在农民的脸上和那些由于生活的困苦与拮据过早衰老而带来的皱纹里,在农村孩子肮脏的小脸上和蓬乱的头发中,找到了他身居都市高楼居室中想象出来的东西。
他在农民那些陌生的眼中看到了好奇和对他这个来自城市中人的敬和畏。
他来到乡间,他的身分(城市人?
记者?
艺术家?
)使他居高临下,使他不像在城市生活中有那种因平等而带来的失落感、紧张感和威胁感。
相反,他作为一个有着特殊身分的身穿满是口袋的衣服,背着好几架奇形怪状的高级相机的城市人,他走在乡村之中只对别人构成一种威胁和征服。
他因这种身分和征服而感到满足和优越。
然后他以一种尽可
能低的姿态来与农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当然不会同劳动,闲时还与房东家孩子玩一玩儿,让孩子摸一摸他的相机什么的。
岂不知,这正是他显示其威胁和优越感的方式。
在农民的眼中,你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手持一架古怪的相机对着他们咔嚓咔嚓地响着。
他们不知道你在对他们干些什么,他们感到恐惧,但他们又不敢拒绝你的侵入,他们只能是茫然不知所措。
他们知道你在做一些类似小偷的事情或者是傻瓜的事情。
他们听不懂你的摄影艺术,他们也不想成为你的艺术中的一部分。
他们如果允许你拍照的话,也不过是想通过你为他们拍下一张照片来然后等你回城后寄给他们,但他们不知道你永远不会寄给他们这张照片。
他们在此生活、呼吸、生儿育女。
他们纯朴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纯朴的,你来表现他们什么样的纯朴?
在他们的判断里,你不过是跑到这里拿走了几件他们的东西,然后回到城市里挂到屋中借此回忆你在乡村渡过的那些类似村长或者是大队支部书记的优越生活而已。
你来了,你拍了,你走了。
而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本来自然平静地生活着,你干扰了他们一下,走时还顺手提走了几只吃完肉之后挂在屋檐下的牛头或者羊头。
而你走后他们依然一如既往地活着。
你解决的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安抚的是你自己的内心焦虑感。
你表现的纯朴是你想象的东西,和这些生于斯长于斯,最终归结于斯的人们没有什么关系。
你拍下的纯朴,不过是你拣来的旅游点的一块石头,一件纪念品,借以证实你到过那里,你关注过这些朴素的事物,并且向他们炫耀你的这种临幸式的到达。
你的这种对农民纯朴生活的向往,从骨子里就是装腔作势,因为你无论如何也不想在此生活下去,就像当年你上山下乡返城后成为了什么狗屁作家便将下乡的生活忆苦一般写成“伤痕文学”那样。
你下乡生活于这穷困的村落时便感到痛不欲生,遍体伤痕,老大的不情愿;
回到城里生活时你再看这种穷困时便成了你要用摄影去表现的什么“纯朴”,要不就拿出个“人文关怀”的架式。
而真正的农民在你来之前就这么活着,在你走之后他们仍然世世代代地活下去,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伤痕,也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纯朴过。
作为摄影家的你只所以作如此想,是因为你从来就是一个以自己的利益得失进行价值判断的人,你从来没有超越个人而站在更高的境界中正视过别人的生存状况。
所以你拍下的这些照片如同电视里、音乐台中每日在唱的那些《纤夫的爱》、《九月九的酒》等等伪民歌一样虚伪和令人作呕。
如此而已。
另一种表现“纯朴”的摄影出自那些当年生活在农村的、后来当了兵、上了学、到城市中生活的人之手。
他们以另外的一种姿态表现出另外的一种虚伪的纯朴情绪,借以回避他们那种固执的自卑感和永远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那种内心焦虑感。
这些摄影家较能与乡村生活融为一体,这源于他出身的那种与乡村的血缘关系。
但他真正作为一个农民时,他并未充分地感受到生活中有没有纯朴与自然,或者是感到这种纯朴自然好不好。
他在乡村生活时感到的更多的是生活的馈乏、艰辛、劳顿、穷困、发愁、为老婆孩子、为老人、为盖房、纳税、生老病死无尽地愁苦。
他渴望过城里人那种“不纯朴自然”的生活。
而这些摄影家与前面我们说的那些摄影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显然是经受过农民生活的困苦而后离开乡村到城镇中吃商品粮生活的人。
他们
的整体生活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但他们进入城镇生活后,又迎来了新的问题,即他们除了通过发愤努力以求事业有成、以最终超越自身的卑微感之外,他们自以为他们重新发现了他们原来的那种乡村生活在精神上给他们一种人与外在环境和谐一体的感觉,而他们感到在城市中失去了这种令他们自信而且没有内在冲突的实在的感觉。
与那些到乡村去旅游观光的城市摄影家们相比,他们比较容易进入或者说深入乡村生活,但他们仍然无法获得像他们标榜的那种认同感。
因为他们重新返回这种生活中来时,是以一个怀旧者回忆他往日时光的带有很强感慨和感伤的眼光来拍照片的。
他像这些农民一样如此生活过,但他那时对这种生活没有任何的感觉,也没有思想过,更没有记录过。
现在他已是一个有学问、有头脑、手中有相机的人了。
他回来了,他现在是衣锦还乡,要把他以前经验过的生活通过现在这些农民的当下生活用手中的相机还原出来重现出来。
这些生活既是他的往日时光的重现,是他的一种资本,同时也以一种怀旧的情绪和悲天悯人的姿态表现了他对往日生活的不平。
他要做一个农民纯朴生活的发言者,因为他觉得他有资格来阐释这种生活,有理由去作为农民的代言人,替他们说话。
岂不知这种姿态也令人起疑。
除了他无法以这种“关怀”的悲悯姿态深入农民的当下生活之外,他这种代言人的姿态已类似于掠夺。
他拍下了他们的照片,并且是以一种合法合情的身分和方式得到了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会被发表,会成为这个摄影家的成就。
因为他来自农民,对农民深有了解,而使他的照片较能深入农民的生活这一点也会成为评价他的摄影水准之高的一条重要标准。
他最后其实是利用了自己这种源于农民的身分。
他通过这一转换方式,使自己作为一个农民的出身的卑微的感觉转化为一种优势--都市摄影家拍农民的纯朴拍不过他。
他因此会获得一种平衡感和成就感,会处身于城市之中再也不发怵。
他甚至还会因此而变得高傲而似乎有些深度。
这种方式拍摄到的纯朴的影像极像是一个家贼的所为,他利用了他的身分和农民与乡村对他的不戒备而偷走或出卖了这种纯朴。
他是唯一的获利者,他在拍取这些照片时已经与他拍摄的这些对象发生了不平等的关系。
可他还在以一个与乡村生活达到认同的艺术家自居。
其实他只不过索取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从最终的结果来说,他无助于也无益于他人的生活。
摄影界的第三种病,是许多摄影家怀有一种浓重的庄严伟大的情结。
也许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过于博大精深的缘故,也许是我们的摄影家们过于的匹夫有责的缘故,也许是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一直在宣传教化的缘故,摄影界一直在坚持着一种美术界早已放弃的美学,即一直在鼓努为力地表现一种庄严伟大的虚幻感觉,以至于这种表现本身构成了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和有史以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成为官方摄影评判和传媒最喜欢使用的标准。
它是爱国的,表现了祖国的伟大,山河的壮丽;
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经验的胸襟,因此有更高的境界;
它具有豪迈的气概和庄严肃穆的精神氛围;
它表现了人民热爱祖国的豪情,你敢怀疑它的正确性?
你敢说它不好?
这种摄影作品基本上是一些风景照片,它主要的影像就是拍长城、拍黄河壶口大瀑布、拍长江大峡、拍黄山、拍西藏高原、拍内蒙草原、拍天安门、拍人民英雄纪念碑、拍北京城的国庆节夜景,或者是拍上海的那座新起来的吊桥或者是拍安塞的腰鼓。
总之,他拉出来一个气势磅礴的架式,以表示这个国家的伟大和人民的有力量。
他们都是一些内心挺严肃的摄影家,他们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吃大苦耐大劳;
他们带着一大堆贵重的器材风餐露宿,爬到长城那些最危险的地方去,选取角度等待日出或者是日落时分,想把这堵墙拍得历史悠久,或者是灾难深重,或者是伟大而且辉煌;
他们乘游客稀少的时候赶往圆明园,在那几块耻辱的石头旁布满灯光拍来拍去,内心还一团悲愤深沉有一种百年苍桑之感。
这些摄影家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特别具有历史使命感,就像一群健美爱好者一样,喜欢把好不容易练出来的健子肉卖弄给别人看,以示他的肉比你的磁实!
问题是这种强努出来的或者说纯粹就是幻想出来的伟大庄严的感觉太空泛了,它缺乏足以引起我们深味的内涵。
从其精神价值来说,它不具有建设性,更无补于人民的身心健康。
这一类影像给人的感觉基本上类似于那些经常出现在电视台组织的大型文艺晚会上的歌手们唱的那些似乎气很足的歌,仔细听一听,全是些类似于大跃进时代的嘹亮口号,“啊……,长江!
”,“啊……,长城!
”,“啊……,黄河!
”,“祖国啊,母亲!
”,满口都是一些毫无实际内容的大话,根本不着边际。
说透了,只是一口气,气一泄了就没戏。
它引发人们一种不着边际的自豪感或者是老子天下第一式的虚妄和傲慢,仅此而已。
它并没有像人们提倡的和那些摄影家想象的那样能够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也没有使人充分地感受到其中有什么值得汲取的精神力量。
它实际上是构成了一种虚假的美学指标。
国内所有的摄影评论和评奖活动直到现在还在鼓励摄影家们追求达到这种虚假空泛毫无实际内涵的美学指标。
这种鼓励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它使摄影家脱离了内在体验的轨道,从而使他的摄影成为完全外在于他个人判断的一种功能性的活动。
摄影家事实上是在按照一种国家主义的美学指标来行动和工作,他自己的内心已经被这种虚假而空泛的爱国主义教育抽空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庄重伟大的幻觉。
他所有的摄影活动和影像都是受这种幻觉指引的结果。
由于摄影家都放弃了(而非超越了)自己,所以这种照片成为类型化的影像,而且从50年代末直到今天,看不出有多大变化。
摄影家在这种成为一个套路的影像中迷失了自己,丧失了个人的良知和判断。
就像那些以唱这类歌曲为业的歌手那样,只有一条好嗓子,而没有一个健全的脑子。
摄影只是他表现自己臣服于他人的一种献媚的姿态,或者是一种用自己的存在与别人的需要进行交换以获取丰衣足食的手段。
摄影根本就不是他选择的一种声音和语言,他还在这里说什么摄影?
摄影界的第四种毛病,是越来越多的摄影家热衷于制造一种造作的撒娇式的优美图像,并且倡导和实践一种十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摄影美学。
这种状态在今日的中国摄影界蔚成风气而且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这种摄影姿态的成因有
多种。
一方面是国内一些八流美学理论家对美学进行了一番十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并且通过传媒和我们的教育将这种理解广泛扩散开来,对人们的价值判断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他们认为所有艺术都要表现什么“真、善、美”,而他们所谓的“美”的事物基本上属于一种非常表面层次的能够引起人的生理愉悦快感的事物和形态。
我们的摄影从来就缺乏面对真实的勇气和行动。
其实他们并没有想到即使从经验的角度来说,所有“真”的事物几乎都是丑陋的,关于真实的体验从未给予人们什么美好的感觉。
而“善”也不过是一种“应该如此”的伦理禁忌;
“美”更只是一种内心幻觉。
人们喜欢“美”是因为我们从未到达过这样一个境界,是因为它永远是极遥远的一个所在。
美只给人希望,但它回避了许多人生实在的苦难。
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倡美的表现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给人以生活下去的信心,它恰恰表现了人们面对生存现实时的那种惶恐、回避和无望。
另一方面,潜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标准,特别是宋元以下,主阴柔的一流发展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特定的审美趣味,在那种貌似优雅清高的风度之中,是一种女性化的手无缚鸡之力的虚弱,同时也是一种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低能。
从那些执一柄扇子握一卷古书成天混迹于勾栏瓦舍与妓女们吟咏酬唱的古代文人,到今天那些动不动就满嘴喷着文化挽着苏小小在外滩上来来回回作文化苦旅状的大师,和那些在《读书》杂志上貌似正经君子一般成天卖弄那点儿无聊学问的学者教授,都是一路货色。
想想南宋,想想晚明,想想民国,看看当今,这等无聊文人的这点儿不成大器的小趣味都是一脉相承。
什么人约黄昏,雾里看花,小桥流水,落叶寒江;
西施、黛玉必成天病病歪歪才有姿容;
北京胡同必这么永远破旧下去才不失古都的文化风貌。
瞅瞅那些挂历、三十年代的月份牌、八、九十年代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