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Word下载.docx
《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Word下载.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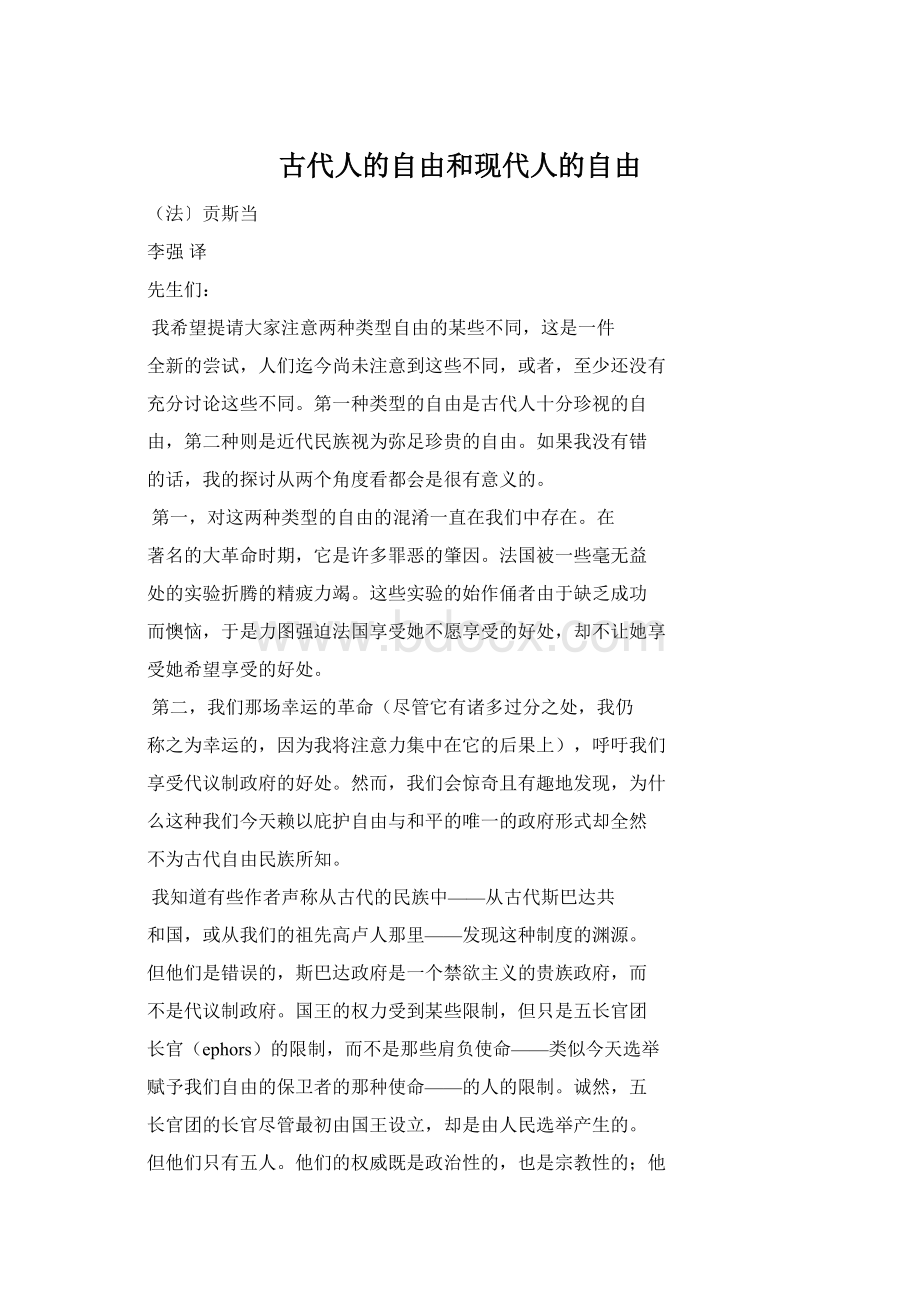
因此,罗马仅有代
议制度的微弱痕迹。
这一制度是现代人的发现。
而且,先生们,您将会看到,人
类在古代的条件不允许这种性质的制度的引人或设立。
古代的
民族既不可能感到对它的需求,也不可能欣赏它的价值。
他们
的社会组织引导他们欲求一种与代议制度赋予我们的自由截然
不同的自由。
今天晚上的演讲将集中向诸位展示这一事实。
首先,先生们,请问一下您自己,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
一个美国公民今天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涵义是什么?
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一个人
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
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
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
徙的权利。
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
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
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
或几小时。
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
当权者或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
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
府的行政行使某些影响的权利。
现在,我们将比较这种自由与
古代人的自由。
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
部分:
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
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
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其指责、谴责或豁免。
然则,如果
这就是古代人所谓的自由的话,他们亦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
完全服从是和这种集体性自由相容的。
你几乎看不到他们享受
任何我们上面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
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厉
监视。
个人相对于舆论、劳动、特别是宗教的独立性未得到丝毫
重视。
我们今天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宗教派别的自由
在古代人看来简直是犯罪与亵渎。
社会的权威机构干预那些在
我们看来最为有益的领域,阻碍个人的意志。
在斯巴达,Ther
pandrus不能在他的七弦竖琴上加一根弦,以免冒犯五人长官团
的长官。
而且,公共权威还干预大多数家庭内部关系。
年轻的
斯巴达人不能自由地看望他的新娘。
在罗马,监察官密切监视
着家庭生活。
法律规制习俗,由于习俗涉及所有事物,因此,几
乎没有哪一个领域不受法律的规制。
因此,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
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
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
与和平;
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
作为
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
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
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
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
死。
与此相对比,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
但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他也仅仅在表面上是主权者。
他的
主权是有限的,而且几乎常常被中止。
如果他在某些固定、偶尔
的时候行使主权的话(在这些时候,也会被谨慎与障碍所包围),
更经常地则是放弃主权。
先生们,我必须在此时稍停片刻,来预先考虑人们可能对我
发出的责难。
在古代有一个共和国,那里,集体机构对个人存在
的奴役并不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彻底。
这个共和国是十分著名
的:
你们会猜出我在讲雅典。
我将在下文讨论雅典、我将承认这
一事实,并揭示其原因。
我们将会看到为什么在所有古代国家
中,雅典与现代国家最为近似。
除雅典外,在所有其他地方,社
会的管辖权都毫无限制。
正如孔多塞所言,古代人没有个人自
由的概念。
可以这样说,人仅仅是机器,它的齿轮与传动装置
由法律来规制。
同样的服从情形亦可见于罗马共和国的黄金时
期。
那里,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市所吞没。
我们现在将追溯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这种本质区别的根
源。
所有古代的共和国都局限于狭小的领土上。
它们之间人口
最多、最强盛、规模最大者也无法与最小的现代国家相提并论。
狭小疆域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这些共和国的精神是好战的。
每个民族无休止地攻击其邻国或被邻国攻击。
这样,被彼此对
抗的必要性所驱动,它们不停彼此战斗或彼此威胁。
那些没有
征服野心的国家也不可能放下武器,以防止它们自己被征服。
所有国家都不得不以战争为代价来换取它们的安全、独立以及
存在本身。
这就是古代自由国家永恒的兴趣或者说几乎是习惯
性的关注。
最后,作为这种生存方式的另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所
有这些国家都有奴隶。
手工劳动的职业(在某些国家甚至包括
工业职业)都委托给带镣铐的人。
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
今天,最小
的国家也比斯巴达或存在长达五个世纪的罗马大得多。
由于启
蒙思想的发展,就连欧洲分裂为众多国家也更多是一种表面现
象,而不是真正的事实。
过去,每一民族形成一个孤立的大家
庭,它是其他民族家庭的天然敌人;
今天,在不同名称与社会组
织下生存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本质上是相当同质的。
他们已强
大到足够的程度,不必恐惧蛮族的游民。
他们也文明到足够的
程度,来发现战争是负担。
他们的一致倾向是和平。
这一不同导致另一不同。
战争的出现先于商业。
战争与商
业只不过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两个不同手段——这个目标就是得
到自己欲求的东西。
简单他说,商业是希望占有的人对占有者
缴纳的一种贡赋。
它是一种征服行为,是以相互同意的方式征
服一个人无法希望以暴力方式得到的东西。
一个永远是强者的
人决不会接受商业这一概念。
是经验引导他诉诸商业。
经验向
他证明,战争,即运用自己的强力反对其他人的强力,使他可能
遭遇形形色色的障碍与失败,而商业则是求得他人权益符合自
己适当权益的一种较为温和但较为确定的方法。
战争是彻头彻
尾的冲动,而商业则是计算。
这就意味着,一个商业代替战争的
时代必然会到来。
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一时代。
这并不意味着在古代没有贸易民族。
但是,这些民族在某
种程度上只是一种例外,而不是通则。
这次讲演的篇幅不容许
我详细阐释所有遏制商业进步的障碍。
诸位和我一样,对此十
分了解。
我将仅仅提及其中的一种障碍。
古代人对罗盘仪的无知意味着古代的航海家必须永远在海
岸附近航行。
穿过海格立斯柱,即直布罗陀海峡,被认为是最勇
敢的探险。
最善于航海的腓尼基人与迦太基人也只是在很晚的
时候才进行这种探险,他们的行为在很长时间没有模仿者。
雅典人中——我们将马上论及他们——航海企业支付的利息达
百分之六十,而现在只有百分之十二:
这就是远距离航海的想法
在当时显得多么危险。
此外,先生们,如果我允许自己离开目前的论题——不幸的
是,这将是冗长的,我将详细描述古代贸易民族的风俗、习惯以
及它们与其他民族贸易的方式,并以此向诸位展示:
古代贸易民
族的商业本身浸透了时代的精神,浸透了笼罩在这些民族周围
的战争与敌对的气氛。
那时,商业是一种幸运的意外,而在今
天,它是正常状态,是所有国家的唯一目标、普遍趋势与真正的
生活。
这些国家要求安定,要求舒适,要求能够提供舒适的工
业。
战争愈来愈不再是满足它们愿望的有效手段。
战争的危害
为个人提供的益处再也无法与和平的工作与有规则的交换所产
生的后果媲美。
对古代人而言,一场成功的战争既增加私人财
富,也增加公共财富,增加他们所分享的奴隶、贡赋与土地。
而
对现代人而言,即使一场成功的战争,其代价毫无疑问会超过其
价值。
最后,由于商业、宗教以及人类道德与知识的进步,欧洲各
国已不再存在奴隶。
自由人必须从事所有职业,提供社会的所
有需求。
先生们,这些不同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国家规模的扩大导致每一个人分享的政治重要性相
应降低。
在斯巴达与罗马,即使最卑微的公民也有权力。
而英
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普通公民却并非如此。
他的个人影响仅是
决定政府方向的社会意志之难以察党的组成部分。
第二,奴隶制的废除剥夺了自由民因奴隶从事大部分劳动
而造成的所有闲暇。
如果没有雅典的奴隶人口,20000雅典人
决不可能每日在公共广场议事。
第三,商业不同于战争,它不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一段无所事
事的间歇。
不断行使政治权利,日复一日讨论国家事务,争议,
商谈,派别斗争的所有环境与运动,必要的鼓动:
可以这样说;
古
代民族的生活被强制性地充满了这些必须履行的职责。
对古代
民族而言,没有这些职责,他们就会在无所事事的折磨下痛苦不
安。
而对于现代民族而言,这些职责只会造成困扰与疲倦。
现代民族,每一位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事业。
自己
得到的或希望得到的快乐。
他不希望其他事情分散自己的专
注,除非这种分散是短暂的,是尽可能少的。
最后,商业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
商业在没有权
威干预的情况下提供了人们的需求,满足了他们的欲望。
权威
的干预几乎总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几乎”,这种干预实
际上总是——令人困扰与窘迫的。
每一次集体权力希望干涉个
人思考,它便侵扰思考者。
每一次政府声称为我们做事情,它都
比我们自己做更无能、更昂贵。
先生们,我说过,我会回到雅典这一题目上来,雅典的例子
也许会被用来反驳我的某些论断,但实际上,它将印证我的所有
论断。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所有古希腊的共和国中,雅典与
贸易的关系最为密切:
因之,它容许公民享有比斯巴达与罗马
大得多的个人自由。
如果我可以进入历史细节讨论的话,我将
会向诸位展示,在雅典,商业消除了区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
若干区别。
雅典商人的精神与现代商人的精神颇为近似。
芝诺
芬告诉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商人把他们的资本从
阿提卡大陆运走,放在列岛的岛屿中。
商业使他们建立了货币
流通。
在伊索克拉底那里,有迹象表明汇票的使用。
请注意
他们的习俗如何与我们的习俗相似。
假如我再次引用芝诺芬的
话,诸位将会看到,丈夫在处理与女人的关系时,每当家庭充满
和平与庄重的友谊时便会心满意足。
他们体谅无法抵御自然之
强大力量诱惑的妻子。
他们会在无法抵御的激情的力量面前闭
上眼睛,原谅妻子的第一次软弱,忘记其第二次软弱。
在他们与
陌生人交往时,我们会看到他们将公民权利扩展到每一个人,只
要这个人携带家庭,迁徙到他们中间,兴办某种贸易或实业。
最
后,我们将会为他们那种对个人独立的超乎寻常的挚爱而震惊。
一位哲学家尝言,在斯巴达,当执政官传唤时,公民会加快脚步;
而一个雅典人如果被视为依附于执政官,他会感到绝望。
不过,由于决定古代民族特征的其他外部环境也存在于雅
典,由于存在奴隶人口以及领土极度狭小,我们在雅典也发现古
代自由所特有的特征。
人民制定法律,审查执政官的行为,宣召
伯里克利解释其行为,判处指挥Arginusae战争的将军们死刑。
与此相似的,还有陶片放逐法那种充满法律任意性的制度。
雅
典时代所有立法者都赞美这一制度,而我们却恰当地将它视为
一种令人憎恶的罪恶。
这一制度表明,在雅典,个人隶属于社会
整体的程度远远超过今天欧洲任何自由国家。
从我们上面的描述中可以得出,我们已经不再欣赏古代人
的自由了,那种自由表现为积极而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力。
我们
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
在古代,每
个人分享国家主权决不仅仅像我们今天那样是一个抽象的假
定。
每一位个人的意志都有真正的影响:
行使这种意志是一种
真实的、不断重复的乐趣。
惟其如此,古代人随时准备作出许多
牺牲,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及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力。
每个
人都因为自己的投票具有价值而自豪,他们从这种个人重要性
的感觉中发现巨大的补偿。
这种补偿对于今天的我们已不复存在。
个人淹没在广大民
众之中,他几乎从来感觉不到自己的影响。
他个人的意志也不
会给整体留下任何印记;
在他自己的眼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
实他自己的合作。
因此,行使政治权利为我们提供的乐趣仅仅是古代人从中
发现的一小部分。
但是,与此同时,文明的进步、时代的商业趋
势、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却无限扩展并丰富了个人幸福的
手段。
于是,我们必然会比古代人更为珍视我们的个人独立。
对
古代人而言,当他们为了政治权利而牺牲个人独立时,他们是以
较小牺牲换取较大所得;
而我们如果作出同样牺牲,我们便是以
较大损失换取较小所得。
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相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
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
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
私人快乐;
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
我在演讲一开始便说过,在我们那场旷日持久且充满风暴
的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清这些区别,引
发了无限的罪恶。
但愿我对他们的谴责不会过分严苛。
他们的
错误本身是情有可原的。
当一个人阅读古代那些优美的文字
时,当一个人追忆古代那些伟人的行动时,他不可能不感到一种
不可名状的特殊冲动,任何现代的东西都不可能激发这种冲动。
我们几乎可以说,在这些追忆面前,某种先于我们本身而存在的
古老的自然因素似乎在我们身上觉醒。
人们很难不怀念那个古
老的时代,那时,人的能力虽然沿着一条已经荆棘丛生的道路发
展,但他们从事如此广泛的职业,他们自身的权力如此强大,他
们有如此强烈的活力与尊严。
一旦我们沉湎于这种怀念,我们
便不可能不希望模仿我们所怀念的。
尤其当我们生活在邪恶的
政府之下时,这种感觉会十分深切:
这些邪恶政府尽管软弱无
力,但其施政充满压迫性,原则荒谬,行为卑劣,它们以专断权力
为后盾,为了自己而贬低人类。
某些人在今天仍然敢于在我们
面前赞誉这种政府,似乎我们某一大会忘记我们曾经是这些政
府顽固、无能及其被推翻的见证人与牺牲品。
我们的改革家的
目标是高尚而慷慨的。
在他们似乎揭示了新的方向之时,我们
之中谁没有感到内心充满希望?
即使在今天,当人们指出我们
最初的导师们犯了一些错误时,如果谁不觉得有必要表明这并
不意味着可以将他们从记忆中抹去,或放弃那些所有时代人类
的朋友都接受的观念,谁就会觉得可耻。
然而,这些人的理论导源于两位哲学家的著作,这两位哲学
家本人都未能认识到两千年的时间所导致的人的气质的变化。
我也许将在某个时候审视这些哲学家中最著名的一位(即卢梭)
的理论体系,我将向诸位显示,这位卓越的天才把属于另一世纪
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他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
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
毋庸
置疑,我将指出他的误解,揭示这一点很重要,不过,我将在批驳
时十分谨慎,在批评时不失敬意。
我肯定会避免与那些诋毁这
位伟人的人为伍。
假如有时我在某些特定观点上恰好显得与这
些人们一致,我便会怀疑自己。
为了使自己在某一局部问题上
与这些人一致时尚能自慰,我必须用我所有的精力否认并谴责
这些所谓的盟友。
不过,对真理的追求必须超越其他考虑,这些考虑能使一位
天才人物的荣誉以及一个享有巨大名声的人享有如此巨大的力
量。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卢梭并不是我将
要批评的错误的首要承担者。
这一错误更应归咎于卢梭的一位
后继者,这位后继者虽不及卢梭雄辩,但在道德的严峻方面不但
不比卢梭逊色,而且比前者夸张一百倍。
这位后继者就是马布
利神父(deMably),他是这样一种制度的代表,该制度根据古代
自由的教条,要求公民为了国家的主权而完全服从,要求个人为
了民族的自由而被奴役。
像卢梭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马布利犯了与古代人相同
的错误,即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自由。
对马布利而言,任何
手段只要能扩展他对入的存在中最倔强的部分控制住的权威似
乎就是好的。
他谴责人的独立性。
他在所有著作中表达的一个
遗憾是,法律只能控制行动。
他希望法律管制瞬息万变的思想
与意见,毫不留情地监视人们,不给人们留下任何可以逃避其权
力的避难所。
一旦他了解到某些压迫性方法——不论他是向哪
些人学到的——他便立即以为是自己的发现,并立即提议把它
作为效法的模式。
他像憎恶自己的敌人那样憎恶个人自由。
论他在历史上任何时期发现一个完全剥夺个人自由的国家,即
使这个国家并没有政治自由,他也会情不自禁地赞美它。
他曾
为埃及人欣喜若狂,因为他认为,在埃及人中,所有事情都是由
法律规定的,即使休息与日常需求也不例外:
所有事情都服从于
立法者的绝对统治。
一天中每时每刻都被赋予某种责任;
爱情
本身也是这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干涉的对象,正是法律依次打开
或关闭洞房床前的帷帐。
斯巴达那种将共和国的形式与对个人的奴役相结合的模式
在这位哲学家的精神中激起更生动的热情。
那些巨大的禁欲主
义的兵营在他看来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共和国的理想。
他对雅典
抱有深刻的蔑视,并乐于用一位杰出的贵族、院士描述法兰西学
院的话来描述这个希腊最早的国家:
“多么骇人听闻的专制!
那
里每个人都做他喜欢做的。
”我必须补充一句:
这位杰出贵族
所谈论的是三十年前的法兰西学院。
盂德斯鸠有一个相对而言不易激动、因而更具观察力的头
脑,他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
他为我所描述的古代与近代的那
些差异震惊,但未能揭示其真正的原因。
他认为,生活在平民政
府下的古希腊政治家不理解除美德外的任何其他权力。
而今天
的政治家则只谈论制造业、商业、金融、财富、甚至奢侈品。
将这种差异的原因归之于共和制与君主制。
而事实上应该归因
于古代与现代相反的精神。
无论是共和国的公民还是君主国的
臣民都希望得到快乐。
确实,在今天的社会情势下,没有人会不
希望得到快乐。
在今天的时代,那些挚爱自由、将自由置于法兰
西解放之上的人们,也就是那些热爱生活中所有快乐的人们。
这些人尤其珍视自由,他们把自由视为他们所珍爱的快乐的保
障。
在过去,哪里有自由,哪里的人们便可以忍受艰辛。
而在今
天,哪里有艰辛,哪里的人们就不得不忍受专制主义。
今天将一
个受奴役的民族变为斯已达人比把自由人变为斯巴达人更容
易。
那些被历史事件推到我们革命前沿的人们,由于其所受教
育的必然结果,醉心于一些过时的古代观念,这些观念由于我在
上文提及的那些哲学家而成为时尚。
这里有卢梭的哲学,其间
偶尔闪烁着真知的见,也不乏令人兴奋的雄辩的段落。
这里还
有马布利的质朴,他的不宽容,他对人类情欲的憎恨,他那迫切
希望禁锢所有人类激情的愿望,他关于法律效能的夸张的原则,
以及在他所推荐的与从前事实上曾经存在的东西之间的差异,
他反对财富甚至反对财产的主张。
所有这些都必然会吸引那些
被最近的胜利所激动的人们,这些人们已经取得凌驾于法律之
上的权力,于是迫切希望将这种权力延伸到所有方面。
两位诅
咒人类专制主义的高尚作家居然以格言方式拟定了法律条文,
这确是支持他们的宝贵渊源。
他们希望像若干自由国家曾经做
过的那样行使公共权力——他们从这些哲人的指引中知道这
些。
他们相信所有事情都必须屈从于集体意志,对个人权利的
所有限制都会由于对社会权力的参与而得到充分补偿。
先生们,我们都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基于对时代精
神的理解而建立的各种自由制度可以存活下来,但恢复起来的
古代人的大厦却崩溃了,尽管许多努力、许多英雄行为值得我们
景仰。
不容置辩的事实是,社会权力以其所有可能的方式伤害
个人独立,却无法摧毁对这种独立的需求。
我们的民族并未发
现对抽象主权的理想化分享值得她作出所需要的牺牲。
卢梭
的权威并未能使她相信自由的法律要比独裁的枷锁严苛一千
倍。
她对这些严苛的法律毫无欲求,她相信在某些时候,独裁的
枷锁比严苛的法律更值得拥有。
经验最终使她不再受骗。
她看
到过人治的专断权力比最差的法律更糟糕。
然而,法律也必须
有其限度。
先生们,如果我已经成功地使您接受这些事实必然导出的
结论的话,您将和我一样承认下列原则的真实性。
个人独立呈现代人的第一需求:
因此,任何人决不能要求现
代人作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
由此导出,许多倍受赞赏的制度在古代共和国曾阻碍个人
自由,在现代无法被接受。
先生们,您也许立即会觉得确立这一原则是多余的。
今天
的不少政府似乎无意效法古代共和国。
然而,尽管它们也许不
钟爱古代共和国的制度,它们对共和国的某些习俗却有一定的
感情。
令人不安的是,恰恰是这些习俗允许它们实行放逐、流放
与掠夺。
我记得在1802年,它们通过特殊委员会在法律中塞进
一个条款,将希腊的陶片放逐法引入法兰西。
为了使这一条款
得到批准,天知道有多少雄辩的发言者向我们阐述雅典的自由
以及为了维护这些自由个人必须作出的牺牲!
同样,最近,当胆
怯的当局畏首畏尾地试图准备举行选举时,一份很难被怀疑为
共和主义的杂志提议恢复罗马的监察官制度,以取消所有危险
的候选人。
因之,我并不以为我在从事一项无用的讨论,如果我可以就
这两个被大肆炫耀的制度说几句话,来支持我的论点的话。
雅典的陶片放逐制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即社会对其成员
有完全的权威。
在这一假定之上,该制度可以证明其合理性。
此外,在一个小国,当某一个人由于其崇高的威望、众多的门徒
以及辉煌的业绩,影响常常与大众的权力抗衡时,陶片放逐法似
乎是有用的。
然而,在我们这里,个人拥有社会必须尊重的权
利,而且,正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个人的利益被众多平等的或
更高贵的人的影响所湮没,任何以需要削弱这种影响为动机的
压迫都是无益的,因而也是不正义的。
任何人都无权流放一个
公民,除非这个公民被一个常设的法庭根据正式法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