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的盛世辉煌和市场繁荣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唐代长安的盛世辉煌和市场繁荣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唐代长安的盛世辉煌和市场繁荣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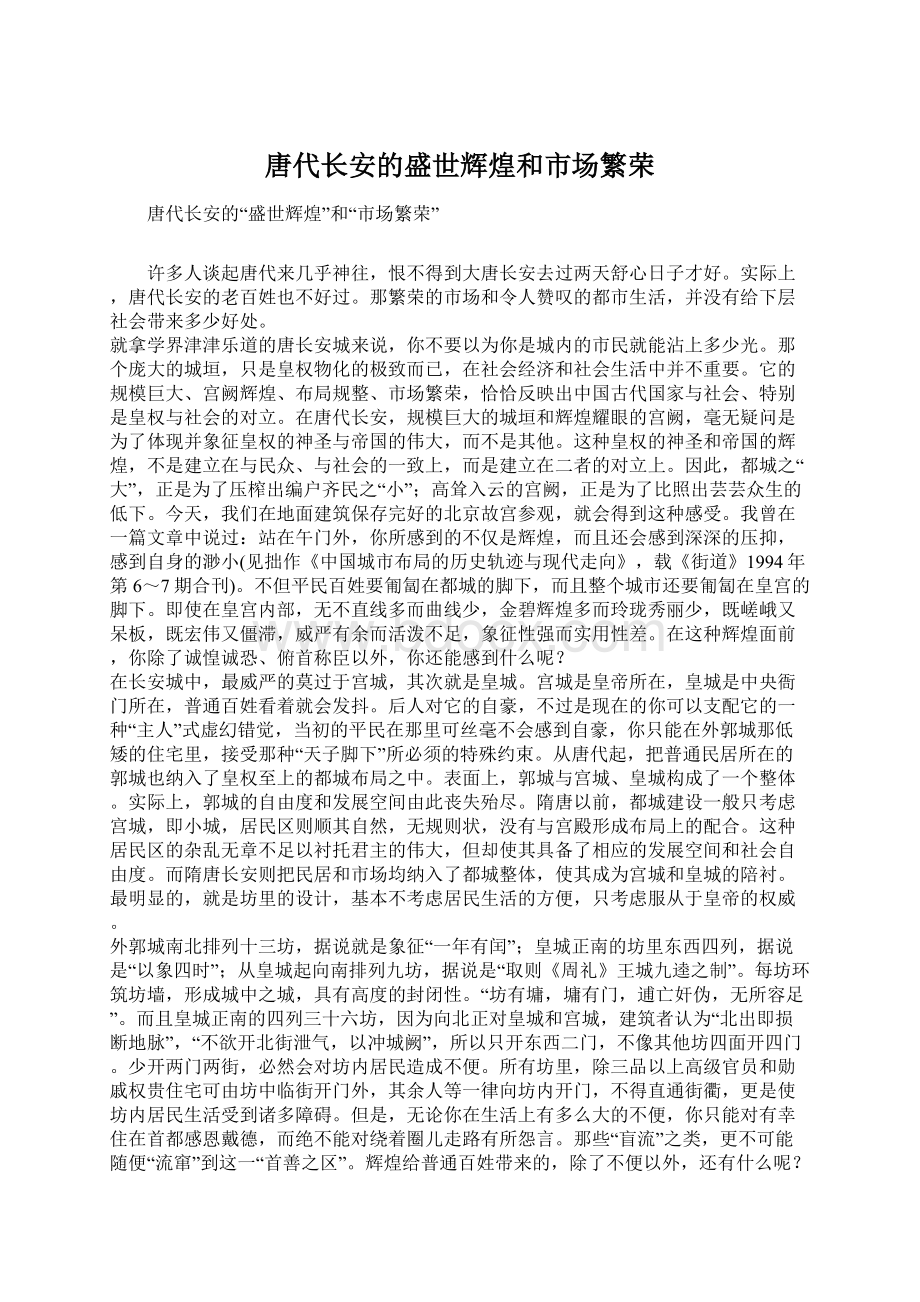
今天,我们在地面建筑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宫参观,就会得到这种感受。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
站在午门外,你所感到的不仅是辉煌,而且还会感到深深的压抑,感到自身的渺小(见拙作《中国城市布局的历史轨迹与现代走向》,载《街道》1994年第6~7期合刊)。
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脚下,而且整个城市还要匍匐在皇宫的脚下。
即使在皇宫内部,无不直线多而曲线少,金碧辉煌多而玲珑秀丽少,既嵯峨又呆板,既宏伟又僵滞,威严有余而活泼不足,象征性强而实用性差。
在这种辉煌面前,你除了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以外,你还能感到什么呢?
在长安城中,最威严的莫过于宫城,其次就是皇城。
宫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普通百姓看着就会发抖。
后人对它的自豪,不过是现在的你可以支配它的一种“主人”式虚幻错觉,当初的平民在那里可丝毫不会感到自豪,你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里,接受那种“天子脚下”所必须的特殊约束。
从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纳入了皇权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
表面上,郭城与宫城、皇城构成了一个整体。
实际上,郭城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由此丧失殆尽。
隋唐以前,都城建设一般只考虑宫城,即小城,居民区则顺其自然,无规则状,没有与宫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
这种居民区的杂乱无章不足以衬托君主的伟大,但却使其具备了相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
而隋唐长安则把民居和市场均纳入了都城整体,使其成为宫城和皇城的陪衬。
最明显的,就是坊里的设计,基本不考虑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虑服从于皇帝的权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
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
从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据说是“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
每坊环筑坊墙,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
“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
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建筑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所以只开东西二门,不像其他坊四面开四门。
少开两门两街,必然会对坊内居民造成不便。
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内居民生活受到诸多障碍。
但是,无论你在生活上有多么大的不便,你只能对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绝不能对绕着圈儿走路有所怨言。
那些“盲流”之类,更不可能随便“流窜”到这一“首善之区”。
辉煌给普通百姓带来的,除了不便以外,还有什么呢?
由于坊里布局目的在于体现皇权的伟大,所以,尽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却仍照设不误。
正南距郭城南门明德门尚有两坊的开明坊,“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兴庆宫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见《长安志》开明坊、升道坊条)。
由此推测,郭城南侧的各坊,居民不多,本无设坊的必要。
之所以设坊,显然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古代版本。
这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的呆板整齐,宋人赞誉为“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吕大防《长安志图》语)的“一代精制”,究竟是适应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还是束缚其需要,一眼即明,无需多辩。
作为都城,长安的街衢极为宽广,而且方向笔直。
“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
”(《长安志·
唐京城》注)据考古实测,除横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宽者达米,通城门的大街多宽100米以上,最窄的顺城街也宽20至25米(《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这么宽广笔直的街道,显然不是为实用性的交通而设,而是为统治需要而设。
空旷的街道,高耸的坊墙,封闭的闾巷,使居民无处不在专制帝国的庞大身影之下,造就了国家强暴社会的文化氛围。
许多人都对长安的市场繁荣深信不疑,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许多问题。
长安的市场,以东西两市为代表。
而规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业区限定在两市,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活动的实际是高度不适应的。
如果说长安市场贸易有过繁荣的话,那也是一种专制集权帝国的畸形繁荣。
东西两市各方六百步,考古实测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过1平方公里,相对于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说,商业区实在是太小了,仅仅占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二。
加之高宗武周时还在东西两市设立了常平仓,修建了放生池,又占用了相当一区地盘。
常平仓的储粟大约在二三十万石之间(据《唐会要·
常平仓》载:
元和六年宪宗赈济京畿饥荒时的诏文有“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之语),其面积不会太小。
常平仓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机构占地之后,真正的贸易区域实在寥寥无几。
在这样一个面积和空间十分有限的市场中,到底能容纳多少大商小贾,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够受惠其间,是大有疑问的。
仅仅从规模来看,也可以断定东西两市不是为一般居民服务的市场。
同整个城市布局相适应,东西两市的建筑规整划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划分为九个区域,市中央设置市署和平准局进行管理。
各种店铺集中设置,形成不同的“行”。
为了求得店铺的整齐,中宗时曾专门下诏称:
“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
”(《唐会要·
市》)这种禁置偏铺的做法,显然不同于今日的禁止占道经营,因为唐代两市的道路两侧有两米多深、近一米宽的水沟,偏铺不可能伸展到水沟之外的街道上。
各行的集中设置、显然不是经济规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制的表现。
所谓的“行”,并不是由贸易活动自然形成的行业,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预下形成的“某某一条街”。
这种集中设置的行,不是商贸活动的发展需要,而是一种“供给”制的需要。
如果从东西两市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角度来考察,从政府的“方便”来考虑,不难得出合理的解释。
东西两市的位置,都临近皇城和宫城,这只能说明其贸易活动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
而西市的繁荣,又以“胡商”最为着名。
胡商所经营者,多为珠宝珍贵,非寻常百姓可问津。
因此,东西两市,从设计思想到实际效果,主要是为宫城和皇城以及周围的官邸豪宅服务的,“公款消费”有可能占主要地位。
许多文章引吴凑任京兆尹时请客一事为例来说明两市饮食业的繁荣。
“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唐国史补》卷中)。
其实,这同现今某些贫困地区的餐饮业和娱乐业畸形发达没有什么两样。
以东西两市某些豪华奢侈消费说明长安城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论据不足。
另外,最为文人称道的平康里,即青楼,恰好就紧挨着皇城。
看来,即使在古代中国,色情业只有紧紧傍上权贵才能昌盛,早已成为铁定的法则。
东西两市的店铺规模都不大,1961年发掘的西市房址遗迹,最长的不过十米,最短的只有四米,进深均为三米多。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店铺乃是官贵修造,租赁收利。
从店铺的租金来看,其商业的繁荣程度颇有疑问。
众所周知,租金的高低反映着铺面商业利润的高低。
而在唐朝最为繁盛的时期,官定租金限价月不过五百文。
玄宗曾为此颁发诏书称:
“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全唐文》卷32)。
显然,显然,由租金之低可以推测出一间铺面的每月利润是十分有限的。
至于唐朝中期以后,朝廷对两市商贾的“借钱”盘剥,增加商税,括僦柜质,间架除陌,特别是宫市白望,已经有多种文章述及,对商贸活动的打击摧残累累见诸史篇,这里不再赘述【注】。
值得注意的是,德宗在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才搜刮得八十万贯。
经京兆少尹韦祺建议,又按僦柜质库法,四取其一,再搜刮得二百万贯(《旧唐书·
德宗纪》)。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动用国家暴力、激起了罢市抗议的行动,几乎扫荡了长安市场,所得不过如此,仅够帝国两个月的开销。
即使考虑到富商的抵制和隐匿,也反映出长安商贾的资本和流动资金十分有限。
长安市场的所谓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唐都长安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代表性。
长安城的设计建设,就其本质来说,是皇权的物化,它给予人们的观感,是天子的威严和王朝的神圣,是和当时的皇帝制度紧密结合为一体的。
它充分反映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威严,而远远没有经济中心的风采。
史学研究中,往往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下意识的偏差。
同样是大兴土木,秦造阿房宫就是暴政的罪证,汉修建章宫就是强盛的象征。
对待唐长安城的研究,如果不囿于“盛世”的先入之见,我们则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被我们有意无意遮蔽起来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至今还在我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改头换面反复再现。
如市民望而生畏的某些政府大楼,如只有长官意志而没有经济效益的某些市场商厦,如一窝蜂上马的某某开发区或某某一条街等等。
尽管时代变了,形式变了,但文化传统的延续,历史基因的遗传,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
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一辩。
————
【注】“括僦柜质”为政府强行借贷;
“僦柜”本为民间典当质钱,其时唐朝政府将商业钱粮强制借用四分之一,称“括僦柜质”。
“间架”为商业用房税,上等每间二千贯,中等一千贯,下等五百贯。
“除陌”为商业交易税,每成交一贯纳税五十文。
以上均在建中三年实施。
“宫市白望”为太监宫人以皇宫需要为名强索货物。
《唐会要》载:
“京都多中官市物于廛肆,谓之宫市,不持文牒,口含敕命,皆以监估不中衣服绢帛,杂红紫之物,倍高其估,尺寸裂以酬价。
……市后又强驱于禁中,倾车乘,罄辇驴,已而酬以丈尺帛绢。
”《资治通鉴》注称:
“白望者,言使人于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还本价也。
”白居易的《卖炭翁》:
“两骑翩翩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就是宫市白望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