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言诗与新诗现代派文档格式.docx
《魏晋玄言诗与新诗现代派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魏晋玄言诗与新诗现代派文档格式.docx(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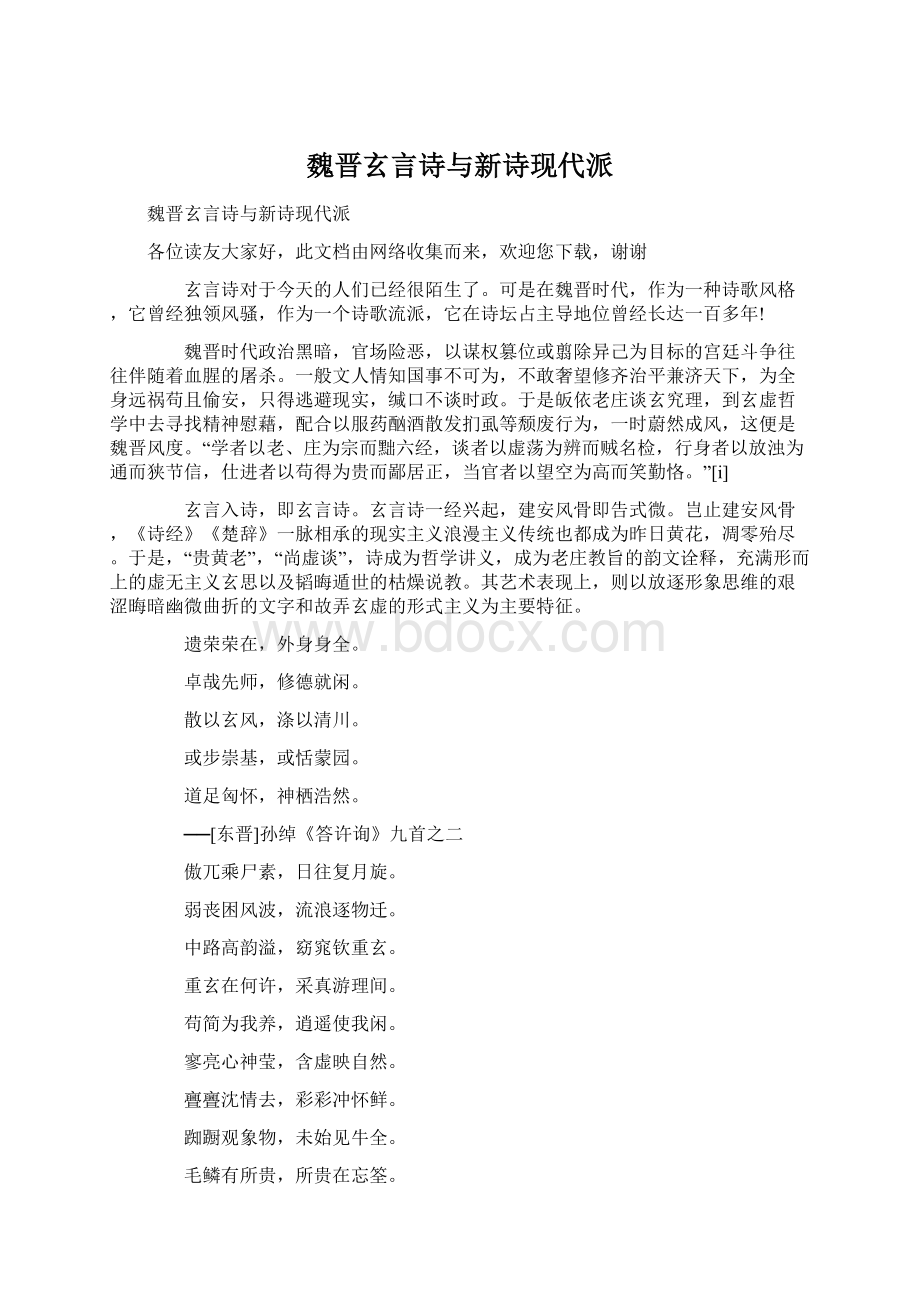
于是,“贵黄老”,“尚虚谈”,诗成为哲学讲义,成为老庄教旨的韵文诠释,充满形而上的虚无主义玄思以及韬晦遁世的枯燥说教。
其艺术表现上,则以放逐形象思维的艰涩晦暗幽微曲折的文字和故弄玄虚的形式主义为主要特征。
遗荣荣在,外身身全。
卓哉先师,修德就闲。
散以玄风,涤以清川。
或步崇基,或恬蒙园。
道足匈怀,神栖浩然。
──[东晋]孙绰《答许询》九首之二
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
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
中路高韵溢,窈窕钦重玄。
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
苟简为我养,逍遥使我闲。
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
亹亹沈情去,彩彩冲怀鲜。
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
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筌。
──[东晋]支遁《咏怀诗》五首之一
当是时也,玄理之风,如紫气东来,纵横诗国,大行其道;
如浩月当空,笼罩四海,领导新潮。
玄言诗在当时并非没有受到批评。
不满玄谈之风的葛洪就曾指出:
“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
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
”[ii]然而,批评归批评,风行归风行,当一种诗风甚嚣尘上时,圈中人是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的。
“间有斥其非者,世反谓之俗吏。
”[iii]批评的声音客观上还会成为被批评者的推销广告,这一效应想必古今皆然。
这也就是批评界往往失语的原因。
当然,一股逆流是不可能永远汹涌下去的。
玄言诗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夏侯玄和钟会为其代表;
至东晋更为盛行,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是其中坚。
但各家作品多已散佚。
其中被鲁迅称为空谈和吃药(药名“五石散”的一种毒品)两大祖师[iv]的何晏仅存两首与玄理无关的《言志诗》,许询仅存一首并非谈玄论道的咏物小品《竹扇诗》,王弼、夏侯玄、钟会、桓温、庾亮则徒留诗名,囊中空空,并无一字传世。
只有孙绰、支遁二人,或领袖文坛,或终老佛山,得存诗较多,像是历史老人有意为玄言诗派留下一份供后人评说成败得失的文本。
作为诗史上的一个曾经显赫百年的流派,玄言诗到晋末终告衰落,其诗坛主导地位为山水诗所取代。
(尽管那影响并不容易消除,例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拖着玄言诗的尾巴。
)在后来一千多年的中国诗史上,渐至湮没无闻。
这个结局,应该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关于玄言诗,刘勰《文心雕龙》指其“江左篇制,溺乎玄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v]钟嵘《诗品》斥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皆切中要害之语,可谓盖棺论定。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玄言诗却死灰复燃,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复兴,尽管人们并未想到祭起何晏、孙绰们的亡灵。
这便是新诗的所谓“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的粉墨登场。
现代派新诗几乎是具备了魏晋玄言诗的一切特征!
如放逐情志,独重理念,所谓“主智”;
沉湎于形而上的玄想,将诗作为哲学讲义或哲学笔记,以阐释玄理为诗之要义和时尚,只是不局限于中国的老庄,而更热衷于西方哲学,兼及若干宗教教义;
如逃避现实,不涉美刺,远离人间烟火,鄙夷时代使命感,否定并嘲弄诗歌的社会功能,无论是教化还是批判;
如轻慢意象,倾向于以抽象思维代替形象思维;
如语言艰涩隐晦,故作深奥,且更为放纵,恣意对语言施虐施暴;
如形式主义和技巧至上,所谓“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
如蔑视读者,以曲高和寡自得自炫……可以说,玄言诗的幽灵已悄然附体于“现代诗”,新诗现代派就是二十世纪的玄言诗派。
中国的现代派们实在是不必数典忘祖,远道西游去寻求衣钵和牙慧的,“现代派”在咱们地大物博的中国确实是“古已有之”。
现代派以“现代”自诩,其实并没有多少现代性可言,“现代派”(“现代诗”、“现代主义”)这个名目只是基于时序所取,与其流派特征完全无关。
或者,鉴于中国诗史上早已有一个“玄言诗”的现成名目,不妨沿用,所谓现代派,不如称之为“后玄言派”,倒还有利于标明其流派特征和历史源流,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现代派们总以为别人都是传统的顽固守旧的,只有他们自己是反传统的锐意创新的。
他们怎么也不曾想到,他们自己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竟也是“传统”的,作为它的原型,玄言诗在一千六七百年前的魏晋时代还曾经是诗坛的主流派,只不过他们的那个“传统”却早已不幸成为了“失传之统”、“不传之统”,在艺术世界的生存竞争中被适者生存的法则给无情地淘汰了,他们坚守那一套才真正是顽固守旧呢!
文学艺术的许多观念、理论、风格、流派,在文学艺术史上都是能找到它们的原型的。
文学艺术历经几千年发展,到今天,恐怕任何认为自己的一套乃是全新的、从零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创造之所谓“首创论”、“空白论”,都只能是幼稚的妄言。
──我不大有把握这一判断是否有例外,但我相信,即便有,也不属于新诗现代派。
新诗在当今中国受到读者的空前冷遇,现代派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因为其理论的鼓吹和作品的充斥,在参与扫荡了十年浩劫登峰造极的极左派的假大空话语之后,又从另一个极端搅乱了诗坛的是非,败坏了新诗的声誉。
近日,一位报考鄙所诗学研究生的湖北某中学语文教师在给我的信中说:
“我校一些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语文教师,平素是从来不看诗歌的,问之则曰‘不知在胡弄些什么,我看它干嘛?
’诗歌创作无人喝彩。
这该是多么尴尬的情形!
”这决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
现代派的弊端天人共鉴,整个诗国怨声四起,有艺术良知的人们不会视而不见。
然而,尽管许多人幡然醒悟,从其阵营中分裂出来,甚至其领袖级人物也频频发言指斥其积弊,现代派的若干新老盟友却仍然痴心不改,苦苦地坚守着阵地。
其中一个“建设性的”举动便是抬出穆旦[vi],将他拥上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第一把交椅。
七鼓八噪,如今,穆旦研究已成为热点了,穆旦的地位已不亚于当年东晋的玄言诗大师孙绰了,穆旦的诗集已是注家蜂起了,穆旦门下如今也差不多是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了。
我却总也弄不明白,现代诗为什么要写得比古诗还难懂?
为什么现代人写的诗给现代人看,还要借助于冗长的注解导读?
穆旦篇幅有限的《诗八首》(八八六十四行,据说是情诗),为什么需要数千字、数万字的长文来作反反复复的“细读”?
我怀疑是否真有什么用平易流畅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深邃的思想和深沉的情感?
既然一种语言可以译成另一种语言,同一种语言内的艰涩表达难道就不能译为平易表达?
是的,诗人应该是思想者,但思想者是否就是诗人?
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水泊梁山,如果缺少晁天王,就让它缺少好了,用不着匆忙拥立谁或改立谁。
神化穆旦救不了玄言诗。
才从现代迷信的香火中逃出来的我们,不免对一切新的造神运动过敏。
诚然,玄言诗的某些作派,如逃避现实谈玄究理,可能是时势使然,有时也不妨理解为一种消极的抗议;
如幽微晦涩的语言风格,有时可能是为藏锋避讳,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曲折表达方式的需要;
如形式主义,有时也可能是不无积极意义的艺术探索。
可是,当少数不失真诚的探索者身后聚起庞杂的等而下之的追随者,当一切语病、黑话、结巴、晦涩、怪诞、苍白、猥琐、浅薄、痞气、唯丑、没文化、没教养、下半身……都瘟疫般地集合于探索者的旗下,探索者却不加甄别地引以为党羽,一往情深地予以呵护,喜剧效果便发生了。
有时我甚至想,现代主义最大的敌人也许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那些皈依到现代派旗下的诗人自己,因为正是他们的作品(《石室之死亡》《0档案》之类)更加败坏了现代主义的声誉。
“没有偏激就没有深刻”这一命题是不能到处滥用的,我们不要忘了另一至理名言:
“真理再往前跨出一步就是谬误!
”说深耕就掘地三尺,说密植就密不透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某些人的狂热和瞎指挥对于中国农业的伤害,使我老家的农民至今提起来还痛恨不已。
将现代主义的某些不无合理因素的理论主张推向极端即推向谬误。
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可能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那些自称为最激进、最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四人帮”和红色高棉波尔布特之流一样。
马克思主义难道就不能不与专制和恐怖搅到一起吗?
现代主义难道就不能不与晦涩和怪诞搅到一起吗?
君不见,被公认为台湾现代诗始作俑者的纪弦,其晚年也颇有悔意,说“从前在台湾,有人故意逃避情绪,切断联想,把诗写得十分晦涩难懂,而自认为很‘前卫’。
我大不以为然,决不点头。
说现代诗是‘难懂的诗’,如果不‘难懂’,就不‘现代’了,那真是一大笑话!
”[vii]
还有所谓后现代,其调侃一切、亵渎一切的痞子口吻,与文革之初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红卫兵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们应该知道建构什么,解构什么,知道破坏之后还须建设,解构之后还须重新建构。
人毕竟要有理想,人类的理想未来不能寄于乌托邦,也不能存于荒漠或废墟。
况且,并不是任何既有的建构都是可以亵渎和解构的,譬如爱国情怀,譬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对着黄河洒泡尿的小痞子作派终究是难以容忍的。
作为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在一个宽容和多元的诗坛上,玄言诗、后现代其实都不妨存在,不妨聊备一格。
“不管它多么怪异,多么令人倒胃口,都有它们存在的权利,正如癞蛤蟆和赤练蛇都有存在的权利一样。
看不懂癞蛤蟆和赤练蛇并不是生物学家的光荣,看不懂某些后现代诗也不是诗歌评论家的自豪的本钱。
”[viii]可是,癞蛤蟆和赤练蛇有存在的权利,却没有主宰生物圈的权利,没有成为生物圈中巨无霸的权利,没有吃天鹅肉,剥夺天鹅和夜莺们生存权的权利。
而“癞蛤蟆和赤练蛇”在某些理论家那里一贯被唤作“第三代”(如果把艾青等当年的归来者算作第一代,朦胧诗算作第二代,第三代就只有“癞蛤蟆和赤练蛇”吗?
)备受鼓噪,正是试图赋予它这种权利,张扬着它的这种权利欲。
而对于非生物学非诗学职业的,不愿意自讨苦吃自找罪受的一般动物观赏者和诗歌爱好者,咱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也像咱们一样忍受着痛苦和恐怖,倒着胃口,去看直到懂咱们这丑陋可怖的癞蛤蟆、赤练蛇和第×
代的诗呢?
而论者立论,是不能不照顾一般观赏者、读者的审美心理,只以一己偏好和怪癖为依据的。
温故而知新。
魏晋玄言诗早已被诗史所遗弃,“后玄言诗”在诗史上的命运,也不会比它的上一轮回更为美好。
如果不满足于聊备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