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爱情感想散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林徽因的爱情感想散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林徽因的爱情感想散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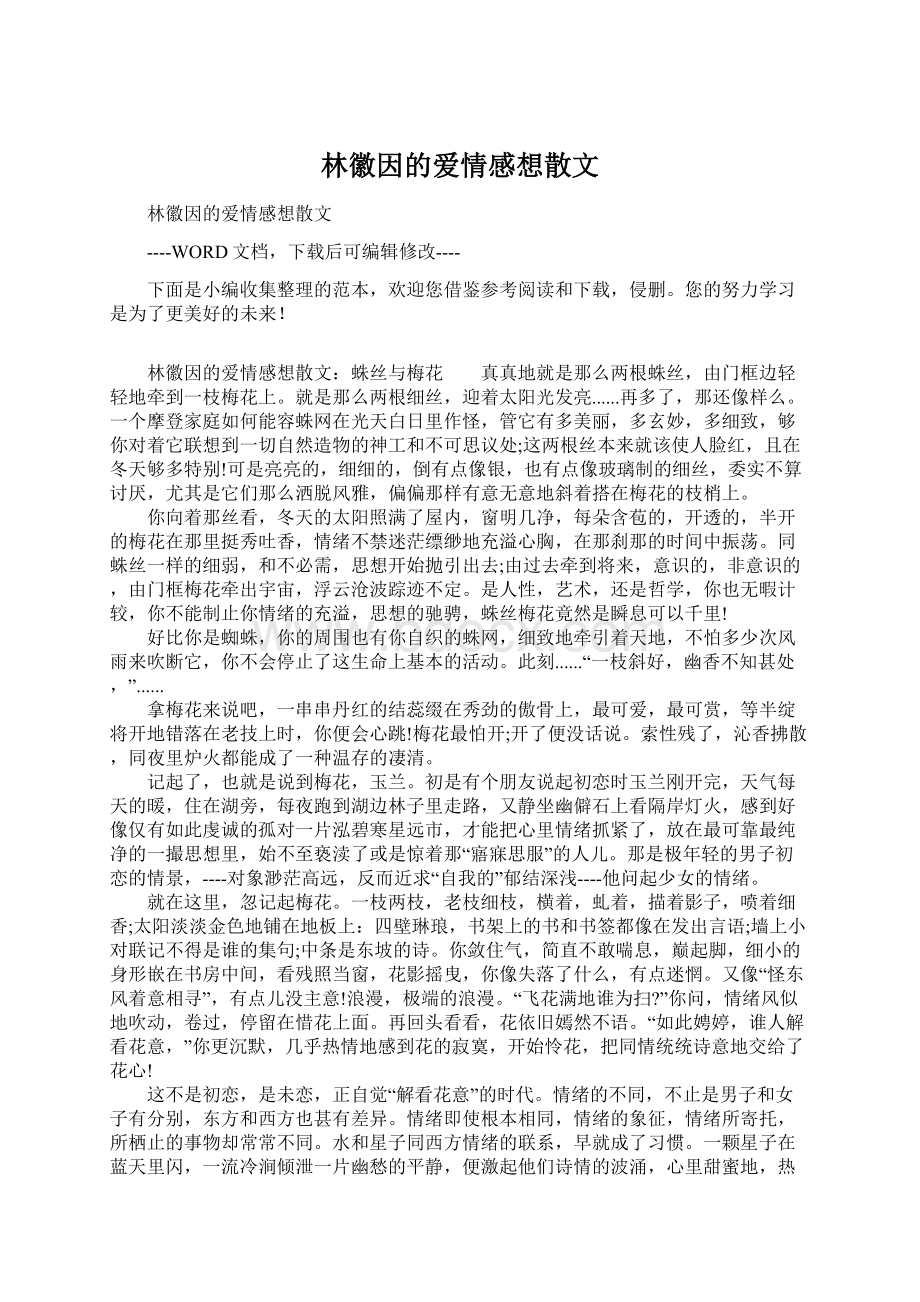
你敛住气,简直不敢喘息,巅起脚,细小的身形嵌在书房中间,看残照当窗,花影摇曳,你像失落了什么,有点迷惘。
又像“怪东风着意相寻”,有点儿没主意!
浪漫,极端的浪漫。
“飞花满地谁为扫?
”你问,情绪风似地吹动,卷过,停留在惜花上面。
再回头看看,花依旧嫣然不语。
“如此娉婷,谁人解看花意,”你更沉默,几乎热情地感到花的寂寞,开始怜花,把同情统统诗意地交给了花心!
这不是初恋,是未恋,正自觉“解看花意”的时代。
情绪的不同,不止是男子和女子有分别,东方和西方也甚有差异。
情绪即使根本相同,情绪的象征,情绪所寄托,所栖止的事物却常常不同。
水和星子同西方情绪的联系,早就成了习惯。
一颗星子在蓝天里闪,一流冷涧倾泄一片幽愁的平静,便激起他们诗情的波涌,心里甜蜜地,热情地便唱着由那些鹅羽的笔锋散下来的“她的眼如同星子在暮天里闪”,或是“明丽如同单独的那颗星,照着晚来的天”,或“多少次了,在一流碧水旁边,忧愁倚下她低垂的脸”。
惜花,解花太东方,亲昵自然,含着人性的细致是东方传统的情绪。
此外年龄还有尺寸,一样是愁,却跃跃似喜,十六岁时的,微风零乱,不颓废,不空虚,巅着理想的脚充满希望,东方和西方却一样。
人老了脉脉烟雨,愁吟或牢骚多折损诗的活泼。
大家如香山,稼轩,东坡,放翁的白发华发,很少不梗在诗里,至少是令人不快。
话说远了,刚说是惜花,东方老少都免不了这嗜好,这倒不论老的雪鬓曳杖,深闺里也就攒眉千度。
最叫人惜的花是海棠一类的“春红”,那样娇嫩明艳,开过了残红满地,太招惹同情和伤感。
但在西方即使也有我们同样的花,也还缺乏我们的廊庑庭院。
有了“庭院深深深几许”才有一种庭院里特有的情绪。
如果李易安的“斜风细雨”底下不是“重门须闭”也就不“萧条”得那样深沉可爱;
李后主的“终日谁来”也一样的别有寂寞滋味。
看花更须庭院,常常琐在里面认识,不时还得有轩窗栏杆,给你一点凭藉,虽然也用不着十二栏杆倚遍,那么慵弱无聊。
当然旧诗里伤愁太多:
一首诗竟像一张美的证券,可以照着市价去兑现!
所以庭花,乱红,黄昏,寂寞太滥,时常失却诚实。
西洋诗,恋爱总站在前头,或是“忘掉”,或是“记起”,月是为爱,花也是为爱,只使全是真情,也未尝不太腻味。
就以两边好的来讲,拿他们的月光同我们的月色比,似乎是月色滋味深长得多。
花更不用说了;
我们的花“不是预备采下缀成花球,或花冠献给恋人的”,却是一树一树绰约的,个性的,自己立在情人的地位上接受恋歌的。
所以未恋时的对象最自然的是花,不是因为花而起的感慨,----十六岁时无所谓感慨,----仅是刚说过的自觉解花的情绪。
寄托在那清丽无语的上边,你心折它绝韵孤高,你为花动了感情,实说你同花恋爱,也未尝不可,----那惊讶狂喜也不减于初恋。
还有那凝望,那沉思......
一根蛛丝!
记忆也同一根蛛丝,搭在梅花上就由梅花枝上牵引出去,虽未织成密网,这诗意的前后,也就是相隔十几年的情绪的联络。
午后的阳光仍然斜照,庭院阒然,离离疏影,房里窗棂和梅花依然伴和成为图案,两根蛛丝在冬天还可以算为奇迹,你望着它看,真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偏偏那么斜挂在梅花的枝梢上。
悼志摩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残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
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
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
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
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
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
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翼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
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帷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
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
待时间来剥削着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
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
但是除去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谁也没有主意,谁也没有话说!
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
默然相对,默然围坐......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没有音讯,永远地不会回头,永远地不会再有音讯。
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谁不感到惊异,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
世事尽有定数?
世事尽是偶然?
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质的事实:
“是的,他十九晨有电报来给我......
“十九早晨,是的!
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派车接......
“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的......
“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
“派车接去了,等到四点半......说飞机没有到......
“没有到......航空公司说济南有雾......很大......”只是一个钟头的差别;
下午三时到南苑,济南有雾!
谁相信就是这一个钟头中便可以有这么不同事实的发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
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
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
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
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儿,喝了一壶茶,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
我到桌上一看:
----
“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阵不痛快,却忙给他一个电话。
“你放心。
”他说,“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
......”
话虽是这样说,他却是已经死了整两周了!
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
志摩是死了,这个简单残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一周,两周,一直的增长下去......
我不该在这里语无伦次的尽管呻吟我们做朋友的悲哀情绪。
归根说,读者抱着我们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请柏雷一样,要从我们口里再听到关于志摩的一些事。
这个我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们满意,因为关于他的事,动听的,使青年人知道这里有个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实在太多,决不是几千字可以表达得完。
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的,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
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生。
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
他到康桥之后由狄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
一直到最近两个月中源宁还常在说他当时的许多笑话,虽然说是笑话,那也是他对志摩最早的一个惊异的印象。
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任何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
源宁说,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读书,外边下起了倾盆大雨----惟是英伦那样的岛国才有的狂雨----忽然他听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门,外边跳进一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
不用说他便是志摩,一进门一把扯着源宁向外跑,说快来我们到桥上去等着。
这一来把源宁怔住了,他问志摩等什么在这大雨里。
志摩睁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兴地说“看雨后的虹去”。
源宁不止说他不去,并且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国的湿气岂是儿戏,志摩不等他说完,一溜烟地自己跑了。
以后我好奇地曾问过志摩这故事的真确,他笑着点头承认这全段故事的真实。
我问:
那么下文呢,你立在桥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没有?
他说记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
我诧异地打断他对那虹的描写,问他:
怎么他便知道,准会有虹的。
他得意地笑答我说:
“完全诗意的信仰!
”
“完全诗意的信仰”,我可要在这里哭了!
也就是为这“诗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达到他“想飞”的宿愿!
“飞机是很稳当的”他说,“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运命!
”他真对运命这样完全诗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就比这生苦,“我们不能轻易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但是我前边说过最难堪的是这永远的静寂。
我们生在这没有宗教的时代,对这死实在太没有把握了。
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丽的诗意的信仰!
我个人的悲绪不竟又来扰乱我对他生前许多清晰的回忆,朋友的原谅。
诗人的志摩用不着我来多说,他那许多诗文便是估价他的天平。
我们新诗的历史才是这样的短,恐怕他的判断人尚在我们儿孙辈的中间。
我要谈的是诗人之外的志摩。
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
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
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
我不说了解,因为不是许多人爱说志摩最不解人情么?
我说他的特点也就在这上头。
我们寻常人就爱说了解;
能了解的我们便同情,不了解的我们便很落寞乃至于酷刻。
表同情于我们能了解的,我们以为很适当;
不表同情于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也认为很公平。
志摩则不然,了解与不了解,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张,他只知道温存,和平,体贴,只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无论出自何人,在何等情况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
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摘凡是与他不同的人。
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
他觉得人类各种的情感动作全有它不同的,价值放大了的人类的眼光,同情是不该只限于我们划定的范围内。
他是对的,朋友们,归根说,我们能够懂得几个人,了解几桩事,几种情感?
哪一桩事,哪一个人没有多面的看法!
为此说来志摩的朋友之多,不是个可怪的事;
凡是认得他的人不论深浅对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极为自然的结果。
而反过来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
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
但是他却未曾为这个鄙吝他给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为受了刺激而转变刻薄暴戾过,谁能不承认他几有超人的宽量。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
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
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
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
我说神秘,其实竟许是傻,是痴!
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
他愉快起来他的快乐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忧伤起来,他的悲戚是深得没有底。
寻常评价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轻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纯是艺术的情感的脱离寻常的原则,所以往常人常听到朋友们说到他总爱带着嗟叹的口吻说:
“那是志摩,你又有什么法子!
”他真的是个怪人么?
朋友们,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
朋友们我们失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急难得可爱的人格。
至于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么?
他的兴趣只限于情感么?
更是不对。
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
他始终极喜欢天文,他对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认得很多,最喜暑夜观星,好几次他坐火车都是带着关于宇宙的科学的书。
他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
他常向思成说笑:
“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今夏我在香山养病,他常来闲谈,有一天谈到他幼年上学的经过和美国克莱克大学两年学经济学的景况,我们不禁对笑了半天,后来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里也说了那么一段。
可是奇怪的!
他不象许多天才,幼年里上学,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优等的,听说有一次康乃尔暑校里一个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莱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
我不是为志摩在这里夸张,因为事实上只有为了这桩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乐乎!
此外他的兴趣对于戏剧绘画都极深浓,戏剧不用说,与诗文是那么接近,他领略绘画的天才也颇为可观,后期印象派的几个画家,他都有极精密的爱恶,对于文艺复兴时代那几位,他也很熟悉,他最爱鲍蒂切利和达文骞。
自然他也常承认文人喜画常是间接地受了别人论文的影响,他的,就受了法兰(ROGERFRY)和斐德(WALTERPATER)的不少。
对于建筑审美他常常对思成和我道歉说:
“太对不起,我的建筑常识全是RUSKINS那一套。
”他知道我们是讨厌RUSKINS的。
但是为看一个古建的残址,一块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热心,都更能静心领略。
他喜欢色彩,虽然他自己不会作画,暑假里他曾从杭州给我几封信,他自己叫它们做“描写的水彩画”,他用英文极细致地写出西(边?
)桑田的颜色,每一分嫩绿,每一色鹅黄,他都仔细地观察到。
又有一次他望着我园里一带断墙半晌不语,过后他告诉我说,他正在默默体会,想要描写那墙上向晚的艳阳和刚刚入秋的藤萝。
对于音乐,中西的他都爱好,不止爱好,他那种热心便唤醒过北京一次----也许唯一的一次----对音乐的注意。
谁也忘不了那一年,克拉斯拉到北京在“真光”拉一个多钟头的提琴。
对旧剧他也得算“在行”,他最后在北京那几天我们曾接连地同去听好几出戏,回家时我们讨论的热毛,比任何剧评都诚恳都起劲。
谁相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忠实于“生”的一个人,会这样早地永远地离开我们另投一个世界,永远地静寂下去,不再透些许声息!
我不敢再往下写,志摩若是有灵听到比他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拿着老声老气的语调谈到他的为人不觉得不快么?
这里我又来个极难堪的回忆,那一年他在这同一个的报纸上写了那篇伤我父亲惨故的文章,这梦幻似的人生转了几个弯,曾几何时,却轮到我在这风紧夜深里握吊他的惨变。
这是什么人生?
什么风涛?
什么道路?
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
窗子以外 话从哪里说起?
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个源头。
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
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
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
每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
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
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
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官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
铁纱窗以外,话可不就在这里了。
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
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
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
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
其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
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
在家里罢,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
那里两树马缨,几棵丁香;
榆叶梅横出风的一大枝;
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个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
廊子幽秀地开着扇子式,六边形的格子窗,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
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脸;
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掮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屏门;
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
更有时厨子来个朋友了,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门房;
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唧唧哝哝争吵的声浪。
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生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个窗子,----扇子式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
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
你站起来,穿上不能算太贵的鞋袜,但这双鞋和袜的价钱也就比----想它做什么,反正有人每月的工资,一定只有这价钱的一半乃至于更少。
你出去雇洋车了,拉车的嘴里所讨的价钱当然是要比例价高得多,难道你就傻子似地答应下来?
不,不,三十二子,拉就拉,不拉,拉倒!
心里也明白,如果真要充内行,你就该说,二十六子,拉就拉----但是你好意思争!
车开始辗动了,世界仍然在你窗子以外。
长长的一条胡同,一个个大门紧紧地关着。
就是有开的,那也只是露出一角,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有南瓜棚子,底下一个女的,坐在小凳上缝缝做做的;
另一个,抓住还不能走路的小孩子,伸出头来喊那过路卖白菜的。
至于白菜是多少钱一斤,那你是听不见了,车子早已拉得老远,并且你也无需乎知道的。
在你每月费用之中,伙食是一定占去若干的。
在那一笔伙食费里,白菜又是多么小的一个数。
难道你知道了门口卖的白菜多少钱一斤,你真把你哭丧着脸的厨子叫来申斥一顿,告诉他每一斤白菜他多开了你一个“大子儿”?
车越走越远了,前面正碰着粪车,立刻你拿出手绢来,皱着眉,把鼻子蒙得紧紧地,心里不知怨谁好。
怨天做的事太古怪;
好好的美丽的稻麦却需要粪来浇!
怨乡下人太不怕臭,不怕脏,发明那么两个篮子,放在鼻前手车上,推着慢慢走!
你怨市里行政人员不认真办事,如此脏臭不卫生的旧习不能改良,十余年来对这粪车难道真无办法?
为着强烈的臭气隔着你窗子还不够远,因此你想到社会卫生事业如何还办不好。
路渐渐好起来,前面墙高高的是个大衙门。
这里你简直不止隔个窗子,这一带高高的墙是不通风的。
你不懂里面有多少办事员,办的都是什么事;
多少浓眉大眼的,对着乡下人做买卖的吆喝诈取;
多少个又是脸黄黄的可怜虫,混半碗饭分给一家子吃。
自欺欺人,里面天天演的到底是什么把戏?
但是如果里面真有两三个人拼了命在那里奋斗,为许多人争一点便利和公道,你也无从知道!
到了热闹的大街了,你仍然像在特别包厢里看戏一样,本身不会,也不必参加那出戏;
倚在栏杆上,你在审美的领略,你有的是一片闲暇。
但是如果这里洋车夫问你在哪里下来,你会吃一惊,仓卒不知所答。
生活所最必需的你并不缺乏什么,你这出来就也是不必需的活动。
偶一抬头,看到街心和对街铺子前面那些人,他们都是急急忙忙地,在时间金钱的限制下采办他们生活所必需的。
两个女人手忙脚乱地在监督着店里的伙计秤秤。
二斤四两,二斤四两的什么东西,且不必去管,反正由那两个女人的认真的神气上面看去,必是非同小可,性命交关的货物。
并且如果秤得少一点时,那两个女人为那点吃亏的分量必定感到重大的痛苦;
如果秤得多时,那伙计又知道这年头那损失在东家方面真不能算小。
于是那两边的争持是热烈的,必需的,大家声音都高一点;
女人脸上呈块红色,头发披下了一缕,又用手抓上去;
伙计则维持着客气,口里嚷着:
错不了,错不了!
热烈的,必需的,在车马纷纭的街心里,忽然由你车边冲出来两个人;
男的,女的,各各提起两脚快跑。
这又是干什么的,你心想,电车正在拐大弯。
那两人原就追着电车,由轨道旁边擦过去,一边追着,一边向电车上卖票的说话。
电车是不容易赶的,你在洋车上真不禁替那街心里奔走赶车的担心。
但是你也知道如果这趟没赶上,他们就可以在街旁站个半点来钟,那些宁可盼穿秋水不雇洋车的人,也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而必需计较和节省到洋车同电车价钱上那相差的数目。
此刻洋车跑得很快,你心里继续着疑问你出来的目的,到底采办一些什么必需的货物。
眼看着男男女女挤在市场里面,门首出来一个进去一个,手里都是持着包包裹裹,里边虽然不会全是他们当日所必需的,但是如果当中夹着一盒稍微奢侈的物品,则亦必是他们生活中间闪着亮光的一个愉快!
你不是听见那人说么?
里面草帽,一块八毛五,贵倒贵点,可是“真不赖”!
他提一提帽盒向着打招呼的朋友,他摸一摸他那剃得光整的脑袋,微笑充满了他全个脸。
那时那一点迸射着光闪的愉快,当然的归属于他享受,没有一点疑问,因为天知道,这一年中他多少次地克己省俭,使他赚来这一次美满的,大胆的奢侈!
那点子奢侈在那人身上所发生的喜悦,在你身上却完全失掉作用,没有闪一星星亮光的希望!
你想,整年整月你所花费的,和你那窗子以外的周围生活程度一比较,
严格算来,可不都是非常靡费的用途?
每奢侈一次,你心上只有多难过一次,所以车子经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