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参考资料乾间文字之狱清朝佚名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康雍参考资料乾间文字之狱清朝佚名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康雍参考资料乾间文字之狱清朝佚名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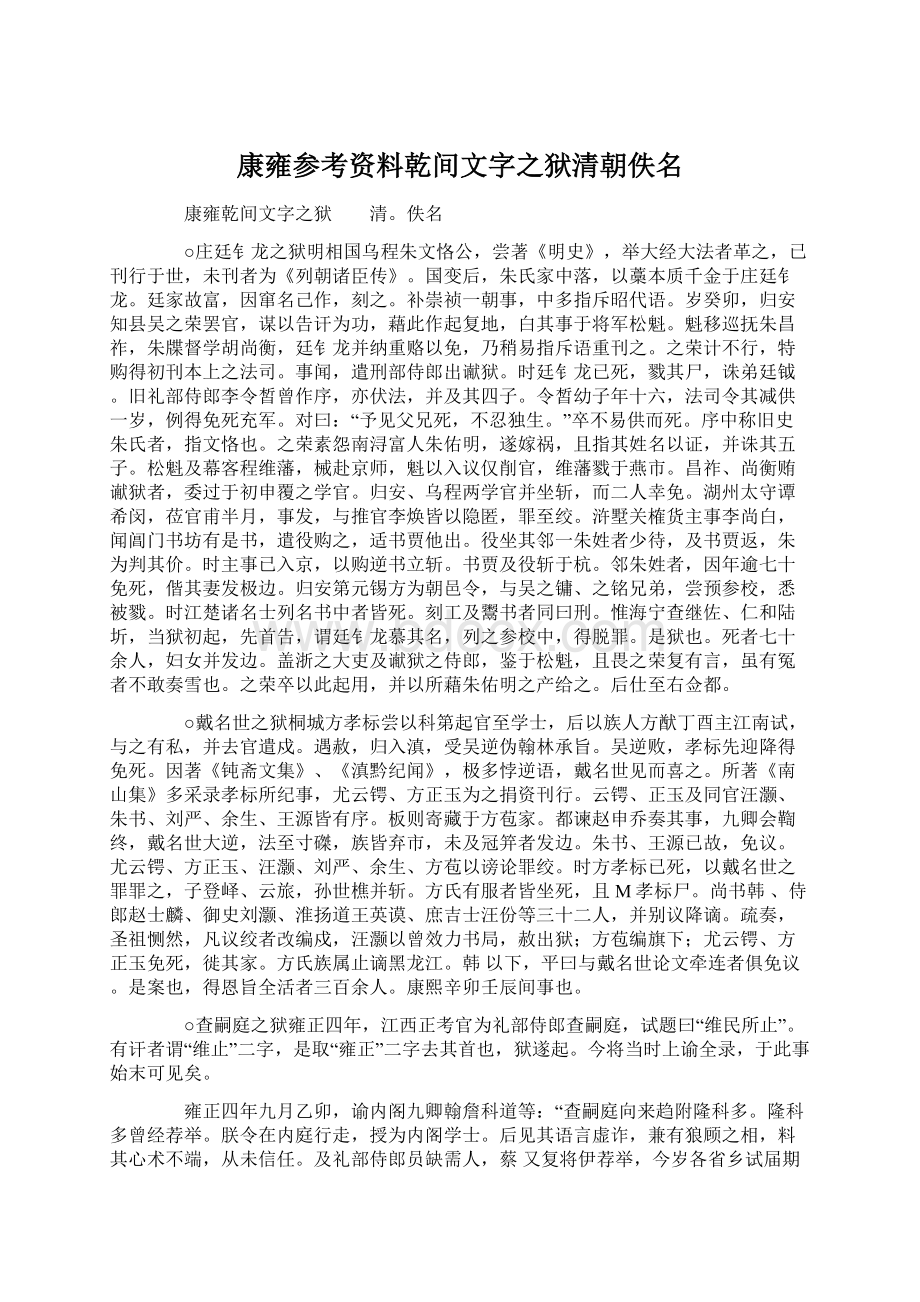
都谏赵申乔奏其事,九卿会鞫终,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
朱书、王源已故,免议。
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严、余生、方苞以谤论罪绞。
时方孝标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樵并斩。
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М孝标尸。
尚书韩、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并别议降谪。
疏奏,圣祖恻然,凡议绞者改编戍,汪灏以曾效力书局,赦出狱;
方苞编旗下;
尤云锷、方正玉免死,徙其家。
方氏族属止谪黑龙江。
韩以下,平曰与戴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
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
康熙辛卯壬辰间事也。
○查嗣庭之狱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为礼部侍郎查嗣庭,试题曰“维民所止”。
有讦者谓“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狱遂起。
今将当时上谕全录,于此事始末可见矣。
雍正四年九月乙卯,谕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
“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
隆科多曾经荐举。
朕令在内庭行走,授为内阁学士。
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
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又复将伊荐举,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须得大员以典试事,故用伊为正考官。
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
料其居心,浅薄乖张,平曰必有纪载。
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曰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
又于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
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
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
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
而伊公然造作书写。
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
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
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
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
尔等汉宫,读书稽古,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
况世祖圣祖,重熙累洽,八十余年,深仁厚泽。
沦肌浃髓,天下亿万臣民,无不坐享升平之福。
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视同仁。
及朕即位以来,推心置腹,满汉从无异视。
盖以人之贤否不一,各处皆有善良,各处皆有奸慝,不可以一人而概众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概众事。
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处之,尔等当仰体朕心,各抒诚悃,交相勉励,殚竭公忠,无负平曰立身立德之志。
或有一二心术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悛改。
朕今曰之谕,盖欲正人心,维风俗,使普天率土,永享升平之福也。
尔等承朕训旨,当晓然明白,勿存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职,屏去习染之私,朕必知之。
朕惟以至诚待臣下,臣下有负朕恩者,往往自行败露。
盖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
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
报应昭彰,纤毫不爽,诸臣勉之戒之。
查嗣庭读书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
而伊逆天负恩,讥刺咒诅,大干法纪。
著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
甲戌谕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
尔等多出自科甲之人,既诵法圣贤,读书明理,当知君臣之大义,须上下一体,情分相联,方克致升平之治,人人共受其泽。
自唐宋以来,去古已远,习俗浇漓,人心诈伪。
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滂,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
我国家恩养休息,海宇晏清,八十余年,万民乐业。
即尔等父母妻子,孰不沐浴膏泽,安享其福耶?
且士人立身行己,以礼义廉耻为重。
乃至昏夜乞怜,上书投扎。
满纸称功颂德之语,何廉耻荡然至于此极。
又有将子弟姻戚门生故旧私书请托者,不知以素所亲爱之人为之请,若先有请托,彼心以为势力可恃,肆其狂妄,无所不为,及实在赃托照拂,实属无益而有损。
盖彼无倚恃,尚知警惕自守,勉励供职。
款发觉则受请托者不能为之庇护,是非所以爱之,而实以害之也。
又尔等皆系各省州县之百姓,受制于有司者。
如请托之风尽除,凡地方有司,皆有所畏惧,而廉洁爱民。
则尔等之子孙宗族,咸受其庆,不亦善乎?
如请托之风不绝,则地方官员各有倚赖,将肆其贪婪,则尔等之家产,不足饱贪官污吏之溪壑,尔等自为身家桑梓计,亦断应速改历代之陋习也。
查嗣庭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
其曰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
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胜举,实共工兜之流也。
○陆生楠之狱以论前史而获罪者,白陆生楠之狱始。
自兹以往,非惟时事不敢论议,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读矣。
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前闻也。
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奏在军前效力之陆生楠,细书《通鉴论》七十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
其论封建之利,言词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时政。
参奏前来,陆生楠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履历奏折,前惟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
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
知其人必非醇谨,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
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楠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
转多愤懑之色。
彼时将伊扣缺,令以主事试用。
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冀悛改也。
后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
显然逆抗,形于词色。
夫主事职列部曹,外任知县,历俸多年,或卓异行取,始得升补。
而陆生楠以边方举人筮仕之初,即膺兹职,尚何负于伊,而伊竟敢怼及君父乎?
伊系广西人,平曰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
是以将伊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
一则令其观满州尊君亲上之心,如此其谨懔。
一则令其观我朝兵营之制,如此其整严。
一则令其观各蒙古部落熙醇朴之风,如此其诚实。
庶冀伊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
讵意陆生楠素怀逆心,毫无悔悟。
怙恶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
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
前锡保起行之时,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
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
今果得陆生楠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
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
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
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
皆郡县之故”等语。
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为尽善,而特创此以驾驭天下也。
洪荒之世,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
有圣人首出,则天下之众,莫不尊亲。
而圣人即各因其世守封之,亦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
盖时势如此,虽欲统一之而不能也。
夏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
周武王孟津之役,来会者八百侯国。
岂非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
孔子曰: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孟子曰:
“天下恶乎定?
定于一。
”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启一统之先几矣。
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自汉以来,遂为定制。
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功。
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功。
唐柳宗元谓公天下自秦始,宋苏轼谓封建者争之端,皆确有所见而云然也。
且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古之有部落耳。
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
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
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
咸凛正朔,以迄于今。
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
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
至若贾谊、晁错,欲削弱诸侯,乃虑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县为失而欲分之也。
李泌因藩镇之兵连祸结,思以封建为自固之谋,岂尝谓三代之制必可复乎?
今==成大一统之天下。
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
而陆生楠云:
“以郡县之故,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
”试问今曰之祸害何在?
陆生楠能明指之乎?
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
盖此种悖乱之人,自知奸恶倾邪,不容于乡国,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
殊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实天下所不容也。
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工为治。
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
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
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
同寅协工,固为治之要。
至于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
汉唐以来,有贤君图治于上,则必有良将助治于下,岂万世无一知人之主乎?
且同寅协工之道,于封建何与?
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
书有教胄子之文,礼有文王世子之篇。
仪文明备,教戒周详。
凡以养成德性,欲其学于古训。
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间疾苦,稼穑艰难之故,岂可禁之不闻外事乎?
至于父子天性,家国一理,惟有至诚至敬,可以为事亲之道,危机之说,岂人子所忍形于言存诸心者乎?
设使江充掘蛊之时,太子能居易挨命。
不诈出武库兵,发长乐卫,则决不至有湖城之难。
是戾太子之祸,正由于晓危机也。
又陆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
夫建储之事,乃宗庙社稷之业所关,天下苍生万民之命所系也。
倘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其后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至激为多故者,前代史册,历历可稽。
孟子曰:
“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
”又曰:
“为天下得人难。
”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
足以承先启后者,然后可以付之也。
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以来,未尝预建储位。
而我太宗文皇帝继位丕承,恢宏大烈。
世祖章皇帝绍业膺图,抚有中夏。
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御宇绵长。
凡我朝圣圣相承,皆未由显积青宫而后践天位。
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锡亿兆臣民之洪庥。
逮朕缵登大宝,重熙累洽之盛统。
七年以来,中外安。
是我朝国本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
昔宋孝宗时虞允文请早建储贰,孝宗曰:
“恐储位荚积,人性易骄,即自纵逸,不勤于学,寝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几无后悔耳。
”孝宗尚知立储之不易,况我圣哲高远之见,十倍于孝宗乎?
如陆生楠借汉武之事以讥刺者,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也。
其论兵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
“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
至今为梗,上陵下替。
”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
唐初府兵之制,本于北周苏绰之议,其后变为广骑,乃府兵废弛,不得不出于召募也。
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复府兵之法,然其时亦竟不能复。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无事耕种之农,岂能娴于武备?
有事征发之扰,岂能兼顾农桑?
以此为制,不但弃其兵,并弃其民矣。
古者六乡六遂之法,远不可稽。
后世民以养兵,兵以卫民,彼此相资。
唐宋以来,法制渐详,军农实称两便。
安有惜养兵之费,而弃不教之民者乎?
本朝设立八旗,京师重地,禁旅云屯,又有巡抚三营,以诘奸禁暴。
外省分设驻防将军,以及提镇。
内外相维,训谏甚备。
无事则分处什伍,兵不扰民。
有事则整旅出疆,兵以卫民。
此万古之良法。
今八十年来,太平无事。
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孰非兵防卫守之力哉?
民间虽有正供以佐军糈,然所出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养兵之利也多矣。
而陆生楠之为此说者,盖其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国无养兵之费,以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
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非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不宥也。
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
隋文帝以勤学节俭为治,史称其仓库实而法令行。
至隋炀帝以骄奢淫佚,自取败亡,非可诿之于天也。
后之人主,不为炀帝之行,岂至有炀帝之祸?
又何为而望天幸乎?
陆生楠之意又何指也?
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
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
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人主身为天子,富有四海。
自尧舜禹汤以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岂有位尊而即危祸者乎?
至于生杀赏罚,人主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
其生杀赏罚者,皆其人之自取耳。
朕临御以来,曰理万几,皆奉若天道。
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
而陆生楠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
试问在廷诸臣,朕自雍正以来,曾以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
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
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报哉?
且云蓄必深,发必毒,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陆生楠自蓄此心也?
阿其那等各案,内外臣工之所共知,无俟朕再为告谕。
陆生楠亦身列仕籍,岂无见闻而为此论?
其狂悖恶乱,不亦甚乎?
又云:
“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
”乃陆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
虽蓄怒而不敢显言,是以托于论列通鉴。
以微泄其愤,又怨而欲报,欲报而不能,但以身为祸烈等语,肆为咒诅。
其逆谋发露,公然形于纸笔矣。
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
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
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
夫从来不废密奏者。
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无专令参揭相臣之理。
况尊贤之道,最要在于去谗。
敬大臣之道,在于官盛任使。
君臣一德一心,乃为元首股肱之义。
是以择相之道,惟在得人。
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
且奏或不当,而犹多方掩饰。
是窥伺挟诈,教人以谗慝而招人以排陷也。
且臣相果属忄佥邪,便当露章宣奏,而群小故为排沮。
或欲动摇大臣,或从门户起见,人主自宜分别是非,以定邪正,岂可调停和处于其间乎?
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
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
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
舜命禹曰:
“无稽之言勿听,勿询之谋勿庸。
”召公告武王曰:
“言以道接。
”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此内外臣工所共知者,陆生楠何为而有此讥议乎?
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
君臣之间,岂容丝毫权术乎?
三载考绩,必以政事为据。
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
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
圣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有何作用乎?
宋神宗锐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张,其失在于作用明矣。
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
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
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
安石之误国,在于不引其君于当道。
非谓知天知人,惟有端居深拱,静默无为。
笃恭于无声无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
故夫笃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劝威之道,而极言其效如此。
非百务尽隳,上下暌绝而后可为治也。
其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又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
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纳领。
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
不事事而理,止理付元之人。
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
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等语。
从古圣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劳自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
是以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
理财一事,自应付之臣下。
至用人之权,不可旁落。
今试以铨选之权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
无论稍存容私徇情之见者,固不可一曰当此重任,即秉公持正之人,于同舍黜陟之际,不为怨府,即为祸源矣。
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迩,不忘远,古训昭然。
汉宣帝综核名实,治理一新。
光武务勤吏治。
唐太宗书守令姓名于御屏,朝夕省览。
古来贤主,未有不本于勤劳者,岂可以用人大节,为笾豆之事,置之不问也?
又云“绛度教谏,异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
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
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
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
夫嘉谋嘉猷,入告于尔后,乃朕曰所望于大小臣工者。
即位以来,时时谕令诸臣,以忠言谠论,面折廷诤。
凡内外诸臣条陈政务,有当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详议施行,并未尝拒谏诤而喜顺从也,至于人臣朋比,历代有之。
有以阿谀谄附为朋比,亦有以倾险幸直为朋比,如汉之梁窦,唐之牛李,宋之绍述,明之门户是也。
若唐虞之世,盈廷师济,一德一心,谓之朋比可乎?
以上皆陆生楠论断通鉴中语,朕指出数条如此。
陆生楠生当盛世,服习诗书,身叨乙榜,赴选朝官。
非若曾静之僻处深山旷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顽不灵之人也。
且观其人,未尝不小有才。
谓宜感恩戴德,勉恩报效,而乃怀不逞之邪心。
于进身筮仕之时,肆无稽之横议;
于政教修明之曰,对越大廷,则暴戾恣睢之气,形于词色;
远逐边塞,则猖狂怪诞之说,任意发舒。
其意专以摇惑众心,扰乱政纪为务。
朕实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愤懑何自而积。
此真逆性由于夙成,狡恶因之纷起。
诚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中之尤无忌惮者也。
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
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
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拟具奏。
○曾静、吕留良之狱曾、吕之狱,本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巨案也。
世宗至将其始末自著一书,名曰《大义觉迷录》,颁之学官,使秀才人人同读,与卧碑圣谕、广训等同视。
后至乾隆间,而《大义觉迷录》始为禁书。
雍正间之颁之学官,世宗之深心也。
乾隆间之列为禁书,又高宗之深心也。
各从其时,要之皆专制国之雄主矣。
今采《大义觉迷录》中上谕汇列之,共省览焉。
事之缘起,皆仍原文,不加褒贬,读者当能得之于言外也。
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静,因考试劣等,家居愤郁,忽图叛逆。
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以同谋举事。
岳钟琪拘留刑讯,究问指使之人,张熙甘死不吐。
岳钟琪置之密室,许以迎聘伊师,佯与设誓,张熙始将曾静供出。
岳钟琪具奏,并其逆书奏闻。
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至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捉曾静审讯。
据曾静供称生长山僻,素无师友,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遂被蛊惑,随遣张熙至浙江,吕留良家访求书籍。
吕留良子吕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诗文,内皆愤懑激烈之词。
益加倾信,又往访吕留良之徒严鸿逵。
与鸿逵之徒沈在宽等,往来投契,因致沈溺其说,妄生异心等语。
随将曾静张熙提解来京,旋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藏书籍。
所获曰记等逆书,并案内人犯,一并拿解赴部。
命内阁九卿等,先将曾静反复研讯,并发看吕留良曰记等书。
据曾静供称,前因轻信吕留良邪说,被其蛊惑,兼闻道路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弥天重罪。
今蒙一一讯问,并发吕留良曰记等书,极其狂悖。
又知圣朝深思厚泽,皇上大孝至仁,心悦诚服。
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等语。
因俯首认罪,甘服上刑,内阁九卿等备录供词,进呈御览。
雍正七年四月乙丑,谕内阁九卿等:
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圣相承,中外从,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思德教,超越百王。
普天率土,心悦诚服。
虽深山穷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尊亲。
讵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讥。
夫仪宾之后裔,于亲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
且生于明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
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
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
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
乃于康熙六年,因考试劣等,愤弃青衿,忽迫思明代,深怨本朝。
后以博学鸿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
按其岁月。
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
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
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凭虚撰造,公然骂诅。
所著书文以及曰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
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
盖其悖逆狂噬之词。
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
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
其曰记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
至致逆藩吴三桂,书亦曰清。
曰往讲。
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
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
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
于本朝疆宇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
于忠臣殉难,则污以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
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
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祸结兵连为幸。
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至此极也?
又如伪永历朱由榔窃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劫,贻祸民生。
后兵败逃窜缅甸。
顺治十八年。
定西将军爱星阿等,领兵追至缅城。
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
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
此伪永历之实迹。
岂有被执时满汉官兵,转于伊马前皆跪之事。
瞽说荒唐,诞谬极矣。
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实有征应之事迹。
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
快其私愤,又文集内云“今曰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
夫明末之时,朝廷失政,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
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曰蹙,每岁饷千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
我朝扫清寇气,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
逮我圣祖仁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久道化成,休养生息,六十余年,民安物阜。
即考羲皇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乎?
又曰记所载怪风震雷,细星如慧,曰光磨荡,皆毫无影响。
妄捏怪诞之处甚多。
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其失实不经,皆不顾也。
夫灾异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
若以捉影捕风之语,指为灾异,传诸后世,或谓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傥遇曰月星辰水旱之变,必生轻忽,漫不经心。
凡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可胜言乎?
其他猖狂悖乱之词,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举。
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
且曾静止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
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
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
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
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罪,皆吕留良之遗害也。
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
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
比时惊疑相煽。
逃避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