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文档格式.docx
《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文档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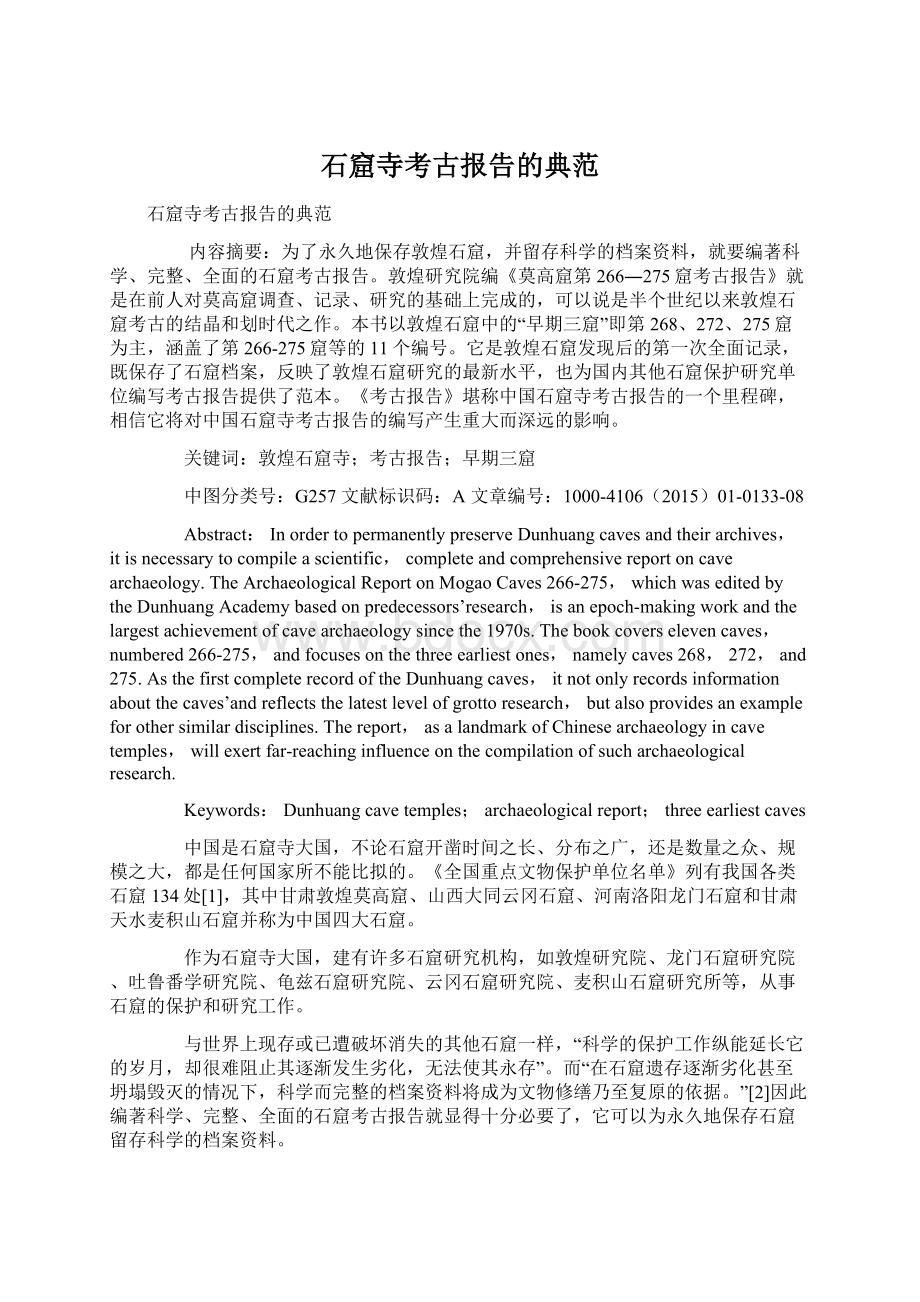
Dunhuangcavetemples;
archaeologicalreport;
threeearliestcaves
中国是石窟寺大国,不论石窟开凿时间之长、分布之广,还是数量之众、规模之大,都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列有我国各类石窟134处[1],其中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作为石窟寺大国,建有许多石窟研究机构,如敦煌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麦积山石窟研究所等,从事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与世界上现存或已遭破坏消失的其他石窟一样,“科学的保护工作纵能延长它的岁月,却很难阻止其逐渐发生劣化,无法使其永存”。
而“在石窟遗存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科学而完整的档案资料将成为文物修缮乃至复原的依据。
”[2]因此编著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报告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它可以为永久地保存石窟留存科学的档案资料。
我国的石窟寺考古已有了一定的成绩,如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编《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1卷[3]描述了20多个洞窟,并附录有“德国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概况”和“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
李裕群的《天龙山石窟》[4]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考古报告,但它对前人成果的追述、石窟考古调查报告和历史分期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景龙、杨超杰编著的《龙门石窟总录》(共36册)有龙门石窟的照片、实测图和文字记录[5];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写的《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6]、《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7]对所属石窟的位置、形制、内容与现状都有详细描述,有助于我们对石窟进行全面了解。
《中国石窟》丛书17卷由具有代表性的我国石窟群组成,是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国平凡社合作出版的大型彩色系列图书,由中日两国著名学者夏鼐、宿白、金维诺和长广敏雄、冈崎敬、东山健吾等组成编辑委员会,各有关文物考古单位负责编辑,两国学者分工撰写论文,从1980年12月开始,在北京和东京两地陆续出版中日两种文版。
它包括《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巩县石窟寺》等。
每卷发表图版192―300幅,论文2―5篇,并有图版说明、大事年表和实测图,还发表各石窟群的内容总录。
《中国石窟》虽然不是考古报告,但对读者了解各有关石窟提供了许多便利。
最早的有关中国石窟的考古报告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云冈石窟》。
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于1938―1944年对我国云冈石窟等文物进行了多次的调查测绘[8],考察成果就是1951―1956年作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陆续出版的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其副题是“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
与此同时,他们调查龙门石窟的成果是1941年出版的《龙门石窟的研究》,调查鼓山响堂石窟的成果是1937年出版的《响堂山石窟》[9]。
敦煌莫高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石窟最完整,壁画、彩塑最丰富,艺术成就最高的石窟寺,现存洞窟735个,其中有彩塑的洞窟492个(其中南区487个,北区5个;
北区另有243个供僧侣居住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埋葬的瘗窟、仓储的仓廪窟,窟内均无壁画、塑像)。
另外敦煌西千佛洞有洞窟22个,瓜州榆林窟有洞窟42个,这两处洞窟与莫高窟“因相同的地理位置、历史条件、题材内容、艺术特征,共属敦煌佛教石窟艺术范畴,统称为敦煌石窟。
”[2]1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长期以来没有对其完成考古报告。
虽然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996年又出版了敦煌研究院编写的增补本《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再加上以前出版、发表的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①[10]、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②[11]、张大千《漠高窟记》[12]、石璋如《莫高窟形》[13]及《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共5卷)和《安西榆林窟》等,对我们了解、认识敦煌石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它毕竟不是考古报告。
1988―1995年,在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的主持下,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共确认新编洞窟号243个,随后出版了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3卷)[14-16]。
但作为莫高窟主体的南区石窟却一直没有发表考古报告,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可喜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由敦煌研究院编,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8K本,共771页,以下简称《考古报告》)两大册已于201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中国石窟和敦煌学界几代人的夙愿。
《考古报告》既是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之作,也是敦煌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一全面系统的敦煌石窟考古记录
《考古报告》以敦煌石窟中的“早期三窟”即第268、272、275窟为主,涵盖了第266―275窟等的11个编号,也就是第266、267、268、269、270、271、272、272A、273、274、275窟。
这是因为第268窟本身就包括5个编号,即第267、268、269、270、271窟,以268窟为主室,其他4个编号是位于第268窟南壁和北壁的4个禅室;
第272窟包括2个小窟,即第272A和273窟,它们分别位于第272窟外壁的门南和门北。
此外还纳入了第266、274窟,这是由于第266窟与第268窟毗邻,第274窟位于第275窟的外壁南侧,不便与其他的洞窟编在一起,而它们的开窟、绘画时代也与第268窟表层壁画接近,故将这些洞窟放在一起,编为《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考古报告》所收第266―275窟“位于莫高窟南区石窟群中段自上而下第三层洞窟崖壁上,坐西向东,左右毗邻。
南邻北魏第265、263、260、259、257等窟;
北连隋代第457、456、455等窟;
上承盛唐第264、460、458等窟,晚唐第459窟;
下接隋代第56、59窟,初唐第57、58、60等窟和五代第61窟”。
[2]19
《考古报告》第一分册除序言外,共由7章组成,即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第266窟;
第三章:
第268窟(含第267、269、270、271窟);
第四章:
第272窟(含第272A、273窟);
第五章:
第274窟;
第六章:
第275窟;
第七章:
结语。
另外还有6个附录,即一:
本卷洞窟调查记录文献摘录;
二:
本卷洞窟历史照片选辑;
三:
本卷洞窟相关论著、资料目录;
四:
本卷洞窟碳十四(14C)年代测定报告;
五: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敦煌石窟考古测绘中的应用;
六:
莫高窟早期三窟壁画和彩塑制作材料分析。
其中“本卷洞窟调查记录文献摘录”又包括11项内容,即《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摘录,奥登堡《敦煌千佛洞叙录》摘录,张大千《漠高窟记》摘录,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摘录,石璋如《莫高窟形》摘录,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摘录,史岩《千佛洞初步踏查纪略》摘录,李浴《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摘录,阎文儒《洞窟内容说明》摘录,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摘录和樊锦诗、蔡伟堂《重订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
“本卷洞窟历史照片选辑”包括李约瑟敦煌摄影、罗寄梅敦煌摄影和敦煌研究院藏历史照片多幅。
除文字描述外,第一分册还收有各种插图250多幅,与文字描述交相辉映,增加了许多直观性,既保存了历史资料,也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理解文字说明。
第二分册全是图版,收有测绘图版99版、摄影图版246版和数码全景摄影拼图44版。
这些图版有些是一图一版,有些则是一版多图,如测绘图版中的第99版“塑像等值线图”就包括第275窟北壁和南壁的6尊塑像;
摄影图版中的第12版包括第266窟西壁龛外的弟子和塑像4幅,第55版包括第268窟南壁东端上层重绘壁画4幅,第155版包括第272窟东壁遗迹6幅。
这些高质量的图版,既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如测绘图基本上都是实测的成果,其中反映洞窟整体结构和内容的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都集中在第二分册,而有关洞窟遗迹的各种局部图,则作为插图放在第一分册的正文之中。
摄影图版“主要用彩色反转片拍摄,适当补充数码照片,从洞窟外景到窟内,表现洞窟结构、塑像、壁画、各立面相互关系、遗迹重层叠压以及考古学方面值得注意的其他现象,全方位拍摄照片,以全景和局部取景构图,力求再现现存石窟文物的全貌。
”数码全景摄影拼图“是采用当前数码技术拍摄制作的洞窟全景照片,一定程度避免了照相镜头的透视变形。
”[2]25-26
《考古报告》除第一章“绪论”和第七章“结语”外,每章基本上都由“窟外立面”、“洞窟结构”、“洞窟内容”和“小结”等4节组成,只有第四章“272窟(含第272A、273窟)”加了“窟外小窟”一节,另外,有关洞窟“近现代遗迹”的内容,基本上都在“洞窟内容”中介绍,只在第二章“第266窟”中单独列为一节。
《考古报告》首先对窟外立面有历史性的全面介绍,第266―275窟开凿在莫高窟南区中部偏北的崖面上,距离现地面高约6米,“所处崖面相对向前凸出,属于开窟造像比较理想的位置。
而且,此处岩质在酒泉系砾岩中相对较为坚固,在南北两端及上方崩塌之后益显前凸。
鸣沙山东麓石窟开凿伊始,选择此处当非偶然。
此后,北朝石窟的开凿由此向南延伸”。
从洞窟崖面布局及各种遗迹,“可推测至少第268、272、275三窟在历史上或许有过一定的规划”[2]243。
第三章“第268窟(含第267、269、270、271窟)”是这样描述的:
“第268窟坐西向东,方向为东南偏8度,高程1337米,南邻第266窟,北接第272窟,上方为第460窟,下方为第57、58窟”;
“第268窟早年因崖面崩塌,外立面受到破坏,又于20世纪60年代莫高窟大规模危崖加固工程中被修建砌体覆盖。
据现存残迹和历史照片,此窟甬道北侧已无存,损毁及于窟口和窟室北壁前端的上方。
在196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调查测绘的《莫高窟南区立面图》中,第268窟窟口呈纵长方形,高187厘米,宽72厘米;
窟口北沿距第272窟窟口南沿约228厘米,距第275窟窟口南沿约606厘米;
窟口南沿距第266窟(窟)口北沿约210厘米,窟口上沿距第460窟前室地面约180厘米;
窟门下沿距第57窟前室顶边146厘米,所反映的应是此前未经过维修时的情况。
”[2]48
同时还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变化,如第266窟“北壁中部约于近代开凿穿洞,向北与第267、268窟相通。
20世纪60年代危崖加固工程中将其封堵,抹以石灰面”;
“1948年至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原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调查记录洞窟壁画和塑像时,在窟室各壁面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墨书于壁画的下边或塑像座上”;
“20世纪50年代,为崖体崩塌形成敞开的窟口敷泥,进行修整,并涂白灰”。
“窟内地面于20世纪60年代维修,随后铺设水泥。
现有的甬道地面、南壁和窟室东壁南侧壁面及南壁东端、窟顶东南角为20世纪60年代危崖加固工程时修建,甬道北壁、窟室东壁经维修;
窟门为1987年安装。
”[2]46-47
这样全面、详细的描述既保存了石窟的历史与现实状况,留存了档案资料,又给人以直观、全面的立体感,很便于读者理解。
另外,《考古报告》附录所收照片是第二分册“图版”的重要补充,“鉴于石窟文物历年发生的变化、受到的残损,以及遗迹因维修而发生的改变,需要利用这些照片作为参照。
”[2]26
二石窟考古报告的划时代之作
敦煌研究院虽然竭尽全力与世界合作保护敦煌石窟,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与世界上现存或已遭破坏消失的其他石窟一样,仍然“无法使其永存”。
为了永久地保存石窟,并留存科学的档案资料,就要编著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报告,它是几代敦煌人的夙愿,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石窟界和敦煌学界的期盼。
《考古报告》是在前人对莫高窟调查、记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敦煌石窟考古的结晶,是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划时代之作。
早在1957年4、5月,作为主管文物与博物馆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曾率队对敦煌进行参观考察,并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敦煌考古报告的编写提出了意见。
在其日记中就有“拟印行《敦煌》二百四十多本,其中‘图录’占一百二十多本”和约敦煌研究所有关同志谈话,说明编辑《敦煌》的计划[17]。
“1957年郑振铎先生视察莫高窟时,提出编辑出版敦煌图录的设想,计划全书为120卷,次年成立《敦煌图录》编委会。
1962年文化部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对《敦煌图录》的出版工作计划再次予以肯定,此后编辑计划又多次修改调整”[18]。
1958年成立的《敦煌图录》编委会由王乃夫、王冶秋、王振铎、王朝闻、叶浅予、刘敦桢、吴作人、张珩、周一良、金维诺、赵万里、赵正之、夏衍、夏鼐、宿白、常书鸿、梁思成、董希文、谢稚柳、翦伯赞等20位学者和艺术家组成,并于1958至1959年召开过三次编委会,制订了出版规划纲要、选题计划、编辑提纲和分工办法等文件草案。
到1959年时,已经编出了第285窟的样稿{1}[2]1。
1962年,北京大学副教授宿白先生带领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樊锦诗、马世长、段鹏琦、谢德根到莫高窟进行考古实习,并指导学生按照石窟寺考古学的方法,选择了包括第275窟在内的一些典型洞窟做全面的实测和文字记录。
在此期间,宿白先生还于9月11日至11月8日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11次学术讲座,这就是在敦煌学术史上著名的《敦煌七讲》{1}。
宿白先生的学术讲座,对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后的学术研究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指导意义。
如果说此前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以石窟的保护研究为主的话,现在则是在石窟保护研究的同时,开始了遗书的研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宿白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尤其是石窟寺考古研究的权威,他的《敦煌七讲》中有五讲都是关于石窟的,除了敦煌石窟外,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对地处偏远、交通信息闭塞的敦煌,无疑是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此,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了敦煌莫高窟的考古学记录工作,先后绘制了第248窟、285窟的测绘图,写出第248窟的文字记录,开始编撰第248窟考古报告的初稿,终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2]1。
1963年,在莫高窟南区石窟维修加固期间,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贺世哲、李永宁先生测量和记录了窟外崖面上窟口及岩孔等遗迹,绘成了《莫高窟南区立面图》[2]23。
20世纪80年代初,为适应国际敦煌学的大发展,1983年8月,在兰州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
随后,甘肃省委于1984年1月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
乘此大好时机,敦煌研究院逐渐恢复了石窟考古和编写报告的工作。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敦煌研究院先后组织人员对莫高窟第268、272、275窟进行了传统的手工测绘,后来又增加了相邻的11个洞窟,作为《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的内容,尝试进行文字记录的撰写。
1994年再次草拟了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计划,并在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报告的编写小组。
2002年,敦煌研究院确定由樊锦诗、蔡伟堂等承担《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编写任务,并与文物出版社达成了共识。
2004年8月,成立了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数字中心、信息资料中心的专业人员组成的考古报告编辑工作委员会,并确定了报告分卷编写的体例。
2006年12月,作者将报告校样分别呈送有关专家审阅,征求意见。
2007年,根据专家的审稿意见,作者开始进行全面修改,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与绘图人员一起“对照洞窟,反复核查,修改图纸”。
从2009年8月起,在重新测绘洞窟的基础上,作者再次对文稿进行全面改写,直到2010年定稿[2]23-24。
由于敦煌石窟的数量庞大,内容丰富,除已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外,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规模还要约100卷。
要完成这样规模宏大的多卷本考古报告,首要的任务是制定分卷原则。
但如何分卷,又是一个难题,其中就有多种意见和方法:
或按洞窟编号的顺序,以相同或相近的分量,依次分为多卷;
或按先重点洞窟、后非重点洞窟的原则分卷编写;
或以洞窟开凿时代的早晚作为脉络,兼顾崖面布局形成的现状,依次组合各卷的洞窟。
还有以编辑出版的先后分卷的意见,甚至不分卷的意见[2]2。
以上分卷意见各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局限。
敦煌石窟的开凿及石窟崖面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石窟的修造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崖面上石窟群的布局呈现出不同时代参差错杂的现象。
“北朝至唐代前后各时代洞窟建造的位置和排列大致有序;
同时代洞窟或成组、或成列,大致形成特定的区域。
至五代、北宋以后,在崖面基本饱和的条件下继续开凿洞窟,或向崖面的两端和上下发展,或在洞窟与洞窟之间插空补缺,或改造、重绘前代洞窟。
另外,石窟分期断代的研究表明,不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相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建筑形制、塑绘内容、艺术特点、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的共同特征,又在建造规模、洞窟结构、艺术水准和保存状况等方面存在差异。
”[2]2敦煌石窟形成过程中的这些复杂因素,都是石窟考古报告分卷中必须认真考虑的。
为了使多卷本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学术性,并避免因编排不当造成撰写时的混乱、重复或遗漏,避免各卷分量的轻重差别太大,编委会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方征求意见,制定了分卷的基本原则:
“以洞窟建造时代前后顺序为脉络,结合洞窟布局走向,以典型洞窟为主,与邻近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若干洞窟形成各卷的组合。
”[2]2
体例确定后,经过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三位编者及许多协助者几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2011年出版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如果从1957年郑振铎提出编辑《敦煌图录》的设想开始,到2011年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已经50多年了;
如果从1962年在宿白先生指导下开始编撰第248窟的初稿,也已经近50年了;
就是从1994年成立考古报告编写小组算起,也已经17年了。
从郑振铎、宿白到樊锦诗经历了整整三代人,现在樊锦诗也已年过古稀,终于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几代人的梦想。
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很长,任务也非常艰巨。
因为《敦煌石窟全集》除敦煌莫高窟外,还包括西千佛洞和榆林窟,总规模大约要100卷{1},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
盼望后继者能不负众望,在已有良好开端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高质量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三具有新意的石窟考古研究成果
除了全面介绍外,本书在详细认真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将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如第272窟外壁的第272A窟和第273窟,在《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等权威分期中,将其归入北朝第二期。
《考古报告》认为,这一看法“似不确。
经测绘证实,二龛大小、高度、内容、形制均一致,在第272窟外立面上分居两侧,规整对称,同第272窟浑然一体,是在统一规划下建造的。
”[2]141另如第275窟壁画敷色中出现了蓝色,曾有意见认为这是莫高窟最早期洞窟的孤例,经过认真细致的考察后发现,“这部分壁画全部处于隔墙遮蔽处,曾受到严重的烟炱污染,呈现蓝色或者偏蓝的绿色是否属烟炱污染所致尚有待研究”,因为“同样内容的描绘,在窟内未受烟熏的部位都表现为正常的绿色。
”[2]238再如经过考察后作者提出,第275窟“曾经过后代数次不同程度的重修,其叠压关系明显,层位大致清楚,可分出三个层次。
”[2]155
第一层壁画和塑像是敦煌石窟最早的作品,是开窟时的原作,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切判定第一层的具体年代,但它属于“北朝第一期洞窟”[2]238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第一层的内容十分丰富,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早期经变画很多,如佛本生故事中的尸毗王割肉贸鸽故事、月光王施头故事、快目王施眼故事、悉达多太子出游故事等。
洞窟建造完成后,历史上可能经过两次重修。
“第一次仅限于对东壁中段壁画的改绘”[2]237。
因此第二层壁画“仅见于窟室东壁南侧中段”[2]211。
第二次重修前,窟前崖面曾有过大范围的坍塌,因此第二次重修规模较大,不仅对窟室进行了改造,而且对壁画做了补绘和重绘,对塑像加以妆銮彩绘,“东壁南侧的第二层壁画,也一并被第三层壁画覆盖。
第三层营修和绘画的时代,可以推定为曹氏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即五代、宋时期。
”[2]237“1991年,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在剥离、搬迁第三层隔墙壁画时将东壁南侧中段的第三层壁画一并剥离。
由此,第二层壁画得以揭露。
”[2]211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是中土最先接触外来文化的地方。
佛教石窟寺源于印度,作为佛教艺术代表的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