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影响力因素分析文档格式.docx
《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影响力因素分析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影响力因素分析文档格式.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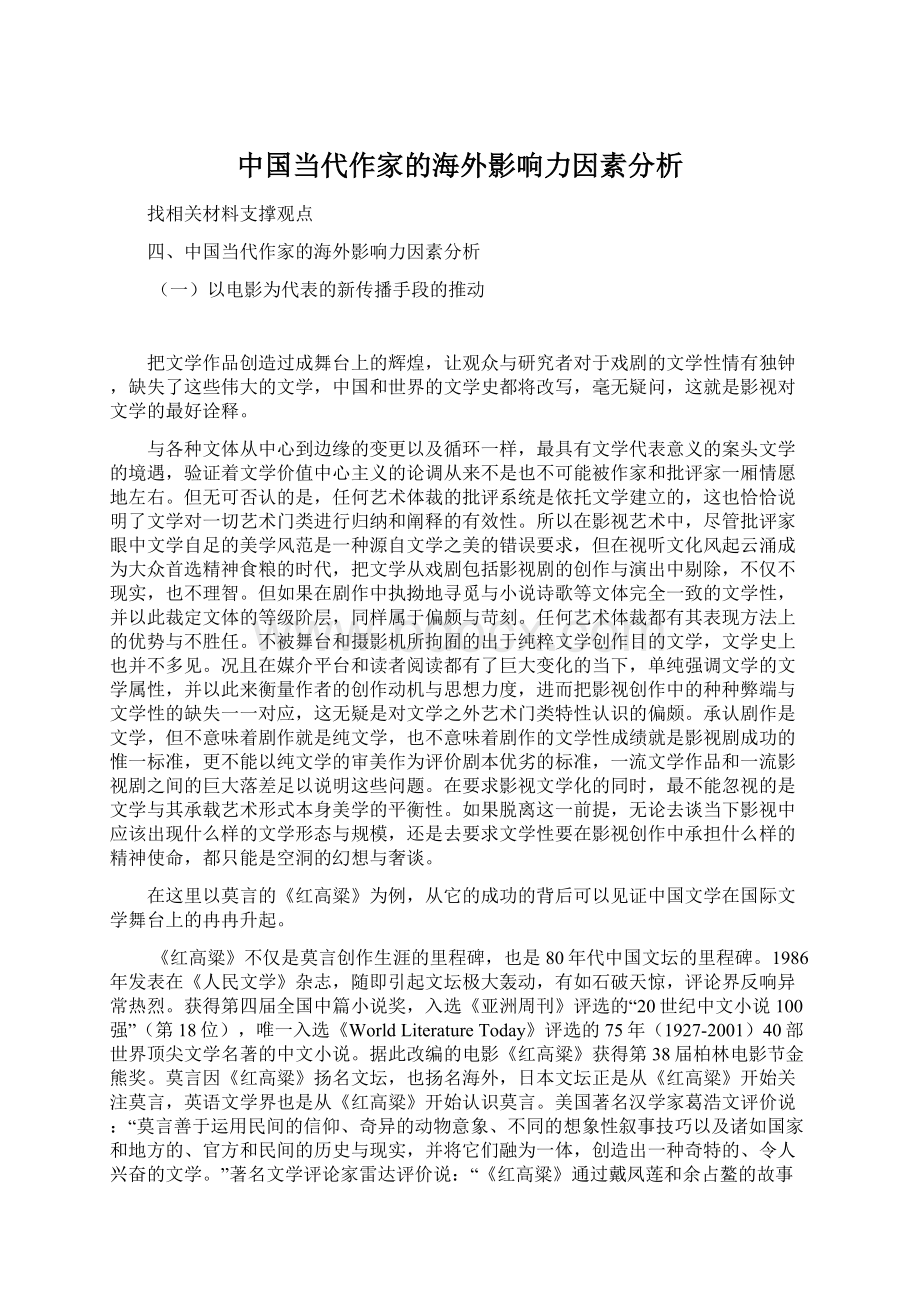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评价说:
“《红高粱》通过戴凤莲和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
莫言以他富于独创性的灵动之手,翻开了我国当代战争文学簇新的一页———他把历史主观化、心灵化、意象化了。
”
台湾作家骆以军评价说:
“《红高粱》展示了不可思议的、魔幻的、乡野之怪的战争场面或性的原始欲力,莫言是像马尔克斯、鲁西迪那级数,是可以不断从故事秘境召唤各种喷发奇想、充满暴力又诗意的魔术师!
”《纽约时报》评论说:
“通过《红高粱》,莫言把他的‘高密东北乡'
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从上面的影响力上看,足以证明它是成功的。
(三)符合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想象
这里选择了几位西方名人,介绍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论断,我个人以为,一个想要追赶世界文明主潮的文化,更需要的是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
从感情上说,我们愿意听的也许是西方哲人颂扬中国文化的话,人们多以此来证明新的世纪必将具有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特征。
但也不妨听听另一类看法。
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一六八九——一七五五)是通行现代社会的“三权分立”理论的创始人。
在孟德斯鸠的笔下,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专制”。
他写道,中国政府只有在施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
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
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论法的精神》,商务版,129页)
对于中国的这种专制,也有人大唱赞歌,比如与孟德斯鸠同时代、同国籍、同知名度(各在不同领域)的伏尔泰和奎奈。
如果对文化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制度和观念在内的一切总和),说专制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并且这种特征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主要是消极的,无疑是正确的。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制度是专制,应该变革,是“五·
四”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
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是对的。
赫尔德(JohannGottfriedvonHerder,一七四四——一八○三),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驱。
他说,在中国,一切都缺乏对真正自然关系的追求,只能使肉失去真正的感受,一切都“就范于政治文化,从而无法摆脱政治文化的模式。
”(《德国思想家在中国》,江苏人民版)
波伏瓦(SimonedeBeauvoir,一九○八——一九八六),法国作家,她的丈夫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萨特(Jean-PaulSartre,一九○五——一九八○)。
她对中国文化的“泛政治化”特征有着更具体的限定。
她说,中国文化“实质上是文官和朝臣的文化”。
“泛政治化”这个词,我是从台湾的报刊上学到的。
台湾报刊上经常用到“泛政治化”这个词,而且大都带有某种贬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词,非常欣赏它。
我更欣赏在使用这个词时赋予它的那种贬义。
“泛政治化”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其的“不敬”并“远之”,标志着文化上的觉醒。
政治文化,就是政治挂帅,权力至上,就是“一切为了权力”、“有权就有一切”,就是一切都被政治权力所垄断、所操纵。
说中国文化特征是政治文化,并不是说每一个(当然也确实是有很多)中国人都热衷于追逐权力,都擅长于玩弄权术。
而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逃脱不了权力的追逐,都避免不了权术的玩弄。
政治无孔不入,权力无所不在,经济、科学、艺术无不屈从政治权力,父子、夫妻、长幼、男女无不重现君臣关系(连中医给人开药方,也要有“君”有“臣”)。
在这种文化中,许多人患有“政治过敏症”,原本与政治毫无牵连的言和(或)行,都被拉扯进政治。
写“清风不识字”的秀才,被砍了脑袋;
抱怨“东风送来乌烟瘴气”的工人,被取了生命。
与中国文化特征是政治文化(或称为官场文化)相对应,西方文化特征是经济文化(或称为市场文化)。
在前者,政治决定经济,市场被官场化;
在后者,经济决定政治,官场被市场化。
(官场市场化,不是指“金权一体”、“官商合流”,而是指政治家与选民的关系就像市场中卖主与买主的关系。
政治家“出售”自己,要靠媒体广告,要靠形象包装,要靠产品——政策——品质,以赢得选民手中的“钞票”——选票)。
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一七七○——一八三一)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古到今都维持着原状,“从无发生任何变化”。
(《历史哲学》,三联版,161页)
斯密(AdamSmith,一七二三——一七九○)在比较欧洲和中国时指出,欧洲在不断前进,而中国则总是在原地兜圈子,虽然中国早先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勤勉的国家,但许久以来,“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版,182页)
李约瑟(JosephNeedhan,一九○○——)提出一个“悖论中的悖论”:
停滞的中国竟是在西方社会结构中起着定时炸弹作用的那么多发现和发明的施主。
他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来描绘这个“悖论中的悖论”,他说,中国“像旋转砂轮那样连续不断地迸发出火星来,它们点燃了西方的火绒,而砂轮仍在支承上继续转动,不摇晃,也不消耗。
”(《李约瑟文集》,辽宁版,273,275页)
托尔斯泰(LevTolstoy,一八二八——一九二○)也认为中国是停滞的,但他认为这种停滞优越于西方的进步。
在一九○五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人们经常谴责中国的停滞,但如果我们将它与西方所取得的成就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这种停滞要比西方文化的“敌意、过敏、无休止冲突的状态好上一千倍。
”(Tolstoy'
Letters,Vol.II,NY,p.654)
停滞不等于安定。
于停滞相对应的,是进步;
与安定相对应的,是动荡。
中国和西方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从大体上说,停滞带来的是动荡,进步带来的反而是安定。
就中国文化(不管是先哲的观念还是君主的制度)的理想而言,追求的是安定。
这是一点不错的,丝毫不应责怪。
应该责怪的,是以停滞作为实现安定理想的唯一操作手段,甚至干脆就将停滞认同为安定。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乱多于治,大乱小乱上乱下乱内乱外乱时而交替、时而并发,社会难以持久安定。
这是历史的教训!
安定只能用持续不断的进步来换取,只有这样的进步才能使国民享受真正的安定。
艾蒂安·
白乐日(EtienneBalazs,一九○五——一九六三),被费正清誉为“欧洲最伟大的中国学学者之一”。
他写道,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它们散布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每一个农民家庭就“成为单独的,互相孤立”的“细胞”。
(《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台北久大版,230页)
我曾经提出一个“经济仿生”的概念(Fu,Hongchun,“EconomicBionics”,The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Economics,Vol.5,No.1[1994],pp.3-10),因此我对于白乐日用“一群分散的单细胞”来形容中国文化特征,很感兴趣。
比起很多中国人自己经常爱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白乐日的说法更具有经济学意义(白乐日本人对于“细胞”和“散沙”倒没有加以区别,行文中是将两者混同使用的)。
从生命科学的观点看,多细胞生物比单细胞生物高级;
多细胞生物中,细胞间功能分化越是细微、越是复杂,其生命形态就越是高级。
中国几千年,一直是小农自然经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大多数家庭都重复着男耕女织的模式,相互之间没有来往。
若干说中国是一群分散的单细胞的话,那末,西方就是一个通过市场使细胞间功能高度分化又高度聚合的多细胞生命体。
分散的单细胞的生命活动,只是取决于它与自然环境的联系,而不是取决于其它与他的单细胞的联系。
在一个多细胞的生命体内,各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则是首先取决于它与生命体内其他细胞的联系。
分散的单细胞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改造能力,都不如多细胞生物。
分散的单细胞如果发生拥挤,在环境恶劣时,相互之间就形成你死我活的争战。
多细胞生命体内的各个细胞,相互之间则是生死与共的依赖。
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并且擅长“窝里斗”,而西方人是既富有个人主义又富有团体精神,两种文化的这种差别,其经济上的原因即在市场的有无及其发达程度的高下。
这也可以解释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不如虫。
”就单个的细胞来说,高级生命体(比如人体)内的某个细胞不能离开这个生命体而独立成活,但单细胞生物却能够维系其生命。
也就是说,在分散的细胞水平上,单细胞生物比高级生物有更强的生命力。
这不是说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人种上的差别,而是说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文化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结构。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体系中,精细的专业化使人们长于一点而不善其余(若唤牛耕地,中国的老农们肯定要笑爱迪生、爱因斯坦们是“白痴”了),但广泛的交往与交换却能使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长足发展,这是任何一个中国小农家庭所不能比拟的。
说中国人“单细胞”也好,“散沙”也好,并不是说中国人相互之间完全没有来往、完全不能协同。
只是这些来往和协同主要地不是基于经济上的“互通有无、等价交换”的内在欲望,而是基于其他(最主要的是政治)的外在强迫。
“八年抗日战争”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十年文化革命”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孟德斯鸠说,贸易很会自然地激起人民的信实,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
中国人在从事贸易的时候特别会表现出,虽然他们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论法的精神》,商务版,316页)
康德关于中国人经商骗人的描写,小说似的,有情景,有形象。
他说,中国人可以把碎块布料缝结成一整块,其手艺之精巧,就连那些最为小心谨慎的商人也难看出破绽;
他们还用铜丝修补联结破碎了的瓷器,使其乍一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
因为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它们往鸡嗉囊里填砂子。
“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版)
黑格尔的批评更尖锐,更推至一般化。
他说,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现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
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
”(《历史哲学》,三联版,174页)
说“中国人最会骗人”,对于自诩“几千年礼仪之邦”的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许多西方人也与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唱“对台戏”。
比如德国哲学家赫尔曼·
凯泽林(HermannKeyserling,1880-1946)就说中国人“最为彻底地讲究礼节并且最有操守。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最为诚实。
”(TheTravelDiaryofAPhilosopher,N.Y.1925)
我不同意说“中国人最会骗人”。
罗素也曾指出,他坚信,“在相互欺骗的比赛中,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十次中有八九次能胜过一个中国人。
”(TheProblemofChina,London,1960,p.204)但我也不认为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人关于“中国人骗人”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
在这里,值得我们检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别人会留下“中国人骗人”的印象?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在中国文化里找到某种答案的。
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把人们可以享用的财富比作一个蛋糕的话,那末,西方文化认为这个蛋糕的尺寸是可以变得更大的,质地是不均匀的。
而中国文化则认为这个蛋糕的尺寸是既很小又很难变大的、质地是均匀的。
由此出发,西方文化重消费(因为可以吃更大的蛋糕),重生产(因为可以做更大的蛋糕)、重交换(因为可以得更合个人口味的蛋糕)。
而中国文化则不重消费,不重生产,不重交换,单单只重分配(因为你少我就多、你死我就活),就是孔子所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换不安。
’”(载台北《今日经济》,一九九四年十月号,43—51页)
联系到“骗人”的话题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化认为,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一个人要满足自己的私利,必然要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手段、为代价;
在市场交换上,要么骗人,要么被骗。
因此,最好是不要私,不要利、不要市场。
这就是中国文化“贬私”、“轻利”、“抑商”的缘由。
用个比喻说(前面说过比喻总是不精确的),对于发生车祸,中国文化是要消灭一切车辆,要人们一律步行;
西方文化则是在增加车、路、交通规则的数量并改进其质量上下功夫。
结果是,事实上根本消灭不了的私(这是人的天性),要么对别人假装出已经消灭(这就是骗人!
),要么进一步通过损害别人而得到满足(骗人加害人!
)。
因为没有将“私”引导到“必须为别人服务才能得到满足”的有效手段与规则。
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缺乏“双嬴”的概念(台湾人现在经常讲“双嬴”,这也是文化上觉醒的一个可喜标志)。
而“双嬴”在西方是有经济学的依据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A有苹果却不喜欢吃苹果而喜欢吃梨,B有梨却不喜欢吃梨而喜欢吃苹果。
交换的结果,两个人都是既满足了自己的私利也满足道别人的私利,这就是“双嬴”!
黑格尔说,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历史哲学》,三联版,181页)
很明显,如果将“文化”限定为“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不包括“凡是属于‘制度’的一切”。
这也确实是当今很流行的一种见解),那末,黑格尔的意思就是,“中国没有文化”。
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一八五六——一九五○)于一九三三年到中国访问,在接受上海记者采访时,发表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意见。
他说,中国没有什么文化可说,因为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人类幸福的行为,尤其是对于自然界的控制。
“在中国,除开乡村的田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的了。
”(《萧伯纳在上海》,的川人民版,111页)
说“中国没有文化”,多数中国人(以及多数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外国人)是不会同意的,笔者即为这多数中国人之一。
可是我们并不能谴责黑格尔和萧伯纳对中国太不客气,只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乱语。
理解黑格尔和萧伯纳上引两段话的关键,在于他们有关文化的特殊定义。
黑格尔的定义是西方标准,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西方文化。
这是事实,不必争辩。
萧伯纳的定义即“人的一切可以增进人类幸福的行为,尤其是对于自然界的控制。
”笔者并不支持萧伯纳这个关于文化的定义。
但如果限定于萧伯纳的定义(前提)之内,我以为,萧伯纳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结论是能够成立的。
也就是说,如果将“增进幸福,控制自然”视为文化的一个部分,(萧伯纳的不当在于他将此视为文化的全部)的话,那末,中国文化里这一部分的缺失,确实是非常严重、非常突出,与西方文化相比完全够得上称之为“特征”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欣赏萧伯纳的洞察力并感谢他的直言不讳。
我对文化定义的理解,倾向于最广义的那种,也就是文化无所不包、什么东西都可以算是文化的一个构成分子。
但我并不认为文化中的任何一个构成分子都能够完全代表这种文化。
比较能够代表这种文化的,是其中既有传统又占主流的成分(特别是在统治地位的观念与制度)。
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特征是“专制”、“泛政治化”,“停滞不前”、“无内聚力”、“不诚实”、“没(西方)文化,虽然难听,但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不难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找到令我们自豪的成分,也不难在西方的文献中读到让我们喜笑颜开、手舞足蹈的夸奖,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还是应该查自己的短处、听别人的批评(而且它们大都也并不是恶意的)。
在这里还以莫言的《红高粱》为例,进行说明,从红高粱中的悲剧人物故事开始讲述中国文学中包含的艰辛以及苦难。
并通过在它所得到西方人的认可,以所取的成就说明其中人物形象被广大的西方人说接受以及高度的认可。
《红高粱》中的九儿被火红的喜轿抬回了十八里坡。
火红的轿子、红红的嫁衣、无一不体现了喜庆和吉祥,但在奶奶九儿的眼里这些火红的颜色与象征死亡的白色没有什么区别。
她是在父亲的逼迫下嫁给麻风病人李大头的,嫁入十八里坡对奶奶来说无疑走向了死亡。
无奈的九儿在父亲的眼里竟然抵不过李大头的聘礼,九儿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无奈和痛苦。
所以在轿把式戏弄式的颠轿下发出了她压抑已久的哭声,这哭声充满了抗争、不平。
片中特意交代了爷爷的身份,他是唯一被雇来的轿把式,他年轻、健壮充满了活力。
这与奄奄一息的李大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有意的戏弄奶奶激发了奶奶抗争的哭声,哭声在十八里坡的野高粱地里回荡。
画面在红高粱的衬托下显的更为壮观,火红的高粱地丝毫没有给人以喜庆祥和。
相反,它给了人一种神秘和恐怖。
《红高粱》对红色的使用可谓是张艺谋所有作品中最登峰造极的一部作品。
影片中的红高粱、高粱酒无一不给人满眼的红色。
但这些红色的使用却更多了神秘、反抗、凄凉。
当日本人的铁蹄走进这片红色的土地时,影片更是为我们展示了红色的血腥。
血红的牛皮被日本人当成了向中国人示威的工具。
血迹顺着牛皮一滴滴地流了下来。
正当我们为这一切惊叹的时候,一向罪恶深重的土匪头子三炮却成了第一个起来反抗的英雄。
在民族面临危险的时候无论你以前干过什么,但民族的召唤都是让你为它付出你的所有。
影片中高粱地的人们也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人的残暴激怒了这火红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屠夫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成了行刑的凶手,但他最终选择了反抗。
他的血不断的流淌着,滋润这片土地,更滋润着人们的心,而罗汗大哥的死最终激起了人们的反抗意识。
“红红的血迹”、“冰凉的子弹”为我们营造了一场动人心弦的红色悲剧。
奶奶是从火红的十八里坡嫁进来的,她大胆的与爷爷野合。
奶奶生活的所有转折点都与这红高粱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影片的结尾处她倒在了象征她一生悲剧的高粱地里,在这里红色再一次被张扬起来,那刺人心痛的红色与奶奶九儿的命运形成了完美的契合,而在结尾处张艺谋设计了日全食这个意象再次为我们突现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并再一次升华了影片中的红色意象。
《红高粱》这部影片折射了太多的血腥和凄凉。
1988年5月,柏林上空的一声霹雳,撕破了西方人对中国电影所持的蔑视与迷幻。
《红高粱》为中国电影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级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可以说,它是中国电影的高峰,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高峰。
在这里,我想谈谈《红高粱》,从而说说它所能代表的中国艺术的精神。
影片以红色为主基调,利用色彩本身对于人的视觉的美感效应以及色彩的象征意义,勾起人们丰富悠远的联想,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审美体验。
“娘,娘,上西南,高高的大路,足足的盘缠,娘,娘,上西南……”“我”父亲高亢童稚的声音回荡不绝,碰得高粱棵子簌簌打抖。
在剪破的日影下,“我”爷爷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籍,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浸泡成深红的稀泥。
血色夕阳,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的血海。
奶奶安详地倒在血泊中,高粱齐声哀呜,慷慨、悲凉。
太阳被暗红色的血抹成深红,红色的太阳燃烧着,世界都是红色……我沉浸在极度的美的感觉中,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电影《红高粱》的结尾,是影片最富有形式感的部分。
有人认为它太过于形式化,其实不然。
这样的红,代表着大爱大恨、大悲大喜、大彻大悟、大执著、大解脱,这是中国艺术雄浑壮丽的“境界”之美。
同时,这种独特的美感形式和艺术风格,也构成了中国艺术的精神气质。
就像影片中热烈而淳朴的鲜红,就像云门《水月》的静谧,就像阿炳《二泉》的凄婉,就像太白“飞流直下”的豪迈,无需多言,一看就是“中国制造”,一看就是中国精神。
在《红高粱》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
因此.摆在观众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
这种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阳崇拜”的神话中。
《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影片,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
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
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
影片中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这是张艺谋的一种风格,也是中国艺术的一种风格。
淡化社会,突出情感,这是中国艺术的情感性精神,它着重表现中国人深厚的情感与人格感染力,表现真实的灵魂。
艺术生命的核心是灵魂的真实。
没有真实的灵魂,就不可能有真实的艺术。
就像中国的山水画,重在写意,画家即便站在同一角度也无法描摹出同样的意境,境由心生,心中的意境不同,笔下就有不同的景色。
电影中还有一些颇具原始状态的情节,比如“颠轿”——一群赤膊光头的汉子抬着个漂亮的小媳妇,再加上几段俏皮粗野的歌词儿,颠傻了所有观众;
“酿酒”——完整地虚构了一套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