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失格Word下载.docx
《人间失格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间失格Word下载.docx(4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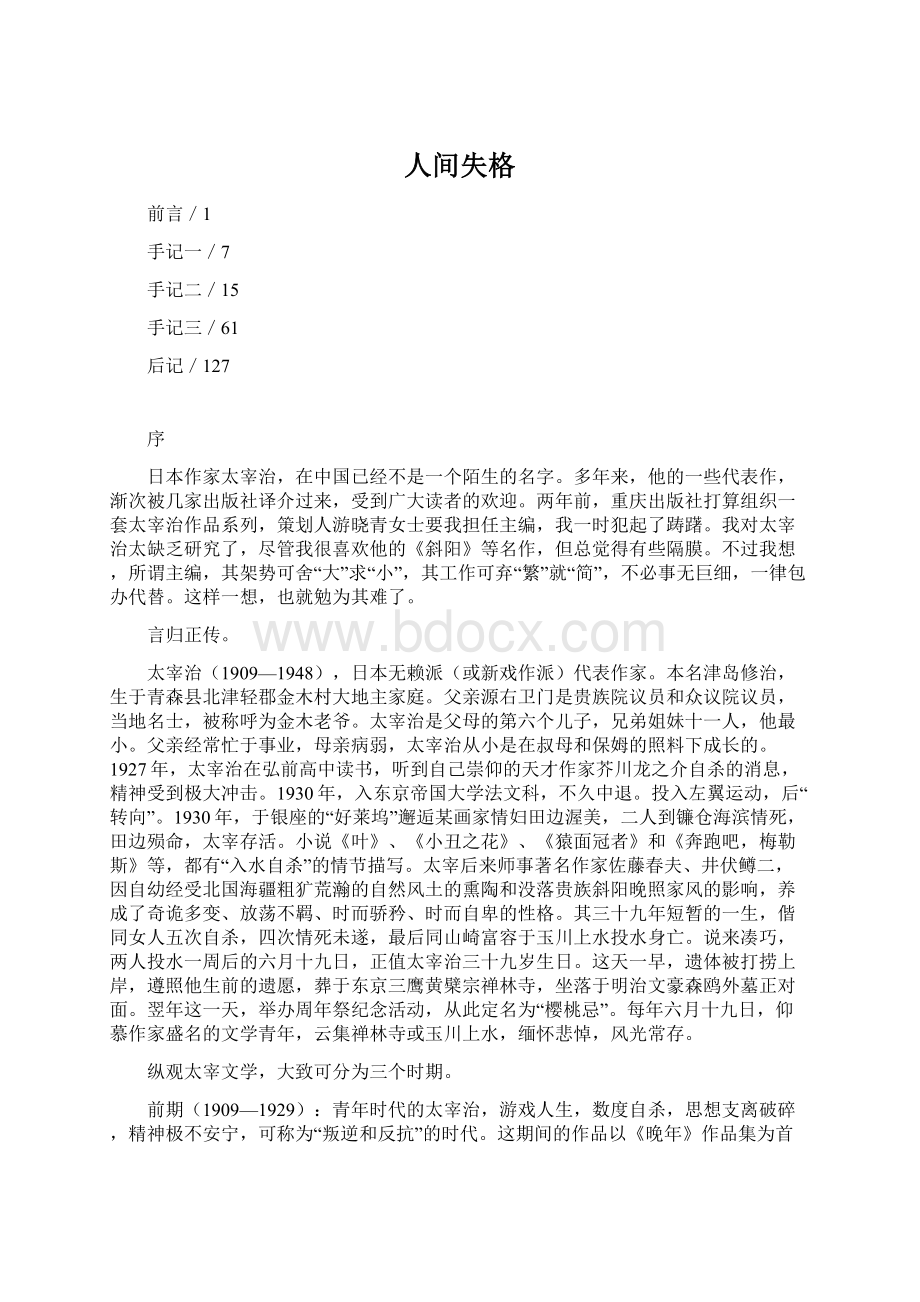
太宰同石原(津岛)美智子结婚后,在亲友的安抚下,不安的灵魂渐趋稳定,立志做一名“市井的小说家”。
这个时期的作品,个性鲜明,笔墨多彩,文字细腻,佳作倍出。
举其要者有《富岳百景》、《奔跑吧,梅勒斯》、《女生徒》、《故乡》和《潘多拉的盒子》等。
这一系列作品内容多触及严肃的社会问题,格调明朗而不沉郁,行文轻捷而不浮华,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后期(1946—1948),战后三年,战争的创伤再度引起作家精神的不安定,这是太宰文学走向成熟和个体毁灭的悲壮时期。
作为作家,三十九岁,正是创作思想渐趋稳固、成就一代文名的大好年代。
不料这颗文坛明星,留下《维庸之妻》、《樱桃》、《斜阳》和《人间失格》等作品后,猝然陨落。
连载中的《Good-bye》,即刻断弦,遂成绝响。
日本太宰文学研究家、中央大学教授渡部芳郎将太宰治誉为“心灵的王者”,他认为太宰治作为一名作家的基本人格类型,属于“赠你一朵蒲公英的”心中怀有幸福感的人(《叶樱与魔笛》),向过路人(读者)献上一支美妙音曲的街头音乐家(《鸥》、《想起善藏》)。
太宰文学所具有的善性,来自作家“原罪的自觉”,所谓“罪多者,其爱亦深”。
太宰治曾经对弟子们谈及自己的文学理想,他说:
芭蕉(江户前期俳谐作家——笔者),闲寂、简素,喜爱纤细的余情,最后达到“轻妙”之境地。
新的艺术进取的方向即为轻妙。
好比剑道,气力顿时集中于手腕。
那种感觉啊,苦恼下沉,心地澄明。
……若论音乐,好似莫扎特。
(桂英澄《箱根的太宰治》)
太宰治轻妙而明朗的作品中,从文学形象的角度分析,同时又脱不出前期难解、后期颓废的反俗的情调。
小说《维庸之妻》,暗喻“放荡男人的妻子”。
其依托对象为15世纪法国抒情诗人弗朗索瓦·
维庸(Franç
oisVillon1431—约1463)。
此人在巴黎大学求学期间,频频交往妓女、流氓,1455年在一次社会骚乱中杀死司祭,逃往巴黎郊外,参加盗窃集团,获罪入狱,后获赦。
1462年,因再次犯强盗杀人罪,被宣告施以绞刑,后减为10年期流放,不久便杳无消息。
200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三十三届世界电影节上,由根岸吉太郎导演、松高子和浅野忠信主演的同名电影《维庸之妻》荣获最佳导演奖。
《斜阳》中的女主人公和子的原型,本名太田静子,1941年在朋友家中偶遇太宰治,一见钟情。
此后两人常常书信来往,坠入爱河,不得自拔。
1944年,太宰到小田原车站同静子相会,并一起探望住院的静子的母亲,然后前往静子住处下曾我。
太宰再次到下曾我会见静子是战后的1947年,为了创作《斜阳》而去向静子借阅日记。
太宰治绝命前的一两年间,原配美知子和情妇静子同时怀妊,第二年分别生下女儿,这就是后来的著名女作家津岛佑子和太田治子。
本系列选入的五部作品,均属中短篇小说。
太宰治这些为读者耳熟能详的名作,再次有机会付梓出版,能否不辜负读者们的期待,老实说我心中没底。
一来毕竟是名家名作,且不乏名译,珠玉在前,难以企及;
二来译者多属新手,锋芒初试,经验不足,译文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
望读者多加批评,以便再版时改进。
走笔至此,忽然记起今日是所谓“宪法纪念日”,电视里正在播送东京街头为反对“改恶”宪法,政界和民间纷纷举行各种类型的保卫和平宪法的活动。
正当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改宪”和“护宪”斗争逐渐走向白热化时期,再度阅读太宰文学,重温战争给广大民众造成的苦难和精神创伤,对当代读者来说,或许更具深义。
陈德文
2013年5月3日杜鹃花开
记于爱知县春日井迓光亭
前
言
我看过三张那个男人的照片。
一张据推测是那个男人十岁前后——或许应该称作幼年时代的照片。
他穿着粗条纹的裙裤,站在庭园的池畔,被一大堆女人包围着(想来应该是这孩子的姐姐、妹妹和堂姐妹们吧)。
他的头向左歪成三十度,笑得很丑。
丑?
迟钝的人(也就是那些对美丑漠不关心之人)见了也许会毫无表情地敷衍着说上一句:
“好可爱的孩子啊。
”这话听上去也并非全是恭维,因为那孩子的笑容上也并不是丝毫看不到通常所讲的“可爱”的影子。
不过,但凡对美丑有些许经验之人,只消看一眼就会极为不快地小声抱怨:
“什么啊,真是个讨厌的小孩。
”说不定还会像扒拉毛毛虫一样,将那张照片扔掉。
的确,越看这孩子的笑脸,越会不知不觉地涌起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本来嘛,那根本不是笑容。
那孩子根本没有笑。
证据就是,他的双拳紧握。
人是不会死死地握着拳头发笑的。
是猴子,是猴子的笑脸。
他不过是在脸上挤满了难看的皱纹罢了,让人看了不禁想给他起个“褶子弟”的诨名。
这张照片上的表情就是如此奇妙,看上去脏兮兮的,让人不由得怒气冲天。
我以前从未见过有如此匪夷所思的表情的孩子。
第二张照片上的脸变化惊人。
一副学生打扮。
虽分辨不出是高中时代的照片,还是大学时代的照片,但总归是个美貌异常的翩翩学子。
但不可思议的是,看上去同样不像是活生生的人。
他身穿学生服,盘腿坐在藤椅上笑着,白色的手绢从胸口的口袋里露出来。
这张笑脸不再是皱巴巴的猴子的笑容,而是巧妙的微笑。
但总有什么地方跟人的笑容不大一样。
该怎么说呢,血液的沉重也好、生命的历练也罢,反正就是没有这种充实之感。
那笑容像羽毛一样轻飘飘的,但又不是鸟,仿佛是一张白纸在笑。
也就是说,给人一种彻头彻尾的人造之感。
轻薄二字不足概括,说是轻佻也不过分。
当然,时髦二字是不准确的。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俊美学生甚至让人感到恐怖。
我以前一次也没见到过此种不可思议的美貌青年。
另一张照片最奇怪了。
似乎根本判断不出年龄。
头上夹杂着些许白发的他待在一间极其肮脏的小屋的角落里,两手烤着小小的火盆,没有笑。
什么表情也没有。
那照片看上去就像他一边坐着烤火,一边自然而然地死了一般。
散发出一种不祥的气息。
奇怪之处不止如此。
因为面部照得很大,所以我能仔细看清他的脸部构造。
平凡的额头、额头上平凡的皱纹、平凡的眉毛、平凡的眼睛,鼻子、嘴巴和下巴均是如此。
啊,这张脸不仅没有表情,甚至给人留不下半点印象。
简直就是没有特征。
可以这么说,我看了这张照片,只要闭上眼,就已经忘了他的长相。
倒是能想起来房间的墙壁和那个小火盆,但房间的主人公的脸早就云消雾散,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
这是一张无法入画的脸。
甚至画不成一幅漫画。
即便睁开眼,也体味不到一丝“啊,原来长这样啊,想起来了”似的喜悦。
说得极端点,就算睁开眼再看见那张照片,也想不起来。
看客反倒越发难受、焦躁,转而背过脸去。
就算“死相”,也好歹有表情,能叫人记住。
但那张照片给人的感觉,就像在人的躯体上安了一个驮马的脑袋。
不知为什么,就是让看着人害怕、不愉快。
同样,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么不可思议的男人的脸。
手记一
我这一生出过不少丑。
我丝毫捉摸不透“人的生活”究竟是怎么一副样子。
我出生在东北的乡下人家,第一次见到火车,已经是成年之后了。
我登上站台的天桥,又从上面走下去,竟全然没有意识到那是为了从顶上穿过铁轨而修建的,只以为它是一个复杂而愉悦的、光图时髦的设备,是用来把车站改成外国的游乐园的。
而且,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我始终都这么认为。
在天桥上上下下,这对我来说更像一种洋气的游戏,是铁路服务中我最为中意的一项。
后来,当我发现那玩意儿不过是用来让旅客穿越铁道线路的实用楼梯时兴致顿减。
小时候,我在图画书上看见地铁,同样没觉得那是为了实际需要而考虑出的方法,反倒一直以为与在地面上乘车相比,在地下乘车是一种特别而有趣的游戏。
我自幼体弱多病,常年卧病在床。
躺在床上,我常常深切地感慨床单、枕套、被套之类是极其无聊的装饰。
直到二十岁左右,我才意外获悉那些都是实用的日常物品。
我顿为人之简朴而心情黯淡,很不是滋味。
我还不知道何谓空腹。
不,这并不是指我生长于衣食住行无忧之家。
才不是这种愚蠢的含义呢。
我只是丝毫没有“饿肚子”的感觉。
换个怪异的说法,就算肚子饿了,我自己也察觉不到。
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放学归来,周围的人总是七嘴八舌地叽叽喳喳个不停:
“肚子饿了吧?
我们也知道那滋味。
从学校回家时肚子会饿得饥肠辘辘。
要不来点甜豆?
蛋糕和面包也有。
”我则拿出天生的拍马屁精神,随口应和:
“肚子饿了。
”然后将十几颗甜豆塞进嘴里。
但空腹感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可一点也不知道。
当然,我饭量很大,可几乎没因为肚子饿而吃过东西。
我吃稀罕之物,吃高级的东西。
另外,如果去了别的地方,我一般会强迫自己吃掉端上来的东西。
对孩童时代的自己来说,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自己家的吃饭时间了。
在我乡下的家里,一开饭,全家十口人就会面对面坐成两列,前面分别摆放着各自的餐盘。
身为老小,我自然坐在最后面。
餐厅幽暗,十几口人挤在那里默默无言地吃午饭的情景总会让我不寒而栗。
另外,我家保守老派,菜肯定是有的,但不能指望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或奢侈料理,这越发让我害怕吃饭的时间了。
我坐在那个昏暗房间的末席,冻得哆哆嗦嗦地把饭一点一点塞进嘴里,心想:
人为什么一天要吃三顿饭呢?
放眼望去,大家都在表情肃穆地吃饭,仿佛某种仪式一般。
全家人一天三次,准时坐在幽暗的房间里,按顺序摆上饭菜,即便不情愿也得无言地咬牙咀嚼。
在我看来,就像低着头向在家中四处蠢动的精灵们祈祷一般。
不吃饭就会死。
这句话在我听来,不过是一句令人生厌的威胁。
然而这种迷信(至今,我仍旧觉得这是迷信),总是让我感到不安和恐怖。
人要是不吃饭就会死,因此必须工作、吃饭。
我觉得这句话晦涩难解,再没有比它更具强迫震撼的句子了。
总而言之,可以说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何为“人的营生”。
我有一种自己的幸福观念和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念全然相反的不安,我被这不安搅得辗转反侧、呻吟不断、夜不能寐,有时甚至差点发疯。
自己究竟是否幸福?
小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是个幸福的人。
我倒觉得自己正经历着地狱般的煎熬,那些说我幸福的人,反而安乐得多。
我还有过这种想法:
自己身上有十个灾难,哪怕其中一个要是降临到邻居头上的话,都足以取走邻居的性命。
说到底,我还是不懂。
我想象不出邻居的痛苦的性质和程度。
那或许是某种实用的痛苦,只要吃上饭就能解决。
然而,这也是最为强烈的痛苦,说不定能把我那十个灾难吹得一扫而光。
我说不准。
不过,要是不自杀、不发疯、不绝望、不屈服地谈论政党,继续与生活做斗争的话,未免也太痛苦了吧?
或当个利己主义者,自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从未怀疑过自己。
若能如此,反倒轻松了。
人,说到底都是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做个打一百分的完美的人。
我说不准……能夜里酣睡,清早神清气爽吗?
做了什么梦,边走边想些什么呢?
钱?
不会吧,不会只有这个吧。
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我仿佛在哪儿听过这个说法。
但从没听说过人是为了钱而活的。
不,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我不敢保证……想来想去,我越发混沌了,一种世上独我一人疯癫的不安和恐惧席卷全身。
我和邻居几乎从不说话。
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
这时,我想到一个词,滑稽。
这是我对人最后的求爱。
一方面,我对人极度恐惧,另一方面,我又始终无法对人断念。
最后,我终于凭着滑稽这一条线与人扯上了关系。
表面上,我强颜作笑;
内心里,却怀着某种也许能够撞大运的千钧一发的紧张感——为了讨好他人,我总是挤出一身黏汗。
从小到大,自己的家人究竟如何痛苦,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事苟活于世的,我丝毫想不明白。
不过,我因为忍受不了这种可怕的尴尬,早就成了个滑稽高手。
可以这么说,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就成了个从不说一句真心话的孩子。
看一看那时跟家人一起拍的照片就能发现,其他人都一副认真的表情,只有我自己,从来都是歪着脸奇怪地笑着。
这也是我幼小而悲哀的滑稽的一种。
另外,不管亲戚们如何说我,我也从不反驳。
别人一句无心的玩笑,有时对我是晴天霹雳,让我发狂。
可我不仅不会还嘴,反倒还觉得那玩笑话一定是万世一系的人间“真理”。
自己正是因为缺乏践行真理的力量,才没法与人一起生活。
我以前总是钻牛角尖地这么认为。
因此,我不会跟人争吵,也不会替自己辩解。
要是被旁人恶言相加,我总觉得是自己误会了,于是默默承受着外来的攻击,内心却感到近乎发狂的恐惧。
手记二
离海岸很近的地方——近得都能拍到浪花似的,耸立着二十多棵枝繁叶茂的山樱,树皮黑黝黝的。
新学年一开始,山樱就会萌生出黏糊糊的褐色嫩叶。
与此同时,在蓝色的大海背景下,绚烂的花朵连成一片。
凋落之际,数不尽的花瓣像落雪似的纷纷坠入海中,三五成群地漂浮在海面上,在海浪的冲击下重新被翻卷到海边。
这片种满樱树的沙滩其实是东北某中学的校园,我虽然没怎么用心复习,却也顺利地考进了那所学校。
对了,那所中学的制帽上的徽章,还有制服的纽扣上都有抽象的樱花图案。
在那所中学的附近,住着我们家的一户远亲。
也是因为这层原因,父亲才为我选择了这所海边的种着樱花的中学。
我从此寄养到了那个远亲的家里,反正离学校很近,每天都是听见晨会的钟声响过之后,才连飞带跑地赶到学校。
反正,我是个不怎么勤快的懒学生。
但我还是靠着逗乐的本事,渐渐地成了班上的人气王。
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背井离乡。
但对我来说,这处所谓的“他乡”待着远比自己出生的故乡要轻松舒服得多。
可以这么解释,那时我已经熟练掌握了逗乐的精髓和妙义,哗众取宠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吃苦受累了。
一般来说,在亲人和外人、故乡和他乡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演技的难易之分吧。
这对于无论什么样的天才,哪怕是神之子耶稣来说,都是一定存在的。
对演员来说,最难施展演技的地方,其实是故乡的剧场,尤其是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围坐一堂的时候,再有名的演员,想必也无从披露自己的高超演技吧。
而我,确是在家人面前一路表演过来的,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对我这种游历江湖的老狐狸来说,根本不可能发生演砸了的情况。
我那天生的“人间恐怖”仍旧剧烈地在心底蠕动,不增不减。
但我的演技却在着实地提高。
教室里,我总是让同学们哈哈大笑。
就连老师都一边感叹似的说“我们班要是没有大庭同学,绝对是个模范班”,一边用手掩着嘴窃笑。
就连那位总是扯着嗓子叫唤、声音如焦雷炸响的将校,我也能轻易地让他喷笑出来。
就在我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下总算能隐藏起自己的真实面目之时,没想到被人从背后捅了一下。
那个从背后捅我的男生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在班上体格最为瘦弱,脸色发青,穿着一件袖子比圣德太子的袖子还要长的上衣——想来应该是他哥哥或父亲的旧衣服吧,各科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军事训练或体操时间总是站在一旁参观,说白了就像个白痴。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对这种学生还需要警戒。
一天,做体操的时候,那位同学(他的姓我记不住了,名字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竹一)照旧不用参加。
他站在一旁看我们练习翻单杠。
我硬是故意装得一脸正经,盯着单杠,“啊”的大叫一声,像跳远似的往前方飞去,最后“咚”的一声在沙地上摔了个屁股蹲。
这都是我有预谋的失败。
大家果然一阵哄笑,我也一边苦笑着一边起身拍打裤子上的沙子。
这时,竹一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他捅了捅我的后背,声音低沉地小声说道:
“招数,招数。
”
我听了大为震撼。
我没想到的是,故意搞砸的计划居然被这个白痴竹一看穿了。
我仿佛一下子在眼前看见世界瞬时在地狱之火的包围下熊熊燃烧。
我险些发疯,拼命抑制住了自己想要“哇”的大吼一声的情绪。
打那以后,不安和恐怖日夜与我相伴。
从表面上看,我依旧靠着凄惨的逗乐取悦大家。
但冷不丁也会沉重而痛苦地长叹一口气,害怕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会被竹一从头到尾地识破。
一想到他没准儿会告诉别人,闹得满城风雨,我的额头上就会布满密密麻麻的汗珠,用疯子一般奇怪的眼神,鬼鬼祟祟地打量四周。
如果可能,我真想早、中、晚,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不弃地跟在竹一身旁监视他,以保证他不泄露半点秘密。
我甚至还幻想找机会跟他做独一无二的好朋友,用尽全力告诉他,我那些逗人一乐的所作所为,都不是故意为之,而是真心的。
如果这些都收效甚微的话,我甚至想到只能祈祷他死了。
不过,我倒没有杀他的打算。
从出生到现在,我虽说极度渴望被别人杀死,但从没有想过要杀死别人。
对那些我恐惧的对象,我反倒只想过给他们幸福。
为了让他乖乖就范,我三五不时地像伪基督徒一样满脸堆着温柔的媚笑,脑袋左倾三十度,轻轻抱住他那瘦弱的双肩,用肉麻的甜言蜜语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做客。
而他总是一副茫然若失的眼神,沉默不语。
好像是初夏的一天吧,放学后,阵雨白花花地下了起来,同学们都在发愁没法回家。
我因为住得近,所以满不在乎地就要飞奔出门。
忽然,我发现竹一像霜打了似的站在鞋柜边上。
“走吧,我借伞给你。
”说着,我拉起还没缓过神来的竹一的手,冒着大雨跑回了家。
我让姑姑把两人的上衣晾干,并成功地把竹一邀请到了自己位于二楼的房间。
亲戚家只有三口人。
姑姑五十多岁了。
大女儿三十多,戴着眼镜,个子很高,看上去病怏怏的(她以前嫁过人,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回了娘家。
我学着其他人,也叫她大姐)。
小女儿唤作阿节,刚刚从女子学校毕业,跟大姐长得一点儿也不像,个头低,圆脸庞。
一楼开店,兼卖些文房用具和体育用品。
主要收入,来源于已故户主留下的五六栋平房的房租。
“耳朵疼。
”竹一站着说道。
“肯定是淋了雨才会疼。
”我说着看了看竹一,他的两只耳朵都害了严重的耳漏,脓液眼看着就要流到耳朵外面了。
“这怎么能行。
肯定疼吧。
”我夸张地摆出吃了一惊的架势,“下这么大的雨,硬是把你拉来,对不住了。
”我像个女人似的贴心地向他道歉后,跑到楼下去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把脑袋枕在我的膝盖上,小心翼翼地给他清理起了耳垢。
竹一到底没有发现这是一出伪善的阴谋,他一边躺在我的膝盖上闭目养神,一边无知地对我拍马屁:
“女人肯定会对你着迷的。
然而,我直到晚年才回想起,竹一当时的这句话简直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的预言,恐怕连他都没有意识到吧。
着迷这个词,下流而随便,给人一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
无论是何种“严肃”的场合,只要这个词露一下脸,忧郁的樊笼眼看着就会崩塌瓦解,心里乱得一团糟。
倘若把“被人着迷的痛苦”换成“被人爱上的不安”这等极富文学色彩的语汇,那忧郁的樊笼也就不会分崩离析了。
想来真是奇妙。
竹一在我为他处理耳漏的脓液时,突然傻乎乎地冒出一句笨拙的赞美:
”那时,我只是羞得面红耳赤,笑着没有作答。
其实,我内心也隐隐觉得他说得不错。
不过,“被人迷上”这种卑贱的语言难免让人生出沾沾自喜的得意之感。
对此,如果诚实地写上“我觉得他说的不错”,就成了向别人展示自己愚蠢的感怀,连相声里常常讥讽的少爷的台词都不如。
所以,我根本不会扬扬自得地想到“他说得不错”。
对我而言,女性要比男性难懂数倍。
我家里的女性比男性多得多,亲戚家也是女孩子居多,再加上那些诱使我犯罪的女佣们,可以这么说,我从小就是在女人堆里泡大的。
不过细细想来,跟女人的交往总是有种如履薄冰的紧张感。
我几乎寻不着门路,常常如坠五里雾中。
一不小心,就会踩了老虎尾巴,败得落花流水。
这种伤害跟男性对我的鞭笞不同,好像内出血似的从内发功,久久不能治愈。
女人有时主动靠过来,却又悄悄离开。
女人在旁人面前鄙视我、对我恶言相加,可没人的时候却紧紧抱住我。
看到女人沉沉入睡,好像死了一般,我总觉得女人是为了入眠才活着的。
总之,我在孩童时代就有了自己对女人的种种观察,明明都是人类,男人却好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物。
奇怪的是,这么一种难以理解且容不得疏忽大意的生物,总是来招惹我。
“被人迷上”或“被人喜欢”等词语用在我身上都不合适,“被人招惹”才能恰当地说明我的实际情况。
比起男人,女人更容易被逗乐。
我像个小丑似的在人前演戏,男人通常不会一直哈哈大笑。
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如果在男人面前得意忘形地演得太假,肯定不会成功,所以总是提醒自己在适当的时候结束。
女人似乎不知道适可而止四个字,总是没完没了地让我逗乐,我则每每顺从地答应她们无休无止的请求,直到自己筋疲力尽为止。
她们可真是能笑啊。
看来,女人对于快乐更贪心。
中学时对我照顾有加的亲戚家的两姐妹,一有空就爬上二楼来我的房间。
每次我都吓得差点蹦起来,一个劲儿地哆哆嗦嗦。
“学习呢?
“不。
”我微笑着合上书,“今天,我们学校那个叫棍棒的地理老师……”从嘴里畅通无阻地说出来的,又是无心的玩笑。
“小叶,你戴上眼镜瞧瞧。
一天晚上,妹妹阿节跟大姐一起来我的房间玩儿,纠缠不停地让我逗笑,最后竟冒出这么一句。
“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快戴上试试。
大姐,把你的眼镜借给他。
她总是一副粗俗无礼的命令口气。
我这个小丑顺从地戴上了大姐的眼镜。
见状,姐妹俩捧腹大笑。
“像极了,简直跟劳埃德一模一样。
当时,外国有个名叫哈罗德·
劳埃德的电影喜剧演员,在日本很受欢迎。
我站起来举起一只手说道:
“诸位,这次,承蒙日本各位影迷的……”这短暂的演讲惹得两人笑得前仰后合。
打那以后,只要劳埃德的电影在当地的剧场上映,我都会去看,还私下里细细研究了他的表情。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正一边躺着一边看书,大姐像小鸟一样嗖地破门而入,扑倒在我的被子上哭哭啼啼地说道:
“小叶,你肯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对吧。
肯定会的。
我们不如一起离家出走吧。
帮帮我,帮帮我。
”她语速飞快地说罢这令人目瞪口呆的想法,又哭了起来。
对我来说,我并不是第一次看见女人在我面前摆出这副态度。
所以我并没有对大姐过激的言语吃惊,反而觉得她的说辞陈腐而空洞,甚至有些扫兴。
我一下子从被子里钻出来,剥起了桌上放的柿子,还把其中一块塞到了大姐手上。
大姐一边抽抽搭搭地吃着柿子,一边说道: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书给我看看?
我从书架上为她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柿子。
”大姐娇羞地笑着离开了我的房间。
不仅是大姐,我每当思索女人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活着的时候,就觉得比琢磨蚯蚓的心思还要麻烦琐碎,有时还会后背发凉。
不过,我至少凭着幼年的经验知道,碰到女人突然哭起来,只要让她吃些发甜的东西,她就会马上破涕为笑。
妹妹节子常常带着朋友闯入我的房间,我也总是照例让每个人都笑得开心。
朋友回家后,节子却总会讲她们的坏话。
她的口头禅是:
那人可是不良少女,你要小心。
我心想,这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