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教学辅导一Word格式.docx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教学辅导一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教学辅导一Word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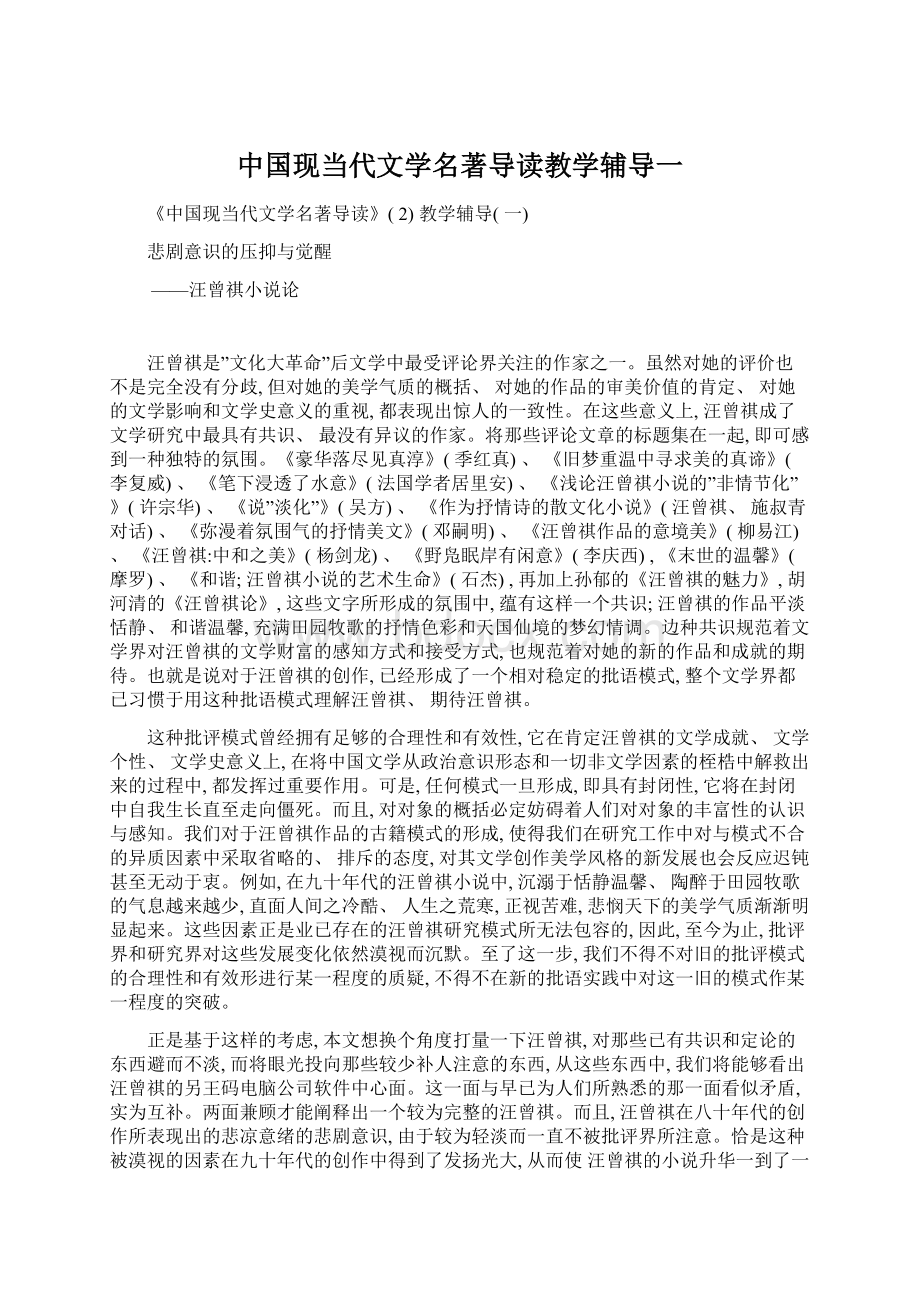
汪曾祺的作品平淡恬静、和谐温馨,充满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和天国仙境的梦幻情调。
边种共识规范着文学界对汪曾祺的文学财富的感知方式和接受方式,也规范着对她的新的作品和成就的期待。
也就是说对于汪曾祺的创作,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批语模式,整个文学界都已习惯于用这种批语模式理解汪曾祺、期待汪曾祺。
这种批评模式曾经拥有足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它在肯定汪曾祺的文学成就、文学个性、文学史意义上,在将中国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和一切非文学因素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可是,任何模式一旦形成,即具有封闭性,它将在封闭中自我生长直至走向僵死。
而且,对对象的概括必定妨碍着人们对对象的丰富性的认识与感知。
我们对于汪曾祺作品的古籍模式的形成,使得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对与模式不合的异质因素中采取省略的、排斥的态度,对其文学创作美学风格的新发展也会反应迟钝甚至无动于衷。
例如,在九十年代的汪曾祺小说中,沉溺于恬静温馨、陶醉于田园牧歌的气息越来越少,直面人间之冷酷、人生之荒寒,正视苦难,悲悯天下的美学气质渐渐明显起来。
这些因素正是业已存在的汪曾祺研究模式所无法包容的,因此,至今为止,批评界和研究界对这些发展变化依然漠视而沉默。
至了这一步,我们不得不对旧的批评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形进行某一程度的质疑,不得不在新的批语实践中对这一旧的模式作某一程度的突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想换个角度打量一下汪曾祺,对那些已有共识和定论的东西避而不淡,而将眼光投向那些较少补人注意的东西,从这些东西中,我们将能够看出汪曾祺的另王码电脑公司软件中心面。
这一面与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那一面看似矛盾,实为互补。
两面兼顾才能阐释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汪曾祺。
而且,汪曾祺在八十年代的创作所表现出的悲凉意绪的悲剧意识,由于较为轻淡而一直不被批评界所注意。
恰是这种被漠视的因素在九十年代的创作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从而使汪曾祺的小说升华一到了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
缺这方面的考察,就会对汪曾祺的精神高度和文学成就估价不足。
而当我们进入这方面的考察时,既是对汪曾祺美学发展的及时肯定,也是对中国文学素来贫弱稀薄的悲剧精神的强调与呼唤。
平淡中的奇崛与骚动
《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总是坐在鞋匠铺里,悉心观察着满街各色人物。
”她那从眼框上面露出来的眼睛是彬彬有礼,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
”汪曾祺这位高大头,为人为文皆然。
这段文字可说是夫子自道。
惟其不露声色,平淡。
惟其彬彬有礼,温馨。
可是这段话极为重要,它引导我们去关注汪曾祺小说的另一面,那与平淡与温馨不一样的一面,那一面是奇崛,锋利,骚动,挣扎,甚至还有一点作者直抒胸臆的嘲弄与愤恨。
从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而言,汪曾祺的许多小说并不价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片和谐,而潜伏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大多数时候,汪曾祺都以息事宁人之心,化解这些矛盾,以维持她所追求的和谐与平淡。
有时实在控制不住,这些矛盾就会冲突起来,使和谐与平淡受到挑战。
那些与环境不和谐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小人物,而且是安守本分的小人物。
她们不象欧美文学中许多小说人物(如于连、毕巧林、马丁伊登等等)那样,带着强大的自由意志,主动地审视环境、批判环境、征服环境,她们不象鲁迅笔下的觉醒者那样具有伟大的强烈愿望,汪曾祺的小说人物都是卑微而且自甘卑微的人,她们对环境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审视与批判。
她们所追求的无非是平平安安的生存。
然而,就是这退的不能再退的立场,低的不能再低的要求,与她们的环境构成了无法化解的矛盾,她们不得不承受着环境所加给她们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催迫与凌辱。
高大头、朱雪桥(《皮凤三楦房子》)、陶虎臣、王瘦吾(《岁寒三友》)、沈源(《寂寞和温暖》)、高北冥、高雪(《徒》)等等人物,无论是市井平民,还是读书人,都是无野心、无恶欲的善良人。
她们全都勤劳与本行,无取于她人。
她们的愿望也十分平常,无一丝非分之想王瘦吾虽然想发财,其动因不过是让怒儿穿上雨鞋,儿子穿上雨鞋,以让她们跟上学校里的大众水准。
高北冥只不过想保住一个教职,以求集点资金为恩师印一本文集。
沈源不过是希望有权利从事她的农业科学研究,另外为父亲立一块墓碑。
然而她们这么小的愿望也得不到外界的理解与支持。
她们全部都遭到失败。
王瘦吾的生意被更有贪心的人挤垮;
高北溟被恶人解职;
沈源被打成右派分子,连给父亲奔丧的权利也没有;
高大头的房产被剥夺,怎么也要不回来;
高雪想外出求学而不得,最后抑郁而死。
在人物与环境的矛盾中,人物是彻底的被动者、弱小者,环境总是主动地、蛮横地剥夺人物、蹂躏人物。
汪曾祺总是避免把人物逼上绝路。
她的息事宁人之心不但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
但一个作家的现实体验会在进入本文时顽强地自我生长,最终挣脱作家的主观控制而自我生长,最终挣脱作家的主观控制而自我呈现。
高北溟、高雪父女俩双双郁闷而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陈四被乔三太爷痛打,陈小手被联军团长击毙(《故里三陈》),猫在受尽戏弄和凌辱之后、被摔下楼时慘叫不已(《虐猫》),老舍被逼得投入太平湖(《八月骄阳》)等等,都是汪曾祺所不愿表现、却又无从掩藏的奇崛峻急之笔。
人物被环境摧迫致死,冲突可谓大矣。
这些血淋淋的故事,终究是要冲破”人物与她们的社会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神话的。
如果我们细加追索还将发现,除了这些被动地随蹂躏和倾轧的人物之外,汪曾祺小说有时还会出现一些不甘于沉寂与灭绝的人物,她们出自本能地表示着她们的微弱的反抗,使得生活出现一些微弱的骚动。
这些骚动与挣扎让人感觉到她们有血有肉的存在,感觉到她们的抗议与悲叹。
《受戒》里的和尚几乎没有一个严守戒律的。
汪曾祺不但极其欣赏地这样总结道:
”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她实际上在暗示读者蔑视清规、反抗清规。
这些反抗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于许多小说中。
和尚娶妻、方丈养小老婆是一种反抗(《受戒》),仁慧尼姑在土改工作队的压力下依然拒绝还俗,宁愿四方漂泊捍卫自己的信仰是另一种反抗(《仁慧》)。
小王在极度的经济困难中发现老汪的工资比自己的高出许多,她只是意味深长地感慨了一句:
”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为什么你就挣那么多?
”(《七里茶坊》)这是对社会对命运的含蓄的抗议。
在这同一篇小说中,几位过路的车夫在历数了社会上种种弊端后总结说:
”当官的说谎,老百姓遭罪!
”与小王的感慨一样沉重而又无奈。
高大头向报社写信揭露谭凌霄的种种恶行(《皮凤三楦房子》),郭庆春把诅咒臭大兵的话编进了吆喝生意的口诀之中(《晚饭后的故事》),老舍自沉太平湖(《八月骄阳》),凡此种种都是对生命意志的表现与弘扬。
最壮美最有力的反抗当是来自天鹅。
一只天鹅被人们残酷杀害了,另一只整天不鸣不食,最后”从高高的空中摔下来,把自己的胸脯在坚冰上撞碎”(《天鹅之死》)。
我不得不对此表示遗憾:
汪曾祺小说中最有光辉的悲剧形象竟是一只动物而不是人类。
可能汪曾祺内心对人类深深悲悯也深深失望。
好在就审美活动而言,动物形象与人物形象的美学效果是一样的。
在汪曾祺小说中,更广泛更顽强的骚动表现在男女性爱上。
可能因为中国文化中性意识特别强,给人造成的压抑感也特别强,汪曾祺几乎无需选择,自然而然地就用性爱题材表示她反抗戒律与禁忌的愿望。
她的兴趣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性爱--比如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
那些小说人物之因此破戒求爱,乃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诗性向往。
汪曾祺特别迷恋私奔故事。
《受戒》在极力渲染仁渡和尚精美绝伦出神入化的神事表演之后,不无赞赏地写道:
”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
”在《大淖记事》中,一群妇女将老光棍的裤子扒下来挂到树上,有一回她们当着老光棍的面脱光衣服下水洗澡。
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
巧云的母亲就是跟戏班子的一个小生私奔远去的。
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
《护秋》、《尴尬》、《迟开的玫瑰或胡闹》都是写破格的性爱。
另几篇小说比这些更为破格。
《窥浴》是女老师”性”上了她的男学生。
《小孃孃》是小姑姑”性”上了自己的侄子。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同时”性”上了王家父子俩,而她真正喜欢的却是王家的另一兄弟。
在《受戒》中,众所周知,小姑娘偏偏爱上了一个小和尚。
所有这些不同寻常的性或爱,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的最精彩的篇章。
在所有这些性爱小说中,无论是正常的性爱,还是破格的性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真正敢于蔑视戒律率性而为的,全是女性。
的确全是。
那些女人总是能看准时机,及时表示自己的感情,然后又再一次看准时机,突然剥光自己,赤裸裸地面对男方,逼得男方不得不将戒律与禁忌抛到脑后。
《窥浴》、《小孃孃》、《小姨娘》中都有很典型的例证。
更详尽的工、描写能够从另两篇小说中读到。
六十几岁的邱韵龙背着老妻与一位三十几岁的寡妇约会,有一次,”邱韵龙送她回家。
天热,女的拧了一个手巾把儿递给她:
‘你擦擦汗。
我到里屋擦把脸,你少坐一会’。
过了一会,女的撩开门帘出来:
一丝不挂。
”(《迟开的玫瑰或胡闹》)这一举措大大推进了她们关系的发展。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为了给父亲治病,以卖淫的方式与王老板和她的大儿子保持着性爱关系。
可她内心想的是王老板的二儿子王厚堃。
她把王厚堃接到家里来看病,王厚堃开好方子准备离开时,”辜家女儿忽然把门闩住,一把抱住王厚堃,把舌头吐进她的蟕里,解开上衣,把王厚堃的手按在胸前,让她摸她的奶子,含含糊糊地说:
‘你要要我、要要人我,我喜欢你,喜欢你……’”(《辜家豆腐店的女儿》)这些人物都是极为安守本分的人,即使给生活压得奄奄一息也无所抱怨。
惟在性爱上割不断那丝向往与遐想,一旦有机可乘,就无可遏止地表现出内心的追求与骚动。
如果向更深层追索,能够发现,她们是以性反抗的方式,表示着对阴暗死寂的生活的质疑与抗议。
这种质疑与抗议,在汪曾祺小说中不算太少。
从中能够总结出两个特点:
在读书人与非读书人之间,敢于质疑与反抗的总是那些非读书人(例如高大头、小王、少年郭庆春、游行示威的锡匠、挟民女私奔的和尚与戏子等等);
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敢于质疑与反抗的总是女人(这些例子太多)。
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