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坊 姜东霞风和破碎的阳光Word文档格式.docx
《小说坊 姜东霞风和破碎的阳光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小说坊 姜东霞风和破碎的阳光Word文档格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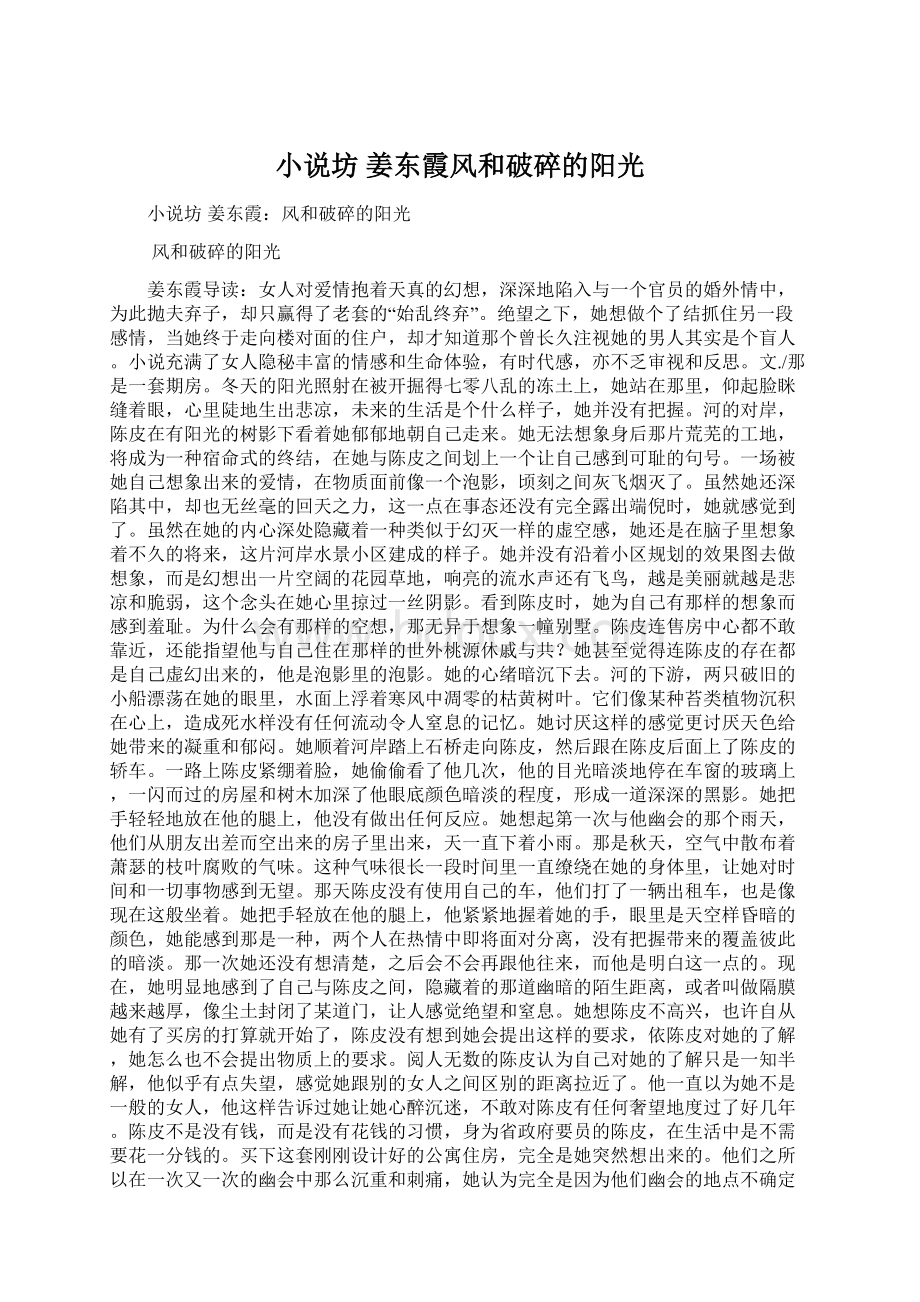
虽然在她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类似于幻灭一样的虚空感,她还是在脑子里想象着不久的将来,这片河岸水景小区建成的样子。
她并没有沿着小区规划的效果图去做想象,而是幻想出一片空阔的花园草地,响亮的流水声还有飞鸟,越是美丽就越是悲凉和脆弱,这个念头在她心里掠过一丝阴影。
看到陈皮时,她为自己有那样的想象而感到羞耻。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空想,那无异于想象一幢别墅。
陈皮连售房中心都不敢靠近,还能指望他与自己住在那样的世外桃源休戚与共?
她甚至觉得连陈皮的存在都是自己虚幻出来的,他是泡影里的泡影。
她的心绪暗沉下去。
河的下游,两只破旧的小船漂荡在她的眼里,水面上浮着寒风中凋零的枯黄树叶。
它们像某种苔类植物沉积在心上,造成死水样没有任何流动令人窒息的记忆。
她讨厌这样的感觉更讨厌天色给她带来的凝重和郁闷。
她顺着河岸踏上石桥走向陈皮,然后跟在陈皮后面上了陈皮的轿车。
一路上陈皮紧绷着脸,她偷偷看了他几次,他的目光暗淡地停在车窗的玻璃上,一闪而过的房屋和树木加深了他眼底颜色暗淡的程度,形成一道深深的黑影。
她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腿上,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她想起第一次与他幽会的那个雨天,他们从朋友出差而空出来的房子里出来,天一直下着小雨。
那是秋天,空气中散布着萧瑟的枝叶腐败的气味。
这种气味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缭绕在她的身体里,让她对时间和一切事物感到无望。
那天陈皮没有使用自己的车,他们打了一辆出租车,也是像现在这般坐着。
她把手轻放在他的腿上,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眼里是天空样昏暗的颜色,她能感到那是一种,两个人在热情中即将面对分离,没有把握带来的覆盖彼此的暗淡。
那一次她还没有想清楚,之后会不会再跟他往来,而他是明白这一点的。
现在,她明显地感到了自己与陈皮之间,隐藏着的那道幽暗的陌生距离,或者叫做隔膜越来越厚,像尘土封闭了某道门,让人感觉绝望和窒息。
她想陈皮不高兴,也许自从她有了买房的打算就开始了,陈皮没有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依陈皮对她的了解,她怎么也不会提出物质上的要求。
阅人无数的陈皮认为自己对她的了解只是一知半解,他似乎有点失望,感觉她跟别的女人之间区别的距离拉近了。
他一直以为她不是一般的女人,他这样告诉过她让她心醉沉迷,不敢对陈皮有任何奢望地度过了好几年。
陈皮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花钱的习惯,身为省政府要员的陈皮,在生活中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
买下这套刚刚设计好的公寓住房,完全是她突然想出来的。
他们之所以在一次又一次的幽会中那么沉重和刺痛,她认为完全是因为他们幽会的地点不确定,游击式的方式所造成的。
有那么几次,他们约好了见面,而地州煤矿透水了,他接到这样的紧急任务要赶赴现场。
出发前的空隙里,他跑到她母亲住的地方去找她,站在那栋破陋的红砖墙隔出来的大门前往她妈妈家里打电话。
放下电话她觉得他又笨又蠢,根本没有必要跑到楼下来丢人现眼地站着。
她责备他说你站在这里不觉丢人,我倒是觉得丢人,电话里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他站在那里,半个身体挡在已经歪斜的铁门柱子后面,郁郁地看着她。
她母亲住在城乡交界的居民区,出了铁门爬一个很大的坡,沿街住满了外来做生意的小商贩,路口就是一家废品回收站。
他拥着她走过废品站时停了下来,他告诉她别的人都往火车站赶,离上火车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他必须要见她一面,这一走不知多久,因为紧接着他又要赶到北京开两会。
他在火车上让她听哐啷哐啷的声音,告诉她就要到了。
他在电话里告诉她死了很多人,停水停电连喝的水都难以保证,他有很多天没有洗脸了。
她握着电话一句话也不说,他说那些工人们漆黑着脸咬一口馒头,馒头都是黑的,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或许这样的情景是因为从他的口里描述出来,才让她感觉到那么浓重的生命感。
她为他对生命有这样的关注而感动,并更加深信不疑地爱他,相信他跟别的官员有本质上的差别,哪怕他并没有给她丝毫的安全感,哪怕他终将离她而去。
于是她突发奇想地以为买套房子固定下来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况且他们有固定下来的理由和能力。
或许就是因为她想固定下来,给陈皮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威胁,或者叫做厌恶。
之前,她疯狂地离了婚,搬到父母家去住着。
陈皮并不想将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他毕竞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岂能背上个破坏百姓家庭的名声。
而她却不能够完全明白这一点,一意孤行把自己碾碎压扁。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她认为一无所有的她买下这套房并不过分。
后来,她单独来过工地几次,在房屋的修建过程中,她长时间地坐在河对岸,看那片荒地和渐渐远离的爱情。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仅仅因为要求买一套房子?
如果这个简单的要求,是造成她与陈皮之间的距离,那么爱情这东西真的是不堪一击到了极点。
她这样一想不免就有了一些悲伤的情绪,眼泪就淌了出来。
她是那样地爱陈皮,她一直天真地认为陈皮跟她的爱是一样的,也可以无怨无悔。
现在陈皮仿佛从她生命的某个角落脱离而出,弄得她破碎不堪。
当然对于陈皮,事情也许并不是这样,她不过是众多肉体中令他有所动的一个。
这个时候的陈皮是不是已将她同更多的肉体置于同一案板,她不得而知。
第二年的夏天,她经历了装修房子的复杂过程之后,住进了她认为属于她和陈皮的房子。
她打开所有门窗,让阳光和空气穿过宽大的房间。
于是她坐下来疯狂地打电话。
陈皮一直不接电话,很久以来他就这样。
那时来电显示还没有普及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她直觉地感到依他的地位和工作性质,不可能没有来电显示。
为此她问过他,他却说没有。
但是她相信是有的,所以有时候,她为了打一个陌生的电话让他防不胜防地接电话,她会跑很远的路到公用电话亭。
她对他突然的冷漠感到愤怒,她不停地打电话,她幼稚到只想让他亲口对她说了结,而不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躲闪,这有多么地卑鄙。
她曾经冲着他在电话里冷静地说,你的人格与你的地位、个头,正好成反比。
他沉默不语,粗壮的气息起起伏伏地在她耳朵里萦绕。
她又有点后悔了,觉得话说得太狠了。
她盘腿坐在地板上,宽大的落地窗外是一片空阔的工地。
她拿着听话筒,听着电流声一次又一次地击响陈皮的电话铃。
她的目光掠过那片空阔的空地,游移在河对岸的一片小树林子里。
实际上她的耳朵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眼前的漆黑使她感到存在的虚无以及她无能为力的滞重。
她把头埋下去,额头几乎贴到了地板上,很久以来她经常用这个姿势来减轻心里的疼痛重压。
当她抬起头来,并将整个身体匍匐在地板上的时候,工地上已经亮起了灯,几个工人在那里拉线打桩,他们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飞扑在玻璃上,让她笼罩在一种久远的空洞感里难以自拔,如同浑身裹挟着湿泥奔走在一个又一个的陷坑里,她对着手机中映出的自己冷冷地笑了一下。
她重新拨打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陈皮就接了。
他说:
“喂,你好!
我在开会。
”她对陈皮这样厚颜无耻的装腔作势的表演感到十分厌恶,她咬着牙冷冷地说:
“我在我们的房子里等你。
”陈皮毫不思量地说:
“好,我尽量吧。
”这话听上去像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无可奈何的勉强交易。
电话挂断之后,她觉出了他话里的冷淡和居高临下的无耻。
她面对着那片工地坐着,她始终没有拉亮室内的电灯。
她知道他不会来,她却会一直等待着。
黑夜里郊外的风格外空旷,一路从河面吹过来,空气中充满了水藻的味道。
这味湿湿的,扑朔迷离般散布在她的身体上。
她就想这会儿,陈皮在干什么。
也许他正坐在柔软的沙发里,与另一个女人传递着身体的快感和疲惫。
她似乎听见了陈皮的身体游荡到某个顶端时,在另一个女人耳边发出的咆哮般的声音。
于是她有了五脏俱碎的感觉。
黑暗的天空好像出现了几颗星星。
她重新伏在地板上,远处的稻田里传来一些蛙鸣,忽明忽暗地掠过她的耳畔,穿过屋子时已变得破碎,如一些黑暗的颜色样弥漫在屋子里,往事也就像这些颜色样飞扑下来,她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滋味,伤痛怨愤抑或是黑暗之黑暗。
陈皮第一次朝她走来的时候,像沙漠里的一头大骆驼扑踏扑踏地掩蔽了她。
在那样一个夜晚,她没有做任何思考,两个人便上了床。
她想起始乱终弃这个词,真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她举起手张开五指在黑暗里,希望时间湮灭自己所犯下的过错。
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自己的家庭和丈夫,她是一个唯爱情论的虚无主义者,她一厢情愿地坚信世间最高贵的情感就是爱情。
那个秋天,街道上到处弥漫着炒板栗的味道,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破了几个洞那样四面透着风,她无法面对自己的丈夫,她感觉整个房间都拥堵得让她窒息慌乱。
她从家里跑出来,走到大街上给陈皮打电话说她的身体四面透风。
陈皮听到她这样说,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也许陈皮从来没有听哪个女人这样表达过,也许跟他上床的女人一个个都目标明确,所以她们不会有破碎感或失落感。
你毁灭了我。
她感觉自己坠落深渊,一切的挣扎都是徒劳的。
陈皮让她领略了经久不退的疲惫和惶恐,陈皮在奔向顶点时像一头驴那样,使她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土崩瓦解似的震荡。
她从来没有听见过男人那样的声音,她想起河东狮子吼这句话,心里激荡出来的温情像是被声音推出来的。
她喜欢这样的感觉并很快从先前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消解和沉浸在那样的声音和悸动里。
她甚至觉得那样的声音,似乎是生命中一种永久的期待,现在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从天而降,让她坠落万劫不复。
在一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她经常坐在树荫下想起那声音,那声音就如潮水样把她彻底地掩盖和消解了。
伴随那声音接踵而来的便是那些组成电话号码的数字,密密麻麻地覆盖下来如水那样漫卷了她的空间和时间。
他们隔三差五地打电话,一打就是几个小时,他在电话里唱歌,唱《恋曲1990》,他的声音浑厚宽大,同样可以让一个人或一个事物陷进去而不能自拔。
她就是那样感觉他的存在以及他给她带来的虚无中的甜蜜感。
他让她读书给他听,她就一字一句地读给他听,间隙时她听到他的呼吸从电话里传来,她就有意停下来静静地感受着,那种匀速进入体内的温度让她觉得天宽地阔。
爱是如此美妙地张开翅翼遮挡天地,而自己身处其中,被裹挟被覆盖最终被抛弃。
他说她读得真好,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跟任何人如此相处过,甚至连他的母亲都没有读过书给他听过。
那时她的生活完全由电话组成,丈夫在家的时候,她就跑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去打。
有时候她还会跑到很远的人民广场去打电话,那里的电话亭立在黑暗里,远离大街,她站靠在那里仰着头可以看到月光从树影间漏下来,天空暗蓝被分割成细碎的斑块,随着云层浮动。
手拿电话她的心里充满一种渺茫的幸福感,如同风划破的一道痕迹。
下雨天,她喜欢坐着公交车去广场的感觉,街面上霓虹灯闪烁,而她的心沉在那些忽明忽暗的闪耀里,将自己变成一个虚幻出来的影子。
这一切都是她虚幻出来的吗?
陈皮早晚都要离开这座对他来说偏远的城市,回到北京去继续做他的官,平步青云,而自己只会如同秋天的一棵植物那样在灰暗中凋敝。
想到这些她不免感到凄惶和悲凉,生命是如此地渺茫如此地不堪。
她想不起是谁说的一句简单又明朗的话,意思是当爱已成往事,要学会放弃。
于是她很快便在地板上睡着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突然惊醒了。
她在黑暗中思索了一阵,然后她翻身去看窗外,工地的灯仍亮着,那片光亮在一团雾气中显出摇摇欲坠的样子。
她拿过电话机按拨了陈皮的电话。
她平静地听着电话接通之后的声音,这个时候的他正睡得昏昏糊糊,不可能去看来电显示屏。
她坚持着听他睡意未消地拿起话筒说:
“喂,你好。
”她说:
“喂。
”她完全能感觉到对方在明白了打电话的人之后,那种短暂停顿中所包藏的厌愤和防不胜防的狼狈。
“我昨晚4点才睡,你再让我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