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应用上的利与弊Word文档格式.docx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应用上的利与弊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应用上的利与弊Word文档格式.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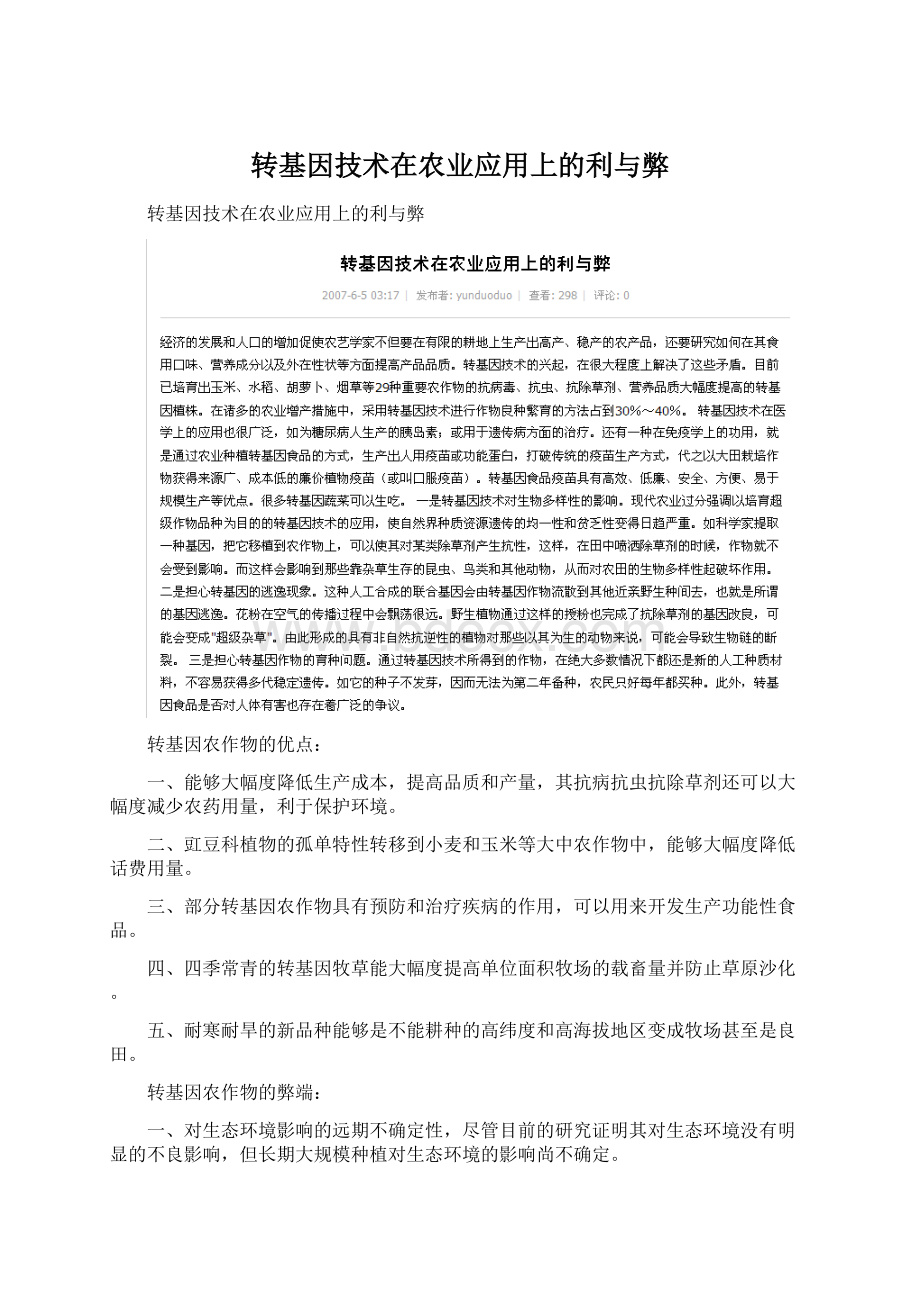
三、已有研究证明对于某个物种过敏的人群由于该作物的基因转移到了另一个物种,该过敏人群也可能会对该新物种产生过敏反应,而该过敏人群可能预先并不清楚从而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
四、医疗上抗生素长期大量使用产生了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变种,使部分抗生素失灵,高抗性物种的大规模推广也可能催生新的有害物种。
二、科学研究“始于机会”和“始于问题”或“始于观察”之区别
区别科学研究“始于机会”、“始于问题”和“始于观察”这三种观点,是重要而且有意义的。
科学始于观察的观点一直被视为支持着科学积累观,是观察与理论二分之基石。
③自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后,由于观察与理论无法截然两分,使得“科学研究始于观察”相当于“科学研究始于理论”,因此,科学始于观察的观点受到很大质疑。
此后,波普尔提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的观点,成为支持证伪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基点之一。
但是,虽然后来证伪主义科学发展观受到质疑,科学始于问题的观点却逃避了检验,学界依然认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
事实上,这可能是由于还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起点观来取代科学始于问题观,而后者能较好地适合于表征主义科学观,所以没有受到本来就属于表征主义的科学哲学的质疑。
其实,不仅表征主义的科学哲学存在问题,因而从表征主义的观点根本无法产生对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观的反驳,而且从论证的角度看,波普尔对于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观的论证也并不充分。
因为他只是基于一个诘难,即把观察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无法回答“究竟要观察什么”的问题,而提出其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观的;
然而,仅仅根据科学要研究问题以及问题可能指导观察什么,是推不出问题一定是科学研究的起点的。
当然,在理论表征主义观点下,只要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成立且具有普适性,观察的基础性地位就不复存在,从而也就无需再对“科学研究始于观察”做辩护了。
况且,从科学作为活动的观点看,构成当下科学研究的直接动因一定是问题吗?
大量的事实证明不是这样。
从科学作为理论表征的逻辑看,我们把科学理论中蕴涵的不相容性称为问题,把理论预期与实验结果之间的冲突也称为问题,然而,这些所谓的问题并不一定会成为在真正科学活动中实践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起点。
首先,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看,理论不是一张天衣无缝的信念之网:
虽然理论之间会产生冲突,但冲突常常被科学家们视为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人类活动从来就不是完美无缺的,不同理论也是不同科学家活动的地方性产物,因此它们的冲突很正常,而不是科学哲学家们所谓不可容忍的事情。
理论不是我们的统一“世界图景”,而是范围广泛的各种表象和操作。
因此,即便实验与理论有冲突,也可能只是与某种理论表象相冲突。
科学家在实践中并没有把这种冲突看成很大的事情。
历史上科学家寻找“以太”的案例表明,虽然科学家为电磁波不断寻找自己相信的传统性“传递媒介”,但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给出“零”的结果后,他们也十分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因此,当不相容性无法解决时,它并非像传统科学哲学所言,是科学家完全不可容忍的事情。
其次,不是所有已经显现的问题都能构成科学研究的问题,更不要说那些潜在的问题,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它们对科学家意味着“无”)。
即便进入科学家研究视野中的问题,如果没有机会、能力和资源的支持,也不一定能够成为科学家当下研究的问题。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这个小孩子提出的问题,只有当天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及其资源仪器达到一定水准时,才构成天文学研究的问题。
换句话说,没有机会,科学家不会意识到问题;
没有机会或者研究条件不具备,即便意识到问题,科学家也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
所以,一概而论地、全称肯定地说科学研究始于问题是不能成立的。
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区分机会和问题对于科学哲学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表征主义科学观看,在被接受的理论中,要确定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及其如何构成,主要应对其中隐含的不相容性进行探查,建构新实验以验证理论的内涵,评估理论领域中还不清楚的东西,这些才是理论性任务,值得去做;
而实践性地确定哪些问题值得动用现有资源去研究,则是不值得去做的。
因为前一种评估是规范性评估,后一种评估是实践性评估,受制于特定的地方性情境,而表征主义科学观只考虑规范性问题。
但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上述区分是错误的。
机会性的研究概念打破了这种区分,因为研究机会的构成与现有的地方性资源和需要的思考是不能分开的。
不存在与产生机会的具体境况区分开来的抽象的研究机会,从而也没有独立于特定情境的问题。
并且,并非所有理论上可识别的问题都构成研究机会。
如果没有人去研究这些问题,不论是因为缺乏资源、旨趣或者合作者,还是因为现在似乎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么它们就不会出现在我们当前的研究中(Rouse,p.88),甚至不会出现在我们关注的视野中。
这种对于研究机会的评估关注,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寻视性关注(circumspectiveconcern)。
在这种寻视性关注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当下在手的资源和知识状态,例如,现有的可资利用的成果是什么,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成果基础上做出多大程度的创新;
现有可资利用的工具和技巧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条件能够构成多大程度的科学进步。
而且,我们的评估依然是实践性的、介入性的。
加之体制要求,我们常从自己的地方性情境以及竞争环境的影响来考虑可能的科学研究进展。
仔细想想我们周围所进行的常规科学研究和突破性研究,我们不都是从自己身处的地方性情境及其所掌握的技能、资源的前提上进行评估从而推进研究的吗?
我们的科学方法论教科书在讨论获取科学问题的原则(即获取的规范性)时,常认为有四项基本原则,即科学性、创新性、需要性和可行性。
这最后一条可行性原则,不就是在讲机会、资源的评估吗?
可见,我们实际上是一边承认要先行对什么构成问题的机会进行评估,即作可行性评估,一边却在大谈科学研究始于问题;
一边把可行性置于基础性地位,一边却又不假思索地认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
我们已经破坏了波普尔论题,但我们自己却浑然不知。
即便退让一步,也可以建立一个弱版本的“科学研究始于机会”观。
当然,就这种机会观而言,即便是在一种综合的或者整合的视野中,也不应并列观察、问题和机会,不是说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研究的起点。
我们的观点是,说科学研究始于机会,意味着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整合着观察和问题对于研究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只有机会真正地反映了实际中的科学研究。
正是基于资源的机会性寻视,使得一些问题进入科学家视野,足以成熟到变为科学家当下可以研究的问题;
机会也使得观察成为有意义的观察。
科学的工作确实要研究问题,而不是研究机会。
但是机会给出问题,机会挑选问题,机会磨砺问题。
同样,机会使得观察成为深入的观察、有意义的观察。
当然,有了机会后,还需要有资源:
“机会+资源”造就研究路径,形成研究的历程。
我们要研究什么,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现有条件即基于资源的机会性寻视决定的。
问题只构成我们可能要研究的空间,而机会和资源制约着这个可能性空间,给出实际的研究进路,决定着实际的研究起点。
观察、问题和机会共同形成一种科学研究的起点性链条,形成实践性的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
(1)通过机会性寻视,我们在评估自己和同行所掌控的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先前的实践寻找合适的研究项目或者问题;
(2)然后通过问题,我们去更加具体地实践,并且观察到新的差异和推进原有的研究;
(3)接着在原有研究推进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实验室中的科学家社会协商的实践,寻找研究的新机会。
在这点上,SSK学者给出了很好的研究支持。
拉图尔和伍尔伽在《实验室生活》中,通过考察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交谈,将交谈归结为四种类型:
(1)利用“已知事实”:
讨论关注的是自多久以来这一现象是已知的;
交流的作用是传播信息,有助于重新发现与当下所关注的问题有关的实践、论文和过去的想法。
(2)寻求正确的方法并且评估其可靠性:
在这种关注中注意到了研究小组获得的投资额度以及避免对赝象(artefacts)进行研究的前景。
(3)针对理论问题的项目评估,也涉及学科未来和实验室方向确定等诸多问题。
(4)针对其他研究者的竞争性评估。
而且,这四种类型的讨论经常从一个主题转移到另一个主题,从一个兴趣中心转移到另一个兴趣中心。
拉图尔等人认为,实验室交谈(即话语实践)所关心的主要有:
已建构事实、这些事实的个体创制者、事实制作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主张,以及最后,实践的主体和允许操作执行的铭写装置,其中绝大部分涉及的是研究者可能掌控的资源和对可能研究机会的寻视(LatourandWoolgar,p.167,Figure4)。
对于“谁(who)”、“什么(what)”和“怎样(how)”的机会性寻视分别导致了“铭写(inscribing)”、“宣称—争论(stating-arguing)”和“写作—发表(writing-publishing)”这些实验室谈话的更为显明的结果。
经过研究,拉图尔等人也认为,研究人员在研究领域中更多地注重研究资源(capital):
他们是从可能掌控的资源和对机会的寻视上开始研究的,并且经常从一种资源转移到另一种资源上,这些资源包括“承认(recognition)”、“获得授予(grant)”、“作为资本的货币(money)投入”、“设备(equipment)投入”、“大量的数据(data)产出”、“论据(arguments)”和“论文(articles)”,以及“正式的宣读(reading)”,从而机会和资源获得了类似解释学的循环(同上,p.201)。
皮克林和塞蒂纳也都认为研究源于机会。
皮克林更早地指出,科学家的“研究战略是根据科学家个人以享有的资源在不同的语境下做出创造性探索的机遇而定的”(Pickering,p.11)。
每一个科学家在选择和处理问题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资源,这既包括物资设备方面的,也包括职业训练和专业技能方面的。
这些资源将决定科学家在面对问题时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总是要使科学家自己的资源被最好的利用。
塞蒂纳比喻地说,科学家就像修补匠,而“修补工是机会主义者。
他们了解自己在特定的地方遇到的重要机会,并且利用这些机会来完成他们的计划。
同时,他们认识到什么是可行的,并且相应地调整和发展他们的计划。
当行动起来时,他们不断从事生产和再生产某种中用的物品,使其成功地符合他们暂时决定的目的。
……谈及研究的机会主义并不是表明科学家在他们的做法中是无系统的、非理性的或以职业为导向的,……机会主义,表示了一种过程而非个体的特性”(塞蒂纳,第65页)。
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做的工作与织补工类似,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源、技能和机遇。
因此,是机会而不是问题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皮克林也指出,这种机会主义虽不能解释所有实践中的问题,但它是针对新传统如何生长而言的。
在皮克林的争论案例研究中,最能体现他的“研究中的机会主义”模式的是1974年11月新发现的J/Ψ粒子及其所引起的对该粒子解释的“色”与“味”之争(王延锋,第102页)。
皮克林认为,是新老两派物理学家所占有的文化资源的差异,决定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