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平台劳动者的就业状况身份认定与权益保障文档格式.docx
《我国平台劳动者的就业状况身份认定与权益保障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国平台劳动者的就业状况身份认定与权益保障文档格式.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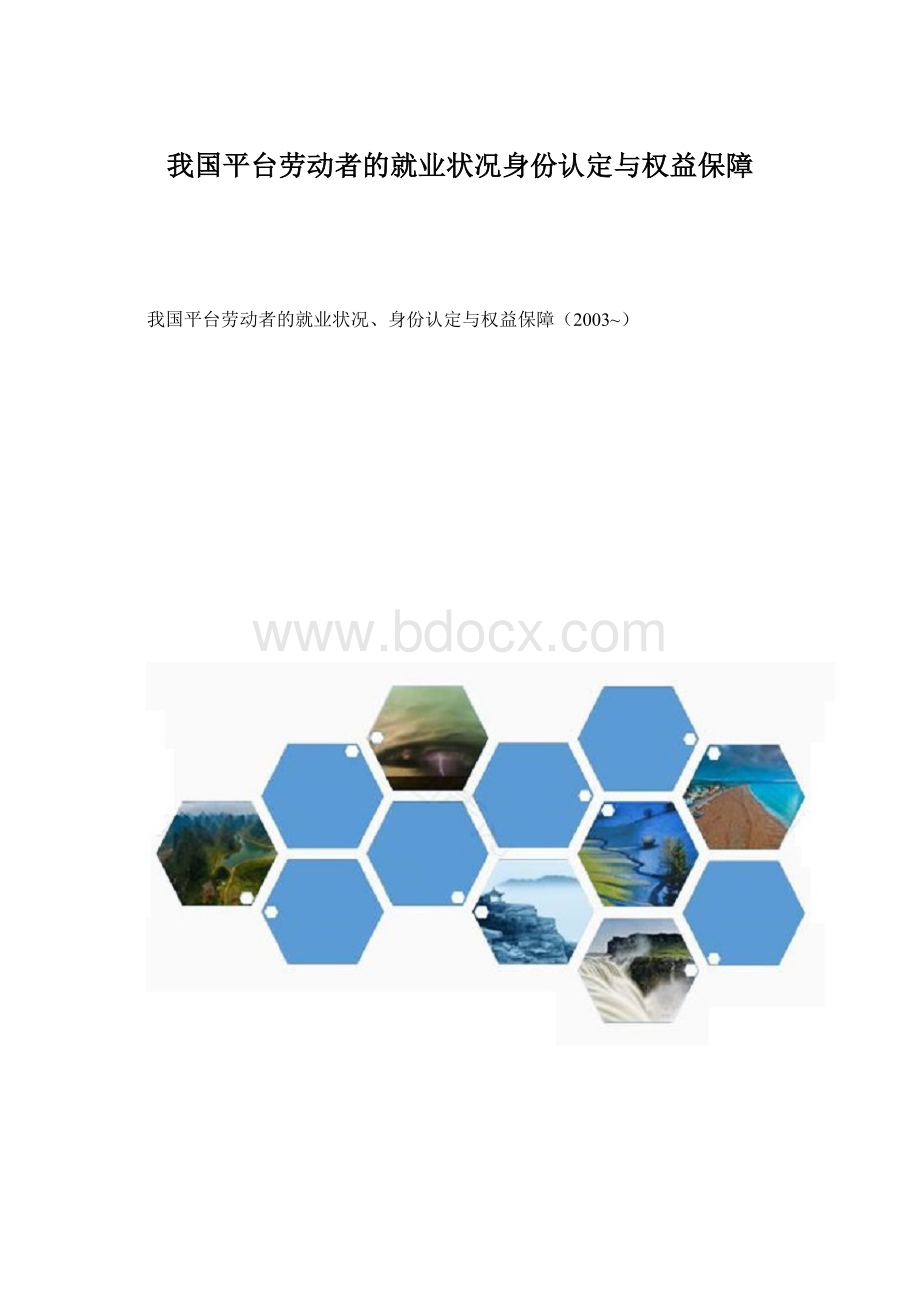
(一)平台企业的发展对就业的促进作用
1.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新及分享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工业化基础上的传统就业方式
共享经济在就业方面的“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更加凸显。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将根据自己的兴趣、技能、时间和资源,以弹性就业者的身份参与到各种共享经济活动中。
《第八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显示,有54%的职工认为基于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分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带来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正在或曾经从事互联网行业工作的劳动者比例高达59.9%,有48.3%的职工明确认为离开互联网无法或只能部分完成现在的工作,正在做、曾经做过互联网工作的劳动者比例达16.6%。
[2]
2.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和匹配能力
信息技术为搭建网络平台成为可能,增加了灵活就业岗位,特别是为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非专业化人才提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提供就业缓冲,缓解了结构性失业,为就业创业者提供了新的实现途径,改变着职工就业生态。
同时,平台也为社会特定群体提供了就业渠道。
滴滴平台的网约车司机中有6.7%是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员,12.0%是退役军人,21%的司机是家里唯一的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为全国百万家庭带来了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2018年,有270万名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其中有77%来自农村,有25%来自贫困县。
[3]网络平台就业等新就业形态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不同利益群体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收入。
(二)平台就业的零工经济特征
2018年,平台就业出现新的趋势。
随着共享经济领域从出行、住宿等生活服务领域向工业制造、农业等生产领域持续扩展,新的平台不断涌现,平台就业所涉及的领域亦不断扩展,对劳动力吸纳的广度和深度也在加强,共享经济平台日益也成为“双创”活动的重要平台,为一批有创业理想的青年提供创业式就业机会。
然而,平台就业更多地显示出零工经济特征。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其2016年发布的报告——《独立工作:
选择、必要性和零工经济》中,将零工经济界定为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主要包括群体工作和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两种形式。
[4]学者黛安娜·
马尔卡希认为,零工经济在人类工作史上其实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兼职工作,以及合同工、顾问零工由来已久。
新鲜的是,零工经济已经扩展到中产阶级、白领的工作中,并逐渐融入高价值、高度透明的科技初创企业的商业模式里。
[5]零工经济的发展是科技进步、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新生代职业群体的职业态度改变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零工经济的兴起和繁荣改变了20世纪工作所具有的正式、持久和全职的特点,使21世纪的工作呈现出无边界、多雇主化和强适应性的特征,即劳动者不再局限于在一家企业或一个组织中工作,而会以项目为导向扩大工作的边界;
劳动者会同时为多个雇主从事多项工作,会按照工作需求改变和提高自身工作能力,以增强自身对工作需求的适应性。
这些零工经济中所呈现出的就业趋势与特征,在平台用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三)平台经济的用工模式及其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1.平台经济的用工模式
按照共享资源的类别,可以把目前共享经济平台分为物品共享、服务共享、金融共享、交往共享、娱乐共享、信息共享等不同类型。
其中,涉及劳动与工作资源的共享平台,主要是服务型共享经济平台,可分为资本密集型平台和劳动密集型平台。
后者从模式上可大致分为“平台自营”“平台他营”“平台混营”三大类。
平台自营即搭建平台,自己唱戏,如以B2C模式为主的网约车平台,以神州专车、首汽约车等为代表,多以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为主要用工形态。
平台他营为搭建平台,他人唱戏,其用工形式是目前争论的焦点问题,如以C2C模式为主的网约车平台,以快递平台、劳务平台为代表,是零工经济的典型用工方式。
其又可进一步区分为“线下网约工”和“线上众包工”两类,前者称为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是客户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搜索,寻找提供运输、家政、维修等服务的人员,工作者多是本地居民;
后者一般称为众包工作,通常由一群能够接入互联网的个体在网络平台上远程完成工作,包括常规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任务,工作者可能来自世界各地。
[6]平台混营则兼具平台自营和他营的特性,在同一平台上可能包含多种用工方式。
作为平台用工争议最大的是“线下网约工”和“线上众包工”这两种用工模式。
在以“线下网约工”为主,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则以“线上众包工”为主。
在网约工模式下,我国滴滴出行平台注册司机有1000多万人,而美国uber公司全球网约车司机数量仅为200万人;
美团注册“骑手”约为270万人,而美国最大外卖配送公司Deliveroo注册“骑手”仅3万人。
在众包模式中,我国虽然也存在猪八戒网、一品威客、任务中国网等众包平台,但其影响力与国外知名众包平台如Upwork、Innoventive,特别是美国Amazon’sMechanicalTurk平台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我国目前在理论、实务和制度设计层面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网约工模式。
网约工和众包工虽然存在一些差别,但作为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的典型用工模式,二者具备如下共同特征。
一是劳动者都拥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性,可以自由决定承接工作、工作时间和上线的权利。
二是劳动者获得报酬的基础不再是工作时间,计酬方式是按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由平台或任务委托方付费。
三是劳动者要接受平台的工作指令,平台对劳动者的工作过程和结果拥有一定的控制权。
有学者认为,在共享经济的用工模式中,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权是同时并存的,因此其与传统雇佣组织用工有巨大的差别。
[7]这种不同于传统用工模式的经济形态,对劳动关系产生相应的影响。
2.平台经济发展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1)平台经济发展加剧了用工的“非正规化”和劳动者的“原子化”。
2015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下文简称“第204号建议书”)中,将“非正规经济”界定为“在法律或实践中——未被正规安排所覆盖或覆盖不足的工人和经济单位的所有经济活动”。
平台经济和用工的迅速兴起,急剧扩展了非正规用工的覆盖面,使其将众多劳动力吸纳在非正规经济和用工之下,并因制度界定与调整滞后而产生诸多“非正规化”所固有的问题。
而且平台虽日益成熟,但基于平台上的经营和任务的交易越来越“小微化”,这就加剧了平台用工的“非正规化”。
而平台用工的“非正规化”则使劳动者趋向“原子化”,这与平台就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相关,可以吸纳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力资本价值的劳动者群体。
劳动者开始不再将自己束缚于一个企业或组织,而是对应多位雇主;
“用人单位”的概念日益模糊,劳动者的身份也难以用一种职业界定,且更愿意以自己的知识、技能甚至是体力作为资源加入有需求和市场的平台,“为自己工作”的理念和实现路径更为盛行和清晰,平台经济的劳动者呈现出“单枪匹马”“单打独斗”的“原子化”职业状态。
(2)平台经济发展强化了灵活用工需求并降低了劳动关系的稳定性。
平台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组织对非全日制用工、兼职劳动等灵活用工的需求,其劳动关系整体灵活化的趋势与传统企业劳动关系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加剧了不同社会群体对平台用工的质疑与争议。
有学者认为,以平台用工为典型的零工经济,实质上是“劳动关系的碎片化和去劳动关系化”[8],在目前劳动关系认定与劳动及社保权益相互绑定的制度前提下,以“去劳动关系化”为本质的灵活用工,实际上剥夺了部分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职业安全感。
同时,平台经济虽方兴未艾,但也不乏一时兴起、更迭频繁,近年共享经济各领域已有数个平台经历资本洗礼和市场优胜劣汰而消失,必然也伴随着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解除、终止,此间变动必然容易引发劳动争议,从而对劳动关系的稳定性产生消极作用和影响。
(3)平台经济发展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提出多重挑战。
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而言,平台用工首先从根本上挑战了劳动法的逻辑起点,即劳动者身份暨用工关系的“从属性”或“控制”判断,这一根本性的模糊点导致以此为原点而展开的劳动权利与社保权益的适用存在制度性障碍。
此外,新型用工模式而产生的新问题,诸如弹性工时、工作地点的非确定性,以及异地履行服务等,对《劳动法》的工时制度、工伤认定以及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均提出了新的挑战,并对实务处理和制度更新提出了迫切需求。
(四)平台劳动者就业的特点
1.平台劳动者出现从普遍兼职转向逐渐专职的趋势
平台经济兴起之时,平台劳动者绝大部分都是兼职人员,此时“共享经济”尚且名实相符。
但随着市场的发展,部分领域的服务提供者出现了专职化趋势,一批基于共享平台的专职司机、房东、“骑手”、主播等开始大量涌现。
特别是在网约车行业,基于新政实施后对市场准入的要求,在准入门槛严格的城市,司机专职化趋势更为明显,这导致对平台劳动者“专职”和“兼职”的比例会基于不同的统计对象和口径而呈现不同的样态。
例如标准排名研究院2016年对北京市网约车司机的调查显示,全职司机占比79.4%,从事兼职网约车运营的司机,均为时间较为自由的职业,其中以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者、企业职工为主。
兼职性质的网约车司机日平均在线时间在4小时以下的比例为56%,在4~8小时的比例为37%。
兼职司机日平均在线时间过长,也是网约车日渐职业化的明显特征之一。
[9]该调查于新政实施前进行,考虑到新政实施后对网约车、司机及平台的准入要求,兼职司机会被进一步挤出市场。
滴滴公司发布的《新经济新就业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滴滴就业报告》)显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全国共有2108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
每天工作不到2小时的司机占比为50.67%,多数司机有本职工作,具有典型的分享经济特性。
在企业事业单位上班的占比为25.34%,其他为“自己开公司”“打零工或散工”“个体工商户”“自雇/自由职业”等,均具有极强的自雇佣属性,可随时以全职身份从事网约车工作。
2.平台劳动者日益以平台收益为主要收入来源,总体不高且缺乏稳定性
《滴滴就业报告》显示,网约车收入占司机家庭月收入的22.3%,而对平台上137万个零就业家庭和单人就业家庭来说,平台收入占其家庭收入的77.1%。
《第八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显示,从事专兼职开网店、网约车、网约快递和外卖、网上自媒体和公众号、网约生活服务等新兴工作群体的平均月收入为3449元,其中专职工为3473元,兼职工为3361元,略高于全国同龄职工平均水平。
北京市总工会对网约工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专职网约工中,月均收入在3000~6000元的占65.8%;
在兼职网约工中,兼职月均收入在1890元以下的占35.32%,在1891~3000元的占34.5%,在3001~4000元的占17.4%,另有超过10%的月收入超过4000元。
表示做网约工后收入比以前收入有所增加的占70.78%。
[10]其中,收入水平发生明显变化的是网约车司机收入,伴随着各大网约车平台补贴力度的降低和收入分成方法的变化,网约车司机月入轻松上万的“神话”早已不复存在。
《2016网络约车司机生存状况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