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发声与劳动者的自我赋权新工人戏剧十年随想录.docx
《底层发声与劳动者的自我赋权新工人戏剧十年随想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底层发声与劳动者的自我赋权新工人戏剧十年随想录.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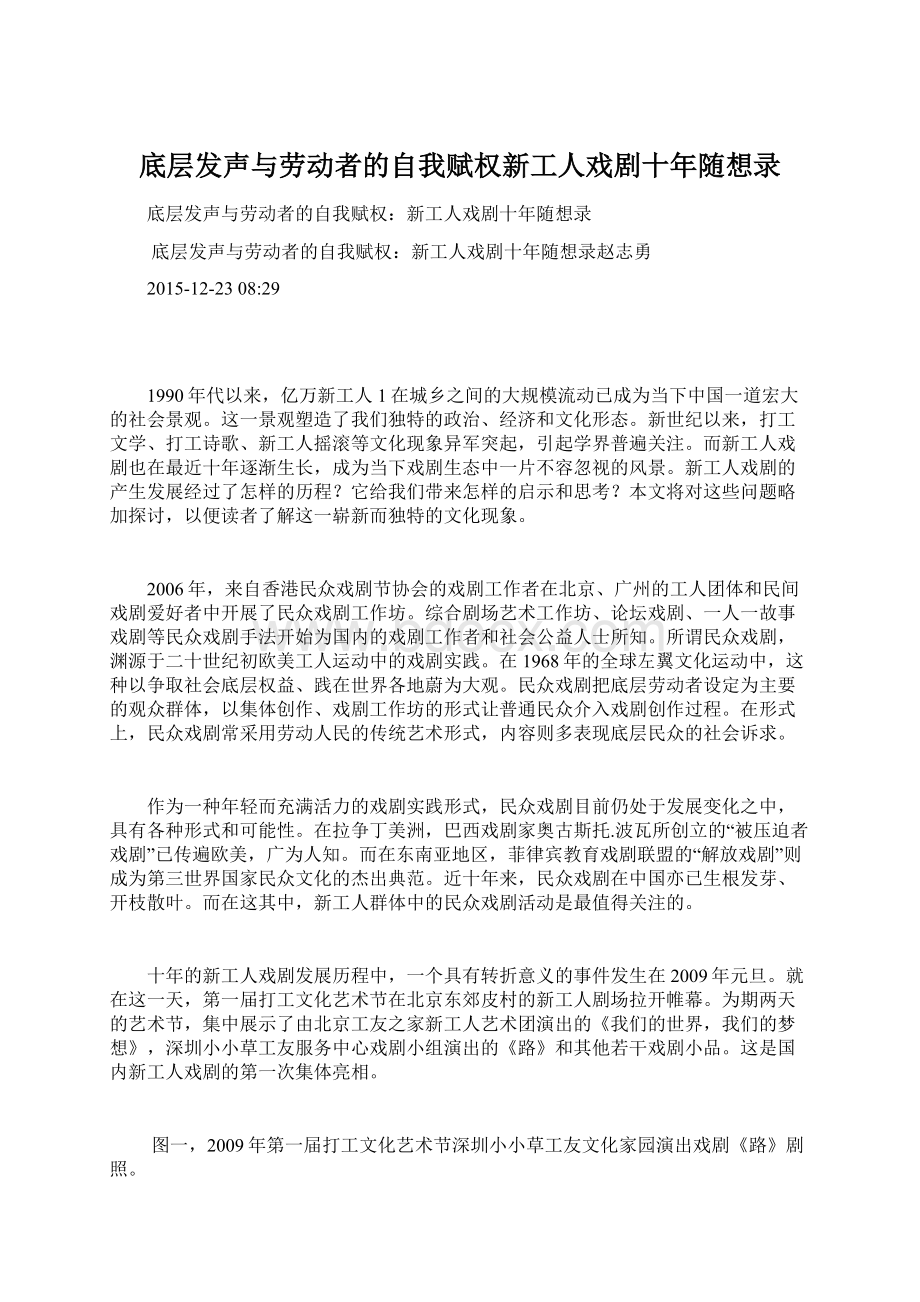
底层发声与劳动者的自我赋权新工人戏剧十年随想录
底层发声与劳动者的自我赋权:
新工人戏剧十年随想录
底层发声与劳动者的自我赋权:
新工人戏剧十年随想录赵志勇
2015-12-2308:
29
1990年代以来,亿万新工人1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已成为当下中国一道宏大的社会景观。
这一景观塑造了我们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
新世纪以来,打工文学、打工诗歌、新工人摇滚等文化现象异军突起,引起学界普遍关注。
而新工人戏剧也在最近十年逐渐生长,成为当下戏剧生态中一片不容忽视的风景。
新工人戏剧的产生发展经过了怎样的历程?
它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和思考?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略加探讨,以便读者了解这一崭新而独特的文化现象。
2006年,来自香港民众戏剧节协会的戏剧工作者在北京、广州的工人团体和民间戏剧爱好者中开展了民众戏剧工作坊。
综合剧场艺术工作坊、论坛戏剧、一人一故事戏剧等民众戏剧手法开始为国内的戏剧工作者和社会公益人士所知。
所谓民众戏剧,渊源于二十世纪初欧美工人运动中的戏剧实践。
在1968年的全球左翼文化运动中,这种以争取社会底层权益、践在世界各地蔚为大观。
民众戏剧把底层劳动者设定为主要的观众群体,以集体创作、戏剧工作坊的形式让普通民众介入戏剧创作过程。
在形式上,民众戏剧常采用劳动人民的传统艺术形式,内容则多表现底层民众的社会诉求。
作为一种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戏剧实践形式,民众戏剧目前仍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具有各种形式和可能性。
在拉争丁美洲,巴西戏剧家奥古斯托.波瓦所创立的“被压迫者戏剧”已传遍欧美,广为人知。
而在东南亚地区,菲律宾教育戏剧联盟的“解放戏剧”则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民众文化的杰出典范。
近十年来,民众戏剧在中国亦已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而在这其中,新工人群体中的民众戏剧活动是最值得关注的。
十年的新工人戏剧发展历程中,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发生在2009年元旦。
就在这一天,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在北京东郊皮村的新工人剧场拉开帷幕。
为期两天的艺术节,集中展示了由北京工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演出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深圳小小草工友服务中心戏剧小组演出的《路》和其他若干戏剧小品。
这是国内新工人戏剧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图一,2009年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深圳小小草工友文化家园演出戏剧《路》剧照。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以打工青年来子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为线索,呈现和思考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大历史,诉说着打工群体在这三十年里经历的坎坷和艰辛。
在剧中我们见证了以致丽玩具厂大火为代表的新工人受难史,聆听了新工人艺术家对现实的困惑和思考,更分享着他们对更公正、美好的未来的展望与期待。
而《路》则用娓娓道来的方式,把发生珠三角工业园区里那些充满迷惘、伤痛的青春故事呈现在观众眼前。
故事中有少年离家的孤独与漂泊,有工伤致残导致的身心痛苦,有迷失在传销和六合彩骗局中的堕落人生,更有普通工友之间相濡以沫的劳动感情,以及为光明的未来而奋斗的信心与勇气。
而在舞台形式上,两部作品把新工人民谣、新工人诗歌等其它门类艺术有机融入舞台。
尽管演出稍显稚嫩粗糙,但其对现实的有力揭示,深沉的主题和真挚的情感,仍有着极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和《路》展示了新工人自发创作所具有的巨大魅力。
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之后,新工人群体中的戏剧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而一年一度的新工人文化艺术节2则为工友们提供了作品发表的平台。
珠三角地区的工友们还在2010年组织了南方工人艺术节,各种充满奇思妙想的戏剧小品成为艺术节最受喜爱的节目。
戏剧开始成为新工人群体凝聚自我意识的有力武器。
2009年至2010年,新工人艺术团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和《家在何处》等作品登上了北京朝阳文化馆“想入非非”非职业戏剧演出季、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上海下河迷仓“秋收季节”演出季的舞台。
新工人戏剧开始正式步入主流戏剧观众的视野。
自2012年开始,一年一度的“打工春晚”开始连续举办,工人戏剧小品成为晚会重头戏。
打工春晚通过网络和电视媒体面向全国播出,新工人的文化艺术有了更大的展示平台。
图二,北京地丁花家政女工戏剧工作坊。
2010年,北京打工妹之家“地丁花”家政女工剧团成立。
这个所有成员皆为普通家政女工的戏剧社,是国内自发组织且持续活动时间最久的新工人文艺小组。
三年的戏剧活动,家政大姐们排演了长剧《我的劳动、尊严与梦想》及若干小品,讲述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酸甜苦辣。
《我的劳动、尊严与梦想》先后登上“想入非非”戏剧演出季和北京青年戏剧节的舞台。
“家政女工演话剧”的话题一时为媒体所争相报导。
2014年,位于北京昌平东沙各庄的木兰社区文化中心社区女工文艺队开始展开戏剧活动。
社区女工们将自己生活中切身相关的议题班演成戏剧和小品。
小品《三十年女工梦》讲述了四代进城打工女性的经历和心声;而戏剧作品《我要上学》则对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求学的困难进行了舞台呈现。
该作品于2014、2015年在多所高校巡回演出,与大学生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发挥了民众戏剧作为社会公共论坛的作用。
以上所述,是十年来作者所见证和亲历的新工人戏剧发展历程。
除此之外,还有若干新工人的戏剧小组在大江南北的工业园区、流动人口社区活动着。
这些戏剧活动丰富了新工人群体的文化生活,让主流大众听到了新工人群体的真实声音,也让我们当下的戏剧文化生态变得更加多元和包容。
它们值得戏剧研究者、实践者和爱好者进一步加以关注。
图三,《我的劳动,尊严与梦想》剧照。
图中左边舞蹈者为沈姐。
新工人戏剧十年来的发展,对于我们社会的总体文化建设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其意义首先在于它满足了底层劳动者的文化诉求。
身为新工人戏剧文化实践的见证者,我对此有深切的感受。
在指导“地丁花”家政女工剧社期间,我结识了来自陕西关中地区的沈姐。
关中平原悠久深厚的戏曲传统,造就了沈姐对戏曲艺术的极度热爱。
离家打工多年的沈姐,身边总带着厚厚几大本手抄的戏曲唱词。
闲来无事时,沈姐就会打开随身播放器听上几段乡音。
家乡的戏曲艺术给她带来巨大的心灵抚慰。
说起在外打工的经历,沈姐曾经告诉我,她有段时间在新疆给别人摘棉花。
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沈姐回忆说:
“真的特别累,不过累了我就开始唱秦腔,大声地唱。
唱着唱着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在“地丁花”剧社演出的《我的劳动、尊严与梦想》中,沈姐精心装扮登场,演唱了家乡的眉户剧《梁秋燕》片段。
给观众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实际上,有很多打工的兄弟姐妹和沈姐一样,怀揣着对艺术的本能热爱来到城市。
这些普通劳动者的精神需求理应得到满足。
遗憾的是,当下城市的文化生产日益商品化。
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者由于其购买能力较低,很难进入都市的文化消费空间。
如何满足底层劳动者的精神生活需求,让文化艺术能够为全社会所共享?
在这方面新工人的戏剧实践无疑是有着积极的贡献的。
新工人的戏剧活动往往在新工人聚集的城市流动人口社区中展开,而这些社区恰恰是城市中文化资源最为匮乏之处。
此外,新工人戏剧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新工人群体为对象的文化公益活动,它也为新工人群体中的文化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身艺术才能的平台。
可以说,新工人戏剧在改善社会文化资源分配不公方面做出的贡献是非常显著的。
巴西民众戏剧大师奥古斯托.波瓦一生致力于创造一种为底层劳动者所共享的文化。
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梦想着有一天,在巴西和全世界的每个城市、每个小镇和乡村都能有一个文化中心。
在那里人民可以表达自我,创造自己的艺术,可以在艺术创造中将现实加之转化从而更好地理解它。
倘若那一天能够到来的话,我们的民主也将同时诞生。
”3波瓦这番话耐人寻味。
保障民众享有充分的文化权利,无疑是社会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要实现文化艺术的全民共享,不仅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也有赖于新工人戏剧等民间力量的持续努力。
图四,台北应用剧场中心艺术总监赖淑雅女士(后排左二)与本文作者于2015年1月19日晚在北京昌平东沙各庄木兰社区中心为木兰社区文艺队举办民众戏剧工作坊。
事实上,当底层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时,他们身上所迸发出的尊严和力量足以令其生活焕然一新。
奥古斯托.波瓦在回忆自己的民众戏剧实践时曾讲过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有一次,波瓦长期指导的一个女佣剧团进行了其首次公开正式演出。
演出非常成功,剧场座无虚席,观众们在演出结束时给予了热烈掌声。
当大家兴奋地庆祝成功时,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波瓦,有一位演员正在后台化妆间里哭泣。
波瓦找到这位演员,不安地询问她为何哭泣。
而这位演员坐在镜子前,边哭边说:
“今天是我第一次站在灯光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出自己的想法,谈论自己的感受。
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一个女人。
”“那么你以前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什么呢?
”波瓦问道。
她回答说:
“从前照镜子的时候,我在镜子里看到的只是一个女佣。
”讲述完这个故事之后,波瓦意味深长地说:
“她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
实际上,每个人只要走上舞台,说出自己所想的,讲出自己的感受。
他就会发现真实的自我。
”4
正是这真实的自我,让人敢于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挫折和磨难。
这些年带领女工戏剧小组,我见证了许多打工姐妹因为走上舞台而收获了自信和勇气。
一位腼腆内向的大姐经过地丁花戏剧工作坊半年的历练之后,学会了与雇主谈判,使得雇主之后每次出门时,再也不能把她一个人锁在屋里。
而一位十六岁就出门打工的小伙子,在其工作的机构里是为工友组织文艺演出的积极分子。
在回答我的书面采访时,他洋洋洒洒地讲述了戏剧活动给他个人带来的成长。
写着写着,他自己也忍不住惊叹:
“真不敢我居然能写出这么多!
因为我自上学以来,语文和作文成绩几乎很少及格。
”5我想,所谓弱势群体的文化赋权,不就体现在这一点一滴的成长和改变中么?
图五,排练场里的“地丁花”在绽放美丽。
在当下中国社会,新工人无疑是个相对弱势的群体。
新工人戏剧的主要诉求,就是要对新工人自身的处境进行反思,探索改善其命运和前途的可能性。
新工人群体的文化创造,把“中国新工人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带入了全社会的视野。
如果没有打工诗歌、新工人摇滚、新工人戏剧等新工人文化艺术的持续发力和广泛影响,就不可能引发主流社会对新工人群体的普遍关注。
这些年来我关注和介入新工人戏剧活动,见证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因观看新工人戏剧演出而引发的种种思考与精神碰撞。
这些思考和精神碰撞不仅仅在剧场里发生,更延续到剧场之外的社会生活中,剧场由此承担了社会公共论坛的角色。
在相关的讨论中,最经常听到的问题就是:
这样的演出究竟有什么用?
它能改变我们的社会现实么?
坦率地说,这样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的确,现实生活不可能因为一出戏而发生改变。
然而,在我看来,新工人戏剧的力量,恰恰就在于它让我们一刻也无法丢开这样的追问。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曾说过:
剧场应该是社会生活的延续,人们3走进剧场,就是要带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和疑问,来思考和寻求变革现实的方案。
而在当下中国,戏剧的启蒙和教育功能几乎已被遗忘,人们更倾向于把戏剧看作一种冷月高阁的高雅艺术,或者逃避现实压力的文化消费。
而新工人戏剧却总在提醒我们:
戏剧究竟有什么用?
我们的社会能从其中获得何种益处?
这种迫切而毫不掩饰的现实关怀,正是当下中国戏剧的稀有品质。
新工人戏剧的文化意义,还在于它发出了新工人自己的声音,在舞台上呈现了真实的中国新工人形象。
九十年代以来,新工人的形象在主流艺术作品中已不绝如缕。
从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打工妹》,到新世纪初的舞台剧《新北京人》,直至近年来诸多舞台剧作品如《西京故事》、《操场》、《问苍茫》等,主流影视戏剧中塑造了一批进城农民工的形象。
其中不少角色因其宽忍善良的美好品质而感动了观众,但也确实有一些作品把进城农民工塑造成性格扭曲、心灵阴暗,专事坑蒙拐骗的负面形象。
这样的写法无疑是不自觉地流露了艺术家自身作为“城里人”的某种偏见。
更重要的是,不论主流影视戏剧中的新工人形象被塑造为正面还是负面,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