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公共卫生社会学视野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全球化与公共卫生社会学视野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全球化与公共卫生社会学视野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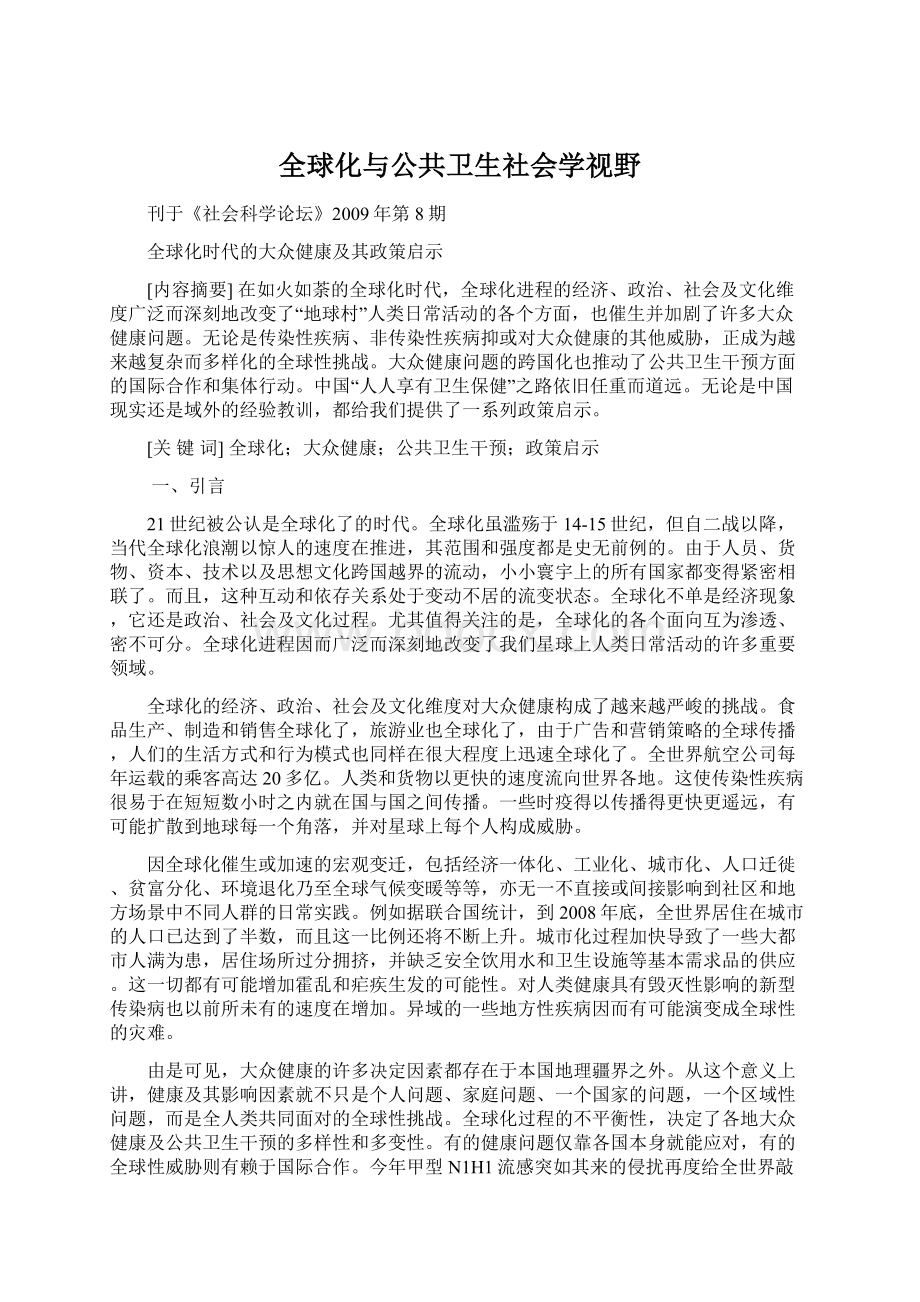
一、引言
21世纪被公认是全球化了的时代。
全球化虽滥殇于14-15世纪,但自二战以降,当代全球化浪潮以惊人的速度在推进,其范围和强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人员、货物、资本、技术以及思想文化跨国越界的流动,小小寰宇上的所有国家都变得紧密相联了。
而且,这种互动和依存关系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变状态。
全球化不单是经济现象,它还是政治、社会及文化过程。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化的各个面向互为渗透、密不可分。
全球化进程因而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星球上人类日常活动的许多重要领域。
全球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维度对大众健康构成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食品生产、制造和销售全球化了,旅游业也全球化了,由于广告和营销策略的全球传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迅速全球化了。
全世界航空公司每年运载的乘客高达20多亿。
人类和货物以更快的速度流向世界各地。
这使传染性疾病很易于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就在国与国之间传播。
一些时疫得以传播得更快更遥远,有可能扩散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并对星球上每个人构成威胁。
因全球化催生或加速的宏观变迁,包括经济一体化、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迁徙、贫富分化、环境退化乃至全球气候变暖等等,亦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区和地方场景中不同人群的日常实践。
例如据联合国统计,到2008年底,全世界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到了半数,而且这一比例还将不断上升。
城市化过程加快导致了一些大都市人满为患,居住场所过分拥挤,并缺乏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等基本需求品的供应。
这一切都有可能增加霍乱和疟疾生发的可能性。
对人类健康具有毁灭性影响的新型传染病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
异域的一些地方性疾病因而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灾难。
由是可见,大众健康的许多决定因素都存在于本国地理疆界之外。
从这个意义上讲,健康及其影响因素就不只是个人问题、家庭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区域性问题,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
全球化过程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各地大众健康及公共卫生干预的多样性和多变性。
有的健康问题仅靠各国本身就能应对,有的全球性威胁则有赖于国际合作。
今年甲型N1H1流感突如其来的侵扰再度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这一新型瘟疫首先袭击的墨西哥一向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一个“实验室”。
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墨西哥城成为这场灾害的“震中”。
甲型N1H1至今仍在世界各地蔓延,究竟何时制服还是一个未知数。
大众健康问题的跨国化及其对大众健康越来越大的威胁一再昭示世人,世界各国在预防、控制疾病和促进、保护健康方面采取国际层面的集体行动已变得刻不容缓!
大众健康不再只是一个健康问题,而是任何国家可持续人类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大众健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敏感折射,也是检视和衡量全球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像墨西哥一样,中国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很高的一个国度。
与国内经济改革同步,中国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积极参与了全球化进程。
中国全球化成功的故事引起了举世瞩目。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当下的许多发展问题正是深嵌在这种“经济奇迹”之中的。
如何使疾病全球化的危害最小化并使公共卫生干预的益处最大化,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严峻考验。
投资于公共卫生干预对于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福祉具有巨大的潜力。
如同发展经济一样,健康干预也同样需要有国际眼光。
甲型N1H1的流行也再次印证,惟有在当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背景下来审视,全球和当地的大众健康问题、公共卫生干预和健康政策方可得到全面而系统的理解。
二、大众健康问题的全球化
全球化过程制造、催生并加剧了许多大众健康问题。
无论是传染病、非传染病抑或对大众健康的其他威胁,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全球性的大众健康问题不仅愈来愈多,而且日益复杂化。
这一切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
(一)非传染性疾病迅速增多
20世纪抗生素和疫苗的发明和普遍使用,连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实施,先是改变了发达国家而后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疾病谱,并戏剧性地降低了各国传染病发病和死亡的负担。
全球化图景下的社会经济革命,转变了许多地方传统的生活方式。
伴随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像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症、恶性肿瘤、中风、糖尿病等原先被当作富裕社会独有现象的非传染性慢性病,已开始侵扰许多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
与营养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急剧转变相伴生,一些发展中国家死于非传染病和伤损的人数迅速上升,远比传染病造成的死亡要多得多。
中国总的疾病谱也出现了与发达国家趋同的态势,即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和损伤的人数与日俱增,占八成以上。
根据对部分城市和农村县死因的统计,2008年城市居民前十位死因顺位为:
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病、损伤及中毒、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消化系病、泌尿生殖系病、神经系病、精神障碍。
前十位死因合计占死亡总数的92.4%。
农村居民前十位死因顺位是:
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病、心脏病、损伤及中毒、消化系病、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泌尿生殖系病、神经系病、精神障碍。
前十位死因合计占死亡总数的93.5%。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农村贫困者仍遭受营养不良的危害,而城里的一些人却受到了营养过剩的肥胖症的困扰。
这一切都表明,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既不纯粹由得个人,亦不完全在医疗保健机构掌控之中。
(二)一些古老传染性疾病死灰复燃
人类与肆虐的传染病进行了长久的抗争。
尽管如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人类至今仍未能将传染病关进笼子。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急剧变迁,像肺结核、疟疾、性病等一些人类宿敌卷土重来,继续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传染病仍是全球残疾和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主要的大众健康问题。
其中,结核病是世界传染病中的最大杀手,每年夺取约200-300万人的生命。
当然,并非所有这种传染性疾病都是全球性,或是越界传播的。
这里不妨以我国为例来看一看。
2008年中国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发病3541163例,死亡12433人。
发病数居前五位的分别是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痢疾、梅毒和麻疹,占报告发病总数的92.6%;
死亡数居前五位的是艾滋病、肺结核、狂犬病、病毒性肝炎和新生儿破伤风,占报告死亡总数的94.9%。
我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宣告成功消灭了性病,但到了70年代末它开始死灰复燃。
据报道1980年全国只有48例性传播疾病,但1985到1989年间的年增长率已达到了三位数,平均约为121%。
例如,全国梅毒报告的发病率由1987年的0.08/10万增长到2006年的13.35/10万,年增长率达到了30.66%。
更具有挑战性的是,大流感、疟疾、结核病等传统疾病不断产生变种,并增强了抗药性,从而使这些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不仅如此,很多这种传染性疾病被全球化了,成了跨越国界的一个重大政策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在聚焦于新老传染病的《世界卫生报告(1996)》中就曾告诫:
“我们正处于一场传染性疾病全球危机的边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免受其害,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对此高枕无忧”。
2000年联合国召集的世界高峰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仍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三种传染病明确列入全球优先关注的目标之列。
(三)一些新型传染病开始滋生和蔓延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诞生的具有更强传播性和更大威胁性的传染病,如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即SARS)和禽流感等,都会通过全球社会、经济、贸易活动不断跨越洲界和国境波及其他地方。
尽管这些新发传染病的发生率不是很高,但人类至今仍未找到非常有效的治疗措施。
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进程中,这类传染性疾病也很有可能在短时间演变成区域内外高发性的传染病,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因而会对国际公共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
2003年SARS的传播即是这么一个实例。
SARS的降临和制服也为全球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和借鉴经验。
艾滋病是疾病全球化最典型的一例。
自1981年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将艾滋病阻挡在国门之外的,不管其发展水平如何。
虽然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做出了大量不懈的努力,但艾滋病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2008年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全球艾滋病防治在2007年首次出现了“明显的重要进展”,艾滋病病毒新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有所下降。
全球艾滋病病毒新感染人数从1998年的320万下降为2007年的250万;
死亡者2007年降为200万,比2001年减少了20万。
但全球目前仍有332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2250万名感染者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众多非洲国家,亚洲有近500万人。
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发源于境外的艾滋病时疫不只是一个大众健康问题,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挑战。
作为地球村一偶,艾滋病危机正是在这种势不可挡的当代全球化风潮、在中国改革启动后急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入、传播并加剧蔓延的。
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5万,当年新发感染者5万。
当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正处于由吸毒者、商业性工作者、同性恋男性等高危人群向低风险或无风险的一般人群大规模扩散的临界历史关口。
遏制艾滋病病毒的进一步蔓延不容我们有丝毫的懈怠。
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过程使病媒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将疾病和死亡风险带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生发也变得难以逆料。
2003年春夏之交发生的SARS至今令国人记忆犹新。
该疫情缘起于广东,但在半年之间快速蔓延到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8000多人发病,700多人死亡。
SARS最清楚不过地表明,新传染病沿国际航线向世界各地的传播有多迅速。
SARS时疫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而且对一些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乃至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例如,亚洲各国总的花销和商业损失估计高达600亿美元。
这类传染病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不仅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而且还影响全球安全。
类似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还有可能在“地球村”不断上演。
地方性公共卫生事变得越来越具有国际重要性。
全球化过程引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的大众健康问题,还远不止一些传染病和非传染性慢性病。
除了这双重负担外,其他许多疾患也不容忽视。
例如,工农业污染助长了恶性肿瘤、出生缺陷、不孕症、哮喘等疾病的发生。
铺天盖地的广告营销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丧失了传统的健康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
我国一些贫困地区的居民还遭受血吸虫病、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及地方性氟中毒等地方病的危害。
此外,抽烟、酗酒、吸毒、不良饮食习惯及缺乏身体锻炼等不良生活模式,连同职业危害、工伤交通事故等等也使很多国家的负担更为严重。
在全球化时代,人口和流行病学转变同营养和膳食结构转变相结合,更增添了各国保护健康和降低疾病威胁的挑战。
以中国来说,我国1999年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的行列。
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5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达到了1005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7%;
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2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3%。
预期寿命的延长势必导致了慢性病大为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世界9%左右的耕地解决了世界上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