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美文阅读.docx
《优秀美文阅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优秀美文阅读.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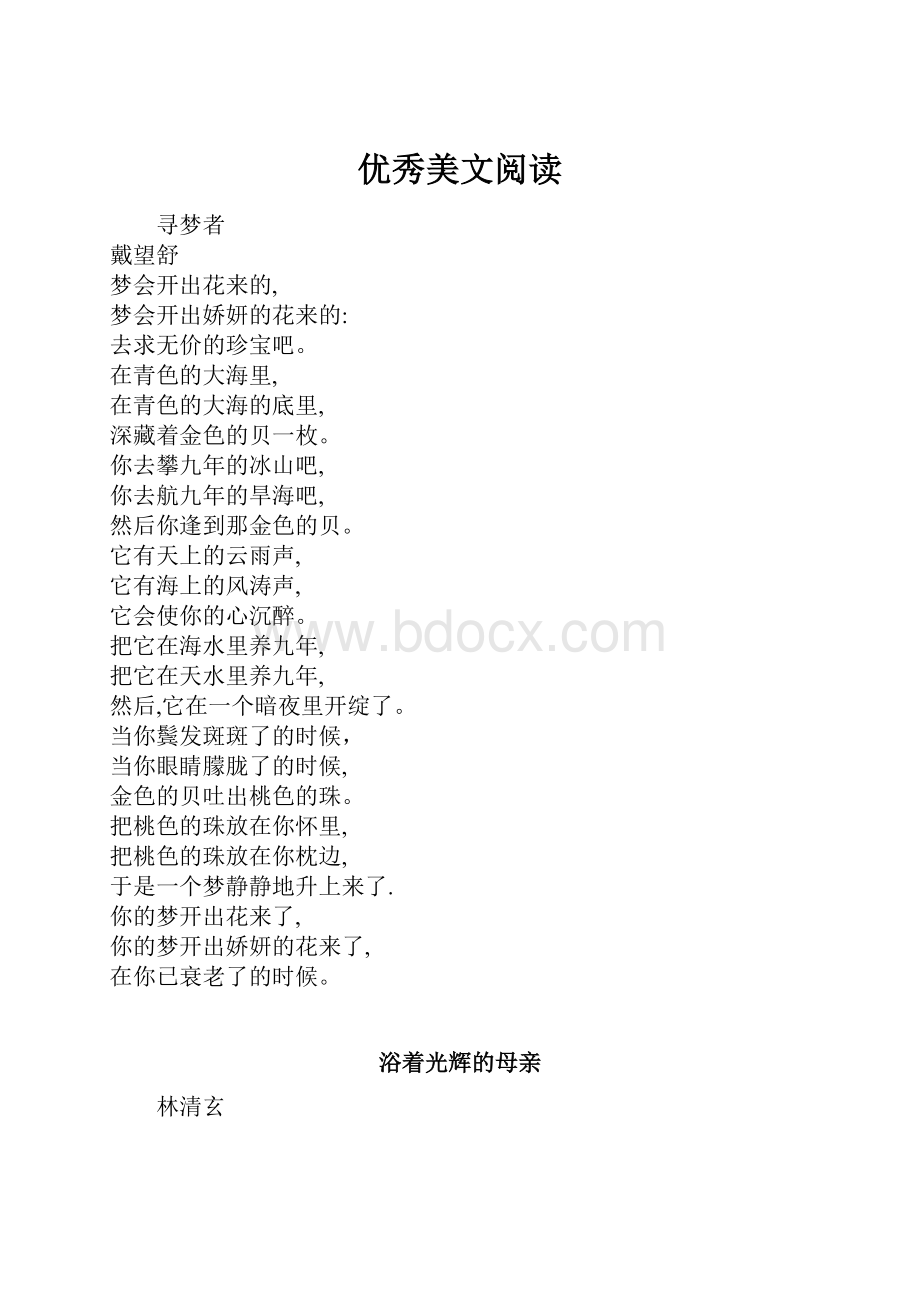
优秀美文阅读
寻梦者
戴望舒
梦会开出花来的,
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
去求无价的珍宝吧。
在青色的大海里,
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
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
它有天上的云雨声,
它有海上的风涛声,
它会使你的心沉醉。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
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
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
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
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
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
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浴着光辉的母亲
林清玄
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母亲不断疼惜呵护弱智的儿子,担心着儿子第一次坐公共汽车受到惊吓。
“宝宝乖,别怕别怕,坐车车很安全。
”——那母亲口中的宝宝,看来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了。
乘客们都用非常崇敬的眼神看着那浴满爱的光辉的母亲。
我想到,如果人人都能用如此崇敬的眼神看自己的母亲就好了,可惜,一般人常常忽略自己的母亲也是那样充满光辉。
那对母子下车的时候,车内一片静默,司机先生也表现了平时少有的耐心,等他们完全下妥当了,才缓缓起步,开走。
乘客们都还向那对母子行注目礼,一直到他们消失于街角。
我们为什么对一个人完全无私的溶入爱里会有那样庄严的静默呢?
原因是我们往往难以达到那种完全溶入的庄严境界。
完全的溶入,是无私的、无我的,无造作的,就好像灯泡的钨丝突然接通,就会点亮而散发光辉。
就以对待孩子来说吧!
弱智的孩子在母亲的眼中是那么天真、无邪,那么值得爱怜,我们自己对待正常健康的孩子则是那么严苛,充满了条件,无法全心地爱怜。
但愿,我们看自己孩子的眼神也可以像那位母亲一样,完全无私、溶入,有一种庄严之美,充满爱的光辉。
那个搭车的青年
毕淑敏
那一年,我“五一”放假回家,搭了一辆地方上运送旧轮胎的货车,颠簸了一天,夜幕降临才进入离家百来里的戈壁。
正是春天,道路翻浆。
突然在无边的沉寂当中,立起一根土柱,遮挡了银色的车灯。
“你找死吗?
你!
你个兔崽子!
”司机破口大骂。
我这才看清是个青年,穿着一件黄色旧大衣,拎着一个系着棕绳的袋子。
“我不是找死,我要搭车,我得回家。
”“不搭!
你没长眼睛吗?
司机楼里已经有人了,哪有你的地方!
”司机愤愤地说。
“我没想坐司机楼子,我蹲大厢板就行。
”司机还是说:
“不搭!
这样的天,你蹲大厢板会生生冻死!
”说着,踩了油门,准备闪过他往前开。
那个人抱住车灯说:
“就在那儿……我母亲病了……我到场部好不容易借到点小米……我母亲想吃……”
“让他上车吧!
”我有些同情地说。
他立即抱着口袋往车厢上爬:
“谢谢谢……谢……”最后一个“谢”字已是从轮胎缝隙里发出来的。
夜风在车窗外凄厉地鸣叫。
司机说:
“我有一个同事,是个很棒的师傅。
一天,他的车突然消失了,很长时间没有踪影。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个青年化装成一个可怜的人,拦了他的车,上车以后把他杀死,甩在沙漠上,自己把车开跑了。
”
我心里一沉,找到司机身后小窗的一个小洞,屏住气向里窥探。
“他好像有点冷,别的就看不出什么了。
”我说。
“再仔细瞅瞅。
我好像觉得他要干什么。
”这一次,我看到青年敏捷地跳到两个大轮胎之间,手脚麻利地搬动着我的提包。
那里装着我带给父母的礼物:
“哎呀,他偷我的东西呢!
”
司机很冷静地说:
“怎么样?
我说的不错吧。
”
“然后会怎么样呢?
”我带着哭音说。
“你也别难过。
我有个法子试一试。
”
只见司机狠踩油门,车就像被横刺了一刀的烈马,疯狂地弹射出去。
我顺着小洞看去,那人仿佛被冻僵了,弓着腰抱着头,石像般凝立着,企图凭借冰冷的橡胶御寒。
我的提包虽已被挪了地方,但依旧完整。
我把所见跟司机讲了,他笑了,说:
“这就对了,他偷了东西,原本是要跳车了,现在车速这么快,他不敢动了。
”
路面变得更加难走,车速减慢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紧张地盯着那个小洞。
青年也觉察到了车速的变化,不失时机地站起身,重新搬动了我的提包。
我痛苦地几乎大叫,就在这时,司机趁着车的趔趄,索性加大了摇晃的频率,车身剧烈倾斜,车窗几乎吻到路旁的沙砾。
我想到贼娃子一举伤了元气,一时半会儿可能不会再打我提包的主意了,心里安宁了许多。
只见那个青年艰难地往轮胎缝里爬,他把我的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往手上哈着气,摆弄着拉锁上的提梁。
这时,他扎在口袋上的绳子已经解开,就等着把我提包里的东西搬进去呢……
“师傅,他……他还在偷,就要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我惊恐万状地说。
“是吗?
”师傅这次反倒不慌不忙,嘴角甚至显出隐隐的笑意。
“到了。
”司机突然干巴巴地说。
我们到一个兵站了,也是离那个贼娃子住的村最近的公路,他家那儿是根本不通车的,至少还要往沙漠腹地走10公里……司机打亮了驾驶室里的大灯,说:
“现在不会出什么事了。
”
那个青年挽着他的口袋,像个木偶似的往下爬,狼狈地踩着轱辘跌下来,跪坐在地上。
不过才个把时辰的车程,他脸上除了原有的土黄之外,还平添了青光,额上还有蜿蜒的血迹。
“学学啦……学学……”他的舌头冻僵了,把“谢”说成“学”。
我们微笑地看着他,不停地点头。
他说:
“学学你们把车开得这样快,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在赶路……”他抹了一把下颌,擦掉的不知是眼泪、鼻涕还是血。
他点点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看着他蹒跚的身影,我不由自主地喝了一声:
“你停下!
”
“我要查查我的东西少了没有。
”我很严正地对他说。
司机赞许地冲我眨眨眼睛。
青年迷惑地面对我们,脖子柔软地耷拉下来,不堪重负的样子。
我爬上大厢板,动作是从未有过的敏捷。
我看到了我的提包,像一个胖胖的婴儿,安适地躺在黝黑的轮胎之中。
我不放心地摸索着它,每一环拉锁都像小兽的牙齿般细密结实。
突然触到棕毛样的粗糙,我意识到这正是搭车人袋子上那截失踪的棕绳。
它把我的提包牢牢地固定在大厢的木条上,像焊住一般结实。
我的心像凌空遭遇寒流,冻得皱缩起来。
合欢树
史铁生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但丁
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
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
“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
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
”我听得扫兴,故意笑:
“可能?
什么叫‘可能还不到’?
”她就解释。
我装做根本不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
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
那时,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我20岁时,我的两条腿残废了。
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
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
医院已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法治。
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了很多钱。
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灸。
“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
”我说。
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
“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
”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
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
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
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
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
“怎么会烫了呢?
我还总是在留神呀!
”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
她跟我说:
“那就好好写吧。
”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
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
那就写着试试看。
”她提醒我说。
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
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
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母亲已离开我整整7年了。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
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
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
我摇着车躲了出去。
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
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
“她心里太苦了。
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
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子去。
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
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
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
“到小院子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
”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
大伙就不再说,忙扯到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
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
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
第三年,合欢树不但长出了叶子,而且还比较茂盛。
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太大意。
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
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哀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
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
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
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喜欢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
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
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
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过道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去也要侧身。
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
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
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
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想急着回家。
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
悲伤也成享受。
有那么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
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
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
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我喜欢出发
汪国真
我喜欢出发。
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
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
太深的流连便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
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
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
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
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
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
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
真庆幸,我还没有老。
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
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
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
人能走多远?
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
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
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树起一个高远的目标。
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
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
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个性
汪国真
一个人没有个性,便失去了自己。
生活中一味的模仿之所以不可为,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抹杀了个性。
同为名山,华山险;泰山雄;黄山奇;峨嵋秀。
“险”、“雄”、“奇”、“秀”,就是不同的个性。
山如此,人亦然。
生活之中,适当地改变自己的个性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自我的完善,恰恰在这一点上,有一些人常常本末倒置。
钱钟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是一种美德,而雨果先生生平的一大愿望是要把巴黎改为自己的名字也并非缺德。
画家的个性挥洒在作品的线条里;诗人的个性倾注在作品的感情里;音乐家的个性融汇在作品的旋律里。
不过,有为大多数人欣赏的个性,却没有为所有人欣赏的个性。
保持自身的个性和尊重别人的个性同样重要。
不能保持自身的个性是一种“懦弱”,不能尊重别人的个性是一种“霸道”。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个性可能不合于“潮流”,却合于生活。
为了追赶“潮流”而改变自己的个性,那不过是做了一篇虚情假意的“文章”。
“潮流”总是不断地改变,你的“文章”难道也要不断地重写?
没有个性,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仅有个性,也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狭隘的人总是想扼杀别人的个性;
软弱的人随意改变自己的个性;
坚强的人自然坦露真实的个性。
瞬息与永恒的舞蹈
张抗抗
一盆昙花养了整整六年,仍是一点动静没有。
年复一年,它无声无息地蛰伏着,除了枝条日甚一日的蓬勃,别无吐蕾开花的迹象。
怜它好歹是个生命,不忍丢弃,只好把它请到阳台上去,找一个遮光避风的角落安置了,只在给别的盆花浇水时,捎带着用剩水敷衍它一下。
心里早已断了盼它开花的念想,饥一餐饱一顿地,任其自生自灭。
一个夏天的傍晚。
我再次走上阳台,去给冬青浇水,然后弯下腰为冬青掰下了一片黄叶。
忽然有一团鹅黄色的绒球,从冬青根部的墙角边钻出来,闪入了我的视线。
我几乎被那团鸡蛋大小的绒球吓了一大跳:
那不是绒球,而是一枝花苞——昙花的花苞,千真万确。
昙花入室,大概是下午六点左右。
它就放在房间中央的茶几上,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那一枝鹅黄色的花苞渐渐变得明亮。
晚七点多钟的时候,它忽然颤栗了一下,颤栗得那么强烈,以至于整盆花树都震动起来。
就在那个瞬间里,闭合的花苞无声地裂开了一个圆形的缺口,喷吐出一股浓郁的香气,四散溅溢。
它的花蕊是金黄色的,沾满了细密的颗粒,每一粒花粉都在传递着温馨呢喃的低语。
那橄榄形的花苞渐渐变得蓬松而圆融,原先紧紧裹挟着花瓣的丝丝淡黄色的针状须茎,如同刺猬的毛发一根根耸立起来,然后慢慢向后仰去。
在昙花整个开启的过程中,它们就像一把白色小伞的一根根精巧刚劲的伞骨,用尽了千百个日夜积蓄的气力,牵引着、支撑着那把小伞渐渐地舒张开来。
现在它终于完完全全绽开了,它更像一位美妙绝伦的白衣少女,赤着脚从云中翩然而至。
从音乐奏响的那一刻起,“她”便欣喜地抖开了素洁的衣裙,开始那一场舒缓而优雅的舞蹈。
“她”知道这是自己多年来一直期盼的一次公开演出,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虽然是初次登台,但是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娴熟完美,昙花于千年岁月中修炼的道行,已给“她”注入了一个优秀舞者的遗传基因,使得“她”婀娜轻柔的舞姿带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绝美。
这一场动人心弦的舞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她”悄然无声地一边舞着,一边用自己身体内多年存储的精华,尽情演绎着生命的辉煌,挥洒着成功的芳香。
盛开的昙花就那么静静地悬在枝头,像一帧被定格的胶片。
但昙花的舞蹈并未就此结束。
“她”忽然又颤动了一下,张开的手臂,渐渐向心口合抱;“她”用修长的指尖梳理着金发般的须毛,又将白色的裙衫一片片收拢;然后垂下“她”白皙的脖颈,向泥土缓缓地匍匐下去。
“她”平静而庄严地做完这全套动作,大约用了三个小时——那是舞蹈的尾声中最后复位的表演。
昙花的开放是舞蹈,闭合自然也是舞蹈。
片片花瓣根根须毛,从张开到闭合,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
“她”用轻盈舒缓的舞姿最后一次阐释艺术和生命的真谛。
我很久很久地凝望着它,满怀歉意地观赏着昙花从帷幕拉开、尽情绽放到舞台定格的全部过程。
“昙花一现”那个带有贬义的古老词语,在这个偶然的夏夜里变成一种正在逝去的遥远回声。
给予我新的启示。
那个傍晚的阳台,那一场绝美的舞蹈中,我是唯一幸运的陪伴者。
想起我这些年来对昙花的冷落和敷衍,愧恨之情油然而生。
此后,我将用清水和阳光守候那绿色的舞台,等待它明年再度巡回。
透明
纳兰妙珠
衰老像夜晚一样徐徐降临,光并不是一下子就散尽,死神有惊人的耐心,有时他喜欢一钱一钱地凌迟。
壮年时的余晖犹在,八十岁时,姥姥的食量仍是阖家之最。
她独个儿住在老房子里,自己伺候一个蜂窝煤炉子,自己买菜做饭,虽是颠着一对小脚,行如风摆杨柳,但还利索得很。
她对大家都很有用,儿女的孩子尚小,都得靠姥姥帮忙看管。
六个外孙,孙女、外孙女,都经她的手抚养。
于是她是有实质的,有威信,说话一句算一句,小辈们都不敢不认真听,稍有点嬉皮笑脸,姥姥脸色一沉,扬起一只大手,“打你!
”喉咙里冒出不大不小的一个霹雳,威风凛凛。
不听话者难免心头一凛,收敛起嬉皮笑脸,承认错误。
后来她越来越老了,城池一座一座失守,守军一舍一舍败退,退至膏肓之中。
她不能再为家人提供帮助,只能彻底地索取,因此她逐渐透明下去,世界渐渐看不见她了。
她的威严熄灭了,儿女们上门的脚踪逐渐稀了,孙儿辈异口同声地说工作忙,好像都在同一家公司。
春节团聚的时候,敷衍地拎一箱牛奶,进来叫一声姥姥或奶奶,这就算交差。
她记忆漫漶得很了,一个孙女站在眼前,她要把所有孙女名字都叫一遍,才牵带得出正确的那个。
除了行动能力,在最后十年中,她也渐渐失掉正常交流谈话的智力。
与人说话,一句起,一句应,一句止,她就很满足了,慢慢点着头,像回味这次对话似的,眼睛若有所思地转向别处。
有时,她想主动与人沟通,就拿手去碰触身边的人,叫着,哎,哎。
脸色有点巴结地笑,郑重地问出一个问题,比如:
我有点不记得,想了半天了——你今年多大?
这当然是可笑的。
被问的人和旁边的人对此都有默契的认识,他们面面相觑,嬉笑着,拿不认真的嗓音说,您看我多大了?
她却仍认真的,我想你是十九,还是二十?
被问的人呵呵大笑,姥姥,我都三十五啦。
然后人们继续自管自说话,不再看她。
剩她独个儿咂摸那一点愕然,并陷入喃喃慨叹,哎呀,我外孙三十五了?
当初我带你的时候,你整天哭,搁不下,只能一只手抱你,一只手捅炉子炒菜……
人们都同意跟她说话只要敷衍过去即可,谁让她活到这样老,老得跟世界文不对题。
“衰老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屠杀。
”菲利普·罗斯说。
除非你幸运地蒙召早退,逃出这环链条。
后来她的听力不太好了,人间把她又推远了一步。
有时她会陷入沉思状态,陷得很深。
盘腿坐着,小脚放在腿弯折叠处,手撑着额角,眼睛盯着墙,浑浊的眼珠停滞了,犹如哲学家整理胸中哲思。
大家围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以这个行动表示孝敬。
所有人当着她的面议论她,毫不避讳,也不用压低声音,就像她是一座标本。
生命和岁月交给她的能力,最终按原本的顺序一样一样还回去。
五年前,很难出门了,用轮椅推到外面花园里,还能搀着别人的手走两步,走到池子边看人用馒头喂金鱼。
后来不再出屋,不过还能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
再后来彻底不能行走,但还勉强能站立。
再后来站起来也不能了,三年里整日只倚枕坐着。
她的食量逐渐减少,食谱逐渐缩短,需要多费牙齿之力与肠胃之力的美味一项一项与她道别。
本来她还能喝几口黄酒,后来终至一喝酒就腹泻。
筛子眼越来越细,兴致、乐趣都被筛出去了,日子唯余越来越纯粹的萧索。
最后半年,她吃得像个初生婴儿,粥,牛奶,一点点肉糜。
到临终两个月,粥和牛奶亦被肠胃拒绝了,只剩了饮水,蜂蜜调制的水,糖水。
再让她喝两口牛奶,下午就泻了一床。
仅余的生命力,负隅顽抗,又把这座孤城苦守了两个月,直至弹尽粮绝。
最后一次回家看她,她的精神已不够把眼皮撑足。
眯缝眼看我,仍笑,喊我乳名,声音又虚又小,像一片揉烂的纸条。
阳光照着她,能透过去。
我拉起她的手,攥一攥,又放下,然后做了一次从没跟她做过的动作:
握着她硬邦邦硌手的肩膀,嘴唇碰着她颧骨,轻轻一吻。
那皮肤薄得像一层膜。
她眼皮下闪出一星欣慰和快活,低声说,哟。
然后问,你回来呆几天啊?
我说,明天就走,你等着我,我再来看你。
她半迷蒙的一笑,代替回答。
倒数第二样能力,吞咽。
除了每天几口水,她无力吞咽更多东西,再多就累着了。
到世上来学会的第一样本领以及丢掉的最后一样,都是:
呼吸。
初夏的上午,她咽下最后一口呼吸。
时间怎样行走
迟子建
墙上的挂钟,曾是我童年最爱看的一道风景,我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拜,因为它掌管着时间,我们的作息似乎都受着它的支配。
我觉得左右摇摆的钟摆,就是一张可以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的嘴,它说什么,我们就得乖乖地听。
到了指定的时间,我们得起床上学,我们得做课间操,我们得被父母吆喝着去睡觉…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没睡够不想起床,我们在户外的月光下还没有戏耍够不想回屋睡觉,都必须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听从父母的吩咐。
他们理直气壮呵斥我们的话与挂钟息息相关,“都几点了,还不起床”,要么就是“都几点了,还在外面疯玩,快睡觉去!
”这时候,我觉得挂钟就是一个拿着烟袋锅磕着我们脑门的狠心的老头,又凶又倔,真想把它给掀翻在地让它永远不能再行走。
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一个看不见形影的家长,严厉而又古板。
但有时候它也是温情的,比如除夕夜里,它的每一声脚步都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可以放纵地提着灯笼在白雪地上玩个尽兴,可以在子时钟声敲响后得到梦寐以求的压岁钱,想着用这钱可以买糖果来甜甜自己的嘴,真想在雪地上畅快地打几个滚…我那时天真地以为时间是被一双神秘大手给放在挂钟里的,从来不认为那是机械的产物。
它每时每刻地行走着,走得不慌不忙,气定神凝,它不会因为贪恋窗外鸟语花香的美景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北风肆虐大雪纷飞而加快脚步,它的脚是世界上最能经得起诱惑的脚,从来都是循着固定的轨迹行走。
我喜欢听它前行的声音,总是一个节奏,好像一首温馨的摇篮曲…时间藏在挂钟里,与我们一同经历着风霜雪雨、潮起潮落…
我上初中以后,手表就比较普及了,我看见时间躲在一个小小的圆盘里,在我们的手腕上跳舞,它跳得静悄悄的,不像墙上的挂钟,行进得那么清脆悦耳,“滴答”“滴答”的声音不绝于耳。
所以,手表里的时间总给我们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从这里走出来的时间因为没有声色而少了几分气势,这样的时间仿佛也没了威严,不值得尊重,所以明明到了上课时间我还会磨蹭一两分钟再进教室,手表里的时间也就因此显得有些落寞。
后来,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时间栖身的地方就多了,项链坠可以隐藏着时间,让时间和心脏一起跳动;台历上镶嵌着时间,时间和日子交相辉映;玩具里放置着时间,时间就有了几分游戏的成分;至于计算机和手提电话,只要我们一打开它们,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有时间…时间如繁星一样到处闪烁着,它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显得匆匆了…
十几年前的一天,我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痕迹,我在梳头时发现了一根白发,它在清晨的曙光中像一道明丽的雪线一样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知道,时间其实一直悄悄地躲在我的头发里行走,只不过它这一次露出了痕迹而已。
我明白,时间让花朵绽放的时候也会让人的眼角绽放出花朵――鱼尾纹;时间让一棵青春的小树越来越枝繁叶茂;让车轮的辐条越来越沾染上锈迹;让一座老屋逐渐地驼了背…时间还会变戏法,它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瞬间消失在他们曾为之辛勤劳作着的土地上,我的祖父、外祖父和父亲,就这样,让时间给无声地接走了,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脚印,只能再清冷的梦中见到他们依稀的身影…他们不在了,可时间还在,它总是持之以恒、激情澎湃地行走着…在我们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