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诗学.docx
《空间的诗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空间的诗学.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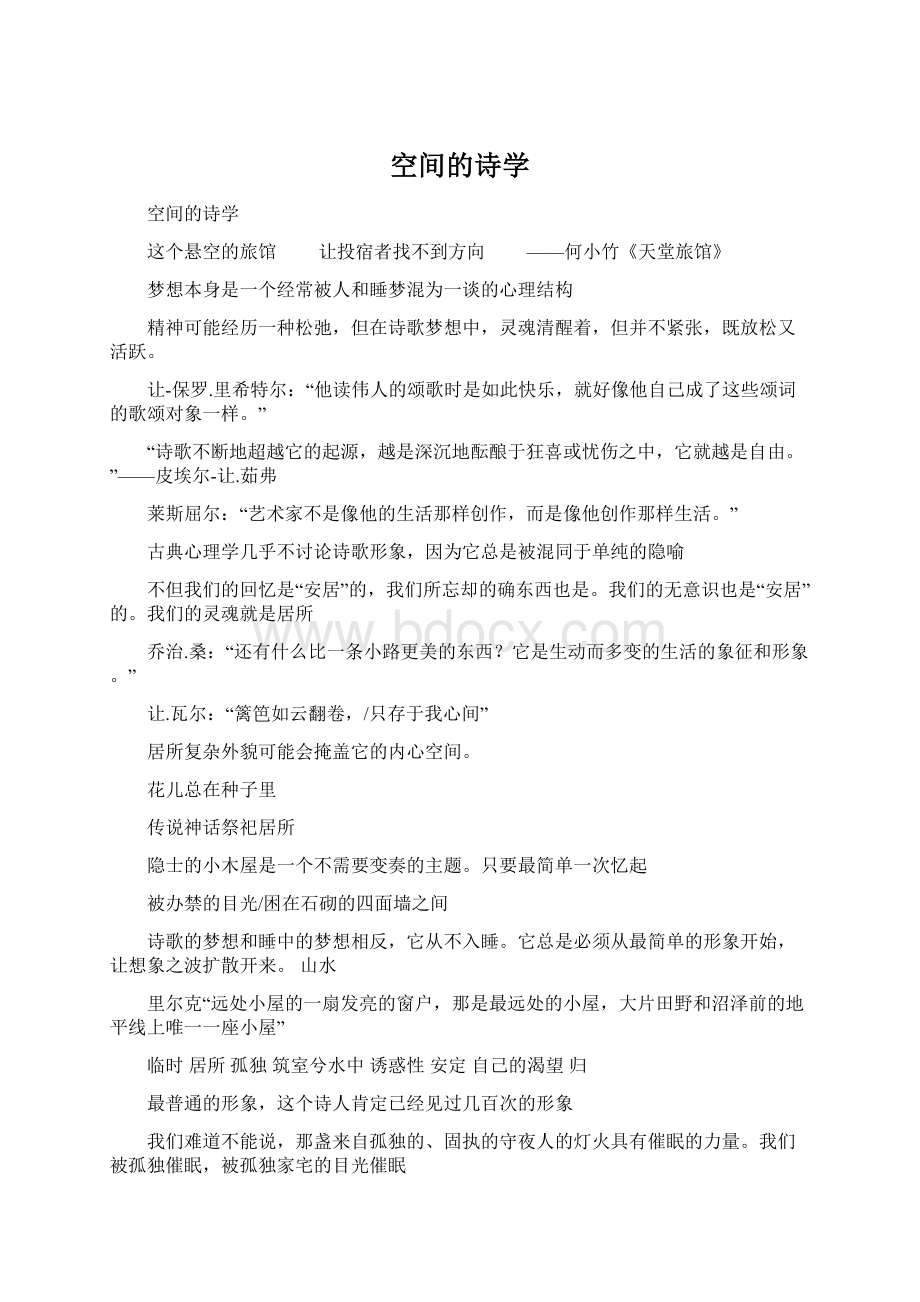
空间的诗学
空间的诗学
这个悬空的旅馆 让投宿者找不到方向 ——何小竹《天堂旅馆》
梦想本身是一个经常被人和睡梦混为一谈的心理结构
精神可能经历一种松弛,但在诗歌梦想中,灵魂清醒着,但并不紧张,既放松又活跃。
让-保罗.里希特尔:
“他读伟人的颂歌时是如此快乐,就好像他自己成了这些颂词的歌颂对象一样。
”
“诗歌不断地超越它的起源,越是深沉地酝酿于狂喜或忧伤之中,它就越是自由。
”——皮埃尔-让.茹弗
莱斯屈尔:
“艺术家不是像他的生活那样创作,而是像他创作那样生活。
”
古典心理学几乎不讨论诗歌形象,因为它总是被混同于单纯的隐喻
不但我们的回忆是“安居”的,我们所忘却的确东西也是。
我们的无意识也是“安居”的。
我们的灵魂就是居所
乔治.桑:
“还有什么比一条小路更美的东西?
它是生动而多变的生活的象征和形象。
”
让.瓦尔:
“篱笆如云翻卷,/只存于我心间”
居所复杂外貌可能会掩盖它的内心空间。
花儿总在种子里
传说神话祭祀居所
隐士的小木屋是一个不需要变奏的主题。
只要最简单一次忆起
被办禁的目光/困在石砌的四面墙之间
诗歌的梦想和睡中的梦想相反,它从不入睡。
它总是必须从最简单的形象开始,让想象之波扩散开来。
山水
里尔克“远处小屋的一扇发亮的窗户,那是最远处的小屋,大片田野和沼泽前的地平线上唯一一座小屋”
临时居所孤独筑室兮水中诱惑性安定自己的渴望归
最普通的形象,这个诗人肯定已经见过几百次的形象
我们难道不能说,那盏来自孤独的、固执的守夜人的灯火具有催眠的力量。
我们被孤独催眠,被孤独家宅的目光催眠
兰波:
就像一个寒冬的夜晚,雪让世界彻底窒息
可就这个虚无的背景下长出了人性的价值!
相反,如果我们超出回忆,前往幻想深处,那么在那前记忆中,我们仿佛年岁虚无抚摸着存在,渗透着存在,轻柔地解开存在的各种关联。
树对鸟来说已经是一处庇护所陋室的渴望
休息的形象、安静的形象一样,鸟巢直接关联着简单家宅的形象
山水缩影文学中缩影,这些很容易被文人缩小的对象
家宅空想
内部美
那种在长期形成的科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哲学思考会要求把新观念纳入已经过检验的观念体系中去,即使那个新观念会迫使整个观念体系发生深刻的重组,就像当代科学中的所有革命一样。
然而这个理性主义者的微小冲突,这个仅仅出现在新形象问题上的冲突,却包含着想象力现象学的全部悖论:
一个往往非常奇特的形象如何能够作为全部心理活动的浓缩而出现?
还有,一个奇特的诗歌形象的出现,这一奇特而稍纵即逝的事件,如何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别的灵魂、别的心灵中引起反应,而这一切又完全不受制于任何常识所形成的障碍,不受制于任何不求改变的理性思维?
正是在这个地方,共鸣和回响在现象学上的同源异词才得以彰显。
共鸣散布于我们在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回响召唤我们深入我们自己的生存。
在共鸣中,我们听见诗;在回响中,我们言说诗,诗成了我们自己的。
回响实现了存在的转移。
仿佛诗人的存在成了我们的存在。
因此共鸣的多样性来自于回响的存在统一性。
它变成我们的语言的一个新存在,它通过把我们变成它所表达的东西从而表达我们,换句话说,它既是表达的生成,又是我们的存在的生成。
在这里,表达创造存在。
JeanLescure在研究画家Lapicque的作品时写下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
“尽管他的作品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各种空间表现力的了解,但它并不是在运用这些东西,它不是根据现成方法做成的……因此技艺必须伴随这同等程度的忘记技艺。
无技艺不是无知,而是艰难地超越知识的行动。
正是通过牺牲技艺,作品每时每刻都是一种纯粹的开端,这一开端把创作变成了练习自由。
”
我们想要研究的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形象,那就是幸福空间的形象。
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的探索可以称作场所爱好(topophilie)。
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
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当存在找到了最简陋的庇护之处时,想象力如何以这个逆命题的方向运作起来:
我们将看到想象力用无形的阴影建造起“墙壁”,用受保护的幻觉来自我安慰,或者相反,在厚厚的墙壁背后颤抖,不信赖最坚固的壁垒。
并非只有思想和经验才能证明人的价值。
有些代表人的内心深处的价值是属于梦想的。
梦想甚至有一种自我增值的特权。
它直接享受着它的存在。
然而,除了回忆,出生的家宅从生理上印刻在我们心中。
它是一组器质性习惯。
时隔20年,尽管我们踏过的都是无名楼梯,我们仍会重新感受到那个“最初的楼梯”所带来的反射动作,我们不会被这个略高的台阶绊倒。
家宅的整个存在自行展开,与我们的存在相契合。
在此,我们处于一种轴线上,围绕它旋转的是各种相互作用的解释,用思想来解释梦,用梦来解释思想。
解释这个词把这种转化过于僵硬化了。
事实上,我们处于形象和回忆的统一之中,想象力和记忆力的功能性混合之中。
童年肯定不只是实在的东西。
正是在梦想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事实的层面上,童年在我们心中才保持鲜活,并且从诗歌的角度来说是有用的。
通过永恒的童年,我们保留着关于往日的诗歌。
在梦中居住出生的家宅,这不仅仅是通过回忆来居住,而是如同我们梦见它那样,生活在消失的家宅里。
于是,抛开所有保护方面的实证价值,在出生的家宅里建立起了幻想的价值,这是当家宅不复存在之后仍然留存的最后价值。
屋顶立刻说出了它的存在理由:
它把害怕日晒雨淋的人置于遮蔽之下。
地理学家总是反复提到,在每个国家,屋顶的坡度是关于气候的最可靠信号之一。
我们“理解”屋顶的倾斜。
事实是否确曾有过记忆赋予它们的价值?
久远的记忆只有通过赋予它们价值,赋予它们幸福的光晕,才能够被忆起。
一旦抹去价值,事实也就不复存在。
它们可曾存在过?
请注意,门上的“把手”按照家宅的比例尺本不应该画出来。
它的功能比所有尺寸上的考虑更重要。
它代表了开启的功能。
只有逻辑思维才会反对它具有同等的关闭和开启的作用。
在价值的领域里,钥匙起关闭作用的时候比起开启作用的时候多。
把手起开启作用的时候比起关闭作用的时候多。
关闭的手势总是比开启的手势更干脆、更有力、更简短。
正是在衡量这些细微之处上,我们应该像明科夫斯卡一样做家宅的心理学家。
正如我们所知,抽屉的隐喻以及其他几个诸如“批量生产的成衣”之类的隐喻被伯格森用来形容概念哲学的缺陷。
概念是用来对知识进行分类的抽屉;概念是批量生产的成衣,它们剥夺了亲身体验得来的知识的个体性。
每个概念都在范畴的家具中有它自己的抽屉。
概念是死去的思想,因为它在其定义上就是被分类的思想。
“正如我们已经尝试证明的那样,记忆不是把回忆分门别类放入抽屉或者登记在记录册上的能力。
记忆里没有记录册,没有抽屉……”
每一把锁都是对撬锁者的召唤。
锁是怎样的一个心理学门槛啊。
想象力从来不能够说:
仅此而已。
永远都不止此。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多次,想象的形象并不受制于现实的检验。
维克多•雨果用短短一句话把形象和有居住功能的存在联系起来。
他说,对卡西莫多而言,教堂先后是“蛋壳,鸟巢,家宅,祖国,宇宙”。
“几乎可以说,他以它为形状,就好像蜗牛以壳为形状一样。
这就是他的居所,他的洞穴,他的罩子……他依附于教堂,就好像乌龟依附于它的龟壳一样。
毛糙不平的教堂就是他的甲壳。
”这些形象必须一个也不能少,才能说明一个外表丑陋的存在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建筑物的各个角落找到他提心吊胆的藏身之处。
就这样,诗人通过形象的多样性让我们感觉到各种各样庇护所的力量。
但他立刻在大量堆叠的形象后面加上了一个节制的信号。
雨果接着说:
“无须警告读者不要从字面上理解我们不得不在这里使用的比喻。
这些无非是为了表达一个人和一座建筑物之间奇特、匀称、直接、宛如同体的结合。
”
因此,价值会改变事实的地位。
一旦我们喜欢上一个形象,它就不再是事实的摹本。
“实际上,鸟儿的工具就是它自己的身体,它的胸膛,它用胸膛挤压并夯实建筑材料,直到把它们彻底驯服,混合在一起,使它们服从整体的建筑构思。
”米什莱向我们揭示了用身体建造的家宅,为身体建造的家宅,它从内部成型,就像一个贝壳,在用身体塑造而成的内部空间里。
鸟巢的外形是由内部决定的。
“在内部,决定鸟巢的圆周形状的工具不是别的,正是鸟的身体。
正是通过不停地转圈,从各个角度往外推墙壁,鸟儿才能够形成这个圆圈。
”
鸟巢(我们能很快理解它)是临时性的,但它却在我们心中激发起关于安全的梦想。
显著的临时性如何能够不妨碍这样的梦想?
对这个矛盾的回答很简单:
我们在梦想时不自觉地成为了现象学家。
我们在某种天真状态中重新体验了鸟的本能。
我们喜欢强调掩映在绿叶中的绿色鸟巢的模仿本领。
我们确实看见它了,但我们却说它藏得很好。
“软体动物从贝壳中流溢出来”,“任凭”建筑材料“渗出”,“适量地分泌出它的神奇保护层”。
从第一次分泌开始家宅就是完整的。
我们将会在另一章里说明,在想象中,进去合出来从来不是对称的形象。
像所有重要的动词一样,“出自”要求我们做许多研究,除了具体的心理区分之外,还要收藏一些难以感觉到的抽象运动。
我们在语法派生、演绎和归纳中几乎不再感觉到行为。
动词自身凝固不动,好像成了名词。
只有形象能使动词重新运动起来。
当我们用电影加速花朵的绽放时,我们获得了祭献的崇高形象。
想象的生命冲动所具有的加速度欲使出自大地的生物立刻获得一个外形。
我们跟随想象力的扩张活动,直至超出现实以外。
为了超越,必需首先扩张。
化石不再只是一个曾经有过生命的生物,它是一个仍然活着的生物,沉睡在自己的形状里。
如果我们从这里面只看到用和常见事物作比较的方式来命名新事物这一语言习惯的简单沿用,那就错了。
然而,从原则上抛弃任何批判态度的现象学家不能不承认,当运用语词的人超乎常理之时,当形象超乎常理之时,梦想正在深层上揭示自身。
我们在目前的研究中所要做的是对自己提问,那些最简单的形象如何能够在一些天真的梦想里形成一种传统。
由于我们给一些词加了着重号,我们恳求读者注意,“如同”这个词超越了“像”(comme)这个词,确切地说,“像”忽略了一个现象学上的细微差别。
像一词在于模仿,而如同一词意味着我们变成了梦想着梦想的那个主体本身。
……我们开始想到,想象力是先于记忆的。
于是“蜗牛无论旅行到何方,它都在自己家里。
”
固然,自然很擅长制造庞然大物。
人却能轻易想象出更大的东西。
翁加雷蒂对这幅古老的版画梦想良久以后,毫不含糊地说,艺术家成功地让“狼令人同情,而乌龟令人讨厌”。
如果我有这幅版画的复制品,我就会做一个测试来区分和度量人们参与在世饥饿这一冲突的角度和程度。
我们在阅读中所能收集到的文献数量很少,因为这种完全生理上的缩成一团已经具有了否定主义的特征。
当孩子向外部展开的时候,她才发现她就是它,这或许是对紧缩在存在一角里的那种状态的反应。
这里不再是一种颜色覆盖在事物上面,而是事物自身结晶成忧伤、遗憾和怀念。
心理学家,尤其是哲学家,很少注意童话故事里常常出现的缩影术。
为了让人相信,必须自己相信。
对一个哲学家来说,针对这些“文学中的”缩影,这些很容易被文人缩小的对象,是否有必要提出一个现象学问题?
意识——作家的意识、读者的意识——是否能够真诚地活动于这类形象的起源本身?
……那么几何学上的矛盾就迎刃而解,再现被想象所支配。
再现不过是一种表达的载体,用来向他人传递我们自己的形象。
“我以为人的想象力所发明的任何东西没有不真实的,不论它们是在这个世界之中还是在别的世界之中。
”
我们简要地提出这一点是为了强调自行完成的绝对形象和后于观念,只作为思维总结的形象之间的本质区别。
用放大镜的人轻而易举地将司空见惯的世界划去。
他是崭新对象面前的新鲜目光。
植物学家的放大镜是一段重新找回的童年。
它重新赋予植物学家以儿童特有的放大眼光。
借助于它,植物学家重新回到花园里,在花园里:
孩子们眼里什么都很大。
拿起一个放大镜是集中注意力,但集中注意力难道不已经是有了一个放大镜吗?
注意力本身就是一块起放大作用的玻璃。
在《空间的诗学》中,巴什拉声称“所有的庇护所,所有的藏身处,所有的卧室,都有共同的梦境价值”,“家宅庇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家,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
好梦的尽头总会如期出现一只现实的闹钟,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设置了恩格斯的警钟——“在这样的社会中,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种制度。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家宅,人就成了居无定所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员。
倘若按照“存在先于本质”的判定,人在成为无房者之前早已经成为了流离失所的存在。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金融危机的严冬中,对无房者而言,“目标虽有,道路全无,我们所谓的道路无非是踌躇”,家宅的形象就体现在卡夫卡的这句箴言中,它犹如一座清晰可见却又无法靠近的梦的城堡。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里尔克《秋日》
列斐伏尔不厌其烦地强调,空间是政治性的,任何空间都置身于权力关系网之中,几乎所有的空间无一不成为权力的角斗场。
“没有房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之一,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对于空间的占有,来达到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以及维持他们自身的统治。
因此,“不必建造”(也根本没有建造的可能),无产阶级与无房者要想获得对于空间的使用权唯一的途径就是革命。
空间作为一个可读性文本,左派人士见到革命,诗人见到诗意,当然也不乏如波德莱尔这样持有左派立场的诗人,在革命的街垒战斗的血泊中发现诗意。
相对而言,巴什拉并不具备波德莱尔那样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家宅中他满眼看到的都是关于“孤独”的诗意形象,而非革命的宏大主题。
有别于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念更多的体现了公共空间的特征,巴什拉认为,家宅首先意味着封闭的、隐私的内心空间,构成内心空间的精神元素就是孤独感。
形而上学家说人的孤独感由于“被抛于世界”,巴什拉反驳说,此前“人已经被放置于家宅的摇篮之中。
在我们的梦想中,家宅总是一个巨大的摇篮”。
换言之,巴什拉认为生存的孤独感和梦想的幸福感与形而上学的论断没有关联。
出生的家宅同是孤独感和幸福感的摇篮。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谁此时幸福,就永远幸福。
在巴什拉看来,家宅将人封闭在孤独之中,并且使得他的激情存在乃至爆发。
这种爆发沿着家宅中阁楼和地窖之间某种独特的垂直性展开。
屋顶象征着白天经验中的阳光与理性,地窖象征着无论白天黑夜都充满着的阴暗与非理性,两者自上而下贯穿了整个家宅的形象(尽管,这种说法在文学形象中存在一些偏差。
地窖里的人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找到吻合的形象,屋顶的理性难以培养出一个哲学家却会意外地产生“阁楼上的疯女人”。
)。
在实际生活中,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伴随着商品的普遍化,土地也成了商品”,都市居住者并不能在有限的空间内随心所欲地拥有地窖与阁楼。
巴什拉引用布斯凯的诗句描述这种状况——“这是一个只有一层楼的人:
他的地窖就在阁楼里。
”——在他看来,相对于过去的精神维度中垂直的性质,如今,“在家的状态只不过是单纯的水平性。
嵌在一层楼当中的一套住宅的各个房间缺乏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来区别和划分他们的内心价值”。
甚至可以说,“居所和空间之间的关联成了人为的。
在这种关联中一切都是机械的,内心生活从那里完全消失了”。
这个悬空的旅馆
让投宿者找不到方向
——何小竹《天堂旅馆》
现代都市中悬于高层的家宅,是居住者按照天堂的幻象构建起来的旅馆,他们把家宅想像成天堂和旅馆的中间状态,却又找不到真正的方向,最后只能把家宅沦为长期逗留的旅馆。
这些世俗的巴别塔,在巴什拉眼中丝毫不具备诗学意义,“城市里的建筑物只有外在的高度。
电梯破除了楼梯的壮举。
住得离天空近不再有任何好处”;在列斐伏尔眼中,都市住宅却充满了政治学的意味,这种类型的空间“在统一性的伪装下,是断离的、碎片化的,是受到限制的空间,也是处于隔离状态的空间”,一言以蔽之,就是资产阶级通过对于空间的规划权从而异化和奴役人。
两人观点的差别即在于,巴什拉认为现代住宅无法提供完满而自足的诗意气息与孤独感;而列斐伏尔则恰恰认为现代住宅提供了孤独感,只不过它与诗意无关,是一种受他者限制和隔离的孤独感。
巴什拉所谓的孤独感跟个人与他的记忆过分贴近有关,家宅中无处不在的个体性印记足以标示出个人独一无二的孤独感。
家宅是形象的载体,是一座收藏个人记忆的博物馆。
抽屉、箱子和柜子等家具最大限度地保存着那些凝固与附带记忆的物件,它们全都指向过去的时间。
借用柏格森的“绵延”与胡塞尔的“悬置”这两个哲学术语,巴什拉认为,空间的作用就是“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
并且,记忆穿越这些小洞,时光的飞逝就此在绵延的时间中得以悬置。
最终,这种奇妙的过程通过记忆与家宅,赋予人内心空间的广阔性。
既是幸运,也同是不幸,这种广阔性只可能内在于人。
列斐伏尔宣称,“都市空间最核心的本质或属性:
构成性中心”,即都市必须先有一个具有向心力的中心,然后以辐射状向外扩张,在使用价值相等的条件下,空间的交换价值依次递减。
这样,他所谓的“进入都市的权利”也可以理解为靠近构成性中心的权利。
两人都认可空间包含着时间,但侧重点各有不同。
巴什拉认为空间包含个人的记忆,即过去的时间;列斐伏尔则认为空间包含个人的现状,即当下的时间。
在他看来,都市空间的辐射状分布表明了它的等级制度,越是靠近都市中心,也就越是靠近权力中心和最高等级,反之亦然。
那么,在都市中购买空间的实质就是“购买了对时间的支配,也就是同时节约了时间又得到了愉悦”,节约时间是因为靠近地理中心,获得愉悦是因为靠近权力中心,而这两个中心本就合二为一。
我需要广场
一片空旷的广场
放置一个碗,一把小匙
一只风筝孤单的影子
占据广场的人说
这不可能
——北岛《白日梦》
在一个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地方,或者说在一个权力宰制型社会中,都市的构成性中心往往不是高楼云集的商业中心,而是一片政治功能极强的空旷广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入都市的权利”尚且可以通过填补不同地段的地租差额来获得,而在一个权力宰制型社会中,连这样的可能都不存在。
列斐伏尔为无产阶级振臂一呼争取“进入都市的权利”,却发现那些已经占据都市的权力者们只把这样的呼喊看作白日梦。
比起依靠资本形成等级制度的社会来,极权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壁垒森严,那里容不下一个碗,一把小匙,一只风筝孤单的影子。
在那里,占据广场的人回答列斐伏尔说——这不可能。
尽管存在着程度不同和性质差异,但不论何种社会类型,只要构成性中心遥不可及、高不可攀,满怀跻身都市中心希望的年轻人最终都将感到异常残酷的绝望。
因此,在一个经济萧条又革命无望的年代里,年轻人迫不得已地纷纷从空间的政治学退回到了空间的诗学。
他们成为了一个既非由社会属性、也非由政治身份,而是由诗学身份确立起来的新群体——御宅族。
“宅男”与“宅女”的学名是“御宅男”与“御宅女”,这份舶来品的原产地是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称呼。
所谓“御宅”,也就相当于“您的家”,这种尊称最早是流行于日本动漫迷之间的江湖切口,他们见面询问彼此的“御宅”中珍藏有什么漫画书。
因此,“御宅族”就被借代来表示那些动漫迷、游戏迷的家。
久而久之,“御宅族”的含义引申为那些耽于迷恋动漫与游戏,并且因此而足不出户终日在家的男女。
如今,广义上的御宅族即是指那些不愿意上学、上班,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接触他人,宁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的人。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涂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在一个不带任何道德与价值评判的层面上,完全有理由认为御宅族是一群任性的孩子。
他们无力改变列斐伏尔揭示的现实,而只是想涂去一切不幸(仅仅是想,而不能做;涂意味着掩盖,却并不能消除);他们无法改变大地上的格局,却只想画满窗户,在不改变现实的情况下让自己接受另一种光线。
他们渴求家宅,渴求巴什拉揭示家宅的三种隐喻意义上的形象:
鸟巢、贝壳与角落。
“鸟巢是临时性的,但它却在我们心中激发起关于安全的梦想”;“贝壳在这里成了独居着的‘要塞城市’,他是一位伟大的孤独者,懂得用简单的形象来自我防卫和自我保护。
不需要栅栏,不需要铁门,别人会害怕进来”;“角落首先是一个避难所,它为我们确保了存在一个基本性质:
稳定性”。
凡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御宅族是空间的政治学与诗学中双重孤独感的合成品。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旁敲侧击地描绘了御宅族的成因,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则详尽地勾勒了御宅族的心理图式。
谁能够从它坚实的俄式建筑中看到旧时代
的阴影?
一代人的梦境却从这里开始。
如今,当我站在院子中,回首童年,
一切那么遥远,像从月亮到地球的
距离。
哦,我的母亲,已度过她生命
的黄金岁月,成为一个衰弱的老人。
而惟有那些桉树长得更高更粗,枝叶遮天。
——孙文波《铁路新村》
尽管如此,我认为御宅族的普遍情绪既不会像是列斐伏尔高亢激昂的文风,也不会像是巴什拉温情动人的语句。
不论是端详如今安居的家宅,还是年老之后回眸曾经的旧宅,御宅族想必都会透露出这首诗中的忧郁气息,它来自对于这个时代不动声色的绝望。
而在东方,这样诗学多为自然的。
植物、动物、鸟虫、山川及部分人造物如琴、棋、书、画。
一种整体表现的诗和直觉把握的诗学。
其隐喻性与转喻性,不同于西方诗学的垂直性,而是一种平面展开的散点。
如陶潜的《饮酒•其五》、柳宗元《江雪》、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苏轼的《题西岭石壁》,一直到马致远的《天净沙》等等。
甚于到中国当代最后的田园诗人海子的现代诗歌,其作为隐喻与转喻的形象,多为以风为马的自然形象。
梵高曾说:
生活似乎是圆。
他的向日葵,他的云团,他的宇宙都燃烧的圆球体。
中国的四合院的回环式、线与点;中国的高台建筑与亭台楼阁塔建筑的结构,也是深深进入诗的结构。
想象与幻想,从四合院天井望星空的梦幻;登上高台或塔俯视大地山川的视角,也是建筑对诗歌的进入。
如果运用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来析理东方的自然诗学,那也是相当的有意思的。
当然,这便为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的另一种仿写的文本:
空间意识的诗学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