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的牛津哲学.docx
《二战前的牛津哲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二战前的牛津哲学.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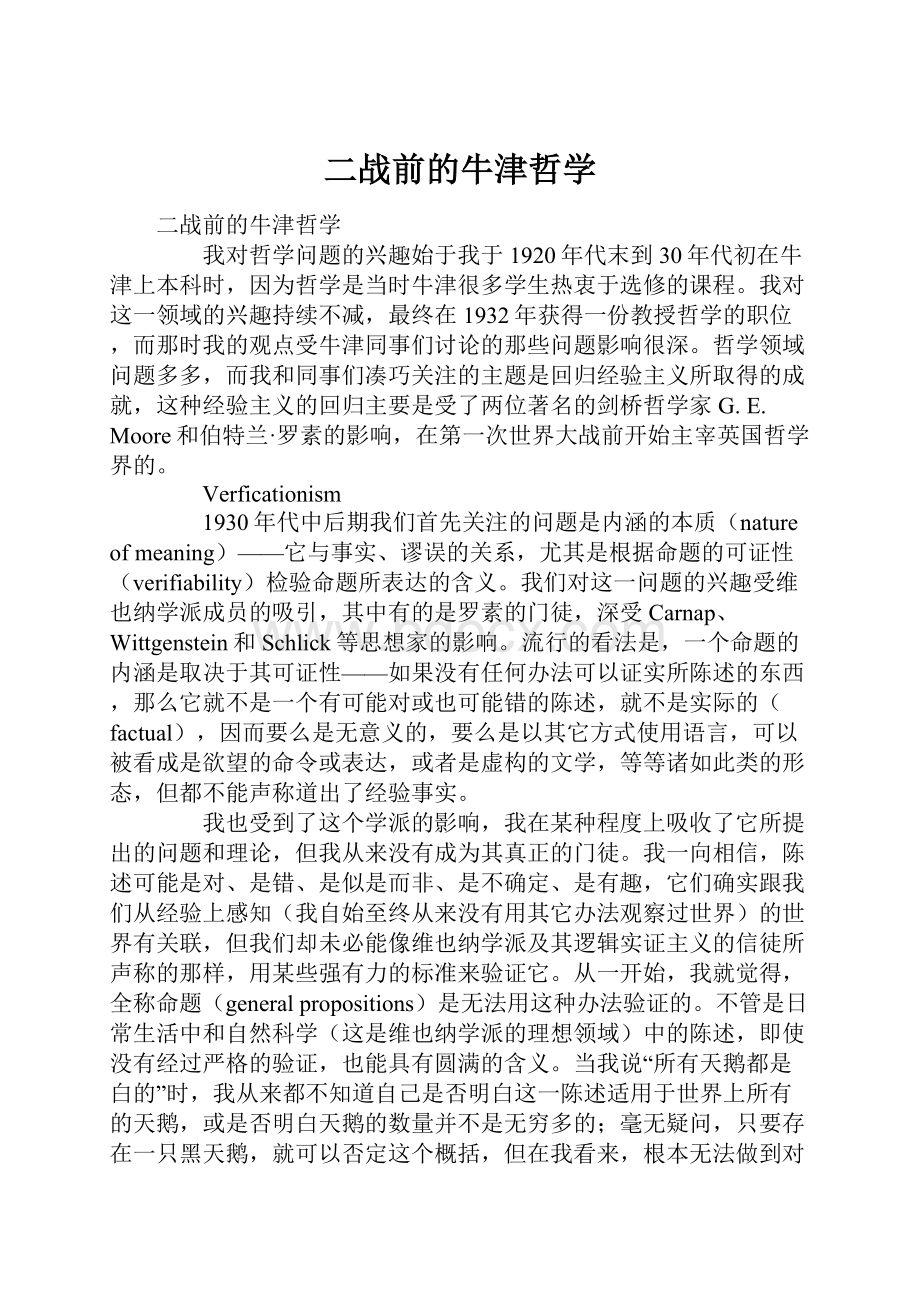
二战前的牛津哲学
二战前的牛津哲学
我对哲学问题的兴趣始于我于19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牛津上本科时,因为哲学是当时牛津很多学生热衷于选修的课程。
我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持续不减,最终在1932年获得一份教授哲学的职位,而那时我的观点受牛津同事们讨论的那些问题影响很深。
哲学领域问题多多,而我和同事们凑巧关注的主题是回归经验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这种经验主义的回归主要是受了两位著名的剑桥哲学家G.E.Moore和伯特兰·罗素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主宰英国哲学界的。
Verficationism
1930年代中后期我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内涵的本质(natureofmeaning)——它与事实、谬误的关系,尤其是根据命题的可证性(verifiability)检验命题所表达的含义。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受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吸引,其中有的是罗素的门徒,深受Carnap、Wittgenstein和Schlick等思想家的影响。
流行的看法是,一个命题的内涵是取决于其可证性——如果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证实所陈述的东西,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有可能对或也可能错的陈述,就不是实际的(factual),因而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以其它方式使用语言,可以被看成是欲望的命令或表达,或者是虚构的文学,等等诸如此类的形态,但都不能声称道出了经验事实。
我也受到了这个学派的影响,我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它所提出的问题和理论,但我从来没有成为其真正的门徒。
我一向相信,陈述可能是对、是错、是似是而非、是不确定、是有趣,它们确实跟我们从经验上感知(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用其它办法观察过世界)的世界有关联,但我们却未必能像维也纳学派及其逻辑实证主义的信徒所声称的那样,用某些强有力的标准来验证它。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全称命题(generalpropositions)是无法用这种办法验证的。
不管是日常生活中和自然科学(这是维也纳学派的理想领域)中的陈述,即使没有经过严格的验证,也能具有圆满的含义。
当我说“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时,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明白这一陈述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天鹅,或是否明白天鹅的数量并不是无穷多的;毫无疑问,只要存在一只黑天鹅,就可以否定这个概括,但在我看来,根本无法做到对其进行充分的实证的验证;即便可以充分验证,说这个陈述没有意义,也是荒唐的。
对于假言命题(hypotheticalpropositions)同样如此,未实现的假说(unfulfilledhypotheticals)更是如此,而坚持说可以通过经验观察来断定它们是真是伪,是非常荒谬的;然而,显而易见,它们却依然是有意义的。
我想到过很多这类陈述,从字面上看显然都有意义,但是其意义却不能通过直接的经验观察——感觉的世界——这一狭隘标准的验证。
结果,尽管我活跃于这些讨论(实际上,后来被称为牛津哲学的思想就是那些夜晚从我的宿舍中开始形成的,当时参加聚会的有后来声名大振的哲学家A.J.Ayer、J.L.Austin和StuartHampshire,他们都受到牛津经验主义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牛津实在论的影响——也就是说相信外部世界是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但我却始终是一个异端,尽管大家关系很好。
我从来没有偏离过我当时就形成的看法,一直相信,言语所能表达的必然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不存在另外的现实——尽管如此,可证性并不是唯一的判断知识、信仰或假说的标准,相反倒可能是最似是而非的判断标准;我后来始终坚持这一点,它也在我思想的方方面面打下烙印。
我跟年轻的同事们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诸如此类的命题:
“这种粉红色(图案)更象这种朱红色,相比之下不是很像这种黑色”。
抽象地说这显然是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反驳它——各种色彩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
但是,全称命题不能被认为是先验的(apriori),因为它从形式上不能从任何定义出发,因此它不属于逻辑或数学这些形式学科,这些学科都是从先验的命题出发,因而说全称命题是先验的等于是同义反复。
因此我们得从经验领域中寻找一个普遍的真理。
“粉红色”、“朱红色”等等饿定义是什么?
没人知道。
颜色只有在看到的时候才能被认出来,因此它们的定义只能是归入用例证解释的那一类中,从这样的定义出发得不出任何逻辑的推论。
这就很接近康德提出的综合先验命题(syntheticaprioripropositions)这一古老问题了,我们有好几个月时间都在讨论这一问题及类似问题。
我确信,我的命题如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先验命题,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其自相矛盾就难以理解。
我不知道我的同事们后来是不是还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但是当时着确实是我们很认真讨论的问题。
它与罗素在一本题为《经验主义的限度》一书中所论述的观点相一致。
现象论
我当时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现象论(phenomenalism)——就是说人类经验是否如英国哲学家柏克莱和休谟(密尔和罗素的著作中也有这种印迹)所说的,只能被局限于感觉所提供的范围的问题,或者说是否存在着一个独立于可感知的经验的现实。
在洛克及其追随者等哲学家看来,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我们不能直接地接触它——这个现实形成了我们的可感知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是我们当下可以直接把握的。
另有一些哲学家则主张,外部世界是一种物质的现实,可以被直接感觉到,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也可能被曲解,这就叫做实在论,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我们的世界完全是由人的才能——理性、想象力等等之类的东西创造的,这就是唯心论,我从来也不信这套说法。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形而上学的真理——不管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及康德以自己独特方式阐释的唯理论的真理,还是(客观)唯心论的真理,其开山始祖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一直传承不绝。
因此,意义、真理和外部世界的本质是都我思考过的问题,甚至也写过文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甚至还见诸报章。
对我曾产生过非常大影响的另一知识现象是哲学家普遍地追求绝对的确定性,寻求没有任何疑问的答案,追寻完全的知识可靠性的想法。
我从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种虚幻的希望。
不管一个结论或直接的证据看起来立论多么坚实、普适、必然、“不证自明”,但是总是可以设想,必有某种东西将更改它甚至颠覆它,尽管我们此刻可能无法想象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
有很多哲学正是建立在这种虚幻的希望之上的,对此现象的这种怀疑后来逐渐主宰我的思想,各种思想元素由此形成了一种全新而不同的连结。
我在教学和探讨上述哲学问题之余,还接受委托撰写一本马克思传记。
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从来没有给我留下有特别的原创性或有趣的印象,不过研究他的观点使我得以上溯他的前人,尤其是18世纪法国哲学——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地反对教条主义、传统主义、宗教、迷信、无知和压迫。
我对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曾经为自己设定的使命颇为钦敬,那是个伟大的使命:
即把人类从黑暗——即教会、形而上学、政治等等的黑暗——中解放出来。
尽管我毕生都在反对他们的某些共同信念的基础,但我从来没有丧失对这一时代的启蒙运动的钦佩,对他们我一直是心有戚戚焉:
我之成为其批评者,抛弃其经验主义的缺陷,正是其逻辑和社会的某种结果;我认识到,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教条主义,部分正是由于他们背弃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信念。
思想与政治理论的历史
二战期间,我曾在英军中服役。
退役回到牛津后,我完全被两个重要问题吸引住了:
一是一元论(monism)——从柏拉图至今的西方哲学的中心论题(thesis),二是自由概念的含义与应用。
在这两个题目上我投入了很大精力,它们塑造了接下来多年我的思想。
一元论
爱尔维修、霍尔巴赫、d“Alembert、孔狄亚克等哲学家及Yoltaire、卢梭这样的天才宣传鼓动家,为他们那个世纪及以前时代的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所折服,他们都相信,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揭示关于社会、政治、道德和个人生活的根本真理;在研究外部世界,这种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百科全书学派(Encyclopaedists)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获得这种知识的唯一关键所在,卢梭等人则相信可以通过內省(introspective)的方法发现永恒的真理。
尽管他们有这种区别,他们仍都属于同一代人,他们都确信,这个时代正在通往解决所有自人类诞生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
在这种信念下面隐含着一个广泛的论题:
对于一切真正的问题,必然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而且是只有一个,所有其它的答案都是错误的,要不然的话,问题就不是真问题。
必然存在着一条道路,可以引导思路明晰的思想家对这些问题得出正确的答案;道德、社会、政治领域跟自然科学没有区别,不管其所采用的是不是同样的方法;一旦找齐了占据(或者应该占据)人类的最深层面的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全部正确答案,最终得出的的结果就是对现存一切问题的终极解决之道。
当然,我们也许永远也找不到这些答案:
人类也许太多地受他们的激情、愚蠢或运气不好的制约,而无法找到全部答案;这些答案或许也太过艰深,而我们又缺乏发现的手段,或者发现的技术太过复杂,然而他们仍然相信,只要问题是真问题,那么答案就必然存在。
假如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后代也许可以弄明白或者也许古代的智者已经掌握了,也许他们也没有掌握,那么也许天堂里的亚当曾经弄清楚了,如果他也没有,那没准天使懂了,如果甚至连天使都不懂,那上帝必然知晓——总之,答案是一定存在的。
如果对于社会、道德和政治问题的答案可以被发现,那么,就去了解它们,因为它们是真理——人们就不能不遵循它们,因为它们没有别的想望。
然后,就可以构思一种完美的生活,这种生活也许不是可以实现的,但在原则上,是可以形成这样的概念的——事实上,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坚信是有可能发现重大问题的唯一真正的答案的。
相信这种信条的,不只局限于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尽管其它人提出的方法也许有所不同。
柏拉图就相信,数学是通往真理之大道,亚里士多德相信应该是生物学;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从圣经中、从受到神启的先知的宣示和神秘家的幻想中追寻答案;另有些人相信实验室和数学的方法能够解决问题;还有些人,比如卢梭相信,只有未被玷污的人的灵魂、天真无邪的孩子、纯朴的农民才能了解真理——他们对真理的了解也优越于被现代文明毁灭了的污浊的人们。
(尽管有这些不同,)然而他们就跟法国大革命后他们的追随者一样,或许都假定,比起他们的更天真和更乐观的先辈来说,自己更难掌握真理了,但仍然一致认同一点:
到彼时仍在寻找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最终是可以找到的,人们是可以找到如何生活和在道德规范、政治生活、政治组织和人际关系等领域该如何行动这样的问题的答案的,然后完全可以根据以正确的方法所发现的真理组织起来,不管这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从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改良者和革命家所信奉的就是这样一种哲学母题(philosophiaperennis)。
这正是主宰两千年来人类思想的核心信念。
如果不存在真正的答案,那么怎么可能获得任何学科的知识呢?
这是很多世代欧洲理性、实际上是精神思想的核心所在,不管人们的差异有多大,不管文化有什么差异、道德、政治观点分歧多深,但形形色色的学说、宗教、伦理、观念无不坚信:
对于困扰人类的最深层次的问题,一定存在着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向对这种普遍的信念表示怀疑,我确实对此不以为然。
这也许是气质使然,但事实就是如此。
维科(GiambattistaVico)
我的思想第一次发生震动是我在阅读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的著作时。
在我看来,他是头一个构思文化观念的哲学家。
维科想理解历史知识和历史本身的本质:
要研究外部世界我们必须依靠自然科学,但是自然科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石头、桌子、星星、分子之类物体的变动(behaviour)的记录。
而在思考历史的时候,我们超越了这种机械的变动,我们想理解人类是如何生活的,这就意味着要理解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恐惧、希望、野心、爱憎——他们向谁祈祷,他们如何在诗歌、艺术、宗教中表达自我。
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人,在这些场合,我们就是在理解我们内在的生活。
我们知道一块石头、或一张桌子如何运动,是因为我们观察它,提出假说,并进行验证;但是我们不知道石头为什么希望成为现在这样子——事实上我们认为石头不可能有愿望,不可能有任何意识。
但是我们却确实知道我们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我们追求什么,什么让我们遭受挫折,如何表达我们心底的感受和信仰;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要多于我们所能对石头或溪流的了解。
真正的知识是那种回答事物为何如此的知识,而不仅仅只是告诉人们事物是如此,我们越是钻研,我们越清楚地认识到,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提出的问题是不同于罗马人提出的问题的,罗马人提出的问题是不同于基督教的中世纪或者是17世纪科学文化或者是维科自己所处18世纪所提出的问题的。
问题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如果需要表达则使用的语言也不同;对一套问题给出的答案,不能回答其它文化的问题,与之可能都没有多大关系。
当然,维科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相信,惟有天主教能提供答案。
但是,无论如何,这并没有妨碍他明确阐述了一种原创性的观念:
5世纪的希腊人所关注的东西截然不同于印第安人或中国人或18世纪实验室中的科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文化不同,则他们的观点就不同,因此对于不同人的问题,并不存在一个普适的答案。
当然,存在着某种共通的人性,否则的话,一个时代的人就无法理解另一个时代的文学、尤其是其法律,作为法学家,维科精通法律。
但这并不能阻止存在着广泛多样的文化经验,因此在某一个文化体内部一类人的活动是跟另一群人的活动有关的,但他们不大可能跟另一文化体中类似的活动有如此紧密的关联。
赫尔德
后来我深入阅读了跟他有关的思想家的著作,即德国哲学家、诗人赫尔德(JohannGottfriedHerder)。
赫尔德并不是第一个起而反对当时法国人的观念的人(他的老师JohannGeorgHamann当可享有此荣誉):
这些法国哲学家相信。
存在着一切时代一切地方的所有人都秉持的普适的、永恒的、无可置疑的真理,而差异完全可归罪于失误或幻想,因为真理是唯一的和普适的——`quodubique,quodsemper,quodabomnibuscreditumest.赫尔德则相信,不同的文化对其重大问题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相比于外部世界,他更感兴趣的是人文学科、精神生活,他开始确信,葡萄牙人眼里的真理并不一定是波斯人心中的真理。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同样的话,但即使是他也相信,人是受环境即他所说的“气候”塑造的,他最终仍然是一位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他相信,即便对于不同地区的暂时性问题的答案可能不同,但核心的真理是永恒的。
赫尔德则论证了每种文化都拥有它自己的“引力中心”(centreofgravity);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参照点;不同文化为什么彼此竞争是找不到理由的——因而必须要有普遍的宽容——而统一(一致,unification)必导致毁灭。
再没有比帝国主义更坏的东西。
罗马为了建造一个统一的罗马文化而毁灭小亚细亚当地文明,实足是犯罪。
世界是一个大花园,其中百花齐放,众树齐长,各有其道,各有其资格和权利、过去和未来。
由此必然得出推论:
不管人们有多少共同点——当然人类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共同本性——并不存在什么普适、对此一文化与对彼一文化同样有效的正确答案。
赫尔德是文化民族主义之父。
他不是政治民族主义者(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发育出这种民族主义),但他坚信文化的独立自主,坚信要维护每种文化的独特个性。
他相信,归属某种文化、即把一个群体、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联结为一体的东西,是基本的人类需求,与人之欲求食物、水或自由居于同一层次,这种归属一个共同体的欲求是发达的、成熟的人类生活的基础,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他人说的话你能理解,你可以自由地迁徙,在那儿你可以与他人实现感情以及经济、社会、政治的结合。
赫尔德不是相对主义者,尽管总有人这样形容他。
他相信存在着基本的人类目标和行为规则,但是它们在不同的文化体中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因此,不同的文化可以具有类似的、相同的观念,从而此一文化可被彼一文化所理解,然而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又是不能彼此混淆的,人类不是一种,而是有多种,对于社会问题的答案也有多种,尽管这些答案之核心本质也许只有一个,或者是彼此相同的。
浪漫主义及其余绪
这种观念被浪漫主义者进一步发挥,他们提出了某种全新的并且令人不安的东西:
理想并不是写在天国、人必须予以理解、模仿和实践的客观的真理,相反,它们是人创造出来的。
价值不是被找到的,而是制造出来的,不是被发现的,而是生成的——这就是有些德国浪漫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与之相对的是肤浅的法国人所相信的客观主义的普遍化的趋势。
独特性才是至关重要的。
德国诗人用德语写诗,用这种语言写作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创造这种语言:
他并不仅仅是用德语写作的人。
德国艺术家是德国绘画、诗歌和舞蹈的创造者——余此类推。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AlexanderHerzen)曾经问:
“一首歌在演唱之前在哪儿?
”是啊,在哪儿?
答案是“根本不存在”——人们通过演唱、通过作曲创造了它。
同样,生命也是那些生活着的人一步一步地创造出来的,这是对道德和生命的某种美学解释,而不是应用外部的模式来解释。
创造就是一切。
从这一点繁衍出形形色色的思想运动——无政府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英雄崇拜。
我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也许不是有意识地。
除此之外,还有个问题,“我”是谁?
在拜伦式的浪漫主义者看来,“我”确确实实是个个人,是局外人(outsider),是探险者,是歹徒(theoutlaw),他公然挑战社会及其公认的价值而只随己心之所欲——这也许是他的宿命,但这也比千篇一律、比受制于庸才要好。
不过,在另一些思想家眼里,“我”则是某种更加形而上学的东西。
它是属于某个集体的——民族、教会、政党、阶级,一个大厦我只是它身上的一块石头,或者是一个组织,我只是其微不足道的组成分子。
它才是创造者,而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我归属于这一运动、种族、民族、阶级、教会;我不会设想自己是这个超人中的具体实在的个体,我的生命已经有机地跟其结合为一体。
这就是德国民族主义:
我做这件事不是因为它好或正确或者因为我喜欢这样——我之所以做这事,只是因为我是个德国人,这是德国的生活方式。
现代存在主义也是如此——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把自己投入到这种存在形式中。
没有什么东西能塑造我,我不会因为某事是我遵守的客观命令或我必须坚持的普适的规则而去做此事;我做某事,只是因为我像按自己的意愿创造自己的生命;我自己要成为现在的样子,我给予它方向,我为其负责。
否定普遍的价值、强调人首先是某一超级自我(super-self)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忠于这一超级自我,是欧洲历史上相当危险的趋势,它已经导致了现代历史上巨大的破坏和灾难。
现在已经到了从政治上反思早期德国浪漫主义及其在法国等地的门徒之理论的时候了。
我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这形形色色的超我(super-egos)观念,但是我得承认他们在现代思想和历史中的重要性。
“没有我只有党”、“没有我只有教会”、“国家不管对错都是国家”之类的口号,已经在人类思想的核心信念上割开了创伤——这一信念即如上所述:
真理是普遍的、永恒的、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所有人——并且再也没有得到康复。
人类不再被看作是客观的,而被看成是主观的,是一种变动不居的精神,自我创造、自我推进,是一出自我创作的多幕戏剧,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人最终将达到某种完美状态——所有这些,都源自浪漫主义革命。
我从小就拒绝这种对人类生命的高度形而上学的解释——我始终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只了解我所能经历的事,只思考所能体验的东西,而从来不会相信超个人的实体——尽管如此,我得承认,它对我还是有某种影响,详见下文。
多元主义
我的结论是,存在着多元化的理想,就像存在着多样性的文化和气质性情一样。
我并不是相对主义者;我不是说“我喜欢咖啡加奶,你喜欢不加奶,我喜欢仁慈,你喜欢集中营”——对此我们可以各有所好,不能彼此压服对方或非要一致。
我相信这是虚伪的、错误的,但是我确实相信人们所追求的价值是多样的,这些价值各不相同。
这些价值并不是无穷多样的:
人类价值的数量、在保持我的人类外表和我的人类特征的前提下能够追求的价值的数量是有限的——我们可以说有74种,也许是122种,或者是26种,但确实是有限的,不管是多少。
这种价值之有限性所带来的结果是,如果一个人追求这些价值中的某一种,而我尽管没有追求这种价值,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要追求这种价值,或者在我看来,在他自己的境况中是什么东西促使他追求这种价值的,由此而保证了人类理解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些价值是客观的——就是说,它们的本质及对它们的追求,都是人之成为人的本质的一个部分,它是客观给定的。
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而不是猫狗桌椅,这一事实是客观的事实;在这类客观事实中就包括存在着某些价值,人们要维系人之存在就只能追求这类价值。
如果我是一个具有充分想象力的男人或女人(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就能参与到某种价值体系中,此一体系虽然不是我自己的,但是我却能够想象,正在追求它的人能够同时保有人的本质、仍然是我可以与之沟通的生物,是我与之具有某些共同价值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必然具有某些共通的价值,否则他们就不成其为人,而一些不同的价值最后也会逐渐缩小差异直到分歧消失,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因此,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多样的价值是客观的,是人性的本质之所在而不是人们主观想象之随意构造。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有人追求一套憎恨别人的价值,我觉得这种憎恨对我生活或容忍的唯一一种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我自己或他人,我可能会攻击这种价值——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向其开战。
但是我仍然承认它是一种人类的追求。
我觉得纳粹的价值是可恶的,但是我依然能够理解它,假定信息被大大扭曲、人们对现实持错误的信仰,那么人们肯定会相信他们是唯一的救赎。
当然他们他们必然要受到攻击,如果需要的话会爆发战争,但是我不认为纳粹分子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变态或者是精神病,相反他们是错误透顶,完全曲解了事实,比如他们相信有些人是劣等人,或者某个种族是是重要的,或者只有日耳曼人是真正有创造性的,如此等等。
我能够明白,只要你受到足够的错误的教育,受到广为流传的幻想或错误的影响,人虽然还是人,却会相信这些,并犯下謦竹难书的罪行。
。
如果多元主义是一个正当的观念,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互相尊重就是有可能的,而不必彼此敌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宽容和自由主义,而一元论(只有一套价值是正确的,其它的都是错误的)或相对主义(我的价值是我的,你的价值是你的,如果我们想碰撞,那就太可惜了,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的是正确的)却是不会带来这种后果的。
我的政治多元主义思想是在阅读维科和赫尔德、理解浪漫主义的渊源的过程中形成的,暴力的、病态的浪漫主义形态走得太远了,威胁着人类的宽容。
现在谈谈民族主义:
在我看来,归属于一个民族的感觉是很自然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甚至都不应该批评。
但其狂热的状态——我的民族比你的民族好,我知道应该如何塑造世界,你必须服从我,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低我一等,因为我的民族是是高等的,你的民族是低等的,比我的民族低等,所以只能作为我随意加工的材料,我的民族是唯一有资格创造最好的世界的民族——这就是病态的极端主义,它必然会导致,事实上已经导致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它是根本与我所竭力阐述的多元主义不相容。
顺便提一下,还有一些我们已经公认的某些价值,也可能是早期浪漫主义创造出来,而在那之前还不存在:
比如多样性(variety)就是一个好东西,在一个多样性社会中,人们持有多种看法,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彼此宽容,这种社会要比把一种看法强加于所有人的那种独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