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经中的女性意识.docx
《浅谈诗经中的女性意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浅谈诗经中的女性意识.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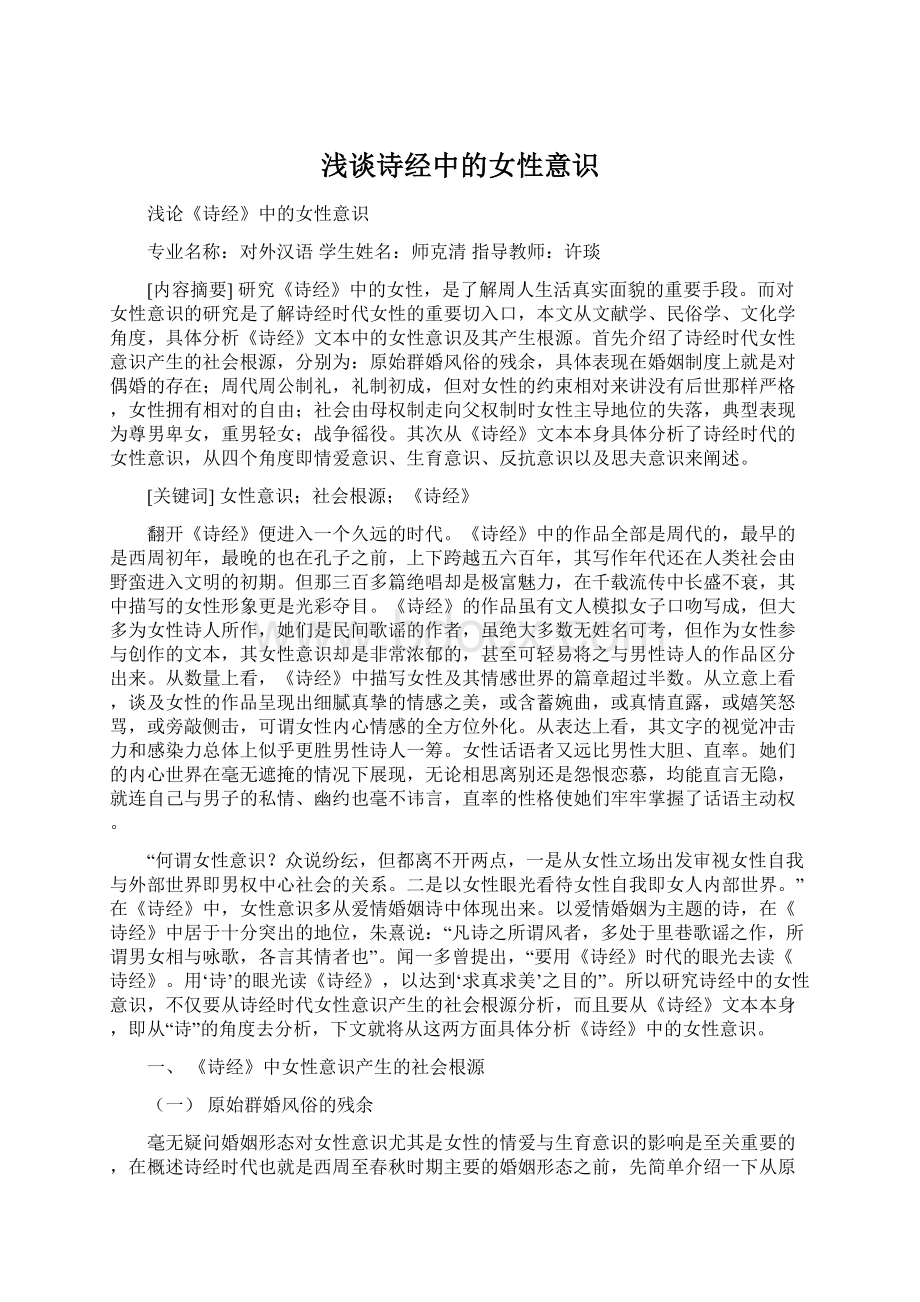
浅谈诗经中的女性意识
浅论《诗经》中的女性意识
专业名称:
对外汉语学生姓名:
师克清指导教师:
许琰
[内容摘要]研究《诗经》中的女性,是了解周人生活真实面貌的重要手段。
而对女性意识的研究是了解诗经时代女性的重要切入口,本文从文献学、民俗学、文化学角度,具体分析《诗经》文本中的女性意识及其产生根源。
首先介绍了诗经时代女性意识产生的社会根源,分别为:
原始群婚风俗的残余,具体表现在婚姻制度上就是对偶婚的存在;周代周公制礼,礼制初成,但对女性的约束相对来讲没有后世那样严格,女性拥有相对的自由;社会由母权制走向父权制时女性主导地位的失落,典型表现为尊男卑女,重男轻女;战争徭役。
其次从《诗经》文本本身具体分析了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从四个角度即情爱意识、生育意识、反抗意识以及思夫意识来阐述。
[关键词]女性意识;社会根源;《诗经》
翻开《诗经》便进入一个久远的时代。
《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是周代的,最早的是西周初年,最晚的也在孔子之前,上下跨越五六百年,其写作年代还在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初期。
但那三百多篇绝唱却是极富魅力,在千载流传中长盛不衰,其中描写的女性形象更是光彩夺目。
《诗经》的作品虽有文人模拟女子口吻写成,但大多为女性诗人所作,她们是民间歌谣的作者,虽绝大多数无姓名可考,但作为女性参与创作的文本,其女性意识却是非常浓郁的,甚至可轻易将之与男性诗人的作品区分出来。
从数量上看,《诗经》中描写女性及其情感世界的篇章超过半数。
从立意上看,谈及女性的作品呈现出细腻真挚的情感之美,或含蓄婉曲,或真情直露,或嬉笑怒骂,或旁敲侧击,可谓女性内心情感的全方位外化。
从表达上看,其文字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总体上似乎更胜男性诗人一筹。
女性话语者又远比男性大胆、直率。
她们的内心世界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展现,无论相思离别还是怨恨恋慕,均能直言无隐,就连自己与男子的私情、幽约也毫不讳言,直率的性格使她们牢牢掌握了话语主动权。
“何谓女性意识?
众说纷纭,但都离不开两点,一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女性自我与外部世界即男权中心社会的关系。
二是以女性眼光看待女性自我即女人内部世界。
”在《诗经》中,女性意识多从爱情婚姻诗中体现出来。
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诗,在《诗经》中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朱熹说: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处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闻一多曾提出,“要用《诗经》时代的眼光去读《诗经》。
用‘诗’的眼光读《诗经》,以达到‘求真求美’之目的”。
所以研究诗经中的女性意识,不仅要从诗经时代女性意识产生的社会根源分析,而且要从《诗经》文本本身,即从“诗”的角度去分析,下文就将从这两方面具体分析《诗经》中的女性意识。
一、《诗经》中女性意识产生的社会根源
(一)原始群婚风俗的残余
毫无疑问婚姻形态对女性意识尤其是女性的情爱与生育意识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概述诗经时代也就是西周至春秋时期主要的婚姻形态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婚姻的演化过程。
我们知道,人类经历了原始群婚、血族混、亚血族婚、对偶婚这些阶段然后到一夫一妻制,传统的婚姻形态最后定型。
对于原始早期阶段的婚姻形态,《吕氏春秋·侍君兰》中这样描述“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而不知父,无亲戚兄弟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
”可以想象在数万年前,生产力极其低下,为了生存人类以群居方式生活于极其有限的空间,人与人的交往也极其有限。
这个时期人类有的只是生存的本能反应,不可能有对两性关系的约束与规范,在两性关系上,更多的是基于本能,基于物种繁衍的需要。
《列子·汤问》记载远古时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
”这种乱婚没有特定的两性规范,构不成家族、亲族,这种蒙昧时期没有任何规范约束的两性结合我们称为原始群婚。
后来经过血族婚与亚血族婚的的发展演变,对偶婚出现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这样描述对偶婚:
“一个男子在许多个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女子来说,也是她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
”对偶婚仍是多夫多妻的生活,所生子女依然属于女方氏族,但相对于之前的婚姻形态,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约束和规范,是向一夫一妻制过度的婚姻形态。
西周时期,进入封建社会,父权制的被确立致使婚姻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原地区在婚制上已经摆脱蒙昧时代的群婚制和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制,进入了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时代。
可以说,到一夫一妻制,传统和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形态最后定型。
虽则如此,由于西周是由野蛮向文明过度的阶段,婚制也呈野蛮向文明的逐渐过度的形态,而不是突变。
群婚风俗的残余在当时社会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一点体现在《诗经》篇章中便是对“仲春三月,令会男女的野合婚”的描写上。
野合是指男女在野外相识,自由幽会甚至可以直接结合的一种行为。
野合带有原始群婚的痕迹,是原始群婚的残留,它对两性关系的约束很小,只要男女双方愿意便可在野外交合。
在春秋时代这种野合婚是十分盛行的,众所周知,孔子就是其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的,有《史记·孔子世家》载明“泆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周礼·地官·媒氏》载: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罚之。
”这就是说,当时的统治者对这种风俗是认可的。
当时的礼也认可这种风俗。
《太平御览》引《韩诗章句》云:
“当此盛流之时,士与女众芳执兰,拂除邪恶。
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与此水之上,招魂续魂,除拂不详。
”其记载风俗与《溱洧》相同,可见三月上巳节不假。
民间男女在盛大的节日里欢会,除了拂凶辟邪之外,还为了野合之便。
在《诗经》文本中反映男女野合调情的例子很多,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
在野合婚中,性自由与求子嗣是十分明显的特点。
仲春之月,万物复苏,古代民间相信这个时节人们的生育是顺利的、兴旺的。
因此,按照风俗与政策,民间男女尤其是超龄未婚者纷纷出来寻找野合的机会,已达到求子嗣的目的。
可以说,诗经时代野合婚的普遍来自统治阶级强制政策的施行与民间对求子嗣心态的认同。
为了有男丁传宗接代,甚至已婚而未得子嗣者(这里专指男性子嗣)也被允许参加。
据《孔子家语》载:
“梁泆娶鲁之施氏,生九女。
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与颜氏征在。
”说明孔子之父在与其母野合之前已有一妻一妾,并且生有一子九女,由于独子身有残缺,于是与颜真在野合。
孟子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无后”定义在一个十分重大的“罪名”上。
的确,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子孙后代的繁衍与发展,认为子孙满堂是家庭兴旺的标志,多子多孙是光耀门楣的希望。
这一“无后为大”的观念,是诗经女性生育意识产生的主观原因。
古风犹存的野合婚除去原始群婚的影响外,其很大目的也是为了求嗣。
在婚礼过程中,无论庶民还是贵族,都有各种祈愿夫妻和睦、早生贵子的仪式和祝辞。
比如纳吉、纳征都以雁为礼,寓其“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象征女子到了适当的年龄应当及时完婚育子。
(二)礼制初成时期女性的相对自由
诗经时代女性意识的存在于当时女性拥有相对自由是分不来的。
《诗经》的诞生是建立在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基础上,整部《诗经》占主流地位的显然是礼乐文化,这是由时代决定的,孔子说: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
”西周初期,统治者汲取了殷商败亡的重大教训,出于统一局势的政治方向,对上古社会的宗教礼节、行为习惯和生活规范方面进行加工改造,规范成型,制定出一整套维护国家制度和统一思想观念的礼乐制度,并愈渐发展成熟趋于完备。
《礼记·明堂位》曰: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诸侯于名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可见,当时礼乐文化已得到很大发展,反映到《诗经》婚恋诗中,便是婚恋婚俗的礼教化已经成为基础和主流,在周代生活中广泛存在。
尽管如此,对普通百姓而言仍有相对的自由与宽松,这便是诗经中那些女性表达真情实感和行为自由得以产生的客观环境之一,虽然当时对女性有许多礼制规范,例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礼之制,民间男女的自由恋爱常常受制于此礼,但女性在周代仍有很大的发言空间,女性能以诗歌宣泄真实情感,能够借由诗歌表达内心的欲求与不满。
《礼记·王制》言凡民间之风俗与礼制不相抵触时,亦能受到官方的尊重,“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奇,无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意思是说,各民族之间因为地理环境与气候状况有差异,所以各地有不同的风俗,执政者对于各地不同的风俗,抱持的态度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宽大与包容,当正统的婚姻礼法与民间自由恋爱相冲突时(例《诗经·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等,于这些诗句,都能看到自由恋爱与婚姻之礼的对立),只要民间婚姻符合统治者的政策就可以了,至于是否符合贵族那些婚配的标准,这对统治阶级而言,无关紧要。
因此,礼制对于民间婚姻的指导与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就显得宽松和开放,正如李泽厚指出的,周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变而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与人民性。
”所以在民间的婚恋当中,男女相悦的情感是可以直接表达的。
总之,诗经时代父权制刚刚建立,礼制和道德规范对女子的要求远不及后代苛严,对女子的道德要求是比较宽松的。
(三)尊男卑女的社会文化制度
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是整个封建社会在男女关系上一开始就具有的突出特点。
母权制被推翻,父权制被确立,导致男女之间绝对的不平等。
以婚姻为例,几千年的发展趋势是社会越发展,男女之间的地位越不平等,女性被歧视与摧残的程度越严重。
自从女人离开自己的家出嫁到男方这种男娶女嫁的婚姻形式被确立之后,妇女就开始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成为丈夫的附庸与玩偶。
“夫,至尊也。
”一语道出了丈夫在婚姻与家庭中的主宰地位,妻子则依附于丈夫,严守礼制对她们的种种要求与约束。
《礼记·郊特牲》规定妇女“幼从兄弟,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天官》中有执掌教导“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四德的“九嫔”。
丈夫可以娶妾或休妻,妻子则必须严守贞操无权休夫。
另一方面,女子出嫁后既没有继承父家财产的权利也没有继承夫家财产的权利,因此出于宗祧传承、保证家庭财产有男性后代来继承的目的,男性后代比女性后代也要受重视得多。
(四)战争徭役给女性心灵的创伤
诗经中女性的幽怨意识有相当一部分是与丈夫的分离造成的,与丈夫分离的原因便是战争徭役。
战争徭役是周代社会历史生活的重要内容,它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当时整个社会都卷入了残酷的战争的漩涡,没有哪个阶层能够逃避开。
先秦时代是中国社会最为分化与动荡的历史阶段,集中表现在邦国之间剧烈而残酷的兼并战争与中原地区与周边“四夷”的长期军事冲突上。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封建考》中记载:
春秋时代有国一百三十一,至战国时期,仅存齐楚韩赵齐魏燕七国。
从夏禹时期的万国到战国七雄的巨大变局,无疑是王室与诸侯之间长期的武力征伐兼并的结果,这种频繁而激烈的征战杀伐,形成了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于戎”的鲜明的社会特征。
这种社会现实必然会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诗经》中的女性思夫意识便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
这类思妇思夫的诗篇在诗经中也不少,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具体分析。
二、《诗经》中的女性意识
(一)《诗经》中女性的情爱意识
自《诗经》始,以女性情爱为表述对象或话语中心的文本在所皆有,它们以各自的方式讲述关于女性的性爱意向。
可以说,《诗经》开启了女性情爱的第一章,是楚辞、唐宋诗坛中女性性爱的开源发流处。
在之前的母系社会中,女性是生命、权威和力量的象征,当时的情爱意识以女性为中心而形成,女性不仅被崇拜、爱慕和尊敬,还有着主宰自己感情世界的自由。
诗经时代,女权的失落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情爱关系中,女性虽还不曾受到壁垒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吃人礼教的迫害,但却不再占据着绝对主动的地位,有的甚至还倍受凌辱和抛弃。
虽则如此,在《诗经》中,女性的情爱意识已初步形成,这从大量的爱情诗章中可窥见一斑。
《诗经》中的爱情诗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的百般滋味:
有写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有写情侣游春的《郑风•溱洧》,有写野合欢娱的《召南•野有死麕》,有写挥之不去的情愁的《周南•卷耳》,有写痴盼情郎的《郑风•子衿》,有写情侣斗气的《郑风•狡童》,有写距离带来的绮思和惆怅的《周南•汉广》,有写表现意中人渴望不可及的《秦风•蒹葭》,有写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车》。
从以上的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哭,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
这些爱情诗歌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的情爱意识热烈张扬,如同行将落山的夕阳晚霞最后那色彩绚丽无比灿烂的光芒,这与后来堕入封建礼教深渊的晦涩暗淡、饱受压抑的女性情爱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张扬的情爱意识构成了《诗经》时代女性情爱意识的主旋律。
首先表现在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毫不污浊,舒芜曾准确地评价了诗经中的男慕女现象:
“这都是些什么声音,不是轻薄调笑的声音,而是真挚严肃的声音,不是施以爱宠的声音,而是祈求允诺的声音。
不是任由我去爱她的声音,而是惟恐她不理睬我的声音。
”这或许与当时古朴的民风有关。
“一切皆源于自然,一切都源自情愫,一切都发自内心。
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这就是《诗经》中的女性”。
如《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思我,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诗经》中女性的生育意识
如同上文论述,《诗经》中的情爱意识目的指向非常明确,那就是生育的责任。
享受爱情与生育责任相比,前者只是婚姻生活中的一个过程,后者却是一种生为女子必须完成的使命。
在宗法时代,子嗣代表生命的延续,多子多孙成了众人的期待,而女性便被赋予了生育的责任。
从《大雅·生民之什·既醉》、《大雅·文王之什·思齐》以及《大雅·生民之什·假乐》诸篇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多子多孙的期望。
《周南·螽斯》也借着繁殖力惊人的螽斯,作为子孙众多、家族兴旺的象征。
《周南·桃夭》全诗更藉由结实累累的桃实,暗示女性的生殖能力,和乐美满的婚姻是与生儿育女的神圣职责紧蜜联系在一起的,试想桃夭一般的女子,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她的婚姻的前景堪虞,出嫁时的祝福会变成诅咒的利箭。
子嗣的观念,成为女性的责任与压力,也成为她是否受到肯定的评定标准。
关于这一点,《诗经》时代的女性也是认同的。
祝福出嫁女子多子多孙的话语应是由陪同的女人说出,她们因袭了一个时代共同的思想观念。
而在古人的意识中,也早就有了重男轻女的思想。
如《小雅·斯干》中有诗句:
“维雄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
载衣之裳,载弄之璋。
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
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分别叙述生男生女的不同待遇和期望,其中“寢床”、“衣裳”、“弄璋”和“寢地”、“衣裼”、“弄瓦”相比,一是尊贵盛饰,一是普通平凡。
对女性,只要求她学会持家,不连累父母就行了。
女性被杜绝了参政议事的意识,于是,一门美好姻缘对她们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
嫁个好男子,终身有靠,生下男嗣,可巩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再加上贞洁操守,这辈子便可以安稳无忧地过来了。
这是当时大多数女子所祈求的平实的幸福生活。
(三)《诗经》中女性的反抗意识
如前文所述,男尊女卑的轻视妇女的价值观和束缚妇女的道德礼教观在诗经时代业已形成,这些观念深深烙印在世世代代的中国的男男女女的头脑之中,习以为常,根深蒂固。
《诗经》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起步时期,至西周时期已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有了对女性不公正的吃人礼教。
《郑风·将仲子》便写了一个女子因畏“父母之言”、“诸史之言”、“人之多言”,怕被别人斥为“淫奔者”,而不敢让他的情人前来相会。
可见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连幽会的自主权都没有,涤荡着苦痛与思念,又夹杂着淡淡的哀怨与不平。
这是父母之权、兄长之权及众人的习惯势力束缚了他们的自由婚配。
与之相对应,便有了反叛者的呐喊和抗争。
《诗经》中的反叛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的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抨击吃人的礼教,二是反抗婚姻不自由。
反映青年婚姻不由已的诗篇在《诗经》中还是不少的。
如《鄘风·柏舟》,其诗云: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
髧彼两髦,实维我特。
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她的爱情受到世俗礼教的阻挠,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爱面临着强大的舆论压力。
然而似乎爱情具有激发抗争意识的超常潜能,为了捍卫爱情的尊严,温顺的弱女子发出“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
不谅人只!
”的强烈呼号。
这是她爱坚情贞的自我呼唤,也是她对阻碍婚姻自由者们的控诉。
不管多么严酷的礼教束缚,多么强悍无情的外界压力,这个少女依然坚毅刚强,对少年男子的追求和爱慕是一往情深、宁死不易其志。
其中饱含的由爱情波折而引起的无限辛酸以及对婚姻不自由的深沉怨恨,是对“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的蔑视和反叛,这一呼号有力地抨击着世俗礼仪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偏见无形中也受到了嘲讽与轻蔑。
结婚是恋爱的深化和升华,是爱情的归宿和结晶。
没有爱情的婚姻自然是不幸的。
那么,大胆地反抗无爱情的婚姻便是自我意识的张扬,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显现。
《国风·行露》反映的就是对仗势逼婚者的坚定反抗。
其诗云:
“厌邑行露,岂不夙夜?
谓行多露。
维谓雀无角?
何以穿我屋?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
何以穿我塘?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讼,亦不女从!
”这首诗表现了女孩子的坚强意志和反抗强暴的战斗精神。
开始时“厌邑行露,岂不夙夜?
谓行多露。
”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只是怕遇人不淑,如同露水沾湿衣服一般。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讼,亦不女从!
”这话语中包含着悲剧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强者,她依然坚强不屈,机智地捍卫自我的人格与爱情的尊严。
她不愿意受金钱、虚名的诱惑,这就使得她不同于时代的平庸女子,她不顾权势的威逼,这更是她勇敢的表现,她用自我的行动愤怒地捍卫着作为女性的尊严。
其间更多的是幽幽的怨,是对男子强行逼婚的怨,是对男权至上的怨,是对一夫多妻制的怨,是对男人的喜新厌旧的怨、重色薄情怨,是对女性地位的卑微的怨,她的怨代表着所有时代女性的心声。
这是《诗经》中第一首反抗妻妾制度的诗歌,这个勇敢的女性成了后世女性抗拒逼婚的榜样。
也许有了它的照明指引,才有了后来梁祝用生命来抗婚捍卫爱情尊严的悲美,千载而下,令人依然为那样的执著那样的爱恋深深感动。
(四)诗经时代女性的思夫意识
上文已阐述诗经时代战争徭役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对女性的意识与生活同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诗经中思妇怀人的作品多以情感细腻见长,但情调悲伤哀怨。
数量不多,但分布地域较广,如出自周南的《卷耳》,召南的《殷其雷》,王风的《君子于役》,卫风的《伯兮》等。
这些诗歌中的女性出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各异,其思念丈夫的形式内容亦不同,这些女性的思念主要集中于对丈夫物质生活的关心上,情感表达平和克制,语言质朴,但更为真切。
《君子于役》的主人公是一位辛勤劳作的妇女,她的思念表现在一天辛勤劳作之后的触景伤情,内容很具体,一是归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何至哉?
”二是丈夫的生活: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于细微处表现出村妇对丈夫的深情厚意。
《卷耳》、《殷其雷》、《伯兮》等诸篇出自中上层女子之口,她们的思念侧重于精神层面,情绪表达更为强烈直露。
《卷耳》中的女子在采摘卷耳时突然想起征戍在外的丈夫,其情思的涌起更多是因为丈夫不在身边而引发的内心失落感,她设想丈夫在征行途中如何地思念自己,从侧面映衬自己的思念之苦,“陟彼崔嵬,我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登上高山,遥望妻子,但战马已经筋疲力尽,只好借酒浇愁,以消除心中的忧伤。
较之《君子于役》情感的表达更为强烈,《殷其雷》写闺中女子想念行役的丈夫,诗中女子思夫心切,恍惚中将雷声当成丈夫行归的战车声。
但空闻车响,不见君归,只有祈求丈夫早日归来,“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连续的叠句表达了女主人公焦灼不安的思念之情。
《伯兮》是思妇诗感情作为强烈的作品,远远超出诗经一贯“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原则。
“伯”是一个高大威猛,武艺高强的人,正在从军征战,由于他“为王前驱”而导致夫妻长久分离,遂成为女子痛苦的根源。
因此,开篇便极力赞美夫君之英武而尽显思念之切: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第二章以自己无心打扮,表达自己孤苦伶仃的寂寞与痛苦: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岂无膏沐?
谁适为容!
”最后两章写思念“伯”的心理感受,“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因思念而痴狂的心理一点也不会让读者觉得夸张。
这类诗歌感情真挚,情绪悲伤,体现除了当时女性的怀人意识。
妇女的女性意识,实际应该包括社会(即男性中心社会处于主体地位的男性)对妇女的认识和妇女的自我意识两个方面。
而妇女的自我意识,是指妇女作为有感觉能思维的人的认识主体,对自身客体存在的价值、道德、审美等一系列的活动的认识、感受和评价。
而中国妇女女性意识的历程,就是一部女性意识在男性社会和个体家庭中沉浮的历史。
女性意识沉潜的过程,就是女性权力被剥夺,自由失落陷入依附地位的过程。
随着历史的进程,中国妇女女性意识必然会迈向由积极性复苏到自觉性解放的缓慢进步道路。
诗经中的女性意识为我们展现了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对于审视女性在古代以及现代的地位与价值是有着深远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