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评论 汇总版.docx
《诗歌评论 汇总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诗歌评论 汇总版.docx(4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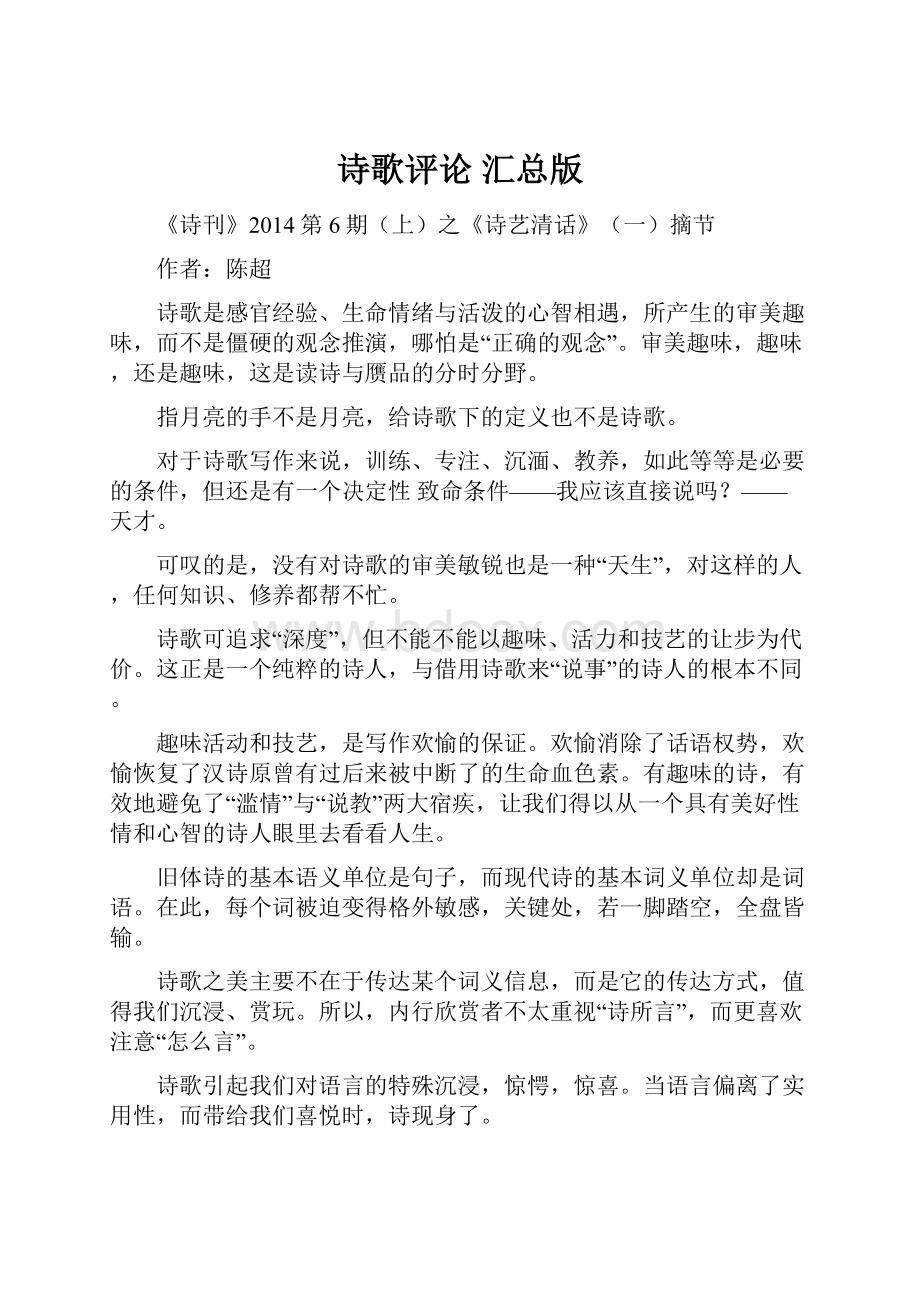
诗歌评论汇总版
《诗刊》2014第6期(上)之《诗艺清话》
(一)摘节
作者:
陈超
诗歌是感官经验、生命情绪与活泼的心智相遇,所产生的审美趣味,而不是僵硬的观念推演,哪怕是“正确的观念”。
审美趣味,趣味,还是趣味,这是读诗与赝品的分时分野。
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给诗歌下的定义也不是诗歌。
对于诗歌写作来说,训练、专注、沉湎、教养,如此等等是必要的条件,但还是有一个决定性致命条件——我应该直接说吗?
——天才。
可叹的是,没有对诗歌的审美敏锐也是一种“天生”,对这样的人,任何知识、修养都帮不忙。
诗歌可追求“深度”,但不能不能以趣味、活力和技艺的让步为代价。
这正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与借用诗歌来“说事”的诗人的根本不同。
趣味活动和技艺,是写作欢愉的保证。
欢愉消除了话语权势,欢愉恢复了汉诗原曾有过后来被中断了的生命血色素。
有趣味的诗,有效地避免了“滥情”与“说教”两大宿疾,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具有美好性情和心智的诗人眼里去看看人生。
旧体诗的基本语义单位是句子,而现代诗的基本词义单位却是词语。
在此,每个词被迫变得格外敏感,关键处,若一脚踏空,全盘皆输。
诗歌之美主要不在于传达某个词义信息,而是它的传达方式,值得我们沉浸、赏玩。
所以,内行欣赏者不太重视“诗所言”,而更喜欢注意“怎么言”。
诗歌引起我们对语言的特殊沉浸,惊愕,惊喜。
当语言偏离了实用性,而带给我们喜悦时,诗现身了。
诗歌是需要高度专注语言艺术,与小说家不尽相同,在特定意义上说,诗人不仅需要“开放”信息,同时更需要必要的“自我封闭”,凝神静心默想。
不要用舞台上矫揉造作的范儿写诗。
不要使用与你腻友调侃时的以佻调调写诗。
诗是与处于喑哑之地的潜在知音的交流,要质朴,谦逊,诚恳,还要一点羞怯的自我克制。
记住要把自我迷恋,转换为对诗本身的专注和沉浸,这样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写作不是描摹世界的表象,而是让存在现身。
诗人不应照相式地反映事物,而要潜入对象的内部,将对象“比它自身中解放出来”,让他所创造的世界替他说话,达到心与与道合的天地同参之境。
诗人毋庸去制造更多的玄想,他对着感知的对象凝神领悟,直到对象向他走来,并“要求”在话语中展露它自己。
诗歌不必要你懂,而是要你感受。
差的诗人往往在该含混的地方太清晰,而在该清晰的地方又太含混。
对诗人而言,整个宇宙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外界事象与人的内心能够发生神秘的感应与契合。
因此,“象征”等等不是一般的“修辞”技巧,而是内外现实的“相遇”、“相融合”。
诗中的形象不是从属的工具,它自身拥有自足的价值。
有许多诗人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诉说自已心灵的苦难,但并能打动我。
诗人责问道:
“我说的还不够多么?
”
——让我们告诉他:
“不。
一个致命的原因恰恰是你说的太多,而‘诗’说得太少。
”
诗的本质不是抒情,不是经验,而是诗本身。
不管你属于哪种创造力形态,每个真正的诗人内部,都有个“绝对的诗”的幽灵,或舍利。
诗的含混和清晰一样,本身不等于诗的价值。
诗的价值:
含混,必须有内在精敏做基础;清晰必须有“光明”的神秘。
“你的美是月光下的庭院”(含混),比“你是一朵红玫瑰”(清晰),前者更精敏。
….不能为其它语言转述的言语,才是个人信息意义上的“精确的言语”,它远离平淡无奇的公共交流话语,说出了个人特殊感受力,和个人灵魂的独特体验。
诗,是个体生命和语言的瞬间展开。
与其它文体相比,在于它的不可复制性,不可复制别人,也不可复制自己。
优秀的诗歌关心的不只是可以“类聚化”的情感,更应是个体生命的经验。
类聚化的情感只能“呼应”我们已有的态度,而个人情感才会“加深”乃至更新我们对生存和生命的感受与洞识。
因此,我们在读那些优异的诗作时,会感到诗人是将自己的生命经验一点一点“捺”入文本中去。
经验是“呈现的”,感情“告知的”,对真正的好诗而言,“呈现”总是比“告之”的信息量更多,艺术劲道更足。
是呵,浪漫主义滥情的衰退早已警示过我们:
允许写得不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诗歌是由感性而生的。
但是,再好的感性,也无法绝对地保证写出一首好诗。
诗是语言中的语言,这意味着,从你感到的世界到你写出的“诗的世界”,中间还对语言艰辛地提炼、磋商的考验。
而缺乏技艺,你感觉的浓度就被磨损掉了。
诗歌要有适合于特定题材的流畅、美妙、自如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效果是诗人久经磨砺、反复调试的结果。
音义协调好声音,自然的声音,其实等着诗人去提炼和发明。
找到并校准那绝对的声音。
别相信自然而然就会流畅的说法,这么说,不是外行,就是自矜的谎言。
诗歌的声音也是意义的一种。
它聚拢、塑型了时空。
我未尝见过哪个好的诗人,对声音没有特别的敏感。
对现代诗而言,声音直到的绝对装饰,它也是诗创造性存在本身。
对好的诗人来说,声音也要求原创性。
声音本身也是讲述,吟述、回忆、畅想、讥诮、反讽…..
惊动了诗人,使他觉得会值得以诗歌处理那些事物,都有自己内在的节奏,诗人寻找它、呈现它。
好的现代诗,节奏像是一事物自身的;坏的现代诗,节奏是诗人强行嵌入的。
诗歌的话语区别于其它话语的特征,一般地说表现在以下四组差异对比:
音乐性/松驰性;创造性/约定性;表现性/平面性;构成性/单维性。
传统诗歌也非常讲究音乐性,但它的音乐性是由预先设置的声律音韵决定。
也可以说是“音在笔先”。
而现代诗的音乐性,是与诗人瞬间生命体验节奏共时生成的,声音是特殊的“这一个”意义的回声。
重读旧读,发现我年轻时写的诗,元音发的很足,那是潜意识中写给别人看的。
中年之后,有喑哑感,摩擦感,触及感,那是自言自语。
现代诗的声音,不等于“韵脚”。
在我看来,诗歌韵脚的有与无,都不会自动带来一首诗的成败。
在使用现代汉语的情意下,许多时候,规律而密集的押韵,反而会毁掉一首诗的音义谐和——就像一个人的“好事”做得太多、太急切、太机械,反而让人不适或生厌一样。
现代诗人虽普遍追求非韵化,但其实特别重视个人的生命节奏。
成功的诗歌既是心灵的动动,也是“声音的动动”。
高妙的声音,能在语义、字词结束之处继续鸣响,召唤出语义不能说出的东西。
非韵化并不意味着诗歌的“非体化”。
好的自由诗是“非韵而有体”的。
体,与声音也有密切关系。
非韵化不是刻意反韵(在恰当的地方诗人不必刻意回避韵脚),但他们更重视是“体”的自觉。
诗是汩汩的泉源,但却是道“被引导的泉源”。
在声音节奏上保持着语感、语速款款的奔逸性,在境界上逡巡着前行——回塑力量。
不同的诗的节奏,也暗示诗人对时间的重塑力量。
隐喻诗歌的修辞复杂含混,但能更清晰地把诗歌说话的声音和写作者自己的声音区分开。
保罗策兰说:
“诗歌从不强行给予,而是去揭示”。
何谓“强行给予”?
就是诗人处理材料时,以单一的视点和明确的态度直接“告知”读者,他的伦理装判断、价值立场、情感趋向。
这样的诗表面清晰、透彻,但实际上往往成为枯燥的道德说教,成为一篇精心修饰过的“美文的训话”。
如果诗歌变为简单的道德承诺,诗人会在不期然中标榜所有所有正义、纯洁、终极关怀都站在自己一边,这样就取消了诗歌的多样性和与读者的平等对话。
表面看这种诗歌获得了“统一性”,但这种统一贫乏的,对事物的“清晰透彻”认识恰好遮蔽了事物固有的复杂内容——它“透彻”到了独断地压抑透彻的程度。
而“揭示”,就是保持对事物多样性的认识,如其所是地呈现它鲜活的状貎,将含混多义的世界置于词语多角度的当照之下,标志或呈现它自身内部的种种丰富性,同时维护着读者沉思、提问、自由地二度创造的权利。
一首真正有创意的诗,不只是结束一次成功的创作,同时也为其它的诗作敝开可能性。
隐喻,只是诗歌的语型之一,不应形成“专权”。
诗意的经验未必都要用隐喻表现,有不可言说的神奇,也有可用口语言说的平中见奇,表面波澜不惊中,隐含内在心灵的陡峭。
不一定奇诡。
这也是好的诗歌语言踏实而膄润,经过淬砺又像是脱口而出,单纯而又有骨子里的丰富感。
平和深邃不再蛊惑,诚恳自尊又触动人心。
《诗刊》2014第7期(上)之《诗艺清话》
(二)摘节
作者:
陈超
以出世的眼光,写入世的诗歌。
能真切得教你恍惚,熟悉得教你陌生,是为上品。
好的诗人,不是煽情的“啊——”,他的艺术个性是沉毅的。
这种沉毅既是对世界与人生的神秘,而持有的优雅的、审慎的态度,也是一种缄默的、恭谨的观察事物细节的风度;同时,审慎、缄默和恭谨,还体现了“写作的伦理“——诗人要避免给人以眼花虚张声势号令般的专横压力,要删除那些突兀的刺耳的声音,为”音高设限。
”
写物时,诗人要在能力提供物的本真自然之美,更重要的是,他应提供一种陌生化的“说法”,一种全新的“冷客观”的措辞方式。
我们常说,“诗是命名”,这话不错。
但别忘记了诗不仅为“我”的经验命名,它还应向现象敞开,为“物自体“命名。
后一种命名常常是更为困难的,它它意味着你要将观察力、专注力和书写突入到喑哑未名领域的极限。
好的现代诗,每三句之内,应有个趣位点。
六行之内,应有个“炸点”。
九行之后,应让人既心领神会又无从转达。
三、六、九者,约数也。
叶芝说“有话语力量的诗人,要敢于重新处理被别人处理过的题材。
”在似乎已被过度开伐,几乎耗尽的语言密林中,诗人要有能力在那干上,以新异的方式雕刻出个人化的、细腻深邃的纹理。
“诗人是孤独的”。
这种说法似乎是诗人的另一种定义。
….我认为,诗人不只是孤独,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力将孤独话语化。
他观照孤独,寻找友情和对话的安慰。
语言比诗人更孤独,
我的基本想法是,现代诗可以有不同的类型,相应也有不同说法。
但对我来说,有个朴素但主要的尺度,说起来也简单,真正做做到很难——诗,一定要让人读得下去。
要有趣味,要有活力,无论是近乎情、切于事,是智性,是抒情,还是另类式的锋利诙谐、奇境式的隐喻,如此等等,前提是都要有诗特殊的劲道或魔力。
为什么读寺?
因为它有让我们愉快的、吸引我们本能趋近的语言磁力。
现代诗更喜欢“实验”。
但你“实验”得让真正的内行都看不下去,无论它多么“前卫”,你没什么可争辩的,因为你写砸了。
检验是否是好诗人,有一个看似不通,却十分有效的标志,即你在诗坛的“敌人”是否真看你的作品,不仅为了攻击。
好的诗歌,心灵大于学养,性情逾越头脑,只有个人才有心灵。
真正的诗歌应该是“轻逸”的,不一定要沉重、艰涩,郑重轻才会带来艺术意义上的轻逸。
草率的轻,带来的常常是轻浮。
卡尔维诺说得好:
要写得像鸟一样轻,但不要像鸟的羽毛一样轻。
对于那些真正成熟而优秀的诗来说,无法截然分出“悲观”与“乐观”,“坚信”与“迟疑”。
它像坚实润泽的蛋白石一样,它的光能在转动的不同角度下放射出不同的色彩,成人写作,经验的包容力在此产生。
一个有雄心、有才能的诗人,应该广泛阅读不同类型的经典。
不是为了仿写,而是为了知道应该超过什么。
海明威说得对,“好的作家要写出前人没写过的东西,或者说,超过死人写的东西。
最好的诗,是活着的有机自在物,会随着读者年龄和阅历的丰富,而不断焕发丰富的意味。
次一等的诗,使读者愿意重温原来的语境。
再次一等的诗,既不能接引读者超越原来的语境,也无法吸引他回到原来的语境。
一首诗能让人读下去,除了趣味外,还有个要素,简单说,就是确系有惊动了诗人自己的什么东西,要表达出来。
“难度”不在表面的修辞效果,而在陡峭的角度的精审册繁就简,表现出貌似随兴般的风度。
新鲜、坦率、诙谐、角度刁,会激发经验读者的兴趣。
现在的阅读与八、九十年代不同,经验读者的趣味变了不少,与生存发生真切摩擦,带着生活质感和鼻息的诗,恰逢其时成为显豁潮流。
当然,说诗歌要充实,还难以完全尽意,关键是充实本身的质量如何。
生活细节,体验,感悟思考,不仅要诚实,还得真正有新意、有亲鲜清冽的味道,像早晨猛然打开窗子一样。
诗歌既可能被过度修辞吞噬,也可能被鸡零狗碎的无聊事实吞噬,把真话说成真诗,难度很大。
诗不必起承转合,亦不好强行发生。
机敏而舒服地插进,像是心照不宣接续中断的谈天。
一旦进入写作,我们的心智和感悟和自足的话语形式的光照之下。
用具体超越具体,其运思图式或许是这样的:
具体——抽象——亲的具体。
有魅力的诗歌,既需要准确,也需要准确,也需有精敏的想象力;语言的箭矢在触及靶心之后,应能有进步延伸的能力。
所谓的诗性,就存在于这种高电荷的想象力的双重延伸之中。
我认为,无论什么类型的诗歌,不仅要呈于象、感于目、达于情,最好还能会于灵(“灵韵”),这就需要诗人自我提醒,为写作中自然出现的那些“陌生的投胎者”留出一定的空间。
再写不出好诗,至少可以不写。
这不写,算不得对诗歌严肃敬意中最高级的那一种?
我想,它就是。
诗人专注于生命的感悟和心智的闪烁,他不直接去写空阔的“风云史”而是将自我放在细屑、具体的生活处境中。
与那些分行的“格言体”之思考深刻相比,诗人追求的是“生命的深刻”。
无论隐喻,还是口语,诗人自有“诗家语”。
在常人实用指称的层面上,诗人更心仪于其丰富的暗示性。
诗家语,无论是隐喻还是口语,都要接受诚恳度的检验。
有人说现代诗的修辞是暗示、隐喻。
未必如此。
我看到,有些现代诗,回避间接性,其最打眼的反而是一系列准确、本真的细节提炼。
你简直就勿需用“言此意彼”方式进入,也不必调动你的直觉,它快捷跳脱不留余地,“嗒”一下就撞在你心上。
说实在话,这类不饰险崛的细节提炼,更是衡量一个诗人“手艺”重要尺码之一,因为它难以蹈袭,愈显其功实倍。
口语诗歌表面看好写,其实更难鱼目混珠。
没有天赋的人,莫以为口语诗是捷径。
天呐,我没想到口语诗“现”了这么多人。
成功的口语诗,其实是口语目的性的秘密变体。
针对有人说‘“新诗散文化”,在一种抗辩的语境中,艾青干脆提出了“诗的散文美”,它是指新诗的语言要鲜活、真切。
有些外行见到用口语诗,即惊呼:
“不是诗”!
他使用的是我们说话的语言。
是啊,就因为你只看到了诗人使用了共同的语言,所以你和诗人永远没有共同语言。
新的语言不一定要有明显的、尖得的棱角,但绝不能光滑。
它要有摩擦力,总是硌你一下,抻你一把。
现代诗逐渐渐褪去繁缛的修辞和绚烂的神话,更关乎诗人内在的真实。
许多诗人在用基本词汇和句型写作,摆脱了造作的“文艺腔”。
过去写作需要修辞才华,现在更需要懂得对才华的控制力。
遣词造句准确而内在,气韵贯通而入情入理。
更多地加入恰切成熟的口语成分,于诚朴中求真切,于直接中求隐奥,有着内在湿润而透明的品质。
只有阅历丰富,久经锤炼,诗心沉潜的人,灵魂深处才会涌出有韵味、有个人化形式感的单纯的清澈,使经验在话语中真正扎下根来。
如果说在哲学学眼中,“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话,那么一个诗人则应对生活保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种审美的自由的高傲态度。
正所谓“理论是灰色,而生命之树常青”。
在现代诗学语境中,何谓长诗?
它不仅是指长度,同时也是指诗歌承载力,话语的变秦的意思。
在现代诗中们不仅看到长度,其标准也在变化。
而我们称之为“扩展“变奏”的东西,主要就是惊奇与复归、创新与重复、断裂与持续的结合。
我认为,真正的现代长诗不惟情感,更应有强烈而连贯的智性和叙事性融合的结构,仅凭感情和修辞炫技的驱动,200行之后再优秀的诗人也会将自己渐渐耗空——除非诗人硬“赖”在情感和修辞的空洞中循环往复。
成功的长诗,在诗人奇妙而宽阔的“吟述”中,叙事与抒情,幻象与智性,形而下与形而上,应能做到彼此忻合无间的穿逐游走。
诗人的结构能力,感情强度,捕捉具体事象的动力,丰盈的想象力,修辞才智应得到较为均衡而完整的发军、变演。
在此,我们不仅想看到心灵与事物的隐秘跃动,而且还同步领悟到某种超验的精神图式。
诗歌永远只是诗歌,它首先在语言上应令人沉默和玩味,否则题材再“重要”也无效。
好的诗人,不止提供新的经验和境界,同样重要的是他必须提供新“令人产生快感的说法”。
过去的“抒情诗”主要是抒发诗人的情感。
现代抒情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更多是表达诗人想象力和挖掘语言魅力的艺术。
2014第8期(上)之《诗艺清话》(三)摘节
作者:
陈超
“语言言说”按照罗兰.巴尔特的表述,诗是不可读的,而是可写的。
它狂暴地打击读者的预结构期待。
…..诗歌本身应有更充分的可供读者参与词语事件的权利;阅读本身也变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写作活动,即模仿诗的写法去读它。
读者最快成为特殊的“文本生产者。
”
写作,不是为了提取先行预见的“意义”,和对先验设定的真理的模仿。
它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写作过程自身,引向意味的持续扩散、重新生产和自由分配。
语言结构与诗人之间,不再是后者赋予者,而是一种双方彼此的照亮、选择和发现。
如果说常规的诗歌,其语义是潜在散文式的似断实连的“线条”,那么“语言言说”的诗就是发散式晶体点的状面,是依靠纯语言事实支撑的。
前者直线运动到一个终点的结束,后者互动、摩擦出更小的“话语微粒”。
前者构成“意思”后者构成“意味”。
前者是由粮食酿成的酒,后者像酒精燃烧时发出的热量。
前者是存在,后者是空无。
前者是地面,后者是地面和天空两面拉开的力量:
看不见却可以触摸,听不到却可以感受。
“语言乃存在之家”。
我们不断深入语言之家时,理应学会以聆听“它说”。
不只是诗人说语言,而是诗人与语言彼此的“聆听”、“对话”、“应答”。
语言只有在“我说”与“它说”的交互打开中,才称得上是不可公度难以替代的奇妙的诗歌话语,它最终会独立于诗人之外,成为积极的、自我运动的、更无常的、更有神奇的生命力的精灵。
从这里看过去,我们会在更深的层面来理解那些追求“它说”奇境的诗人们喜欢说的话——
不是诗人写诗,而是诗写诗人。
受于诗歌语言的绝对性,阿兰.巴丢说,“我们可以严格地说,诗歌反对的就是数学或者说数元对思维的控制。
诗歌是一种不妥协的练习。
诗歌拒绝投票民主和电视民主。
诗不存在于交流之中。
诗歌没有需要传递的东西。
它只是一个表达,是一项仅仅从自身获取权威的声明。
赫塔.米勒说多干脆:
“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聆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深意。
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
当一个人的写作进入“更成功的瞬间”,他会发现,真正的写作更像是一种“聆听”:
聆听语言自身的言说,听从语言对你的引导和召唤。
永远不可能奢望完全把握诗歌——否则就是对陌生者的不尊重,诗人身上已有的或前来投宿陌生之物;否则就是忘了诗歌本身是有呼吸的忘了诗歌会把你吸走。
现代诗人在重新打量“抒情”在诗歌中的价值。
过去,“情感饱满,表达生动”就可以成为一首好诗了,现在,“情感”却成为一个需要审视的问题。
我以为,抒情本身不会自动给诗带来成与败,关键是抒情的内蕴,抒情的技艺高下。
现代诗人认为,诗歌应以隐喻世界,反对单维度直陈其事,直抒胸臆,强调在表层文本之下应有深层文,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超量的审美和智性的启发。
很明显,几种相近的意味组合在一起就没有多少张力,而几种相异的意味组合在一起才会有强烈的张力。
现代象征具有多义性、暗示性、双重视野、超越性。
诗的结句,非常重要。
既要结束,又不能封口。
它不是关好一扇门,而是打开另一个空间,“留终接混茫”。
好诗不应拒绝对日常生活的表现,但是诗歌不能成为枯燥的生活小型记事。
一个诗人无论怎样对生活的召唤殷勤备致,他都不应放弃对艺术本身的信义承诺,但更具有“挖掘语言奥秘的艺术魔力。
…..主要有三种期待:
个体节奏化期待;非指称化期待(深远的暗示);整体化期待(相信诗歌短短数行便可完成,其跳跃的部分由经验读者的想象连接)
成熟的诗人应警惕精美的平庸之作。
诗人与“写诗的人”之不同,有一个硬性指标,看他在专业共同体中,有无站得住的代表作。
成熟的诗人,不排斥对‘智性“的探寻,但更不排斥对“情感”的亲和,他试图融汇、平衡这无声二者,找到自己恰切的话语方式。
因为过度主智,会使诗干燥;而过度主情,又会让诗飘忽。
教内在的田思悟和真醇的情感,浸渍于奇异的物象——情景之中。
与散文相比,诗歌应有“无法结束的部分。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对不可说的东西,应保持沉默。
”这句话对早期的维特斯坦而言具有确指性:
坚持经验证实的原则,认为语言是表达经验事实的,凡是经验事实都是要说的;而超经验的东西是不可说的,对这部分内容应保持沉默。
现代诗没有一元主义的绝对标准,但永远有好坏之分,真正的内行心中一定有个神异之声只在碰到真诗时才共鸣。
无论你用什么历史语境(诸如新启蒙、亲浪漫、现代、后现代、性别意识、后殖民、全球化、新左派等等)衡估诗,永远有好坏之分。
人们说,诗歌要想自我证明,必然要有文体的仪轨。
这是只知其一。
其二是,先锋诗就是对“从来如此”“众所周知”的仪轨的质疑和超越。
其三是,先锋诗若要具有艺术意义,在对仪轨的颠覆之后,必须创造出自己的形式。
《钟山》2014年第5期《新诗话:
龙虫并射》
作者:
陈超
我们今天追求现代性,无非是要解决语言与扩大了的经验之间的矛盾关系,使语言更为有力地在现实经验中扎下根。
以往支配诗人的整体话语、宏大抒情、或本质主义、绝对精神书写,有赖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视阈”。
而当下,这个文化共同体已然解体,它的魅惑和感召力也就同步消磒了。
人们说电视、网络延伸了我们的感官。
岂不知它们也代理了我们的感官对世界的鲜活体验。
我感到80年代的诗,再有缺陷,诗还有大自然的各种气味,90年代至今的诗,一股电脑散热的气味。
诗歌是否开阔常常不是由读者多少决定的,我看到恰恰是那些“大众诗”其意蕴极为狭窄、枯燥。
科技市场时代的物品,可进入大脑而很难进入情感,这可能也是诗歌干燥的原因。
臭诗以豪华精装本形式传播,会显得更臭。
其实,我听到的对诗人最真实、最干脆、最准确的评价,是在我们私下“说别人小话”的聚谈中。
我看到,有的诗,意在塑造诗人自身的形象;有的诗却展示了诗自身的魅力。
后者更靠谱。
如果一个诗人40岁还在表演个人魅力,这个诗人已经废了。
诗应为诗而存在。
它不但应有能力回避仿哲学的“深度”,也要有勇气藐视写“日常生活”这个新的权势话语。
诗大约每五行之内应有细节,不要被情感和智性蒸发掉诗句的“质感”。
但五行之后,应切断这个细节,否则它主面了。
你应转换或变奏,使诗有“呼”有“吸”才舒服。
当然,是自己写得舒服。
别人是否,你管不着。
如果写诗一定会教导人一些什么,我倾向认为,它使人懂得羞愧。
一个长时期牛气冲天的诗人。
他又会真正说出点啥呢?
应有对自己诸多败笔的羞愧,应有对自己有成千上万天真或蒙昧的拥戴者的羞愧。
诗人,诗/人,不单是指写诗的人,他还应是一个独抒情灵,具有纤敏的特殊感受力,让个体生命在语言中扎根的人。
杰出的诗歌不一定是美。
这是现代诗了不起的发现。
我经常并上,个别先锋诗人的知识大部分来自资讯或浏览,耳食之言。
但常常是他们,能把一知半解发挥到别有洞天的高度。
一知半解,留下更大的想象,创造空间。
对诗人来说,一知半解是合法的。
天才诗人有一个标志,在三言两语的言辞中“聚拢“起存在本身。
诗人用来谋生的职业身份并不重要。
诗是一个人精神行动,内在的‘“我“。
现代诗只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感兴趣。
诗的,太诗的,多少非诗假汝之名。
多褶皱的现实,吁求多褶皱的文本。
无论多褶皱文本,还是多流畅文本,都不是艺术评价标准。
了不起的诗人,必能写出神秘的“合情理”感。
可对现代诗“读不懂”,他就敢空前自信地认定诗人是“艺术的败家子在胡闹”,而从不想是否自己有问题。
难道现代诗不是某种有关生存和生命复杂经验的“特殊知识”,一门严肃而难能的复杂语言技艺吗?
凭什么它就还应该是老少咸宜的“哲理”?
一种行云流水闲遣兴的“雅好”?
日常生活不等于诗。
把日常生活情景写得不可重复,令人惊愕,屏息凝神,重新打量,容留自反性和意料之外的关联,诗歌于此才脱颖而出。
这个时代独立特行的人太少,关心灵魂问题的人太少,受过合格的艺术教育的人太少(瞧瞧那些大学的大多数文学教授、博导,他们怎有能力启发真正的艺术趣味?
)有沉思默想的人太少,安静地坐在家中阅读的人太少,有诗歌敏识力的图书编辑太少,够格的文学出版社太少(或根本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