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康访谈录.docx
《何康访谈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何康访谈录.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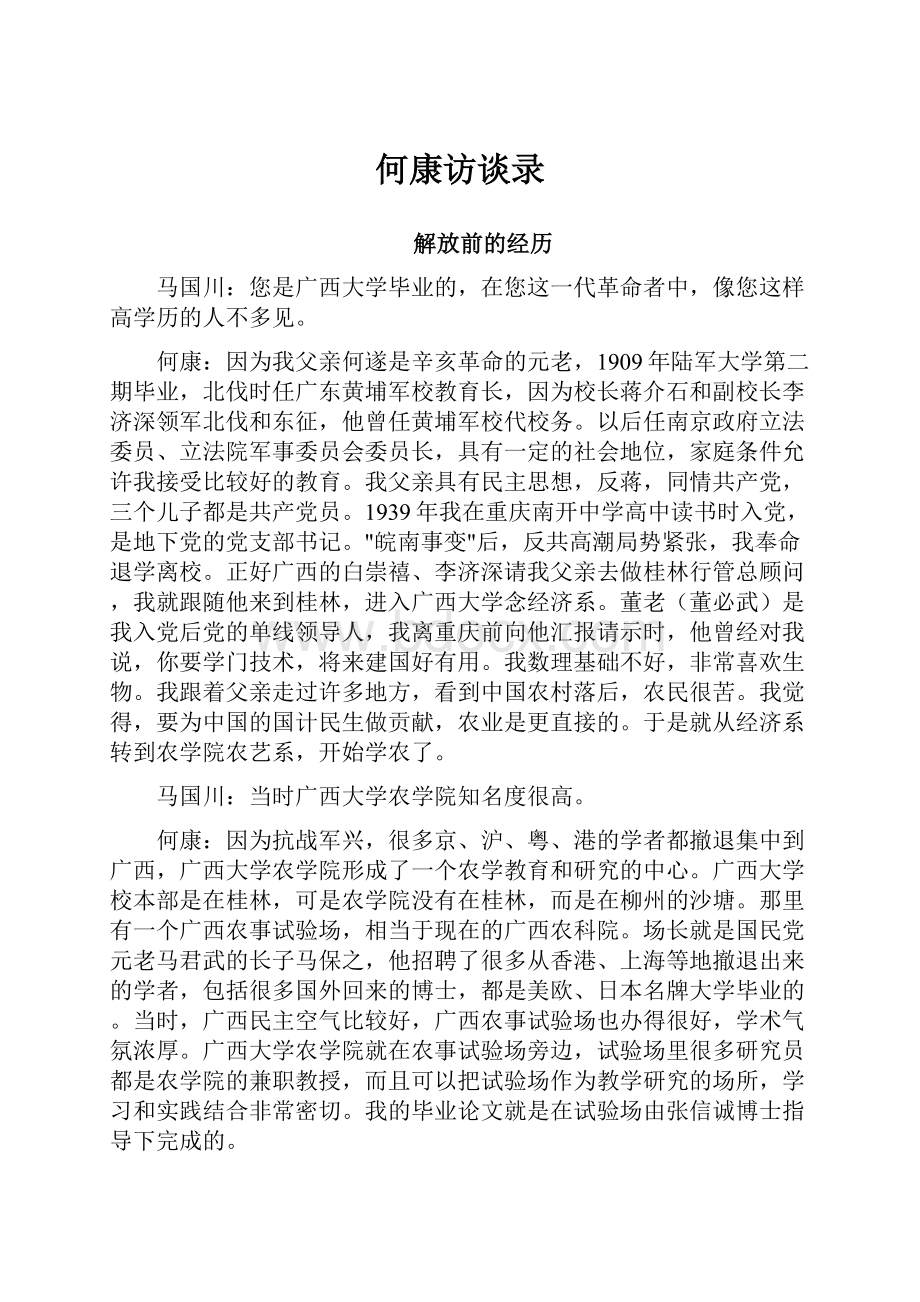
何康访谈录
解放前的经历
马国川:
您是广西大学毕业的,在您这一代革命者中,像您这样高学历的人不多见。
何康:
因为我父亲何遂是辛亥革命的元老,1909年陆军大学第二期毕业,北伐时任广东黄埔军校教育长,因为校长蒋介石和副校长李济深领军北伐和东征,他曾任黄埔军校代校务。
以后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家庭条件允许我接受比较好的教育。
我父亲具有民主思想,反蒋,同情共产党,三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
1939年我在重庆南开中学高中读书时入党,是地下党的党支部书记。
"皖南事变"后,反共高潮局势紧张,我奉命退学离校。
正好广西的白崇禧、李济深请我父亲去做桂林行管总顾问,我就跟随他来到桂林,进入广西大学念经济系。
董老(董必武)是我入党后党的单线领导人,我离重庆前向他汇报请示时,他曾经对我说,你要学门技术,将来建国好有用。
我数理基础不好,非常喜欢生物。
我跟着父亲走过许多地方,看到中国农村落后,农民很苦。
我觉得,要为中国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农业是更直接的。
于是就从经济系转到农学院农艺系,开始学农了。
马国川:
当时广西大学农学院知名度很高。
何康:
因为抗战军兴,很多京、沪、粤、港的学者都撤退集中到广西,广西大学农学院形成了一个农学教育和研究的中心。
广西大学校本部是在桂林,可是农学院没有在桂林,而是在柳州的沙塘。
那里有一个广西农事试验场,相当于现在的广西农科院。
场长就是国民党元老马君武的长子马保之,他招聘了很多从香港、上海等地撤退出来的学者,包括很多国外回来的博士,都是美欧、日本名牌大学毕业的。
当时,广西民主空气比较好,广西农事试验场也办得很好,学术气氛浓厚。
广西大学农学院就在农事试验场旁边,试验场里很多研究员都是农学院的兼职教授,而且可以把试验场作为教学研究的场所,学习和实践结合非常密切。
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在试验场由张信诚博士指导下完成的。
马国川:
那是抗战时期,生活一定很苦吧。
何康:
很艰苦,生活上的一切都很艰苦,吃糙米饭、睡大通铺、点桐油灯。
但是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和学习的乐趣,很多同学是从沦陷区逃难出来求学的,大家都恨不得多学些知识。
我在那里学业收获很大。
后来我成了农业部长,我的同年级同学李崇道,也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哥哥,后来成为台湾"农复会"的主任委员。
还有一个比我们低两班的同学黄成达,后来成为香港的渔农处处长。
我们三个人曾住在同一个宿舍,我跟李崇道是上下铺,三个人都得了"中正奖学金",就是每个系第一名。
我是农学系的,黄成达是园艺系的,李崇道是畜牧兽医系的。
我在广西大学学习了三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毕业,回到南京家中办农场。
党组织又将我派到上海,利用父亲与岳父的关系,组织成立了上海瑞明企业公司,由我任总经理,归上海局刘晓和张执一领导。
马国川:
这个公司主要做什么生意?
何康:
主要是处理善后救济总署分配给解放区救济机关的药品和物资,并从事统战工作。
上海一解放,就宣布我担任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处长。
原来在进城之前,华东局就在苏州拟定了上海军管会的领导名单。
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我还是瑞明公司总经理,站在欢迎队伍里呢。
儋州立业,宝岛生根
马国川:
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您才26岁。
您这个军管会农林处处长负责什么工作?
何康:
一开始,就是接管上海本地的国民党农业、林业、渔业和农机机关。
上海军管会结束后,成立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下面设有各种业务部,我担任农林部副部长分管农业工作。
部长是张克侠,就是电影《佩剑将军》里主人公的原型。
一共有四个副部长,其中一位是党外人士,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金善宝。
因为内战,很多山东、安徽、苏北等地有钱人,还有一些不了解共产党政策的人,跑到上海来避难,所以一开始工作就是动员这些人回乡,恢复农业生产。
那时候包括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申新纱厂经理荣毅仁老板和各界人士都出来替农业说话,出钱、出力,拿出美元进口化肥、农药,协助恢复生产。
农林部主要工作就是下乡动员指导农民恢复生产,特别是粮食和副食品生产。
当时下乡有时会遇到散兵和土匪,下乡时还有卫兵带枪保护,防止坏人袭击。
我在华东农林部工作了两年,1952年调到北京来,担任林业部特种林业司司长。
马国川:
什么是特种林业司?
为什么调您来做司长?
何康:
所谓"特种林业司"就是橡胶司。
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政策,禁运天然橡胶到中国。
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苏联决定援助中国一百多个项目。
根据斯大林提议,要求中苏合作在中国南方热带地区海南岛、云南等地发展天然橡胶。
当时是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天然橡胶是重要战略物资,飞机坦克都需要,特别是超音速飞机和重载大型运输机速度快,重量大。
合成橡胶比重大,摩擦生热后轮胎变质丧失弹性不能使用。
因此必须使用天然橡胶。
可是苏联不出产天然橡胶,橡胶草的产品质量也不行。
在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工程时,斯大林知道海南岛有天然橡胶,所以就提出把橡胶作为中苏合作项目。
于是,中央由陈云主持这项工作,马上成立华南垦殖局(后改为总局),由广东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兼任局长,调20万民工,以两个师一个团部队转业官兵为骨干,在湛江、广西、海南、云南热带地区大力发展橡胶。
橡胶是乔木大树,归林业部管,林业部根据需要新成立了一个特种林业司管理天然橡胶工作。
要在各大区农业部长里面挑一个懂技术的人来当这个司长,我是学农的,华东又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就把我调来当司长了。
马国川:
当时您知道特种林业司是干什么的吗?
何康:
我不知道,更没看见过橡胶树。
我们学农的时候也没学过,有人还以为是吃的水果香蕉呢。
上任后不久,我就跑到南方适合热带植物生长的地方,希望找到更多能够种植天然橡胶的自然环境。
那时候国家安排了经费25亿元,决定在海南、雷州半岛、云南建100个橡胶农场,从全国农林院校中抽调数以千计的师生进行垦殖调查,勘察测量,规划建场,参加垦殖建设。
组织20万胶工,从现有部队中组建林业建设两个师一个团,建立国营橡胶农场,准备三年种植800万亩橡胶。
完全是军队的建制,我们地方干部到那儿很不适应,我是作为专家出现的,又当过大区农林部的副部长,还是稍微有点威信,但是太年轻,还不到30岁啊。
那些老红军不懂橡胶,经我们介绍,互相沟通,慢慢地同他们搞好了关系,大家互相尊重。
中苏合同里订的是三年搞800万亩橡胶林,苏联支持中国肥料、机械设备和技术,中国以橡胶偿还。
苏联送来了汽车、化肥,还派了苏联林业部的副部长带了五十多位专家来指导工作。
其实这些专家也不懂怎么搞橡胶种植,就是抓进度,只要我们按照规定时间偿还橡胶。
在大森林里开荒,20万民工简直拼了命,生活十分艰苦。
我就在中间协调两边,因为我是中央的代表啊。
而且部队要吃要喝,开荒有时跟老百姓发生矛盾,甚至发展到打群架,要处理场社纠纷。
马国川:
这些都是棘手的事,对您来说也是考验。
何康:
1953年矛盾就相当大了。
正好那一年斯大林去世,苏联的副部长跟着我们一起考察,消息传来,我们在湛江原地站立向北方默哀。
几天后就把他调回去了。
不久,苏联来了一个电报,建议废除中苏双方协定,因为苏联在国际市场可以买到橡胶了。
毛泽东说,本来就是不平等条约,废除了,早应该废除。
马国川:
合同就这样废除了?
何康:
废除了。
中央决定先种200万亩橡胶,以后再扩种200万亩橡胶,橡胶司也被缩编为橡胶办公室。
我们喘了一口气,马上决定缩减种植面积,遣散了民工,把骨干留下来,减缓开荒的速度,主要是提高产量和质量,加强科学研究。
恰好在这个时候,华侨送给我美国农业部的一本世界橡胶考察报告,我如获至宝。
在中苏合作大种橡胶时,在苏联专家支持下,1953年初在广州建了华南热带特种林业科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
1954年3月正式成立并定名为华南热带科学研究所。
1956年中央正式成立农垦部,研究所划归农垦部领导,改名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1956年我主动要求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当所长。
爱国华侨陈嘉庚从国外运回优良品种,逐步由实生树变为芽接树,提高了产量。
马国川:
放弃司长不做,甘心做个所长,这很难得。
何康:
其实没什么,我愿意做科研工作。
1956年成立农垦部后,橡胶转归农垦部主管,并在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建立四个直属橡胶垦区。
当时,热带作物研究所设在广州,我是1957年初到广州,第二年就是"大跃进",我就把研究所搬到了海南,因为海南的自然条件更有利于进行橡胶的科学研究。
在研究所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一套人马,挂两个牌子。
当时海南没有大学,广州有一个华南农学院,我们就在儋州设立了一个华南农学院分院。
这是建国后国家在海南岛设立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后来发展成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两院归海南行署和农垦部双重领导,主要经费是农垦部给的。
马国川:
您既是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又兼任华南热带作物学院院长。
何康:
我们在海南办了三万亩农业试验场,实现了橡胶技术人才培养、橡胶技术研究、橡胶新技术推广"一条龙"。
当时提出"一统四包三结合","一统"就是党委统一领导,"四包"就是包科研、包教学、包生产、包推广,"三结合"就是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
同时对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地种植天然橡胶和热带作物进行指导。
马国川:
当时海南的条件一定很艰苦吧。
何康:
很苦啊。
刚去的时候都是住草棚,我把全家都搬到海南岛去,就是想在那里干一番事业。
我跟大家同甘共苦,艰苦创业。
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生活资料严重短缺。
于是就建立了副食品生产基地,种菜养猪,提供副食。
同时,我们当领导的也身先士卒与职工、师生一起劳动,开荒种甘薯、木薯、花生等粮油作物,改善生活,渡过暂时困难。
1960年周恩来总理来视察,看到我家门口写的一副对联:
"儋州立业,宝岛落户。
"总理对我说,可以改两个字,把"宝岛落户"改为"宝岛生根",生了根才能发展,知识分子才有用武之地。
我们确实在海南生了根,事业也有了大发展,把橡胶发展成为一个大产业。
外国都是在赤道南北纬10°以内种植橡胶,我们发展到北纬235°,突破了北纬15°橡胶种植的"禁区",这是一个重大的科研成就,为此曾于1982年获得国家一等发明奖。
我和同事们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即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头,我也没有受太大的罪,大家对我明斗暗保。
有一些学生年纪轻,要打两下,有人就抱着我,我实际上没受什么罪。
有一天晚上批斗完回来,我在家里看书,忽然有人敲门,夜里十一二点了,我打开门,没有人啊,后来看见一锅鸡汤。
过后才知道是试验场工人跟研究人员商量以后,炖了一锅鸡汤给我补身子。
"林彪事件"以后,我被"解放"了,任广东省农垦总局的副局长,主管教育和科研,同时还兼着两院院长。
一直到1978年调回北京,我为橡胶事业奋斗了整整二十六年。
科技兴农,挖掘潜力
马国川:
1978年您调回北京,在什么部门工作?
何康:
在农林部当副部长。
农业部成立于1949年10月,李书成为第一任部长。
当时农业部和林垦部分设,1954年廖鲁言继任农业部长,直到"文化大革命"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后,197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等部,合并为农林部。
1979年2月撤销农林部,恢复农业部、林业部和农垦部,我在农业部,还是副部长,主管农业区划、科技、教育、外事等,以后是常务副部长,慢慢管全面工作了。
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农业部、农垦部、国家水产总局合并设立农牧渔业部,林乎加担任部长,离休后我接任他。
马国川:
当时还有一个农委。
农委和农业部是怎么一个关系?
何康:
1979年,为了加强农业,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任主任,后来是万里,副主任有张平化、杜润生、李瑞山、张秀山和我共五位。
农口的涉农部门,其中包括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农垦部、农业机械部、水产总局、国家气象局等。
当时我还兼任农业部副部长和国家计委副主任。
杜润生主要工作是主管农业改革政策,我主管农业科技、教育和外事等工作。
马国川:
您回北京的时候,正是中国大变革的时期,尤其是农业。
何康:
一些地方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国家农委主任万里很有魄力,对农业又熟悉,还有安徽的经验,再加上杜润生本身是一个老干部,经历很丰富,熟悉农业和农村。
他们大力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我专程到山东菏泽地区的县、乡、村直至农户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总结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经验。
我应山东省政府邀请,在山东济南做了一次农业、农村问题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几百人。
马国川:
一个是搞生产关系,一个是搞生产力。
何康:
粮从哪里来?
要靠提高生产力,依靠勤劳,依靠科学。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积极性,勤劳有了,还要加上科学。
科学种田,才能提高产量。
1978年7月,我率领由26人组成的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美国。
这是中美正式建交前第一个访美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引起了美国朝野的重视。
历时40天,走遍美国主要农业生产区中西部14个州,参观了农业科研推广机构、大学农学院、农场牧场、种子公司、农畜产品加工厂以及农场主合作组织、农业展览会等102个单位。
我特别考察了美国的园艺场和农业教育,对美国农业的高生产率和当代农业的现代化格局有了具体了解,也认识到中国农业的差距,对美国现代农业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
访美归来,邓小平、叶剑英以及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亲自出席了汇报会,听取了我们的考察报告和结合中国实际所提出的七项建议。
马国川:
哪七项呢?
何康:
包括增加农业投资、发展社队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健全科教机构、建立种子公司、加强水土保持、实行农林牧三结合、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
我是从事科研出身的,深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我就提出,中国的农业要想发展,必须注重科学技术,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县,都要加强农业教育。
解决农业问题,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一定要重视智力开发,培养一大批既有知识、又掌握技术的人才,才能提高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
所以到农业部和国家农委工作后,我立即着手恢复与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的农业科研院所与高等农业院校,把被拆散、撤销和下放在缺乏科研教学基本条件不能开展工作的科研院校机构,想方设法迁回原址。
当时解决了一个复校办学的大难问题,就是把农业大学迁回原址办学。
"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农业大学(后改名为中国农业大学)被外迁到陕西省甘泉县的清泉沟和河北涿县,条件恶劣,根本没有办法办学。
"文革"结束后,农大强烈要求回到北京。
当时回迁的阻力很大,占用校舍的单位拒不退房,有人认为北京农业大学回北京增添了城市生活的压力。
我们顶住各种压力,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终于在1978年11月将农大搬回北京马连洼原址办学。
与此同时,我还与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多次商议,促成了南京农学院(后改名为南京农业大学)顺利地从扬州迁回了南京。
还有福建、甘肃等农业大学。
在抓好农业部的八所重点大学共16所部署院校的同时,倡导在全国农业大学中推进教学、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农科教结合工作。
我和教育部长何东昌联合发起成立了全国农科教结合办公室,由国务院发了专门文件,推动了这项工作。
在全国高中等农业教育中进行了若干项改革,特别是为农村基层和农业生产第一线培养了大批高质量人才。
在全国推行"绿色证书工程",培养农民科技示范户和农民技术员,已有一千多万农民获得了"绿色证书",并已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农民培训"项目。
我还极力争取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资助,支持农业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建设,引进先进设备,培养了大批能应用先进技术设备的人才。
在任期间,为了解决农民缺乏农村能源和改变农村的环境,在全国大力推进沼气建设,以点带面,逐步推广,持续发展。
目前已成为三农工作中的一个"利民计划",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马国川: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教育水平落后的国家,要求县一级都要有农业科学研究机构,谈何容易。
何康:
确实有困难。
因为农业技术都在科学院、大学里面,县里的农业局只有很少几个技术干部到处跑,也推广不了农业技术。
怎么把技术直接推广到农村?
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提出在县一级建立四级科研网,即从县、乡、村,一直到户。
不到户那就是空的。
如果只到镇上,弄个展览室,大家看着挺好,老百姓没有实惠。
中国八亿农民,两亿多农户,怎么培训?
最好是听喇叭。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中央农业广播学校,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所有农民进行科学普及和教育,广播频率覆盖全国。
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市、县、乡的五级办学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职业教育、农民科技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最大的基地。
马国川:
这也是全中国没有课堂的最大的学校。
何康:
我兼任这个广播学校的校长。
全国两千四百多个县,不少县长都是这个学校的学员。
在农闲时我们还安排一个月的面授,在这个学校修业及格的学生,可以获得中专毕业文凭。
二十多年前,能够有中专毕业文凭就不简单了,所以许多人都积极学习。
我们还在县里成立三结合的"农技推广中心",就是教育、科技、推广三结合,网络搭建起来,农业科技信息就能够真正流到农家的田间地头。
我们还争取到了国家对县一级建立技术推广中心的补助投资,全国每个县基本建成了一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当时,为加强对农技推广队伍的建设,向国家申请增加农业推广人员的编制,得到人事等部门的支持,一次得到了全国十万推广人员的干部指标。
此外,在推广和提高农业科技工作发展方面,我还十分重视和支持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农学会的组织领导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紧密合作,使科学技术进步在农业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专家的咨询参谋、审议作用,使他们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国川:
当时还有一个中央农业干部管理学院。
何康:
这是农业部直接办的。
我们发现,光有劲头不行,还要用马力大的拖拉机来带。
谁是马力大的?
县委第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他们不抓,底下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副县长力度就小多了。
"抓头头,头头抓",不解决这个问题,"肠梗阻",到他们那里就堵住了。
农业要马力大的人来拖,中央农业干部管理学院由此而生。
我们把这个学院设在北京农业大学里,专门培训省长、省委书记,地、市领导,特别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
当时还利用省委书记、省长到中央开会的机会,事先沟通联系好,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花个一两天时间,找最有名的教授、校长给他们授课,我自己也去讲。
一般第一讲都是由我来,主要是讲宏观形势及政策。
全国有什么新的东西,带他们参观一下,他们有了兴趣,把这些东西带回去,推广力度就大得多了。
马国川:
中央农业干部管理学院相当于成人高等学校吧。
何康:
对,直属于农业部的成人高等学校,在二十多年前是很被认可的。
在当时,学历成了大问题,"升官"要有文凭,而许多地方领导都没有上过大学。
农业部就和教育部商量好,许多地方领导有很多实际经验,实际经验比大学教授强多了,就是没有系统受过教育,补上这一课就行了,我们中央农业干部管理学院可以发相关培训证书。
这样一来地方领导来学习的积极性高涨了。
我们还建立中央农业干部管理学院与各大区依托国家重点高等农业院校建立分院,有计划地培训从县到省的各级主管农业行政领导干部。
另外,我们还把各门课程中最好老师的讲课内容制成录音带,下发到偏远县份。
学院设总院和分院两级,总院设在北京,下属分院设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内,覆盖全国各地,形成包括农、牧、渔、农机等各方面的干部培训系统和网络,为有计划地开展农业系统干部培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国川:
听说您在部长任内去过上千个县,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
何康:
没有那么多县,而是主要的农业县,每个省区倒是都去过了。
我就是想推动农业科技在全国的普及。
因为中国在用世界上7%的可耕土地养活世界20%的人口,解决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就是提高单产,而提高单产就不能靠天吃饭,必须主动出击,有所作为。
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工业还拿不出力量支援农业,所以农业工作者应该从自身角度挖掘潜力。
我坚信,如果做好这一点,我国的农业可以大进一步。
"农产品的出路在于商品化"
何康: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了108项重大科技攻关课题,第一项就是开展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研究。
1979年7月,在我的建议下,召开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会议。
会上,我引用大量数据,着重说明我们再不能满足于"地大物博"那个笼统的概念。
要发展农业,首先必须摸清家底,掌握全国土地、气候、生物、水等一系列的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情况,做好区划工作,才能更好地因地制宜,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安排措施指导生产。
也只有掌握了全面的资源情况,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进行农业区划,建立商品粮、棉等基地,培养相应的人才,逐步走向农工商一体化。
会后,成立了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副总理王任重担任主任,后来万里、宋平、陈俊生等都曾经担任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我一直兼任农业区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具体组织领导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目的是要把农业自然资源调查清楚,根据不同的条件作出农业区划,在区划基础上,制定发展农业、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划。
最后我们完成了《中国农业资源调查报告》,摸清了农业资源的家底。
这些成果的问世,为农业区域开发的国家投资立项和农林牧渔各类商品基地的建设以及重点开发项目的确定,提供了依据。
全国两千多个县,哪个县适合干什么,一看就清楚了。
把家底摸清楚了,确定商品粮基地就有根据了。
马国川:
为什么要建立商品粮基地,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何康:
我国人口众多,除了现有人口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所消耗的粮食外,还要解决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饲料等工业的增长需要,这就要求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建立一批能解决粮食产销矛盾的商品粮基地。
还有,长期以来,农业投资习惯于撒胡椒面,加上管理不严,收效不大。
农村改革以后,全国的粮食供求形势迅速好转,政府也对农业及粮食生产有所忽视,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支出中,农业投资占的份额下降。
同时,由于乡村非农产业迅速扩展,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户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投资也相对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为更加集中地使用有限的资金,调动地方及农户增加投资的积极性,我们就大胆改革,选择具有发展粮食生产优势,能够稳定地提供较多的商品粮,在地区上连片分布的产粮区,以县为单元,建设商品粮基地,一个基地给启动资金几百万,以后每年给几百万,几年验收,最后拿出多少商品粮交给国家。
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技推广网络、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小型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农机具配套等方面。
另一方面,我逐渐认识到,粮食商品化才是实现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购买力的根本途径。
以前,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粮食市场,没有一个开放的市场,都由国营粮食部门统一定价、统一定级、统一购销,因此粮食市场化程度低,都是农民留足自需后,"多余"的卖给国家,超过国家征购任务的部分,国家以较高价格收购,形成一个"准市场"。
但是这种"多余"粮食的"准市场"实际上是在农民之外进行循环和交换平衡的市场。
在这种条件下,市场的调节弹性小,稳定性差。
当农业丰收,"多余"量大时,很快出现供过于求,农民卖粮难,价格下降,谷贱伤农;当农业歉收,"多余"量少时,马上出现供不应求,严重时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这也与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业生产规模小、分工不发达密切相关。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粮食的商品化。
粮食商品率是反映粮食生产发展水平和商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世界粮食生产大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的粮食商品率都比较高。
可是我国粮食生产仍以自给性为主,粮食商品率普遍较低。
为什么要建设"商品粮基地",为什么叫做"商品粮基地"?
其深层含义就在这里。
马国川:
建立商品粮基地以后,效果明显吗?
何康:
很明显。
如1983年,我国在黑、吉、皖、豫、苏、赣、湘、鄂八个省,选建了50个商品粮试点县,经一年的建设已形成一定规模新的生产能力,第二年提供的商品粮就占同年全国商品粮总数的八分之一,对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说明,集中一定的资金,建设一批有粮食优势的生产基地,是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好办法。
建立商品粮基地的好处是明显的:
第一,有利于粮食生产地区专业化的形成,充分发挥粮食生产的地区优势。
第二,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粮食生产的专门技术水平。
第三,能够较快地提高粮食生产商品率。
第四,商品粮基地的合理布局,可以减少粮食的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