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同欧洲的比较.docx
《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同欧洲的比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同欧洲的比较.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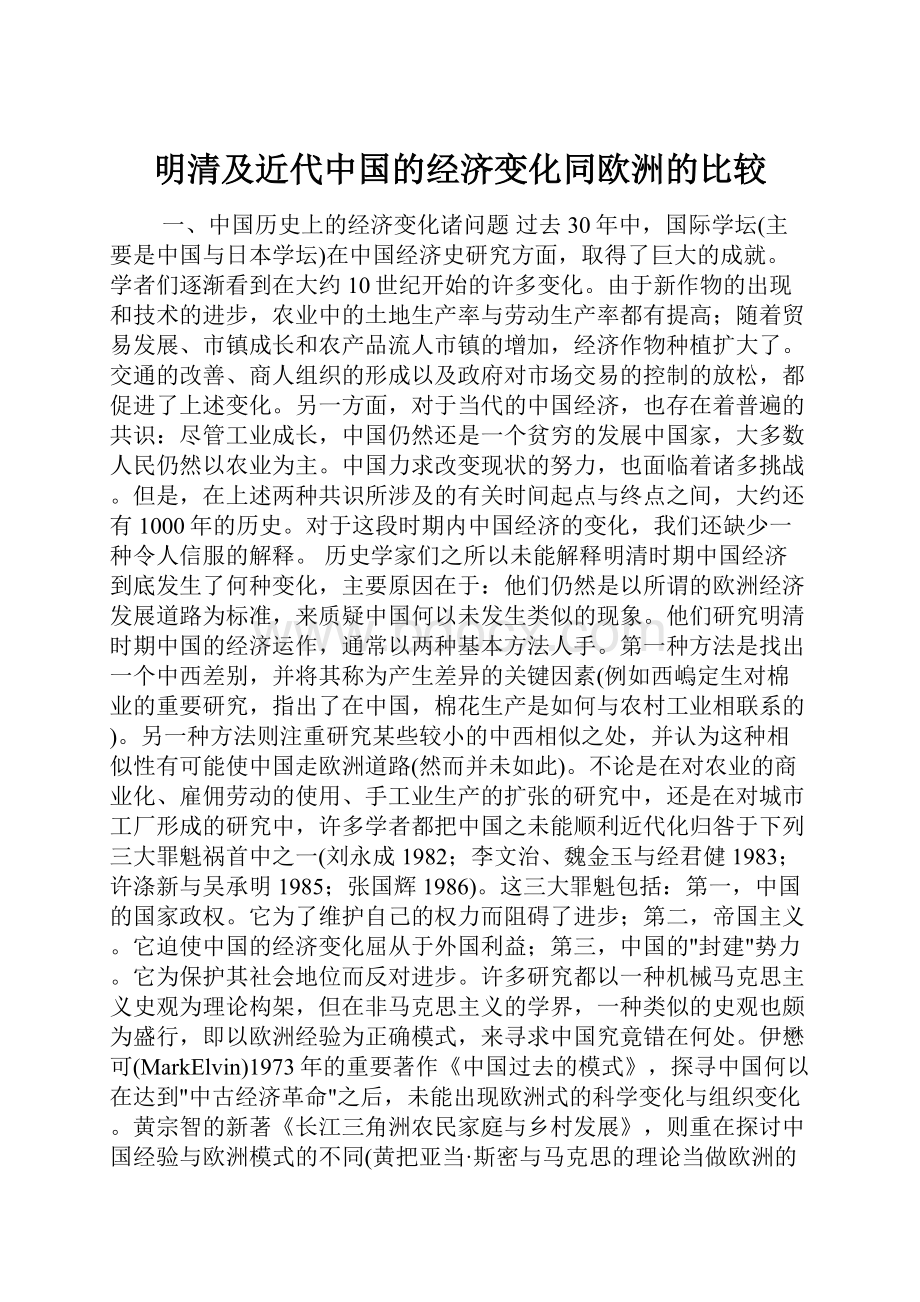
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同欧洲的比较
一、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化诸问题过去30年中,国际学坛(主要是中国与日本学坛)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学者们逐渐看到在大约10世纪开始的许多变化。
由于新作物的出现和技术的进步,农业中的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随着贸易发展、市镇成长和农产品流人市镇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扩大了。
交通的改善、商人组织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市场交易的控制的放松,都促进了上述变化。
另一方面,对于当代的中国经济,也存在着普遍的共识:
尽管工业成长,中国仍然还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仍然以农业为主。
中国力求改变现状的努力,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但是,在上述两种共识所涉及的有关时间起点与终点之间,大约还有1000年的历史。
对于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变化,我们还缺少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未能解释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主要原因在于:
他们仍然是以所谓的欧洲经济发展道路为标准,来质疑中国何以未发生类似的现象。
他们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运作,通常以两种基本方法人手。
第一种方法是找出一个中西差别,并将其称为产生差异的关键因素(例如西嵨定生对棉业的重要研究,指出了在中国,棉花生产是如何与农村工业相联系的)。
另一种方法则注重研究某些较小的中西相似之处,并认为这种相似性有可能使中国走欧洲道路(然而并未如此)。
不论是在对农业的商业化、雇佣劳动的使用、手工业生产的扩张的研究中,还是在对城市工厂形成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把中国之未能顺利近代化归咎于下列三大罪魁祸首中之一(刘永成1982;李文治、魏金玉与经君健1983;许涤新与吴承明1985;张国辉1986)。
这三大罪魁包括:
第一,中国的国家政权。
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阻碍了进步;第二,帝国主义。
它迫使中国的经济变化屈从于外国利益;第三,中国的"封建"势力。
它为保护其社会地位而反对进步。
许多研究都以一种机械马克思主义史观为理论构架,但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界,一种类似的史观也颇为盛行,即以欧洲经验为正确模式,来寻求中国究竟错在何处。
伊懋可(MarkElvin)1973年的重要著作《中国过去的模式》,探寻中国何以在达到"中古经济革命"之后,未能出现欧洲式的科学变化与组织变化。
黄宗智的新著《长江三角洲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则重在探讨中国经验与欧洲模式的不同(黄把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理论当做欧洲的理想模式)。
这种关于中国经济史"缺少什么"的探索,也不仅限于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
约翰。
霍尔(JohnA.Hall)从欧洲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世界历史作了范围广阔的评述。
在其著作中,他也谈到了中国"对市场的制度性障碍"。
同时E.琼斯(E.L.Jones)在其第二部饶有兴味的比较经济史中,指出若以欧洲的政府政策为标准来看,中国的政府是"很不尽责的"。
从而阻碍了发展(霍尔1985:
56;琼斯1988:
141)。
上述各种对中国经济变化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国的经济在宋代有一重大变革;此一变化并提供了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寻找阻碍向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罪魁。
E.琼斯虽决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经济一旦上了轨道,就会持续自我再生产。
除非是被某些没有道理的干预使之越出轨道,否则经济成长仍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对于中国,他认为政府是一种负面力量,既未为经济的持续成长提供必要的构架,又阻碍了原有的积极发展。
他代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
一方面认为国家太过软弱,以致不能积极有为;另一方面则又认为国家十分强大,足以对进步起否决作用。
[!
--empirenews.page--]大多数学者都在探索寻找某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障碍。
少数学者则想找出中国所缺少的关键因素到底何在。
在这类研究中,最有名的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把基督教新教精神与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信仰所作的对比。
但是,新教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论点,在好几方面是有限制的。
首先,天主教地区也有经济变化。
而在欧洲之外,对于宗教与经济变化的关系争议更大。
关于中国,余英吋近来证明,16、17世纪儒家的新思潮,与当时随商业迅猛发展而兴起的独特的商人观念,是相并出现的(余英吋1987)。
关于18世纪的日本,名下的研究显示,一批大阪商人,从儒家世界观中,也为自己赢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名下1987)。
由于两方面的理由,我们很难对以下见解避而不谈,而这些见解已证明是对社会变化至为重要的。
第一,中国与欧洲的情况都指出:
相似(或至少是部分相似)的思想变化,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社会中,并且也不一定以相同的经济变化为动力。
第二,欧洲天主教与新教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指出:
无论是有宗教变革的地区,还是没有宗教变革的地区,都能经历相同的经济变化。
思想信仰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关联,实在非常复杂。
我们不能把这种关联简单化,从而对宗教信仰会对经济行为有何影响的问题,持一种简单的看法。
要借助中国经济史上并未发生之事来解释已经发生之事,会有一些困难。
一方面,有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欧洲范畴。
而上述做法使得对这些中国实际情况的评价大成问题。
这一点,我在本书"中编"还要进一步讨论,因为欧亚各地在国家形成与政治经济方面的差异,似乎部分地是被坚持采用欧洲标准的做法蒙蔽了。
另一方面,上述做法使得解释变得太容易。
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是许多变化的结合,具有众多的历史特定因素。
找出差别并不很费力,但如果缺少一些主要的分析标准,就很难评价这些差别有多重要。
我们可以把能用普通逻辑进行解释的那些相似之处做为底线,然后去找这样的分析标准。
一旦有了这种标准,我们就能在可以找到重要的早期差别的地方,也找到基本的共同性。
然后,可以导人其他的差别,以探讨欧亚不同地区所走的独特道路。
然而,如不首先辨认找出一组共同之处,就无从确定什么差异最值得注意。
下面,我就从亚当·斯密开始,讨论上述相似之处。
二、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的动力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较高生产率。
人们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较丰的利润。
劳动分工仅止受市场大小所限。
市场扩大,给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
分散化的价格体系拓宽了市场范围,并且也扩大了从劳动分工获得的优势(布劳格[Blaug]1985:
61)。
这些经济扩张的动力,都受制于人口的节奏以及难以预见的收成波动。
与1348-1350年间黑死病有关的人口损失,大大减少了从黑海到地中海,然后再到北欧的整个欧洲的人口。
城镇受祸最烈,引起了许多经济后果。
首先,近代手工业被摧毁了,城市间的贸易也衰落了。
其次,城市对农业产品的需求下降,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弃农就牧的转变。
西欧的人口与经济在黑死病之后逐渐恢复,到16世纪时,在人口总数与农业总产量方面都达到较以往更高的水平。
[!
--empirenews.page--]在15、16世纪,为了支持远程贸易,一种新的金融经济出现了。
银行与交易机构的完善化,使越来越复杂的交换方式成为可能,而这些交换方式又都承认劳动分工与生产专业化。
然而,这些发展都以脆弱的农业经济为基础。
收成情况决定了每年度的食物价格波动,后者又严重影响到制造业中的劳动成本。
每当连续的歉收提高了手工业与制造业的工资,非农业的生产通常就会下降,结果是歉收引发工业与农业的循环衰落。
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Labrousse)对这种循环做了详尽的分析。
这项著名的研究指出19世纪以前的经济,具有由长时间的成长阶段和衰落阶段构成的周期性。
欧洲经济的逐渐恢复与而后的成长,表现为持久的波动。
这种波动包括:
欧洲大陆最活跃的经济中心,发生了意[1][2][3][4][5][6][7]下一页义重大的转移。
随着新的市场网络的发展以及纺织品生产和其他手工产品生产的变化,旧有的地中海地区经济中心,逐为北欧经济中心(特别是荷兰与英国的经济中心)所取代。
因此,如果仅止把注意力放在成长最快的地区的话,欧洲的经济成长特别显著。
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一个更大的欧洲,并且承认各个地区经济是此兴彼衰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更容易看到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所面临的更大极限。
17世纪欧洲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人口的剧增。
其影响所及,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领域。
人口因素有助于解释当时人民所面.临的困难,如30年战争及法国的佛隆第(Frounde)之乱,均与人口的增加有关。
此外,人口的增加亦受经济能力所限。
这一点可从法国的人口趋势看出。
法国人口在1560、1630、1720及1730年代均曾达到其上限,约为2000万左右(勒·罗伊·拉杜里[LeRoyLadurie]1987:
269-270)。
马尔萨斯主义者对人口危机的恐惧,在对17世纪的分析中获得了支持。
但是在18世纪,当令的是另一位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一一亚当·斯密,其思想看来更加合适。
斯密从增加贸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而贸易又以劳动分工和相对优势为基础。
在18世纪,欧洲许多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日益卷入商业。
英国在18世纪摆脱了大饥荒的威胁;在同时期的法国,生存危机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严重。
斯密所分析的欧洲,处境肯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但尚未开始其19世纪的城市工厂工业化,而正是这种工业化,导致了社会与经济的根本变革。
斯密《国富论》时代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所以无怪乎斯密强调农业投资,假定经济成长有限度,并认为实际工资最终会下降到维持生存的水平。
马尔萨斯与斯密生活在同一个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很有限的世界。
斯密的世界并不是19世纪的欧洲。
在主要方面,18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之间的共同之处,超过18世纪的欧洲与19、20世纪的欧洲之间的共同之处。
三、斯密型动力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
在16至19世纪,中国许多地区都存在斯密型动力(译者按:
即亚当·斯密所指出的经济成长动力)。
即使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看出斯密的原则,并以此来解释当时中国经济变化的许多方面,但是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手工业与贸易的发展的主要特点,在中国与日本史坛早已众所周知。
最著名的是长江下游地区丝、棉业的发展。
这两项主要手工业,连同水稻以及其他经济作物,创造了中国最富足的区域经济。
长江上中游省份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中特别是湖南)所产的稻米,大量沿长江而下,以养活长江下游地区人口。
市场的扩展,把越来越多的地方联系起来。
上述省份中的若干地区,也出现了棉花、靛青、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与相应的手工业,以及陶瓷、纸张等手工业(许涤新与吴承明1985:
82-95,143-155,272-276)。
今日的长江及其支流和与长江相连接的运河,承担了中国大约80%的水运运量。
长江流域集中了中国1/3的人口,农业产量则占全国的40%上下(凡·斯莱克[VanSlyke]1988:
16)。
[!
--empirenews.page--]市场扩展在长江沿岸为最明显,但并不限于这一广大地区。
在华南一些地区,经济作物种植与手工业也在扩大。
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产甘蔗、水果、蚕丝、棉花、桐油、麻油等,佛山铁业则是主要工业的代表(唐森与李龙潜1985;罗一星1985)。
在东南沿海,16世纪的对外贸易刺激了茶叶与蔗糖的生产(罗友枝[EvelynRawski]1972)。
中国北方的市场扩展不如南方那样明显,很大原因是水运局限。
但即使是在北方,经济作物种植也在扩大,手工业和贸易也在发展。
大运河沿岸城市如临清,成为主要商业中心,商人云集于此,贩卖布匹、粮食、陶器、纸张、皮革、茶叶、食盐等(许檀1986)。
天津地区成了鱼盐贸易中心;在山东省,市场的发展更为普遍,而且棉花与烟草的种植尤为注目(郭蕴静1989;李华1986)。
随着商业化把相距遥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经济活动联为一体,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提高的征兆。
有的学者认为:
市场刺激对华中与华东南地区农作方法的改进、灌溉的扩大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至为关键(罗友枝1972)。
关于长江下游以及中国其他地区土地生产率的资料很分散。
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表明自lO世纪以后,亩产量一直在提高。
有一些迹象显示出长江下游的土地生产率很高,并已名列全国榜首,但到18世纪出现下降(在一些孤立的例子中,更被他地超过)。
一般而言,土地生产率增加,是由于多施肥料、培育更加适合各地土质的抗灾作物品种以及采用更有效的耕作技术而致(李伯重1986A;闵宗殿1984;黄冕堂1990)。
虽然从比较优势与专业化获得的好处不断增加,但18、19世纪中国所增加的人口中,有一部分却转向较为贫瘠的土地和收入微薄的职业。
这个时期山地的开发,常常是杂粮作物种植与经济作物种植及手工业并行。
陕西省南部的例子,很有启发性。
在明代后期,这一地区曾经成为战场。
清代建立以后,移民重新开发这一地区,不久人口就超过了明代水平。
新的粮食作物一一玉米与马铃薯,补充了粟、麦之不足,养活了包括从事木材贸易、造纸和制铁的人员在内的本地人口(方行1979;谭作纲1986;萧正洪1988;陈良学与邹荣楚1988)。
在这一颇为偏远而且决非肥沃的土地上,仍然出现了发展。
而市场交换,是农民所获成功的基础。
但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基本资源潜力劣于长江三角洲等生态优良的地区,所以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水准也不可能赶上情况较佳地区。
同样的逻辑也大致适用于清代开发的其他许多山丘地区(傅衣凌1982;张建民1987)。
因此,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即使在斯密型动力创造了经济变化的同时,不断增加的人口迁往生产条件较差的地方,从而减弱了斯密型的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①在16与18世纪之间,中国的不同地区都经历了经济扩展的周期。
16世纪的经济扩展,以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为最。
新的商人组织创造了扩大交换的方法,不仅把中国的主要城市彼此联结,而且把主要城市同市镇网络以及各市镇周遭农村也都联结为一体。
明代末年的暴乱和满人人侵引起了经济的衰落。
而后,到了18世纪,抛荒的土地还耕了,新一波的商业扩展席卷了中国更多的地区。
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成长帮助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成长。
华北与东北的若干地区生产也增长了。
斯密型的经济扩展到处可见。
[!
--empirenews.page--]_________________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移民都是朝向不太肥沃的地区。
四川的再垦殖和满洲的开发,就是移民到肥沃地区的明显例子。
19世纪的经济发展如何呢?
大多数中外学者对1850至1950年间的中国经济,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洋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帝国主义扭曲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且堵塞了中国走欧洲道路的可能性(严中平1989)。
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则认为:
洋人为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开创了机会并提供了技能与技术(侯继明1965;登伯格[Demberger]1975)。
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弄清楚的一点是:
在贸易机会方面(这种贸易机会的原理与前几个世纪中贸易机会的原理并无不同),中国大多数人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外国的影响?
我认为:
新的商业机会扩大了斯密型动力运作的空间,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斯密型动力。
国外市场对中国各地的影响,以靠近交通中心和交通干线的地区最著。
这些地区包括通商口岸、洋人享有治外法权的城市以及在水运条件不佳地区所建铁路的沿线。
铁路特别刺激了中国北部铁路沿线地区的商业化。
这些地区因而开始种植烟草、花生、芝麻和大豆。
国外需求也促进了长江流域诸省和华南地区的桐油生产(刘克祥1988)。
但是,对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中国经济变化的评价,一些美国学者新近却提出了与斯密型动力相左的看上一页[1][2][3][4][5][6][7]下一页法。
四、对斯密型动力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罗伦·布兰德(LorenBrandt)在其新近出版的书中,以1890年至1930年间长江中下游沿岸诸省(即华东与华中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增进为基础,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出了一些引入注意的估计,并且认为这主要是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整合的结果。
他通过各种间接估计,得出以下结论:
在1890年代与1930年代之间,华东与华中地区的人均收入增加了44%,农业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40%(布兰德1989:
133)。
然而,即使我们接受他所作的这些估计,仍然必须承认:
增长的基本动力属于斯密型动力。
布兰德故事的主角是市场,故事情节则披示了专业化与市场整合所能带给人们的一切。
由于其放事中的人们生活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是:
如果市场在中国各地都会带来成功的话,那么在布兰德所研究的地区,市场的运作一定最佳。
国际贸易无疑为中国产品开创了新的市场需求,但是由市场驱动的发展逻辑,仍属嘶密型动力的变种。
这种发展逻辑在中国早已存在,并非由欧洲人带来。
而且,无论这种逻辑以国际贸易的形式表现得如何强有力,其推动力也并不是没有限度的。
如果布兰德所作分析正确的话,那么由国际贸易所代表的斯密型动力,就比过去研究所指出的更为重要。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布兰德的结论。
他的结论有若干部分依赖于未经证实的假设,而且这些假设又互为依据。
这种循环论证的假设之一例,见于其对农村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所作的估计。
布氏首先根据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对1893年人口的估计和1953年的人口晋查数,提出在1890年代与1930年代之间,华东与华中的城市人口增加了1000万-2000万(布兰德1989:
72、73)。
既未提出任何资料,也未作进一步论证,布氏接着又指出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以同样的比例增加。
这个人口变化,对他后来估计农村非农业人口所需要、而又经过交换的农业剩余产品的数量,至为重要。
他相应地假设,在1890年至1930年之间,经济作物的贸易量增加了1/3-1/2。
但他依然没有清楚地说明此假设为何最为可能,而只是着眼于此假设与其所作的以下另一假设相一致一一非农业人口对经济作物的需求以一个确定的比率增加,从而符合他假设的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情况。
接着,他又得出了其对商品化水平的估计,这个估计自然与上述所有假设相符。
然而,这些估计只有在其赖以设立的各种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除非有关假设得到更充分的实证研究的支持,否则布氏的上述所有论证,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很薄弱的。
譬如,如果我们假设华东与华中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在1890年已很多,而且在而后的40年中增长得并没有城市人口那么快,那么人均商品化增长的估数就会变小。
要是我们相信1890年时经济作物的贸易量可能比布兰德所推测的数字高,而且1930年的贸易增长率也不可能升到16%以上,那么我们又可以把布兰德引入注目的高数字大大压低。
[!
--empirenews.page--]说实在的,并没有多少理由相信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会像布兰德假设的那样迅速增加。
特别是如果你像布氏那样,相信劳动市场会顺利地运作并根据劳动的边际生产来配置劳动资源的话,那么你就没有理由相信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会迅速增加。
在布氏所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
由于近代工厂的技术条件较之传统手工业企业更佳,劳动组织更为严格和有效,因此流动劳动从手工业转向工厂工业,将会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和工资。
当人们转到报酬较高的工厂工作时,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将会保持不变或缩小。
这比布氏所说的农村非农业人口增长,更属可能。
反之,如果劳动市场并未如布兰德假设的那样顺利运作,农村中非农业部门的工资将会更低,从而对粮食和其他货品的需求也将会比布氏所推测的为低。
布兰德的数字可信与否,还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检测。
如果我们同意他所说的农业年增长率为1.2%-1.5%,并把此增长率应用于1895年至1935年间的40年,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解释其所默认的结果的规模呢?
这样的成长率意味着1935年的农业总产量,比1895年增加了60%-80%。
然而,在某些地方,1.2%-1.5%的年增长率,至少对几年而言还是可以讲得通的。
但是在40年中以此速率连续增长,情况就非同小可了。
谁要为布兰德的农业成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数字辩护,就必须找到确切的证据,说明导致生产发展的原因何在。
但是布氏在其书中,并未提供很多资料(如农业部门中的技术改良或大量资本投入等),以证明经济规模的扩大。
商品化的发展和贸易条件的改善,无疑提高了1895-1935年间的农业产量,但是这两个原因是否能够充分说明布氏所作的那些估数,却完全取决于他在计算中所作的各种假设。
布兰德对斯密型动力的功效所作的热情讴歌,我看似乎太过分了。
而与此同时,黄宗智却拒绝以斯密理论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变化的一个向导。
黄氏相信:
斯密研究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并无此现象。
髓后,他又以此作为其论证的前提。
如果斯密心目中的近代经济确实是以商业发展为先导、而商业发展又是通向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当然可以推断说在中国肯定有另外一种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商业。
以此为基础,黄氏力求把华北及长江下游的情况从欧洲经济变化的范畴中分离出来。
黄氏旨在勾画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的历史独特性,这自然应予赞扬。
可惜的是他未能抓住良机,把他关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证据与论述,放到发展经济学的比较研究的框架之中。
根据发展经济学,劳动过剩的现象会导致就业不足或隐性失业。
早在1954年,W·阿瑟·路易斯(W.ArthllrLewis)就在其《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章中指出:
假定有一种由资本主义性生产部门和糊口性生产部门所组成的经济,那么在此经济中,资本主义性生产部门的成长,会以不变的工资,把劳力从糊口性生产部门中吸走,原因是劳力供过于求。
路易斯在这篇文章中,刻意以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来补充新古典经济学派对较为发达地区的经济所作的分析。
以此文为开端,发展经济学家创建了"二元经济"学说的主干。
虽然黄宗智声称反对"二元经济论"(黄宗智1990:
115-116),但是他对城乡这两个部分所作的区分,与在某些受路易斯启迪的发展经济学论著中出现的区分,并无二致。
而他对市场工资与家庭劳动所作的特别区分,更显示了一种二元经济。
因此黄氏的论述与发现,可以归人发展经济学关于过剩劳动的一个根本性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一方是西奥多。
舒尔茨(了heodoreSchultz),他反对隐性失业之说。
另一方是W·阿瑟·路易斯。
黄氏书中引用了舒尔茨的话,并反对舒氏关于农业市场的观点。
至于路易斯,黄氏未援引其文,但至少就某些地区而言是含蓄赞同其观点的。
[!
--empirenews.page--]黄氏声称:
自1350年代至1950年代,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一直停留在一种糊口(或维持生存)的水平。
但是"糊口"的涵义,并不完全清楚。
因为在1350年代很少有人穿棉布,而至1850年代绝大部分人(基本上是所有人)都穿上了棉布,所以棉布消费的这广变化,表现了生活水准的提高。
有关明清人士对普通百姓生活日益奢侈而深感忧虑的史料,在中日两国明清史研究中比比皆是。
如果在黄氏所研究的6个世纪中,一直是"糊口农业"(或"维持生存的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话,上述情况怎么可能出现呢?
除非是人民减少对其他一些物品的消费或者改用劣质品,否则,当棉布消费增加时,整个生活水准实际上也提高了。
此外,"糊口"的涵义,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黄氏未能对一种"糊口"性的经济明确下定义,同时也未能对生活水准作精确计算。
他所作的讨论,主要是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
这一差别很重要,因为讨论的中心问题现在变成了:
此上一页[1][2][3][4][5][6][7]下一页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在黄氏所论的长时期中,是如何维持下来或被改变了的?
在中国,没有出现那种将经济推向近代成长进程的突破性经济变化。
对于这一点,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并无争论。
对一些学者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何未发展起资本主义的问题;而对另一些学者而言,问题则在于解释中国经济所特有的动力是什么。
黄宗智明确说他所研究的重点在后者。
但是,哪些特点他认为值得讨论,哪些问题他觉得无关紧要,却又取决于前者。
黄氏关于糊口性经济的观点,与柏金斯(DwightPerkins)关于14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中国人均产量保持不变的看法(柏金斯1969),大体一致。
柏氏假设在以往的六个世纪中,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大致相同;他同时又对亩产量的增加、耕地的扩大和人口总数的变化,作了估计,以此来证实其关于人均粮食消费不变的假设。
粗看之下,柏金严关于人口与资源保持普通平衡的看法,与黄宗智的观点颇为相符。
但是,与黄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