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邓伟门轻轻地敲.docx
《摄影师邓伟门轻轻地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摄影师邓伟门轻轻地敲.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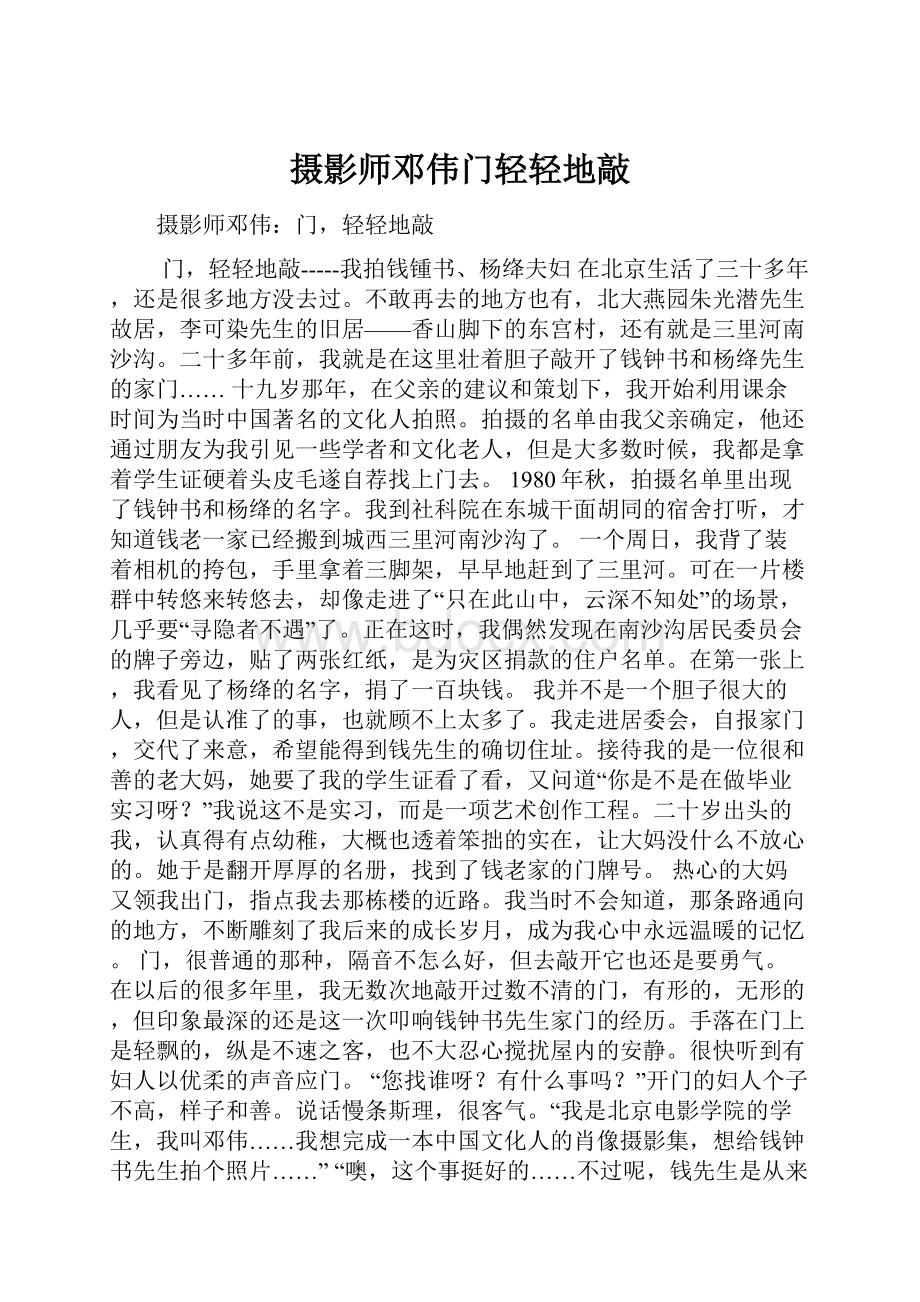
摄影师邓伟门轻轻地敲
摄影师邓伟:
门,轻轻地敲
门,轻轻地敲-----我拍钱锺书、杨绛夫妇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还是很多地方没去过。
不敢再去的地方也有,北大燕园朱光潜先生故居,李可染先生的旧居——香山脚下的东宫村,还有就是三里河南沙沟。
二十多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壮着胆子敲开了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家门……十九岁那年,在父亲的建议和策划下,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为当时中国著名的文化人拍照。
拍摄的名单由我父亲确定,他还通过朋友为我引见一些学者和文化老人,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拿着学生证硬着头皮毛遂自荐找上门去。
1980年秋,拍摄名单里出现了钱钟书和杨绛的名字。
我到社科院在东城干面胡同的宿舍打听,才知道钱老一家已经搬到城西三里河南沙沟了。
一个周日,我背了装着相机的挎包,手里拿着三脚架,早早地赶到了三里河。
可在一片楼群中转悠来转悠去,却像走进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场景,几乎要“寻隐者不遇”了。
正在这时,我偶然发现在南沙沟居民委员会的牌子旁边,贴了两张红纸,是为灾区捐款的住户名单。
在第一张上,我看见了杨绛的名字,捐了一百块钱。
我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但是认准了的事,也就顾不上太多了。
我走进居委会,自报家门,交代了来意,希望能得到钱先生的确切住址。
接待我的是一位很和善的老大妈,她要了我的学生证看了看,又问道“你是不是在做毕业实习呀?
”我说这不是实习,而是一项艺术创作工程。
二十岁出头的我,认真得有点幼稚,大概也透着笨拙的实在,让大妈没什么不放心的。
她于是翻开厚厚的名册,找到了钱老家的门牌号。
热心的大妈又领我出门,指点我去那栋楼的近路。
我当时不会知道,那条路通向的地方,不断雕刻了我后来的成长岁月,成为我心中永远温暖的记忆。
门,很普通的那种,隔音不怎么好,但去敲开它也还是要勇气。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无数次地敲开过数不清的门,有形的,无形的,但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次叩响钱钟书先生家门的经历。
手落在门上是轻飘的,纵是不速之客,也不大忍心搅扰屋内的安静。
很快听到有妇人以优柔的声音应门。
“您找谁呀?
有什么事吗?
”开门的妇人个子不高,样子和善。
说话慢条斯理,很客气。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我叫邓伟……我想完成一本中国文化人的肖像摄影集,想给钱钟书先生拍个照片……”“噢,这个事挺好的……不过呢,钱先生是从来不喜欢拍照的,更不喜欢上什么书或者是画报,像你说的名人录,他就更不感兴趣了。
非常谢谢你。
”说完,妇人客气地关上了门。
对于钱先生的澹泊我是早有耳闻的,所以并不因了这样的遭拒而灰心。
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钱家门口,等待着再次积聚起全部的勇气,第二次敲响了面前的这扇门。
开门的依然是刚才的那位妇人,“您怎么还没走呀?
不是已经告诉您,钱先生不同意拍照吗?
”她依然和颜悦色地说。
妇人的平和多少缓解了一些我的忐忑,我忙说:
“钱先生不同意拍摄,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她是翻译家和文学家,我也想为她拍照。
”妇人笑笑,说:
“我是杨绛。
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
我们也不算什么名人,不想凑这个热闹。
”我忙请杨绛女士原谅我的冒昧,并再次说明经历了“文革”之后,很多文化老人已经不在,健在的很多人也年高多病,我实在是希望能做一点文化抢救的工作。
杨绛女士点点头,“你的动机很好,我看您也是个很努力的青年。
但是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夫妇俩都不能接受您的这个邀请,再一次谢谢您。
”门在礼貌的谢绝后又紧紧地关闭了。
我仍然不想离开,静静地站在那里。
不时有邻人说笑着经过我的身边,被搅动过的空气静下来,显得格外空落。
不知过了多久,我面前的门又被打开了。
杨绛女士好像是准备出门的样子。
“呦,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呀?
”她吃惊地问。
我老实回答:
“我还是在等……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钱先生本人见见面,跟他谈一谈,看看他有没有兴趣……”这时,一个人从屋里走了出来,说道:
“那好,我就跟你谈谈。
”他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气质沉稳。
身上蓝色的对襟上衣已经洗得有些发白,脚上是一双布底鞋。
“我就是钱钟书。
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我很感谢你的诚意,你请回吧。
”我说:
“钱先生,今天能见到您,真让我高兴。
我想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意思。
我没有任何官方色彩,不受任何人指使,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希望拍摄一些像您这样的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物,现在大家都很想领略您们的风采……”钱先生伸出一只手摆了摆,“不要说这些,不要说这些。
我是不会让你拍照片的。
你还是走吧。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却还是不想放弃,“钱先生,我不会离开,还是请您考虑……”门“咣”的一声,又一次在我面前紧闭了。
我不知道继续等待是为了什么,只知道一旦离开,我将再也没有勇气重新叩响眼前这扇门。
我只是站着,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
或许已经过了十二点吧,不知谁家传来了菜进到油锅时“哗”的爆响,很快楼道里开始弥漫起依稀的饭香。
就在我的思绪被午间的各种响动引领开去的时候,面前这扇几开几合的门再一次敞开了,是钱钟书先生走了出来。
“我们商量一下吧。
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上午了。
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我忙说:
“这个不敢,这个不敢。
我是摄影专业的学生,我只是想用我学到的技巧和对您的理解,为您拍摄一张肖像照片……相机和三脚架我都带来了,现在就可以为您拍摄……”钱先生点点头:
“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
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
”我连声说行。
这时,钱先生又请过妻子杨绛,让我跟她也商量商量。
杨绛女士也破例地答应了我的拍照请求。
多少时常忆起的相见呢?
这个秋天的上午发生的事,在后来我还是常常想起。
其实,钱先生的“破例”,是一个多么大的让步,如果没有这个台阶,我都不知道会在他家门口站到什么时候呢。
对一个像我这般执拗任性的青年,他却是以诚相待,给予了一个长辈的极大的包容和迁就。
一周之后,我如约来到钱钟书先生家。
先生的家很简单、非常整洁。
水泥地面擦得很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上满满摆放的都是书。
钱先生和杨绛女士仍是穿着家常的衣服,朴素干净,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当我在相机标准镜头允许的最近距离—0.45米远的地方,为他们拍摄大特写镜头时,他们没有丝毫的紧张。
当镜头凑到钱先生跟前,我发现他竟然微微地笑了。
我不失时机地将他的笑容定格下来,同时不禁猜想,在先生的日常生活里也一定不会缺少这样会心的笑吧?
过了一个星期,我将放好的照片拿给钱先生看,“这就是钱钟书,就是我。
”他高兴地说。
杨绛女士也很满意。
“我要送你一句话。
”钱先生坐在桌旁,拿起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道“笔补造化天无功”。
“我给你翻译一下,翻译一下。
”钱先生接过笔,在纸上补充写道:
“相机能够弥补自然的不足”。
夫唱妇随的默契尽在不言中,让我好羡慕。
谈话间,钱钟书先生取出一本他写的小说《围城》送我。
他指着书的封面说:
“你看,‘围城’这两个字,是杨绛给我题写的。
”这时,杨绛女士也走过来,说道:
“我也应该送你一本书。
这本《干校六记》,书名是钱先生帮我题的。
”原来夫妇俩不仅是对方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而且,其中一位出书的时候,题写书名的活儿就由另一位包揽下来了。
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和许多我接触过的学者夫妇一样,生活简单,物质要求甚少,却以钻研学问为乐,追求着内心里的充实。
《干校六记》里写了这么一个插曲,当年,钱钟书夫妇被下放到农村后,就不得不分开了。
为了能有机会觅到钱先生,杨绛主动申请承担了给大家送信的任务。
一旦有信来,杨绛要步行很远,去到各个生产队送信。
但她却巴望着,因为可以顺路去探望负责看水渠的钱先生。
因为共同经受过风雨的洗礼,他们的感情弥深弥坚。
他们的爱并不言说,只是用尽一生去寂寞相守。
那些我目睹过的弦瑟和鸣的场景感染着我,不知不觉凝成我心中理想的婚姻生活的图景。
钱先生的性格有温文尔雅,沉静孤傲的一面,有时,又是开朗甚至是激昂的。
我曾见他一时兴起,在房间里踱着大步,高声行吟。
因为地面是水泥的,很光滑。
我生怕他浑然忘我,赶忙提醒他留神摔跤。
他反答道:
我不穿皮鞋,在这水泥地上怎会摔倒?
1982年,我作为摄影师参加了电影《青春祭》的拍摄。
在云南的外景地,我不知怎么患上了风湿痛,可能跟时常下河拍戏有关系。
当地的民间医生用梅花针为我治疗,倒是让我撑到了影片拍完。
可刚回到北京,我就突发黄疸性肝炎,住进了医院。
原来,是梅花针消毒不力,造成了肝炎病毒的交叉感染。
我病愈出院后,又过了些时间,才敢去拜会钱先生。
先生见到我很开心,他仔细地询问我身体感觉如何,在吃什么补药。
听了我的回答,他站起身,笑着说:
“这些天,你肯定吃了不少苦药。
我这儿有一种药,不过不苦,还很甜呢。
”他说完,大步流星地从里屋抱出一个大盒子,塞给我,我一看,是一箱蜂乳。
“我听你说治风湿在用虎骨酒,这酒对年轻人来说太烈了,我怕会有副作用。
以前杨绛也有风湿痛的毛病,她服用蜂乳,感觉挺不错的。
我们也给你买了一些,你试试看吧。
”我没有道理接受先生这么重的礼,连忙推却,解释说老北京有一个说法,药必得自己买给自己,否则就不灵验了。
先生听罢,开怀大笑,“天真,你可真是天真得像傻瓜……就是按你的说法,这蜂乳,顶多算是营养品,也不算是药。
你还年轻,养好身体太重要了!
”见我还是不肯接受,他走到桌边,提起毛笔,稍加思索,欣然落笔,行云流水般一挥而就。
之后,他招呼我说:
“我呀,送你两句话,改自苏东坡的名句。
希望你接受我们的这点心意,不要再推辞了。
”说罢,钱先生在刚刚书写的纸上,端端正正地加盖了印章,递给我,“因病得闲殊不恶,白蜂乞乳别无方”的诗句以先生特有的酣畅笔墨一下跃入我的眼帘。
二十年过去了,先生送的蜂乳早已消融在我的体内,他的充满幽默和关爱的题句我至今珍藏着。
每每翻看,如初的墨迹仿佛落笔于昨日,先生朗朗的笑声又在字迹间晌起,我也在神往中随了先生笑起来,突然恍觉先生已乘黄鹤西去,人间再无缘相见,不禁泪眼婆娑……十多年前,我计划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当时钱钟书先生得知后,是不赞成的。
他担心我既没有雄厚的资金又没有过硬的关系,一个人在海外,语言也不通,困难太大了。
他形容就像置身于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船上甚至没有桨,只能借双手向前划行。
这种情况下,要想靠岸,谈何容易。
1990年的春天,我即将赴英前,特意去钱先生家辞行。
先生晓得我的执拗,不再劝我。
那一天他的话不多,或许是预见了我的前路的不易,不免忧虑吧。
道别时,杨绛女士将四百元钱塞进我手里。
钱先生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穷家富路嘛。
我们虽然不赞成你走这条路,既然你非去不可,我们还是希望你一切顺利。
”正如钱先生所担心的,后来我在国外的生活,真的好似海上行舟。
我依靠日日打工谋生,同时只能用原始的寄信的方式,争取为全球各地的世界名人拍照的机会。
1991年8月,我按动快门,为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拍摄了肖像照,自此我的环球拍摄正式启动……1999年,在完成了为百位世界名人拍照的行程后我回到北京。
当年出游时刚过而立之年的我,此时已接近不惑,略显了中年的臃胖。
不久,我得知了钱钟书先生于年前辞世的噩耗。
1997年短暂回国时,我曾去医院探望钱先生。
当时他很虚弱,躺在病榻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
他的意识还清楚,只是语言表达已很困难。
当我向他汇报我的环球拍摄已经接近尾声,并且诉说起这些年里我对他的想念,却再也聆听不到他风趣的谈笑和睿智的教诲,只有漫起的泪水缓缓地从老人的眼角淌下来……这是阔别多年后,我和钱老的第一次相见,竟也成了今生今世我和钱老最后的别离。
一个早晨,阳光很暖和,我拨通了钱先生家的电话。
听筒那端传来了杨绛老徐缓的声音。
我本是希望登门拜会杨老,但她讲已经久不会客了。
因为每每再见熟人,情绪波动难抑,常常整夜不眠,造成血压高。
杨老说钱先生留下了很多手稿,那都是留给人类的财富,她必须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去加以整理,完整地留给后人。
听杨老讲,钱先生一直到临终,头脑都很清醒,最后的心愿是死后不举行告别仪式,不保存骨灰。
这个事有关方面经过请示,最终还是决定尊重钱先生的意思。
先生去世后,只是杨老和几个亲近的朋友到火葬场送行。
杨老一直陪钱先生至火化炉前。
火化之后,钱老的骨灰同许多普通百姓的骨灰一道,深埋入土,化作了春泥……放下电话,略略宽了些心,钱先生的文字日日陪伴着杨老,她的寂寥总是好过些吧。
“如果你惦念钱老,就写点什么吧。
”杨老说。
或许她是说,不必寻找一个外在的纪念地去瞻仰,当我们回忆起往事,当逝者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眼前,那就是开放在我们心灵里的纪念地,在这里思念与生命同样绵长。
几天前,偶然经过三里河,静静地站在南沙沟那个我熟悉的院落前,却不敢走近。
院里的楼都重新进行了粉刷,院门口也加设了门卫站岗。
只有那块“南沙沟居民委员会”的牌子依然没变,还是早先的那块。
从这里匆匆经过的人们,他们不会知道,二十年前,一个腼腆的青年壮起胆子敲开了怎样的一扇门啊……(写于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