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户抢劫.docx
《入户抢劫.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入户抢劫.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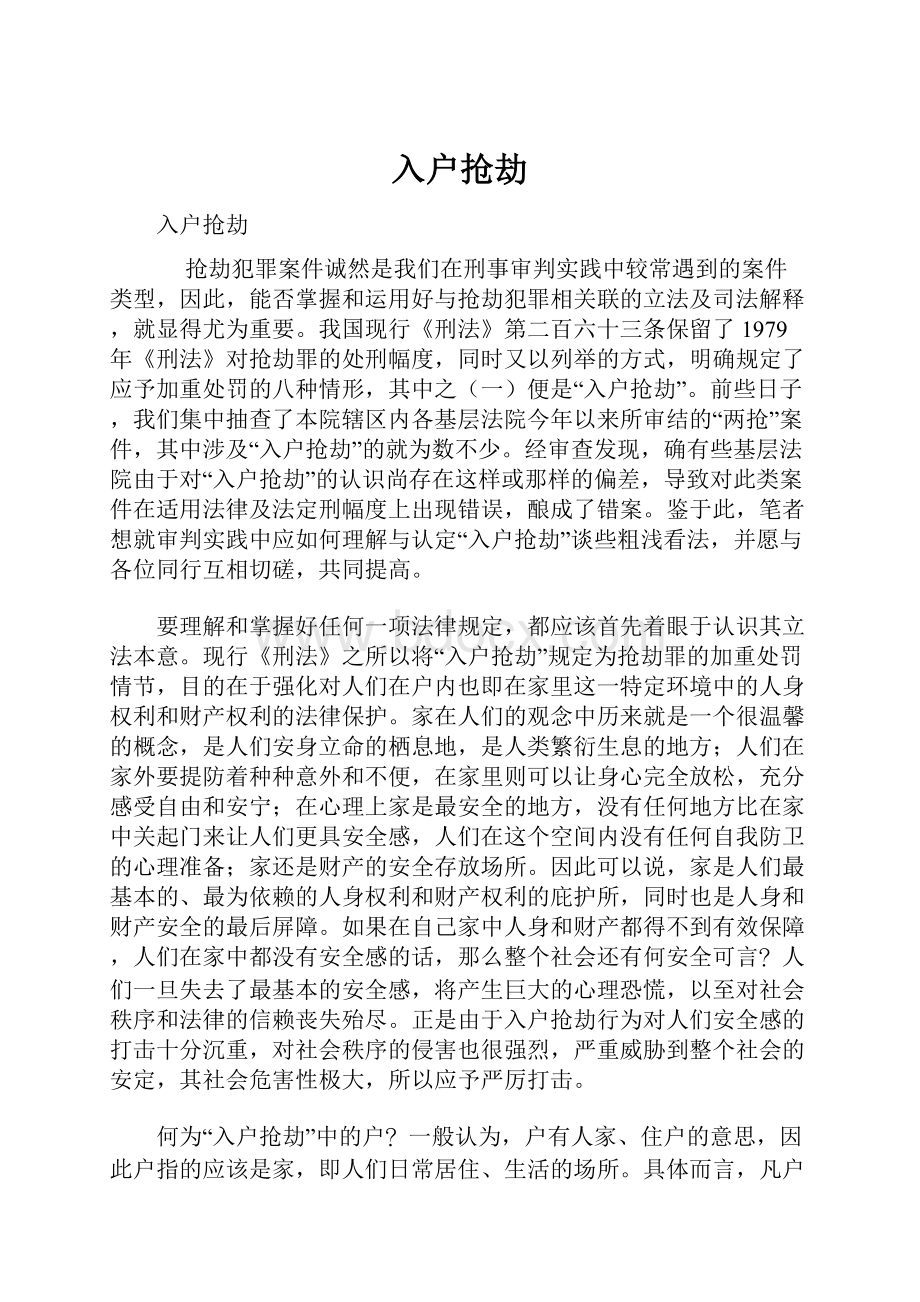
入户抢劫
入户抢劫
抢劫犯罪案件诚然是我们在刑事审判实践中较常遇到的案件类型,因此,能否掌握和运用好与抢劫犯罪相关联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保留了1979年《刑法》对抢劫罪的处刑幅度,同时又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应予加重处罚的八种情形,其中之
(一)便是“入户抢劫”。
前些日子,我们集中抽查了本院辖区内各基层法院今年以来所审结的“两抢”案件,其中涉及“入户抢劫”的就为数不少。
经审查发现,确有些基层法院由于对“入户抢劫”的认识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导致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法律及法定刑幅度上出现错误,酿成了错案。
鉴于此,笔者想就审判实践中应如何理解与认定“入户抢劫”谈些粗浅看法,并愿与各位同行互相切磋,共同提高。
要理解和掌握好任何一项法律规定,都应该首先着眼于认识其立法本意。
现行《刑法》之所以将“入户抢劫”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目的在于强化对人们在户内也即在家里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
家在人们的观念中历来就是一个很温馨的概念,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栖息地,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人们在家外要提防着种种意外和不便,在家里则可以让身心完全放松,充分感受自由和安宁;在心理上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任何地方比在家中关起门来让人们更具安全感,人们在这个空间内没有任何自我防卫的心理准备;家还是财产的安全存放场所。
因此可以说,家是人们最基本的、最为依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同时也是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最后屏障。
如果在自己家中人身和财产都得不到有效保障,人们在家中都没有安全感的话,那么整个社会还有何安全可言﹖人们一旦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将产生巨大的心理恐慌,以至对社会秩序和法律的信赖丧失殆尽。
正是由于入户抢劫行为对人们安全感的打击十分沉重,对社会秩序的侵害也很强烈,严重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其社会危害性极大,所以应予严厉打击。
何为“入户抢劫”中的户﹖一般认为,户有人家、住户的意思,因此户指的应该是家,即人们日常居住、生活的场所。
具体而言,凡户在实质上应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户的功能在于供家庭生活、居住所用,这是户的最基本特征;二是户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场所,人们在户内享有私生活的自由及免受他人干扰和窥视的权利,并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三是户还具有排他性,即人们对户的空间区域拥有占有、使用、支配和自由进出的权利,非经同意他人不得随意出入。
至于户的外在形式则不应受到严格限制,它可以是华丽的别墅,也可以是简陋的茅屋、帐篷。
在掌握户这一概念的外延时,我们应该留意它与室的区别。
室通常指屋子,可以理解为房屋的空间范围,如办公室的公共场所。
而公共场所不具备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属性,因此户与室在实质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新《刑法》的颁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为了纠正各地法院在认定“入户抢劫”问题上出现的偏差,统一认识标准,曾在2000年11月颁发的《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明确指出: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
(一)项规定的‘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
”“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根据上述《解释》,结合我们在审判实践中认定“入户抢劫”尚存在的种种不足,笔者认为应着重掌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入户抢劫”不同于在户内抢劫,它指的是行为人萌生抢劫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在先,继而为使犯罪目的得逞而闯入他人家里实施抢劫的行为,这体现了犯罪的主观与客观要件的统一。
至于行为人是否实现了其犯罪目的,则只是犯罪形态问题,与能否认定“入户抢劫”并无关联。
实践中,有些类似案件的被告人虽实施了在户内抢劫的行为,但其在入户之前主观上并不存在抢劫的犯罪故意,其犯意形成于入户之后。
例如被告人甲某于某日来到其老乡乙某家喝酒,闲谈中甲某得知乙某家中有数千元现金存款,于是顿生抢劫念头。
后甲某趁乙某家人外出之机,以暴力手段将乙某存款劫走。
此案中对甲某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而应作为一般抢劫对待。
当然,如甲某的抢劫数额达到巨大或因抢劫致人重大伤害,则属其他情形中的加重处罚情节。
其二,为了照应《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盗窃罪向抢劫罪转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又阐明:
行为人在入户盗窃时,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需要指出的是,《刑法》关于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与《解释》中的入户盗窃转化为“入户抢劫”,其要求具备的条件是否相等同﹖笔者认为,《刑法》所述盗窃罪与抢劫罪的相互转化,着眼点在于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否一应具备,因此,其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中的“当场”,既可以是实施盗窃行为的场所,也可以延伸到行为人实际控制所盗财物之前被追捕过程中的任何处所。
而《解释》中的由入户盗窃转化而成的“入户抢劫”,所强调的乃是一种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因此,对其中的“当场”的外延的理解,就应当比前者更加严格,不得随意扩充。
笔者认为,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发生在户内是认定“入户抢劫”的必备要件,故《解释》中的“当场”只能限定于在户内。
倘若行为人是在被追赶至户外时才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则不应以“入户抢劫”论处。
其三,在集体宿舍、宾馆旅店、临时工棚内实施的抢劫行为可否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认为,上述场所在一般情况下均是用于休息和群体活动的地方,他人可以自由出入,并不具备户的属性中供家庭生活、居住所用及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特征,因此不能以户对待。
当然,在特定情况下以上场所也可能转化成户。
如某人全家都生活和居住在其长期租住的旅店,以此作为家庭居住场所,此处的旅店就具有了家的属性,应以户看待。
其四,当居住场所与生产经营场所混杂时,如何认定“入户抢劫”﹖有人认为生产经营和生活居住合为一体的场所不能认定为户。
笔者认为,对此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应以是否具有家的属性来具体分析。
如果生产经营和生活居住场所确不能明显分开,那么在营业时间内,此类场所中他人可以自由出入,属于开放的公共场所,显然不具备户的特征;而在营业活动停止后,即不允许他人随意进出,此时它就成了单纯的家庭居住生活用房,理应认定为户。
其五,切莫将公民个人生活居住的场所排除在户的范围之外。
现实生活中,户通常表现为由多人组成的家庭,但也有以公民个人构成一户的。
家庭组成成员的多与寡,只是它的外在形式,只要它具备了户的实质属性,就不应被排斥在立法上对其人身和财产权利予以特别保护的户的范围之外。
(谈谈如何理解与认定“入户抢劫”)2/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它不仅侵犯了公私财物的财产权,同时也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被认为是最严重的侵犯财产犯罪,一直列在刑法“侵犯财产罪”这一章的首位。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原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0条规定的抢劫罪使用重刑的情形予以了修订,明确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七)持枪抢劫的;(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入户抢劫”被列在该重刑情形的第一项,足见其重要性。
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正确认定和适用“入户抢劫”这一重刑情形,存在有诸多分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22日制定了《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
《解释》),该《解释》第一条规定: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
(一)项规定的‘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
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该《解释》对“入户抢劫”的含义、“户”的范围及入户盗窃转化为“入户抢劫”的情形予以了明确。
根据这一司法解释的精神,结合有关案例,笔者拟对“入户抢劫”认定和适用中争议较多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地分析探讨,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帮助。
一、除了《解释》列举的四种“户”以外,“户”还包括哪些,其范围如何界定?
案例1
1999年10月至2001年3月,被告人杨某、汪某、张某、余某、常某、周某等二十名被告人单独或分别结伙,多在凌晨零时以后,先后窜至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阳平镇、尹庄镇、故县镇、阳店镇、焦村镇、函谷关镇、程村乡、西阎乡、川口乡及陕西省潼关县城郊乡、太要镇、桐峪镇个人所住的日用小商店、苹果园房子、修车补胎门市、首饰店、旅店、诊所、粮油店、选厂、砖厂、饭店(小餐馆)及个人家庭等处,蹬门入室,持刀、棍、枪等威胁、捆绑并殴打各被害人,共计实施抢劫五十四场,后各被告人相继被抓获。
此案涉及的问题是,各被告人在凌晨零时以后,进入被害人家庭抢劫可以认定为“入户抢劫”;但对于各被告人在凌晨零时以后,进入被害人所住的小商店、苹果园房子、修车补胎门市、首饰店、旅店、诊所、粮油店、选场、砖厂、饭店(小吃店)等处抢劫,能否认定为“入户抢劫”呢?
根据《解释》的精神,“入户抢劫”中的“户”是指住所,即供人们日常居住生活的场所,一般应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私密型”特征,即具有供他人家庭生活的功能特征,是指人们在户内享有私生活的自由和生活上的安宁权,免受他人干扰和窥探。
二是“排他性”特征,即具有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场所特征,是指人们对户内空间区域享有占有、使用、支配、和自由进出的权利,非经他人同意不得随意出入。
本案中的个人家庭,与《解释》中列举的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一样,由于明显具备上述两个特征,因而当然地应认定为“户”。
本案中的修车补胎门市、首饰店、诊所、粮油店及饭店(小餐馆),白天店主在店内搞经营,晚上则在店内居住。
上述场所,在白天是经营场所,他人可以自由出入,此时入内抢劫,显然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但是到了夜晚或其他停止营业时间,经营活动已停止,他人不能随意进入,该场所仅用于居住,由于其具备了私密性与排他性两个特征,已变成“户”,故此时被告人入内抢劫的,则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豫西灵宝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较大,是当地的主产业,而苹果又需要看护且生产周期较长,为了适应这一特点,农民在苹果园内一般都建有小房。
白天农民在苹果园内劳作,晚上则全家在此居住。
在晚上时,苹果园房子实际上已成为农民的居室,已基本具备“户”的两个特征,故我们认为在凌晨零时以后,被告人进入该房内抢劫的,也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厂矿的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的工棚,一般情况下由于不具备“户”的上述两个特征,所以也当然不能认定为“户”,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认定为“户”。
如本案中,各被告人进入砖厂、选厂中看厂工人的房内进行抢劫,由于该房系看场工人长期工作与居住用房,晚上是看厂工人的住室,基本具备“户”的特征,所以被告人夜晚入内抢劫的,我们认为也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本案中,被告人杨某、汪某、张某及商某,当天晚上住进某私人小旅店,第二天凌晨三时许,进入店主夫妇居住的房内进行抢劫,该房系店主夫妇长期居住用房,虽然属于旅店的一部分,但由于有了家居的性质,所以就可视为“户”,被告人的行为,我们认为也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由于“户”不同于“室”,所以我们认为,凡认定为“户”的房屋、窑洞等住所,户的范围当然及于附属于该房屋和窑洞的院落,并不仅限于该房屋与窑洞。
《解释》在列举“户”时之所以用“封闭的院落”而不用其他表述,其用意恐怕就在于此。
二、子女进入父母居室抢劫的,能否认定为“入户抢劫”?
案例2
被告人明某因好吃懒做、乱花钱而与其继父李某关系不和。
1999年5月4日,明某欲去河北打工,向李某要钱,李未给,明某十分恼怒。
次日凌晨一时许,明手持铁棍,翻墙进入李某经营的粮油门市部二楼李的卧室,再次向李要钱,遭到李拒绝,明即用铁棍向李某头部猛击三下,因李欲呼喊,明又用手掐李的颈部,致李昏迷。
明找到李某保险柜的钥匙,将屋内保险柜内的6.3万元现金拿走,后逃至湖北省竹溪县。
李伤后经抢救脱险,经鉴定,李某的伤情为重伤。
此案涉及的问题是明某进入其父母居室抢劫,能否认定为“入户抢劫”?
我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为了保障公民这一宪法权利的实现,维护公民居住生活的自由和安宁,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了非法侵入住宅罪,即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或者未经住宅主人同意,非法进入他人住宅的,或者虽经主人同意进入,但在主人要求其退出时,拒不退出的,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入户抢劫”犯罪,客观方面首先表现为行为人采取非法手段强行入户,或者利用被害人的邀请与信任以抢劫为目的入户。
非法强行入户抢劫的,“入户”是手段,“抢劫”是目的,行为人的行为属于牵连犯罪,既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又构成抢劫罪,按照刑法的一般原理应从一重罪处罚,即按抢劫罪从重处罚;利用被害人的邀请与信任为抢劫而入户的,行为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但却具有非法抢劫的动机与目的,所以构成“入户抢劫”的前提,是被告人的行为首先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或者具有非法抢劫的动机与目的,简言之,“入户”行为必须具有非法性。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成年人,在晚上12点钟以前,未持有凶器进入父母房间抢劫的,一般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因为未成年人、未分家另过的成年人与其父母属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根据我国的国情,按照一般的常理,其进入父母的房间都是正常的,故很难准确认定其入户就是为了非法抢劫。
本案中,被告人明某系成年人,其深夜持棍翻墙进入其继父李某的卧室,从其进入的时间与方式、手持的工具,再结合本案的结果,可以认定明某进入其父母卧室就是为了抢劫,其入户的“非法性”非常明确,所以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明某的行为系“入户抢劫”是正确的。
总之,我们认为,对于子女进入父母房间抢劫的,是否具有入户的非法性,进而是否构成“入户抢劫”,应从子女的年龄、与父母是否分家另过、进入房间的时间与方式、是否持有凶器等方面,同时结合案件的结果,予以区别认定,不能一概而论。
三、行为人在户外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但在户内取得财物的,能否认定为“入户抢劫”?
案例3
被告人雷某与被害人李某相识,曾是朋友。
2001年8月22日晚9时许,被告人因无钱吸毒,想以借钱为名找李某要钱,而将自己的一只手缠上纱布,并在纱布上涂抹红药水,伪装已杀了人并且负伤流血的假象,携带一把水果刀藏于腰部,到被害人李某家敲门。
当时李与其父母在家,李的父亲开门后,雷某进屋,向李某提出“借”钱。
李某以没钱相拒绝,并要雷某出去。
雷、李二人来到室外,雷再向李提出“借”钱,李仍不答应。
雷便露出水果刀,并以“已经杀了人,不怕再杀第二个人”相威胁,李某被迫答应向其父母借钱给雷,雷即随李某走进李家,李让其母亲王某给雷某200元钱。
王坚持让雷写借条,雷便用假名“雷志民”写了一张借条后离去。
此案涉及的问题是,被告人雷某在户内取得财物,但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发生在户外的,是否属于“入户抢劫”?
根据《解释》的精神,“入户抢劫”的,行为人的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必须发生在户内。
入户盗窃被发现,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如果该行为发生在户内的,可以认定“入户抢劫”;反之,则不能定为“入户抢劫”。
所以行为人在户外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但在户内取得财物的,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
本案中,被告人雷某携带凶器进入他人住宅,伪装凶相以暴力威胁被害人,并当场取得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从主观上讲,雷某具有抢劫的故意,可以认定其为抢劫而入户;但其实施的露刀、扬言杀人等胁迫行为均发生在户外,而不是在李某的住宅内,因此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
四、“入户抢劫”是否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
案例4
2002年11月4日,南某携带三角铁块闯入徐某家,趁徐某不备,用三角形铁块打击徐某后脑部,欲抢徐某所拎包。
徐某被击打后转身训斥南某,并告知其行为是违法的、要坐牢的,南某见状即扔下手中三角形铁块,摸了摸徐某被击中的后脑部,表示不再抢徐某的包,并要求徐某不报案,随后迅即离开徐某家。
徐某当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次日南某被抓获。
经清点,徐某包内共有现金及物品共计人民币4348.13元。
经鉴定,徐某系轻微伤。
此案涉及的问题是,被告人南某入户抢劫的行为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
关于如何确定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问题,法学界和实务界存在有很大争论,大致有四种观点:
1.认为抢劫罪属于侵犯财产罪,应当以是否抢得财物为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对于侵犯人身权的情况可以不论。
2.认为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财产权利,也侵犯了人身权,因此,不论是否抢得了财物,只要在抢劫中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就是抢劫既遂。
3.认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对抢劫罪分两种情形作了规定,实际上是两个犯罪构成,因此应按照两种情形,分别确定既遂与未遂的标准;第二种情形是结果加重犯罪,不存在未遂的问题。
4.认为应当以是否成立结合犯抢劫罪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在没有造成人身伤亡的情况下,不成立结合犯,应当以是否抢得财物为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在造成人身轻伤、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况下,成立结合犯,不存在未遂。
根据抢劫罪侵犯双重客体这一突出特点,依照我国刑法关犯罪预备、未遂与中止的规定,结合《解释》的精神,我们认为: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八种情形,属于结果加重犯罪。
正是由于这八种抢劫情形,与一般抢劫不同,对公民人身、财产有其特殊的社会危害性,所以立法者给其配置了较一般抢劫更重的刑罚,并使其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犯罪构成,这种规定本身较好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立法者的本意就在于强调如果存在这种结果或情节,就应处以重刑,这种结果本身在这里就是一种既存的客观事实,其表现就是一种既遂的状态,因而对“入户抢劫”等八种适用重刑的抢劫行为来说,当然地不能再去谈及其是否存在预备、未遂与中止的问题,“入户抢劫”犯罪不存在未完成形态。
对于入户抢劫,如果行为人仅使用轻微的暴力,没有劫到财物的,可以在法定刑幅度内对行为人从轻处罚,但绝不可在法定刑幅度外,对其减轻处罚。
需要澄清的是,上述“轻微”的入户抢劫,由于与行为人为了抢劫非法侵入了他人的“户”内,构成了对“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这一宪法权利的侵害,严重影响了公民生活的自由和安宁,“家不安全,还有什么地方比家更安全”。
因而这种抢劫,与行为人致人轻伤且劫取财物数额较小的一般抢劫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显然要大,故理应处以较一般抢劫更重的刑罚,这样的处罚才能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这一原则,真正实现罪与刑科学的有机的统一。
本案中,南某在遭到被害人的训斥后,明确表示不再要被害人拎包,还摸了摸被害人被铁块击肿的后脑部,并要求被害人不报案而离开现场。
孤立地看,被告人是在没有外界因素及被害人的明显反抗情况下,主动、彻底地放弃了犯罪,并且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因而应属犯罪中止;但是纵观全案来看,被告人南某为了抢劫而非法入户的行为已经完成,且已在户内为了劫财当场实施了暴力行为,已完全符合入户抢劫的构成要件,“入户抢劫”罪已经构成。
至于被告人南某是否继续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以及是否劫走财物,只是南某“入户抢劫”这种犯罪结果中的两个情节,是对被告人南某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并不对“入户抢劫”这种相对独立的犯罪构成形成实质影响。
结合本案,对被告人南某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死刑之间适用刑罚,并应考虑到被告人南某中途停止犯罪这一情节,可对其从轻予以处罚,但不应对南某按一般意义上的中止犯予以减轻处罚。
被告人南某中途停止犯罪,仅是“入户抢劫”犯罪中的一个从轻情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中止。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构成“入户抢劫”中的“户”有其特定的范围;入户行为必须具有非法性;行为人必须当场在户内实施暴力胁迫行为,这是正确认定和适用“入户抢劫”时必须注意的三个方面。
同时,“入户抢劫”犯罪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犯罪构成,其本身就是一种结果或情节加重犯罪,并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但存在从轻处罚的情节。